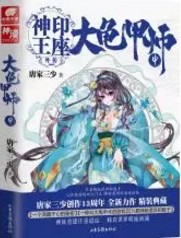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十五章 谋兵(2/3)
的脚步声外,满营静寂。
阮靳正于帐中撰写军文,白鹤慵然趴伏一旁,百无聊赖之下,阖目休憩。
案上烛台明暖,阮靳在融融光晕下落笔最后一个字,正待从头审阅,一旁白鹤忽扑簌翅翼腾地站起,阮靳乍然被惊,手一抖,笔端余墨溅上藤纸,洇成乌黑一团。
阮靳板起脸,训斥白鹤:“鹤老,不要捣乱。
” 白鹤却置若罔闻,兀自兴高采烈地,举翼朝帐帘飞去。
阮靳竖耳,这才听闻帐外有马蹄轻纵的声响,忙起身,掀开帐帘。
帐外来人身影纤瘦,头戴斗笠,背负着一个大包裹。
背着光线,他还未看清来人面容,身旁白鹤却一声清呖,倏然朝那人扑去。
“鹤老,对不住,我现在无手抱你。
”那人微笑轻语,跃下马,取下马背上挂着的另一个硕大包袱,来到阮靳面前,唤道,“姐夫。
” “怎么这么晚来营中?”阮靳笑容温和,看着她手上沉沉拎着的包袱,玩笑道,“难道是要出走?竟带这么大两个包裹?” 夭绍笑而不语,望了眼远处灯火茕然的帅帐。
阮靳了然,道:“阿彦和少卿去了白震泽视察水门,怕还没有回来。
” “白震泽?”夭绍唇角弯了弯,“果然如此。
”她看着阮靳,轻声道:“我找姐夫有事。
” 阮靳打量她颇为慎重的神色,点点头:“入帐说话。
” 外帘挑起,帐内烛色透过薄薄竹幂,一丝丝渗透夜雨。
“这都是些什么?”阮靳扶额,看着夭绍将那个大包袱在案上摊开,无数瓶瓶罐罐叮叮当当滚落出来,另有一堆各色布囊,十数个牛皮水囊,一片琳琅满目。
夭绍俯身拾起掉落在地的瓶罐,并不忙着解释,先问阮靳:“姐夫,北府军陆寨将士近日是否要沿怒江南下?” 阮靳目光倏然一深,声色不动,盯着夭绍:“你听谁说的?” “并非听说,我今日偶过白震泽,看到水上有大批新造的艨艟斗舰,是以斗胆一猜。
”夭绍察言观色,知晓揣度无误,低声问道,“不知大军何日启程?” 阮靳看她良久,摇了摇头,慢慢一笑:“郗元帅不日前下达严命,军中若有私议战事者,格杀勿论。
” “如此……”夭绍一笑,“那便不说战事了。
”她移目一瞥帐外风雨,道,“姐夫通晓天文地理,能观风辨云,知雨识雾。
夭绍想问问,这雨势绵延至此,但若一停,是否将有大雾?” 阮靳望着她,目中颇有赞意,言词却仍谨慎:“青梅熟黄,雨水连绵,江上扶摇风自起,晨间暮晚必有雾气,太阴愈盛时雾气越浓,过两日是五月望日,若雨水能住,怒江或起大雾。
” “我明白了。
”夭绍轻轻点头,又道,“但以今日云翳来看,云层密而乌,风微而凉,雨细而疏,此二日内这雨怕不会停。
” “是啊。
”阮靳慢条斯理地叹了口气,挥了挥羽扇驱走烛火处的飞虫。
夭绍不再询问,说道:“姐夫身为军师,应该能时时随在阿彦身侧,有几件事,夭绍想拜托姐夫。
”她指着包袱里的物事,一一解释道,“这是犀牛皮制成的水囊,甚为坚实,且内有冰玉衬底,不畏火灼,共十五个,皆装上古桃花酿。
阿彦每日服过寒食散后必要温酒行散,行军之际携带酒坛酒壶之物怕是不便,这些水囊倒占不了多大地方,可让他随身带着。
还有这些锦囊,也为十五个,每一袋皆是阿彦一日所服药量,纵是鏖战之际,姐夫也不要忘记提醒他吃药。
” 阮靳微笑:“好。
” 夭绍又指指那些琉璃瓶罐:“前几日听姐夫说过,荆州多为蛮荒野地,闷热潮湿,毒虫毒瘴甚多,北府将士初到怕多有不适,病疫易发。
这些都是茯苓、紫苏、白术、甘草磨成的药末,可治痱毒、苦夏等常见疫患,姐夫随军带上吧。
” 阮靳随手拿起一个药瓶闻了闻,叹道:“这是都是军医该做的,你郡主之尊,何必忙这些。
” 夭绍笑道:“举手之劳而已。
我也知仅这些药末,对两三万大军来说,并不算什么。
只不过我也为东朝子民,此刻如能添一分力,他日你们得胜,我也与有荣焉。
”话尽于此,见帐侧沙漏横线已近戌时三刻,心想不便再久留,起身与阮靳告辞。
离帐时,白鹤拉扯着夭绍的衣袂依依不舍,夭绍看看它,一笑:“你今后跟着他们也是不便,且陪我几日吧。
”遂抱着白鹤,出帐而去。
郗彦与萧少卿至白震泽时,谢粲正驰马于江津高坡上慢慢徘徊。
由午后忙至深夜,平原上所有战舰皆已入水。
白震泽浅滩二十里,艨艟横撞,斗舰攀浪,船舷处无数火把飘飞蜿蜒,夜雨下粼粼然宛如蛟龙夺然出水,翻江倒海,气势慑人。
“元帅,郡王!”谢粲远远望见二人,纵马迎上,对郗彦禀道,“新战船俱已入水试行,斗舰三百艘,艨艟两百艘,三翼船一百艘,楼船八十艘,连舫二十艘,另有海鹘三百,共能乘将士两万余人。
战舰外女墙弩窗等俱以牛皮覆之,另有拍竿一万,皆已安置好。
” 郗彦听罢,微微颔首:“自明日起,你与钟晔领两万陆寨士卒登舟操练,熟悉水情。
扬帆掌揖等事不必求之甚解,仅适应逐浪颠簸即可。
” 谢粲抱揖应下:“是!”拨辔转身,当先而行,引着郗彦二人沿白震泽江岸飞马而过,直朝最西南处的水门而去。
西山延绵至此已无高丘,平原旷荡,四野无声。
江中浪潮起伏,此处水门停泊战船近千,灯火通明,映照着水心天幕,朗朗如昼。
郗彦几人乘小舟前往水寨中军,巡梭江面时,目望楼船林立、无穷无尽,宛若行步于巨大城郭,巷陌毗连无际,难辨身处何境。
帅船上,阮朝早已听闻消息,手扶佩剑,昂然侯于甲板之侧,望见萧少卿跃身上船,放声一笑:“我日日夜夜都在盼郡王来此,今日终于等到了!” 萧少卿笑道:“我来此却是要调用阮将军的精锐去行险事。
旁人避之不及,你倒日日期盼?” 阮朝道:“善战之将,自可立于不败之地。
何况是郡王用兵,计策无穷,奇谋不竭,早已为天下将才共仰。
” 萧少卿再洒脱骄傲,闻言也不免脸上一烧,转目看郗彦:“阮将军这等言词倒是少见。
如此狡猾,想是有人唆使的。
要是我此战不幸算漏一步,岂不愧对了天下?” 郗彦淡淡一笑:“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我知道你必然是不会愧对天下的。
”轻飘飘言罢,提步先入了舱阁。
萧少卿愣了须臾,咬牙失笑,随后走入舱中。
此番密谈不过半个时辰,于殷桓今日之变,三人心照不宣,都已早有预见,所思所图皆不谋而合,因而拟定诸策十分顺利。
出舱时,瞧见船舷处静静等待的谢粲,萧少卿想起一事,对郗彦道:“明日起要调动大批兵马埋伏西山各处险地狭谷,夭绍现居西山中,若被不知事的将士冲撞,倒生事端。
她也只听你的话,过几日你一走,我若去说搬迁诸事,她只会和我吵。
你还是让她尽早回江夏城吧。
” 郗彦闻言微笑:“她何至于你说的那样不懂事?你若好好和她说,她何曾有一次故意惹恼你?” “原来每次都是我惹恼她?”萧少卿眉目间略生异样,侧首望着漫江红火,轻轻道,“令她着恼,我也不想的。
” 郗彦静静注视他一瞬,未有多言。
二人就此沉默下来,登上小舟,原路返回岸上,骑上马背,各自驰回营寨。
回到北府行辕,时已子夜。
郗彦入帅帐时,亲卫跟在他身后,神情忐忑而又微妙,欲言又止。
“何事?”郗彦褪下斗篷,疲惫地叹了口气。
风吹着帐中烛影倏忽一动,不等那侍卫出声,郗彦目光一寒,人影如魅,直飘里帐。
亲卫怔愣,还未反应过来,耳边已听闻里帐传来一人轻呼,异常恼怒地:“郗彦!你做什么!”几声鹤唳也惊叫而起,翅翼扑打的声音更是不住传来。
亲卫自知坏事,喃喃道:“元帅,属下刚刚想说,谢公子来了……” 公子?这声音如此娇柔,分明是女子。
亲卫惶然的瞬间,里帐二人早已镇定下来,唯有鹤鸣仍是不断。
半晌,郗彦一脸无奈之色,拎着一只丰硕的白鹤出来,丢给亲卫,淡淡道:“带它出去吧。
”待亲卫灰溜溜出帐,郗彦在外帐静立了片刻,才再度转入里帐,燃亮了灯烛,垂眸看着案边犹自抚着脖颈喘息不已的少女,歉疚道:“还疼吗?” 夭绍恨恨盯他一眼:“你让我掐了试试。
” 郗彦无言,撩袍在案侧坐下,拉开她的手,看了看那细白肌肤上赫然醒目的五指痕迹,忍不住叹息:“夜深至此,你怎么会来营中?” 夭绍心中原本酝酿了诸般柔情,却在方才那冰凉五指扼上咽喉的一刻尽数消散,此时纵见他恢复了往日的温润柔和,余怒还是未消,因此冷冷道:“我来与你道别。
” “什么?”郗彦一怔。
夭绍抽出被他握在掌心的手,淡淡道:“你不是要出征了吗?我先搬去江夏城云阁住着。
” “如此,”郗彦松口气,并不询问她如何得知出征之事,只微笑道,“我明日遣人送你和丹参、白芷回城中。
” 夭绍却道:“不必,今日下午我已让人将丹参他们送回宋渊大人身边了,明日一早我也自会动身。
郗元帅军务紧要,无须多顾小女子的去留。
” 郗彦听她话语虽冷漠,然行止周全却分明处处顾及自己,唇角不禁一扬,目光又瞥见一侧摆放的包裹,见其中都是他二人在静竺谷换洗的衣物,笑了笑:“原来你连行李都收拾好了?是要连夜回江夏?” “你!”夭绍瞪着他,又恨又气,豁然起身。
“外面雨水未止,路上泥泞难行,”郗彦笑意轻轻,不慌不忙道,“今夜先歇于此处吧。
” 夭绍再瞪他一眼,却望到他温柔的目光,忽然气短,微微垂头,抿着唇不语。
郗彦静望住她浅浅发红的面庞,已知她今夜来意,心头骤有暖流而过,忍不住伸臂将她拉入怀中,柔声道:“帅帐是何等重要的军机之所,常人不可随意进出。
即使是你,也不能任意胡来。
不过方才我是过于紧张了些,误伤了你,是我不对,原谅我吧。
” 夭绍犹豫了一会,终于低声道:“我不怪你。
”转念想想,又很委屈很颓然,“而且如你方才所说,做错事的貌似是我。
” 郗彦微笑,抚了抚她柔顺的乌发,轻声道:“脖上还疼吗?” 夭绍无话可说了,横他一眼,仍是道:“你让我掐掐就知道了。
”话虽如此,她也没有再纠缠,安静依在他胸前。
时已深夜,夭绍这一日劳累甚多,心境一旦平和下来,便觉倦意阵阵袭来,但感困顿纠缠眼皮时,想起一事,忙微微一挣离开他的怀抱,目光不安地,转顾里帐四周:“今夜我睡哪里?” 帐中只有一榻,二人对望一眼,俱有些局促。
郗彦难得地尴尬起来,道:“你先睡吧,我还要看书。
”转身要离开时,衣袖却被人轻轻扯住,他回过头,见到那女子早已绯霞满面。
“你分明也很累了,”夭绍低着头,艰难地道,“我并不介意……” 言至此处,再鼓足勇气,却也说不下去。
郗彦望她须臾,淡淡一笑,转身熄灭烛火。
帐中暗下来的一霎,身后女子明显呼吸一滞。
郗彦也不多言,拉着她径往长榻走去。
感受到掌心所握的手指愈来愈凉,郗彦紧了紧手掌,抱着她躺下,只褪了长靴,并未解衣。
二人静静躺在榻上,彼此呼吸可闻。
郗彦转过头,看着夭绍在黑暗中益发明亮清澈的双眸,于她耳畔轻声一笑:“只是这样陪着我,就很好了。
” 他以唇轻轻吻了吻她柔软的面颊,将她揽在怀中,紧紧地,却不妄动分毫。
温热的气息一缕缕拂过脸庞,夭绍唇角浅浅一弯,终于放松下来。
她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抱住身边的人,慢慢闭上眼眸。
从今往后,无论是什么梦魇,都不能夺去他分毫了。
他并非轻烟,更非鬼魂,如此紧密地拥抱着她,温暖而又安心,真真切切,再非虚幻。
(四)
十三日一早,萧子瑜果然不曾按耐住,冒雨提兵北上,赶往上庸拦截苏汶。殷桓也正于此夜到达怒江前线。
乌林军营一派鼎沸,将士们事前得知消息,一个个摩拳擦掌、持剑挽弓,对着南岸俱是一脸跃跃欲试的兴奋。
士气蓬勃如斯,殷桓却格外冷静,如常巡视过各军操练,而后仍命众将各司其职、按兵不动。
严令之下,诸将不敢抱怨,暗中却是疑窦丛生,私揣元帅行为:整日登高望远,观风察水,俨然沉迷于隽秀山河不能自拔,却将行军部署的筹谋抛之脑后,正是贻误战机。
军中因此渐生怨怼流言,军心已动,诸将不得不帐下请命,殷桓却依然无动于衷地,于高坡上搭建的草棚中静望长天一色,淡言避退之,时候未到。
大利诱于前,殷桓竟能如此沉得住气,大出萧少卿事前预料。
相对彼岸乌林的从容不迫,江夏周遭却颇有些兵荒马乱的意味。
且不说城中贵胄富贾早已逃亡一空,穷苦百姓闭门绝户,城镇空寂,四顾荒芜。
便说城外,铁衣寒光披山遍野,毫无秩序,旗帜胡乱充塞于道,车马任意进出西山,其形其状,难谈一分军纪军容。
萧璋对萧少卿再过信任,却也不免身旁有人谈及城外情形时的长吁短叹,听得多了,也不禁有些坐立不安。
至五月望日,子夜初过,本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城外却骤起乱马嘶吼,声响之巨,扰得全城难安。
萧璋睡眠极浅,骚动尚未延展时便已惊醒,因细闻乱声中并无金鼓之音,这才稍松了一口气,披衣下榻,至外间高楼时,清风拂面,冷雾湿目。
他也才愕然发觉:梅溽风雨至此已成微末之势,远处雾气屯屯漠漠,正充盈无垠乾宇,江面上火束连云,沉沦于岩壑间的战舰一时俱出,黑色的箭楼、赤红的火焰扑洒遍江,浩浩漫漫,蔚为壮观。
“怎么?是要战了?”萧璋有些不确定,“难道是选的今夜?” “看起来应该是。
”主簿宋渊陪行一侧,望了望对岸形势,叹息道,“看来殷桓选的日子也是今夜。
” 远处江水间墨龙搅浪,金鳞滚滚,风头浪尖直扑东北而去。
萧璋皱眉道:“雨刚停,雾气将起,明日正午前必然大雾盈江,并不适合水上作战。
” 宋渊捏着胡须,微笑道:“想来郡王和殷桓都是这么想,皆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以大雾为遮掩,奇袭得逞。
” 萧璋不语,薄唇紧抿,双目注视着江上动态,眉目峥嵘寒烈,却又在漫起的水雾中隐隐添上了几分柔软的担忧。
“既都是这么想,却总有算多算少的时候,”他轻轻叹了口气,望了望夏口火光最为浓烈的营寨处,“雾中作战,这是咫尺之间的战局,一旦落败,便要万劫不复了。
” 宋渊笑道:“王爷也不必太过担心,依我看,小王爷今夜最大的企图,却不是夺得江上大胜。
”他挥挥羽扇驱散夜色下缠绕上来的蚊虫,指着西南一角:“王爷看看那里。
” 萧璋凝目,隐约是白震泽的方向,隐蔽的山岩下,正有暗影顺流漂浮,悠长而又缓慢,夜雾下难辨轮廓。
萧璋先是一愣,继而眸中微动,笑起来:“原来是暗度陈仓。
”目送那条冗长暗影消失夜雾中,他忍不住又轻轻叹了口气:“南下多劫难,又要辛苦那孩子了。
” 宋渊道:“复仇在望,想来他是心甘情愿、万死不辞的。
” 赤水津陆寨此刻已是空营一座,仅数百老弱留守各处辕门哨口。
夭绍自江夏城中赶来,至中军时营中已空无一人,马背上呆愣片刻,念光闪过脑海,忙又拨转马辔,挥鞭直朝南方赶去。
自前日起,她便离开军营回到江夏城中,于官署侍奉萧璋两日,极尽乖巧懂事,萧璋再是铁石心肠,一时却也被她的温顺言行哄得心生柔软,成见皆除不说,更难得地提笔为她写了一封向沈太后陈情的信函。
夭绍原打算北府兵出师时,与郗彦和谢粲道别之后,她便一人先回邺都。
然郗彦从不曾透漏南下的具体时辰,她也不知是今夜兵动,夜间听闻动静赶出城来,急马快鞭,不料还是迟了一步。
纵使雾瘴迷道,马蹄常有踏空的危虞,夭绍也不愿稍作减速。
便是这样的赶路,她驰马至白震泽时,战舰已开赴半数以上。
中军所居楼船已然滑入江水深处,夭绍勒马慢慢徘徊江岸,默望半日,一声叹息。
黯然低头,手臂收拢马缰时触碰到背上木盒,心念一动,忙下了马就地盘膝而坐,将背上古琴取下,放平膝上,微微调拨琴弦,而后凝了凝心神,将内力运于指尖,铮铮弹奏起来。
清越的琴声破出金鼓之响、江浪之急,曲调醇醇烈烈、慷慨恢弘,恰似云雾之上铺泄而下的千丈水瀑,浑厚沉着,溢漫怒江深流。
“阿姐?”琴音骤然入耳,谢粲握着杯盏的手不禁一颤。
楼船舱阁中,灯烛明暄如昼。
诸将本正商议战事,于兵力部署上各有争执,正说得面热耳红之际,不妨有缕缕琴音渗透江风,就这样悠悠缓缓地传入舱中来。
战乱之下丝竹兀起,着实有些诡异。
诸将茫然四顾,但觉这琴声空阔且清澈,自天而下,人间从未听闻,端然是九霄之外的仙乐。
而那弹琴之人必然内力极深,曲音盘旋百里方圆,一转一顿,一扬一挫,无不纤毫必现。
舱中人人心生疑虑,一时难解,只得都朝上首那人望去。
“元帅,你看这……” 光火之间,郗彦着头,神情模糊难辨,然自紧抿的唇角来看,容色略有冷凝,显是心中不豫所致。
问话的将军见他这样的脸色,后半句还不曾说出口,便讪讪咽了回去。
“这是何人奏琴?”北府大将褚绥是个彻头彻尾的粗人,既无赏琴辨音的雅识,更无察言观色的眼力,见众人突然都哑口无声了,忍不住道,“这厮竟敢这样扰乱军心,我且派个人上岸逐走!” “莽夫你敢!”谢粲横目过去,瞪了瞪褚绥,而后视线不经意于郗彦脸上淡淡一顾,冷冷道,“早知于某些人而言,这是对牛弹琴。
亏得她在大雾之下,还这样辛苦地赶来送行!” 褚绥岂知这话中有话,只想论军阶爵位,自己可万不敢忤逆谢粲,惶惶危坐,吞了口唾沫,安静听琴。
至于其他诸将,虽比褚绥明白些,却也不知谢粲怒气何来,面面相觑,再无多言。
“浪击青云阵前曲?”舱中一片沉寂,独阮靳无所顾忌,听了片刻琴声,自榻上直了直身子,微笑道,“此曲倒是与当前景象颇符。
那丫头终于能弹这首战曲了吗?别又是逞强而为,到时又伤了筋脉。
”见谢粲直了眼睛瞧过来,阮靳低低叹息一声,眼角瞥瞥郗彦,脸色微有无奈。
谢粲这才知郗彦冰寒颜色下另有担忧,不由自主地羞惭起来,慢慢低了头,只是饮茶,不再吭声。
岸上琴声仍不绝传来,初始尚有婉约秀丽之音,而后竟愈行愈激荡,一扫浮华往生,音出纤指,却如刀剑一般铿铿然然穿行虚空,恰与远处的厮杀怒吼相映,气韵空旷苍茫,引得听琴诸人皆是难以自抑的心潮澎湃。
谢粲也正觉热血喷薄得激越,然入耳琴声却忽地一滞,再接下去的几个音,破碎疲倦,气力不足。
他面色一变,正待离案出舱,不料有人却比他更快一步,青袍闪过眼前,门扇啪嗒一声,那人悠长的清啸已回荡江面上,穿透雾光水色,直撞人心。
空中的琴音缓缓止住。
收尾之音甚柔,飘行浓雾间,余音刻骨。
江风湿面,郗彦揉着眉,低头笑了笑。
看来在战事之后,他将有二事要做:一则,此后无论行去哪里,何时启程,必要提前告知于她,否则她必然乱来;二则,此女子太过争强好胜,弹奏那首战曲的心法,他得尽快琢磨透彻。
(五)
江边,夭绍慢慢收住内息,轻舒出口气,望着渐去渐远的江中红火,微笑温柔。她收拾起古琴,准备返程回江夏,转过身,入目却见一袭修长锦袍,受江风牵绊,雾气中微微飘卷的衣袂振出一派朦胧金光。
夭绍怔愣当地,看着那人缓步走至面前。
“师父……”夭绍喃喃,乍然相逢,于此地此间,前尘往事携带不解恩怨下意识掠过眼前,一时心中纷乱,喜哀不辨,“你……怎么会来东朝?” 沈少孤在黑暗中微笑:“听说阿彦要报仇了,我是他师父,也因他一族受尽冤屈侮辱,来看看他如何手刃仇人,如何替我翻案,如何平天下民心。
” 夭绍勉强一笑:“师父的话总是这样冠冕堂皇。
天下战火纷飞,如此乱世,你贵为北柔然融王殿下,千里迢迢南下江左,岂能只为观战,而无他求?” 沈少孤笑意微淡,黑暗中的双目略有了几分冷意。
他叹息了一声:“此处也是我的故土,我当年被人嫁祸不得不离去,一别九年,归心似箭。
如今连阿彦都能认祖归宗,我悄悄地回来缅怀一番,又有何不可?” 夭绍微怔,但要言语时,沈少孤环顾天地,轻笑道:“罢了,你不必解释。
想来也知,九年风雨,山川万物都在变,人心又怎能一如既往?今夜你口口声声皆称师父,为师还以为你对我隔阂尽消,但此刻看来,提防之心倒更胜往日了。
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汉人的礼教,原来都是些无稽之谈。
” 夭绍愧疚难安,忙单膝跪在沈少孤面前,低声道:“徒儿不是有意怀疑师父的,只是……”迟疑难语,顿了顿,才道,“当年是师父冒险救了徒儿性命,我却一直错怪师父。
是徒儿有负师父。
” “起来吧。
”沈少孤扶住她的双臂,拉她站起。
夭绍低着头,双颊因心中歉疚而微微发红,如此模样站在他的面前,浑然还是当年那个做错事后不知所措的小女孩。
往日她尴尬时,他可轻言笑语缓解。
如今呢? 沈少孤看着她静柔清美的眉目,久久沉默。
“你并没有做错,如今你我立场有异,心存警惕也是应该。
”沈少孤淡淡一笑,“既是你问,为师本也不该瞒。
”他转过身去,轻声道:“为师南下确有所图,除要带回阿奴儿,另有事找阿彦。
” “找阿彦?”夭绍微有讶异。
“是。
不过来得不巧,今夜才至江夏,却逢如此战事。
”沈少孤遥遥望向江北某处,“我本在夏口一带观摩萧少卿调兵遣将,不料听到有人弹琴,曲音似曾相识,想来是故人,寻来一看,果不其然。
”话语至此,他转过头来,注视着夭绍:“只不过,那战曲虽好,却是某人……你父亲生平得意之作,曲中处处是刁难人的指法和心法。
你内力不够,阅历不足,奏那首战曲除了自损气血筋脉,别无好处。
以后不可再弹。
” “我知道。
”夭绍想起曾有人也这么嘱咐过,垂首微微一笑,“其实若非今日为阿彦送行,我也并不想弹那首曲子。
” “送行……”沈少孤若有所思,“这样的战曲奏出去,必然是大胜而回的预兆吧。
” 他慢慢上前几步,望着漫江战舰,言词深远:“这一去战场,数万男儿,不知有几人想过,胜负只在家国社稷,存亡却是危及自身。
最终又能有几人归呢?” 夭绍诧然望着他:“师父原来也是这样的仁善心地?” “仁善?”沈少孤冷冷一笑,“为将者护家国存亡,为君者立不世功业,为百姓者,经历战火、颠沛流离。
此景此理千古不变,并没有什么值得怜惜同情的。
为师也为他人臣子,战乱当前若不能替君分忧,徒自心存不忍,只能是妇人之仁,必败大局。
” 话毕,他盯着夭绍,目色暗深如渊,唇角却微微扬起:“要说仁善之心,即便是阿彦、阿伊,怕也不曾真正有过。
你难道从不明白?” “我明白。
”夭绍言语艰涩,“不仅他们,我身边的人,也许人人如此。
师父,曾有人告诉我,战争都是无奈,是为护得百姓安居乐业而不得不为的行事。
若一场烽火可平疆土,从此免黎民于战乱,那这场战争,是不是没有错?” “是没什么错,因为战争本就不能简单论以是非,但你见过能鼎定乾坤、再无乱事的战争吗?”沈少孤轻轻一笑,“不过又是谁和你说这样的话?想来必定不是沈太后和谢太傅,这话听着老成,却还是太过意气用事。
殊不知每次引发战火的,从来不是黎民百姓,而是当权者的野心、贵胄之间的矛盾。
百姓只是借口,战前承受恐慌、战中承受离别、战后承受苦难,除此无它。
” “这原来就是所谓的天理公道、泱泱民心?”师徒之间的对答于此瞬间恰如昔日的平和默契,这一刻,夭绍忍不住地对他坦诚倾诉,“若是天下一统,九州山河归于一家,或者纷争战乱就不是这么多了。
先晋立国三百年,毕竟也曾有百年无大战的平静时期,是不是?” 沈少孤大笑不已:“天下一统?”他摇了摇头道:“先晋开国太祖文成武就,既有匡扶社稷之机,又有斡旋天地之手,身旁更有将相之才无数,这样的人,于当世我还不曾遇到过。
” 夭绍静默片刻,低声道:“我却认识这样的一个人。
” 沈少孤看她一眼,不曾多思,冷笑道:“你说独孤尚?” 夭绍不置是否,秀眉轻轻上扬。
江雾蔓延间,但见她眸如浓墨染就,深沉宁静,望着北方的天宇,微微而笑。
沈少孤拂袖身后,哼了一声:“你心中还放不下他?” 夭绍愕然,收回视线,看着沈少孤:“我与他是知音。
”她转过头看着江中另一方向,柔声道,“师父,我和阿彦有婚约,待他此战回来,我就要嫁与他为妻。
”她语中温和平静,虽含几分羞涩,却无露骨缠绵,漫溢眉目间的,只是一生一世的柔软期盼。
“阿彦……”沈少孤不知为何深深叹息起来,“此子虽难得,只是体弱多病,沉疴难愈,又兼命途多有不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当真咬春饼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夜行歌紫微流年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仙君有劫黑猫白袜子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江湖人独孤红
- 虫屋金柜角
- 穿书后我爱上了蹭初恋热度清越流歌
- 射雕英雄传金庸
- 圣武星辰乱世狂刀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仙尊一失忆就变戏精哈哈儿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控制欲叙白瓷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鱼游入海西言
- 学长在上流麟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羞耻狼空
- 离心ABO林光曦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竹木狼马巫哲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嗨,保镖先生棠叶月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追随者疯子毛
- 猪肉铺与小精英沐旖乘舟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不息阿阮有酒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情敌五军
- 大叔,你好大江流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财神在身边金家懒洋洋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如何才能将目标勾引到手南柯良人
- 共同幻想ENERYS
- 新婚ABO白鹿
- 没完晚春寒
- 动物爱人魏丛良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男主今天翻车了吗吐泡泡的红鲤鱼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明明有颜却偏要靠厨艺青渊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