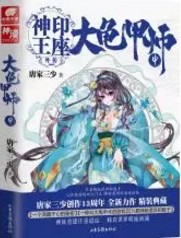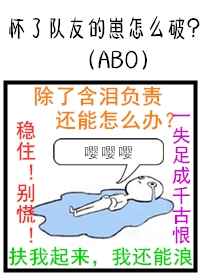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十五章 谋兵(1/3)
(一)
怒江源起蜀西岷山,浊浪滔滔,下夔峡而抵荆楚,江陵为之都会。自战国起,此处便是四战之地,为诸侯所争霸业之资。
前朝晋室一统天下,荆襄十三郡通衢诸州,户别百万,控带梁、益、宁、交、越五州,堪称分陕重镇。
百年前萧氏趁乱而定江左,荆州为国西门,北邻强国,西对劲蜀,苍山茫野间,周旋万里以筑邺都屏障,民风劲悍,士卒尤为善战。
东朝开国太祖帝曾言:荆襄强藩,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匡济一方,为社稷存亡忧地,绝不可轻怠。
因此历代历朝出镇荆州者必为当权者心腹,虽是戎武之地,但最初的藩任刺史却无一不为江左高士。
以文而治虽是断了内患,外患却由此滋生不断,尤以三十年前庆宁帝一朝为最,西蜀与北朝联兵,连夺荆西六郡,兵甲顺流而下,直指邺都。
满朝慌乱,人人怯于自保,而当时出镇豫州的沈弼不过为仕途新秀,却挺身而出,与北府统帅郗珣带甲二十万,截江横陈,血战北朝与西蜀劲卒,免国于危难。
此战胜后,沈弼与郗珣掌权中枢自不必说,而荆州使君之位也自此沦为武者囊中物。
自最初为任的鹰扬将军裴道豁算起来,三十年风云变幻,因朝中势力角逐、派系分明,荆州也非世外之地,藩镇者无一任可逾三年。
而今日的荆州刺史、卫将军殷桓,却显然是这些人中任职最久的。
掐指算算,永贞四年至今,已然九载。
草木再无情,风雨再冷酷,历经九年光阴,对殷桓来说,江陵城里里外外,每一颗人心,每一丝空气,都已烙上了殷氏的刻痕.这里的甲兵精骑,这里的良田沃土,俱是自己辛苦经营所得,绝无他人再可轻言占有。
暮晚细雨霏霏,江陵城长街上人影萧条。
往昔通衢南北的都会,此刻在不远处弥江烽烟的压迫下,早褪去了旧日的浮华与繁盛。
城北贺阳侯府也是池馆静深,数重楼阁掩映在葱郁林木中,风灯摇晃出幽柔的光线,织影迷蒙如画。
殷桓立于府中高阁,看着风雨中隽秀的城池,默然回味过往一切,心底被某种眷恋深沉的情绪堆得满满,曾几何时驰骋沙场不顾一切的果敢与决绝,在这软风凉雨的吹拂下,再一次淡然远去了。
身后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殷桓未曾回头,低声道:“湘儿如何了?” “已经醒了,只是还不肯吃药。
来治的大夫说……”来人声音淡柔,清和中却又透着女子鲜有的刚毅,话至此处,她停顿下来。
“什么?” 女子缓缓透出口气:“大夫说,湘儿又是咳血,又易昏厥,再如此折腾下去,怕是……早夭的迹象。
” 殷桓这才转过头来,看着站在楼梯上的女子,神色怒而悲伤:“她究竟想要如何?” “女儿的心思你真的一点也不知晓?”女子目视殷桓,慢慢问道。
她的容貌不见得多美,然眉眼间却是寻常峨眉难及的英气,虽已入中年,眸光仍黑亮如刀剑一般的爽利,只是此刻看着窗旁那高大威武的男人,目中锋芒却悄然褪尽,似水的温柔中,略有一丝悲沉的无助慢慢浮现。
“阿桓,还是把瑞儿放出来吧。
”她柔声道,“事已至此,如今即便杀了他,也于事无补。
难道非要伤透女儿的心,你才觉得解恨?” “放了他?”殷桓咬牙道,“葫芦谷中百万石的粮草,我费心筹谋了五六年,却被那吃里扒外的混账尽数挪空,不杀他祭旗,何以泄我心头之恨?又何以面对我麾下三十万的将士?” 女子叹息一声:“既是如此,那你便杀了他吧。
”她转身下楼,走了两步,忽又止住,轻声笑了笑:“不过阿桓,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如今困境至此,何尝不是我们当年罪孽的报应?只是这一切本该由我们自己承受,女儿又何其无辜?” 报应?殷桓浑身一震,目色阴厉如惊风刮过山野。
诸般情绪颤抖其中,却不知该怒,还是该哀。
江陵城外三十里,青山绵延,河水碧翠。
天色已晚,河岸上早无行人,渡口也只剩一艘小舟停泊。
一渔夫蓑衣斗笠,自舱中探出身来,往岸上看了看,见山水静寂深深,料想再无渡客前来,正要上岸解开绳索,却忽闻踏踏马蹄响。
数匹骏骑在晦暗的天色中飞驰而至,渔夫望清为首一人的面容,忙敛袖肃立,候在道侧。
“侯爷。
”骏马停在身前,渔夫深揖行礼。
殷桓瞥一眼渔夫:“可曾有人来过?” 渔夫摇首:“不曾。
” 殷桓也不多问,弃马登舟,令他划去对面。
轻舟离岸,在水波中划出一道长弧。
殷桓坐在舱中,不时闻得斜风微雨中几缕清香,转目望了望,方见水中娇荷初绽,青叶蓬蓬。
眼前景致幽美清静,正是属于人间的悠然气息,绝不同前几日在怒江看到的兵戈相持、血红飞浪的炼狱战场。
雨丝飘在眼中蕴成薄薄水雾,想着自己无可奈何从前线回来的缘由,殷桓双眉微皱,唇边笑痕隐隐下沉,昏暗的光线下有种狰狞的凌厉。
“侯爷,到了。
”轻舟稳稳停住,舱外渔夫轻声道。
殷桓起身出舱,站在舟头,若有所思地望着阴郁山岭间那处火光微弱的洞穴。
周遭静得异样,隐约有弓箭搭弦的声响在岩壁暗影间响起。
渔夫沉默着一拂衣袖,那股在草木间飘荡的杀气霎时停顿下来,继而无声无息消没在夜色深处。
“侯爷,请吧。
”渔夫躬身引路。
殷桓走入山洞,瞥目两侧:“都退下。
” “是。
”渔夫招了招手,守在洞穴两边的士兵迅疾退出,仅留独坐在洞中深处,那位落魄憔悴的年轻男子。
男子面壁而坐,听闻动静,缓缓转过头来。
石洞中不知何处穿风,吹得那一点灯火不断飘摇,照着男子血痂凝结的左目,十分悚然。
殷桓静静望着他,男子唇角含着几许淡淡的笑意,站起身,手腕处铁锁沉沉作响。
他看着殷桓,未眇的右目在火光下透着幽幽的光芒,低了低头,声音和润如初:“韩瑞见过贺阳侯。
” 殷桓在案旁坐下,不动声色道:“如今连二伯也不叫一声了?” “二伯?”韩瑞一笑,“鄙人身为犯臣之子、阶下之囚,岂敢冒犯贺阳侯?” “好个犯臣之子!”殷桓冷笑,盯着他惨白的面容,“让你静居此处反思,已逾一月,如今看来,你却无半分清明,还是死不悔改?” 韩瑞微笑道:“侯爷此话差矣,我自始至终神思清明,需要悔改什么?” 殷桓并无耐心与他言词争辩,拍案而起,抡起手掌重重霍上他的面颊。
韩瑞内力尽失,身形孱弱,纵是殷桓此掌未曾使出三分劲道,却也让他脚下踉跄欲跌,不得不扶住石壁,勉强稳住身形。
打得好。
他越是如此,自己心底那一缕似有似无的愧疚才可越发消淡。
韩瑞轻笑,伸手抹去唇角血迹。
“你现在想着与我划清界限?晚了!”殷桓何尝不知他所想,怒喝道,“我早就说过,我殷桓纵负了这天下,也不曾负你!这天下谁都可以叛我逆我,唯你不行!” 韩瑞平静地看着他,笑颜清淡依旧,只右目愈见沉静深暗,一抹哀色浸沉在彻骨仇恨中,郁郁难散。
殷桓厉声道:“九年前我带你到荆州时,你怎么不记得你是犯臣之子?我将湘儿许配给你时,你怎么不记得你是犯臣之子?我养你教你,视你如子,你一身的武功、一身的才学,哪一分不是出自我殷桓?我待你一片诚心,而你呢?原来自始至终都当我是杀父仇人!毁我军机,阻我大事,为他人细作,竟如此狼心狗肺!” “狼心狗肺?”韩瑞沉默了良久,终于笑起来,“二伯,你虽教我许多,可独缺仁义二字。
狼心狗肺,怕也是避不可免的吧。
”他轻叹,眸波轻动,愁苦褪去,换之少见的讥讽之色:“当年二伯背叛郗峤之元帅,不知可曾想起狼心狗肺四字……” 话音未落,殷桓的掌风已袭至他的胸口。
雄霸的内力似要摧毁五脏六腑,韩瑞眼前昏黑,身子飘飞出去,落于数丈外。
看着沉步走近的殷桓,他张了张口,想说什么,不料却吐出一大口鲜血,气息虚弱如丝。
殷桓看着地上的血迹,也不曾想伤他如此,愣了一愣,俯身下来。
“瑞儿。
”他瞳孔一缩,目中隐有痛苦和懊悔之色。
不,不要这样。
韩瑞微微一退避开他伸来的手掌,低低道:“你杀了我吧。
当初你救了我,如今我背叛了你,杀我,也是应该。
” “死就能了结一切恩怨?”殷桓冷冷看着他,“我若真要杀你,当初你给郗彦通风报信时便早已死了!还能等着你毁我粮草?”他沉吸一口气,轻轻发笑:“你当真以为你的命是如何了得,一死就能抵偿所有?即便你父亲当初被害有我之过,我对你九年悉心抚育,也算是弥补他了吧?即便你今日一命还我,你我之间或就此恩怨两清了,那么湘儿呢?你欠她的又该如何还!” 韩瑞发怔,死灰一般的右目似被强光刺入,不堪一击地,放任悲伤之意溢满眸中。
殷桓恨道:“你若真拿我当杀父仇人,就不该靠近她,更不该招惹她!” “我……”韩瑞面容发青,颤抖着唇,在锥心刺骨的痛楚下,无言以对。
上天从未给过他选择或者逃避的机会,于此事上,他也从无一刻能够想明白,既是那样生死不容的仇恨,又为何能生出那样欲断不断的爱意? 石洞中沉寂良久,殷桓耐心等着韩瑞急促的呼吸渐转沉缓,冷冷问道:“上个月湘儿曾带人来想救你出去,你知道吗?” 韩瑞沉默,半晌才道:“她……那一夜似乎受了伤,伤势如何了?” “放心,还没死,不过也快了。
”殷桓言词利落,欣赏着韩瑞一霎僵直的目光,心头略生快意,“她是为你才病入膏肓,如今甚至还拿这剩下的半条命威胁我,让我放你出去。
”殷桓目色有过片刻苍凉,轻声道:“她待你情深如此,你们也有夫妻之名,你扪心自问,如今你真能与殷氏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吗?” 韩瑞不语,胸口窒闷却再度逼入喉中,低头,忍不住又吐出一口血来。
殷桓却如释重负般站起身:“话尽于此,你私藏我百万石的粮草,如今该告诉我囤于何地了吧?” 韩瑞闻言,抚着胸口,虽喘息不住,却仍放声笑起来。
殷桓冷冷看着他,韩瑞笑过良久,筋疲力尽,仰卧地上,凝望着暗沉沉的洞穴顶端,缓声道:“我不曾骗你,那百万石粮草,三个月前就已付之一炬了。
” “畜生!”殷桓忿然瞠目,拎起他的衣襟,一时杀意横生。
韩瑞笑了笑,轻轻闭上右眸,神情极度平和,慢慢开口道:“不过我有一计,可助二伯再得一月粮饷。
若我猜测不错,只要熬过这个月,怒江于梅雨之季水势激涨,二伯控制上游,迟早可长驱东进,剑指邺都,是不是?” 殷桓不语,手指却缓缓松开,居高临下望着躺在地上的气若游丝的韩瑞,目中再无分毫温度,一字一字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 翌日清晨,江陵一带飞雨未歇,水珠哗然有转盛之势。
天色微微亮时,殷桓亲信副将苏汶在官署接到前线战报,想着自己也有事与殷桓商议,便亲自来了趟贺阳侯府。
刚至侯府偏门下马,一辆马车忽自西侧急速驶来,溅得他一身污水。
苏汶正要喝骂,却见那马车也在偏门前停下,车门打开,一着淡蓝长袍、面容清瘦的年轻男子走下车来,在轩昂的府邸前静立片刻,慢慢踏上石阶。
苏汶望见来人的面容,心中虽惊疑,但也不敢慢待,堆起满脸笑意,揖手行礼:“韩公子回府了。
” 韩瑞点了点头,并不与他寒暄,只轻声询问府中迎来的家老:“湘君在何处?” “凤鸣轩,韩公子快去看看吧,唉……”家老不住叹息,递给他一柄竹伞。
韩瑞执过伞,衣袂携风,直往内庭。
苏汶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想了顷刻,方整了整衣冠,由家老引去书房见殷桓。
殷桓正在檐下行气练功,淅沥雨水将满庭花草湿润得清澈,映衬着殷桓的面容,也显出不同往日的爽朗精神。
苏汶笑道:“侯爷气色不错,想来昨夜睡得很好。
” 殷桓缓缓收了内力,神清气闲:“在江陵可听不到百里外的兵戈争伐,一入夜满城清静,如何睡不好?”他接过侍女递来的丝帕擦了擦脸,目光一转,看着苏汶手里捏着的战报,“说吧,前线是吃了败仗,还是小胜?” 苏汶强颜笑道:“为何就不能是大胜?” “此时正是他们滋扰生事、让我不得安宁的时候,即使战,意也不在胜败,而是不能让乌林众军休养生息。
”殷桓目光犀利,一瞥苏汶的脸色,冷道,“败了?” “是,”苏汶将战报递上去,低声道,“小败。
五月初九,萧少卿趁江上雾起,率兵绕过乌林水寨夜袭汉阳,军中防备不及,死了三千,伤近五千。
” “这还是小败?”殷桓笑了笑,却无怒意,目中不掩赞赏,“萧少卿……此子确是天生将才,奇谋诡计用之不竭,百年难得一遇。
可惜……” 可惜如此俊秀人才,却等不到他人生鼎盛之时。
不出数月,迟早会败于我手。
殷桓将战报掷回给苏汶,言道:“传命前线,诸军厉兵秣马,坚守不战。
以一万水师掩江佯动,足以应付对岸的骚扰。
” “是,”苏汶跟在殷桓身后步入书房,轻声道,“还有粮草一事。
前往南蜀和交越的使者昨夜都已回来了。
南蜀自顾不暇,交越则称刚与东朝定下盟约,于支援粮草之事上爱莫能助。
我另求人外购粮草,但天下货殖皆由云阁把持,富商大贾俱恐市廛骤变,祸及自己,无人敢贩粟至荆州。
此前前线粮草再度告急,我算了算,荆州各处囤粮,恐怕支撑不过半月……” 以往每每提及总让殷桓头疼的粮草一事,今日再闻,却不能损及他半分心情。
他坐于书案后,看着案上地图,沉思半晌,忽而一笑。
苏汶只觉这笑容实在来得诡异,忍不住道:“侯爷?” 殷桓扬手止住他的疑问,道:“你带江陵守军两万精兵,挂豫州军旗帜,即日启程,去上庸关取粮草。
” “何处?”苏汶骤闻地名,愕然一愣。
“上庸!”殷桓笑意深远,手按北朝南疆,“中原早已大乱,北帝眼中只有西北,无暇兼顾南疆诸州。
上庸关以往为防东朝战事,囤粮上千万石,足以应付我荆州军数年所需了。
那里守兵不足两千,梁州府兵如今也已尽去中原战场,你取上庸关,如探囊取物。
至于挂豫州军的旗帜——” 他话语蓦地一止,苏汶却很明白,道:“是要嫁祸萧子瑜,并使两朝生隙?” “也不尽然。
”殷桓摇头,慢慢道,“据邺都谍报,如今苻子徵周旋朝中诸臣之间,正是北帝有求于东朝的时候,何况萧璋有云阁鼎助,并不缺粮草,这等劣拙伎俩,瞒不过两朝那些火眼金睛的老狐狸,矛头迟早还是对向我们。
” 苏汶不解道:“依侯爷的意思,如此假以豫州军名义行事,不是多此一举?” “当然不!”殷桓断然道,“北帝纵使恼怒,一时鞭长莫及,只能忍耐不发。
只不过在怒江对面,有一人却绝不能容忍被人嫁祸的恶气,以他莽撞暴躁的脾性,听说此消息必然北上阻你南归,断我粮道。
” 苏汶心知肚明,殷桓所说之人定是萧子瑜无疑。
只是粮草若被截,此行又有何意义?苏汶思量片刻,垂首抱揖:“属下糊涂,还请侯爷明示。
” 殷桓指尖游移战图上,言道:“你即刻出发至上庸,夺得粮草后,谴五千精兵快马送回江陵,再率剩余人马,绕道新城另择南下道路。
若我所料不错,萧子瑜北上的路线定是沿襄江直奔樊城,你于荆山设下埋伏,以逸待劳,必能大败豫州军。
” 苏汶闻言连连颔首,奉承道:“侯爷果然妙计,萧子瑜如一怒北上,石阳防线定然中空,却是侯爷乘虚东进的机遇到了。
” 殷桓冷笑道:“这条妙计可不是本侯想的。
”他抬起头,目望窗外,面容残忍,话语却无尽慈蔼地:“有人给我献了这条瓮中成鳖计策,那我便如他所愿,将计就计,看看天遂谁愿!” 苏汶感受到此话下的刻骨恨意,不免怔了怔。
风吹窗棂,一阵湿寒猛地扑入室中,苏汶在乍然一现的念光中恍悟过来时,那缕湿凉之气正透心渗骨地绕身而至,令他不由自主地、冷然一个寒噤。
(二)
江陵雨水不绝,千里之外,怒江亦于乌沉沉云翳的遮蔽下,接连八九日未逢晴光。这日暮晚,天色渐暗,西山峰影沉沉,雨雾笼罩的怒江上空,有雪白鸽影飘飞而过,扑簌翅翼,掠入梁甍起伏的江夏城。
城中官署内庭,琴声缕缕弥漫池馆间,冲和温雅,令人闻之心宁。
书房内,萧少卿却不知何故被这琴声搅得心起纷乱,在侍女入室送茶汤时,嘱咐她道:“去告诉苏琰大人,她肋下伤未痊愈,夜间风雨甚凉,亭中长久抚琴怕是不利养伤,让她早些回阁休息。
” “是。
”侍女应声离开。
萧少卿才要定下心继续批阅文书,魏让却大步而至,呈上一卷丝绡:“是江陵来的密函。
” “江陵?”萧少卿忙接过密函,于灯下阅罢,叹息着揉了揉额。
“我儿为何事困恼?”萧璋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外,含笑步入书房。
魏让揖了一礼,退出室外,将门扇轻轻关闭。
萧少卿待萧璋落座,方将密函递上:“江陵细作探报,五月十一日,殷桓令苏汶引兵北上,欲夺上庸关粮草。
” “上庸?”萧璋不解,“殷桓疯了不成,如今还敢招惹北朝?” “并非如此简单。
”萧少卿道,“殷桓令苏汶所部皆着豫州军甲衣,沿途所执也尽是汝阳王旗帜。
” 萧璋恍悟,怒道:“这是要嫁祸子瑜?”见萧少卿欲言又止地望过来,萧璋一怔,勉强静下心看罢密函,转念思了思,咬牙切齿道:“好个殷桓,只怕是要借此激得子瑜率兵北上,他才可趁机攻打石阳!” 萧少卿道:“殷桓图谋想必确是如此。
” 萧璋摇头苦笑:“难怪十余年前他们能结拜兄弟,殷桓对他这个四弟倒是了如指掌,子瑜性情耿直,目中无尘,这口冤气定然咽不下。
他若要领兵去截苏汶,谁能阻止得了?” 萧少卿略微思忖,道:“那就让小叔叔率兵北上。
” 此话一出,萧璋当即皱眉。
萧少卿解释道:“我们若无任何行动,那是放任殷桓自上庸夺千万石粮草。
如今怒江北岸荆州军不下三十万,我们三州府兵统共不过十六万,勉强守住江夏三处浅滩,与他拼的便是粮草军饷。
如今他粮草短缺捉襟见肘,我军却可以逸待劳,拖敌疲惫,从而才有胜算。
” 萧璋沉吟道:“话是如此,但石阳距离上庸千里迢迢,子瑜纵是即刻北上,也不一定能拦截住粮草,反而却让石阳防线就此空虚。
” “父王顾虑得当。
”萧少卿从容一笑,扬眸看向墙壁上的战图,指了指江陵方向,“但倘若我军能在十日内夺下江陵城呢?苏汶即便是夺回了粮草,也无粮道可援殷桓。
” 萧璋深看他一眼:“十日内夺江陵?是否太过异想天开了些。
” “不然。
”萧少卿摇头道,“殷桓此举看似高明,实则遗患重重。
苏汶率两万精兵北上,上庸距离江陵并不近,这一趟来回,不出半月怕难回来。
再倘若上庸关的守兵强硬一些,苏汶的返程就更难预料了。
” 萧璋点点头:“继续说。
” “前段日子苻子徵来江夏,阿彦向他购买了八千战马,由苻氏部曲两千人护送战马南下,想必此刻也该到达了上庸附近。
四日前,阿彦也已另谴三千人北上接应。
苏汶如今面对的上庸关,是原有的两千劲卒并两千苻氏部曲,另还有北府军三千人断后,此一战能轻易得手吗?” 萧璋唇边露出笑意,目中也逐渐明朗:“天下岂有这般巧合之事?想来江陵这番动静,原是有人布的局,正请殷桓入瓮。
” 萧少卿眸波轻动,微微一笑,也不置是否,又道:“小叔叔若在此刻引兵北上,襄江沿岸的荆州守军必然全神戒备,如此正可牵制住殷桓在沔阳、华容的精锐骑兵。
依眼下局势,殷桓既要防豫州铁甲,又要集乌林、汉阳的水师趁机攻占石阳,南边洞庭一带的部署怕是再无法固若金汤。
”说着请示萧璋,“父王,我们但可让小叔叔的豫州军在北线沿襄江佯动,而后再谴一支奇兵自巴陵攻入洞庭,趁敌不备,火速沿江西进,直夺江陵城。
只要谋划周全,十日内江陵必失,这也并非异样天开的事。
” 萧璋望他一眼,满目赞赏:“不错。
” 萧少卿接着道:“江陵若失,荆州大乱,即便苏汶夺了粮草,返回也是待屠之物。
殷桓到时也只有两个选择:一则回救江陵;一则与我军血战,在怒江南岸杀出一条活路。
但无论那一条路,我军却是以静制动。
若各路部署得当,到时必成四面合围之势,殷桓将无路可逃。
” 萧璋听到此刻却摇了摇头:“计策虽好,只是用兵之法,十倍方围之。
我军如今以寡敌众,如何能成合围之势?” 萧少卿微微一笑,清透的墨瞳间忽有冷锋浮现,缓缓道:“先贤曾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如今殷桓是有二十五万人马,但到合围之时,能剩五万人马便算天幸于他!” 此番话如冰水缓流,在这般宁静的雨夜慢慢道出,宛若是一把寒剑凌厉游走绵湿雨雾间,果敢决断,锋芒四溅,那样的锐气傲然夺目,令人凛然生畏。
萧璋沉默起来,目光细细流顾萧少卿的面容,感慨叹息:这便是我调教出来的儿子,排兵布阵比之当初的郗峤之,亦不逊色半分,确是世上绝伦——心头欣慰极甚,却又微微含酸。
他站起身,拍了拍萧少卿的肩:“五月以来雨水连绵不绝,怒江水线日益升涨,荆州军居上游,扬帆下驶,十分便速;我们居下游,逆流仰争,形势本就不利,如今殷桓既有所动,你们也有良策,便放手一战。
朝廷前日也已下促战旨意,后方粮草战马俱已筹备妥当,你们不必再顾虑其他。
” 萧少卿颔首微笑:“多谢父王。
” 送走萧璋,萧少卿望望天色,黑夜已降。
满庭静寂,水轩中琴声不知何时已然停止,耳中唯闻得雨水打叶声淅沥不绝。
他看了看轩中,那雪衣飘然的女子依然静坐原处,背对着他,面朝轩外水色,动也不动。
“苏大人,”萧少卿步入轩中,眸中湛湛清朗,看向苏琰,“还未歇息?” 轩中风灯微摇,苏琰手执茶盏轻轻抿着,细眉明眸,秀颜如画,看他一眼,声色不动:“方才郡王嫌琴吵,我已不弹了。
此刻难道是嫌我坐在这边也碍眼,过来逐我?” 她言词冷漠,话锋迫人,端然是拒人千里之外。
萧少卿习以为常,并不介怀,笑道:“方才是我扰了你抚琴的雅兴,别生气。
”他撩袍坐在栏杆旁,似随意问道:“你肋下伤如何了?” 苏琰垂目:“早不疼了,有劳郡王垂询。
” “那就好。
”萧少卿微笑,就此止了言词,不再言语。
沉寂良久,苏琰终于放下茶盏,自嘲一笑:“郡王行事如风,从不会浪费时间与我这般静坐。
有事请说。
” “知我者唯有阿荻。
”萧少卿剑眉微扬,轻声笑道。
苏琰目光一闪,凝目端详他须臾,摇头叹气:“郡王但凡露出这样的神色时,必有所求。
只是苏某且将话先撂于此处,鉴于一年前曾在某人帐下被驱逐的经历,苏某已发过誓,今后再不入军营,再不为人军师,再不去战场无情地。
” 萧少卿噎住,无奈道:“阿荻。
” 苏琰眸光流转,盎然生辉,眉梢添上几缕温和之色,柔声道:“除此之外,其他事郡王但言无妨。
” “你明知道我有何事求你。
”萧少卿轻轻揉额,甚是疲惫的模样,“再帮我一次,去石阳豫州军营,暂领一月军师,如何?” 苏琰无动于衷,笑道:“苏某才疏学浅,恐难胜任。
” 萧少卿道:“若非事关紧要,你尚在孝中,我也不会强求于你。
但如今殷桓打着豫州军旗帜去夺北朝粮草,小叔叔必然怒而发兵相截。
他若沿襄江北上,石阳水寨便由此空虚,我虽另有计谋,但三日内三军水寨却必须坚守不动,豫州军前锋颜谟想必是留守石阳的。
你与他一文一武,行事正为互补。
有你二人守着石阳,我才能放心在江夏与赤水津调动兵马。
” 他言词顿了顿,静静注视苏琰:“阿荻,如今除你之外,我别无他人能托付。
” 苏琰神色冷淡,沉默半晌,抱着琴站起身。
“苏大人!”萧少卿振袍而起,拦在她身前。
“你方才不是还顾及我的伤势吗?怎么现在又让我去前线?”苏琰盯着他,面孔微微发白,“我原来真的只是郡王麾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小官吏?” 萧少卿看着她一贯沉静的目光骤然如此咄咄逼人,怔忡之下,恍惚明白出什么,不由一惊。
他缓缓避开她的视线,轻声道:“既如此,你在江夏歇着,我让宋叔去石阳。
” “宋叔已是老朽,且有风湿旧疾,如此雨季,不堪长途跋涉。
”苏琰冷冷出声,“你放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方才是苏某莽撞了,郡王请勿介怀。
我明日一早去石阳,不会负郡王军命。
”衣袂倏然一转,人已飘然离去。
萧少卿望着那缕雪衣消失在夜色深处,虽有过一刻的悔意,却也未曾过多踟蹰,至书房唤过魏让,二人连夜纵驰出了江夏城,直奔赤水津方向。
(三)
已是戌时,夜色深浓。赤水津中军行辕内篝火飘动,如丝细雨中,红光映染半边天际。
此刻早已到了诸军入帐而眠的时辰,除了巡逻甲士岿然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当真咬春饼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咸鱼飞升重关暗度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春日颂小红杏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末世对我下手了一把杀猪刀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虫屋金柜角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重生女配之鬼修雅伽莎
- 流氓老师夜独醉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真爱没有尽头科林·胡佛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纨绔心很累七杯酒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持续高热ABO空菊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单恋画格烈冶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网恋同桌归荼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宠夫日常[娱乐圈]阿栖栖
- 秃头之后,我在前男友面前变强了鱼片面包
- 听说我很穷[娱乐圈]苏景闲
- 被影帝碰瓷后[娱乐圈]唤舟
- 媳妇与枪初禾
- 金枷马鹿君
- 我和死敌的粮真香青端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球”嗨夕尧未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财神在身边金家懒洋洋
- 离心ABO林光曦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老大,你情敌杀上门了沐沐不是王子
- 他们今天也没离婚廿乱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独立日学习计划一碗月光
- 竹木狼马巫哲
- 校服绅士曲小蛐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