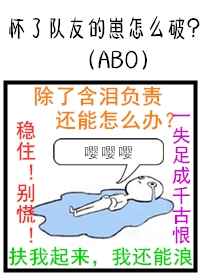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俱邀侠客芙蓉剑(2/3)
一只被猎杀的野兔一样,声音,表情,全都冻住了,好像吞下了一块冰,爆裂了,从喉咙里发出声嘶力竭的大喊。
我不敢出去,只能听着他凄惨叫喊的声音回荡在四面八方,好像一列在夜里高速行驶的火车,轰隆隆地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
他求饶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怀疑他的脊椎断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音乐一直没有停。
我把即将爆发的喊声往胸腔里压下去,挤进心脏,高大的树木哗哗直响。
这里真他妈安全,没一个人能发现我。
我站不起来,用手狠狠地捶着树干,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狂乱的挣扎,然后啪的一声巨响,彻底炸开了。
像核弹爆炸一样,炸碎了几百万平方公里所有的灵魂。
该死的黑人还在唱着歌。
Johnnymyfriend,isnotwhatitseems. 这些日子,我经常这样从梦里醒来。
我一直梦见我在打人机,不断地被人机击杀。
这梦总是在每个发生大事的夜晚和我重逢。
每次醒过来都觉得呼吸困难,喉咙里梗着一块冰,连隔夜的烟草味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都会去冰箱里拿一罐可乐,无数的气泡在我舌尖破灭,仿佛劫后余生。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对面的电脑,是未来战士伊泽瑞尔。
他在我的尸体前面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跳舞。
他面前的屏幕蓝莹莹一片。
召唤师峡谷一片死寂。
我猛然想起简意澄最喜欢的就是EZ,他们这些飘逸狗都喜欢用这个。
送几十个人头,喷人喷得飞起,偶尔杀了人,兴高采烈地站在尸体前跳舞。
我跳起来,抹了一把脸,发现脸上全是眼泪。
我怀疑简意澄死了,开始疯狂地拨打他的电话,已经变成空号,短暂而空旷的滴滴声,好像时间一下子过了许多年。
夏蝉永无止境的鸣叫,窗外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
这个世界都死了。
我又打了几个电话,有的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
深夜里电话那头响起世界各地带着金属音色的英语,广东女人,印度男人。
我开始怀疑他们在多年前也早已死去。
就在这个时候,我猛然想起其中一个黑人,他一口不标准的英语,大喊大叫,我只能听清楚几个骂人的词。
这些陈年累月的细节好像投进水里的鱼雷一样,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在五脏六腑里炸出一片水花。
那是个广东人。
老天和我开了个该死的玩笑,那是和徐庆春他们一起玩儿的广东人。
【林家鸿】,2015
顾惊云的葬礼在西雅图的市区里举行,下着雨,天气阴凉。凯莱的所有学生和老师几乎都参加了,我也看到了他的家人。
只有爸爸,和他长得很像——我是说他如果能活到那时候,大概就是那副样子。
啤酒肚,满身都是从铺着油花花的桌布的小饭馆里刚走出来的味道,眼睛里装满平静的放弃。
教堂的穹顶很高。
牧师在台上致辞。
后来我想到这个情景,总觉得他的死亡清静而辽远,好过必须行走在大地上漫长而苦难的一生。
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他的偏见。
后来我见过很多死人,村庄的医院里,屋前地头,拆迁工地上。
有的死亡像是随便扔在地上的空矿泉水瓶子一样,沾了土灰,被人飞快地忘记,视若无睹。
而我那几天也听说了太多的事情。
信息量太大,让我一下反应不过来,甚至忘了这时候该默哀。
比如顾惊云其实不是自己开车掉下山崖的,是被简意澄那个小混蛋撞下去的。
法院判的是事故,加上简意澄家里交了200万美金的保释费,人就这么逍遥法外了。
徐庆春披着一件黑外套,头发乱蓬蓬地站在人群里。
脸上的妆好像好多天没洗,又哭花了,眼线沾了满脸。
前些天我在学校里看到她,刚从IPOffice出来。
她这几天一直穿着这么一套衣服,脏兮兮的睡裤上还印着HelloKitty。
她一直不说话。
满脸都是憎恨。
她告诉我她一定要把简意澄弄得比顾惊云凄惨十倍。
苏鹿就站在我身后。
她不远处就是简意澄。
我不知道简意澄哪来的勇气敢参加这葬礼。
他穿着一件纯黑的衬衫,但我能看出来那料子和别人穿的都不一样。
那是手工定制的,一件至少要2000美元。
苏鹿站在我身后,目光望向极远的远方。
这几天我一直陪着苏鹿。
每次看到她我都觉得说不出来的难受。
我把她喜欢的香辣蟹过桥鱼炸酱面放到她身边,看着她面无表情地睡着,脸色苍白地醒过来。
只有我帮她剥螃蟹满手油的时候她才会笑出来,笑着笑着就把脸转过去。
不让我看到她难过的表情。
她现在的室友是个新生,问我是不是来看女朋友。
我一直告诉他们我来看我妹妹。
这词听着太矫情,只有90年代申请QQ叫阳光男孩的那批人才能毫不脸红地叫出来。
所以我后来看见她室友都转身就走。
有时候我会像老头一样坐在苏鹿的房间门外。
这座城市里的空气都是阴凉的,带着刚刚焚烧过的树叶的清香,有一种深深的苍凉,很适合举行葬礼。
我想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参加学校组织的西雅图一日游,同学都去逛超市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过唐人街的小饭店,上海菜,奶茶店,还有用红色的胶布贴出来的粥面两个字。
当时夏天还没过去,树叶特别浓,碧绿碧绿地遮下来,街道安静得就像中国的小城一样,一点也不华丽,但是阳光太美好了,它照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变成那些砖砌的建筑,变成树,变成鸽子的影子。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西雅图就是举世闻名的雨城。
我当时以为日子就真能这么过下去了,好像秋天的黄昏,老家院里浓浓地覆盖了一地的凤凰花。
后来百年历遍听闻。
笑赏月吟风莫要论。
最近我总想起这首歌,只唱到这儿就停了。
后面的两句词无论如何也不敢想下去,似乎每个字都锋利无比,在胸膜上一戳一个血洞,呼吸里都带着腥甜的血味儿。
有一些人会隔三差五地过来看看苏鹿,简意澄也来过一次。
我当时就想把满满一桌的螃蟹壳都摔到他脸上。
苏鹿在旁边睡觉,睫毛轻轻地抖动着,薄如蝉翼,让人感觉她的灵魂正在云海的某处一望无际地漂泊。
我低声吼了几句,叫他滚。
简意澄抖了抖嘴唇,好像要告诉我什么。
他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苏鹿听到他走就睁开了眼睛。
“我还没死呢。
”她盯着门板,眼睛里是两轮紫红色的夕阳,混混沌沌,日渐下沉。
我一直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千个一万个人都是活在阴影中的。
他们大同小异地苟且偷生,有的甚至可以悠然自得。
只有苏鹿不一样,就像海面上壮丽绝伦的夕阳。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人们惊喜赞叹的霞光,是她滚烫跳动的鲜血。
她现在站在我背后,我看着她。
她看起来好像是薄薄的一张纸,已经流干了所有的血。
这葬礼结束之后很多人聚在一起,等着外面的雨停。
苏鹿撑开黑色的雨伞,慢慢地逆着人潮,逆着雨,从繁华走向荒芜。
我跟在后面,我不喜欢淋雨,但是我觉得这场该死的雨永远都不会停了。
那些欧陆式的庞大建筑,银行,政府,共同组成了一片长久沉默的锈绿色荒原,永远潮湿,寒冷,没有春夏秋冬。
我听见拖鞋打在水面上噼噼啪啪的声音。
徐庆春蓬头散发地跑过来,睡裤踩在脚下,溅的满是泥水。
她几步跑到苏鹿面前,二话不说抬起手来就是一耳光。
我冲过去想拦住她,走位太差,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么一下。
我当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冒金星。
“苏鹿啊,我×你妈你知道吗?你妈养你这么久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白吃干饭的吗?”徐庆春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心平气和,这话听起来并不像骂人,好像在陈述一个什么事实。
“你什么事情不好说,非要这样?”我把苏鹿挡在身后,一遍遍地告诉自己站稳了别摔倒。
“林家鸿你他妈还没看出来?”徐庆春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她就是个克夫命,谁沾上谁倒霉。
别的不说,出事儿这么长时间,你见她出头说过一句话?和西雅图一样,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城市,满身咖啡豆味儿的文艺婊子——” “你还有完没完?”我想推开她,她抓起苏鹿的胳膊把她扯过去。
“简意澄就在屋里,我今天就带着你们俩傻×找他算算账。
你俩现在明白了吗——?”她指着身后的教堂,“这一切都是从简意澄那儿开始的,他是个杀人嫌疑人。
以为家里能拿出两个保释金就可以逍遥法外?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
一切都是从他那张狗嘴开始的。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
” 海岸悠长的汽笛和着水雾,公交车沿着轨道驶向黑暗。
徐庆春几步跑过马路,差点被一辆车撞翻,掉了一只拖鞋也没顾上。
她拉着苏鹿,满身都滴着泥水,教堂里只剩下几个人,寂静得好像手术室一样。
简意澄回过头来,和以前的很多次一样,不卑不亢地盯着她。
徐庆春上前一步揪住他的头发,熟练地甩了他几个耳光,声音清脆地在教堂里回响。
“那些话是你传出去的,对吧?7月4日你和顾惊云在一起,对吧。
”徐庆春眼神平静,她不是不想发火,我能看出来,她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疯狂地乱抓着手可以触及的所有东西,大黄鸭,空瓶子,死鱼。
好像这样她就可以活下去了。
“对。
是我干的。
”简意澄越过她,平视着苏鹿。
那个眼神恶毒而勇敢,就像小的时候眼保健操画报上的小人一样。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在街上忽然见到他,哪怕只是远远的一眼,都会让我感觉到突如其来的,凉彻心底的恐怖。
“你们都以为我嫉妒苏鹿?你们以为我还喜欢顾惊云?我告诉你们我死都不愿意变成苏鹿那样的人。
什么东西。
”他的嘴唇苍白凉薄,像是冰刻出来的。
我听到他胸腔里薄膜裂开的喘息声,“我每天看着他们,就像看一个笑话。
就像我看你一样,徐庆春。
苏鹿和你男朋友在一起,你竟然会替她说话?” “好,简意澄,既然你承认了,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
”徐庆春不管不顾地拿起手机。
“我和别人不一样,反正都有案底。
我不怕和你拼个鱼死网破——” 苏鹿抬起头,好像要用眼睛去承接满世界的雨水。
有人推开教堂的门,慢慢悠悠地走过来。
那是张伊泽,额前的头发被压得乱七八糟,好像抱着臂睡了很久。
他看到这个场景,挡在徐庆春面前。
徐庆春啪的一声打开他的手,“你今天他妈的别拦我,我总算知道人人上那些狗话是谁发的了,到现在作成这样他还不知悔改!” 张伊泽回头看看简意澄,低声问:“是真的吗?” 简意澄点点头,眼睛里刷刷地淌出两行泪水。
“还有啊,他之前不知道和多少个男人睡过。
还主动爬上贺锦帆的床,人家理都不想理这个死基佬。
”徐庆春在教堂里公然点了一支烟,火光的颜色很凄厉,好像是被谁用放旧了的铅笔胡乱涂抹出来的霞光。
“不知道你俩以前是哥们儿还是别的什么。
总之看你们以前关系挺好的,我没忍心告诉你。
” 简意澄闭上眼睛默认了。
他身后是巨大的十字架,表情仿佛一个不知名的殉道者。
张伊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胡乱地抓了抓本来就乱蓬蓬的头发。
徐庆春平静地看着他们,想继续叫人过来。
张伊泽一瞬间的表情让我以为他马上就要爆炸,大喊一声对所有人输出成吨的伤害,但是他没有。
他走过去,抱住徐庆春,然后手臂滑落下去,在我们面前跪了下来。
“徐庆春,我知道他对不起你,他也对不起苏鹿,对不起顾惊云。
对不起这个世界。
”他吸吸鼻涕,头好像永远都抬不起来了。
“可是法院已经判过了。
你们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 他抬起手,想拉住徐庆春满是泥水的衣角,犹豫了片刻又放开了,好像他自己身上有着什么病毒。
徐庆春指着门,声音里带着哭腔,好像是长满野草的荒凉坟墓。
“老子不想和你扯上关系。
你快滚吧。
别再让我看到你。
” 张伊泽站起来,似乎想要抚摸徐庆春的头发,被徐庆春一把推开。
“基佬快滚。
”她坚定不移地指着门,平静而悲哀。
我的电话就在这时候恰到好处地响了起来。
是我妈妈的电话。
他们几乎从不这样打越洋长途。
我跑到门外接起来,费了很大力气才弄懂他们的含义。
国内出大事儿了,我家里被调查,他们打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我,千万不要联系他们,也不要回国。
尽量完成学业,就算打黑工也要完成。
西雅图的雨水就像钉子一样,可以把人钉在地上,冰凉地穿过心脏。
我看到张伊泽从教堂里冲出来,冒着大雨跑过街道。
他们的身影被雨冲刷得渐渐模糊,好像是纸扎的风筝,宽袍大袖,一阵风吹过去就离地半尺,不着尘埃。
可能他们刚才看我也是这样,人只有在拥有相同的苦难的时候,才会在泥潭里挣扎着相依为命。
我又想起那首歌,我终于可以把后面的歌词一字不差地默背出来。
大雨里满目疮痍的楼群渐渐融化成了一种液体,我闭上眼睛,眼前只有城市的万家灯火。
纵今相逢,满面俗尘,妄嘲天真。
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就像我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徒劳无功的挣扎,以及像被随手丢弃的鸡蛋壳一样,冗长到连我自己也不想要的一生。
【梁超和苏鹿】,2015
小镇的雨越来越大。这是个凉爽的清晨,空气里都是烧焦的树叶的味道,好像刚举行完一个葬礼。
我躺在床上,烧得快要融化了,看着天花板,听到苏鹿推开我房门的声音。
我是昨天联系到她的。
她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线索。
就算被打几个耳光我也得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本来我也应该和简意澄一起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简意澄救了我。
就凭这个,再给我一百次机会我也要和他并肩作战。
苏鹿走进我的房间来,搬过一把椅子,静静地坐在我的床边,好像在等待着我死去。
屋里灯光极为黯淡,窗外的乌鸦迎着雨鼓噪两声,是病重的少女垂死的瞳孔。
“苏鹿。
”我把重心从身体的左边移到右边,一阵天翻地覆的眩晕。
“你就告诉我,人到底是不是你找的。
” “你想干什么?”她端坐在转椅上,不动声色地问。
上早课的学生们已经下课了,从社区的大门里三三两两地走进来,喧哗声和吵闹声被泡在雨里,贴在窗户上,从几百年前遥远的传过来。
她们踩在一个一个的小水洼上,好像一大群水鸟。
“我其实已经知道了,就想听你自己说。
除了你和江琴之外再没人知道我们俩那天去给顾惊云送花,对吗,但是那些黑人里面有一个广东人。
我知道你不和广东人一起玩儿。
在我报警之前,你不觉得你应该为自己辩护几句?” 她不为所动,站起身来,给我倒了一杯滚烫的热水。
“你发烧挺严重的吧。
吃药了吗?” 我盯着她手里那杯水扭过头去,“你至于吗苏鹿,简意澄不就是多说了几句话吗?就因为说了你几句,你就能把他的一生都给毁了?你至于下这么狠的手?” 她笑起来,好像我在谈论的是什么陌生人。
“没吃药就快吃吧。
干吗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又不会在水里下毒。
” 隔壁语言班的女学生踩着拖鞋跑了出来,头发乱蓬蓬的,书包掉了一半,踩在草坪上好像范进中举。
“终于过了!我们全班都过了!全班4.0!”她手里挥舞着一张成绩单,眼含热泪地追上她的同学。
她的同学纷纷嬉闹起来,“你可得感谢那个叫简意澄的学长——” 我认得她,她叫常羲,已经在语言班蹲了三年。
苏鹿抬起头去看着她从窗外跑过,用泡感冒药的汤勺轻轻地搅着手里的水。
我咽了一口唾沫,把泛着恶狠狠气味的泡沫压下去。
“我知道,你觉得简意澄有罪。
觉得他活该。
你平心而论,简意澄说的有多少是假的?你跟顾惊云就是干干净净的?”我心里清清楚楚,无论人是谁找的,简意澄就是活该。
没人会为他伤心,甚至没人会过问他一下。
只是那天晚上的灯光好像是揉碎了一大把的玻璃片,揉进我大脑的缝隙里,让我每天头痛欲裂。
“很多事情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你装出一副全世界不懂的样子来——” 在我提到顾惊云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死了。
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手足无措的样子,取而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我的师尊遍布修真界/全修真界为我火葬场薄夭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仙君有劫黑猫白袜子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怀了队友的崽怎么破西山鱼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末世对我下手了一把杀猪刀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综]混沌恶不想算了!安以默
- 江湖人独孤红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首辅大人重生日常/今天也没成功和离时三十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御佛o滴神
- 全星际都等着我种水果一地小花
- 锦帐春慢元浅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纨绔心很累七杯酒
- 极品修真狂少墨世
- 持续高热ABO空菊
- 你们练武我种田哎哟啊
- 情终孤君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眼泪酿宴惟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夏日长贺新郎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不息阿阮有酒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鱼游入海西言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球”嗨夕尧未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循规是笙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球”嗨夕尧未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杨九淮上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如何才能将目标勾引到手南柯良人
- 治愈过气天王落落小鱼饼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他只是我男朋友廿小萌
- 你叫什么?我叫外卖晒豆酱
- 他喜欢白月光味信息素等登等灯
- 媳妇与枪初禾
- 小可怜开心是福嘛
- 这个小贼姓苏爷子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单恋画格烈冶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游弋的鱼乌筝
- 情敌五军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学长在上流麟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替身夺情真心
- 共同幻想ENERYS
- 戏精配戏骨陈隐
- 404信箱它在烧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独立日学习计划一碗月光
- 竹木狼马巫哲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穿女装被室友发现了怎么办linglongzizizi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