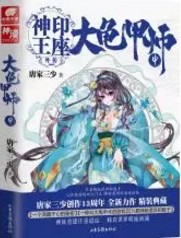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俱邀侠客芙蓉剑(3/3)
代之的是一种灵魂出窍的镇定。
我发觉我的声音在身边六神无主的飘,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一个死人。
“来,先吃药再和我说话。
”她轻轻地吹了吹,水杯里的水像是涟漪一样化开。
“我们之间不是还有好多话没说完吗?比如7月4日那天晚上,到底是谁开车出去的。
你也知道不是简意澄,但你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对不对?” 我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像是被烧干了的湖,漆黑寂静,一点儿响动也发不出来。
“简意澄是在替什么人顶罪。
你好几个星期之前就告诉过江琴。
这是对的。
当年我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机智。
”她就像是我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里的那些亡灵,还未察觉到自己已经死了,在人间盲目地游荡了百年千年。
“梁超,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最近有没有觉得脚疼?” 我的脚踝适时的疼了起来,浑身发冷,好像踩在深广的河面上。
我尽力地控制住嘴唇的颤抖,“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都知道简意澄是在替什么人顶罪。
谁会相信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就能毫发无伤,还能在学校里活蹦乱跳?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有什么东西沉沉地朝我的眉毛上压过来,催促着我快些睡着。
“我也想知道。
”我尽力地睁大眼睛,房间里散发着药的苦味,衰败和死亡的气味。
黑暗像水银一样缓缓流动。
“7月4日那天,贺锦帆喝多了,去找地方随地大小便。
亲眼看到你和顾惊云一人开着一辆车往郊外开过去。
他说你们当时差点撞到他,把他的酒吓醒了一大半。
”苏鹿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码。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他。
” “胡说八道。
”被子把我裹成一团,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拼尽全力地想从被子里挣扎出来,头上的每根毛细血管都快要爆裂开了。
我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好像一具破旧的风箱。
“你犯了法不想承认,跑到我这里来胡说八道——” 我喘着气靠在床上,停止了挣扎。
好像有无数小虫子在空气里嗡嗡的响。
那些小虫子最终都绕到她的身边去,跟着她的声音一起在光晕里凝固。
她的眼睛镇定而悲怆,好像里面从来没有过生命。
“徐庆春昨天已经投案自首了。
我有什么事不想承认?”苏鹿喝了一口水杯里的水。
烧干的橘子皮味,西药干净的苦味,在房间里缓缓的弥漫开来。
“梁超,我没必要骗你。
江琴是顾惊云的前女友,她有顾惊云的人人密码。
她觉得你以前还和我们是朋友,不想让你知道。
还去修改了顾惊云的转发记录。
只是她忘了每条转发记录上都有时间——” 我看到自己的胸腔剧烈地起伏着,血往喉管上涌。
我的五脏六腑似乎还没放弃和这个世界做最后的挣扎,但是过去不由分说地涌上来。
这个镇子四周环山,被一条长河穿过。
我从前住在寄宿家庭,每天放学都看到那条河流过一地的草,夕阳照在水面上,河边是一排墓碑。
我那时候每天听着ifIdieyoung,从半山腰上俯视着这条河。
“简意澄也和我认识这么久了,他和我说过不少关于你的事儿。
其实我们都不信简意澄这种人还能替别人顶罪。
他有一天喝醉了,一边哭一边和张伊泽吵架。
说张伊泽看不起他,只有你是真心地对他好——没冒犯的意思,我知道你不是基佬。
”苏鹿的声音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客气,不紧不慢,穷追猛打。
“你喝了酒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事儿发生过好几次。
简意澄说过,你有一次喝了酒之后,带他去看你寄宿家庭旁边那条河。
说这条河边从古至今有那么多的死人,连骨头都不剩了,只有这条河无情无义,一直在颠沛流离,苟且偷生。
”她的手指敲打着玻璃杯,发出怆然的脆响。
“梁超,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艺了?” 过去像是雾气一样漫过来。
生命似乎从我的眼睛和半张的嘴里迅速地流逝。
我的手指连攥紧床单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用最后的力量睁开眼睛看着苏鹿,整个胸腔里都弥漫着一种碎裂般的哀痛。
我到现在才终于看清了苏鹿的眼睛,那是一双长久凝视黑暗的眼睛。
这样的眼睛里看到的从来就不是现在。
我听到耳膜旁边滑过去的风声。
那天晚上的风声太大了,我的喉咙里全是酒,上不去也下不来,堵在喉管里,好像一动就会哗啦啦地吐出来。
顾惊云找了简意澄去约架。
他说要和简意澄比谁先开到那座山顶,没人知道简意澄根本就不会开车。
我偷偷地对他说上了车之后换我开。
有个黑影从窗户外面闪过去,我没看清那到底是不是贺锦帆。
简意澄孤零零地坐在离那栋房子遥远的树丛旁,好像是丧尸来临的夜晚被我丢在一旁的小女孩儿。
外面的黑暗掺着零星的灯光慢慢融化了,变成了一种液体四散泼溅开来,拍在我们的窗子上,每当我想起来这个画面的时候都觉得耳鼓膜像要被涨破了一样,有风呼呼地吹过去,这让我不得不去拿一罐冰可乐,让自己稍稍沉静下来。
那条路的尽头,站在树木黑影里的东西是一头鹿。
它迎着我的挡风玻璃,端然地张着眼睛。
每当我想起这个画面的时候心脏都会剧烈地颤抖。
雨太大了。
那头畜生的眼睛就像现在苏鹿的眼睛一样,没有一分一毫的偏私,也没有活气。
那不是活的东西。
我忘了我往哪边转了方向盘,踩得是油门还是刹车。
顾惊云就在我的右边。
红紫色的光和尖厉的呼啸声像是被打碎了一地的酒瓶片,对,我终于想起来了,黑夜此刻就是一瓶被砸碎的酒,混着浓烈的气息四处流淌。
我知道顾惊云当时也吓坏了。
我的车头没法控制地朝他那边冲过去。
轮胎锁死了。
在声嘶力竭的鸣笛声里他的车打了个悠然的回旋,然后猛地向山路的围栏冲过去。
围栏哗啦啦地倒了一片,他那辆车从高处划了道惊世骇俗的弧线,像满载着烟花的货箱被点燃了丢进河里。
那一瞬间那条河慈悲地吐出了没烧尽的夕阳,湿漉漉地燃烧着,把天际线都烧红烧化,深红,暖黄,五颜六色的搅杂在一起,烧出软绵绵的一锅稠汤。
之后我曾去看过那辆车的残骸,已经成了具炭黑的空架子,好像是夕阳没烧尽的遗骨。
我再也不知道顾惊云去了哪里。
那天晚上我站在雨里,全身都湿透了,脚卡在车里,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
简意澄接到我的电话,从山下跑过来,每一次喘气都能淋出一大盆水。
他告诉我他没喝酒,还是未成年。
法院不会拿他怎么样。
他说没人会知道,到时候就告诉警察是他开的车。
让我放心。
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一头鹿,他心惊胆战地问我,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我相信你是真的不记得了。
”苏鹿的声音好像是天际的梵诵,高远而缥缈。
“我相信你这些日子一直在拼命地调查这件事不是在掩饰自己。
至于简意澄,你最好还是去医院看看他。
虽然我不觉得他可怜,也没人觉得他可怜。
大家都为了GPA感谢他,恨不得把他从医院拖出来在祖宗灵牌上烧几炷香。
但他至少是帮了你。
”水从杯子里溅出来。
她的袖子湿透了,而她浑然不觉。
好像是一盘刚从冰箱里端出来的尸体,在潮湿的天气里慢慢融化。
我忽然想到她的魂魄是不是已经化成了那头鹿,早已经死在了公路上。
而她自己却一直没有发现,还留在人世间,准备面对漫长而残破的一生。
黑暗迅速地没顶。
我听到空气在自己的五脏六腑里哗啦哗啦地乱响,但是却不觉得疼痛。
灵魂跟着这些话从我的身体里生拉硬拽地扯了出来,在天花板上奇异地漂浮着。
那条河流在夕阳下静静地翻涌着,流过千古兴废,断壁残垣。
简意澄跟在我身后,我其实一直嫌弃他。
只是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表达出来。
我自己家境不好,成绩也不好。
和他们不一样。
“超哥你一直陪着我,我也没什么能帮得上你的。
”简意澄低着头,踢走脚下的一块石头。
“要是现在打仗就好了。
我可以替你上战场。
” “你以为你是花木兰替父从军?”我顺手拍了拍他的头。
他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
晚霞在他的眼睛里轻盈地漂浮,好像飞鸟。
房间里的药味,腐朽霉烂的味道,衰败和死亡的味道,都没有了。
我隐隐约约能听到杯子扣在桌上清脆的声音和苏鹿短促的叹息。
我知道那就是我的墓志铭。
眼前的这条河是埋葬我的地方,我的身体里回荡着河流的声响,沉默地朝夕阳翻腾奔涌。
泥沙,人骨,枯枝败叶,青灰色沉沉的屋顶,年少的岁月,欢声笑语,促膝长谈,都随着这条河顺流而下。
岁月在烟尘里被晚风吹散,夕阳温柔地归落到水底,美国人的房子上升起了炊烟,人间圆满而荒凉。
而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
后来我听说她和江琴、林家鸿在一夜之间启程,一起去了加州。
我忽然想起来很多年以前我们曾经一起去过那个地方,简意澄点了一首《还珠格格》的片尾曲,我们站在沙发上一起唱着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这一切现在都被折旧,弄脏,变成一朵插在花瓶里歪歪扭扭的纸花。
忆我少年游,跨我青骢马,仗剑江湖行,白首为功名。
都过去了,任的是风生水起,梁山聚义,拼将一生只争朝夕,你最后总得被招安,总得反过头来说当年那些风华正茂对酒当歌的日子都是错的,都是不应该的。
这没什么好说的。
站在梁山上再看下去,也就看得到水枯石烂,看得到桃花落地,看得到一眼望不到头的烟消云散,满目疮痍。
【林家鸿】,2015
光芒透过车玻璃照进来,刺眼而带着点点污渍。天空蓝得发亮,像结上了一层薄冰一样——不过这是4月末,4月是不会结冰的,我们从美国的最北端往最南端行驶。
这座城市有个奇怪的西班牙名字,大路上都是尘土,从车里看向外面,南美人众多,卷得厉害的口音和酱油色的皮肤,把这块烈日坦荡的贫瘠土地衬得像一张暴晒过的底片。
再往远看过去,是一家墨西哥菜老旧发灰的标牌,白色的塑料袋被风刮向蓝天。
昨晚换了江琴开车,我忘了什么时候在车后座上躺下,一路颠簸地睡过去。
这段旅途漫长得让人窒息。
广播里没完没了的贾斯丁·比伯听得多了,我想他妈砸车。
昨天半夜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我快要死了,真皮的座椅和四面八方渗进来的冷空气包裹着我,我觉得我整个人结上了薄薄的霜,风一吹就前赴后继地变成泡沫。
就在我冻得迷迷糊糊快失去意识的时候,电台广播里又开始放贾斯汀·比伯的歌,我用尽了最后一口气挣扎着够到前面把电台关了,然后我就清醒了,贾斯汀·比伯救了我的命。
我睁开眼睛,眼前白茫茫一片,浑身的骨头一动就咔嚓咔嚓的响。
江琴在穿过玻璃炙热的阳光下打着哈欠,真皮座椅摸着烫手,车里又被烤得像个面包机一样。
“迷路了,”苏鹿像说一件什么好玩儿的事似的回过头来对着我说,“我们走错了。
”她的双眼通红,嘴唇干瘪,好像是被熊熊大火烧过的荒漠,她身后的玻璃外面有只秃鹰,狰狞,肃杀,毛色像是乌鸦,大得让人恐惧,从满地扬起的尘埃里飞上来,拍打着翅膀,大叫着飞上高远的苍穹,声音凄厉欲绝。
我觉得它像整个辽阔的荒漠一样,马上就要扑过来,就要把我们吞没了。
她的话一次一次地震荡着我的耳膜,像电磁波一样在我脑子里来回冲撞。
“走吧,接着走吧,把GPS打开。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接着躺下,平躺在被阳光烤得炙热的真皮后座上,好像在进行火葬。
对面走过来一个卷毛的墨西哥人,挥着手,对我们狂怒地大吼大叫,江琴一踩发动机,车突突地行驶起来了,像个东风拖拉机在乡村尘土飞扬的小路上一往无前。
哐当哐当的声音好像车里的每个零件都七零八落地掉下来了,风吹进去,吹出空荡荡的声音,太阳照在我额头上,照在每个酱油色的人身上,照在土路上,饭店标牌上,它是为那些卷着舌头的语言和西班牙语准备的,他们一生在这种炎热的炙烤下忍辱负重,不怕热,也不怕死,把日子熬成一锅冒着泡黏糊糊的沥青。
在这个时候我才决定了好好想想那个问题,几个月以来一直盘亘在我心里的那个问题,我一直不敢去想它,好像是我小时候在北方看到的那么一幅景象。
冬天,凛冽而清脆的寒意,挂在电线杆上的那么一只红气球,在蓝得渗出水的天空下面孤零零地漂着,像是个小姑娘新鲜的头颅一样。
树杈是白晃晃的尖刀,竖直着刺上去,天像一块将化未化的冰,晴空万里。
这幅景象一直在我记忆里,它简直太可怕了,说不出来的可怕,让我长久以来不敢直视,就算它已经被岁月消磨成一张黑白相片。
——你该怎么活下去?林家鸿,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混在这些墨西哥人和中国偷渡来的小工中间,污迹斑斑,不分彼此。
种树,端盘子,把日子消耗在饭店满是油烟污渍的厨房里,消耗在广东老板笑里藏刀的骂声里,装孙子,嘴上抹蜜,手脚麻利,回家数着这一天赚来的几元钱小费,就像贵妇人盘点她毕生的首饰珠宝,过10年靠政治庇护办出身份,15年开一家自己的餐馆,30年,40年,你就和所有唐人街上头发花白,一身运动服的老头儿一样,与中药和老式挂钟为伴,被世界遗忘,自得其乐,儿女满堂。
就在那么几个月之前,生命像发生了一场大爆炸,硫磺四溢,岩浆滚滚,从前少年时代的赌书泼茶,鲜衣怒马,恋慕,烦恼,惊惶,平静,轻狂,梦想,都迅速地分崩离析。
就像飘到半空中日渐干瘪被扯得粉碎的红气球。
我甚至来不及回头看一看。
生命中所有的颜色都消失殆尽,只剩下坦荡贫瘠的土地和一望无际的炎热阳光。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每天拔节,疯长,遮天蔽日。
——“我该怎么活下去?”
【镜】
我一直站在这栋房子里,尘霜满面,劫灰零落。你走了很久,一屋子衣物散乱地摊在地上,我有些忧伤地看着它们,好像是看着几只不死心的行尸走肉。
那些晚上十几辆警车几乎把整座城市封锁了。
窗外整个城市的红光从玻璃反射进来,好像是熊熊燃烧的火。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学生来找你,义愤填膺地支持你,给学校写联名上书。
你在没有犯法的时候声名狼藉,真的犯了法却被谅解。
这让我很庆幸没有和这些人生为同类。
那些人走之后,你从不开灯。
在黑暗里静静地用指节敲打着我,仿佛在给自己雕刻一块墓碑。
我从没有什么话想对你说,人间太过疯狂。
好像是炽炽沸腾的铁水,把每个人都蒸得皮溶骨消。
你看起来就像那部电影里的人,你经常看的那部电影。
你的家乡,中国北方的农村。
老头儿背着同伴的尸体回家,走过繁华,走过荒野,随着人流挤上嘈杂的大巴,跟着货物一起睡在卡车后车厢。
后来他的钱没了,家也没了。
有个路人无动于衷地提醒他,你背上这人已经死了。
于是他就杀掉了那个人。
老头儿站在万里晴空下面,云轰轰烈烈地滚过去。
原野都收获了,被烧焦了。
他的身后曾经伏尸百万,兵败如尘。
他一手血污未干,黑色的塑料袋在空中慢慢地飘。
他的眼睛盯着地上的尸体,咳了一口浓痰,嘟囔一句,幸会。
天空辽阔而苍凉。
那种让人胆战心惊的颜色,可能只有你的家乡才有。
你从一时风头无两,到最后孑然一身。
初次见到你,你还披着一件单衣,身影显得分外单薄。
你举起双手,仿佛张开双翼。
那形象让人迷惑。
但我始终在不自觉地效仿着你,如何坚定地站立着,背负起一片土地上的所有罪孽。
星期日的夜晚,你从楼梯走下去,门外是划破黑夜的警车声。
你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你披好了外衣,紫红色的灯把你的脸照得更加曼妙。
封锁整个城市的搜捕结束了,让无数人惴惴不安的夜晚结束了,猜测和追忆都已经结束了。
夜晚的风揣着寒意,污浊的夏天已经过去。
你在我面前化妆,身后是喧嚣扰攘的破败尘世,脚下是散乱一堆的名牌包装。
无人为你掌灯,无人为你吟咏,无人愿意对你娓娓道来,无人愿意陪你共度余生。
这个夏天已经过去。
毕竟你们的一生太过漫长,而良辰美景又太过短暂。
我都知道的。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夜行歌紫微流年
- 与婠婠同居的日子李古丁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咸鱼飞升重关暗度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春日颂小红杏
- 怀了队友的崽怎么破西山鱼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看见太子气运被夺后花里寻欢
- 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01入学篇(上)佐岛勤
- 江湖人独孤红
- 佛系女主崩坏世界[快穿]实心汤圆
- 穿书后我爱上了蹭初恋热度清越流歌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御佛o滴神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全星际都等着我种水果一地小花
- 流氓老师夜独醉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锦帐春慢元浅
- 女配不想死(快穿)缓归矣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鱼游入海西言
- 夕照斑衣白骨
- 游弋的鱼乌筝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情敌五军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鱼游入海西言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情敌五军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球”嗨夕尧未
- 替身夺情真心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杨九淮上
- 离心ABO林光曦
- 流量小生他天天换人设西西fer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嗨,保镖先生棠叶月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无可替代仟丞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