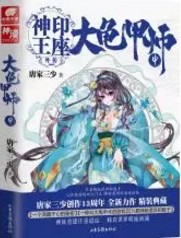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I 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3/3)
起了她的怒气。
“你一边说我胖,一边又像喂猪一样让我吃这吃那!”她喊道。
“阿维娃。
”我说。
“不对,你很会说话。
你从来不会直接说我胖,而是隔三岔五就把话题引到我的体重上,问我吃得健康不健康,水喝得够不够多,说哪条裙子看着有点紧。
” “没有的事儿。
” “你说我不应该把头发剪得太短,因为这样显得我脸太圆。
”阿维娃说。
“阿维娃,你哪里来的这些怪念头?”我说,“你是个漂亮姑娘。
你生来是什么样,我就爱你原本的样子。
” “别撒谎了!” “怎么了?你就是留长发更好看。
我是你妈妈,我想让你展示出最美的样子,这有什么错?”我说。
“只有你才会一刻不停地想着自己的外表,吃甜点从来超不过三口,健起身来像疯了一样,别以为你这么做,我就要向你看齐!”她说。
“你当然不用向我看齐。
”我说。
“究竟哪件事让你更嫉妒?是我能够迷倒亚伦·莱文那样的男人,还是你没法迷倒他那样的男人?” “阿维娃!”我说,“够了。
这种刻薄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
” “而且我知道你背地里肯定说过什么!你要么就是说了话,要么就是捣了鬼!承认吧,妈妈!别再撒谎了!求求你别撒谎了!我必须知道真相,不然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原因非要在我?难道就不可能是学校的环境让他想起你年纪还小,他跟你保持这种关系很不恰当吗?这难道就不可能吗,阿维娃?” “我恨你,”她说,“我永远不会再跟你说话了。
”她走出家门,关上了门。
“永远”只持续到了八月。
夏末时节,我和迈克在缅因州波特兰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了一幢房子。
我给阿维娃打电话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说话,难道还不够吗?无论我做了什么,或者你觉得我做过什么,我都非常抱歉。
到缅因州来看看我和你爸爸吧,我非常想你,爸爸也很想你。
我们可以每天都去吃龙虾卷和巧克力派。
” “龙虾?妈妈,你怎么了?”阿维娃说。
“不要告诉你外婆,不过我拒绝信奉不许我吃龙虾的神。
”我说。
她笑了:“好吧,好,我会过来的。
” 我们在一起住了大约四天,她忽然说:“过去的一年就像一场梦,好像是我着了魔,而现在这个魔咒终于解除了。
” “我为你感到高兴。
”我说。
“不过,”她说,“有时我依然会怀念着魔的感觉。
” “但你不再和他见面了吧?” “不,”她说,“当然不见,”她更正道,“我是说,我不再私下和他见面,只在工作上和他打交道。
” 她仍然在为国会议员工作,这不禁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你会不会很为难?”我问,“经常与他见面,但却不再和他交往?” “我很少见到他,”她说,“我的地位没那么高,何况如今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也没那么高了。
” 8 《卡美洛》事件过去几天以后,罗兹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把《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票转让给她。
她妹妹要来看望她,他们三人同去,岂不正好?我说好,因为没人想看音乐剧版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剧场的套票总免不了混进几部并不好看的剧目。
她说要把票钱给我,我说我不会要你的钱,罗兹·霍洛维茨,我正巴不得自己不用去看《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呢! 罗兹干笑几声,然后说:“唉,瑞秋,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她还没开口,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我知道,那位胳膊肘先生一定颠倒了黑白,告诉她是我想向他献吻。
他这么做是想先下手为强。
我本该给她打个电话,可是站在我的角度说话,谁会想到别人的婚姻里去蹚浑水呢?尽管已经猜到他的招数,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嫁给出轨浑蛋的女人,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撞上。
难道我想让好朋友在这个年纪离婚?难道我希望她继续为网络头像发愁,梳妆打扮,把自己硬挤进塑形内衣,去跟一个又一个老男人相亲?不,我不希望她那样。
“罗兹,”我说,“罗兹,亲爱的,我想你误会了。
” “他说你想给他——”她压低声音,愤怒地低声说,“打手枪,瑞秋。
” “打手枪?罗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究竟为什么要编出打手枪这回事?这人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知道你很寂寞,瑞秋,”罗兹说,“可是从1992年起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了解你这个人。
你很寂寞,而且你自以为是,爱管闲事,所以我相信他。
” 我说:“我绝不会为了他而背叛你——我们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为了区区一个玻璃经销商?永远不可能。
” 罗兹说:“瑞秋,别说了。
” 于是我没有再说。
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9 到了那年秋天,阿维娃回到迈阿密大学,决定不在学校里住,而是搬进了位于椰林区的一幢小公寓。
我们一起布置她的小窝,其乐融融。
我们选的是“清新复古风”,从慈善商店买来木制家具,用砂纸打磨做旧,涂成奶油色,买来带有花卉图案的褪色床单,又从旧货店买了一床米色的被子。
我们找来一个青绿色的大碗,往里面装满贝壳,还准备了栀子花和薰衣草味的大豆蜡烛。
我们把墙壁刷成白色,挂上半透明的薄纱窗帘,又歪打正着买到了一把韦格纳设计的法式Y椅,是白桦木的真品——那时五十年代的家居风格尚未风靡,我记得我们只花35美金就买下了它。
我最后买的一件东西是一株白色的兰花。
“妈妈,”她说,“我会把它养死的。
” “只要别浇太多水就好了。
”我说。
“我养不好花草。
”她说。
“你才二十一岁,”我说,“还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好、什么做不好呢。
” 这个小房子太美好了,一切都很完美,留白也恰到好处,我还记得自己暗地希望能搬去和她同住。
我甚至有点嫉妒阿维娃,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布置公寓。
那是我们母女关系中的一段快乐时光,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舒心。
董事会最终决定不再另寻新校长,于是我成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正式校长。
大家为我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准备的点心是烟熏三文鱼吐司,不巧的是三文鱼不新鲜,我当时没吃三文鱼,可吃了的人后来都恶心反胃。
我当时并没把这当作一个兆头。
罗兹请我吃饭,庆祝我的四十九岁生日。
她说我看上去气色非常好,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我最近很开心。
” “有空我也要试一试。
”她说。
不知为什么——或许是红酒喝得太多的缘故——我哭了起来。
“瑞秋,”罗兹说,“我的天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正相反,”我说,“我以为会出事,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我太庆幸了。
” “你不用强迫自己全都告诉我,”罗兹一边说,一边给我又倒了一杯红酒,“是你身体出了问题吗,还是迈克的身体?是不是你发现了肿块什么的?” “不,不是那些事。
” “是阿维娃?”罗兹说。
“对,是跟阿维娃有关。
” “你想和我说说吗?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她说。
“罗兹,”我说,“之前她跟一个有妇之夫有染,现在终于结束了。
全都结束了,谢天谢地。
” “嗨,瑞秋,这不是什么大事。
她还年轻,年轻人就是有做错事的特权嘛。
” 我垂下目光:“这不仅仅是婚外情的问题,重点是对方是谁。
” “是谁,瑞秋?”她说,“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 我附在她耳边悄悄说出了那个名字。
“阿维娃真是好样的!” “罗兹!”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有家室,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而且还是她的上司!” “起码他长得不难看,”罗兹说,“再说我们过去也常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会纵情约会的对象,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你说阿维娃会不会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罗兹说。
“我也不知道。
”我说。
“他那个老婆啊,”罗兹这时已经微醺,“我要更正一下,他才是捡了大便宜。
阿维娃是个可人儿,他们俩在一起会生出多么漂亮的宝宝啊!” “好了,都过去了,”我说,“谢天谢地,没有宝宝。
” 10 我想首先说明,这起事故既不怪阿维娃,也不怪莱文议员。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老太拿着失效的驾照开车上路,左转时没仔细看,一头撞上了议员的雷克萨斯轿车。
老妇人不幸死亡,于是人们对车祸展开了调查。
调查不仅查出了老妇人是过错方,也查出了我的女儿与国会众议员有染——出事时她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这就是阿维娃·格罗斯曼在南佛罗里达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缘起——阿维娃门。
不过我扯远了。
在阿维娃门爆发前,这件事还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都在静待事态进展。
我们等的是这件事最终会不会酝酿成型,或者更确切地说,阿维娃会不会成为这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
当时有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期,她只是与众议员同乘一辆车的“不知名女实习生”。
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会不会被公之于众,我相信莱文议员也曾努力不让阿维娃牵涉其中——尽管这个人德行有失,但是心肠不坏。
不幸的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关注愈演愈烈,对我女儿的保护远非议员力所能及。
不把当晚与议员同行之人的身份查清,公众决不罢休。
阿维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一直拖到了警察把她的名字公之于众的前一天。
那天议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警察即将公布她的身份。
我说我可以替她告诉迈克,但她说想亲自告诉他——她的勇气值得称赞。
我们带迈克去了一家清静的饭店,那里过去是大桥宾馆,如今变成了一家希尔顿酒店。
我和罗兹常开玩笑,说世间万物最后都会变成希尔顿酒店。
那是我们全家最爱去的饭店之一,主要是为了欣赏近岸内航道的景致和来往船只,食物倒是平平无奇,无非是游泳池畔的常见点心,聚会吃的三明治、薯条,诸如此类。
阿维娃点了一份科布沙拉,一口没动。
后来为了把这顿饭拖得更长,她又点了一杯咖啡,仍然一口没动。
我们漫天闲聊:我的工作、阿维娃的课业、迈克的工作,我们没有谈到莱文议员,不过那个事件早已微妙地悬浮在我们之间——阿维娃的名字尚未卷入其中,但迈克对那些街谈巷议本就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时间也过得飞快。
我知道迈克打算回办公室,我考虑过要不要催促阿维娃,最终还是决定按兵不动。
这毕竟不是我的秘密。
迈克核对账单时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与他几年前做过心脏手术的一位女患者有关。
“六十一岁,四处冠脉搭桥,”他说,“没有并发症,但是康复花了很长时间。
总之手术大约一年以后,她正在陪孙女玩,忽然随手用橡皮泥给家里的腊肠狗捏了个惟妙惟肖的泥像。
” “橡皮泥!”阿维娃的语气热情得有点假。
“是啊!谁能想到呢?然后她孙女说:‘多蒂,再做一个。
’于是多蒂又给孙女捏了个像,又捏了自己小时候住的房子——那栋房子在扬克斯,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
到这会儿,全家人都围过来看她捏东西,多蒂的儿子说:‘或许我们应该把你送到雕塑工作室去,妈妈。
’得心脏病之前她从来不是搞艺术的料,不懂透视法,连火柴人也画不好,现在她却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立体半身像,大理石、陶土,什么材料她都能做。
她为所有亲朋好友都做了塑像,还做了几尊名人塑像。
她做得特别好,这件事很快就被当地媒体知道了,大家都管她叫雕塑界的摩西奶奶。
现在多蒂已经开始接受委托创作了,为城市、公众场地和庆典活动做雕像,每件作品都能赚几千美元。
” “你应该抽些提成,”我说,“这可多亏了你。
” “我倒不会狮子大开口,不过现在她正在为我做一尊半身像,”迈克说,“免费的。
” “你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接待处,”我说,“就叫‘伟人的头像’。
” “依你看,为什么会这样?”阿维娃问。
“疏通了心脏,增进血液流动,大脑的机能就会提升。
说不定是大脑机能提升以后创造出了新的神经通路,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才能。
谁知道呢?”迈克说。
“人心真是神秘。
”我说。
“那纯属胡说,瑞秋,”迈克说,“人心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要我说,真正神秘的是大脑。
” “你能把人心解释得一清二楚,”我说,“我们可是什么都不懂。
” 迈克在收据上签了字。
“爸爸。
”阿维娃说。
“嗯?”迈克抬起头。
她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 “我也爱你。
”迈克说。
“对不起。
”阿维娃哭了起来。
“阿维娃,怎么了?”迈克坐回桌边,“出什么事了?” “我闯祸了。
”她说。
“不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补救。
”他说。
“这件事没法补救。
”她说。
“任何事情都能补救。
” 阿维娃回到了迈阿密,迈克取消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日程安排,跟我开车回家进行无谓的争吵。
“我猜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他说。
我叹了口气:“我有过疑心,我的确有所怀疑。
” “既然你有所怀疑,”迈克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我试过了。
”我说。
“光是试过根本不够!” “她是个大人了,迈克。
我又不能把她锁在房间里。
” “我一直以为,你再不济还算是个称职的母亲。
”迈克说。
他吵起架来一向是浑蛋,这也是我对这段婚姻毫无留恋的原因之一。
“你怎么能纵容她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迈克说。
“说得好像你自己是个道德模范似的!”我轻声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两个互相攻击一点儿用也没有。
得赶紧想个对策才行。
” “除了给她找个律师,等这件事平息,还能怎么办?”迈克说。
“我们必须支持女儿。
”我说。
“这不是废话吗,”迈克双手拄着头说,“她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 “我猜她当时并没考虑到我们。
”我说。
“你在她这个年纪会做出这种事吗?” “不会,”我说,“而且我在议员那个年纪也不会做出他那样的事。
我绝对不会跟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下属睡在一起。
你呢?” 他没回答,而是在翻电话本:“我给无数个律师做过手术,这其中怎么也该有一个厉害的。
” 阿维娃和议员先生都宣称这段婚外情早已经结束,阿维娃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
可能事情的确如他所说,他当时只是顺路捎实习生回家(但我要说,车祸发生时他们行驶的路线既不通往她在椰林区的公寓,也不通往我们在茂林会所的房子),那位老妇人左转弯时阿维娃也在车里,这不过是个巧合。
有时候,一则新闻就能激发一整片地区居民的想象力,国会众议员和我女儿的花边新闻也是如此。
我可以向你详细解说这件事愈演愈烈的过程,不过,即便你不住在南佛罗里达,相信你也会对类似的事情有所耳闻。
这件事的发展跟其他花边新闻别无二致。
议员和艾伯丝参加了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他们说,这桩婚外情发生恰逢他们婚姻危机。
他们说,如今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段危机。
他们手拉着手,他眼含泪水,但并没有哭;她则说自己已经抛却前嫌,说婚姻终究是人间烟火,而非童话故事,凡此种种。
我记得她穿了一件不合身的紫色粗呢外套——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由于这一年要参加竞选,议员的竞选团队不遗余力地想把他跟阿维娃划清界限。
她被刻画成了洛丽塔似的实习生、莱温斯基第二,被人扣上各种帽子,都是“荡妇”的同义词。
阿维娃的博客更帮了倒忙,因为里面详细记录了那几个月她为国会议员工作的经历。
当时是2000年,当我得知阿维娃在写博客的时候,我连“博客”是什么都不知道。
“博客?”我对阿维娃吐出这个陌生的词,“那是什么?” “就是网络日志,妈妈。
”阿维娃说。
“网络日志,”我重复道,“什么是网络日志?” “就是日记,”阿维娃说,“是写在网上的日记。
” “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写日记?”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日记?” “都是匿名的。
我从不用真名,而且没出事以前我只有两三个读者。
我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好理清头绪。
”她说。
“那你倒是买个日记本啊,阿维娃!” “我喜欢打字,”她说,“而且我写字不好看。
” “那你就在电脑里建个文件夹,存一份文档,起个名字叫‘阿维娃的日记本.doc’。
” “我知道,妈妈。
我知道。
” 阿维娃的博客叫“只是个普通国会实习生的博客”。
正如她所说,她没有用他或是自己的真名,可即便这样,人们还是猜到了作者。
一时间,破译阿维娃的博客成了风靡南佛罗里达的消遣方式。
她也曾试过删除博文,却删不干净。
这个博客就像个杀不死的僵尸,她这边删掉了博文,它们又在那边冒了出来。
时至今日,若你仔细搜寻,兴许还能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发现它。
说实话,我也读了她的博客——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
有些内容我只是一扫而过,不过说实话,除了那些香艳的部分以外,这其实是个很乏味的博客,即使是那些香艳的内容,也并未给我带来丝毫欢愉,那感觉就像我和罗兹所在的读书会组织阅读《O的故事》一样。
由于媒体时常骚扰她的同学,阿维娃不得不暂时从迈阿密大学休学。
她搬回家中,默默等待事情平息的那一天。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必须承认,茂林会所的门禁系统功不可没。
媒体没法在我家门口的草坪上设伏,便只好在大门外蹲守,等着我们出门。
罗兹一直给我们送吃的,餐食之丰富,仿佛我家有病重或过世的亲友一般——面丸子汤、或甜或咸的糕点、黑麦面包做的牛舌三明治、整条的哈拉面包、百吉圈、冷熏三文鱼、鲱鱼和节日时才吃的三角糕。
说起三角糕,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讲。
离学年结束还有一个星期时,巴尼拉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无花果馅的三角糕。
“瑞秋,吃块三角糕吧。
”他说。
“不用了,谢谢。
”我说。
我一向不爱吃三角糕,因为我总觉得里面的水果馅料不够足,饼干的部分又太干。
“别客气,瑞秋,拿着吧。
我母亲每年会烤两次三角糕,她为这件事总要忙前忙后。
她有独家食谱,而且她现在得了肺癌,这很可能是哈莉特·格林鲍姆做的最后一批拿手三角糕了。
” 我向他慷慨的馈赠表示感谢,但我说这块三角糕送给我就是浪费,并且把自己对三角糕的看法告诉了他。
但他还是坚持要我收下,于是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说实话,它真的非常美味。
水果馅料很足,而且一点也不干。
她肯定用掉了一整块黄油。
三角糕又香又甜,我几乎忍不住快要呻吟出声了。
“瑞秋,”他说,“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辞职。
” 我嘴里正嚼着三角糕,急需要一杯饮料,但是并没人给我递饮料。
我嚼了差不多二十下,才把三角糕咽下去。
“为什么?”我问。
其实我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过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一定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阿维娃的丑闻,这对我们影响不好。
” “可是,拉比,”我说,“卷进丑闻的人又不是我,是我女儿。
她已经成年了,是个独立于我存在的成人。
我没法控制她的行为。
” “我很抱歉,瑞秋。
我同意你的意见。
问题不在于阿维娃的桃色新闻,而是那次筹款活动。
董事会觉得你在去年为议员先生举办的筹款活动有损你的声誉,看上去不太恰当。
” “我当时对这件事并不知情!”我说,“再说筹款活动又不是我牵的头。
你要记住,我当时并不想牵扯进去。
” “我记得,而且我也相信你,瑞秋。
我相信你,但在外人看来就是这样。
” “我为这所学校奉献了十二年的人生。
”我说。
“我知道,”拉比说,“这件事很倒霉。
我们希望你的离开不会兴师动众,你可以说自己想辞职是为了多陪伴家人,你今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换成谁都会理解的。
” “我才不说!”我说,“我不会撒谎的!”我手里还剩下半块三角糕,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扔在拉比脸上。
费舍那个傻瓜去年朝我扔了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派,我突然在想,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传统,每一任校长离职时都会气得扔糕点。
“有什么好笑的吗?”拉比问。
“一切都很滑稽可笑。
”我说。
“好吧,你回去睡一觉,好好考虑一下。
” “我不需要考虑。
” “好好考虑一下,瑞秋。
我们不想主动解雇你,因为谁也不想引起更多的丑闻。
要是你主动辞职,起码还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
” 考虑了一夜,我辞职了。
我收拾完办公桌,开车穿过城区,来到国王大道上一幢低矮的粉红色公寓楼,按响了M.崔的门铃。
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是谁,我说是送货员,那女人说她没有什么货要收,我说送来的是花,那女人问是谁送的花,我说是格罗斯曼医生,那女人便开门让我进去。
我爬上楼梯,M.崔已经打开了门。
她穿着护士服——不是性感的护士服套装,而是带荧光色几何图案的蓝色工作服。
我丈夫的情人说:“你好,瑞秋。
我猜迈克并没有给我送花。
” 我说:“迈克不是那种会送花的男人。
” “对。
”她说。
我说:“我今天被炒了。
” 她说:“真抱歉。
” 我说:“今年过得很糟糕。
” 她说:“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抱歉。
阿维娃的事,还有其他的事情。
”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 “你想喝杯茶吗?”她说。
“不想。
”我说。
“我正好在沏茶,水已经烧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
请坐。
”她说。
她走进厨房,我在她的客厅里四处闲看。
她摆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一只猫的照片、另一只猫的照片。
她只有一张迈克的照片,不过那是她和迈克所在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合影,迈克甚至都没站在她身边。
她端着茶走回房间时,我还在端详那张照片。
我把相框放回壁炉上,但我知道她看见了我在看那张照片。
“你要加糖吗?”她问,“牛奶?” “不,”我说,“什么都不加。
” “我喜欢茶里带一点甜味。
”她说。
“我喜欢甜品里含糖,”我说,“不过在其他时候我都尽量不吃糖。
” “你可真苗条。
”她说。
“我一直努力保持身材,”我说,“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有个怒火中烧的胖女人。
” “你是怎么把她装进去的?”这位第三者问我。
“你真幽默。
”我说,“我没想到你是个幽默的人。
” “为什么?”她说。
“因为我也很幽默。
”我说,“假如他需要幽默感,他完全可以留在家里。
” “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幽默的。
”她说,“过去我对他满心敬畏,不敢太幽默。
” “敬畏迈克?真有意思。
”我说。
“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二十五岁,而他威信过人、事业有成。
我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会看中我。
” “你现在多大?”我问。
“今年三月刚满四十岁,”她说,“把茶包拿出来吧,茶叶泡太久会变苦的。
” 我照做了。
“十五年了。
”我说。
“泡了十五年的茶叶,肯定会变苦的。
”她说。
“我是说,你和迈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感觉很糟糕,而另一半时间,我在纳闷自己的人生都去哪儿了。
”她说。
“我明白,”我说,“不过你还年轻。
” “对,”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至少处在中游,”她长长地望了我一眼,“你也是。
” “你不必故作体贴。
”我说。
“我不是在故作体贴。
我是想说,尽管表面看上去不太像,但阿维娃其实很幸运,这件事现在就公之于众,而不是十五年以后才曝光。
她还有别的选择。
” 我打了个喷嚏。
“上帝保佑,”她说,“你感冒了吗。
” “我不生病,”我说,“从不生病。
” 我又打了个喷嚏。
“不过我很累。
”我说。
她说她冰箱里还有些丸子鸡汤。
“是我自己做的,”她说,“你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 我并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让丈夫的情人给我做鸡汤,但我突然觉得疲惫不堪。
她的公寓很小,不过温馨整洁。
我心想,不知她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想象她梳洗打扮,准备跟我丈夫约会的情形,为了他涂上口红,擦脂抹粉。
我想象她年轻时一直盼着阿维娃长大,这样迈克就可以跟我离婚了。
我为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哀。
她端来的汤盛在一个漂亮的代尔夫特蓝陶碗。
我喝了汤,立刻觉得有所好转。
鼻子通了,喉咙也不再肿痛得厉害。
“你看,”她说,“鸡汤可不仅仅是老女人的鬼扯。
” “我讨厌这种说法,”我说,“老女人的鬼扯。
” “不好意思。
”她说。
“没事,不怪你。
我只是觉得仔细想想,这句话不仅尖刻,还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难道‘老女人的鬼扯’就一定不可信,就没有科学根据吗?‘老女人的鬼扯’其实是在说,不必理会那个愚蠢的老女人说的话。
” “我从前没想到这层含义。
”她说。
“我从前也没想到这层含义,直到后来自己变成了老女人。
” 三个月之后,恐怖分子将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阿维娃门就这样结束了。
人们不再谈论这桩丑闻,新闻的车轮滚滚向前。
那年冬天,阿维娃大学毕业了。
她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大学办公室里接过了毕业证书。
那年春天,她申请了几份工作。
她想继续在政府部门或者政治领域工作,可是在南佛罗里达,人人都对她有所耳闻,并且不是什么好名声。
即便是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只要在谷歌一搜,这事也就泡汤了。
她转变择业方向,在公关、市场营销领域找工作,以为这些行业的雇主不会像政府部门那么——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说法是“把道德奉为圭臬”。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得承认,对于她当时的处境,现在的我比当时的我更有同情心。
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让她从家里搬出去,重整旗鼓,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那年夏末,她彻底放弃了。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漂在家里的游泳池里,任由皮肤晒成深棕色。
“阿维娃,”我说,“你涂防晒霜了吗?” “没有,妈妈,没事。
” “阿维娃,你这样会把皮肤晒坏的。
” “我不在乎。
”她说。
“你应该在乎!”我说,“你只有这一身皮肤。
” “我不在乎。
”她说。
她在读《哈利·波特》。
我记得当时出版了四册,但我不太确定。
我知道成人也会读《哈利·波特》,但我把这看成一种不好的预兆。
那些书封面上画着卡通小巫师,在我看来太过幼稚。
“阿维娃,”我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看书,要不要考虑申请读研究生?” “哦,是吗?”她说,“谁愿意给我写推荐信呢?哪所学校不会到网上搜索我的背景呢?” “那你可以申请法学院。
很多背景复杂的人都去读法学院。
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个被判了刑的杀人犯通过函授学习法学课程,想为自己翻案。
” “我又不是杀人犯。
”她说,“我是个荡妇,这种罪名没法翻案。
” “你不能永远泡在游泳池里。
” “我不会永远泡在游泳池里,我要漂在游泳池里,而且等我读完第四遍《哈利·波特与密室》,就去洗个澡,然后读第四遍《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 “阿维娃。
”我说。
“你自己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阿维娃说。
我接下来做的事很不光彩。
真的很不光彩。
我之前从没打过孩子。
我走进泳池,用腰带系住的夏季羊绒薄开衫沾了水,在我身边的池水里翻腾。
我把浮床从她身下抽出来,《哈利·波特》和阿维娃一起掉进了游泳池。
“妈!”她尖叫起来。
“给我从这个该死的游泳池里出来!”我大喊。
《哈利·波特》沉到了水底,她手脚并用爬回浮床上,于是我再次把它从她身下抽开了。
“妈!你能不能别这么贱!” 我给了她一记耳光。
阿维娃的表情坚如磐石,但紧接着鼻头开始泛红,她哭了起来。
“对不起。
”我说。
我的确感到很抱歉,我想抱住她,她先是挣扎,但很快便任由我抱住她。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疯了,妈妈,”她说,“他真的爱过我,是不是?” “是,”我说,“我想他可能真的爱过你。
”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她那时患上了抑郁症。
我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寻求建议。
“你对待她更像是朋友,而不像个母亲。
”妈妈说。
“好吧,”我说,“我怎么才能改变呢?” “让她从家里搬出去。
”她说。
“我不能那样做,”我说,“她到处受排挤。
她没有钱,也没有工作。
她靠什么生活?” “她有手、有脚、有头脑。
她会想出办法的,我向你保证。
” 我不忍心那样对待阿维娃。
“别再为阿维娃担心了,”妈妈说,“多为你自己的生活留点心。
总会有出路的,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
” 不过几个月以后,阿维娃真的搬走了。
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给我留下地址。
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她每年会给我打一两次电话。
我好像有了一个外孙女。
没错,在我看来这是件伤心事。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当真咬春饼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夜行歌紫微流年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春日颂小红杏
- 怀了队友的崽怎么破西山鱼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综]混沌恶不想算了!安以默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射雕英雄传金庸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御佛o滴神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穿成废材后他撩到了暴躁师兄是非非啊
- 玫瑰帝国6·辉夜姬之瞳步非烟
- 锦帐春慢元浅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眼泪酿宴惟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网恋同桌归荼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鱼游入海西言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球”嗨夕尧未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情终孤君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如何才能将目标勾引到手南柯良人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动物爱人魏丛良
- 恶魔总监:亿万独宠小男友浔弦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竹木狼马巫哲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他只是我男朋友廿小萌
- 被影帝碰瓷后[娱乐圈]唤舟
- 意外招租而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