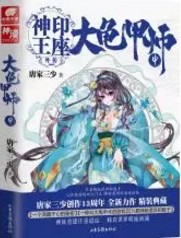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II 无论你去哪儿,你做过的事都跟着你(1/3)
简 1 在一段政治风波不断的日子里,我梦见了阿维娃·格罗斯曼——她是佛罗里达版的莫妮卡·莱温斯基。
除了那些在世纪之交居住在佛罗里达的人以外,也许没人记得她。
那则新闻曾在短时间内登上了全国头条,因为阿维娃·格罗斯曼竟然傻乎乎地写过一个匿名博客,在里面详细记述了那段婚外情的“精彩片段”。
她从未提到过男方的姓名——可所有人都猜得到是谁!有人推测阿维娃早就想让人知道这件事,不然她干吗要写这个博客?可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她只是年轻莽撞,而且人们当时对互联网尚不甚了解——话说回来,他们现在也不太了解。
好吧,说回阿维娃·格罗斯曼。
阿维娃是个二十岁的实习生,与迈阿密的众议员亚伦·莱文有了私情。
按照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吞吞吐吐的说法,他并不是阿维娃的“直属上司”。
“我从来都不是该女子的直属上司,”莱文议员说,“我固然要为自己造成的伤害向我深爱的人道歉,特别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们,但我敢保证,我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 “该女子”!他甚至连直呼阿维娃·格罗斯曼名字的勇气都没有。
那桩私情的细节通过当地每一个新闻频道、每一份报纸被公之于众,足足有几个月——其中的内容有多肉麻、多俗套、多展露人性,你尽可自行想象。
有家电视台甚至开辟了个新版块,叫《阿维娃瞭望站》,仿佛她是一场飓风,又仿佛她是一头莫名其妙在沙滩上搁浅的虎鲸。
十五年过去了,莱文仍然在国会任职,而阿维娃·格罗斯曼空有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和西班牙语文学的双学士学位,拥有一个在谷歌无法删干抹净的博客,还有一段臭名昭著的实习经历,求职无门。
人们没有在她胸前“戴”上红字,但他们根本不必那样做,因为互联网就可以替他们做到。
不过,我梦里的阿维娃·格罗斯曼早已摆脱了这件事的影响。
在我的梦境中,她四十多岁,梳一头干练的短发,身穿中性色调的套装,戴一条样式抢眼的绿松石项链,参加国家级政治职务的竞选,不过我在梦里并不确定她竞争的是什么职务。
我隐约觉得是国会,但那也巧得太有诗意了。
不过这毕竟是我的梦,所以暂且当作是国会吧。
总之,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起了那场私情。
起初,阿维娃给出的回答是政治人物的标准答案——“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于我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我感到很抱歉。
”——她的答案与莱文议员不无相似。
记者继续追问。
“好吧,”阿维娃说,“如今处在这个年龄、这个职位,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绝不会与自己竞选团队里的实习生发生关系。
但是当我回顾过去,反思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和行为,我只能说……只能说我当时太浪漫,也太年轻了。
” 2 我叫简·扬,三十三岁,是一位活动策划人,不过我策划的活动主要是婚礼。
我在南佛罗里达长大,但我现在住在缅因州的艾力森泉,离波特兰大约二十五分钟车程,这里在夏季是个著名的旅行结婚目的地,到秋天热度减退,入冬后则更显冷清,但我仍能维持生计。
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喜欢我的工作,还有,不,我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一行。
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用在工作上,但我发现自己具备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天赋——人际沟通、心理学、政治、舞台表演、创新力等等,都是策划婚礼所需的才能。
哦,我还有一个少年老成的八岁女儿,露比,她的父亲则不在我们母女生活之中。
露比聪明过人,但她过早地与新娘们接触,这对她并无益处。
上个星期露比告诉我:“我永远都不想做新娘。
她们都很惨。
” “没那么夸张吧,”我说,“有些人看上去还是挺幸福的。
” “不,”她坚定地说,“有些人比看上去还要不幸。
” “不幸的新娘各有各的不幸。
”我说。
“我猜你说得对,”露比皱着眉头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向她解释,我不过是挪用了托尔斯泰他老人家的名言而已,露比翻了个白眼,说:“拜托你认真一点。
” “这么说,你永远都不想结婚?”我说,“这对我的生意可没什么帮助。
” “我没那么说,”露比说,“我不确定我将来会不会结婚,我才八岁。
但我知道我不想做新娘。
”露比现在的年纪刚刚好,她能和你正常交谈,说话又不像个青春期的孩子。
她有点书呆子气,身材圆滚滚,容貌可人。
我真想把她一口吞掉,或者咬住她肉乎乎的胳膊。
即便如此,我从不谈及她的体重,因为我不想给她种下心结。
我在她这个年纪时也偏胖,而我母亲总是没完没了地讨论我的体重。
没错,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如今的我自豪地拥有好几个心结。
不过谁还没有几个心结呢?细想下来,人不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创造出的个体吗? 3 我的店面位于镇上的繁华地带,被一家文具店和一家巧克力专卖店夹在当中。
时值十一月,生意冷清,给几位春夏季的客户做完回访以后,我整个上午都在网购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一个女人究竟要有多少条黑色直筒连衣裙才够穿?假如你是我,答案是“非常多”,我最后一次清点数目时是十七条。
婚礼策划人在婚礼上总是穿得像参加葬礼一样。
我正在琢磨露比那番“每个新娘都很惨”的言论,弗兰妮和韦斯走进了我的店门。
他们没有提前预约,不过在这个时节,他们也没必要预约。
弗兰妮全名叫弗兰西丝·林肯,二十六岁,却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
她容貌娇美,可是不知怎的,总给人一种面团没发酵好的感觉。
她是名幼儿园老师——这还用说嘛!世上实在找不出比她长得更像幼儿园老师的人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休假。
韦斯的全名是韦斯理·韦斯特——就凭他这个名字,我推断他的父母很不讨人喜欢,不禁想见识一下这两位是何方神圣。
韦斯是名房地产经纪人,他告诉我,他的办公室离我的门店很近,不过我之前从没见过他。
他说他有志于从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那语气像是在谋划一件大事,他似乎觉得我既然要为艾力森泉未来的大人物策划婚礼,就不应该对此毫不知情。
他二十七岁,握手用力得过了头——兄弟,你装模作样给谁看呢?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客户,这两位也算不得与众不同。
婚礼总能让人不知不觉就落入旧观念里丈夫和妻子的窠臼。
“我们本想雇个城里的策划人。
”韦斯说。
“城里”指的是波特兰,话里透着瞧不起人的意思。
“我就是城里长大的。
”我面带微笑地说。
“但我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找个本地人呢?我是说,我每天都会路过你的办公室,这里装扮得很漂亮,你把一切都布置得非常整洁、雪白,我很喜欢。
而且,因为我想参与市议会的竞选,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本地的生意,也就是我的选民,你懂的。
这个季节你的生意恐怕有些冷清吧。
” 我问他们有没有确定日期。
他看看她,她也看看他。
“我们想一年后结婚,明年十二月,”她说,“这样时间够吗?” 我点点头:“足够了。
” “她觉得冬季婚礼很浪漫,”他说,“但我更看重它的性价比。
我们可以随便挑地点,而且价格只有夏季的一半,我说得对吧?” “不是一半,不过的确会便宜很多。
”我说。
“冬季婚礼就是很浪漫,你不觉得吗?”她说。
“我同意。
”我说。
新娘和伴娘往往冻得半死,而且,要是遇上雪天,外地宾客有一半都不会来。
我想这多少带些捉摸不定的浪漫色彩。
不过,冬季婚礼的照片总是效果绝佳,而且我觉得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比婚礼本身更加深刻。
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大人了,我可不会说错话,白白断送一单冬季的生意。
4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可能是他们去拜见过大城市里的婚礼策划人之后——他们约了第二次到店时间,跟我签合同,再付一笔定金。
这次来的只有弗兰妮自己,这其实没什么不寻常的,不过他的缺席倒让弗兰妮十分尴尬。
“这样古怪吗?”她问,“这看起来是不是不太好?我是说,他也应该来,对不对?” “一点儿也不古怪,”她把支票递给我的时候,我说,“到头来我经常只跟夫妻中的一方沟通得比较多。
毕竟谁也没有分身术。
” 她点点头:“他在带客户看房子,”她说,“什么时候看房子不总是他说了算。
” “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说,“他是怎么向你求婚的?我好像没问过你。
”我把她的合同放进了文件柜。
“哦,那浪漫极了,”她说,“浪漫”是她的口头禅,“起码我觉得很浪漫。
不过等我讲给你听,你也许会觉得很古怪。
”“古怪”也是她的口头禅。
他是在她母亲的葬礼上向她求婚的。
不是葬礼中途,而是葬礼刚刚结束后。
我估计是在公墓的停车场,但我并不确定。
她悲痛欲绝,哭个不停,鼻涕眼泪流了一脸,这时他单膝跪地,说了一番话,大致是“好了,这不该是你这辈子最悲伤的一天”。
真让人反胃。
不过,我猜他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这目前仍然是让我对他印象最差的一件事。
有没有搞错啊,有些日子就应该是你这辈子最悲伤的一天。
再说,让她在母亲刚去世时就作出重大的人生决策真的好吗?我并不了解这两个人,但听上去他好像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乘虚而入了。
我不禁有点开始讨厌韦斯·韦斯特。
只是稍微有点讨厌,而且才刚开始。
合作到最后,我通常都会讨厌新郎,不过一般没这么快。
“哦,这太古怪了,”她说,“这很古怪,是不是?” 这不是古怪,而是糟透了。
这件事糟透了,可它又是件寻常事。
我并不了解她,何况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半是为了填补这段时间,半是为了避免我的想法从脸上流露出来,我做了一个完全不像我的举动。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了她的手:“关于你母亲的事,我非常抱歉。
” 她的嘴唇颤抖起来,蓝色的大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哦,天啊,哦,天啊。
”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我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她说。
“不,你失去了亲人,”我说,“你一定感觉非常无所适从。
” “对,就是这种感觉,无所适从。
你的母亲还健在吗?”她问。
“健在,但我们很少见面。
”我说。
“那太糟了。
”她说。
“我也有个女儿,”我说,“所以我能想象这样的——” “那你母亲也不想见她吗?她的亲外孙女?我不敢相信!” “也许她想见吧。
我们的关系很复杂。
”我说。
“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弗兰妮对我微微一笑,“我管得太多了,”她说,“对不起。
你对人很亲切随和,所以我忘了我们并不熟。
” 她是个好人。
“你们做作业了吗?”我之前让他们回去做个展示板,描绘他们梦想中的婚礼。
她从包里掏出平板电脑。
他们拼贴出了穿牛仔靴的新娘和穿燕尾服、系阿斯特领巾的新郎;馅饼自助宴和七层的婚礼蛋糕;一个装满非洲菊的铁皮桶和一个百合、玫瑰组成的三尺高的花台;红色格子桌布和雪白的亚麻桌布;烧鸡和菲力牛排。
这简直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的婚礼。
“我们还没想太多,有些是他的想法,有些是我的想法。
” “看得出来。
”我说。
“他希望氛围高雅一些,但我更想要乡村风格,”她说,“你能帮帮我们吗?还是我们彻底没救了?” “你们彻底没救了。
”我说。
弗兰妮大笑起来,脸也红了:“我们为此算是吵了一架。
只是很小的一架。
他说我的品位太寒酸,”她说,“但我想让宾客们放松、自在一点。
我不希望办得——”她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阵词汇,最后作了决定,“商业气息太重。
” “优雅而质朴的风格,让我想想。
可以在谷仓里装上大吊灯,铺上白色桌布,既然是在十二月,可以给广口玻璃瓶扎上红白相间的格子布彩带,装进满天星,配上松树枝条、粗麻布,布置成干净利落的舞会大厅的样式。
在舞池上扯起闪烁发光的圣诞节小灯,宾客的座位卡则写在迷你小黑板上。
天棚用薄纱覆盖,餐巾用白色的亚麻布,餐食是烧烤和馅饼,再生一丛熊熊燃烧的篝火。
没错,那个场景几乎就在我眼前。
”而我眼前的确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最近每个人都想要优雅质朴的风格。
“听起来很美。
”她说。
门铃响了一声,露比走进店里,把书包扔在地上。
“这是我的助手。
”我告诉弗兰妮。
露比和弗兰妮握了握手。
“我叫弗兰妮,”弗兰妮说,“你这么年轻就当上助手了。
” “你太客气了,不过我已经五十三岁了。
”露比说。
“她保养得非常好。
弗兰妮想要一场既优雅又质朴的婚礼。
”我告诉露比。
“你应该有一辆冰激凌车,”露比说,“妈妈策划过一场带冰激凌车的清新复古风格婚礼。
所有人都喜欢冰激凌车。
” “在办公室里不能管我叫妈妈,”我说,“你应该叫我老板。
” “所有人都跑到停车场去了,”露比继续说,“他们想要什么冰激凌都可以免费挑选。
这差不多是天下最大的好事。
” “的确很好,可是弗兰妮的婚礼在十二月。
”我告诉露比。
“是的,”弗兰妮说,“不过这听上去太有意思了。
我们能不能在十二月也这样做呢?反正也不是一到十二月就没人吃冰激凌了,在十二月找辆冰激凌车来反而更有趣。
比方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拥抱寒冷吗?”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韦斯的电话,告诉我他对冰激凌车这件事“无法理解”。
“我认为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愚蠢,”他说,“我邀请的客人中有些人以后可能要为我投票,还有的可能要为我的竞选出资,我不希望我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在冬季婚礼上安排冰激凌车的人。
” “好吧,”我说,“不要冰激凌车。
” “我不想扫大家的兴,但这种做法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 “不负责任,”我说,“这话说得有点重了。
” “就是不负责任,”他说,“考虑不周全,脑筋一团乱。
我很爱弗兰妮,但她有时会冒出些想法来。
” 没错,我心想,她长了个脑子,长了脑子就有产生想法的风险。
“你明显反对这种安排,”我说,“说实话,我们目前只是在头脑风暴,韦斯,并没有真的租下冰激凌车。
” “好吧,问题是,”韦斯说,“你能不能告诉弗兰妮,就说你在冬天没法租到冰激凌车?因为她现在打定主意想要冰激凌车,她觉得这样很别出心裁,我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 “如果你亲自告诉她你不喜欢,这样不是更简单吗?我是说,她的确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我觉得这对她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她喜欢的事物很多,她是个开朗的人。
” “对,”他说,“对,我觉得应该你去说。
如果是我说,我就成了那个在婚礼上扫兴的人。
如果是你说,那就只是一个事实:婚礼策划人在十二月找不到冰激凌车。
” “但我很可能能把冰激凌车找来。
”我说。
“好吧,那是自然,但是弗兰妮不必知道这一点。
”韦斯说。
“说实话,向你的未婚妻撒谎,这样做我心里不太舒服,”我说,“我尽量从不向客户撒谎。
而且在我看来,无论我们两个谁去说,都没必要为了冰激凌车这样无关紧要的事情撒谎。
” “既然是无关紧要的事,谁去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这也不算真的撒谎,我付钱要你提供服务,你只是在按照雇主的意思行事,”韦斯说,“我对你有信心,简。
” 我很想告诉这个窝囊废,他大可以到别处去寻求服务,但我没有那么做。
我之前没说,不过我那个可爱的书呆子女儿露比在学校时常受人欺负。
凡是孩子受人欺负的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做过,我跟学校的管理人员见过面,跟其他的家长通过电话,留意她在网上的行为,还为露比报名参加了各种据说可以树立自信心的课外活动——体操!童子军!来者不善的对策,我全都跟露比讨论过,全都没用。
我在考虑让她转学到私立学校去,但那需要很多钱。
缺钱就意味着你没有资格挑三拣四,只跟自己喜欢的人共事。
“简,”他说,“就这样说定了?” “好。
”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我绝对不会给这个人投票,而且,但凡他参加某个职位的竞选,我还要奔走游说,拆他的台。
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婚姻。
我没有对弗兰妮撒谎。
我说我又想了想,觉得在冬天伴随冰激凌车而来的后勤保障很麻烦。
而且,说实话,的确是这样。
仅仅是取大衣、还大衣这一件事就已经是一场噩梦了。
5 “可以,”弗兰妮说,“我也只是突发奇想。
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知道我们基本敲定了用广口玻璃瓶盛放百叶蔷薇,我也非常喜欢这种设计,不过我想问问你对兰花有什么看法。
” “兰花?”我说。
“是这样的,”她说,“我看见你的窗台上有一株兰花。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永远都不会死。
我每次到这里来,它看上去总是和原来一模一样。
而且,我也说不清楚,它让人感觉很平和,很有家的感觉。
” 我从没听过有人评价兰花有家的感觉。
“它们也会死,”我说,“不过只要你坚持浇水,它最后总能起死回生。
” “哦,我喜欢这样,”她说,“我不知道它跟优雅质朴的主题是不是相配——” “什么东西都能搭配这个主题。
”我说。
“我在想,能不能用兰花盆栽做花台,这样人们就可以把花带回家。
那样一定非常高雅,而且还很……怎么说呢?” “质朴?”我接过她的话。
“我其实想说‘绿色’。
这一点对韦斯和我都很重要。
好吧,至少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也说不好,可能是因为它看上去比百叶蔷薇更有特点吧。
” 我带弗兰妮去了席勒的花店。
每当客户夫妇想要不同寻常的花卉,我总是去找埃略特·席勒。
他是我见过最一丝不苟的花商。
我不会用“花卉艺术家”形容他,因为这个词略带调侃的意味,不过,用“艺术作品”来形容席勒的花毫不为过。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略带点偏执,卖的花价格也不便宜。
席勒说:“冬季婚礼?唯一的难题是怎样把它们用卡车运到礼堂。
兰花很怕冷。
” “那客人还能把它们带回家吗?”弗兰妮说。
“能,只要你告诉客人,不要在停车场磨磨蹭蹭就好。
而且我可以打印一些养花指南做成小册子。
你知道的,多长时间浇一次水,浇多少水,什么时候开始施肥,在哪里剪枝,怎样换盆,怎样选土,日照时间。
弗兰妮,你知道吗?兰花喜欢让人摸它们的叶子。
” “真有灵性。
”她说。
“我从来不摸我的兰花的叶子。
”我说。
“那我敢打赌,你的兰花一定很郁闷,简。
”席勒说。
“兰花都有哪些种类呢?”弗兰妮问,“简有一盆白色的,我很喜欢。
” “简那盆是新手养的蝴蝶兰,很普通,在路边摊就能买到。
我没别的意思,简。
我们可以用那种花,没问题。
不过兰花有上千种,你不应该刚看见第一种就马上选定。
” “嘿,席勒,”我说,“你说的可是我养的兰花,我从大学时就开始养它了。
” “那盆兰花很不错,简,它非常适合刚开始养花的人。
不过这可是婚礼,是年轻人开启新生活的时刻!我们应该更加用心才对。
”他拿出了兰花的大文件夹。
她选了白拉索兰,看上去像一簇纤柔的马蹄莲。
“啊,”席勒说,“夜夫人。
” “它真的叫这个名字吗?”我问,“还是你自己给它起的古怪昵称?” “它每到晚上就会散发出香气,”他说,“别担心,弗兰妮。
它的味道很好闻。
” 席勒说他会估个价。
过了几天,他把报价单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起送来的还有一株兰花——花朵是紫色的,叶子有点像竹笋,还有一张便条:“我的名字叫迷你石斛兰。
我想和你的路边摊蝴蝶兰交个朋友。
他虽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他很孤独,希望有人能跟他做个伴儿。
”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的蝴蝶兰是女孩。
” “我可不这么想,”他说,“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你这是性别偏见。
并不是每一朵花都是女孩。
” “我也没那么说。
我只是说我的花是女孩。
花朵也分性别吗?” “你高中没上生物课吗?”席勒说。
“我没认真听讲。
” “真可惜。
有些花朵只有一种性别,有些则有两种,得一株株、一朵朵地观察才行。
而且准确地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春日颂小红杏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末世对我下手了一把杀猪刀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我就是馋你信息素[娱乐圈]夂槿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虫屋金柜角
- 失忆后我招惹了前夫萝卜兔子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锦帐春慢元浅
- 剑海鹰扬司马翎
- 武极宗师风消逝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网恋同桌归荼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鱼游入海西言
- 夕照斑衣白骨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循规是笙
- 非典型NTR一盘炒青豆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夕照斑衣白骨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新婚ABO白鹿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404信箱它在烧
- 老大,你情敌杀上门了沐沐不是王子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他只是我男朋友廿小萌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单恋画格烈冶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情敌五军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影帝是棵小白杨闻香识美人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
- 竹马危机萧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