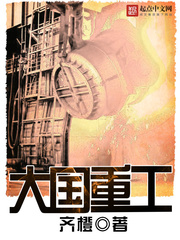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民国廿一年•夏•北平(2/3)
“姊!” “唔?”红莲应,志高神魂甫定,只好问道:“姓什么的?” “姓巴。
” “巴?”志高笑,“长得没有巴掌高的‘巴’?” “别缺德了。
” “好怪的姓,没我的姓好。
” 红莲不知心里想着什么,忽而柔柔牵扯一下。
踌躇着,好不好往上追溯?只是她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
一个男人不要一个女人,她往往是在被弃之后很久,方才醒过来,但没明白过来。
这世界阴沉而又凄寂,仿佛一切前景转身化作一堵墙。
“你姓好,命不好。
”红莲对志高道,“我是活不长了,只担着心,不知你会变成个什么样儿的。
唉。
” “过一天算一天,有什么好担心?别说了。
”志高不愿意重复方才刁刁叨叨,束手无策的话儿。
他最拿手的功夫是回避,马上想以一觉来给结束了前因后果。
红莲喊他进房里,他道: “我睡这。
”指指墙角落儿。
有意地不沾床边。
“睡床上吧?”红莲又赔着笑,也不勉强,“要不我也躺一会。
” 好久没逮着这般的机会了,红莲像有好多话,待说从头。
母子一高一下地对躺,稀罕而又别扭。
志高一蜷身子面壁去。
“我也不想修什么今生来世。
前一阵,四月八日不是佛祖过生日吗?庙里开浴佛会呢,我去求福了。
我没敢进去,只在外头求,诚心就灵了。
我求佛祖指点你一条明路——” “不管用,狗头上插不了金花。
” “你会有好日子的。
” “好好好,要我有好日子,那你就不干这个了——”志高没说完这话。
说不下去。
哪有什么好日子?漫漫的一生,起步起得冒失,都是命,跟个灯篓风儿似的,一点儿囊劲也没有。
比一个卖身的女人更差劲。
志高想,唉,烂眼睛又招苍蝇,总之是祸不单行。
红莲倒是捡了这话:“说真格的,要是不干这个,也不致饿死,我是对你不起。
” “你倒是让多少个男人睡了?”志高冒猛地回身问她。
红莲正思量该当怎么回答。
志高再问了:“你倒是让多少个男人睡了?” “怎的问起这个来呢?” 红莲迟暮的眼睛垂下来了,垂得几乎是睡死了,嘴角那微弯却是根深蒂固的,看清楚,原来这是天生的“笑嘴”。
红莲也没看志高。
儿子盘问起她的堕落经来了。
“志高,”她只得淡淡地道,“你长大了,难道不晓得,我只跟‘一个’男人睡了!要不怎么有你呢?也许,你是到死都不原谅我,那由你——” “姊——” “哎,没人,你就别喊我姊!” “不,喊着顺溜了,改不了。
”志高试探: “那姓巴的,瓜子儿巴,对你倒是不错吧?” “都是买卖嘛,零揪儿的。
”红莲道,“别胡说了。
” 志高马上拿腔儿,装得欢喜轻松。
“喏,你当是为了我,别当为自己,对吧?你瞧你,擦了这许多的粉,还干巴疵裂的,打了这么多的褶子。
嗳,再过一阵,穿得花巴棱登的,都不管用——” “你看你这张损人的嘴——” “不呢,我说的是真心话,你要是专门侍候一个,你想呢,哈,要不知道是谁得了美。
我们都是断了腿的蛤蟆了——跳不了多高,我又没办法养活你……” 才在笑,打哈哈,志高没来由一阵心酸,这样的话,不知是什么话,志高说着,缓缓地把脸别过墙去。
转一下身,轻轻打个呵欠,再用手掌掩一掩嘴,手顺势往眼角一抹,就这样,把那将要偷偷窜出来的泪水不经意地、也不着迹地,给抹掉了。
“我困了。
”再也不打话。
红莲看不出什么来: “不再聊一阵?”好不容易母子聊了一阵话,他竟又困了。
志高一睡,解了千古忧困。
黄昏时分,丹丹一个人来了。
志高还没有醒过来呢。
丹丹摇晃他,唤:“切糕哥,天亮了,起来了!” 他接近软化的四肢,开始有点知觉,腰酸背疼的,也不知睡了多早晚,太阳确已西下,还是熬人的,背上也就汗濡一片。
志高擦擦眼睛,又醒过来了,以为是一天了,谁知还没过去。
见着丹丹,只一个人,问: “怀玉呢?” “还说呢,唐叔叔生气啦,骂你,怀玉帮他收拾烂摊子,还不巴巴地跟着回家去?” 志高听了,口鼻眼睛都烦恼得皱成一团,像个干瘪老头儿,无限地忧伤。
怎么解决呢? 只好把汗臭的上衣给换了,披件小背心,领丹丹出来。
回头跟红莲道: “姊,我走了。
” 红莲眼看一个大姑娘,跟自己儿子那么地亲近无猜,心中不无拈酸醋意,到底是什么人?她一来,他就待不住了?也是个吃江湖饭的标致娃儿,轻灵快捷,几步就蹦出胡同口了。
红莲目送二人走远。
“你姊真怪,不笑也像笑样。
嗳,她瞪着我看,好愣,你姐怎么这么地老?那你娘不是更老了吗?你没娘,对吧?” “丹丹——” “什么?” “没什么了。
”志高回心一想,急急地说了,怕一迟疑,又不敢了,“丹丹,我还是告诉你吧,瞒下去是不成的,反正你迟早都会知道,我非卷起帘儿来唱个明白——” “你说吧,啰里啰嗦的,说呀。
” “好,我说。
”志高坚强地豁出去了,“刚才的,就是我娘。
” “哦?怪道呢,这么地老。
” “她是我娘,因为——她干的是‘不好’的买卖,管我喊她姊……我此后也是喊她姊的。
你就当给我面子,装作不知道。
怀玉也是这样的。
” “好呀。
” “答应了?” “好呀,我不告诉人家,我也不会瞧不起你们,你放心好了。
” “丹丹你真好。
” “我还有更好的呢!” 志高放宽了心,人也轻了,疼也忘了。
自以为保了秘密,其实北平这么一带的,谁会不知道?不过不拆穿便了。
亏志高还像怀里揣了个小兔子,一早晚怦怦直跳——也因为她是丹丹吧? 如今说了,以后都不怕了。
“你怎么不跟黄叔叔呢?你黄哥哥呢?现今下处在哪?来这耽多久?” “哎,”丹丹跺足,“又要我说!我呀,才刚把一切告诉怀玉哥了,现在又要再说一遍。
多累!”末了又使小性子,像她小时候,“我不告诉你。
” “说吧?”志高哀求似的,逗她,“我把我的都告诉你了。
” 原来丹丹随黄叔叔回天津老家去,黄叔叔眼看儿子不中用了,也就不思跑江湖,只干些小买卖,虽是爱护丹丹,但小姑娘到底不是亲骨血儿,也难以照拂一辈子的。
刚好有行内的,也到处矗竿子卖艺,便是苗师父一伙人,也是挂门的,见丹丹有门有户地出来,一拍胸口,答应照顾她,便随了苗家一伙,自天津起,也到过什么武清、香河、通县、大兴……大小的地方,现在来了北平,先找个下处落脚,住杨家大院,然后开始上天桥撂地摊去。
丹丹又一口气地给志高说了她身世。
“你本是黄丹丹,现在又成了苗丹丹。
怎么搅的,越活越回去了?还是苗呢?过不了多久,倒变成籽了,然后就死了。
”志高道。
丹丹嘟着嘴,站住不肯走了。
也不知是什么的前因后果呀。
丹丹,她原来叫牡丹。
“牡丹本是洛阳花,邙山岭上是我家,若问我的名和姓,姓洛名阳字之花。
”——丹丹是没家的,没姓的,也配不上她的名的。
花中之王,现今漂泊了,还没有长好,已经根摇叶动。
真的,在什么地方扎根呢?是生是死呢?这么小,才十七,谁都猜不透命运的诡秘。
志高被她的刁蛮慑住了——就像头憋了一肚子气的猫。
明知是装的。
“你别生气,我老是说‘死’,是要图个吉利,常常说,说破了,就不容易死了。
”志高慌忙地解说。
“要死你自己死!” 丹丹说着,辫子一甩,故意往另一头走,出了虎坊桥,走向大街东面。
“丹丹,丹丹!”志高追上去,“是我找死,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好没有作孽多,我是灰耗子,我是猪八戒……” “哦,你绕着弯儿骂你娘是老母猪?”丹丹道。
“不不不。
”志高急了,想起该怎么把丹丹给摆平?他把她招过来,她不肯,他走过去,因只穿件小背心,一招手,给她看胳肢窝,志高强调: “我给你看一个秘密:我这里有个痣,看到吗?在这。
嗳,谁都没见过的,看,是不是比你那个大?” “嗳,真像个臭虫,躲在窝里。
” 志高笑起来。
他很快活,恨不得把心里的话都给掏出来,一一地告诉了丹丹,从来没那么地渴望过。
真好,有一个人,听几句,抬杠几句,不遮不瞒,不把连小狗儿龇牙的过节儿记在心里,利落的,真心的,要哭要笑,都在一块…… 咦,那么怀玉呢? ——忽地想起还有怀玉呀。
“丹丹,你先回家,我找怀玉去。
” 志高别了丹丹,路上,竟遇上了大刘。
他是个打硬鼓儿的,手持小鼓,肋夹布包,专门收买细软,走街串巷找买卖。
许多家道中落的大宅门,都经常出入。
这个人个头高高,脸长而瘦,在盛暑,也穿灰布大褂,一派斯文。
敲打小鼓儿,一边吆喝: “旧衣服、木器,我买。
洋瓶子、宝石,我也买……” 见到志高,大刘问: “你姊在吗?她叫我这两天去看她的一只镯子。
” “不在。
”志高回大刘: “她不卖了。
” “‘不卖’的是什么?”大刘乜斜着眼问。
一种斯文人偶尔泄漏出来的猥琐。
“镯子。
” “哦——” 志高只想着,娘仅有一只镯子,猜是下落不明的爹所送。
卖了,反悔了,难免日思夜惦,总想要回东西。
志高估摸娘实是舍不得,马上代推掉了。
然后心里七上八落——钱呀,想个法子挣钱才是上路。
来到了怀玉的那个大杂院,远远便听得哭喊声,见一个呼天抢地的母亲,把孩子抱出来,闹瘟疹,死掉了。
在她身后,也有四个,由三岁到十一二岁的。
穷人就有这点划算,死掉了一个,不要紧,还有呢,拉拉扯扯的,总会得成长了几个,然后继承祖先的“穷”,生命香火,顽强地蔓延下去。
那伤心的母亲领了他兄弟姊妹,拿席子卷了尸首去——死了一个,也省了一个的吃食呀。
志高心头温热,他竟是活着呢,真不容易。
敲了唐家的门子,一进去,不待唐老大作声,也不跟怀玉招呼,志高扑一下给跪下来:“唐叔叔,我给您赔罪!” 唐老大气还没消,这下不知如何收拾他。
志高又道:“对不起您,以后我也不敢搭场子了。
” 说完了,起来逃一般地走了。
唐老大也不好再责怪什么了,看着他背后身影:“这孩子就是命不好。
” 怀玉跟他爹说: “命好不好,也不是没法可想的。
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得去‘谋’呀——爹,我也不打算永远泡在天桥的,我明天跟李师父说去,让他给我正正式式踏踏台毯。
” “你去练功,我不数算就是,不过你去当跑龙套的,什么时候可以出头?连挣口饭吃的机会都没有!” “我要去,不去我是不死心的。
” “你不想想我的地步?” “爹,撂地摊吃艺饭又是什么地步?圣明极了也不过是天桥货。
” “没有天桥,你能长这么大?”唐老大气了——他也不愿意怀玉跟随他,永不翻身,永永远远是“天桥货”。
但,怀玉的心志,原来竟也是卖艺。
卖艺,不管卖气力卖唱做,都是卖。
不管在天桥,抑或在戏园子,有什么不同?有人看才有口饭吃,倚仗捧场的爷们,俯仰由人,不保险的,怀玉。
唐老大要怎样劝说那倔强的儿? “谁有那么好运道,一挑帘,就是碰头彩?要是苦苦挣扎,扯不着龙尾巴往上爬,半生就白过了。
” 他说了又说,怀玉只是坚持,强强老半天:“千学不如一唱,上一次台就好!” 唐老大明知这是无以回头的。
当初他跟了李盛天,早已注定了,怎么当初他没拦住他?如今箭在弦上。
唐老大一早上的气,才刚被志高消了一点,又冒了: “你非要去,你去!你给我滚!” 一把推走这个长大了的儿子。
怀玉踉跄一下,被推出门去了。
唐老大意犹未足: “你坍了台就别回来!” 然后重重地坐下来。
孩子,一个一个,都是这样:以为自己行,马上就坍台了,残局还不是由连苍蝇也不敢得罪的大人来收拾么?早上是志高,晚上是怀玉,虎背熊腰的粗汉,胡子就这样地花白起来了,像一匹老马,载重的,他只识一途,只得往前走,缓缓地走着,是的,还载重呀,终于走过去。
他多么希望他背负的是玉,不是石头。
怀玉,自己不识字,恳请识字的老师给他起个好名儿呢,怀的是玉。
没娘的孩子,就算是玉,也有最大的欠缺。
唐老大想了一想,便把门儿敞开,正预备把怀玉给吆喝进来了。
谁知探首左右一瞧,哪里还有他的影儿?做爹的萎靡而仓皇。
——孩子大了,长翅了。
从前叫他站着死,他不敢坐着死。
赶出门了,却瑟缩在墙角落,多么地拧,末了都回到家里来。
啊一直不发觉他长翅了。
他要飞,心焦如焚急不及待地要飞。
孩子大了,就跟从前不一样了。
怀玉鼓起最大的勇气,恭恭敬敬地等李盛天演完了一折,回到后台,方提起小茶壶饮场。
觑着有空档,企图用三言两语,把自己的心愿就倾吐了——要多话也不敢。
他一个劲地只盯着师父一双厚底靴: “——这样地练,天天练,不停练……不是‘真’的呀。
反正也跟真的差不多了,好歹让我站在台上,就一次……” 李盛天瞅着他,长得那么登样,心愿也是着迹的:要上场! “哦,你以为上台一站容易呀?大伙都是从龙套做起。
” “您让我踏踏台毯吧,我行。
” “行吗?”师父追问一句。
“行呀行呀,一定行的,师父,我不会叫您没脸,龙套可以,不过重一点的戏我也有能耐,台上见就好。
” 李盛天见这孩子,简直是秣马厉兵五内欢腾,颜面上不敢泄漏出来,一颗心,早已飞上九霄云外。
师父忍不住要教训他: “你知道我头一回上场是什么个景况?告诉你,我十岁坐科,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手脸都裂成一道血口了。
头一回上场,不过是个喽啰……” 李盛天的苦日子回忆给勾起来了,千丝万缕,母亲给写了关书,画上十字,卖身学习梨园生计,十年内,禁止回家,不得退学,天灾疾病,各由天命。
他的严师,只消从过道传来咳嗽声,师兄弟脸上的肌肉会得收紧,连呼吸都变细了——全是“打”大的。
一个不好,就搬板凳,打通堂。
那一回夏天,头上长了疥疮,上场才演一个龙套吧,头上的疮,正好全闷在盔头里,刚结的薄痂被汗汇水洗的,脱掉了,黄水又流将出来。
就这样,疼得浑身打颤,也咬着牙挺住,在角儿亮相之前,跑一个又一个的圆场…… 怀玉虽是苦练,但到底是半路出家的,没有投身献心地坐过科。
比起来,倒真比自己近便了,抄小道儿似的。
李盛天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他不肯稍为宠他一点,以免骄了——机会是给他,别叫他得了蜜,不识艰险。
怀玉只听得他可跟了师父上场,乐孜孜,待要笑也按捺住。
一双眼睛,闪了亮光,把野心暗自写得无穷无尽。
这骗不了谁,师父也是过来人。
好,就看这小子有没有戏缘,祖师爷赏不赏饭吃,自己的眼光准不准。
功夫不亏人,功夫也不饶人。
怀玉的一番苦功,要在人前夺魁,还不是时候;龙套呢,却又太委屈了。
李盛天琢磨着。
“这样吧,哪天我上‘华容道’,你就试试关平吧。
我给班主说去。
不过话得说回来,几大枚的点心钱是有,赏的。
份子钱不算。
” ——钱?不,怀玉一听得,不是龙套呀,还是有个名儿的角色呢,当下呼啸一声…… “怀玉哥,有什么好高兴的事儿?” 在丹丹面前,却是一字不提。
对了,告诉她好,还是瞒着呢? 头一回上场,心里不免慌张,要是得了彩声,那还罢了;要是像志高那样,丢人现眼的,怎么下台?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心高气傲,更是输不起的人。
不告诉她,不要她来看——要她看,来日方长呀,她准有一天见到他的风光。
怀玉倒是笃定。
在关口,别叫一个娘们给影响怵阵了。
卡算着,就更不言语了。
丹丹跟怀玉走着路,走着走着,前面胡同处青灰色的院墙里,斜伸出枝叶繁茂的枣树枝来。
盛夏时节,枣儿还是青的,四合院里有个老奶奶,坐在绿荫下,放上两个小板凳,剥豆角。
蝉在叫。
怀玉伸手想摘几个枣儿来解渴。
手攀不上呢,那么地高。
只因太乐了,怀玉凭着腰腿,一二三蹦地站上墙头,挑着些个头大的,摘一个扔一个,让丹丹给接住,半兜了,才被奶奶发现:“哎呀,怎么偷枣儿呢!”她忙赶着。
怀玉道:“哈,值枣班来呢。
早班晚班都不管用了!”丹丹睨着这得意非凡地笑的怀玉,正预备跳下来。
还没有跳,因身在墙头,好似台上,跟观众隔了一道鸿沟。
丹丹要仰着头看怀玉,仰着头。
真的,怀玉马上就进入了高人一等的境界了。
心头涌上难以形容的神秘的得意劲,摆好姿势,来个“云里翻”。
往常他练云里翻,是搭上两三张桌子的高台,翻时双足一蹬,腾空向后一蜷身……好,翻给丹丹看,谁知到了一半,身子腾了个空,那老奶奶恨他偷枣儿,自内里取来一把竹帚子,扔将出来,一掷中了,怀玉冷不提防,摔落地上。
猛一摔,疼得摧心,都不知是哪个部位疼,一阵拘挛儿,丹丹一见,半兜的枣儿都不要,四散在地,赶忙上来待要扶起他。
怀玉醒觉了,忍着——这是个什么局面?要丹丹来扶?去你的,马上来个蜈蚣弹,立起来,虽然这一弹,不啻火上加了油,浑身更疼,谁叫为了面子呀?便用手拍给掉了土,顺便按捏一下筋肉,看上去,还像是掸泥尘,没露出破绽来。
忍忍忍! “怎么啦?” “没事。
”怀玉好强,“这有什么?” “疼吗?” “没事。
走吧。
”怀玉见老奶奶尚未出来拾竹帚,便故意喊丹丹,“枣儿呢?快给捡起来,偷了老半天,空着手回去呀?快!” 二人快快地捡枣儿。
看它朝生暮死的,在堕落地面上时,还给踩上一脚。
直至老奶奶小脚叮咚地要来教训,二人已逃之夭夭。
丹丹挑了个没破的枣放进嘴里: “嗐,不甜的。
” 怀玉痛楚稍减,也在吃枣。
吃了不甜的,一嚼一吐,也不多话。
丹丹又道: “青楞楞的,什么味也没有。
” 见怀玉没话,丹丹忙开腔:“我不是说你挑的不甜呀,嗄,你别闷声不吭。
” “现在枣儿还不红。
到了八月中秋,就红透了,那个时候才甜脆呢。
” “中秋你再偷给我吃?” “好吧。
” “说话算数,哦?别骗我,要是半尖半腥的,我跟你过不去!” “才几个枣儿,谁有工夫骗你?” “哦,如果不是枣儿,那就骗上了,是吗?” 怀玉拗不过她,这张刁钻的嘴。
只往前走,不觉一身的汗。
丹丹在身边不停地讲话,不停地逗他:“你跟我说话呀?” 清凉的永定河水湛湛缓缓地流着,怀玉跑过去在河边洗洗脸,又把脚给插进去,好不舒服,而且,又可以避开了跟丹丹无话可说的僵局。
她说他会骗她,怎么有这种误会? 丹丹一飞脚,河水撩他一头脸,怀玉看她一眼,也不甘示弱不甘后人,便还击了。
玩了一阵,忽地丹丹道: “怀玉哥,中秋你再偷枣儿给我吃?” 他都忘了,她还记得。
怀玉没好气: “好吧好吧好吧!” “勾指头儿!” 丹丹手指头伸出来,浓黑但又澄明的眼睛直视着怀玉,毫无机心地,不沾凡尘地,她只不过要他践约,几个枣儿的约,煞有介事。
怀玉为安她的心,便跟她勾指头儿。
丹丹顽皮地一勾一扯,用力地,怀玉肩膊也就一阵疼,未曾复元,丹丹像看透了:“哈哈,叫你别死撑!” 又道:“你们男的都一个样,不老实,疼死也不喊,撑不了多久嘛,切糕哥也是——咦?我倒有两天没见他了,你见过他没有?” “没有。
平常是他找我,我可不知到哪里找他,整个北平都是他的‘家’,菜市的席棚、土地庙的供桌、还有饭馆门前的老虎灶……胡同他姊那里倒是少见。
” “他的‘家’比你大,话也比你多。
你跟我说不满十句,可他都是一箩筐一箩筐地给倒出来呢。
” “他嗓子比我好嘛。
” “这关嗓子什么事?——这是舌头的事。
”丹丹笑,“他有两个舌头!” “你也是。
”怀玉道。
二人离了永定河,进永定门,走上永定门大街,往北,不觉已是前门了。
前门月城一共有三道门,直到城楼的是前门箭楼。
北平有九座箭楼,各座箭楼的“箭炮眼”,直着数,都是重檐上一个眼,重檐下三个眼;横着数就不同了,不过其他八座箭楼都是十二个眼,只前门箭楼有十三个眼。
为什么会多出一个眼来?久居北平城的老百姓都不了了之。
正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悠悠地走着,又过了半天。
忽然,前边也走着一队来势汹汹的人呢。
说是来势汹汹,因为是密密匝匝的群众。
还没看得及,先是鼎沸人声,自远远传来,唬得一般老百姓目瞪口呆。
在没搅清楚一切之前,慌忙张望一下,队伍操过来了,便马上觅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只把脑袋伸张一点——一有不对,又缩回去了。
“弹打出头鸟”,谁不明白这道理?都说了几千年了。
怀玉拉着丹丹站过一旁,先看着。
都是些学生。
是大学生呢。
长得英明,挺起胸膛,迈着大步。
其中也有女的。
每个人的眼神,都毫不忌惮地透露出奋激和热情,义无反顾。
大家站到一旁,迎着这人潮卷过来。
队伍中,走在前头的一行,举起一面横布条,上面写着:“把日本鬼子赶出东三省!”后面也有各式的小旗帜、纸标语挥动着,全是:“反对不抵抗政策!”“出兵抗日!”“抵制日货!”“反对廿一条!”“还我中国!”…… 人潮巨浪汹涌到来,呼喊的口号也震天响至,通过这群还没踏出温室的大学生口中,发出愚钝的老百姓听不懂的怒吼。
“他们在喊什么?” “说日本鬼子打我们来了。
”怀玉也是一知半解的。
“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呀?”丹丹好奇问。
“听是听说过的,你问我我问谁去?”天桥小子到底不明国事。
“唐怀玉!”人潮中竟有人喊道。
怀玉一怔,听不清楚,估道是错觉。
在闹嚷嚷的人潮里,跑出一个人。
是一个唇上长了几根软髭的青年人,面颊红润,鼻头笔直,眼神满载斗志。
怀玉定睛看看这个头大的学生,啊原来他是何铁山。
“何铁山,认得吗?小时候在学堂跟你打上一架的何铁山呀!” 怀玉记起来了,打上一架,因为这人在二人共用的长桌子上,用小刀给刻了中间线,当年他瞧不起怀玉呢,他威吓他:“你别过线!”怀玉也不怕:“哼!谁也别过线!” 后来是谁过了线?……总之拳脚交加了一阵,决了胜负。
怀玉记起来了。
目下二人都已成长。
何铁山,才比自己长几岁,已经二十岁出头吧。
他家趁有点权势,所以顺理成章地摇身一变,成为大学生;自己呢,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雏儿。
真的,谁胜谁负? 只是何铁山再也不像当年的幼稚和霸道了,少年的过节,并没放在心上。
他英姿勃发,活得忙碌而有意义,读书识字,明白家国道理,现在又参加反日集会,游行示威。
因为家道比较好,懂得也比较多,真的,他变了——惟一不变,也许是这一点执著: “你别过线!” 谁“过了线”,他便发难。
何铁山递给怀玉一沓油印的传单纸张,道:“唐怀玉,拜托你给我们派出去,请你支持我们,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反侵略。
你明白吗?现在东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两百万平方里领土、三千万个同胞都已沦于敌手,很快,他们就会把中国给占领了……”他说得很快、很流利,自因不停地已宣传过千百遍了。
只听得怀玉一愣一愣的。
何铁山一口气给宣传完毕,挥挥手,又飞奔融入队伍中,再也找不着了——在国仇家恨之前,私人的恩怨竟然不知不觉地,一笔勾销。
丹丹犹满怀兴奋,追问着零星小事: “你跟他打上一架?谁赢了?” “你说还有谁?”怀玉道。
“哼,是那大个子赢的!”丹丹故意抬杠,“你看是他跑过来喊你。
” “输的人总比赢的人记得清楚一点。
”怀玉道。
“我不信!” 娘们爱无理取闹,你说东,她偏向西,都不知有什么好玩儿。
怀玉只低首把那宣传单浏览一遍。
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他的能耐,多可笑,“号召全国人民抗日”,什么叫“号召”?“全国人民”有多少?怎样“抗日”?该如何上第一步?怀玉皱着眉,那横冷的一字眉浓浓聚合着。
丹丹偏过头望他,望了一阵,见他不发觉,便一手抢了单张去。
“我也会看呢。
喏,这是‘九一八’,九一八什么什么,日本什么华,行动,什么什么暴露……” “阴谋!” “阴谋?是说日本鬼子使坏?是吧?他们要来了,怎么办?” “呀,不怕,咱有长城呢。
”怀玉想起了,“北方的敌人是攻打不过来的。
” “对——不过,如果敌人从南面来呢?”丹丹疑惑。
“没啦。
不会的,南面的全是我们自己人嘛。
攻什么?都是外头乱说的荒信儿,消息靠不住。
” 当下,二人都仿佛放下心来。
而队伍虽然朝西远去了,谁知措手不及地,竟又狼奔豕突,望东四散逃窜了,好似有人把水泼进蚂蚁的窝里,性命攸关。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对,是来驱赶镇压的。
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们都只好把旗帜、标语一一扔掉了。
“把日本鬼子赶出东三省”的横布条,被千百双大小鞋子给踩成泥尘。
鬼子没赶着,警察倒来赶学生,从前当差的老对付书生,今天警察又爱打学生——看来只为赢面大。
然而,输了的人总是永远记得的。
比赢的人清楚。
未几,满世又回复了悠闲,“全国”都被置诸脑后,好像只发生过一场硬生生搭场子的评书。
一个人讲完整个简单的故事。
一鸡死一鸡鸣,倒是传来清朗的喊声:“本家大姑奶奶赏钱一百二十吊!” 原来自西朝东这面来的,是有钱人家抬扛的队伍呢。
这是大殡,丧家讲究体面。
有人敲着响尺,远远听见了。
抬扛的一齐高喊:“诺!” 丹丹忙瞪着眼睛看那打执事的,举着旗、锣、伞、扇、肃静回避牌、雪柳、小呐。
吹鼓手、清音、乐队也列队浩荡前进。
很多人都尾随着围观。
本来街上那吹糖人的,正用小铁铲搅乱铁勺内的糖稀,两手拿起一点儿揉弄成猪胆形,预备在折口的管上吹几下,小金鱼还没吹成,孩子们全都跑去看人撒纸钱了。
只见一辆人力车,拉着百十多斤成串的纸钱,跟在一个老头儿身后,老头儿瘦小枯干,穿一件白孝衣,腰系白布孝带,头戴小帽,两眼炯炯有神,走在六十四人扛的大殡队伍前面,取过一沓厚纸钱,一哈腰,奋力一撒,撒上了半空。
这沓白色的圆钱,以为到了不能再高的位置,却又忽地扭身一抖,借着风势,竟似一只一只圆圆的中间有个洞洞的大眼睛,飘远飘高,风起云涌,兀自翻腾,天女散花,在红尘中做最后一次的逍遥。
人们看他撒纸钱,依依不舍,万分地留恋,这盛暑天的白雪,终于软弱乏力地漂泊下堕了,铺满在电车轨上,没一张重叠。
队伍寸进,丹丹瞥到那老头儿,下巴颏儿一撮黑毛。
丹丹情不自禁地扯着怀玉:“看他的毛多怪!” “这是鼎鼎大名的‘一撮毛’呢!他撒纸钱最好看了!”怀玉道,“绝活儿!” 人人都来看,因为“好看”,谁又明白丧家的心意呢?逢遇庙宇,穿街过巷,一连串地撒,为的是要死者来世丰足。
然而他生未卜,今生却只是一些虚像。
打执事的,现钱闲子,反而是因着领“现钱”,便更加落力吆喝。
那清朗的喊声又来了: “本家二姑奶奶赏钱一百二十吊!” 气盛声宏,腔尾还有余音,这不是他是谁?怀玉和丹丹马上循声给认出来了: “切糕哥!”“志高!”二人几乎是同时地唤着。
天无绝人之路,志高不知如何,又给谋得这打执事的差使。
跟他一块的,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十几二十岁的男孩,打一次执事,可挣几吊钱,要跟了一撮毛爷爷后面呢,打赏还要多一点,志高因为嗓子好,被委以重任。
看他那副得意劲,仿佛是副领队。
怀玉过去,在大殡行列旁,捶他一下:“好小子!真有瞧头!” 在人家的丧事中,两个人江湖重遇了,又似长大了一点——怀玉更是无法敛着了,他撇开丹丹,向志高低首沉声地讲了他的大志: “李师父说……” 志高一壁把厚纸钱递与一撮毛,一壁跟怀玉二人犯彪了地笑将起来。
别看一撮毛是个老头儿,他的眼神可真凌厉,一瞥着志高不专心,瞪他一眼,暗道: “你别混啦,吓?要有点道德,人家办丧事,咱要假科子可得了?” 怀玉识趣。
志高跟他打个眼色,二人分手了,怀玉才记起丹丹等在一边。
丹丹追问:“嗳,你跟他抹里抹登的,有什么瞒人的事?” “没有呀。
” “有就是有。
你告诉我?” “没有就是没有。
” “人家跟你俩这么好,你都不告诉?切糕哥什么都告诉我的。
” “以后再说吧。
” “你说不说?我现在就要知道,说嘛——” “毛丫头甭知道得太多了。
” “说不说?真不说了?”鼓起腮帮子,撒野,“真不说?” 丹丹说着,又习惯性地辫子一甩,故意往大街另一头走去了,走了十来步,以为怀玉会像志高般,给追上来,然后把一切都告诉她,看重她、疼她。
在她过往的日子里,她的小性子,往往得着满意的回应。
咦?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垂着长睫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都市最强战神梁一笑
- 从综武世界开始逍遥诸天沐阳千羽
- 我和兄弟一起穿越红楼爱吃豆豉酱的比丘斯
- 从公爵之子到帝国皇帝老庄屋
- 纵横诸天:从修炼辟邪剑法开始不吃鱼虾的猫咪
- 我,秦王世子,用盒饭暴出百万兵蛟变化龙
- 两界:玻璃杯换美女,买一送一宁衰人
- 签到修仙:我在青城山躺成剑仙慕斯雨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水浒之往事随风间间间
- 穿越古代异界争霸闲人小小
- 明末造反:我的盲盒能开神装七辛海棠
- 我在北宋教数学吉川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青岳
-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南岳清水湾
- 人在古代,从抢山神娇妻开始崛起女帝
- 诗泪洒江湖云里慕白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大明:我崇祯,左手枪右手炮二月十八
- 不良人之大唐麒麟侯隐城的驼龙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我在大明洪武当神仙爱吃肥肠香锅的盛星河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我热痢的马
- 屌丝奶爸变男神垂钓看烟花
- 踏雪寻青梅云笺寄晚
- 穿越大唐:农家子弟挣钱忙智阳雨
- 穿越古代异界争霸闲人小小
- 签到修仙:我在青城山躺成剑仙慕斯雨
- 替弟为质三年,归来要我让战功?芳龄真的二十
- 三国:魂穿刘禅,工业经贸兴汉室作者山语清风
- 星极宇宙社恐的中年人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逆命武侠行随风飘扬的喜哥
-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南岳清水湾
- 幸福生活从穿越开始男人苦咖啡
- 谁主噬心弘狄
- 大唐:身为太子的我只想摆烂交出思想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物流之王之再续前缘笔尖路悠然
- 这破系统非要我当皇帝总有那一天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天娇:铁木真崛起与大元帝国前传天狼峰的古尊人
- 重生六9:倒爷翻身路惊恐不安九仙君
- 轉生成豬的我,突破只能靠雙修爱鯊客
- 武侠:莽昆仑严久霖江洲雨林
- 乱世红颜之凤临三国孟回千古
- 大夏第一神捕木有金箍
- 横行霸道踏雪真人
- 屌丝奶爸变男神垂钓看烟花
- 三国:我辅佐刘备再兴炎汉我才是猫大王啊
- 从天龙活到现代的武林神话歌尘浪世
- 温阮霍寒年温阮霍寒年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水浒之往事随风间间间
- 北军悍卒虎虎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永乐入梦我教我自己当皇帝用钱打我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穿越古代我的空间有军火:请卸甲百万负翁不想再负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我热痢的马
- 我在大明开医馆我就是个保底命
- 龙吟三国小川流水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铁血龙骧:从将门遗孤到开国圣主琪琪拥有小狗叭
- 边军凶猛赤阳
- 东汉末年:我携百科平天下特特eve
- 重生六9:倒爷翻身路惊恐不安九仙君
- 七情碗夜凰
- 洪荒之鲲鹏绝不让位李九郎
- 纯阳第一掌教池宁羽
- 冷艳总裁的超级狂兵北冥听涛
- 极品仙途闻人毒笑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