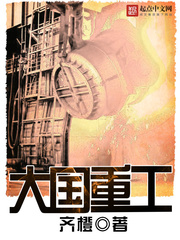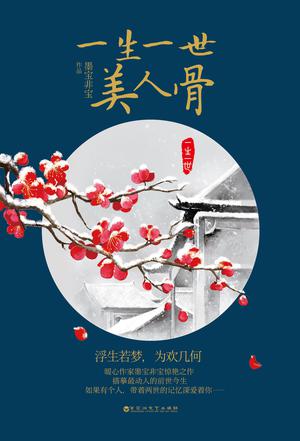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民国十四年•冬•北平(3/3)
交学费的学生。
同学们只见怀玉侧影,腮边牙关一紧,冷冷地,出去了。
等到课上完了,不见有人敲钟,老师出来一瞧,怀玉不知什么时候,一走了之了。
老师只得吩咐放学。
院内有接放学的,也有娘给送加餐来了。
孩子一壁吃点心,一壁眉飞色舞地叙述唐怀玉跟何铁山的事。
家长也乘机教训他们要孝义。
何铁山还没走出绒线胡同口,横地来一记飞腿,他中了招,马上还击,仗着个头大,拳来脚往,好不热闹。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何铁山又怎是对手?怀玉不消几下功夫,就把他打个脸蹭地,哪儿凸哪儿破,嘴唇和下巴颏上头也流血了。
志高赶来时,吓傻了,忙怪嚷: “什么事什么事?” 何铁山落荒而逃。
怀玉拍去泥尘,只道: “没事。
” “什么事?” “没事,走吧。
” 前因后果也不提,便示意志高走了。
志高颠着屁股追问。
不得要领。
丁老师,他知道也好,也许听不见。
只在大庙后他的小房子里,寂寂地拉着胡琴。
当年,他也是个好琴师,一段反二簧,竹腔似断非断,一弓子连拉五个音…… 为了生活,不得不把他赢过的彩声含敛,把他的学问零沽。
今日也没所谓升官发财,来识字又是为了什么?时髦一点的都上教会洋学堂去了。
终于他又拉了一段“楚宫恨”,悠悠回旋地唱:“怀抱着年幼儿好不伤情……” 怀玉领志高来到了“老地方”,这是肉市广和楼。
自后台门进出,也没人拦阻,因为二人常来看蹭儿戏,小孩子家,由他们吧。
志高很会做人,经常帮忙跑腿,递茶壶饮场,收拾切末。
怀玉呢?他还喊李盛天师父的——这是他的小秘密。
今天日场上“四五花洞”。
志高最喜欢看这种“妖戏”了。
因为是日场,不必角色上场,一般都是热闹胡闹的戏。
“四五花洞”演的是武大郎与潘金莲因家乡久旱成灾,同赴阳谷县投奔武松去,途经五花洞,洞内妖魔金眼鼠和铁眼鼠变化为假武大假金莲,与真武大真金莲纠缠不清,官司闹到矮子县官胡大炮那里,反而越搅越胡涂,其时正逢包拯过境,便下轿察看,也难辨真假,无法判断。
后来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到来,便用“掌心雷”的法宝,两妖才现出原形,真相大白。
日戏时几个小花旦为要踏踏台毯,都得到机会出场,妖魔化身为金莲,一变变了三个,是谓“四五花洞”,一真三假的玩笑戏,好不风骚热闹——这几个未成角儿的小花旦,全是十几岁的男孩,也有刚倒呛过来,嗓子甜润嘹亮。
志高听着那人唱:“不由得潘金莲怒上眉梢,自幼配武大他的身量矮小……” 他用肘撞撞怀玉:“怀玉你瞧,金宝哥给咱们飞眼。
” 然后两个孩儿就在上场门边打了个招呼。
台上的戏依旧在唱,小花旦又装作若无其事。
二人一瞥前台稍空,便偷偷自后台走到前台去。
才一上,那空位有人占先,只好站到一旁观看便是。
广和楼楼下靠墙有一排木板,高凳儿,二人一先一后,踮起脚尖儿,站了上去。
妖戏完了,志高忘形地鼓掌,忽地发觉怀玉不在身边。
志高自散场的观众间逆向钻回后台去。
怀玉磨在他“师父”李盛天身后,看他勾脸,看得神魂迷醉似的。
夜场上“艳阳楼”,又称“拿高登”,李盛天贴高登,他是班上的武生,年纪有四十多五十,但武功底子数他稳厚,扮相极有派头。
戏中所持兵器乃七星大刀。
那刀怀玉自是扛不动,他想,总有扛得动的一天。
李盛天已然换上水衣,又用细棉布勒住前额,白粉打了底。
只见他在眼眶、鼻下人中处抹黑灰,再把眉定位,高登画的是刀螂眉。
怀玉看傻了眼,每一回,一张模糊的脸,于彩匣子前,大镜子外,给了一勾一抹一揉,红黑黄蓝白金银……渐渐地它变了,像图画一般,脸上全是故事,色彩斑斓,眼花缭乱,定了型,最后在脑门上再勾一长条油红,师父便是千百年前的一个古人。
他是奸臣高俅之子,他倚仗父势鱼肉乡民……后来,他死在艳阳楼上。
李盛天开始扮戏了,虽然他自镜中也瞧见了这身手机灵、心比天高而又沉默苦干的大男孩,不过他从来没把感觉外露,他调教他,基于看他是料子,但总要让他明白,世上并无一蹴登天的先例。
李盛天换衫裤,系腰带,穿上厚底靴,扎紧裤腿,搭上胖袄衬里,再搭上厚护领。
二衣箱给他穿箭衣,系大带。
盔头箱处勒上网子及千斤条,插耳毛,戴扎巾,戴髯口。
最后,再到大衣箱给穿上褶子,拿大折扇。
——这一身,终于大功告成了。
“师父!”怀玉此时才敢恭敬地喊一声。
“唔。
”李盛天应了,兀自养神入戏,不再搭理。
怀玉知机地便退过一旁。
退回后台,退至上场门外一个角落,一直地退,他还是个雏儿,上不得场——他的场子只在天桥地摊。
夜戏散了,怀玉跟志高嘞嘞絮叨他师父的那份戏报: “老大的一张戏报,大红纸,洒上碎金点儿,上面写着‘李盛天’、‘艳阳楼’这样的字儿。
其他的名儿都比不上我师父,缩得小小地给搁在旁边。
你看见没有?真红!嗳,你识字的呀,你认得那个‘天’字的呀……” 志高觑不到空档儿接碴儿。
只见街巷上点路灯的已扛着小木梯子,挨个儿给路灯添煤油点火了。
一个人管好几十个灯,有的悬挂在胡同铁线上,好高,要费劲攀上去。
虚荣的小怀玉,也许他惟一的心愿是:老大的一张戏报,大红纸,洒上碎金点儿,上面写着“唐怀玉”三个字。
沿街又有小贩在叫卖了。
卖萝卜的,吆喝得清脆妩媚:“赛梨,萝卜赛梨,辣了换!”卖烤白薯的,又沉郁惨淡:“锅底来!——栗子——味!” 勾起志高的馋意。
他伸手掏掏,袋中早已空了。
怀玉的几枚点心钱,又给买了豆汁、爆肚。
怀玉见志高一脸的无奈,便道: “又想吃的呀?” “对,我死都要当一个饱死鬼!要是我有钱,就天天吃烤白薯,把他一摊子的白薯全给吃光了。
” “你怎么只惦着吃这种哈儿吗儿的东西?一点小志都没有,还志高呢!” “哦,我当然想吃鸡,想吃鸭子,还有炒虾仁,哪来的钱?” “你闭上眼睛。
” “干么?”怀玉把东西往他袋中一塞,马上飞跑远去。
一看,原来是十来颗酥皮铁蚕豆,想是在广和楼后台,人家随便抓一把给他吃的。
怀玉没吃,一直带着,到了要紧关头,才塞给志高解馋来了。
怀玉这小子,不愧是把子。
志高走在夜路上,把铁蚕豆咬开了壳儿,豆儿入口,又香又酥又脆,吃着喜庆,心里痛快。
慢慢地嚼,慢慢地吞咽,壳儿也舍不得吐掉。
他心里又想:咦,要是有钱,就天天吃酥皮铁蚕豆、香酥果仁、怪味瓜子、炒松子……天天地吃。
月亮升上来了。
初春的新月特别显得冻黄,市声渐冉,人语朦胧。
来至前门外,大栅栏以南,珠市口以北,虎坊桥以东——这是志高最不愿意回来的地方。
非等到不得已,他也不回来了。
不得已,只因为钱。
胭脂胡同,这是一条短短窄窄的小胡同。
它跟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纱帽胡同、陕西巷、皮条营、王寡妇斜街一般齐名。
大伙提起“八大胡同”,心里有数,全都撇嘴挂个挂不住的笑,一直往下溜,堕落尘泥。
胭脂胡同,尽是挂牌的窑子。
只听得那简陋的屋子里,隐隐传来女人在问: “完了没有?完了吧?走啦,不能歇啦。
完了吧?哎——” 隐隐又传来男人在答: “妈的!你……你以为是挑水哥们呀,进门就倒,没完!”嘿儿喽的,有痰鸣。
女人又催: “快点吧——好了好了,完了。
” 悉悉的穿裤子声,真的完了。
志高甫进门,见客人正挑起布帘子,里头把客人的破棉衣往外扔。
客人把钱放在桌上茶盘上,正欲离去,一见这个混小子,马上得意了。
一手叉住志高的脖子,一边喝令: “喊爹,快喊爹!” 志高挣扎,他那粗壮的满是厚茧的手更是不肯放过。
上面的污垢根深蒂固,真是用任何刷子都刷不掉。
他怎么能想象这样的一双手,往娘脸上身上活动着,就像狂风夹了沙子在刮。
志高拼命要挣脱,用了毕生的精力来与外物抗衡,然而总是不敌。
有时是拉洋车的,有时是倒泔水的、采煤的、倒脏土的、当挑夫的…… 这些人都是他的对头人。
今天这个是掏大粪的,身上老有恶歹子怪味,呛鼻的,臭得恶拉扒心。
“我不喊。
老乌龟!大粪干!” “嘎!我操了你娘!你不喊我爹?” 布帘子呼地一声给挑起了。
“把我弟放下来!”平板淡漠地。
那汉子顺着女声回过头去: “嘿,什么‘弟’?好,不玩了,改天再来,红莲,我一定来,我还舍不得不操你呢!小子,操你娘!” 红莲,先是一股闷浓的香味儿直冲志高的小脑门。
然后见一双眼睛,很黑很亮,虽然浮肿,那点黑,就更深。
颧骨奇特地高,自欺而又倔越地耸在惨淡白净的尖盘儿脸上。
她老是笑,不知所措地笑,一种“赔笑”的习惯,面对儿子也是一样。
只有在儿子的身上,她方才记得自己当年的男人,曾经的男人,他姓宋。
志高的爹称赞过她的一双手。
她有一双修长但有点嶙峋的白手,手指尖而瘦,像龟裂泥土中裂生出来的一束白芦苇:从前倒是白花,不知名的。
不过得过称赞。
男人送过她一只手镯。
红莲在志高跟前,有点抽搐痉挛地把她一双手缠了又结,手指扣着手指,一个字儿也不懂,手指却兀自写着一些心事。
十分地畏怯,怪不好意思地。
她自茶盘上取过一点钱,随意地,又赔罪似的塞给志高了: “这几天又到什么地方野去?” “没啦,我去找点活计。
” “睡这吧?” 志高正想答话,门外又来个客人,风吹在纸糊窗上,哑闷地响,就着灯火,志高见娘脖子上太阳穴上都捏了痧,晃晃荡荡的红。
“红莲!” 娘应声去了。
志高寂寂地出了院子。
袋里有钱了,仿佛也暖和了。
今儿个晚上到哪儿去好呢?也许到火房去过一夜吧,虽然火房里没有床铺,地上只铺上一层二尺多厚的鸡毛,四壁用泥和纸密密糊住缝隙,不让寒风吹进,但总是有来自城乡的苦瓠子挤在一起睡,也有乞丐小贩。
声气相闻的人间。
说到底,总比这里来得心安,一觉睡到天亮,又是一天。
好,到火房去吧。
快步出门了,走了没多远,见那掏大粪的背了粪桶粪勺,推了粪车,正挨门挨户地走。
志高鬼鬼祟祟拾了小石子,狠狠扔过去,扔中他的脖子。
静夜里传来凄厉的喝骂: “妈的!兔崽子,小野鸡,看你不得好死,长大了也得卖!” 志高激奋地跑了几步,马上萎顿了。
胭脂胡同远远传来他自小便听了千百遍的一首窑调,伴着他凄惶的步子。
“柳叶儿尖上尖唉,柳叶儿遮满了天。
在位的明公细听我来言唉。
此事唉,出在咱们京西的蓝靛厂唉——” 志高的回忆找上他来了。
他从来没见过爹,在志高很小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不在?也许死了,也许跑了。
这是红莲从来没告诉过他的真相,他也不想知道——反正不是好事。
最初,娘还没改名儿唤“红莲”呢。
当时她是当缝穷的,自成衣铺中求来一些裁衣服剩下的下脚料,给光棍汉缝破烂。
地上铺块包袱皮,手拿剪子针线,什么也得补。
有一天,志高见到娘拎住一双苦力的臭袜子在补,那袜子刚脱下,臭气薰天,还是湿濡濡的,娘后来捺不住,恶心了,倚在墙角呕吐狼藉,晚上也难受得吃不下饭,再吐一次。
无论何时,总想得起那双摸上去温湿的臭袜子,就像半溶的尸,冒血脓污的前景。
……后来娘开始“卖”了。
志高渐渐地晓得娘在“卖”了。
他曾经哭喊愤恨: “我不回来睡,我永远也不回来!” ——他回来的,他要活着。
他跟娘活在窑调的凄迷故事里头: “一更鼓来天唉,大莲泪汪汪,想起我那情郎哥哥有情的人唉,情郎唉,小妹妹一心只有你唉。
一夜唉夫妻唉,百呀百夜恩……”——一直地唱到五更。
唉声叹气,唉,谁跟谁都不留情面。
谁知道呢?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说起来,还不是一样:短短的五更,已是沧桑聚散,假的,灰心的,连亲情都不免朝生暮死。
志高不相信他如此地恨着娘,却又一壁用着她的钱——他稍有一点生计,也就不回来。
每一回来都是可耻的。
经过一个大杂院,也是往火房顺路的,不想听得唐老大在教训怀玉了: “打架,真丢人!你还有颜面到丁老师那儿听书?还是丁老师给你改的一个好名字!嗄,在学堂打架?” 一顿劈劈啪啪的,怀玉准挨揍了。
志高停下来,附耳院外。
唐老大骂得兴起: “还逃学去听戏!老跟志高野,没出息!”志高缓缓地垂下头来。
“他娘是个暗门子,你道人家不晓得吗?” “不是他娘——是他姊。
”怀玉维护着志高的身世。
“姊?老大的姊?你还装孙子!以后别跟他一块,两个人溜儿湫儿的,不学好。
” “爹,志高是好人。
他娘不好不关他的事,你们别瞧不起他!” 唐老大听了,又是给怀玉一个耳雷子。
“我没瞧不起谁,我倒是别让人瞧不起咱。
管教你就是要你有出息。
凭力气挣口饭,一颗汗珠掉在地上摔八瓣呢!你还去跟戏子?嘿!什么戏子、饭馆子、窑子、澡堂子、挑担子……都是下九流。
你不说我还忘了教训你,要你识字,将来当个文职,抄写呀,当账房先生也好——你,你真是一泡猴儿尿,不争气!” 狠狠地骂了一顿,唐老大也顾不得自己手重,把怀玉也狠狠地打了一顿。
骂声越来越喧嚣了,划破了寂夜,大杂院的十来家子,都被吵醒了,翻身再睡。
院子里哪家不打孩子?穷人家的孩子都是打大的,不光是孩子,连媳妇儿姑娘们也挨揍。
自是因为生活逼人,心里不好过。
唐老大多年前,一百八十斤的大刀,一天可舞四五回,满场的彩声。
舞了这些年了,孩子也有十二岁。
眼看年岁大了,今天还可拉弓舞刀,明天呢?后天呢?…… “你看你看,连字也没练好!” 不识字的人,但凡见到一笔一划写在纸上的字,都认为是“学问”。
怀玉的功课还没写,不由得火上加油。
真的,打上丢人的一架,明天该如何向丁老师赔礼呢?丁老师要不收他了,怀玉的前景也就黯然。
唐老大怒不可遏: “给我滚出去!滚!” 一脚把怀玉踢出去,怀玉踉跄一下,迎面是深深而又凄寂的黑夜,黑夜像头蓄锐待发的兽。
怀玉咬紧牙关,抹不干急泪,天下之大,他不知要到哪里是好?爹是头一回把他赶出来。
他只好抽搐着蹲在院里墙角,瑟缩着。
便见到志高。
“喂,挨揍了?” 志高过来,二人相依为命。
怀玉不语。
“喂,你爹揍你,你还他呀,你飞腿呀,不敢?对不对?怕抛拖!”志高逗他。
见怀玉揉着痛楚,志高又道: “不要怕,你爹光有个头,说不定他是个脓包啊——” “去你的,”怀玉不哭了,“还直个劲儿跟人家苦腻。
我爹怎么还呀?你姊揍你你还不还?” “我姊从来也不揍我。
”志高有点惆怅,“我倒希望她揍我一顿,她不会,她不敢……” “刚才你不是回去吗?” “我回去拿钱。
” “那你要到哪里去?睡小七的黄包车去?” 志高朝怀玉眼睛: “哪儿都不去了,见您老无家可归,我将就陪你一夜。
” “别再诓哄了,谁要你陪,我过不了吗?我不怕冷。
” 蜷缩坐了一阵,二人开始不宁了。
冷风把更夫梆锣的震颤音调拖长了。
街上堆子的三人一班,正看街巡逻报时,一个敲梆子,一个打锣,一个扛着钩竿子,如发现有贼,就用钩竿子钩,钩着了想跑也跑不了。
更夫并没发现大杂院北房外头的墙角,这时正蹲着两个冷得半瘫儿似的患难之交。
志高想了一想,又想了一想,终把身上袄内塞的一沓报纸给抽出两张来,递给怀玉: “给。
加件衣服!” 怀玉学他把报纸塞进衣衫内,保暖,忍不住,好玩地相视笑了。
志高再抽一张,怀玉不要。
志高道: “嘴硬!” “你不冷?” “我习惯了呢。
我是百毒不侵,硬硬朗朗。
” 怀玉吸溜着,由衷对志高道:“要真的出来立个万儿,看你倒比我高明。
” 怀玉一夸,志高不免犯彪。
“我比你吃得苦!”志高道。
方说着,志高气馁了,他马上又自顾自: “吃得苦又怎样,我真是苦命儿,过一天算一天,日后多半会苦死。
” “不会的。
” “会!嗳嗳怀玉,你记得我们算的卦吗?” “记得,我们三个是——” “甭提了,我肯定是‘生不如死’,要是我比你早死,你得买只鸭子来祭我。
” “要是我比你早死呢?” “那——我买——呀,我把丹丹提来祭你。
” “你提不动的,她蛮凶的。
” “咦?丹丹是谁呢?吓?谁?”志高调侃着,怀玉反应不及:“就是那天那个嘛。
” “那天?那个?我一点都记不起了。
哦,好像是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呢,对了,她回天津去了,对吧?嗳,你怎么了?” “怎么?别猫儿打镲了,不听你了。
” “说真的,还不知道有没有见面的日子呢。
要是她比我哥儿俩早死,是没法知道的。
” “一天到晚都说‘死’!怪道王老公唤你豁牙子!” “哦,你还我报纸,看你冷‘死’!还我!好心得不着好报!” “不还!指头儿都僵了。
” ——房门瞅巴冷子豁然一开,凶巴巴的唐老大吆喝一声: “还不滚回屋里去?” 原来心也疼了,一直在等怀玉悔改。
怀玉嘟着嘴,拧了,不肯进去。
“——滚回去!”做爹的劈头一记,乘势揪了二人进去。
冷啊,真的,也熬了好些时了。
渴睡的志高忙不迭怂恿:“进去进去!”又朝怀玉眼睛,怀玉不看他,也不看爹。
是夜,二人蜷睡在炕上。
志高还做了好些香梦:吃鸭子,老大的鸭子。
梦中,这孩子倒是不亏嘴的。
直到天边发白。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一朝恶妇予乔
- 我真的不是大佬[无限]风月不知
- 驭虫师肥皂有点滑
- 邪气凛然跳舞
- 总裁她总是哭唧唧李秋琅
- 兽血沸腾静官
- 诱降竹马轻呼吸
- 箫声咽鬼马星
- 和反派魔尊互换身体后镉圆
- 头柱今天也想被祓除寞寂
- 小可怜手握爽文剧本李温酒
- 被献祭后和恶龙在一起了[重生]不渡星河
- 热搜女王育儿手记/每天都会上热搜!宋家小四
- 我独自美丽一丛音
- 异界龙魂暗夜幽殇
- 打穿西游的唐僧涂章溢.QD
- 蝼蚁你爸爸
- 喜欢你的每一秒鹿灵
- 五个霸总争着宠我/被五个总裁轮流补习的日子[穿书]枯木再生
- 盈盈ABO嗜酒吃茶
- 全民皆萌宠暖暖的茶
- 痴傻蛇夫对我纠缠不休安曦
- 我给男配送糖吃[快穿]五朵蘑菇
- 女配求生日常[穿书]陆灵儿
- 问道红尘(仙子请自重)姬叉
- 灵气复苏:全民海克斯我与君同醉
- 屌丝奶爸变男神垂钓看烟花
- 乱世猛卒燕麦叶
- 我和兄弟一起穿越红楼爱吃豆豉酱的比丘斯
- 三国:刘备,天命所归三造大汉费诺诺
- 三国:我辅佐刘备再兴炎汉我才是猫大王啊
- 新科状元的搞笑重生路2二月沫
- 我,秦王世子,用盒饭暴出百万兵蛟变化龙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玄德公,你的仁义能防弹吗?爱吃鱼2021
- 清宫秘史十二章马踏飞花
- 武林风云之九阳传奇息烽客
- 北疆战神:从边军小卒到杀穿蛮族一心向龙
- 开局神雕侠侣我靠中二拯救小龙女路灯下的流浪猫
- 我在北宋教数学吉川
- 北京保卫战逆转,延大明百年国祚孙苏中
- 用户90391439的新书:悟用户90391439
- 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青岳
- 大明:我崇祯,左手枪右手炮二月十八
- 平推三国,没人比我更快以空空
- 一剑独尊自摸一条
- 大明第一墙头草随轻风去
- 我在仙侠世界研究科学甜荔酒
- 谁主噬心弘狄
- 系统带我闯武侠汴梁的夏大夫
- 武林风云之九阳传奇息烽客
- 抱歉了小师弟,伤害男人的事我做不到!由山自海
- 温阮霍寒年温阮霍寒年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永乐入梦我教我自己当皇帝用钱打我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北京保卫战逆转,延大明百年国祚孙苏中
- 开局神雕侠侣我靠中二拯救小龙女路灯下的流浪猫
- 世子无双,这纨绔不当也罢!老牛爱吃草
-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南岳清水湾
- 大明:我崇祯,左手枪右手炮二月十八
- 系统带我闯武侠汴梁的夏大夫
- 大唐:身为太子的我只想摆烂交出思想
- 大宋第一猎户:女帝别低头!一起抓水母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秦世风云录饺子面条火锅
- 娘娘,对不住了春山果实
- 天娇:铁木真崛起与大元帝国前传天狼峰的古尊人
- 锦衣卫:陛下,何故谋反!叁金诶
- 大明权谋录Four古往今来
- 一世豪权,一世月明非心水京
- 混沌再临之灭仔纳里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
- 权倾朝野,女帝求我别反准备起飞
- 洪荒之亘古大道审判者
- 从公爵之子到帝国皇帝老庄屋
- 穿越大唐:农家子弟挣钱忙智阳雨
- 两界:玻璃杯换美女,买一送一宁衰人
- 我让高阳扶墙,高阳为我痴狂抱星明月居
- 孤鸿破苍穹星光入枫海
- 诸天帝皇召唤系统遗落的影子
- 永乐入梦我教我自己当皇帝用钱打我
- 碎星阁神速熊猫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穿越古代我的空间有军火:请卸甲百万负翁不想再负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我热痢的马
- 水煮大明嗒嗒猪
- 秦世风云录饺子面条火锅
- 东汉末年:我携百科平天下特特eve
- 都市我能望穿万物忘忧无虑
- 我的美艳师姐妹燕山夜话
- 穿越大唐,我靠变身闯天下美溪旺仔
- 七情碗夜凰
- 冷艳总裁的超级狂兵北冥听涛
- 傲神传蚂蚁
- 横行霸道踏雪真人
- 苦闯仙侠界云隐青山
- 在成为西门吹雪的日子里笑点烟波
- 天神之血天明
- 乱世红颜之凤临三国孟回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