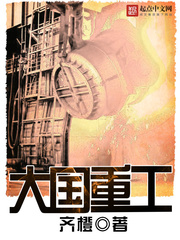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民国十四年•冬•北平(2/3)
太太似的公公在谈,中途竟唉声叹气,一点都不好玩。
怀中的猫又睡着了,所以她轻轻把它放到床上去,正待要走。
呀,不知看“打鬼”的人散了没有,不知叔叔要怎样慌乱地到处找她。
一跃而起: “我走了。
” 说着把一个竹筒给碰跌了。
这竹筒是烟黄的,也许让把持多了,隐隐有手指的凹痕。
这也是一个老去的竹筒,快变成鬼了,所以站不稳。
竹签撒了一地,布成横竖斑驳的图画,脱离常轨的编织,一个不像样的、写坏了的字。
丹丹忙着掇拾,志高和怀玉也过来,手忙脚乱地,放回竹筒中去。
“这有多少卦?”志高问。
“八八六十四。
” “竹签多怪,尖的。
” ——孩子不懂了,这不是竹,这是“蓍”。
它是一种草,高二三尺,老人家取其下半茎来作筮卜用。
它最早最早,是生在孔子墓前的。
子曰……所以十分灵验。
王老公就靠这六十四卦,道尽悲欢离合,哀乐兴衰。
直到他自己也生厌了,不愿把这些过眼烟云从头说起。
以后不算啦。
“给我们算算吧?”怀玉逼切地央求,“算一算,看我们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好?我不信就是这个样子……” “老公,您给我们算?最后一次?”志高示意丹丹,“来求老公算卦,来。
” 三人牵牵扯扯,摇摇曳曳,王老公笑起来。
撒娇的人,跟撒娇的猫都一样。
我不依,我不依,我不依。
这些无主的生命。
现世他们来了,好歹来一趟,谁知命中注定什么呢? 谁知是什么因缘,叫不相干的人都碰在一起。
今天四个人碰在一起了,也是夙世的缘分吧。
王老公着他们每人抓一支。
丹丹闭上眼,屏息先抓了一支。
然后是志高,然后是怀玉。
正欲递与王老公时,横里有头猫如箭在弦,飕地觑个空子,奔窜而出…… “哎呀!”丹丹被这杀出重围的小小的寂寞的兽岔过,手中蓍草丢到地上去。
因她一闪身,挨倒怀玉,怀玉待要扶她一把,手中蓍草就丢到地上去。
志高受到牵连,手中的蓍草也丢到地上去。
一时间,三人的命运便仿似混沌了。
“又是它。
”丹丹眼尖,认得那是在万福阁大佛殿上窜过的黑猫——真是头千方百计的猫。
“老公,我帮你追回来。
”丹丹认定了这是与她亲的,忘了自己的卦。
王老公道:“由它吧。
” “您不是不准它们出去吗?”志高忙问。
“去的让它去,要留的自会留。
” “它会回来的。
”丹丹安慰老人。
怀玉望着门缝外面的,堂堂的世界: “对,由它闯一闯。
要是它找不到吃的,总会回来。
找得到吃的,也绑不住它吧。
” 怀玉省得他们的卦。
拈起三枝蓍草,递向王老公。
“来,老公,给我们说说,我们本事有多大?”怀玉澄澄的眸子,满是热切期望,仿佛他是好命,他的日子光明,他觉得自己有权早日知道。
目下还未到开颜处,绸缪一下,也就高升了。
他心中也有愿呀。
志高丹丹凑上一嘴:“说,快说呀。
” 王老公摇首,只道:“看,都弄胡涂了,这卦,谁是谁的?来认一认。
” 三人认不清。
“不要紧,您都一起说了,我们估量一下是谁的命。
” 算卦的老太监闭上眼睛。
啊,黄昏笼罩下来了,疲倦又笼罩了他,他有点蔫不唧的,萎靡了。
只管把玩手中的卦,十分不耐烦。
“不算了。
年纪轻轻的,算什么卦?”王老公说。
“老公骗人,老公说话不算数!” 三个孩子都气了。
老人闹不过,推了两三回,终妥协了: “好好好。
我说,我说。
不过也许要不准的——” “您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怀玉道。
“——一个是,生不如死。
一个是,死不如生。
”王老公老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暧昧的表情。
是你们逼我的,我不想泄漏的,“还有一个,是先死后生。
” “那是什么意思?”丹丹绕弄着她长辫梢上的红头绳,等着这大她一个甲子的公公来细说她命里的可能性。
老公没有再回答。
他不答。
“哦?老公原来自家也不懂!”丹丹顽皮地推打他,“您也不懂,是吧?” “生不如死,死不如生,先死后生……”怀玉皱着他横冷的一字眉。
“哈,谁生不如死?谁又死不如生?嗳,看来最好的就是先死后生。
”志高在数算着,“说不定那是我——不不,多半是怀玉,怀玉比我高明。
” 说着,不免自怜起来了:“我呢,大概是生不如死了,我哎,多命苦!呜呜呜呜!” 然后夸张造作地号啕大哭,一壁怪叫一壁捶打着身畔的红木箱子。
“别乱敲!你这豁牙子!”王老公止住,不许志高乱动他的木箱子,保不定有些什么秘密在里头,或是贵人送给他的、价值不菲的首饰,他和猫的生计便倚仗这一切,直到最后一口气。
“丹丹!丹丹!” 外头传来一阵喊声。
丹丹应声跃起至门前,不忘回过头来:“黄叔叔找来了!我要走了!” 志高忙问:“到哪儿去?” “回天津老家去,给黄哥哥养病。
” 院子里出现一个矮个子的四十来岁的壮汉,久经熬练,双腿内弯成弓形,步履沉沉稳稳,一身江湖架子。
背上是个脸色苍白中带微黄的、穿得臃肿的十来岁少年,两只手软垂着,眼睛中有无限期望,机灵地转动。
嘴一直咧着,不知道是不是笑意。
他是丹丹那此生也无法再走一两步的黄哥哥。
“走啦!”叔叔唤丹丹。
这苦恼的邋遢的老粗,身上棉袄不知经了多少风霜雨露,竟变得硬了。
如同各人的命,走得坎坷,渐渐命也硬了。
因为命硬,身子更硬了。
他爱怜着眼前这没爹没娘的牡丹。
“牡丹”,花中之王呀,改一个这样担待不起的名字? “你怎的溜到这里来,叨扰人家啦,回去吧。
‘打鬼’完了,人都散了。
” 末了又谦谦对王老公说道:“不好意思,小姑娘家蹦蹦跳的,话儿又村。
您别见怪。
丹丹,跟公公和哥们说再见。
” 丹丹笑着,挥手: “王老公,怀玉哥,切糕哥,我们再见!” 叔叔在她耳畔骂:“看,到处找你,累得滋歪滋歪的!” 怀玉笑:“再见。
” 志高努力地挥手:“再见再见。
喂喂喂,什么时候再见?我请你吃切糕。
真的,什么时候?会不会再来?摇头不算点头算。
” “我不知道呀。
” 丹丹远去了,三步一蹦,五步一跳,辫子晃荡在傍晚太阳的红霞中。
少年的心也晃荡在同一时空内。
初春的夕阳不暖,只带来一片喧嚣的红光,像一双大手,把北平安定门东整座雍和宫都拢上了,绝不放过。
祖师殿、额不齐殿、永佑殿、鬼神殿、法轮殿、照佛楼、万福阁……坐坐立立的像,来来去去的人,黑黑白白的猫,全都逃不出它的掌心。
“老公,她会不会再来?”志高问。
怀玉没有问。
他心里明白,志高一定会问的。
但怀玉也想知道。
王老公没答。
在人人告别后,院子屋里,缓缓传来算卦人吹笛子的怪异闷哼,似一个不见天日的囚徒,不忿地彻查他卑微而又凄怆的下狱因由。
青天白日是非分的梦。
人在情在,人去楼空,这便是命。
腾腾的节气闹过了,空余一点生死未卜,恍惚的回响。
怀玉和志高已离庙回家去。
中国是世上最早会得建桥的国家了:梁桥、浮桥、吊桥、拱桥。
几千年来,建造拱桥的材料有木、有石,也有砖、藤、竹、铁,甚至还动用了冰和盐。
桥,总是横跨在山水之间,丰姿妙曼,如一道不散长虹。
地老天荒。
在北平,也有一道桥,它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东边是天坛,西边是先农坛。
从前的皇帝,每年到天坛祭祀,都必经此桥。
桥的北面是凡间人世,桥的南面,算是天界。
这桥是人间、天上的一道关口,加上它又是“天子”走过的,因而唤作“天桥”。
天桥如同中国一般,在还没有沦落之前,它也是一座很高很高的石桥,人们的视线总是被它挡住了,从南往北望,看不见正阳门;从北向南瞧,也瞧不着永定门。
它虽说不上精雕细琢,材料倒是汉白玉的。
只是历了几度兴衰,灯市如花凋零……后来,它那高高的桥身被拆掉,改为一座砖石桥,石栏杆倒还保存着,不过就沦为沼泽地、污水沟。
每当下雨,南城的积水全都汇积于此,加上两坛外面的水渠,东西龙须沟的流水汇合,涨漫发臭,成了蚊子苍蝇臭虫老鼠的天堂。
大家似乎不再忆起了,在多久以前?天桥曾是京师的繁华地,灯市中还放烟火,诗人道:“十万金虬半天紫,初疑脱却大火轮。
” 年过了,大小铺子才下板,街面上也没多少行人。
两只穿着破布鞋的脚正往天桥走去。
左脚的脚趾在外头露着,冻得像个小小的红萝卜头儿。
志高手持一个铁罐子,低头一路捡拾地上长长短短的香烟头,那些被遗弃了的不再被人连连亲嘴的半截干尸。
拾一个,扔进罐子里头,无声地。
只有肚子咕咕响。
过了珠市口,呀,市声渐渐便盖过他的饥肠了。
真是另有一番景象。
才一开市,满是人声、市声、蒸汽,连香烟头也盈街都是。
志高喜形于色。
虽然天桥外尽是旧瓦房、破木楼,光膊赤脚、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在这里过一天是一天,不过一进天桥就热闹了。
大大小小的摊棚货架,青红皂白的故衣杂物……推车的、担担的,各就各位了。
那锅里炸的、屉里蒸的、铛里烙的……吃食全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志高走得乏了,见小罐中香烟头也拾得差不多,先在一处茶摊坐下来,喝了一碗大碗茶。
口袋里不便,只好对卖茶的道: “三婶子,待会给您茶钱。
” 三婶子见是志高:“没钱也敞开了喝吧,来吧,再喝。
” “不了,一肚子是茶水。
” 志高蹲到茶摊后面旯旮儿,小心地把烟头剥开,把烟丝一丁点一丁点地给拆散,再掏出一沓烟纸,一根一根卷好,未几,一众无主的残黄,便借尸还魂,翻新过来。
志高把它们排好在一个铁盒上,一跃而起,干他的买卖去。
“快手公司!快手牌……爷们来呀,快手牌烟卷,买十根,送洋火!” ——他根本没洋火,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一买十根的顾客。
都是一根一根地卖出去,换来几个铜板。
不一会,他也就有点贃头了。
好,先来一副芝麻酱烧饼油条,然后来点卤小肠炒肝,呼噜呼噜灌一碗豆腐脑,很满足,末了便来至一个黏食摊子前。
卖的是驴打滚。
只见一家三口在分工,将和好的黄豆面,擀成薄饼,撒上红糖,然后一卷,外面沾上干黄米面,用刀切成一截一截,蘸上糖水,用竹签挑起吃。
正想掏个铜板买驴打滚,又见旁边是切糕车子,一念,自己便是丹丹口中的“切糕”啦,马上变了卦,把铜板转移,换了两块黏软的甜切糕,还对那人道: “祥叔,往后我不唤志高,我改了名儿,唤‘切糕’。
哈哈哈!” “得了,瞧你乐鸽子似的!”祥叔笑骂。
忽闻叮咚乱响,有人嚷嚷:“来哪,大姑娘洗澡啦……” 那是一个满嘴金牙的怯口大个子,腮帮子也很大,脸鼓得像个“凸”字。
看来才唱了一阵,嗓门不大,丹田不足,空摆出一副讲演的架势,你无法想象他是这样唱的: “往里瞧啦往里瞧,‘大姑娘洗澡’!喏,她左手拿着桃红的花毛巾,右手掇弄着澡盆边……咚咚咚呛,咚咚咚呛……” 大个子站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子旁边,箱子两头各拴了绳子,他便一边响起小锣小鼓小镲,一边拉绳子,箱子里头的一片片的画片,便随着他的唱词拉上拉下。
“又一篇呐又一篇,‘潘金莲思春’在里边,她恨大郎,想武松,想得泪颠连……咚呛,咚呛,咚咚咚呛……” 观众们就坐在一条长板凳上,通过箱子的小圆玻璃眼往里瞧。
聚精会神的,脖子伸得长长的,急色的。
拉洋片的大个子,不免在拉上拉下的当儿,故弄玄虚,待要拉不拉,叫那些各种岁数的贫寒男人,心痒难熬,在闷声怪叫:“往下拉!往下拉!” 各自挂上羞怯的暧昧的鬼鬼祟祟的笑,唱的和看的,都是但求两顿粗茶淡饭的穷汉,都是在共同守秘似的交换着眼色。
大个子心底也有不是味儿的愧怍,好似虎落平阳——谁知他是不是虎?也许只错在个头太大,累得他干什么都不对劲,尤其是这样地贩卖一个女人的淫荡,才换几个大子儿。
但他支撑着他的兴致,努力地吆喝: “哎,又一出,又是一出……” 志高目睹这群满嘴馋液的男人,天真而又灼灼的眼神,他想起……呸!他没来由地生气了,他觉得这样的兽无处不在,仿佛是他的影子,总是提醒他,即使光天白日,人还是这样的。
志高充满憎厌和仇恨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怪叫: “洗澡!洗澡!妈的,看你们老娘洗澡!” 然后转身朝桥西跑了。
天桥最热闹的,便是这边的杂耍场。
他扒开人群,钻进一个又一个的场子找人去。
在天桥讨生活的行当很多,文的有落子馆、说书场。
武的就数不尽了,什么摔跤、杠子、车技、双石、高跷、空竹、硬气功、打把式、神弹弓、翻筋斗……天桥是一个“擂台”,没能耐甭想在这混饭吃,这块方圆不过几里的地方,聚集着成百口子吃开口饭的人。
虽云“平地抠饼”,到底也是不容易的。
故,每个撂地作艺的摊子,总有他们的绝活儿,也不时变着新花样。
志高钻进一个场子去,左推右撞地才钻出个空儿,只见怀玉正在耍大刀。
大伙都被这俊朗的男孩所吸引。
他凝神敛气,开展了一身玩意,刀柄绑上红绸带,随着刀影翻飞。
刀在怀玉手中,忽藏忽露,左撩右劈,不管是点、扫、推、扎……都赢得彩声叫好。
他一下转身左挂马步劈刀,一下左右剪腕叉步带刀,纵跳仆步,那刀裹脑缠头,又挟刀凌空旋风飞腿,一招一式,都在显示他早早流露的英姿。
刀耍毕,掌声起了,看客们把钱扔进场子里。
怀玉的爹唐老大,马上又赶上场来。
唐老大是个粗汉,身穿一件汗衫,横腰系根大板带,青布裤,宽肩如扇面展开。
在这刚透着一丝春意,却仍料峭的辰光,穿得多,露得少,他手里拎着一把大弓,扎了马步,在场中满满地拉开,青筋尽往他脖子和胳膊绕。
看客自他咬牙卖力的表演中满足了,也满意了,扔进场子里的钱更多,有几张是花花的纸币,更多的是铜板,撒了一地。
江湖卖艺,要的是仗义钱,行规是不能伸手,所以等得差不多了,怀玉方用柳条盘子给捡起来。
演过一场,看客们也纷纷散去。
板凳旁坐了志高,笑嘻嘻地,把一块切糕递给怀玉。
“唐叔叔。
”志高忙亲热招呼。
“唔。
”唐老大淡淡应一下,只顾吩咐怀玉,“拿几枚点心钱,快上学堂去。
别到处野啦,读书练字为要。
去去去!” 唐老大说着,便自摊子后头的杂物架上取过布袋子,扔给怀玉,叮嘱: “回来我要看功课。
” 怀玉与志高走了。
“你爹根本不识字,还说要看你功课呢。
” “他会的,他会看字练得好不好,要看到蹊蹊儿跷的,就让我‘吃栗子’。
他专门看竖笔,一定得直直的,不直了,就骂:‘你看你看,这罗圈腿儿!’可厉害着呢。
” 唐老大不乐意怀玉继承他的作艺生涯。
在他刚送走怀玉的时候,便有官们派来的人,逐个摊子派帖子,打秋风来了,什么“三节两寿”,还不是要钱? 怀玉心里明白,吃艺饭不易,父子二人虽不至饥一顿饱一顿,不过贃得的,要与地主三七分账,要给军警爷们“香烟钱”。
要是来了些个踢场子找麻烦的混混儿,在人场中怪叫:“打得可神啦!”你也得请他“包涵”。
爹也说过: “咱两代作艺,没什么好下场,怀玉非读书不可!穷了一辈子,指望骨血儿中出个识字的,将来有出息,不当睁眼瞎,不吃江湖饭,老子就心满意足了。
” ——怀玉不是这样想。
他喜欢彩声。
他喜欢站在一个睥睨同群的位置,去赢得满堂彩声。
不是地摊子,不是天桥,飞,飞离这臭水沟。
所以他有个小小的秘密,除了志高之外,爹是不知道的。
“志高,我上学堂了。
待会你来找我,一块到老地方去。
” “唉!我到什么地方遛弯儿好?” 怀玉不管他,自行往学堂上路去。
志高百无聊赖,只得信步至鸟市。
前清遗老遗少,每天早晨提笼架鸟,也来遛弯儿。
他们玩鸟,得先陪鸟玩,鸟才叫给你听。
要是犯懒,足不出户不见世面,喂得再好,鸟也不肯好好地叫。
志高走至鸟市,兴头来了。
这个人,总有令自己过瘾的方法。
说起来也是本事。
什么画眉、百灵、红蓝靛颏、字字红、字字黑、黄雀等,叫起来千鸣百啭,各有千秋。
志高听多了,也会了,模仿得叫玩鸟的人都乐开了,有时也赏他几枚点心钱。
志高于此又流连了一阵。
怀玉的教书先生今年五六十。
他穿长袍马褂,戴圆头帽。
学堂其实在绒线胡同的大庙里,这是间私塾,只有十个学生,全是男孩,从五岁到十五岁都有。
怀玉不算“学生”,因为他没交学费,只因唐老大与丁老师有点乡亲关系,求他,管怀玉来听书和干活。
怀玉来了,算对了时间,便径往大庙院内的树下敲钟,当当当,学生陆续也到了。
一般自己走来,也有有钱的,穿黑色的无翻领的中山装,铜钮扣儿,皮鞋,坐洋包车来了。
脚踩铜铃响着——怀玉看在眼内,不无艳羡之情,好,我也要这一身。
人齐了,怀玉才到学堂最后一条二人长桌前坐定。
一见桌上,竟有小刀刻了中间线。
他一瞥身畔那学长,是班上最大的,十五岁,家里有点权势,一直瞧不起卖艺人。
“唐怀玉,你别过线!” “哼!谁也别过线!” 老师今天仍然教《千字文》: “……交友投分,切磨箴规。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节义廉退,颠沛匪亏。
性静情逸,心动神疲。
守真志满,逐物意移……” 正琅琅读着这些困涩难懂似是而非的文字时,班上传来拌嘴口角。
一个竹制的精致上盖抽屉式笔盒应声倒地。
一个布袋儿也被扔掉,墨盒、压尺和无橡皮头的木铅笔散跌。
“叫你别过线!老师,唐怀玉的大仿纸推过来,我推回去,他就动粗!” “老师——” “唉,怀玉,你收拾一下,罚到外头给我站着。
”丁老师无法维护这个不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都市最强战神梁一笑
- 从综武世界开始逍遥诸天沐阳千羽
- 我和兄弟一起穿越红楼爱吃豆豉酱的比丘斯
- 从公爵之子到帝国皇帝老庄屋
- 纵横诸天:从修炼辟邪剑法开始不吃鱼虾的猫咪
- 我,秦王世子,用盒饭暴出百万兵蛟变化龙
- 两界:玻璃杯换美女,买一送一宁衰人
- 签到修仙:我在青城山躺成剑仙慕斯雨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水浒之往事随风间间间
- 穿越古代异界争霸闲人小小
- 明末造反:我的盲盒能开神装七辛海棠
- 我在北宋教数学吉川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青岳
-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南岳清水湾
- 人在古代,从抢山神娇妻开始崛起女帝
- 诗泪洒江湖云里慕白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大明:我崇祯,左手枪右手炮二月十八
- 不良人之大唐麒麟侯隐城的驼龙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我在大明洪武当神仙爱吃肥肠香锅的盛星河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我热痢的马
- 屌丝奶爸变男神垂钓看烟花
- 踏雪寻青梅云笺寄晚
- 穿越大唐:农家子弟挣钱忙智阳雨
- 穿越古代异界争霸闲人小小
- 签到修仙:我在青城山躺成剑仙慕斯雨
- 替弟为质三年,归来要我让战功?芳龄真的二十
- 三国:魂穿刘禅,工业经贸兴汉室作者山语清风
- 星极宇宙社恐的中年人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逆命武侠行随风飘扬的喜哥
-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南岳清水湾
- 幸福生活从穿越开始男人苦咖啡
- 谁主噬心弘狄
- 大唐:身为太子的我只想摆烂交出思想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物流之王之再续前缘笔尖路悠然
- 这破系统非要我当皇帝总有那一天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天娇:铁木真崛起与大元帝国前传天狼峰的古尊人
- 重生六9:倒爷翻身路惊恐不安九仙君
- 轉生成豬的我,突破只能靠雙修爱鯊客
- 武侠:莽昆仑严久霖江洲雨林
- 乱世红颜之凤临三国孟回千古
- 大夏第一神捕木有金箍
- 横行霸道踏雪真人
- 屌丝奶爸变男神垂钓看烟花
- 三国:我辅佐刘备再兴炎汉我才是猫大王啊
- 从天龙活到现代的武林神话歌尘浪世
- 温阮霍寒年温阮霍寒年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水浒之往事随风间间间
- 北军悍卒虎虎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永乐入梦我教我自己当皇帝用钱打我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穿越古代我的空间有军火:请卸甲百万负翁不想再负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我热痢的马
- 我在大明开医馆我就是个保底命
- 龙吟三国小川流水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铁血龙骧:从将门遗孤到开国圣主琪琪拥有小狗叭
- 边军凶猛赤阳
- 东汉末年:我携百科平天下特特eve
- 重生六9:倒爷翻身路惊恐不安九仙君
- 七情碗夜凰
- 洪荒之鲲鹏绝不让位李九郎
- 纯阳第一掌教池宁羽
- 冷艳总裁的超级狂兵北冥听涛
- 极品仙途闻人毒笑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