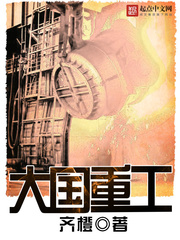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一章 今岁故人来(2/3)
ellip&hellip也没说什么不好的话。
谭庆项的话驳回了她的猜想。
他在问傅侗文是谁,怎么不说话。
傅侗文没有回答。
两人隔着电话线路,像面对着面,辨不清容颜,却能感知彼此的呼吸。
谭庆项不再问了,他那样的一个好奇心重的人,又时刻关心着傅侗文,为何会不问?也许是被他关到了门外去,或是用一个眼神制止了。
沈奚握住听筒,听到他咳嗽了声,心也跟着微颤了颤。
他的声音低下来,问她:&ldquo你在哪里?&rdquo 简单四个字,倒好似他万水千山找她,找寻不到&hellip&hellip沈奚忽然喉头哽住。
&ldquo刚刚来的电话也是你吗?&rdquo他又问。
&ldquo嗯&hellip&hellip我有事想和你谈。
&rdquo她屏着气息。
&ldquo好,我刚刚到上海这里,前一刻才进了家门。
本来是安排了今天下午到你的医院,去看一看你&hellip&hellip可车在路上被事情耽搁了。
你现在是在哪里?医院还是家里?&rdquo他解释着,又笑着道歉,&ldquo抱歉,让你一个女孩子先来找我。
&rdquo 哪里还是女孩子,又不是十几岁的人了。
可他对她讲话的语气和态度,仍像是她的三哥。
沈奚忽然哽咽起来,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病历上,仓促用手抹去纸上的泪水,泪又滴在手背上。
只好将病历合起来,推到一旁去,手压在眼睛上。
傅侗文毫无征兆地停下来:&ldquo我们见一面,好不好?&rdquo 窗口有风灌进来,吹在话筒上。
沈奚微微调整着呼吸,低声道:&ldquo今天吗?我听说你明天就要到医院去了,我们今天在电话里说就好。
你刚到上海,要先好好休息&hellip&hellip&rdquo 况且她还没做好见面的准备。
他安静着,良久才道:&ldquo不要这样哭,我现在就去见你。
&rdquo 所有的景物都被泪水晃得变了形,她低头,想哭,又在笑。
光圈叠在眼前,书架也是,钟表也是,连面前的电话也都像被浸在水下&hellip&hellip其实真正被浸在泪水里的,只是她自己的双眼。
&ldquo你在哪里?&rdquo他再一次地问。
&ldquo在霞飞路上,&rdquo她鼻音很重地说,&ldquo霞飞路的渔阳里。
&rdquo 这是个傅侗文一定会熟悉的地名。
他那间小公寓也是在霞飞路上,在礼和里,离这里步行只需要十分钟,走得快的话,七八分钟足够了&hellip&hellip 聪明如他怎会猜不到,她租赁的公寓选在霞飞路,是因为他。
听筒里,有布料摩擦过的动静,是衬衫袖口蹭过了话筒。
傅侗文像换了个手在拿听筒,或是,站得不舒服,调了姿势。
沈奚隔着电话,猜测着他的一举一动。
&ldquo我就在礼和里的公寓。
&rdquo他说。
他在这里?为什么不去公馆,而回了这里? 她脸挨着话筒,走神着。
&ldquo二十分钟后你再走出来,我会来接你。
&rdquo他说。
&ldquo嗯。
&rdquo她答应了。
听筒被放到属于它的位置上,这通电话结束。
她始终绷着神经在打这一通电话,此刻身体松弛了,傻坐着,像还在梦里。
等到表针跳过十几分钟,她终于梦醒,跑去脸盆架上拿着毛巾,对照镜子擦脸。
镜子里的她只有黑眼珠和嘴唇是有颜色的,余下的都是白的,白得骇人。
是一昼夜没睡,又哭得太厉害了,像个病人。
她来不及上妆,把毛巾丢下,用手搓了搓脸皮,搓出来一点血色。
幸好这两年的职业提升了她穿衣穿鞋的速度,跑到楼梯上,锁上门时,钟表的指针还没到最后的时间刻度上。
&ldquo沈小姐,你要出去啊?&rdquo房东太太在楼下独自坐着,大门意外地没有敞开来。
往日房东太太都喜欢敞着门吃晚饭,顺便还能和隔壁邻居聊上两句。
沈奚无意寒暄,应着声,飞步下楼。
&ldquo沈小姐&hellip&hellip&rdquo房东太太又撸了一下她的碧玉镯子。
沈奚和她接触两年,晓得这位房东太太是个心思藏得很深的人,从不多管闲事,每每她想说点什么,都要前后掂量,把手腕上的镯子撸一会儿,才肯开口。
&ldquo陈太太,你有事情吗?&rdquo沈奚决定先开口,节省时间。
&ldquo沈小姐啊,我刚刚给我先生电话,他说你们医院附近的马路上学生在闹事,砸了车,也伤了人。
&rdquo房东太太低声说,&ldquo你说会不会闹到我们这条路上来啊?我刚刚说好要去拿料子,都不敢出门。
你回来时,遇到了吗?是不是很严重啊?&rdquo 沈奚意外:&ldquo我没有碰到,我很早就走了。
&rdquo &ldquo要不,你还是不要出去了,&rdquo房东太太又说,&ldquo我想早一点锁门。
&rdquo 沈奚看着外边黄昏的日光:&ldquo我尽量早回来好吗?&rdquo &ldquo我不是要管你的私事,你晓得我胆小的。
&rdquo 再说下去,真要迟到了。
&ldquo陈太太你放心,我不会太晚回来的。
&rdquo 沈奚匆忙开门,跑出去,不再给房东太太说话的余地。
里弄里,大家都在烧饭。
沈奚起先走得急,到要转弯的路口,忽然就放慢了脚步。
她低头,两手从头顶摸着自己的长发,顺到下头,以捋顺头发的动作让自己平心静气一些。
身侧的一户人家敞着门,老妇人正端着一盆翠绿菜叶,倒进锅里,水和热油撞出来的炸响蹿出来。
沈奚像被这声音催促着,愈发难以静下心。
她走出小路的拐角,看到弄堂口的一条石板路尽头,停了一辆黑色轿车,半开着车门。
她出现时,车门被人从内打开。
霞飞路上的有轨电车正从轿车旁驶过去,傅侗文背对着电车,慢慢下来,他像很疲累的样子,站立不稳,右手扶在车门上。
仍旧是立领的衬衫、领带,却没有穿着合身的西装上衣,而是穿了件软呢的大衣。
红色的石库门砖,青灰色的瓦,连排的法国梧桐树,还有他&hellip&hellip 沈奚瞧得出他精神状态不佳,但比两年前好了许多。
现在傅家再没人能压制他,傅老爷和傅大爷背靠的大树倒了,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有利于他养病。
沈奚终于在他的注视下,到了车旁。
该叫什么?侗文?三哥?还是傅先生? 她嘴唇微微颤抖着,是要哭的征兆,她低头,咬了下唇,尽量克制。
当年的话未说完,累积到今日,却不晓得从何处起头。
&ldquo我下楼的时候已经晚了,被房东拦住说事情&hellip&hellip还是迟到了。
&rdquo她在解释自己刚刚遇到的困境,解释她晚了的缘由,至少有话来做开场。
&ldquo你没有迟到,&rdquo他反而说,&ldquo是我到得太早了。
&rdquo 这是傅侗文特有的说话艺术,从不让她窘迫,这也是他在相逢后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两人本是隔着轿车门,他绕过来,立到她身前。
沈奚一霎以为他会做什么。
他也以为自己会做什么,可只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伸手,在她的眼角轻拭了下:&ldquo风大,不要哭伤了眼。
&rdquo他低声说。
沈奚眼上的是他手指的热度,稍触即逝,怔忡着。
两人对视着,真是有风,吹在她脸上,眼睛和脸颊都热辣辣地疼。
果然哭过不能见风,她两手压了压眼睛,对他掩饰地笑着:&ldquo我们去哪里?&rdquo 傅侗文腾出手,把车门关上,也笑:&ldquo介不介意陪我吃一点东西?&rdquo 沈奚轻点头。
傅侗文没有再上车的意思,同她并肩而行,在梧桐树下沿着霞飞路走。
轿车缓缓在两米远的距离跟着他们两个的进程。
傅侗文很熟悉这里的饭店和西餐厅,挑了最近的地方。
沈奚进了西餐厅,透过闭合的玻璃门,注意到后边不止一辆车在跟着他们,至少有四辆。
紧跟在两人身后,有五个人守在了门外。
狭小的西餐厅,楼下有两桌用餐的人,见到门外的阵势都在窃窃私语,猜想傅侗文的身份。
老板也不用傅侗文开口,主动带他们两个上了楼。
二楼是个开阔的平层,只在窗边摆了两桌,中间那里有个长木桌,倒像是进步人士用来聚会的场所。
傅侗文在点餐。
梧桐树的叶子压在玻璃上,被桌上蜡烛的光照出了一道道的叶脉纹路。
她隔着叶子,也能看到楼下的轿车,过去从未有过的阵势。
他这次来究竟要做什么?只是为了给父亲看病吗? 二楼从始至终只有他们两个客人。
窗外风很大,碧绿的树叶在深夜里一蓬蓬拥挤着,是一团团彼此推搡的黑影子。
沈奚察觉他没动静,抬眼看他。
傅侗文毫不掩饰、不避嫌地望着她。
方才在马路边,有人、有车,万物干扰,乍一相对,眼前的景物都不是景物,是想象。
而现在椅子对着椅子,人面对着面,一个四方小餐桌下,他的皮鞋在抵着她的鞋尖。
都是真的。
反倒是她懂得收敛,垂了眼,摆弄着手边的银制刀叉。
&ldquo这两年&hellip&hellip变化好大。
&rdquo她含糊说。
&ldquo还是乱糟糟的,&rdquo她想用时政上的话题和他聊,但无奈谈资少,总不见去分析军阀们的关系,&ldquo你有了许多企业,对吗?你已经拿回自己的东西了,对吗?你已经有很多钱了,是吗?&rdquo她记得小报上说的有关他的每个细节,也记得他的&ldquo嗜钱如命&rdquo。
沈奚在试图避开那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拣了许多的话题。
可傅侗文不给她机会,也不接她的话。
他在盯着她的脸、眼睛和嘴唇在看,看每一处的变化,把她的脸和记忆里的重合上。
&ldquo为什么不说话?&rdquo她快演不下去了。
他淡淡地笑着:&ldquo还有问题吗?我在等你问完。
&rdquo 沈奚摇头,轻挪动刀叉。
桌下的脚也移开,他却恰好察觉了,皮鞋又向前挪动,和她挨着。
这样细微的小心思,不露骨的暧昧&hellip&hellip过去两人同居时他常做。
他最懂女人。
沈奚抿着唇角,不再说了。
&ldquo那我开始回答了。
眼下是很乱,但好在总理也在做好事,比如坚持参战。
只要我们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胜出,就有机会在国际上谈判,拿回在山东的主权。
&rdquo &ldquo嗯。
&rdquo她认真听。
&ldquo还有你问我,钱的问题,&rdquo他沉默了会儿,似乎在计算,&ldquo我在天津的银行有九百万,上海汇丰银行存了一千两百万,在境外的银行也有六七百万,有很多的矿,大概十四座,入股的企业更多,超过了二十家。
现在算大约是有八九千万,也许已经到了一万万。
&rdquo 沈奚一个月工资是三百六十七大洋,加上医院给的额外补贴,不到四百大洋,已经算是沪上很高的薪资了,仅次于正、副院长。
她错愕之余,打从心底地笑着,点点头:&ldquo真好。
&rdquo 这两年她时常在想,这样乱的局面恰好适合他大展拳脚,她不在身边,没有拖累,一定会好很多。
要不然光是他父亲和大哥,就会利用自己来威胁到他。
现在看,确实是这样。
&ldquo真好。
&rdquo她忍不住重复。
高兴的情绪到了一定地步就是大脑空白,语言匮乏。
眼下的她正是这样,她是由衷地为他开心。
&ldquo为什么没有去英国?也没有去庆项给你介绍的医院?&rdquo换了他来问她。
&ldquo我想试试自己的运气,&rdquo她说,&ldquo这家医院是新成立的,要是去仁济和中山那样的医院,还真是要介绍人,保证不能离职,不能结婚。
听上去是不是很可怕?&rdquo &ldquo不能结婚?是很不人道。
&rdquo他评价。
&ldquo所以我没去大医院真是幸运的。
后来,又是好运气,诊治了一个在上海有名望的病人,名声就传开来了。
又因为我是女医生,许多名流的太太都要来找我,这时候看,我的性别也占了便宜。
&rdquo 她用简短的话,把两年说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老板送了前菜来。
沈奚轻点头致谢,等老板下楼,她想到了要紧的事:&ldquo为什么不让我参与你父亲的治疗?&rdquo &ldquo明天我会去医院,今晚不说这些。
&rdquo他不愿谈。
也好,想要说服他改变主意,总要拿着病历细细分析,还要让段孟和一起做解释。
还是明天公事公谈好。
老板端来羊排。
他还记得她爱吃羊排,他的是意面。
&ldquo你还在忌荤腥吗?偶尔吃几口,不是很要紧。
&rdquo &ldquo胃口不是很好。
&rdquo他微笑。
沈奚拿起刀叉,在切羊排时,留意到他吃饭的动作很慢,刚刚前菜时在说他父亲的病,没注意到他吃了什么。
此时的傅侗文用叉子在面里搅了两下后,没抬起手,已经做出一副没食欲的神态,随便拨弄了一口后,搁下叉子。
晚餐过后,傅侗文似乎有很要紧的事要去办,交代了自己轿车的司机,让人要亲自把沈小姐送到家门口。
他在车旁,为她关上车门后,微欠身对车窗内的她说:&ldquo今天不能送你回去,抱歉。
&rdquo沈奚摇头:&ldquo只有五分钟的车程,不用送,我走回去也好。
&rdquo &ldquo回去早点上床,&rdquo他在车窗外,低声说,&ldquo愿你有一整晚的好梦。
&rdquo &ldquo嗯,你也要休息好,&rdquo她其实很担心,&ldquo你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
&rdquo 傅侗文笑一笑:&ldquo还不是老样子。
&rdquo 他招手时,车窗自动闭合。
沈奚头枕在座椅上,等车开出路口,悄悄向后窗看。
傅侗文已经在几个人的簇拥下,上了后面的一辆车,她见到的仅有大衣下摆和皮鞋。
那辆车门被关上,车反向驶离。
是去公共租界的公馆?抑或是回礼和里? 也没问他这次来上海,是要全程陪同父亲治病,还只是来办手续?是不是确定了治疗方案就要回京?她手心按在自己脸颊上,是冷的手热的脸,凉的风烫的心。
礼和里的公寓门外,守着十几个人。
傅侗文的这间公寓一直无人居住,只是偶尔会有人来装电话、检修管道和电器。
今日突然来了人,邻里起初都在猜测,是不是那位沈小姐回来了,等到晚上又纷纷打消了这个念头。
来的人是位背景深厚的先生,而跟随保护他的是青帮的人。
身旁人为傅侗文打开公寓大门,万安早在门内候着,要扶他,被傅侗文挡开,他沿着狭长的木质楼梯兜转而上,到二楼,谭庆项和沙发上坐着的男人同时立身。
傅侗文笑一笑,瞥见书桌上有信纸,旁边还有个空墨水瓶。
&ldquo是给你的信,我可不敢动。
&rdquo谭庆项说着,替他脱大衣,身边的人也来帮忙。
两个大男人一左一右,尽量让他的衣服脱得顺畅。
等大衣脱下来,傅侗文单手去解自己的衬衫领口,还是不得劲,只得继续让人伺候着。
直到上半身都露出来,后背和右侧肩膀有大片的瘀青肿胀。
&ldquo还是要敷药,&rdquo他自己说,&ldquo叉子也握不住。
&rdquo &ldquo那帮学生是下了狠手。
&rdquo谭庆项也是气愤,&ldquo你还不让我们动手,要我说,那些人里一定混着江湖上的,裹了层学生的皮而已。
&rdquo 下午,他们到了医院附近的街道,本想顺了傅侗文的意思去看沈奚,没承想被上街游行抗议的学生组织围住了。
不知谁说了句,那辆车上坐的是巨商傅侗文,学生们被军阀背后的黑手、革命和民族叛徒这样的话语刺激着,砸了车。
傅侗文不让人对学生动手,以致被人弄得这般狼狈。
谭庆项把衬衫给他套回去,下楼准备冰敷的东西。
&ldquo今日疏忽了,感觉是中了圈套。
&rdquo傅侗文对另外那个男人笑,&ldquo万幸的是,你没有跟着车,让你一回到上海就看到暴力行径,怕会吓坏了你这个绅士。
&rdquo 周礼巡也笑:&ldquo在美国时什么没见到过,不怕的。
前个月,美国农场主们还聚众烧死了一个黑人,闹得很厉害,我也是在游行里去的港口。
&rdquo 傅侗文把领带还给对方:&ldquo物归原主。
&rdquo 他方才走得急,在一楼接了电话就走,身上是被撕扯坏的衣服,干净的西装衬衫都在箱子里,来不及熨烫,只好临时借用老友的。
衬衫和大衣来自谭庆项,领带来自周礼巡。
&ldquo光是道谢可不行,你要告诉我去见了谁。
庆项喜欢卖关子,害得我猜到现在。
&rdquo 傅侗文拿起那张信纸,将手探出窗口,抖落纸上的灰尘: &ldquo是过去的恋人。
&rdquo 伫立在窗边,这是他少年时候站立的地方,她应该也在这个位置观赏过窗外风景。
他道:&ldquo一个可以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孩子。
&rdquo 傅侗文展开信纸: &ldquo三哥,见字如晤。
假若你看到这封信,那是我同你又错过了&hellip&hellip&rdquo 这是沈奚北上前留下的,多年后终于到了他的手里。
那时她的心情、她的打算和她的忐忑,写明白的,还有没写明白的,傅侗文都能看透。
央央&hellip&hellip 沈奚回到家,房东太太跟她上了楼。
从医院外的打闹说到了房东那个在银行就职的侄子,劝说着沈奚周末和对方见一面。
平时的她还能应付两句,今日实在没心情,草草敷衍着把人送出门。
由于傅侗文的&ldquo没胃口&rdquo,她也没吃多少东西,送走房东太太后,翻找出来新年时患者送来的奶油饼干充饥。
饼干盒子上是一幅西洋画,花园洋房。
她吃一会儿,想到他过去说要在山东买一幢洋房,再吃一会儿,又想到初到纽约时饿得不成样子,翻找出巧克力填肚子,事后在信上讲给他听,就收到了当年还是稀罕物的夹心巧克力。
她拿起玻璃杯,一口口喝着冷茶。
搁下杯子,将书桌上的台灯&ldquo啪&rdquo地一关,在书桌上趴了会儿,迷糊着睡到手臂全麻,再醒来已是凌晨一点。
这么晚了?她的脚在书桌下寻找拖鞋,不晓得被自己睡着后踢到哪里去了,踩到的地方都是地板&hellip&hellip电话铃突然响起,炸开在耳边。
她被震得完全清醒了,来不及再找拖鞋,提起听筒:&ldquo你好,我是沈医生,是什么病人?几号床的?还是来急诊的?&rdquo 完全的条件反射。
深夜电话全是从医院来的,在护士的值班室里,医院大小医生的联系电话都贴在墙上,以备不时之需。
听筒里有着风吹话筒的动静,像在窗边。
&ldquo吵醒你了吗?&rdquo是傅侗文。
她停住,脚还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保持着刚刚离座的姿势,因为听到是他,反而没了下一步的行动,停了半晌,才说:&ldquo没有,我刚好&hellip&hellip睡醒。
&rdquo 是刚刚好,不早不晚。
&ldquo我太久没来南方,不适应这里的天气,&rdquo他忽然轻松地抱怨说,&ldquo自己睡不着,却来打扰你。
&rdquo 她不由得紧张:&ldquo不舒服吗?谭先生没有在附近?&rdquo &ldquo没有,&rdquo他笑,&ldquo我是说我人没有不舒服。
&rdquo 那就好。
&ldquo今天我回到公寓,看到了你留下的东西。
&rdquo他说。
是信吗?那时心乱如麻,一心北上,现在再想内容,青涩、忐忑的心思全都剖白在那封信里。
她还记得自己在信里对他说:&ldquo怕战事一起,你我南北两隔,不堪设想&hellip&hellip&rdquo 仿佛是个预言,最后还是南北两隔,该来的、该面对的,谁都逃不掉。
&ldquo是书架上满满一排的空墨水瓶。
&rdquo他出乎意料地没有提那封信,&ldquo我在想,你在仁济的实习生活一定很辛苦。
&rdquo 是了,书架上还有墨水瓶,她都没丢掉。
当时是想着日后有机会,要对他自卖自夸一番,才整整齐齐地码放了一排。
她含糊着说:&ldquo也不是很辛苦,那么多病历资料都很值钱,段孟和肯让我带回家抄写,已经是帮忙了,我也要卖力还给他。
&rdquo 听筒里,他安静着。
沈奚回忆着那间公寓,记起一楼的柜子:&ldquo还有一楼的柜子我翻过,对不起,擅自动了你的物品。
还是要郑重道歉的。
&rdquo 他笑:&ldquo并不重要,不值得你为这个道歉。
&rdquo 沈奚听着风声,想提醒他不要深夜在窗口吹风,犹豫了会儿,还是没说。
听他又道:&ldquo这间公寓,当初本打算送给你的,这里的物品你也都有处置的权利。
&rdquo 努力维持着的叙旧氛围,被一个&ldquo当初&rdquo轻易打破。
余情未了的人,最怕就是提到当初和曾经。
窗外黑黝黝的,没有光,所有人家都灭灯睡下了。
她在椅子上坐下来,继续去找桌下失踪的拖鞋,也是巧,一下子就寻到了。
好似刚刚撞了邪,明明就在原地。
听筒里有朦朦胧胧的虫声唧唧,是了,那间公寓下有个草坪,只是才初春,怎么就有了虫鸣?也真稀罕。
沈奚漫无目的地走神,把他那句话的余威冲淡、冲散了。
&ldquo我上午还有门诊,如果没有十分要紧的事&hellip&hellip&rdquo她在试图找借口。
聪明如他,自然懂得她的念头:&ldquo我也是饿了,要去问问楼下有什么能吃的东西。
&rdquo &ldquo那正好,&rdquo她马上说,&ldquo明天见。
&rdquo &ldquo明天见。
&rdquo 电话挂断,沈奚才后知后觉地想,他是如何拿到自己的电话号码的?也许是段孟和,或是医院,或是电话局都有可能。
次日在医院食堂里吃早饭时,凡是见到她脸色的同事,都认定她是劳累过度,埋怨段副院长不体恤她的身体,竟然让手下最得力的外科医生如此操劳。
沈奚含糊笑笑,领了早饭,坐到窗边,独自吃着。
身后两个住院医生恰好在说昨天闹事的细节,因为就在医院附近的街道上,这两个医生也远远围观到了砸车的现场。
沈奚听着他们描述,心惊肉跳。
段孟和在她对面的位子落座,单刀直入地问:&ldquo昨天见到病人家属了吗?&rdquo &ldquo见到了,&rdquo她公事公办地说,&ldquo不过家属拒绝在医院之外的地方谈,我准备今天和你一起说服他。
&rdquo 段孟和并不意外:&ldquo昨天他被砸了车,估计是真没心情谈。
&rdquo &ldquo你是说昨天医院外&hellip&hellip是他?&rdquo 段孟和很是奇怪:&ldquo你不是去找他了吗?我听说他还受了伤,你没看出来?&rdquo 沈奚被问住。
自己也是傻,竟瞧不出诸多的疑点。
他所有的西装都是量体定做的,稍不合身形都会让裁缝上门裁改,认识这么久,唯有昨日是穿着不合身的大衣。
还有下车时他扶着门的动作,关车门的姿态,甚至是他的胃口不好,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ldquo他伤到什么地步?&rdquo沈奚脱口问。
段孟和笑了:&ldquo昨天是你见到了他,不是我,沈医生。
&rdquo 她本就懊悔自己的疏忽,被段孟和一说,更难过了:&ldquo他和你约了什么时候见面?&rdquo &ldquo约了下午两点,不过一点他会带着律师先到医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不是你的朱砂痣[穿书]阮寐
- 无敌天下神见
- 我做偏执大佬未婚妻的日子白秋练
- 暴君每晚梦我五月锦
- 穿到七零当厂花唐柒鱼
- 嫁给冷血男主后我变欧了[穿书]/嫁给杀器后我变欧了[穿书]蒸汽桃
- 箫声咽鬼马星
- 大地飞鹰古龙
- 小可怜手握爽文剧本李温酒
- 热搜女王育儿手记/每天都会上热搜!宋家小四
- [聊斋]活人不医南陶
- 我独自美丽一丛音
- 异界龙魂暗夜幽殇
- 身为卧底的我要成为港口Mafia首领了昭文
- 定风波来风至
- 蝼蚁你爸爸
- 至尊剑皇半步沧桑
- 二号首长黄晓阳
- 五个霸总争着宠我/被五个总裁轮流补习的日子[穿书]枯木再生
- 炮灰的马甲又又又掉了冰糖火锅
- 草莓味的A不想恋爱凉皮就面包
- 重生之大画家轻侯
- 我一见你就笑郑三
- 我是校草他姑奶奶十六月西瓜
- 桃枝气泡栖见
- 我和兄弟一起穿越红楼爱吃豆豉酱的比丘斯
- 纵横诸天:从修炼辟邪剑法开始不吃鱼虾的猫咪
- 大秦血衣侯:我以杀敌夺长生鎏金淬火
- 我,秦王世子,用盒饭暴出百万兵蛟变化龙
- 两界:玻璃杯换美女,买一送一宁衰人
- 奉旨当里长:百姓的明义南明蓠惑
- 三国:魂穿刘禅,工业经贸兴汉室作者山语清风
- 水浒之往事随风间间间
- 玄德公,你的仁义能防弹吗?爱吃鱼2021
- 清宫秘史十二章马踏飞花
- 武林风云之九阳传奇息烽客
- 我在北宋教数学吉川
- 逆命武侠行随风飘扬的喜哥
- 北军悍卒虎虎
- 逆世灵霄纪书写杨意
- 天宇守护神雪熬九天
- 一梦江湖之宸霜玄龙锁逍遥九宸天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我李承乾,在大唐和李二斗智斗勇日月兴明
- 幸福生活从穿越开始男人苦咖啡
- 大明第一墙头草随轻风去
- 大明中兴之我是崇祯三千纸
- 大宋第一猎户:女帝别低头!一起抓水母
- 我,大楚最狂太子蜗牛王子
- 大明锦官梦苏梦沉
- 大明:一次呼吸一两银,殖民全球!一木木
- 带着现代军火系统闯大明静静的思考人生
- 大楚武信君冷剑情
- 铜镜约金钩钓金鲤
- 一身反骨,你叫我爱卿着调
- 无名剑主刘治宏
- 穿越成献帝,我为大汉再续三百年言谈橘汁
- 大宋枭雄仙庙的马尔高
- 大明辽国公空樱
- 三国:我辅佐刘备再兴炎汉我才是猫大王啊
- 世子凶猛:谁敢和我抢女人?南朝陈
- 三国:魂穿刘禅,工业经贸兴汉室作者山语清风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逆仙未朗
- 北京保卫战逆转,延大明百年国祚孙苏中
- 用户90391439的新书:悟用户90391439
-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南岳清水湾
- 大明:我崇祯,左手枪右手炮二月十八
- 幸福生活从穿越开始男人苦咖啡
- 谁主噬心弘狄
- 大唐:身为太子的我只想摆烂交出思想
- 大明中兴之我是崇祯三千纸
- 我在大明洪武当神仙爱吃肥肠香锅的盛星河
- 铁血龙骧:从将门遗孤到开国圣主琪琪拥有小狗叭
- 穿越商朝,为了人族而战叫不醒的清醒着
- 祖龙假死,我带领大秦走向日不落!松之江
- 列强?大秦面前哪个敢称列强?流失的回忆
- 综武:堵门道观,开局截胡五绝甜御上弥
- 英烈传奇爱笑的花猫
- 医圣杨洪一用户29394119
- 笔架叉将军悬崖梅
- 绝品仙尊潇然
- 葬魂天刃西门冷血
- 都市最强战神梁一笑
- 屌丝奶爸变男神垂钓看烟花
- 纵横诸天:从修炼辟邪剑法开始不吃鱼虾的猫咪
- 新科状元的搞笑重生路2二月沫
- 穿越大唐:农家子弟挣钱忙智阳雨
- 替弟为质三年,归来要我让战功?芳龄真的二十
- 孤鸿破苍穹星光入枫海
- 逆世灵霄纪书写杨意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我在仙侠世界研究科学甜荔酒
- 谁主噬心弘狄
- 剑影书迷之宝藏寻踪喜欢半减七和弦的子豪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大唐:身为太子的我只想摆烂交出思想
- 这破系统非要我当皇帝总有那一天
- 三国:曹营第一扛把子爱吃腐皮卷的巫玄
- 天娇:铁木真崛起与大元帝国前传天狼峰的古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