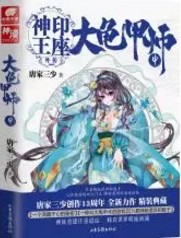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千金兽(3/3)
起,于足趾中间厚实处下刀,上挑至肘尖与后肢,再沿后腿内侧挑至后阴,及另一后肢,再由后阴尾部挑至尾中,如此则开膛完成。
之后就是剥皮,先剥离后肢,再剥出足趾。
雄獍狖剥到腹部,须剪去阴茎,以免毛皮受损。
剥到尾部要抽出尾骨,拉紧獍狖双足,方可扯下整张皮。
如果气力不够,用利索的刀具一寸寸割,也是一样。
” 阴冷的话声如一把火,烧尽了香的芬芳。
原来极艳之后,就是凋谢。
长生颤声道:“剥完皮,它还活着吗?”阴阳道:“自然活着,只是没了毛皮,不出几个时辰必死。
若是可怜它,你不妨给它一刀,送它成佛。
” 长生顿时汪出满眶的泪,侧侧没好气地冲紫颜说道:“好端端问什么剥皮,吓坏长生。
”说罢狠狠挖了阴阳一眼,把长生拉到一边好生安慰。
紫颜若无其事地答道:“易容之术,本与血腥相伴,他不是孩子,该长大了。
” 长生早不是个孩子,剥皮的疼痛,亲历过刀割的人自会明白。
侧侧猛然望向紫颜的双眸,看不清其中潜藏的往事,盈满眼的,永是装点过的流水行云。
熏香过后是染色。
雪白、嫣红、莺黄、粉青、麝金……诸多颜色混杂在金嵌宝石螭虎盘上,另一侧放了断骨、剖面用的大小剪子,刀锋锐得印出绰绰人影。
少见到紫颜的这几样利器,长生忍不住伸头来看,待瞧清楚了,眉头一蹙。
紫颜道:“要易容,少不得动刀子,今次原以为能指望你。
” 想起少爷说过五成的话,长生涔涔汗下。
见了如今这架势,莫说当初自称的三成,就是一成的胆气也消散了。
越是易容得像,就越把要诱骗的獍狖送上黄泉,若反复想这些生死恩怨,他如何敢下第一刀? 紫颜毫不犹豫地持剪而立。
他要剪断猸貉躯壳的牵绊,看偷梁换柱,能否以假乱真。
血光,漫散在众人的双眼。
磨平了尖牙,续长了短尾,紫颜满手血污,悠闲地招呼长生,“你来看,獍狖有一缕藕色的耳簇毛,下颏鱼白,那日你完全没瞧出来。
”说着,把两种颜色混合了香膏,分抹到猸貉耳后、下颏,再取了熏笼微微加热。
在紫颜的手下,猸貉越来越不像它自己,眉眼身形一点点向獍狖转变。
满眼触目惊心,长生不敢看又不得不看,努力成为异类,原来千辛万苦。
千姿不知想到什么,凝视的双眼仿佛望向了虚空,依稀的神情与当日饮下醉颜酡时相似。
这一场易容,直把人心也变易。
紫颜垂手向了围屏后微笑时,众人再辨不出猸貉的身影。
躺于案上的是一只獍狖,景范捧出乌木箱子里的那只摆在一处,简直分不清真假。
两只小兽无声地卧着,众人一脸的解脱,长生见了,抑制不住的难过如泉水喷涌,汩汩地在心头跳动。
他伤感地走出屋去,天已然黑了,空荡荡饿得难受。
忽然想到,獍狖以腹鸣求偶,深山里那只被追踪的猎物,此刻是否在咕咕叫唤?孤独之饿,会让它错认易容后的猸貉为伴么? 那夜,长生睡得颇不安稳,梦中,一时獍狖,一时猸貉,错换交杂。
烈烈阳光下,乍闻到一模一样的香气,原是一喜。
可转身,刺目的尖刀却钉住了身子,疼得再叫不出声。
阴阳的双眸如迎面挥来的刀,想逃,长生已惊叫醒了过来,衣衫尽湿。
次日一早,听到猸貉的叫声,长生打了哈欠赶出去看。
猸貉以新生的容貌在阳光下逡巡,不停地追了尾巴跑跳,想看清究竟是何物。
异样醇厚的香气亦令它茫然若失,时不时嗅嗅足趾,冲阴阳质疑地狂叫。
粗嘎的嗓音让阴阳大为皱眉,频频鞭打训斥,长生见了,忍不住趋上前说道:“我家少爷以落音丹易人音色,太师能否容他为猸貉想想法子?” 阴阳停了动作,冷笑道:“只是,除了腹鸣声外,我们无人听过真獍狖平日里的叫声。
”长生一愣,结巴道:“那……那……我……太师想如何补救?”阴阳道:“毒哑它,或者,你家先生有药只管拿来,不必罗嗦。
”长生拔腿就跑,急急地叫道:“太师且慢,我这就去求药来!” 阴阳望了他的背影,再看脚下惊疑乱转的猸貉,叹了一口气。
还有五日,他勉强能让猸貉习惯如今的身体,可是,獍狖又会习惯这个假同类么? 猸貉哑了,所用的药名“骨笛”,如横亘在喉间的鱼刺,一月出不了声。
慢慢地,像硬骨脆了、碎了,始能恢复本来音色。
只是猸貉不知道,它怀了巨大的恐惧,猜不透为何短短几日,面目全非。
抵不过皮鞭与诱惑,猸貉屈服、忍受,失魂落魄地接受阴阳的训练,规矩地按他每个手势与声调指引,坐卧起行,像一具行尸走肉。
它的眼亦被紫颜易容成了浅褐色,人人都看出它眼神里的不开心,但每个人更关切那只将被捕获的獍狖,因为它更昂贵、更美丽。
长生这时懂得可怜猸貉,先前他怜惜獍狖会死,而如今,觉得猸貉更是生不如死,不会再有同类爱它陪伴它,它的存在,不久后就会是一个奇异的笑话。
当獍狖死后,猸貉何去何从?它会是个永远的怪物,拿什么来容放自身? 紫颜没有长生的伤春悲秋,每日在阴阳训练猸貉时,他就在旁观看,时时提点两句。
阴阳起先有几分恼怒,后来听他说得有理,只能悻悻应了。
约莫五六日后,猸貉逐渐习惯了香气环绕的新皮囊,心情不再异常烦躁。
那时,看它不记得自己的原形,长生有点悲哀。
想,若换了人,是否也如此容易忘本?轻易就抛却从前。
叹息完了,心下不免为猸貉解释,毕竟它又能如何?苦苦地抵抗,不如逆来顺受,有更简单的快乐。
而后,勾引的时刻到来。
山依旧是山,长生眼中,出发前却添了诡异的姿色,林木越发油青葱翠。
亮色中,深褐的树皮上有一只只眼睛般的伤痕,像上了年纪的老人,凝视天地神奇。
一行人舍了马匹,步行走了一枝香的工夫,山回路转,突然流下一道飞瀑。
水势不大,细细长长,如青丝泻下,漂白成人间颜色。
走到跟前,才听到哗哗的水声,一下,一下,连绵不绝,与飞花般的水滴一同奔赴而来。
猸貉从阴阳的掌下抬头,望了欢快的流瀑,双目终有一抹鲜活。
一路逆风走来,众人无声地藏身在阴阳特制的隐秘埋伏中,据说獍狖尚在一里之外。
阴阳松开缰绳,容猸貉自由,而它,这些天最记得的就是獍狖的气味。
猸貉笨拙地走了两步,回头张望,习惯了束缚,它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阴阳抛弃。
等待了片刻,它没有听到阴阳的动静,忽然想通了似的拔腿就跑。
它几乎不假思索地往前方冲去,顺了那些树木上香气的指引,决然地冲向獍狖的巢穴。
直到猸貉消失了影子,千姿斜睨了阴阳一眼,徐徐吐出几字:“几时能回?”阴阳沉吟片刻:“快则半时辰,慢则一日。
”千姿遂不答话。
长生憋住一颗心,满怀期待地注目林木深处,盼望猸貉和獍狖永不要出现。
这一等就从白日等到了天黑。
黄昏时大片彩云热烈地烧着,映红了每个人的脸。
紫颜、侧侧、萤火、千姿、景范、阴阳、轻歌,一个个看去似有心事,眼中光影浮泛。
长生只求天早早黑透,他们困了乏了,再找不到那些精灵们的踪迹。
可惜世间事难如人愿。
千姿毫无倦意,躲了一天,长生想死的心都有,他却神采奕奕,如等待远行的恋人归来。
景范与阴阳不时地伏地听声,细声地向千姿禀告什么,他的眼就愈加像擦亮的火石,要在山林里放一把火。
终于,切切碎碎的足音传来,獍狖香气沿了风的轨迹,优雅飘至。
众人屏息聚目,目睹两只獍狖一前一后玩耍了跑来。
漆漆夜色中辨不清谁是谁,像映照了镜子,它们有说不出的欢喜。
见了这个场面,每个人俱是欣慰异常,唯有长生的脸,倏地僵在了风里。
它们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尽情歆享这刻的欢愉。
一向警觉的獍狖竟会如此大意,骁马帮的人喜出望外。
而长生察觉到他们欲飞的心,恨不能蓦地跳出来,将獍狖吓走。
但是他不敢,纵然内心极度想放走它们,他无法违逆千姿熠熠双眼下的决心。
他怕当面的冲撞会让少爷首当其冲地受伤,只是,此刻他反复问自己,为什么紫颜竟没有说过一句不想接这生意的话。
如果有那么一句,该有多好。
这世上,动情的总是先输。
长生就这样痴痴地望着嬉耍中的獍狖与猸貉,明白自己决不会让任何人剥去它们的皮。
即使是少爷,也不能。
他不禁流下泪来。
想到獍狖总是谨小慎微地藏匿在山石缝里,昼伏夜出,独来独往,此刻有了猸貉,竟能成为一对儿,无机心无烦恼地相处,这大概是前世的缘分。
若不是人心险恶地将它们配在一处,它们终究会各自孤独地过一辈子。
只是梦有醒的一刻。
它们互为异类,能有这短暂热闹的相聚,在它们平庸的人生里已是异数。
很快,猸貉会打回原形,露出它贪吃肉食的本性,而獍狖在被捕后,将猛然意识到信赖的愚蠢,深深恨上一切试图靠近的他者。
当那时,美丽的聚首破碎成了假相,獍狖被猎手死死按在地上,无限卑微地哀号,猸貉的心里会不会哭?獍狖又会有多绝望? 它们是畜生。
长生知道,他依稀看见了有所渴望的自己,在某一日,于一个圈套里幸福地陷落。
他不敢再想下去,眼角的余光里,景范和阴阳慢慢在接近。
那些好时光,到头了。
獍狖绝望的叫声传来,一下下撞击他的耳膜,长生捂住了心眼耳鼻,屈膝跪在地上。
他低声干嚎,眼泪一点点从喉咙里咳出来,乌黑的眼前闪过一团团锦簇。
仿佛被抓的是他自己,带刺的绳索死死勒住了脖子,从上到下的窒息,清晰地从每寸肌肤传来。
他无法呼吸,眼前混乱地闪过无数人影,尖叫怒喝,他像猸貉一样出不了声。
直至有手轻轻搭在他肩上,紫颜的温柔话音如有浮力的水,托他出了汪洋。
“长生,我们回去罢。
” 眼皮终能破开,望了紫颜的眼,长生一脸的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口。
拖了少爷的手臂,他大哭:“我不要它死!少爷,你救救他。
” 从昏沉中苏醒,长生差点忘记了前事,但一个激灵,回忆如恶梦缠身。
他大叫一声坐起,见萤火端了安神汤递来。
“我不要喝药!”长生蛮横地推开。
萤火安之若素,把汤药放在案上,转身就走。
长生连忙叫住他:“少爷呢?”萤火道:“不晓得,我单熬药来着。
”长生道:“谁开的药?”萤火简单地道:“先生。
”长生跳下床榻往外走。
紫颜果然不知去向。
明月高挂,夜已深了,长生微微地失望,对少爷,也对他自己。
路过一间屋,骤然有浓郁熟悉的香气飘来,他立即停住了脚步。
獍狖的呜鸣如婴孩的哭泣,揪得他心酸。
他深吸一口气,蓦地有了个念头。
紫颜的屋门轻掩着,很容易推门而入。
姽婳备好的香盛在红木藤面八方盒里,用格笼隔开,稍取一点就能颠倒众生。
长生依稀知道那些香派何用处,摸索片刻,寻出几块青色的香,稍嗅了嗅便觉头昏目眩。
他捏着香发颤,想了想,终拿了香闪出屋去。
颤颤地持香往骁马帮一众的房门走去,萤火的身影倏地贴了过来。
“拿来,我去。
” 长生按住心口,好一阵平复了,懂他的意思,感激地递过香去,萤火如鬼影般瞬间消失在他眼中。
长生愣愣地站了,慢慢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径自朝獍狖的牢房走去。
若非要放走它们,他根本无颜面对那些无辜的眼神。
竟没有一个看守,长生喜出望外地闯进去,见了笼子里的獍狖和猸貉,反而迟疑起来。
两个小家伙惊惧地望了他,身子互相依偎,并没有因了陷阱而疏分。
长生心下感佩,手在笼栓上粘住,想多看它们一眼,又隐隐地为后果担忧。
门外影子一晃,长生以为是萤火,忙站起身来相迎。
不料花红软玉,进来一个香人儿,正是侧侧。
她瞥了笼子一眼,笑道:“你想做什么,只管做就是。
”长生心头一热,道:“我……怕被少爷骂。
”侧侧道:“有我在!你以为骁马帮的人去哪儿了?” 长生知是她制住了守卫,不声不响跪下朝她磕头,侧侧连忙扶起他,轻声道:“伤天害理的事,就算被人拿刀逼着,也不能做。
你放心,我不会眼睁睁看獍狖被活剥了皮去。
” 长生尚未回答,黑暗中传来一声轻笑:“哦?看来连我也不能阻止你们了。
” 紫颜如幽魅飘进了屋子,望了两人微笑。
长生嗫嚅不语,侧侧一拍他的头,道:“见了他你就矮一截,怕什么,我们要放生,他也不能拦了。
” 紫颜笑道:“是是,就依你。
” 长生惊喜地抬头,侧侧走到笼前,扭头道:“外面安全了?”紫颜道:“我瞧见萤火鬼鬼祟祟的,想是不会有人醒着。
”侧侧闻言,道:“那好,我放生了。
” “等等,送走它之前,我要取件物事。
”紫颜喃喃地说道,“否则真是空入宝山。
” 长生小声道:“不会要取它肚子上的皮吧?” 紫颜道:“若有那一块皮,我能做出世上最完美的面具。
” 长生敢怒不敢言,不知该回什么话,侧侧捏捏他的手,笑道:“他连荤腥都不碰,你以为,他舍得剥皮?” 紫颜道:“呀,吓吓他不是蛮好玩的。
”说话间打开笼子,将手抓住獍狖,在它尾后的香囊中几下一使劲,掏出六七粒蚕豆大的香仁。
獍狖左躲右避,浑不知已在鬼门关走过一遭。
侧侧道:“那只死去的獍狖,是不是也能取香?”紫颜摇头道:“香消玉殒,獍狖一死,体内的香囊立即闭合,永远化在骨肉中。
除非,把它一丝丝剁了……”侧侧嗔道:“又来吓人!” 紫颜朝她和长生一笑,取了绣囊贴身收好獍狖香,拍拍手,萤火的身影忽地从空地上长了出来,两肩挑起獍狖和猸貉直奔屋外。
漆黑夜色里,三人的影子映上空笼,如巨刀砍开了枷锁。
长生默默地看着地上的影连成一线,心腾地紧张起来。
“少爷,该如何向千姿交代?” 紫颜的声音说不出的从容,悠然回道:“别忘了,我是易容师。
明日千姿来之前,你们不许进我屋子。
” 骁马帮的人谁也不敢正视公子千姿的眼。
朗朗白日下,每个人脸上青白闪烁,景范和阴阳也黑了脸不作声。
千姿呵呵冷笑了数回,一个人径直到了紫颜房外,一脚蹬开门。
屋内流过摄魂的香气,云端里一片繁华锦灿裹了紫颜。
千姿想也没想,提剑直撩过去,冰凉的剑锋紧逼他的下颌。
“你放走了獍狖。
” 千姿说完,惊异地看到紫颜身披的裘衣绒毛直竖,根根如针,戳得紫颜仿佛刺猬。
放下剑凝视,香风细细中,裘衣如剪了彩云,撕了霞锦,堆了暖玉,切了金银,仙气缭绕盘旋,恍若天机云锦。
“獍狖皮制的祥云宝衣,传说天下仅有一件。
”千姿眸中盛满浮香秀色,连他亦承认此衣的华贵珍奇世间少有。
何况这身皮毛卷了一个妖狐般的人儿,素面朝天,更现出藏在骨子里的媚绝。
“是与不是都不重要,公子有货可以交给主顾才是关键。
放走的獍狖,就任它去吧。
”紫颜洒脱地掀下祥云宝衣,捧在手里交给千姿。
温润柔滑的皮毛在千姿掌中划过,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心里却无丝毫喜悦。
他未必真想见到最后这一袭华衣,若能目睹紫颜的窘迫无力,或许会有更多快意。
只是,他忽然从紫颜处变不惊的眼角后,扫到一点微弱的疲倦。
细小如眨眼时的轻颦,然而仍被千姿敏感地捕捉,为了那么一点的力不从心,千姿觉得,如今的结局已经够了。
千姿冷静地恢复了常态,道:“有这张毛皮,先生何必给猸貉易容,何必跟本公子捕獍狖?直接献出来不就大功告成?”心下在想那故事之无趣,尚好,他会给人意外。
“我想试炼一下易容的手艺,何况……”紫颜顿了顿,“这张毛皮,你买不起。
” 千姿被他一堵,憋得没了言语。
这世上,他不信有无价之宝,一切皆是交易买卖。
他很想说句话回应紫颜给的难堪,只是目光撞上祥云宝衣,不知怎地折了精神,萧索地冷笑了一声。
笑凝在脸上。
千姿忽然想起来,他鲜少有快活的笑容,那些顽皮的、狡黠的、促狭的、天真的笑意,他不记得几时再有笑过。
其实被剥了皮制成华衣的,何尝不是他自己?僵成了绝美的皮囊,再想不起活着时有怎样的快乐。
他匆忙地撇过脸,要收拾这一刻的悲欢。
紫颜早已背过身去,好像什么也没有见着,躺在云母床上悠悠地说道:“昨夜睡得太少,公子容我再歇息片刻。
” 千姿低下头,默默地抱了祥云宝衣走出屋子。
等他走了之后很久,景范从窗下现身,眼中充满了涩意。
长生走来寻紫颜,见状说道:“二帮主有事?”景范想了想,默然点头,长生遂领他进屋。
紫颜闭目假寐,听到动静,睁开眼来。
景范直截了当地道:“如果我没猜错,先生是以其他皮毛易容成獍狖皮吧?虽然我和太师反复瞧了很久,未看出任何破绽,但獍狖皮有异香,若是先生行囊里就有,恐怕早被太师察觉了。
” 长生听得心惊肉跳,不敢有丝毫反应。
紫颜闻言轻笑,悠闲地坐直身,摸了一把鸦青纸扇轻轻摇着,道:“呀,我不要背这罪名,明明是货真价实的獍狖皮制成的宝衣,莫非二帮主连我也信不过?这般珍贵之物,岂能轻易示人?它一直被九道香气所遮,更放在密封的鎏金铜箱里,压在我行李的最底层。
” 景范将信将疑,苦笑道:“是真皮就好,万一用假的骗过了我们,将来到了识货的眼睛面前,骁马帮就是死罪了!”说出“死罪”两字,他自知失言,镇定地微笑掩饰不安。
紫颜道:“放心,砸你们的招牌就是砸我的招牌,这是多年前一位朋友相赠,他来头很大,绝无花假。
” 景范应了,聊了几句终转过话题,道:“先生易容,规矩太少,稍有身家的,付些金银就换了满意的容貌,其实在下看来,先生的生意原本可做得更大。
” 长生猛然抬头。
骁马帮不仅是雄霸一方的江湖帮派,更是赫赫有名的商旅门户,瞧千姿的慵懒气度,操持帮中上下的定是景范无疑。
骁马帮能在北方屹立多年威名不坠,景范的才能想是了得。
紫颜簇着笑,漫不经心地玩弄手上的一枚墨玉扳指,道:“你是说,我该收得多些?” 景范点头:“先生的易容术再厉害,仅是一双手,而人之欲望无穷,若是谁家的生意都接,岂非疲于奔命?我替先生谋算,平民百姓的买卖大可不必做。
其次,少于千金的亦不必应承。
先生是个雅人,为俗人劳苦,不如多为自己打算。
” 他神情诚恳,说得长生不觉动心。
初听他话时,长生心里暗笑这堂堂帮主锱铢必较,透出一股子小家子气,真是落了下乘。
慢慢地,将他所言听进心里去,想到紫颜果真来者不拒地为人易容,到底为少爷不甘。
毕竟对紫颜而言,多几件赏玩的骨董珍奇、多几千几万的金银,不如多睡几个好觉、少些烦心事更养颜。
紫颜斜过眼,声音轻飘飘地荡进景范耳中。
“如是帮主为我谋划,又该如何打算?” “一年只需接得一桩好生意,就可收手优哉游哉。
”景范爽朗笑道,“骁马帮四季各收货一次,出货一次。
一年中倒有大半时日,各自纵情任性,游山玩水,称得上是当今最逍遥的帮派。
” 紫颜微笑:“如此逍遥,竟跻身一流大帮地位,个中奥妙值得玩味。
” 景范眼中射出炽热光芒,紧接着说道:“如先生肯入我帮,在下情愿让贤,请先生坐这二帮主之位。
”紫颜哑然失笑,用扇子掩口垂眉,把印到嘴边的笑意压了回去,淡淡地说道:“对骁马帮来说我百无一用。
在景帮主眼里,我只是对公子千姿有些用处罢了。
” 景范眼中一灰,脸上的血慢慢聚起,哑了嗓子道:“我没先生看得透彻,不能在紧要关头帮上公子。
以先生的睿智,留在公子身边,说不定能救他一命。
” 不知怎地,长生听到这里心里一酸,想到自己,纵有一腔心思想报少爷的恩情,却没有相应的本事能够保护少爷。
景范文武双全,尚嫌无法护得千姿周全,千方百计为对方寻找支柱倚仗,两相比较起来,长生顿觉自己想得天真。
易容,不仅要学紫颜的手艺,更要把自己的一颗心修炼成精,才可在将来不负少爷所望。
紫颜叹道:“有你这心意,千姿也算无憾。
我答应你,将来若他有难,纵然千山万水,我一定赶来襄助。
至于入帮……”他瞥了一眼长生,澹然说道:“我是个闲散的人。
” 景范知道无法说动他,黯然道:“今趟一别,不知何日再见,紫先生请多保重。
”朝紫颜深深一拜,叹息去了。
长生关上房门,拍了胸口,惊魂未定地说道:“险些就被他看破。
不过我也好奇,少爷究竟拿了什么给千姿?” 紫颜横过眼波,道:“那是玄狐裘衣染色改制的,长短正合獍狖皮。
” “当年制衣时,也是……活剥的?”长生艰难地吐出那两字。
紫颜凝视他紧皱的眉,缓缓答道:“想来是吧。
它早成裘衣,再不知什么是痛,只是它若在天有灵,当为救了獍狖而安慰。
” 紫颜一行人走时,骁马帮悉数赶来相送,千姿却不见踪影,景范护送众人骑马下山,依依惜别。
紫颜一众回到马车上,长生心有所牵地举着帘子遥望。
远处依稀有毛茸茸的身影闪动,刚想定睛细看,倏地不见。
长生想到獍狖和猸貉,怅然拉回目光,小声问紫颜:“少爷,猸貉有一日露馅了怎么办?” 紫颜道:“獍狖狡猾但不凶残,不会拿猸貉如何。
至于它们将来会否好好相处,并非我们能掌控。
” 长生无奈地耸耸肩,唯有顺其自然罢了,心下又闪过一念,道:“少爷,你那些名贵的皮草裘衣,是不是也有假的?” 紫颜掩口失笑:“哎呀,叫你给看出来了。
” 长生目瞪口呆:“真是假的?那……就不值那么些银两。
还有上回在皓月谷,和兴隆祥交换的胭脂雪袍子,莫非也是……” 紫颜神秘地一笑:“不可说,不可说。
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世人想穿的,只是它的名字而已。
” 说完,他陷进了身上的碧缥纻布凉衫里,像一只小兽甜甜地闭目睡去。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表妹软玉娇香渊爻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夜行歌紫微流年
- 我始乱终弃前任后他们全找上门了倔强海豹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01入学篇(上)佐岛勤
- 虫屋金柜角
- 失忆后我招惹了前夫萝卜兔子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御佛o滴神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史上第一祖师爷八月飞鹰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全星际都等着我种水果一地小花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锦帐春慢元浅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纨绔心很累七杯酒
- 极品修真狂少墨世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眼泪酿宴惟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夕照斑衣白骨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春生李书锦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球”嗨夕尧未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学长在上流麟
- 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后桑奈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单恋画格烈冶
- 网恋同桌归荼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情敌五军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不差钱和葛朗台寻香踪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杨九淮上
- 非典型NTR一盘炒青豆
- 新婚ABO白鹿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怀孕之后我翻红了[娱乐圈]核桃酸奶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流量小生他天天换人设西西fer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情敌他失忆了紅桃九
- 成为金丝雀后总是被迫穿裙子泯妍酱
- 你叫什么?我叫外卖晒豆酱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单恋画格烈冶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学长在上流麟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共同幻想ENERYS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治愈过气天王落落小鱼饼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流量小生他天天换人设西西fer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我只想好好谈个恋爱!爱吃肉的羊崽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明明有颜却偏要靠厨艺青渊在水
- 小可怜开心是福嘛
- 万物留痕汉堡年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