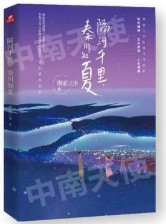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节(3/3)
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
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3 “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
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
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
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
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
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
划船的全是女人。
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
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
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
“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女。
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
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
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
“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
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
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
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
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
还不全。
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
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
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
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
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
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
”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
您工作太多了。
”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
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
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
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
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
她麻利地穿上衣服。
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
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
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
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
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
”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 “你真可爱,我爱你。
”瀚园说。
“我也爱你。
”我说。
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
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
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
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
我一直在‘海鲜馆’。
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
”我说。
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
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
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
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
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
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
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 “行,行。
”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
”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
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嗦了。
我关上车门。
出租车开走了。
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
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
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
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
珠宝店。
时装沙龙。
毛皮装。
皮装。
花店。
然后是一家大银行。
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
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
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
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
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
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
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
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
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
几乎没人在意他们。
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
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
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
周围还没有苍蝇。
他在轻喘。
这么说一切正常。
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
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
又疼了一回。
这我已经熟悉了。
这疼痛我已经经历过。
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剧烈。
某根肌肉,我想。
我不会有心脏病,那位顾问大夫一年前做的心电图检查完全正常。
也许是我对某种食物作出的不良反应。
或是因为炎热。
有可能是我吸烟过多。
我现在急着回“希尔顿”我走得很快,跟路人撞到一起了。
我左脚疼得更厉害了,脚越来越沉重,我感到它是铅做的。
我挣扎着,沿女王中路一米米地走回酒店。
左胸侧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
我喘不过气来。
我紧挨着墙和橱窗走,用手往前摸索,因为我害怕跌倒。
“希尔顿”!“希尔顿”!让我赶到“希尔顿”和我的房间吧,上帝。
我越越趄趄。
我不得不停下来。
空气、空气!我透不过气。
我像一条鱼那样张大嘴吸气。
没人注意我。
霓虹广告彩灯闪烁,变个不停。
人们似乎也一下子动得很快了。
只有我前进得越来越慢。
现在,我已经是真正地拖着我的左脚了。
没什么,根本没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你已经经历过多回了。
你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凶,那妓女刚刚累坏了你。
傻瓜,太傻了。
你应该把她赶出去,呆在你的床上。
女王中路2a号。
也许只剩一百米了。
对于我那是一百公里。
在大厅里我真的脚步踉跄了。
齐默拉吓了一跳,这回他不再微笑了。
“您怎么了,卢卡斯先生?” “没什么。
我不太舒服。
但我就会好的。
” “您不大好,先生,您的嘴唇发紫。
您病了,先生,我叫个大夫” “不!”我喊道,我一下子又能喊了“不要大夫!我禁止您叫大夫!”我不能要大夫。
这没什么。
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因为一旦有人知道了,我的公司就会知道,那么我会怎样呢?“不要大夫,明白吗?”我再一次嚷道。
“当然明白,先生,如果您不想要的话。
如果您非常肯定,一切都好的话。
我我我送您上去。
” 他开电梯送我上去。
我重重地靠在他身上。
要是我随身带着药就好了。
往常我总是随身带在衣袋里。
这回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
当我们来到十一楼时,我相信,我再也无法呼吸了,压根儿走不动了。
走廊的地面似乎在我脚下摇晃。
齐默拉拖着我。
我相当高大,体重七十六公斤。
那位小个子中国人很吃力。
终于到我的房间门外了。
他打开门,送我进卧室。
我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它还散发出瀚园的廉价香水的浊气。
齐默拉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我扯下领带和解开衬衫领子。
“我还是叫个大夫” “不要!”我吼道,他吓了一跳“对不起。
那边的那只盒子,请您把它给我。
” 他拿给我,那是满满一盒硝酸甘油片剂。
一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服用硝酸甘油。
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魁北克的汽车销售商,他跟我有同样的症状。
他说硝酸甘油始终有效。
从此以后我也服用它。
当我打开盒子时,我的手指抖得厉害。
我把两粒片剂倒在手心里,张开嘴,把片剂扔进去,咬碎。
真难吃。
“现在您走吧,”我对齐默拉说“马上就会好。
过上几分钟,我知道。
” “如果不” “您走吧!” “是,先生。
当然,先生。
五分钟以后我打电话来,看看您怎么样了。
无论如何我要这么做。
这是我的义务。
” “出去!”我喘息着说“您快走!” 他走了,忧心忡忡,一脸严肃,连连地鞠躬。
他走得刚好及时,因为紧接着我一直在等待的症状就发生了。
现在那巨大的钳子来了。
这是一只可怕的钳子。
它使我的心紧缩。
紧,紧,越钳越紧。
“呃呃呃”那听上去一定像是受酷刑虐待的痛苦万分的呻吟。
那钳子收缩得越来越紧。
我额上汗流如注。
我撕开衬衫。
我的身体弯成一座桥,落回到床上。
汗从我的后颈、头发根和全身淌出。
“呃呃呃”毁灭,彻底的毁灭。
这是我现在的感觉。
我应该被毁灭,现在,永远。
害怕像一道大潮那样在我体内澎湃。
怕得要命,我无法描述的害怕。
这害怕我已经是如此熟悉,近一年来我一直是怀着它生活,它总是宣告着我的死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从来没有过,没有过。
“噢”我听到自己在呻吟。
我的双手在心脏上方抓着皮肤,冰冷的、汗湿的双手抓着冰冷的汗湿的皮肤。
现在左手像火烧火燎似的。
就这样继续着,一直继续下去。
我被碾碎、挤压、压迫、窒息和毁灭,是的,是的,是的,被一位正义的天使毁灭,因为我一生中做过的各种邪恶。
世界上所有人都做过的邪恶。
难以忍受,恐怖万分。
我感到,我的眼睛从头颅里鼓突出来。
钳子痛不欲生地钳着我。
我的头歪向一侧。
让我死吧,上帝,让我死吧,我想。
对这一切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
死亡,上帝,求你了,死亡。
我没死。
害怕一下子退走了,毁灭感消失,钳子松开了。
我可以呼吸了,先是少量,逐渐增多,最终深呼吸,深深地呼吸。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颤抖着坐到床沿上,发作结束了。
我早就知道,它会像以前的每一次一样过去。
我只需要少吸烟,该死的香烟。
我胸口里的痛楚渐渐减弱,接着是胳膊里和手里的,随后是左脚里的。
我坐在床上,心想,很多跟我有相同职业的人都有这种症状。
人们大概称这为管理病吧。
在我来说不仅仅因为香烟,还有我繁重的工作。
还有家里的折磨。
休假也无济于事,没有大夫能帮得了。
一切都是纯植物性的,这点我坚信不疑。
我得改变一切,全盘改变。
可怎么改?我常这么打算,可是我没改过一点点。
因为我内心深处漠不关心,一点也不关心。
多年来,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无法再让我开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开心,肯定不会。
我床边的电话响起来。
“我是夜班门卫,卢卡斯先生。
您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现在我又能呼吸,自由讲话了“好极了。
” “真的?当真?” “当真,”我说“我对您讲过,齐默拉先生,一切都好了。
” “这让我很高兴,先生。
我放心了。
我祝您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 “谢谢。
”我说完就挂断了。
两分钟后我睡着了,没有梦,沉沉的。
灯开着,我和衣而眠。
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直到次日上午十点我才醒过来。
窗帘拉上了,我看到电灯和我的皱巴巴的西服,撕破的衬衫,那盘硝酸甘油。
这真他妈的是一种好药,总管用。
我拿起电话听筒,要通楼层服务员,订了早饭——只是两大壶茶。
挂断之后,我很快点燃了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当年铁甲动帝王步帘衣
- 在偏执狂怀里撒个娇[重生]茶栗
- 仙界归来静夜寄思
- 杏花如梦作梅花王世颖
- 悍妇她来抢男人了金珠玉豆
- 反派疯狂迷恋我[无限]咚太郎
- 剑胆琴心独孤红
- 养了千年的龙蛋终于破壳了若鸯君
- 想爱就爱艾米
- 婚途脉脉笛爷
- 儒道至圣永恒之火
- 反派他过分阴阳怪气[穿书]从南而生
- 锦鲤大佬带着空间重生了浮世落华
- 七零金刚芭比非酋猫奴
- 烈火如歌·大结局明晓溪
- 八零年小月亮啃苹果的猫
- 入骨娇宠烟云绯
- 大将军和长公主洬
- 协议标记[穿书]童柯
- 执刑者康静文
- 相公是男装大佬兆九棠
- 我辣么大一个儿子呢归途何在
- 摁住他的易感期咿芽
- 谁还不是个仙女希早
- 梦魇图鉴收集记录[无限流]酉时火
- 人在东京,猎杀噩梦驯为鹰犬
- 阿福呀(1v1amp;nbsp;amp;nbsp; h)沈尽欢
- 老流氓疯一阵疯
- 绝对掌控(woo18)多梨
- 大唐之逍遥王爷120笑话
- 春秋我为王七月新番
- 穿越之农门小妻知秋
- 新大明帝国木允锋
- 超能神警六划先生
- 穿越军嫂之肥妻大翻身叫陈皮的橘子皮
- A级攻略浓浓
- 最强特种兵剑韵
- 绝品透视小神医贫道敲木鱼
- 行至彼岸(兄妹)南谯居北
- 千禧姜戈
- 当万人迷穿成万人嫌后(万人迷np)随机刷新npc
- 体质让世界倾倒[快穿]澜间嘉月
- 姐弟交换游戏婵娟染鬓霜
- 我在大秦开酒肆凌云木木木木
- 有关悖论雨升升
- 重生后我在修真小饭堂养老沈江山
- 有只猫说我是她老婆太古季叶人
- 过度依赖[娱乐圈]历青染
- 误刷前男友亲密付后晴空岚
- 我的室友是大明星杳杳一言
- 开局猛猛开锁,隔壁太太顶不住了赫小号
- 我好像在修仙我叫小阿东
- 道士被离婚,无数女神来撩我紫气东来三千里
- 穿越之八路军的传奇征程外传蓝海孤舟
- 被家族除名,觉醒九龙护体你后悔了?银芽白菜
- 冰凰劫:医武镇归墟月幕思华
- [综英美] 了不起的胡安娜Aak
- 清穿之一世夙愿苏墨菀
- [综原神] 退休救世主摸鱼中沧海浮舟
- 别救我,睡我就好把我拴好
- 请把脊骨雕成我的王座(高H、NP)妃子笑
- 匹配到五个老婆的我当场跑路了(百合ABO)尼罗河落日蒙
- 穿越进黄油的我今天抽到了什么马赛克?粉红美丽
- 恶果(骨科 1v1 甜H)岚酱炖肉马甲
- 刺青(简体版)Roxi
- 折桂(1v1 先婚后爱 H)丽丽薇安
- 命運之核 :宿命交錯晴媛
- 香雪(帝妃、高h)晚风情
- 都市龙将乐享斋
- 龙皇武神步征
- 绝对掌控(woo18)多梨
- 全裸,做愛,獸人作品收集金色狂风01
- 供奉的身體,記錄的日子淡驯
- 残疾omega也要被强制爱吗(abo np)柒雨
- 绿皮书(abo)lulala
- 荒岛求生,获救才是劫难的开始谁敢说我不温柔
- 四合院:拒秦淮如,我不当血包如风云
- 重生80:断亲后,他们哭求我赏口饭大真茹
- 龙魂王十四
- 四合院:教秦姨开车,油门呼到底沈胖鱼
- 我嘞个造化玉碟小笼包虾饺
- 清穿之一世夙愿苏墨菀
- 超级王者荣耀系统虐爆全球苏浔儿
- 不想当海贼王的剑豪大人七里晴树
- [综漫] 我的犬生如此精彩吾爱何处
- 人在东京,猎杀噩梦驯为鹰犬
- 阿福呀(1v1amp;nbsp;amp;nbsp; h)沈尽欢
- 老流氓疯一阵疯
- A级攻略浓浓
- 穿成虐了病娇的恶毒女配执竹赠酒
- 前夫哥结婚了,新娘竟是我自己自见山去
- 矩阵天王白雨涵
- 幻梦合集我不是浮萍
- 有关悖论雨升升
- 快穿攻略:妖孽男神,超苏的!皇后不管事
- 折香一天八杯水
- 天团与皇冠青律
- 清冷魔尊恋上我决木
- 万人嫌在高考综艺全网爆火柠檬酥
- 穿越之山野田间尽悠然老妖精18
![非典型求生欲[快穿]](https://www.nothong.com/img/4262.jpg)
![反派疯狂迷恋我[无限]](https://www.nothong.com/img/90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