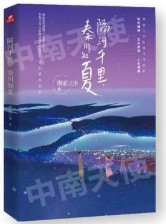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序幕(3/3)
刚开始呢。
你想想,行吗?你想想吧!” 我想点头,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头略微动了动。
然后我累坏了,不得不合上眼睛。
这一下,就像万花筒一样,我经历了色彩、声音和图像的纷呈。
一切都相互交融,颜色、图像和声音,一切都浮游而过。
红的,红得似火。
我的妻子卡琳,那张漂亮的脸扭歪了,她声音尖锐:“你这可怜的胆小鬼!你这混蛋!你这下流的禽兽!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逃脱过去了。
可是你错了。
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惩罚的。
你这虐待狂!你这灵魂虐待狂!你这魔鬼!我让你作呕,是不是?说啊,说啊,说我叫你作呕啊!”那红彤彤跟银色和金色的黏状物交错。
那个意大利女人就躺在那里,胸口插着一把刀。
它漂走了。
那是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的猪眼睛和肥宽的下颚,衬衫袖子上卷,嗓门粗大。
“你觉得太多了吗?罗伯特?这工作让你不能胜任吗?你是不想再做,还是不能再做了?”猪。
猪猡。
金色,现在一切都是金色的。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
我劳碌一生,跟每个人一样有权享受幸福。
是的,但要以另一个人为代价吗?蓝色流进金色,蓝色和深邃的幽黑。
“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罪行,因为它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没有谁会受到惩罚。
七百亿美金,卢卡斯先生,七百亿美金!我们陷进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
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
”讲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弗里瑟,汹涌的蓝色,联邦财政部的弗里瑟。
“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这是谁讲的?这话是药店里的老太太讲的。
她胆怯地微笑着,希望渺茫。
蓝色和银色,银色,橙色和绿色,黏状物和纱巾。
旋翼轰鸣。
昂热拉的眼睛,其大无比,我看着它们里面。
缓慢的音乐。
昂热拉和我在阶梯式饭店“棕榈海滩”的平台上起舞。
其他的所有跳舞者都退回去了。
美国国旗旁边是法国国旗。
橙色更深了。
所有的颜色骤然爆炸,化成星星、转轮和喷泉。
一只爆竹!它的光焰映照出浴室里的那个男人,吊死了。
色彩跳动,跳向我合拢的眼皮,全部一拥而上。
这是谁?这是我。
烂醉如泥,躺在一位黑发女郎身旁,她嘴上有一道开裂的伤口。
她一丝不挂,我们在她的床上打滚。
谁谁噢,杰茜,那个妓女!现在成了绿色,各种各样的绿。
两个家伙痛打我,一人抓着我,另一个人挥拳击打我的下体,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
我跌倒,我跌倒。
扶住我,昂热拉,请你扶住我!但那不是昂热拉,那是那个高大的黑女人。
我沉陷在她里面,像沉陷在海绵里。
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我还有三十二分钟可活。
我又清醒过来,突然置身于一座花的海洋里。
白色的茉莉花,九重葛红色、紫罗兰色和橙色的花蕾,蓝色、白色、红色和紫色的矮牵牛,红色的唐菖蒲,法兰西菊,白的和黄的这是昂热拉的花海,她的屋顶花园。
各种颜色的小玫瑰它们名叫“惊玫”还有丁香。
不,不是丁香!丁香招致不幸。
昂热拉厨房里的凳子。
她煮饭,我坐在凳子上,望着她。
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因为天热,热极了,我感到我的额头在冒汗。
我额上的毛巾,汗没了。
旋翼轰鸣。
现在全是黄色,黄灿灿的。
“什么都在涨价。
钱怎么了?我真不理解,先生!”药店里的老妪。
“但总得有个人理解它!”对,这话也对。
数百万人不能理解,只有少数人知情。
脸孔漂浮而去。
紫色中的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
打高尔夫球的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玫瑰红色的陀螺里迅速旋转。
面无表倩的加柯摩-法比安坐在轮盘赌台旁,白如油脂。
僵硬的希尔德-赫尔曼坐在一张洛可可大床上,这下一切又都成金色了。
这不幸怎么会发生的,先生?为什么?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
布莱希特写的。
共产党。
全是维利-勃兰特的责任。
他也是个共产党。
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是共产党。
明镜报是一家共产党的报纸!您也是共产党吗,卢卡斯先生?许多声音交杂,像颜色一样。
现在一切都在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些声音,那些形象。
我们的饭馆——“黄金时代”粉成白色的四壁。
低矮。
陈旧。
尼古拉,那位侍者,把肉推进一只敞开的圆炉子里。
他的围裙是红的,他的衬衫是白的。
十字架路旁的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的分店。
让-凯马尔和他的妻子。
她冲我们微笑,昂热拉和我。
有什么在闪光。
那只结婚戒指!一切突然都闪亮起来。
我跟昂热拉在她的住房的平台上,在戛纳上方。
艾斯特莱尔山脚下的城市、船只和街道的数千灯光。
数不胜数的灯,红的、白的和蓝的。
我们做ài,昂热拉和我。
我们是一体,我们感觉到我们俩还从没感觉过的东西。
谁在那儿呻吟。
我。
那是我。
棕色和黄色。
博卡的拉齐亚。
一支冲锋枪在猛扫。
又是蓝色。
“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
现在我暂时听到旋翼非常嘈杂。
灰色,灰色,全是灰色。
吊车从旧码头的水里拽出一辆雪铁龙车。
方向盘后坐着阿兰-达侬,早死了,额头上有个小洞,碎裂的后脑上有个大洞。
金色和红色。
红色和金色。
当代最大的罪行——没有和解,不可和解,它是如此之大,跟它相比再没有罪行了。
一切非常、非常大的事,都是不可理喻、无法惩罚的蓝色。
神奇的蓝色。
昂热拉和我在一尊黑色的圣母像前点燃一支蜡烛。
昂热拉祈祷,她的唇无声地蠕动。
那位年轻的牧师,他骑着摩托车开走了,穿着他的长袍,行李架上驮着一篮蔬菜。
一切全是红的,红的,红的。
赫尔曼的宫殿。
盘旋的雷达屏幕。
运行中的大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光线闪烁。
骗到手,转销,卖出,利润大得笑死人。
谁在那里笑?谁?柔和的樱桃玫瑰。
“康托港俱乐部”里的酒吧。
昂热拉为我一展歌喉。
随风而去,德文歌词是:“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和痛苦之街” 三台电视机开着。
三个新闻播音员的面孔和声音。
英镑放开了。
实际贬值百分之八。
总罢工。
银行关闭。
尼斯的私人喷气式飞机。
我知道它们属于谁,那还用讲! “这世界上有多少伤心的海洋”昂热拉唱着,为我而唱。
一只萨克斯管。
一把匕首。
一只象。
昂热拉手背上的白斑。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从没像爱你这样爱过任何一个人。
我再也不会爱其他任何人。
我也不会,昂热拉,我在杜塞尔多夫的“洲际”大酒店我的房间里。
我们脚下是灯光的海洋——蓝色海岸的灯光,洛豪森机场的灯光。
一架起飞的飞机从我头顶上飞走。
床头柜上的表。
早晨四点。
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
您做点什么!一片白色。
您得做点什么!这比谋杀更严重。
我该如何防止,我的先生们!我独自一个人,没有权力。
我们也没有。
您派出了您的缉税官!他来了,被绿色耀眼的光芒包围着。
克斯勒,干瘦,快退休了。
最能干的人之一 昂热拉唱:“还要发生多大的灾难,人类才会觉醒?” “凶手我们全是凶手” 那个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语无伦次。
是的,凶手,我们大家!银色的和黑色的;杜塞尔多夫我的律师。
像雾一样阴郁: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
您受得了真相吗,先生?全部真相?是吗,那么就 昂热拉唱:“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我的酒店房间里有十三支红玫瑰。
信封。
内有卡片。
上面用法语写着:我倾心爱你,忠贞不渝永生永世 这就是全部真相,先生,是您想听它的我谢谢您,儒贝尔大夫 “有多少孩子晚上歇下来饿得睡不着觉?这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昂热拉穿着紫红色衣服在唱。
永远不再,只要活着,这下谁都永远不再离开对方,我听到我讲。
又开始跌落,跌进漩涡,跌进漩涡。
这真糟糕。
噢,这是如此的卑鄙,我现在 完了。
结束了。
原来结局就是这样的! 不,我又一次回到生活中来了。
剧烈晃动。
我被从直升机里抬到了一个担架上。
许多人身着白大褂站在一个屋顶上,那是直升飞机的降落场。
大夫们。
护士们。
昂热拉。
担架滚动起来。
电梯门打开。
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
我们沉陷。
我周围的人们。
那是昂热拉。
爱过,爱得那么深。
眼泪在她的脸上不停地流淌。
我再一次听到她喊的话:“别放弃!求你,求你,别放弃!你不可以” 完了。
她的嘴唇无声地嚅动着。
一切都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飞快。
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
我又在行驶了,在海上行驶,在夜海上行驶。
现在死神来了吗?现在它终于来了吗?不,只不过又是一阵晕厥罢了。
我还有七分钟可活。
当我醒过来时,我刚好被快速地推着穿过一条没有尽头的过道。
它显得像是一条隧道。
灯光无数。
我再也看不见昂热拉了。
有声音传来,但我再也听不懂它们了。
我合上眼睛。
这时昂热拉的声音响起,无比清晰。
她在为我朗读一首诗。
她坐在我面前,坐在她的床上。
我赤裸裸地躺在那张床上。
第一道玫瑰红的晨光透过窗户射进来。
那是一个美国人的,这我知道,昂热拉读的是德语译文。
但我不知道作者叫什么,我记得当时我也不知道。
昂热拉的声音:“挣脱了狂野的生活欲望,挣脱了恐惧和希望” 我又换了床。
什么东西被咝咝地撕裂了。
我的衬衫。
有什么东西照得我眼花。
一只巨盘,里面有许多刺眼的灯,就在我头顶。
戴着面具、头戴白帽子的人们俯下身来 “感谢上帝,不管你的上帝是谁” 一根针扎进我的右臂肘。
昂热拉的声音越来越轻细:“每个生命都会结束,没有死者能够回返” 那些颜色!那些颜色!现在,它们全都在一种美丽的幻影里。
我感到我的胳臂上有什么。
很沉。
有什么东西压在我的脸上。
响起一声细弱的信号。
色彩奇美无比。
我们的世界上没有这种色彩。
现在,昂热拉的声音变得非常轻了:“最疲惫的河流有一天也会找到它通向大海的路途” 咝咝声更响了,我猛然看到了它。
它在长满花的草地上蜿蜒,这条所有河流中最疲惫的河流。
我注意到,光滑的手指在抚摸我的身体,我的左胸侧有什么冰冷的、锋利的东西。
我顿时知道了,这是一条怎么样的河流。
这是阴间的冥河,它把活人的王国跟死者的王国分隔开来。
这条冥河,死者的灵魂从里面啜饮遗忘。
我吃惊地想:冥河的河岸有阳光照耀。
然后,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非常轻柔,我能感觉到。
然后,满是鲜花的草地和冥河的图像缓缓地、小心地消失了。
那些闪烁的色彩消失了,黑暗的漩涡又回来了。
然后,我第一回沉沦、我主动屈从。
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平缓了,停止了,咝咝声逐渐消失。
我的静脉和动脉里的血进入静止状态,然后就只剩下黑暗、温暖和安宁了。
后来我就死了——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当年铁甲动帝王步帘衣
- 在偏执狂怀里撒个娇[重生]茶栗
- 仙界归来静夜寄思
- 杏花如梦作梅花王世颖
- 悍妇她来抢男人了金珠玉豆
- 反派疯狂迷恋我[无限]咚太郎
- 剑胆琴心独孤红
- 养了千年的龙蛋终于破壳了若鸯君
- 想爱就爱艾米
- 婚途脉脉笛爷
- 儒道至圣永恒之火
- 反派他过分阴阳怪气[穿书]从南而生
- 锦鲤大佬带着空间重生了浮世落华
- 七零金刚芭比非酋猫奴
- 烈火如歌·大结局明晓溪
- 八零年小月亮啃苹果的猫
- 入骨娇宠烟云绯
- 大将军和长公主洬
- 协议标记[穿书]童柯
- 执刑者康静文
- 相公是男装大佬兆九棠
- 我辣么大一个儿子呢归途何在
- 摁住他的易感期咿芽
- 谁还不是个仙女希早
- 梦魇图鉴收集记录[无限流]酉时火
- 人在东京,猎杀噩梦驯为鹰犬
- 阿福呀(1v1amp;nbsp;amp;nbsp; h)沈尽欢
- 老流氓疯一阵疯
- 绝对掌控(woo18)多梨
- 大唐之逍遥王爷120笑话
- 春秋我为王七月新番
- 穿越之农门小妻知秋
- 新大明帝国木允锋
- 超能神警六划先生
- 穿越军嫂之肥妻大翻身叫陈皮的橘子皮
- A级攻略浓浓
- 最强特种兵剑韵
- 绝品透视小神医贫道敲木鱼
- 行至彼岸(兄妹)南谯居北
- 千禧姜戈
- 当万人迷穿成万人嫌后(万人迷np)随机刷新npc
- 体质让世界倾倒[快穿]澜间嘉月
- 姐弟交换游戏婵娟染鬓霜
- 我在大秦开酒肆凌云木木木木
- 有关悖论雨升升
- 重生后我在修真小饭堂养老沈江山
- 有只猫说我是她老婆太古季叶人
- 过度依赖[娱乐圈]历青染
- 误刷前男友亲密付后晴空岚
- 我的室友是大明星杳杳一言
- 开局猛猛开锁,隔壁太太顶不住了赫小号
- 我好像在修仙我叫小阿东
- 道士被离婚,无数女神来撩我紫气东来三千里
- 穿越之八路军的传奇征程外传蓝海孤舟
- 被家族除名,觉醒九龙护体你后悔了?银芽白菜
- 冰凰劫:医武镇归墟月幕思华
- [综英美] 了不起的胡安娜Aak
- 清穿之一世夙愿苏墨菀
- [综原神] 退休救世主摸鱼中沧海浮舟
- 别救我,睡我就好把我拴好
- 请把脊骨雕成我的王座(高H、NP)妃子笑
- 匹配到五个老婆的我当场跑路了(百合ABO)尼罗河落日蒙
- 穿越进黄油的我今天抽到了什么马赛克?粉红美丽
- 恶果(骨科 1v1 甜H)岚酱炖肉马甲
- 刺青(简体版)Roxi
- 折桂(1v1 先婚后爱 H)丽丽薇安
- 命運之核 :宿命交錯晴媛
- 香雪(帝妃、高h)晚风情
- 都市龙将乐享斋
- 龙皇武神步征
- 绝对掌控(woo18)多梨
- 全裸,做愛,獸人作品收集金色狂风01
- 供奉的身體,記錄的日子淡驯
- 残疾omega也要被强制爱吗(abo np)柒雨
- 绿皮书(abo)lulala
- 荒岛求生,获救才是劫难的开始谁敢说我不温柔
- 四合院:拒秦淮如,我不当血包如风云
- 重生80:断亲后,他们哭求我赏口饭大真茹
- 龙魂王十四
- 四合院:教秦姨开车,油门呼到底沈胖鱼
- 我嘞个造化玉碟小笼包虾饺
- 清穿之一世夙愿苏墨菀
- 超级王者荣耀系统虐爆全球苏浔儿
- 不想当海贼王的剑豪大人七里晴树
- [综漫] 我的犬生如此精彩吾爱何处
- 人在东京,猎杀噩梦驯为鹰犬
- 阿福呀(1v1amp;nbsp;amp;nbsp; h)沈尽欢
- 老流氓疯一阵疯
- A级攻略浓浓
- 穿成虐了病娇的恶毒女配执竹赠酒
- 前夫哥结婚了,新娘竟是我自己自见山去
- 矩阵天王白雨涵
- 幻梦合集我不是浮萍
- 有关悖论雨升升
- 快穿攻略:妖孽男神,超苏的!皇后不管事
- 折香一天八杯水
- 天团与皇冠青律
- 清冷魔尊恋上我决木
- 万人嫌在高考综艺全网爆火柠檬酥
- 穿越之山野田间尽悠然老妖精18
![非典型求生欲[快穿]](https://www.nothong.com/img/4262.jpg)
![反派疯狂迷恋我[无限]](https://www.nothong.com/img/90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