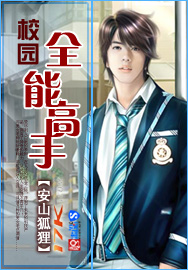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章 一帘风絮(1/3)
慈宁宫内外各殿都掌了灯,琉璃盏在廊沿下挂着,透过听差房的绡纱窗户,只看见一个个晕黄的点儿。
戌初的天已经黑透了,雨还在下,上夜的宫女们排成一溜都到齐了,春荣挨个儿点了名,吩咐寿膳房的小太监摆饭。
上首留给掌事姑姑,余下的六个人围着八仙桌坐下来,等春荣拿起筷子夹了第一口菜,众人才悄无声息地开始用饭。
饭毕春荣带着锦书把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巡视了一遍,寝宫里司浴的宫女伺候太皇太后沐过浴,来春荣跟前回了声就卸差下值了。
春荣对锦书说:“该着咱们上差的时候了,这会子塔嬷嬷已经服侍老祖宗上床歇着了,咱们要接塔嬷嬷的班。
塔嬷嬷有了年纪,所以不上夜,只有出了拿不了主意的大事才去找她。
她住在配殿的梢间里,万一有什么就打发更衣室门口的那个去传话。
” 锦书一一应了,春荣边走边道:“对底下人你用不着客气,该说的就说,该指派就指派。
你既然进卧房了,就是这个。
”她竖了竖大拇指,“别说吩咐,打骂都使得。
平日里好是另一码,立威的时候不能含糊,否则管不住她们。
这帮人,面上恭敬,私底下不知怎么编排掌事呢。
越编排越要往死了管,才好叫她们服帖。
” 春荣不是善茬子,她收拾下面的人很有一套,大家也都敬她怕她。
锦书脾气好,前些年一直是挨姑姑掸把子,或者是跪墙根的,受惯了欺压,绝学不来她的手段。
嘴上答应,行动上未必照做,春荣也不计较,带着她往太皇太后寝宫里去了。
绕过缂丝满床笏围屏,一眼便看见寝宫的全貌。
那张拔步床尤为惹眼,床架子上挂着花卉虫草纱帐,外头罩着妆蟒绣堆幔子。
太皇太后在床上躺着,头下枕着玉色夹纱新枕头,身上盖的是杏子黄绫被。
虽说去了华服妆奁,可哪怕是睡着了,只要人在那里,也压迫得下头的人喘不过气儿来。
春荣近前看了看,打个眼色给锦书,示意她把灯架上的巨烛灭了。
锦书点点头,正蹑手蹑脚地要往灯前去,太皇太后睁了眼睛,“别忙灭。
” 锦书道个是,忙退了回来。
春荣在床头边蹲下来,低声问:“老祖宗今儿是怎么了?这个时辰了怎么还不安置?” 太皇太后坐起来,“才交亥,中晌睡得好,这会子反倒睡不着了。
荣儿,吩咐小厨房做点吃食来,不必太麻烦,收拾盘点心就成。
” 春荣知道太皇太后定是有话要和锦书说,特地把她支开的,便躬身应个是,却行退出卧房去,顺手带上了房门。
锦书取了锁子锦靠背来给太皇太后垫在身后,心里隐隐猜测今天白天面圣的事总归要过过堂的,太皇太后等到夜深人静时才问,也不知是什么用意。
太皇太后脸色有些恍惚,并不急着说话。
视线落在长案上供着的西洋座钟上,一室寂静,只有玻璃罩子下长着翅膀的鎏金小铜人一圈一圈不停地旋转,带动内里零件,发出细微而有节奏的嗒嗒之声。
锦书颇觉忐忑,老祖宗不发话,自己也不敢吭声,便垂手站着听使唤。
稍过了一会儿,太皇太后像是回过神来了,看了她一眼,慢慢地说:“你的脸色不好,回头叫厨房炖碗雪蛤吧。
” 锦书越发的糊涂,上来不呵斥,倒赏吃的,真是叫人摸不着头脑。
也不细咂其中滋味了,只听后面怎么说罢了,忙不迭肃下去,“谢老祖宗赏。
” 太皇太后撩起了眼皮子,“我要问什么,想必你也知道,万岁爷召你进西暖阁,可说了什么话?” 锦书老老实实回道:“万岁爷什么也没说,忙着批折子,只让我在御前磨墨,等折子批完了就打发我回去了。
” 太皇太后直盯着她,若有所思,隔了会儿才道:“我还说你聪明,现如今瞧你不过尔尔。
在我跟前耍心眼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心里倒喜欢,你要是瞒我,我可不懂什么是怜香惜玉。
皇帝让李玉贵拿轿子抬你去研磨,这话说出去谁信?” 锦书道:“老祖宗明鉴,万岁爷只在研磨的当口说了两句话。
问敬烟上有几个人伺候,又说今年交夏避暑往热河,要好好陪老佛爷游山玩水、逛园子,旁的再没什么了。
奴才说的都是实话,绝不敢欺瞒老祖宗。
” 太皇太后审视她,见她面上从容,不像是扯谎的样子,便信了三分。
细想一下,皇帝生了一副叫人摸不透的性子,就是心里真有什么打算,恐怕也不会轻易地表露。
越是上心,越是做出不在意的样子来。
若说拿轿子抬人往养心殿去,只怕不是皇帝的意思,是下面奴才为了讨好主子干出来的糊涂事儿。
原本想传李玉贵来慈宁宫问话的,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妥。
皇帝到底不是太子,太子年少,未及弱冠,办事欠考虑,长辈管束教导是应当的。
皇帝不一样,端午就满二十九了,打下了江山,做了九年的皇帝,是万民之主。
他说什么话办什么事,早就不容别人置喙了,平素的家常话,嘘寒问暖的还犹可,倘或换作别的,就是亲娘亲祖母,过问起来也要适度。
毕竟天威不可触犯,他自己宫里的事,有不满的自会发落,既然对李玉贵的谄媚默认了,也就是说他心底里还是认同他这样做的。
自己虽是他的祖母,过于干涉了也不好。
他点头的事,自己揪住不放,若是处置了总管太监,就是不给皇帝脸面,该当讲究的地方还是要顾忌的。
太皇太后又问:“只说了这些?我看你还是有瞒我的地方,既然说到热河了,只怕皇帝发了话,叫你一道去了吧!” 锦书不得不佩服太皇太后的算计,真叫她料了个十之八九。
这话她原不想说的,可问起了也不好赖,立夏转眼就到,瞒能瞒到多早晚去。
横竖是要穿帮,不如现在就承认了,也免得落个滑头的罪名。
遂低眉顺眼回话,“老祖宗料事如神,万岁爷是吩咐奴才尽心伺候老祖宗来着。
” 太皇太后心头一震,看来自己担心的事真要发生了。
皇帝对锦书动了心思,是变着法子地想和她走近,这怎么了得!这两个人都是犟头,皇帝一碰上感情的事就死心眼,锦书呢?一家子死得那么惨,全拜皇帝所赐,她能抛开仇恨心甘情愿跟着皇帝?只怕是心里恨出了血来,正愁没机会报仇。
皇帝运筹帷幄的安稳日子过惯了,全然忘了利害,真是疯得没边了! 太皇太后越思量越是后背发凉,这爷俩莫非要栽到同一个女人手里?锦书使了什么妖法祸害他们,千方百计得来的江山,到头来仍旧毁在姓慕容的手里,岂不是白做了一场春秋大梦! 太皇太后的眼神深沉,隐隐露出杀机来。
锦书心头大惊,忙道:“奴才自当谨遵万岁爷的教诲,寸步不离老祖宗,好好地服侍老祖宗,替老祖宗解忧。
奴才在宫里是孤身一人的,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也没人能请教,如今在慈宁宫当差伺候老祖宗,老祖宗就是奴才的天,一切但凭老祖宗做主。
奴才万事按着老祖宗的吩咐办,绝不给老祖宗丢份儿。
” 太皇太后倚着靠背,眉间的阴霾渐散了,心道也的确没到要杀她的地步,贸贸然动了手,皇帝那里不能依,太子也要吵翻了天的。
还是再看看吧,一来慕容家的老十六还没现身,指不定在哪个暗处看着。
二来也是为了皇帝和太子,宇文家出情种,如今明面上看不出什么,杀了锦书易如反掌,可万一她一死捎带上那两个,岂不功亏一篑! 眼下叫人操心的是皇帝,太子或许是年轻图新鲜,皇帝呢?他从前对皇考皇贵妃的感情只能埋在心里,眼下一个大活人送来了,就像宝贝失而复得,那股子劲头一时半会儿且消停不了。
还是要看锦书的,她不愿意,谁也逼迫不了她。
远着就成了,拉个清水脸,说话带着疏离,再热的心也经不住一海子的冰水浸泡。
大不了哧溜一声,冒出团白烟来,风一吹,也就散了。
“既这么的,那我就瞧着你了,咱们有言在先,只要你醒事儿,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可你要是给我出幺蛾子,那就不论皇帝还是太子了,谁都救不了你。
”太皇太后深知道打个巴掌给颗甜枣的道理,一通威胁之后,嘴角又挂上了和蔼的笑,招了招手道,“好孩子,到我这儿来。
” 锦书暗暗大松一口气,看来又捡着一条命,忙依言跪在拔步床前头的踏板上,把手放在太皇太后的手里,做出亲热贴心的样子来。
太皇太后反复摩挲,一面不无哀戚地说:“我看着你,就像看见了你姑姑。
你姑姑在时和我最亲,天底下就找不着比我们娘俩更好的婆媳。
她性子好,不端架子,可惜阳寿短,才满二十三就薨了。
我常觉遗憾,我们娘们缘分浅。
如今有了你,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只要你听话,我定然像疼你姑姑一样疼你。
” 锦书躬身道:“多谢老祖宗,奴才一切都听老祖宗的。
” 太皇太后颇满意地点头,这时春荣托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进来,白粉定窑的碟子里码了几块菱粉糕,走到床前来肃道:“老祖宗,小厨房赶着做的新糕,您最爱吃的,尝尝吧!” 太皇太后道:“不吃了,赏你们吧!这会子没什么事,荣儿出去吃了再进来。
” 春荣应个是,和锦书谢了恩,退到卧房外头去了。
前半夜是由春荣当值的,锦书在偏殿的墙角边上拉个毡垫子,半靠半躺地歇上两个时辰。
毕竟刚入春,宫里熄了地炕,冷风从开着的半扇门里灌进来,就算裹着毡子还是冻得直哆嗦。
看边上两个宫女也翻来覆去的不安稳,好容易到了子时三刻,就悄悄地进去替换春荣。
原想着反正冷,索性不睡了,瞪着眼熬上一夜就是了。
于是往太皇太后床榻旁边的地下一坐,傻愣愣地听着出气进气的声响。
开始还好,可时候一长不免也犯起了睏,这才明白春荣受的罪有多大。
午夜时分正是最凉的,太皇太后寝宫里不许摆毡垫子,侍寝的只能席地而坐,冰冷的金砖隔着老绿的春袍子,丝丝凉意直从尾椎骨直蹿上来,蔓延向四肢百骸。
坐了一会儿难敌睡意,床前没着没落的,也没个地方能借把力,只得侧身躺下来。
刚要合眼,老佛爷翻了个身,立时就把她惊醒。
这时只觉身上冷得厉害,硬邦邦的地面硌得骨头疼。
正是又冷又睏,想睡又不敢睡,这样的难挨,相较之下躺在毡垫子里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太皇太后迷迷糊糊喊了声荣儿,锦书忙爬过去,“老祖宗要什么,锦书伺候您。
” 太皇太后半睁了眼,似乎一时没反应过来,稍一顿问:“什么时辰了?” 锦书看那西洋小座钟,回道:“才刚丑时二刻,时候还早,老祖宗再睡会子吧!” “水。
”太皇太后模糊说了句,自己翻起来靠着床架子坐着,又合上了眼睛。
锦书轻手轻脚往月牙桌前去,从暖壶里提出小茶吊来。
水是温的,入口正合适,伺候太皇太后喝了,小心问:“老祖宗,还要么?” 太皇太后摇了摇头,复躺下,锦书替她掖实了被角,把茶盏收到桌上,重回床头边坐着。
熬油似的半夜前仰后合,好容易听到第一声鸡啼,暗盘算着好歹寅正了,再过一会儿就天亮了。
又打了会子盹儿,全京城的鸡都开始吊嗓子,一声接着一声,此起彼伏。
锦书看那西洋钟上的指针正对着五,已经到了卯时,晨曦映在玻璃窗户上,天微微地明了。
估摸着老祖宗该起身了,便打起了精神直起身子。
这一夜没睡好,只觉眼睛胀痛,眼皮子酸涩得张开了就合不上。
不过尚庆幸,这半夜的差总算是当下来了,半点差错也没有。
床上有了动静,锦书把两层帷幔撩起来挂在银帐钩上,对着太皇太后一福,笑道:“老祖宗吉祥,卯时了。
” 太皇太后容光焕发,见锦书笑意盈盈,利索又伶俐的样子,心里也高兴,应道:“起吧。
” 锦书亮了灯,一掀窗帘子,给外头廊庑滴水下的人打暗号,那些人就领着一众大太监小太监准备请安了。
锦书回到床榻前,趴在地下磕头,高呼个“老祖宗万寿无疆”,卧房的门脸子打起一边,门外的人络绎进来,请安问吉祥,开始有条不紊地忙碌。
春荣暗对她使眼色,让她回下处歇着去,后面的活由她接手了。
锦书抿嘴笑了笑,悄声退出去。
寝宫的门大开了,阖宫上下也解了禁,提着袍子跨出门槛,脖子僵得转都转不动。
一面揉捏着,顺着台阶下去,小宫女在月台下面冲她打招呼,一声“姑姑好”叫得又甜又脆。
锦书自嘲地勾起了嘴角,熬了这么多年,自己也当上了姑姑。
虽然这姑姑当得悬乎,很有些朝不保夕,但总算是脱了下三等的行列,尚且值得乐上一乐。
崔贵祥在月台下等她,压低声问:“还顺利吗?” 锦书蹲福道:“昨儿一切都好,顺顺当当的。
老祖宗呼吸匀停,也不咳嗽,半夜只喝了一盏茶,一觉到天亮。
” 崔贵祥连连点头,“这就好,人说万事开头难,你这头开得还不赖。
赶紧上听差房,炉子上有你师傅给你留的粥,喝完了回榻榻里去吧,着紧点儿还能睡上三个时辰。
” 锦书应了,打着飘地往配殿里赶。
真亏了苓子心里有她,桌上摆着个倒扣的碗,下面是个豆腐皮包子,包子叠加在大红洋漆小菜碟上,菜碟里装着十几片法制紫姜,是苓子特地另拨了留给她的。
锦书看着这些东西,心里说不出的什么味道。
慈宁宫里这些人都不坏,他们常说进了同一个宫门就是一窝的,不论是谁,只要在一起当差就要相互照应,因此对她极和煦。
也或许是可怜她,向来厉害出了名的总管太监崔贵祥待她也和风细雨的,她的日子就好过了许多。
试想要是有人天天对你吹胡子瞪眼,那又是怎样的难耐压抑呢? 配殿里做粗使的小宫女眼明手快,见她往炉子前盛饭,忙接过大勺和碗,笑着道:“姑姑快坐着,吩咐一声就是了,哪里用得上自己动手。
” 另一个垂着手道:“姑姑有什么衣裳要浆洗的,回头我上姑姑榻榻里取去。
荣姑姑说了,锦姑姑忙,不叫姑姑自己洗衣裳。
” 这就是做姑姑的份儿了,小宫女们不过十二三岁,知道眼前这位是侍寝的,该奉承的奉承,该拍马的拍马,一点也不含糊。
锦书依稀想起了自己像她们这么大的时候在永巷里受的苦,掖庭里的那口井不像别处的,别的井天越冷水越暖和,那口井的水不论春夏总是冰得刺骨。
隆冬腊月里,井水结了冰,吊桶好不容易敲开冰面,回头一看,衣裳堆得比山还高。
那么多啊,从早洗到晚,冻得手指头没了知觉。
没法子就放在怀里焐,等焐得能动了再洗。
手上的皮在搓衣板上来回地蹭,掉了一层又一层,一沾胰子就钻心的疼。
冻疮肿得像馒头,一旦破了就溃烂,没有药可擦,还要整天泡在冷水里。
这样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都想不起来了,或者也是不愿意想,想起来就是大把的眼泪。
“姑姑。
”小宫女看见她发愣便招呼她,“快吃吧,没的凉了。
” 锦书回过神来,捧着粳米粥焐了会儿,就着紫姜草草打发了,身上暖和了些。
这时天也亮透了,雨淅淅沥沥还在下,拿了把伞正要回西三所,后面大梅赶了上来,把个油纸包往她手里一塞,笑道:“你这丫头有口福,给你样好吃食,淮南湾出的糟鹌鹑。
我这两天吃不得咸,白便宜你了。
” 大梅对吃有讲究,和寿膳房的小太监有交情,常弄些小玩意儿来。
锦书含笑问:“又上哪儿打秋风去了?” “是小皮实拿来的,来路正得很。
”大梅一甩辫子,“别耽搁了,回下处睡你的去吧,我上差了。
” 小皮实是大梅的跟班,一般大丫头都有几个当碎催的小太监,这些小太监年纪小,总要找靠山。
师傅又嘱咐了,和大丫头走得近没什么坏处,所以他们兢兢业业地伺候着,有好的自己舍不得吃,留着孝敬自己的头儿。
锦书捧着油包出了宫门,边走边想,荔枝那里的事不知办得怎么样了。
自己是慈宁宫的,没主子放差事不能随意往别的宫门去,只有盼着今天未正的加餐是贵喜伺候,到时候能从他那儿打听到点什么。
正慢吞吞在甬道上走着,抬眼一看,对面油步遮着的巨大华盖下,一乘肩舆缓缓而来。
她脑子里一懵,暗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分明已经错开晨昏定省的时候了,怎么还能遇上!现在是进退不得,只好熄了伞靠墙垂首侍立。
李玉贵的眼梢儿早就留意皇帝的举动了,只见皇帝原本靠着的身子直了直,眉峰微微攒了起来,忙暗里打了手势让辇慢行。
雨簌簌地下,虽不大,却是又密又急,锦书的头上身上都打湿了。
初春的天又冷,呼出来的气在眼前织成白茫茫的一片。
她低头站着,步辇已经快到跟前了,正打算跪下去请安,辇上人抢先说了声“免礼”。
众人都有些怔,谁也没料到皇帝会说这话,还没跪呢,怎么就免了? 皇帝不说别的,只拿眼瞥李玉贵。
李玉贵猴精的一个人,立马就会意了,笑着对锦书道:“姑娘才大安的,赶紧把伞打起来,别又淋得作下病。
” 说着亲自撑了伞遮住锦书,又问:“锦姑娘这是往哪儿溜达去?老佛爷跟前不必伺候了?” 锦书谦卑道:“回谙达的话,我如今和荣姑姑一块儿给老祖宗上夜呢!这会子不是溜达,是回榻榻里歇觉。
” 皇帝低垂着眼,脸色平常,看不出喜怒,慢慢转动拇指上的扳指,似乎颇有兴致。
李玉贵知道皇帝关心的是什么,所以有恃无恐,不怕皇帝怪罪他大不敬,拉家常般地问锦书:“敢情姑娘这是升发了,那往后早晨就不在跟前了?” 锦书不安地偷着瞄皇帝,踌躇道:“不光早晨,早晚都不在,只伺候下半晌和后半夜。
” 皇帝的视线终于调过来看着她了,眼中那一环金色暗沉沉的,阴霾铺天盖地地袭来。
锦书被吓得忙低下头,李玉贵也窒住了,暗呼个不妙,喃喃道:“这半截差当的……什么道理?” 皇帝似不耐,眉头愈发聚拢,沉声清了清嗓子。
李玉贵被火烫了尾巴尖似的,激灵凛一惊,忙不迭合掌一拍,步辇重又往前行进,朝着慈宁宫方向逶迤而去。
锦书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复撑了伞继续走。
走了几步又觉得哪里不妥,李玉贵居然敢停了皇帝的辇和她东拉西扯,大大的不合常理,显然是故意问给皇帝听的。
这皇帝阴阳怪气的,到底是什么算计?不自觉地回头看一眼,曲柄金顶绣龙黄金伞边缘的幔子迎风飞舞。
肩舆的靠背造得高,密布着葵花瓣的四合祥纹。
皇帝身子向右歪着,一手支着头,只露出鸽血红的宝石顶子和鎏金佛雕的帽正。
帽檐下长发如墨,和着五彩金线织的辫连子,直垂到步辇的底座下去。
一切如常,皇帝神态自若,想是自己多虑了吧!锦书自我开解了一番,脚下加快了些,这会儿除了睡觉,别的都不必想,快些回榻榻里才是正经。
皇帝扭过身回头,眼里雾霭望不见底。
那丫头走得匆忙,恨不得插翅飞到甬道的尽头似的。
他微有些茫然,又有些无奈,原就不该的事,偏要记挂着,分明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何苦来哉! 白天总不及晚上睡得踏实,朦朦胧胧间躺了两个时辰,下房里没有钟,也没有更漏。
撑起身看外头,雨下个没完,看不见日头。
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唯恐睡误了点叫春荣等着,便下炕穿戴好,把被褥收拾进炕头的柜子里。
尽南墙并排摆着两个黑漆大躺箱,包了箱钉的是苓子的,另一个光板的是她的。
这间屋子统共只住她们俩,两个人交好,箱子也不上锁。
因着身量差不多,碰上了阴雨天气,衣裳不够倒换了也相互混着穿。
锦书想着苓子下月就放出去了,总要送她些东西才好,她从箱板边上的袱子下面翻出一个口袋来,里面有几两碎银子,还有几件簪环,是这几年一点点攒下来的体己。
翻来覆去地看,真没一件像样能拿得出手的。
给钱,人家肯定不要,给首饰,都是以前当差送东西的时候小主们随手赏的,并不十分贵重,送出去也寒碜。
思来想去只有上回太子给的那只富贵玉堂春的镯子了,不是说翠中带翡,是极珍贵的上品吗?她从一件棉袍子的夹层里掏出宫制的掐金丝线荷包来,拉开口上的带子,把镯子托在手掌上看。
翠色浓厚得几乎滴下水来,却在一汪碧海中流云般的掺夹着几丝褐黄色,多有缥缈婉转的美态,确实是极罕见的。
拿它送人肯定再体面不过,只是真要拿主意的时候又不免犹豫,这样做好吗?太子是一片情义,他淘换得着的好玩意儿,巴巴地送了来讨她欢喜,她倒好,转脸就给了别人。
先不论市价值多少,这么糟蹋人的一片心,似乎有点造孽。
进退维谷间门被推开了,锦书吓了一跳,宫女的下处是不许锁门的,为的是同住的人来往方便,或是有事宣召时不费手脚。
她只当是苓子回来了,谁知门前站了个太监——袍子,马褂,大辫子。
戴着盖儿帽,头顶上是个玻璃顶子。
脚上穿一双皂靴,微躬着身,帽檐儿遮住了脸,看不清是谁。
按说宫女的榻榻是不让太监随意出入的,这人怎么犯规矩?心里疑惑着,“这位谙达,找谁?” 来人闷声一笑,缓缓抬起头来,浓眉星目,居然是太子! 锦书吓得不轻,“你怎么打扮成这样了?这是大忌讳,叫人看见了像什么?” 太子不以为然,“有什么!换了衣裳办事方便,上这儿来瞧你就没人说话了。
” 锦书让他进了屋子,看他帽子上尽是密密的水雾,忙拿帕子给他掸了。
嘴里嘀咕着,“不成体统,要是叫太皇太后知道了又要出事儿。
” 太子笑道:“别怕,有事儿我担着,再说谁会注意一个太监?我到这儿来没人知道。
” 锦书皱了皱眉,这话也是,太监是阉人,男不男女不女的下三等,谁能料到太子会扮太监!宫里人又多,太监尤其多,这些人满世界乱转悠,像内务府的、尚仪局的,各处宫门每日都要巡视,来来往往的也没个定数,绝不会有谁过问,太子这主意倒是想着了。
太子看着她,笑得异常灿烂,红着脸道:“你这是在想我吗?原来咱们的心是一样的。
” 锦书愣了愣,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什么想不想的,自己哪里想他了? 太子的眼里流光溢彩,他盯着锦书手里的镯子笑得欢实。
真是前所未有的欢喜,姑娘家面嫩,不好意思承认,他每回来她都轰他,自己心里还不受用来着,原来她会在一个人的时候睹物思人啊!今儿来得巧,恰好撞见了,否则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他又有些心疼,这么好的女孩儿,原来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头回见她时,她站在保和殿的丹陛旁,昂着小小的头颅,满脸的矜重高贵。
虽然捞起袖子打架的样子不太符合一个皇室帝姬的标准,但拢好了华袍,扶正了扁方,还是高高在上不可亵渎的气度。
可惜如今掉进泥沼里了,没人护没人疼,每天连喘气都要加着小心。
只恨自己当初年纪小,没有打探清楚,问了额涅和皇阿奶,都说她已经死了,没想到她竟在永巷里活了九年。
要不是上回偶然相遇,怕是一辈子都不知道她还在这世上,白叫她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太子含情脉脉,心想既然她心里也有他,那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了。
就是到皇太太跟前长跪,也要把她讨到景仁宫去。
“往后我常来瞧你,你有话就对我说,等时机成熟了我就接你走。
你什么都用不着操心,一切都交给我。
我是太子,有我在,绝不叫你再受委屈。
”太子喜道,“论起来咱们认识有些年头了,你原就不是个肚子里有弯弯绕的,亏得我这会子来了,否则不知被你瞒到什么时候去!我要是心冷了,娶了妃子,你可怎么办?后悔也晚了。
” 锦书这才恍然大悟,敢情他是看见她拿着镯子误会了。
可自己怎么解释,说是要把它送给苓子?那多伤人啊!这话万万出不了口,太子怎么说都是好人,别人面前是个什么样不论,对她是实心实意的。
他这么三番四次地被她泼冷水,别说是天皇贵胄,就是个平常人也会耐不住。
大不了一咬牙,撂下句狠话,从今以后再不来受这份闲气了。
可他劝不退,还来,倒真叫她刮目相看。
想了想,也无从辩白,就岔了话题问:“你今儿不读书?” 太子大大咧咧在桌前坐下,应道:“今儿天不好,骑射的课业没有了。
我才从布库场回来,半道上想起一桩事,你猜是什么?” 锦书沏了一壶茶,嘴里道:“我怎么知道你又有什么新鲜事,喝茶吧!我这儿可没有极品大红袍,只有上回人家送的高碎,你凑合着用吧!” 太子本是娇生惯养的小爷,从来都是要星星不敢给太阳的。
平时大红袍得用玉泉山的水泡,还计较茶具的卖相,不是旧窑口出的脱胎填白茶盏就不喝。
不光这样,沏茶手法也讲究,什么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凤凰三点头,喝上一盏茶,不知道要怎么个折腾法,出了名的难伺候。
眼下倒好,到了她这里一百件事好商量。
没有红泥小火炉,茶盏不过是普通的江西贡瓷,连叫他喝茶叶沫子都乐意,还乐癫癫的。
太子自己也一叹,当真是遇着能治住的克星了! 这些且不提,他接着话茬子说:“今儿是大年初五,迎财神的日子,也是你的喜日子……你可别说自己的生辰也忘了。
” 锦书笑了笑,那怎么能忘,自己出生的日子就是额涅受难的日子。
半夜里给太皇太后值夜的时候就在想,要是能祭奠一下双亲多好!可这深宫大院容不得,宫里不许随便见火星子,上万间屋子一个烟囱都没有,就是寿膳房,用的都是烟道。
宫女子不说尽孝的话,说了也办不到。
遇上亲人的忌日,大不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念叨上几句,眨几下眼皮子,就算完了。
太子不明白她心里装的事儿,也绝想不到她的生辰,她念的不是怎么过,只是思念自己的父母亲,便道:“我打发冯禄上寿膳房要长寿面去了,拿野鸡崽子汤给你下银丝挂面吃。
今年的生日没法子过好,来年咱们补上,明年我给你摆个敞亮的大宴。
” 锦书别过脸,面上满是哀戚之色,悻悻然道:“我们做奴才的过什么生日,也不稀图什么,不挨罚就是万幸了。
” 太子讨了个没趣儿,低头摸了摸鼻子,看她神色黯然,料想是在为以后的事心烦,于是宽慰着,“你别急,我再想想办法,横竖把你弄到我身边来,这样也好叫我安心。
你如今在太皇太后跟前当差,老祖宗虽公允,有了年纪到底想得多些,总有个转不过弯来的时候,我怕你在那里日子难熬。
” 锦书摇了摇头,“我现在挺好的,你别替我操心了,回头再捅出什么娄子来,倒不好了。
” 太子嘀咕,“敬烟上好好的,怎么又去值夜了?还分派了这么个时辰,本来盼着晨昏定省能见上一见,看来是不中用了。
多亏了冯禄想了这么个法子,我才好来看你,只不过也不能常用,万一遇着好管闲事的怕要穿帮。
” 锦书木讷地嗯了一声,也不管太子怎么为她这一应而沾沾自喜。
推了窗槅看,雨水把甬路上的青砖洗刷得清清爽爽。
再往南北张望,西二条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连常晃悠巡视的大太监也不见踪迹。
这会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就回头道:“我过了晌午要当值的,现在到什么时辰了?” 太子从怀里摸出个西洋珐琅小怀表来,在鎏金的钮子上一捏,表盖儿一下就弹开了。
往上看了看,再一换算,答道:“刚过巳时三刻,还早呢。
”琢磨了下,她要看时辰,屋子里又没有更漏,总不能跑到天街上去看日晷吧!就把怀表递了过去,“这是番邦去岁进贡的,送你吧,好知道时候。
” 锦书忙摆手,“不用不用,一出太阳就成了,这表贵重,太子爷快收起来吧!” “那要是十天半个月的下雨,你怎么办?”太子不由分说把她拉了过来,伸手让她看表面,献宝似的指着那根静止不动的短针道:“杵着半天不挪窝的叫时针,转得中不溜的叫分针,飞转的叫秒针。
” 两个人挨得那样近,呼吸几乎接着呼吸。
锦书有点不自在,脸上火辣辣的,太子身上是一股陌生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多情浪子痴情侠(天观双侠)郑丰
- 穿成炮灰O后他A爆了凉白开开
- 满级绿茶穿成小可怜春刀寒
- 沉迷暧昧李阿吾
- 想你想疯了奚六
- 我真的是酒厂老板手植
- 最美不过湛海深蓝欧阳雪枫
- 昨天不小心死掉了笛鼓声
- 娇宠卿卿眠风枕月
- 特别调查组[刑侦]徐小喵
- 被渣的白月光杀回来了[快穿]核桃果果
- 诸天我为帝兴霸天
- 穿回来后嫁给残疾大佬池陌
- 神级文明(我是光明神)傲无常
- 在惊悚游戏搞网恋[无限]榆鱼
- 桃花痣蓝妯
- 夫君他是科举大佬杜卿卿
- 我养成了未来残疾暴君狐狸浣浣
- 替身他修无情道若兰之华
- 重生七零芳华浓杨李涛涛
- 治愈偏执的他[八零]咚太郎
- 小青鸾今天穿去哪里呀荔箫
- 科技传承一桶布丁
- 神书薪意
- 咒术侵蚀Sp赤红
- 时空测谎师:双生迷局量子叙事
- 楚明探案多情神刀
- 异端事物收容所直角废墟
- 太素佛主:启量子幻域究佛魔玄机诗天意
- 末世之废土之路BE的故事
- 求生从种田开始爱吃油醋拌面的徐津
- 老九门之密藏风云蜻蜓队队长
- 卧底中捡了一个假罪犯南极港
- 诡愿:大学生除灵手册流殇充不起
- 僵尸:逆天徒儿,惊呆师父九叔百无聊赖的如月
- 抗战:开局保安团,手握生存系统刀神约瑟夫
- 作为牛马我活到了末世陆个老六
- 我在九门为非作歹的日子晨小熙
- 鸿蒙战神从地球废墟杀到星神座九龙水晶
- 系统穿越【我靠系统点亮科技树】七彩青龙
- 雾都诡画师木木木木子书
- 盗墓:摸金校尉,解锁风水宝地汴梁城的神兽
- 末世,我的空间能种出世界树X的狂想日记
- 无灯夜话半水先生
- 逃离时间线,我反杀不过分吧?Aenstion
- 血玉噬主无遐想v学如海
- 机械修罗知世乌龙山
- 末世:被困女大寝室,一秒一物资点发光的水
- 付费首发】《让爱消亡于潮汐》温以棠 纪聿城纪聿城路语棠
- 抖音独家】连载至279《媚妾撩人,清冷权臣饿疯了》凌曦 沈晏席秋娘祁照月
- 青史为鉴牛皮糖糖糖
- 全能逆袭系统!assisted
- 雪人迷踪爱吃蓑衣米酒的清芷
- 被骗网赌百万,缅北惊魂求生冀北的馒头
- 恐游,开局病娇妹妹求我别杀她过凌晨是早餐不是宵夜
- 星际兽世:小玫瑰竟是最美雌性!林惊月
- 娇雌万人迷,顶级雄性夜夜争欢小茉莉
- 上岸后,我靠摆烂当星际霸主花卷奶茶青
- 诡阵之战:我的中式恐怖碾压全球不看文言文
- 冰封全球之打劫似梦1似醒
- 刑案侧写师:我靠读心直播追凶星渊劫
- 夜塔集鲤的笔
- 卧底中捡了一个假罪犯南极港
- 雾都诡画师木木木木子书
- 我,后土血裔,轮回诸天快穿狂魔
- 摸金盗墓笔记芝麻小豆
- 子夜异闻古皖老村
- 赛博轮回:我在星际拆解神明阿牛牛牛
- 新编民间故事大杂烩云影流光
- 从契约精灵开始笔墨纸键
- 废柴美人超好孕,五个大佬宠不停梨梨九
- 或许从未有人成仙一心安眠
- 付费首发】《九零弃夫翻身成女团长心上爱》苏忱 傅叶紫傅叶紫苏忱
- 付费首发】《雨过晴天皆是光》孟忻枝 司霆烈孟忻枝司霆烈
- 付费首发】《让爱消亡于潮汐》温以棠 纪聿城纪聿城路语棠
- 智能乱世,我在母系氏族赤身拼搏孤独追梦人
- 绝命盛宴下坠的枫
- 全能逆袭系统!assisted
- 胜天之大夏再起鬼书生
- 快穿:敛财人生之无限资源风砚水
- 鬼玺:我当无常那些年陌镝
- 末世团灭后,我征服了女主后宫风声水祈
- 大妖三千神奇小小猪
- 末世:你有异能,我有神功江州闲人
- 末世重生后,我和疯批反派HE了乐盈忆安
- 七日之门谁特喵吃土豆啊
- 开局烧烤摊?我横穿整个末世暴富瑚溯
- 盗墓之可单开族谱聊聊呗不聊
- 我本是咸鱼,来救世了【无限流】秋天的刺猬
- 穿成兽世娇娇雌,顶级兽夫追着宠转眼烟雨
- 老九门之密藏风云蜻蜓队队长
- 我也不想破案,可尸体围着我转疯小鸟
- 抗战:开局保安团,手握生存系统刀神约瑟夫
- 作为牛马我活到了末世陆个老六
- 灵渊诡秘录山逸君
- 武判九局:我的选择能改命红尘一布衣118
- 恶雌种田不攻略,黑化兽夫急红眼啃月亮的鱼
- 无灯夜话半水先生
- 盗墓:开局选择方士流光下的寒冷
- by《[综武侠]黑店日常经营中》作者:三蔓子陆小凤一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