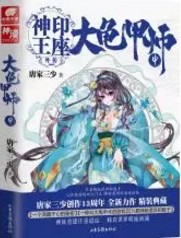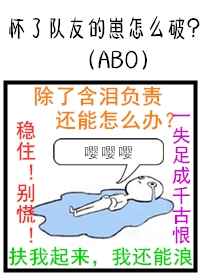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番外 胡骑长歌(3/3)
理,也往往是说得容易,做得难。
”他吸了口气,取过独孤尚手里的宋玉笛,“少主决定的事,贺兰柬无权阻拦。
但鲜卑权令不能流失,我先为少主保管,等你回来再归还。
” “好。
”少年话音落下,黑袍如烟飞逝,跨上山脚的坐骑,勒紧缰绳,急急奔赴沉寂的夜色中。
贺兰柬目送他的背影消失,转过头,却对上一对隐含忧患的冰蓝色眼眸。
“你没睡?”贺兰柬愣了愣,随即有些诧异,“依你的脾性,竟不拦少主?” “不必拦,他会回来的。
”宇文恪说得无比坚定,看了眼贺兰柬,“那个人,也跟着他去了。
” “那个人?哪个人?”贺兰柬念光闪过脑中,面色变了变,“难道是说那个一路跟踪我们的人?” “颠来倒去,你啰嗦不啰嗦?”宇文恪实在难以理解贺兰柬每次提及那人时必有的反常,冷淡道,“就是他。
” 山风拂衣生寒,贺兰柬望着远方夜色,一霎静驻成石。
独孤玄度身为北朝大司马,书房中自有各地关险的详图。
独孤尚从小耳濡目染,亦对北朝各座城关的地势和兵力分布了然于胸。
此刻到了雁门关下,凭借夜色的遮掩,飘身纵上城墙,靠近雁门关城楼,趁主将外出巡逻的一刻潜入,本要盗出令箭就走,然而目光却停留在书案上的一卷帛书上,再也挪动不得。
“独孤一门全族诛灭——” 满卷墨迹,刹那似化作无数刀剑,锋利刺入周身筋骨,不见流血,却挖尽了他的魂魄。
独孤尚脑中空白,耳畔不闻任何声响,仿佛深渊之下,唯他一人在奄奄一息中挣扎不休。
父母族人…… 他难以呼吸,窒闷之间,望见死神森冷的华袍已在面前飘忽隐现,那寒煞的气焰正无处不在流窜全身血液,直夺自己的心脉—— “咳!”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果然不请自到!”身后有人阴恻恻地冷笑,“我就知道,想要从我延奕的防守下逃出,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火光映照的金色铠甲光芒四射,骤然现在室中,铮咛一声,寒光出鞘,那将领挽剑如风,聚着无穷的杀气,刺向书案前呆立的少年。
一缕冷意透背而入,胸膛间清晰可闻“喀嚓”脆响,竟是生生穿裂了他的肋骨。
独孤尚咬紧了牙,随着那柄剑锋在体内一寸寸试探的刺深,一时竟觉解脱,生无可恋地想:就此追随父母去了吧,又有何不可…… 是啊,有何不可。
他想要闭眸,就此束手就擒。
然而眼前的黑暗不但未能带来安宁,却恍惚让他看到了父母散命时的惨状——天地失色,冤案难平。
一时怒气蓬勃气血,他放声冷笑,手指猛地夹住已穿透胸前的剑锋,狠狠运力,震断长剑。
反身横臂荡出连绵剑气,直罩延奕全身命门。
延奕未想他重伤之下竟还有这样的内力,欲点足后退,却抽身已晚,左臂上一阵火燎的刺痛,深入数寸的伤痕流出的黏稠血液,顷刻湿透衣甲。
“真不要命了?!”延奕冷冷望着独孤尚,看着少年的脸色慢慢褪尽血色,扔掉手中只剩一截的残剑,随手夺过涌入城楼中亲卫的佩刀,再次刺向独孤尚。
“右退!”一道极细的声音飘入耳中。
独孤尚喘着气,艰难闪避开延奕凌厉的一刀。
方才最后的那一剑已耗尽了他的气力,他扶着书案,眼前涌出阵阵血黑之色,神思难以控制地散乱,只觉有什么在胸中流动,随着溢出的鲜血,在不断消亡…… “嗬!”闷哼声中,刀锋终于刺上肩头。
他脚下失力,身子踉跄方要跌倒,却有清风拂过身侧,一双有力的臂膀将他紧紧揽住。
“父亲……”他眼前已无光明,模糊记起那是梦中曾遇的温暖,不禁嗫嚅着喊道。
“阿弥陀佛——” 昏死之前,入耳的最后一句,禅音入心。
“竺深大师?”延奕惊异道。
眼前的黑袍人不知何时来到城楼上,悄无声息,数万将士竟无一人发觉。
待他解开头上的斗笠,遮脸的黑纱褪下,却露出一张悲悯世人的僧者面庞。
延奕自知他为当朝幼主的皇叔身份,不敢慢怠,将弯刀交还亲卫,上前笑道:“大师何故来了雁门?” 竺深不语,只探了探独孤尚的鼻息,闭眸一叹。
他伸手虚抚过独孤尚的面庞,低声念经。
延奕听在耳中,依稀辨出是超度之意,不由眯起眼看着竺深怀中渐渐僵冷的少年面庞,得意微笑。
低沉的呢喃声中,等待良久,经才终于念完。
竺深放平独孤尚的身体,站起身,于延奕身前合十行礼:“贫僧不敬,欲求施主一事。
” 延奕忙还礼道:“延某不敢,大师有话请说。
” 竺深低眉垂目,轻声道:“独孤小施主今日既已散命将军手中,想来将军也完成了朝廷的严明。
他的身体,请将军交与贫僧归还云中。
” “这……”延奕犹豫不决,“大师既然遁离世尘,这样棘手的麻烦事,还是不必管了吧。
” 竺深抬起双眸,望着他:“独孤小施主并非旁人,他与贫僧缘深,素为忘年知己。
此事将军亦不必有其他顾虑,将来朝廷若有怪罪,贫僧自会为将军解释。
” “如此。
”延奕透了口气,望了眼躺在地上的独孤尚,并不放心,俯身探过他的鼻息,摸过他的脉搏,见真是全身上下无一生气了,方才点头,“大师既然这般执着,延某不敢再拦。
”他站起身,揖手道,“大师请便。
” 竺深合十谢过,默默弯下腰,抱起独孤尚,飘然离开城楼。
“延将军!”楼外有亲兵禀道,“城楼下有人叫关,苻家小公子连夜求见将军和雁门太守,说有要事相商。
” “苻子徵?”延奕皱眉,“乳臭未干的小孩儿,他能有什么要事?”尽管不情不愿,碍于苻氏一门在乌桓贵族中的地位,延奕还是命人大开关门,亲自迎下城楼。
(四)
独孤尚再度睁开眼时,身处披山霞色中,青鸟啼鸣耳畔,红英遍生岩上,若非胸前隐痛、肩臂难动,一时迷惘倒如隔世重生。他浸泡在温泉中,雾气氤氲,充盈满目,想要爬上岸,稍动一动,竟是骨骸四散的痛楚。
仿佛身体已羸弱至不堪一击,偶有风吹,便可碎裂。
“觉得如何?”祥静的声音在一旁传来。
独孤尚转过头,才见草蒲上一缁衣僧者正静静打坐。
“大师?”他刹那想起昏死前的禅音,那一夜血光剑影更是即刻浮至眼前,不曾散去的致命犀利。
自己竟还活着—— 鬼门关前逃过一截,他却难以理清心里的感受,苦笑了声:“大师,你救了我?” “不算。
”竺深望着他,眸光温和,“依你现在身上的伤,若离开这温泉的治疗或者是我的内力,将随时会丧命。
” 独孤尚摸了摸自己的脉搏,又望了眼竺深苍白的面庞,这才知他为自己的伤势,怕已耗尽了内力。
踌躇半晌,他微张嘴唇,想要致谢,然而恩情厚重,却非言语能够偿还。
“大师……”他开口,又沉默,最终低声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桑乾。
” “已出了雁门?”独孤尚怔了怔,下意识便道,“我还有几位族人……” 竺深微笑着打断他:“别担心,三天前,苻子徵带了蓟临之到雁门关,贩马出关,你的族人们都装扮成苻氏马场的驭马奴,已然安全北上了。
” “三天前?”独孤尚望着天色,他昏睡长久,已难辨人间岁月。
“就是你独闯雁门那夜。
” 独孤尚闻言疑惑:“那日石勒虽已去涿郡请援,但路途遥远,绝不会那样快。
”他思索顷刻,看向竺深,“难道也是大师暗中援手?” 竺深摇头道:“贫僧乃出家之人,血光争斗的谋算之事,于我而言,是毒蛇猛兽,避犹不及。
如今欺世救下小施主,我已是破戒了。
” 独孤尚不再言语,袅袅雾气沾湿他的眼睫。
他眸光转动,惊觉自己竟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事,立即挣扎着攀出温泉,然而身体刚离开泉水,筋骨血液却登时如冰封一般,激得他喉间生生涌出一阵腥甜。
竺深忙过来扶住他:“我方才说过,你暂不能离开温泉!” “马邑,马邑!”独孤尚唇无血色,紧紧抓住他的衣襟,“大师,我的族人……” “阿弥陀佛。
”竺深合十,低低叹息,“已迟了。
两日前,马邑血染残阳,关外之地,就此平添万缕清魂——” 独孤尚目光冷凝,眼前绿水青山,一霎颜色骤变,阴风森森,暗红涌动,尽成冥河血川。
他选择活下去,却不知命运留下的,竟是永无止境、死亡的逼迫。
在桑乾修养了一个月,竺深终于制好可以控住独孤尚伤病的药丸,这才带着他北上云中。
此时已是初秋,塞外黄沙飞舞,树木枯黄,万里晴空之下,风光萧索难言。
之前逃亡一路上因北朝军队的严防死守,难见飞鹰击空,等出了桑乾城垣,马匹上独孤尚抱着竺深的腰,望着蓝天下厉啸不断的飞鹰,恍然了一刻,才促唇吹出哨音。
五六只飞鹰纷纷飞落,拍翅环绕他的身侧,腿上竟无一例外都系着竹管。
独孤尚一一看过,才知是石勒贺兰柬他们回到云中,派出数千只飞鹰,携带同样的信函,一直在沿途找寻自己。
“尚儿,信中说什么?”竺深见他许久不语,回头瞥了一眼,见密函上字迹诡异,非寻常汉文,遂多顾几眼,问道,“这是鲜卑古字?” 独孤尚点点头:“嗯。
”这一个月来,竺深为教他护住心脉的内功心法,已收他为徒,因此言谈间,不免随意亲和了不少。
他沉默了一刻,续道:“柔然兵动,柬叔怀疑柔然女帝将要趁我鲜卑大难之际,夺取云中。
他们……”他言语略住,低下头,轻声道,“世人都当我死了,他们竟还未曾放弃。
” “贺兰柬……”竺深微微叹了口气,“他的确聪明过人,不负‘草原神策’之名。
” 独孤尚将信函收入怀中,拉了拉竺深的衣袖:“师父,事态紧急,我想快点回云中。
” 竺深本担心他的身体难抵赶路的劳顿,但如此形势下,多劝无益,只得将他瘦削的手臂围在自己腰间,夹紧马腹,提缰疾往西北。
到达云中城时,已是八月初十。
那日天色阴霾,西风甚紧。
宽阔的街道上行人稀少,数十万人的城池,昔日繁华鼎沸,号称塞外第一城,如今却静寂成空,处处透着颓败。
塞外烈风穿梭巷陌,吹鼓着酒肆上飞扬的旗帜,一阵一阵地,猎猎作响。
鲜卑诸族老虽不曾放弃希望,但一月过去仍未有独孤尚的消息,却也是各自黯然神伤着,竭力掩饰着已近绝望的心绪。
贺兰柬久病未愈,接连多日卧榻难起,这日石勒与族老们聚在他房中商事,议过两个时辰,见贺兰柬精力难支,众人待要散去,却见贺兰无忧灵活的身影猴子一般窜了进来,手脚飞扬地,一不小心碰落了贺兰柬搁在案上的药碗。
“无忧!”贺兰柬头疼不已,斥道,“说了多少次,还是这样毛毛躁躁!” “叔父……”贺兰无忧人如其名,性情纯真,绝无忧愁,虽怯于贺兰柬的厉斥瑟瑟缩起了脖子,但眨了眨眼睛,下一刻还是天真无邪地对他微笑,气得贺兰柬又是止不住地猛咳。
“叔父,少主回来了。
”贺兰无忧在叔父凶狠的目光下故作文静,轻声轻气道。
“什么?”贺兰柬愣住,满室的人俱是僵住,皆直直瞪着无忧,目光迫切。
无忧遂挺直腰板,大声道:“少主回王府了!是一个老僧人送他回来的!” “僧人?”贺兰柬心念微闪,却也来不及多想,激动之下,赤足下榻,跟着狂喜的诸族老,慌慌忙忙地迎去前庭。
众人到了堂上,方见原本在城外军营中训练士兵的拓拔轩竟是比谁都提早赶到,正抓着独孤尚,神色欣喜却又担忧,不住向他询问雁门关发生的事。
独孤尚面容倦白,气息微茫,眼尖的族老一看便知他重伤在身,忙上前拉开拓拔轩,让独孤尚坐在榻上说话。
“并没有大碍。
”独孤尚勉强笑了笑,“族老们不必担忧,都坐下吧。
”等堂上诸人坐定,他目光流转,却不见宇文恪,心中一紧:“怎么未见恪父?” 石勒道:“恪老双腿不便,正在后庐静养。
” 独孤尚微微放下心,接过离歌递来的茶盏,又问道:“狼跋族老还没有消息吗?” 石勒摇头,叹息道:“没有。
”看了眼独孤尚,取出袖中的信函,递给他,“正巧少主回来了,这是今日刚接到的云阁飞信,云阁主两日前已出雁门关,想必这几日也将到云中。
” 独孤尚读过信函,觉得奇怪:“信中为何不曾提到阿彦?” 贺兰柬与石勒对视一眼,皆是沉默。
独孤尚察觉出满座族老闪避的眼神、凝重的面容,不禁皱眉:“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这个……”贺兰柬斟酌着道,“前些日子曾有密报自江左送出,说彦公子虽已救出牢狱,却被萧璋途中追杀而亡。
”见独孤尚凤目倏地暗冷下去,眉宇也益发凛冽,忙又补充道,“不过依我揣测,此传闻怕是有误。
若彦公子当真丧命,云阁主何故还要千里迢迢赶来云中?他信中虽未提及,怕也是担心信落在别人手中泄了秘密。
我想……彦公子应该还在人世。
” 独孤尚垂眸静思良久,慢慢合起信函。
“柔然那边动向如何?”他抬起头,眉眼间已清寂如常。
未想他就这样转过话锋,诸族老都是一怔,本要松开的那口气,于是再度堵回胸前。
贺兰柬喝了口茶,润了润干涩的喉咙,方替众人回道:“斥候探得,柔然早在七月之初便大举全国军队,近五十万大军,在马邑之变当日,分五拨自柔然出发,西进云中。
本来依他们的速度,快则三日,慢则七日,柔然柱国阿那纥率领第一拨骑兵必已到达赤岩山。
但不知中途出了什么缘故,行军路上,却忽自柔然王城传出女帝病重将殁的消息,阿那纥紧急返回王城,他的军队就此在旷野滞留了一个月。
此前三日,阿那纥方才再出王城,重新整军。
” “七月初?”独孤尚眸间锋芒闪过,“难道柔然人竟早就未雨绸缪,能够未卜先知?” “我也在怀疑,”贺兰柬顿了顿,“听说姚融素与柔然勾连密切,中原事乱,怕与柔然逃不了干系。
” 独孤尚目色冷冷,默思片刻,又道:“匈奴那边动静如何?” “匈奴老单于刚死,诸部争权,此刻正忙于内乱,想来并没有东顾的精力。
” “那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后顾之忧。
”独孤尚眉宇稍舒,道,“我本以为会是北朝借机侵袭云中,不过一路回来,并没有看到边关有调兵北上的迹象。
两面无患,我们只需全力应对柔然便可。
” 贺兰柬道:“少主不知道,北朝如今亦生出了乱子。
姚融和裴行在朝中大肆排除异己,不料触及了司马皇室的利益,清河王、乐安王、北海王等八王正与朝廷对抗着,想来无须多久,便会有人借勤王的幌子策动谋乱。
” 谋、乱—— 独孤尚黑瞳深幽,一瞬的痛楚严严藏在深处,常人并不能发觉。
但他心中却清楚地知道那是怎样的悲哀,独孤一门百年忠烈,然而事到如今,这样的两个字,却成了轻易便可刺痛自己的缘由。
一时议事毕,独孤尚去后庐见过了宇文恪,方才回到自己的庭舍歇息下来。
暖池中洗去一路风尘,换过干净的衣袍,走去书房时,果然见贺兰柬已笔直候立在室外。
“进来吧。
”独孤尚揉着额,在案后坐下。
贺兰柬此刻穿戴整齐,已非方才披头散发、乱衣赤脚的狼狈模样,入室揖了一礼,望着案上早已放冷的一碗药羹,眸光微暗,慢慢撩袍在独孤尚对面落座。
“少主还未用膳吧?”他将随身携来的食盒打开,拿出两牒饼饵、一壶羊奶摆在案上,解释道,“北朝对云中封锁边疆通行,粮草马匹等均不能北上,如今云中城中粮草拮据,吃的东西大多都补给城外军营,王府里只剩这些了。
” “我不饿。
”独孤尚只将案上的药羹喝尽,疲倦地靠向身后墙壁,“柬叔,你实话告诉我,除却老弱妇孺,鲜卑一族能战的男儿还有多少?” 贺兰柬叹息道:“我来也正是要和少主说这事。
” 他从袖中取出一卷书简,摊开摆在独孤尚面前,陈述道:“云中城原有守军将士一万五,这些人曾跟随主公历经烽火,骁勇善战,可称精锐之师。
族中另有精壮男丁六千余人,这一个月来,已由拓拔元延将军齐集城外军营日夜操练。
另有从北朝陆续逃回来的鲜卑武士,差不多有两千人,一回城,也自动归去了拓拔元延麾下。
这些人武功高强,多数曾是主公在北朝的旧部,可自编一部,作为奇兵。
” “也就是说,可战的人数仅两万余人?”独孤尚闻言眉头紧皱。
贺兰柬知他忧虑,轻轻叹了口气,温和道:“少主,其实人数的寡众并不能决定一战的成败。
天时、地利、人和,乃至兵法谋略,才是制胜的关键。
” “柬叔,”独孤尚低声苦笑,“我还从未打过战啊。
父亲教的兵法,你教的谋略……在先前,那些都是纸上谈兵。
” 贺兰柬微笑着鼓励:“凡事都有第一次的。
” 独孤尚默然。
他的第一战,紧系着鲜卑一族的生死、云中百年的存亡。
沙场征伐稚嫩如他,却又如何能有那样从容不迫的信心,去承接起这般沉重的担子? 贺兰柬何尝看不出他的忧患,欲再劝说:“少主……” “不必多说了。
”独孤尚伸手止住他的话,“柬叔,若我如今为帅,只能是轻率之举。
往日我虽跟随父亲远征过高车,却也不过是坐在马背上观望,并不懂排兵布阵,更不知如何上阵杀敌。
”他卷起案上竹简,思索稍瞬,道,“鲜卑与柔然一战,以元延叔父为帅,我只当他帐下先锋便可。
” 鲜卑一族除却独孤玄度与慕容虔,最善战的将军莫属拓拔元延。
贺兰柬如今亦无更好的办法,想了想,只得颔首道:“如此也好。
” 统帅之人已定下,独孤尚想着今晚便要去军营历练,然一路劳顿疲乏犹在,待要歇息稍顷,却见贺兰柬端坐对面,却无丝毫离开的意思。
独孤尚无奈道:“柬叔还有事要说?” 贺兰柬笑了笑:“我听无忧说,今日是一位大师送少主回云中的。
诸族老托付我向那位大师当面致谢,不知——” “师父已不在云中了。
”独孤尚话语微顿,到此刻不得不说明伤情,“我如今伤未痊愈,需岐原山上几株药草,师父为我寻药去了。
” “如此……”贺兰柬愣了一会,才垂首笑道,“也罢,那就下次再见吧。
”他小心翼翼自怀中取出宋玉笛,双手奉还独孤尚,“少主的笛子,完璧无损。
” 独孤尚点头道:“多谢柬叔。
” 贺兰柬微笑起身,再度揖礼,恭肃之处全不同往日。
独孤尚自知他这般举动下的深意,沉默着目送他退出庭外,胸前气息愈发沉闷。
“少主?”有人在窗外小声呼唤。
独孤尚转过头,只见贺兰无忧趴在窗棂上,眸子一如既往地纯澈明亮,只是此刻看着他,却微微有了些忧愁之意。
“什么事?” 贺兰无忧道:“少主,你和小郡主的那只鹰十天前飞回来过……” “画眉?”独孤尚这时才想起逃亡那夜的鹰和信,怔忡片刻,才又道,“那鹰呢?” “又飞走了。
”贺兰无忧轻声道,“它那时身上还有伤,可我却拦它不住。
大概是看你未回,又飞去南边找你了……” 独孤尚静默不语,望着庭间铺洒的阳光,轻轻吸了口气。
良久,才低声道:“我知道了,你自己玩去吧。
”他站起身,疾步走回内室暖池,从旧衣中翻出那片紫绢,凝望良久,缓缓收入怀中。
或许,这是今生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了。
夭绍—— 在父母族人、乃至鲜卑一族的灭顶之难前,即便是这个曾经带给他无数温暖和微笑的名字,此时此刻,亦不能让他自悲戚沉痛之间稍觉一丝的平缓宁静。
正如洛都书房中那些被收藏在玉匣里的美好过往,抄府诛族的屠戮之下,怕也早就沦为了一堆灰烬…… 八月十三日傍晚,柔然柱国阿那纥率领的八万精锐骑兵率先抵达赤岩山下,与鲜卑军营对峙柯伦水两岸。
深夜时分,拓拔元延领着五千步卒绕道赤岩山后,欲趁对方劳军远征、立足未稳之际偷袭敌营。
子夜乌云遮月,五千步卒分成三路,自西北、东北狭窄的山道中悄然靠近柔然营寨。
丑时一刻,正值万籁俱寂、山风渐急时,柔然营寨灯火零星的千帐间忽有一道烈焰随着尖锐的鹰啸划过夜空,一时柔然军营外四面火光冲天,弯刀齐齐出鞘的寒煞杀气撼得山陵亦在颤抖。
柔然将士全然不备,望着面前汹涌无尽的雪锋浪潮,应对之间不免胆怯暗生、手足无措,更兼营寨几处火起,全军大乱。
拓拔元延领着亲兵数百人趁乱杀入中军,本想擒贼擒王,先灭柔然举国侵犯云中的气焰,不料中军行辕的森严戒备远非左右两翼可比,刚入营中十步,数千摇晃刺眼的火把纷纷散去,眼前澄然一清,望到的景象惊得拓拔元延顿出一身冷汗。
“撤退!”他放声喊道。
然而已经来不及,向自己这边瞄准的是数万紧密的箭镞,在远处高岩上一老者威严的喝令下,冷箭飞落如雨,席卷而至—— 八月十四日的清晨,东方曙光刚露,独孤尚与拓拔轩率领两千骑兵成功截断柔然粮道,满载而归。
两人在营前下马,望着络绎不绝驶入军中的粮车,一个多月以来的压抑之下,至此刻才稍觉舒心。
然而微笑还未在唇边漾起,便望见石勒一脸凝重之态,自营中快步而出。
“少主,轩公子,快入营看看拓拔将军吧。
”石勒催促甚急。
拓拔轩疑惑:“我父亲怎么了?”此话虽问出,却也不必等石勒回答,只盯着他眸中的伤痛之意,便如同冰水兜头罩下,面色登时苍白。
“轩。
”独孤尚扶住脚下发颤的拓拔轩。
拓拔轩抿紧双唇,扔了马鞭,疾步奔向中军。
独孤尚望着他跌跌撞撞的背影,默然片刻,方才转过身,无力坐在营前的岩石上,手掌覆住了脸,半晌无声。
“石族老,”他猛地想起什么,一个激灵,立即站起身,“我的药箱可在军中?” “不在……”石勒叹息道,“就算在,也来不及了。
拓拔将军中了六箭,只撑着一口气,想是为了见轩公子最后一面。
现在怕已……”话未说完,声音却在中军突然传出的哭声中生生止住。
“难道真是天灭我鲜卑不成?”他苦笑。
仰天恨望,苍穹无声。
辰时之后,拓拔轩将拓拔元延的灵柩送回云中城。
独孤尚独自执掌营中军务,在贺兰柬的指点下逐渐熟悉军情。
午后,一封谍报自柔然王城送至,言柔然五十万大军最后一拨已离开王城,然而朝中留守监国的融王日前却连续几日不曾上朝,细作套得融王亲信的话,探知融王已私自离开王城。
“融王?”独孤尚皱眉,“之前并不曾听说柔然还有这样一个王爷。
” 贺兰柬道:“据说此人是柔然女帝唯一的幼弟,只是身份神秘,鲜少露面。
”他想了想,又道,“不过柔然监国的人私自离开王城,怕是柔然女帝不曾想到的事,对我们而言,也不喾为扭转局势的机会。
” “柬叔的意思,想要以奇兵偷袭王城?”独孤尚皱眉,“云中距离柔然王城路途遥远,而且柔然军队四面八方赶来云中,路上一旦遇到,必是刀锋相对、你死我亡……” “不是偷袭,”贺兰柬摇头叹息,“经拓拔将军一役之殇,军中将士如今怕是闻偷袭而色变了。
”他沉吟道,“我只是想,利用柔然王城的细作,稍稍弄出些风吹草动,怕就足以让柔然女帝生出后顾之忧了。
” 独孤尚点头:“柬叔说得是,此事便交由你办了。
” “是,”贺兰柬道,“不过这些只是旁门左道,并非两军对阵胜败的关键。
柔然五十万大军,倾国举兵,誓要夺城。
鲜卑百年基业,倾族存亡,誓要坚守。
这一战,以如今的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可避免,其战之难、恶,想来也是亘古未见。
而且昨夜的偷袭,我们虽夺了粮草、杀敌上万,却也损失了三千劲卒,如今将士已不足两万人了,何况,战马粮草等也极缺乏……” “末将有事要禀少主!”帐外忽传来声音打断贺兰柬的话。
贺兰柬住了口,独孤尚道:“进来。
” 那将军大步入帐,因方才拓拔元延殡天之故,他眼角泪痕犹在,然而此刻唇边却又隐隐上扬,含着一丝笑意。
贺兰柬望见他这幅模样不免心中不悦,正要叱责,却听那将军道:“少主,贺兰将军,狼跋族老回来了!” “什么!”独孤尚与贺兰柬都是惊喜起身。
那将军微笑道:“狼跋族老还带回五千战马,另有逾万人的主公旧部随他一道回了云中。
” 独孤尚与贺兰柬对视一眼,皆是疑惑不已,正要再问,那将军又道:“对了,先一步来报信的人还说,江左云阁的云阁主,也与狼跋族老一并来了云中。
” 阿彦! 独孤尚难耐心潮涌动,疾步出帐,跨上坐骑,扬鞭直奔东南。
出了营寨,拂面冷风不住,空中万里云霾蔓延阴沉,苍原上树木飘摇,大雨欲来。
独孤尚驻马在高岩上远望,十里外马蹄声岿然震地,乌泱泱一片正如低坠的云翳,正急急飘往云中的方向。
“这就是所谓的归心似箭了。
”贺兰柬骑马追赶过来,望见此景,忍不住感慨而叹。
独孤尚默默望着那辆摇摇晃晃行驶在马队之后的皂缯盖车,想了片刻,对贺兰柬道:“柬叔,你与狼跋族老领着将士和马匹去军营,清点姓名,通知这些将士的家人,准许他们今晚入营相聚。
” “是,”贺兰柬看着他,“少主不与我回军营?” “我回王府,等姑父和阿彦。
”独孤尚掉转马辔,双腿猛夹马腹,轻骑径入城中。
越过绵绵城垣,云中城门前,前方的队伍马蹄惊风,绕城而过。
独钟晔驾着马车,慢慢驶入云中城门。
位在城中西北的王府前,独孤尚一身黑绫长袍,已等候在阶下。
少年虽未长成,身材已极是修长。
钟晔望着他清寂眉目下再难动色的刚毅面容,不禁轻轻叹了口气。
这样异于常人的快速成长,只有他与自家少主经历过。
血雨腥风,风刀霜剑,绝望之下的挣扎和磨砺,常人何能体会。
他眼眸幽苦,神情暗淡,紧拉缰绳吁马停下,对着独孤尚揖手一礼,转身打开车门。
“阁主,少主,我们到了。
” 淡黄衣袂闪出车厢,云濛面庞消瘦,唇上无一丝血色,走下马车时,右臂袖下空荡无物。
“姑父?”独孤尚脸色一变,“你的胳膊……”他想起自逃亡路上看到的云濛信函,无一例外笨拙艰涩的字迹,这才依稀明白过来,咬了咬牙,没有再问。
云濛眸眼温和依旧,仿佛流血杀戮的风浪只是过眼云烟,对他笑了笑,转身将手伸向车中:“阿彦,下车吧。
” 独孤尚的脚步忍不住向前挪了一挪。
那少年一如既往地淡然平静,缓缓自车中走出。
他面容雪白得透明,眼眸中除了冰寒的幽邃,别无其他。
望向独孤尚时,目光停留了片刻,却又淡淡移开。
血海深仇的伤痛再如何压抑,他也难以伪装出豁达的神色。
只是默然走到独孤尚面前,唇微微张启,无声吐出他的名字:“尚。
” 入耳再无冰玉般雅正清冽的声音,独孤尚心中愕然,望了他片刻,并不追问,只道:“路上劳累了,寒园已收拾好,你先去休息吧。
” 郗彦神色倦累,虽是初秋,身上已着一件轻薄的狐裘。
闻言轻轻点了点头,看了云濛一眼,便与钟晔先去了寒园歇下。
书房,独孤尚将主位让给云濛,自己坐在下首,边煮着茶汤,边问道:“姑父,那些战马可是你出钱向苻氏马场买的?” “也不算,”云濛道,“苻景略另有事要求你虔叔叔和我,算是半卖半送。
”见独孤尚惊讶抬眸,云濛叹了口气,“你是不是还不曾听说北朝的事?” “什么事?”独孤尚道,“自鲜卑人流亡以来,北朝封锁边疆诸城,来往的消息常有阻滞。
” “如此,”云濛沉吟了一下,道,“北朝因鲜卑一族的事生出大乱,清河王、乐安王、北海王等八王趁乱联手夺权。
朝中诸将一时并无统帅之才,各自为政,与叛军相较竟多有不敌,且各州府兵中未曾被牵涉的鲜卑将士亦难服乌桓贵族的统领,频生祸事。
洛都皇权目前岌岌可危,朝中诸臣无法,因你父亲和慕容华俱已被害,他们只得寄希望于流放西域的慕容虔。
” 独孤尚垂眸冷笑:“就凭他们手里仍掌握了数万鲜卑人的生死,还有慕容全族人的性命,虔叔父就不得不答应。
至于战马和放回我父亲的旧部,想来也不过是拉拢虔叔父的一个手段,怕并非对我父亲一案的退步。
” “确实如此。
”云濛望了他一眼,心中暗暗惊诧:不过十四岁的少年,竟能将局面看得如此通透。
一时茶汤煮沸,独孤尚盛出汤汁,递给云濛:“我老师求姑父帮忙的是什么事?” “怒江战事,”云濛单手执着茶盏,看起来并无多少心思饮茶,慢慢道,“两朝虽各自问罪了主帅,但驻怒江两岸的屯兵仍在。
对八王之乱,北朝不得不放手一搏,却又担心东朝趁机北上,因此请我为说客,北朝朝廷愿与东朝休战议和。
” “还需议和吗?”独孤尚目中暗生戾色,“独孤氏和郗氏同时受难,难道两朝当权者就没有一丝的心同意合?” 云濛叹道:“就算真有,没有公开的盟书议和,怕是难堵住天下臣民悠悠之口啊。
” 独孤尚沉默,半晌,才又问道:“先前天下传闻阿彦被湘东王萧璋追杀致死,姑父是怎么瞒过来的?那个萧璋,我倒是曾听父亲说过,此人甚为看待情义,是不是……” “砰!”一声裂响,扼断了独孤尚的话语。
他讶然看向云濛,才见他的脸色是自己从未见过的铁青阴寒。
流淌满案的茶汁映入那双素来温润的双眸,顷刻竟化作无数淬毒怨恨的锋芒。
独孤尚只觉室中空气一霎凝成冰封,心念闪过,全身僵硬,喃喃道:“姑父,难道被杀的是……” “是,”云濛声音嘶哑,闭起眼眸,神容瞬间衰老沧桑,“死的是阿憬。
” 独孤尚手脚发冷,脑海中浮现出云憬意气飞扬的骄傲眉眼,顿时满心悲凉。
“不止阿憬……”云濛话语凄然,低低道,“还有谢攸、陵容公主,也因此事连累,双双殒命。
连他们的女儿夭绍……亦中了雪魂花毒,至今昏迷未醒。
”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当真咬春饼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咸鱼飞升重关暗度
- 仙君有劫黑猫白袜子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看见太子气运被夺后花里寻欢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01入学篇(上)佐岛勤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佛系女主崩坏世界[快穿]实心汤圆
- 失忆后我招惹了前夫萝卜兔子
- 首辅大人重生日常/今天也没成功和离时三十
- 独行剑司马翎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流氓老师夜独醉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真爱没有尽头科林·胡佛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夕照斑衣白骨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游弋的鱼乌筝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非典型NTR一盘炒青豆
- 不朽神王犁天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夏日长贺新郎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后桑奈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羞耻狼空
- 有只海豚想撩我焦糖冬瓜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没完晚春寒
- 他们今天也没离婚廿乱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独立日学习计划一碗月光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情终孤君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学长在上流麟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离心ABO林光曦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有只海豚想撩我焦糖冬瓜
- 独立日学习计划一碗月光
- 嗨,保镖先生棠叶月
- 追随者疯子毛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