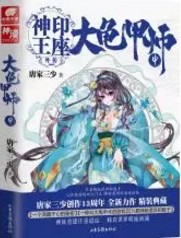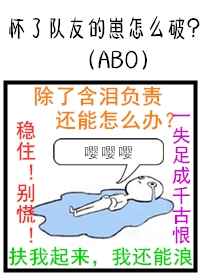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十七章 长袖善舞(1/3)
(一)
永贞十三年,六月十六,邺都。天色还未全白,墨青色的城墙高耸森严,暗淡晨光之下,古石斑驳,略显沧桑。
时辰尚早,沈府总管祁千钦却一早出了西城门,骑马在城墙下兜绕几圈,见远处广潜山侧的官道上空寂一片,青天尽处也无尘土扬起,祁千钦遂未在道上多停留,折转往曲水之畔的酒庐。
庐内灯火若隐若现,却不见小厮迎上,祁千钦下马自拴了缰绳,步入庐中。
这个时辰还没有迎来送往的热闹,满堂空寥,唯临窗他惯坐的席案已被人占据。
祁千钦微微皱眉,借着堂上晦暗的光线,瞧见那人手执杯盏面朝窗外,容貌虽不可见,但一袭金色长袍在微弱的烛光下显得孤秀俊逸,却是似曾相识的眼熟。
祁千钦怔了一怔,盯着那背影再看了几眼,默然转身,坐在另一侧窗旁。
那男子似对他的到来一无所觉,只静静望着远处的城池,看着北方青天下那绵延雍容的宫阙殿阁,良久,才伸手慢慢抚摸起腰侧佩带的寒铁弯刀。
“公子要的玉带糕做成了!”庐间内堂忽起一声长呼,一灰衣小厮匆匆小跑出来,将一盘晶莹如玉的糕点奉至金衣男子面前,“按公子说的,师傅又重做了一遍。
” 男子微微侧首,双瞳深黑如墨,望了望盘中糕点,摇头一笑:“不是这个味道。
” 小厮有些泄气,却仍掬着一脸笑容道:“您尝都没尝……” “香气不对。
”男子轻叹了口气,脸色怅然。
小厮还欲劝说,一旁却有人笑道:“这位公子要的玉带糕,蒸食时需以竹萚裹覆,方得其味。
” 小厮闻言回首,这才发现今日的第二个客人,忙笑脸迎过去:“原来是祁总管,却是多日不见了!今日一早出城,想来又是奉了丞相要命?” 祁千钦不置是否,笑道:“我出来得早,还未用膳。
如我方才所说,再做两份玉带糕,另热一壶杜康来。
” “是。
”承他方才提醒,小厮得了做玉带糕的要领,忙挑起帘子去了内堂。
而那金袍男子仍临窗坐着,头也不回,望着广潜山繁芜密青的草木,许久,才轻声笑了笑:“玉带糕、杜康……九年了,原以为早已物是人非,想不到你还能认得我,甚至还记得我爱吃什么糕点,喝什么酒。
” “过往一切,祁千钦从未相忘。
”祁千钦低声叹息,至男子案前深深一揖,“见过融王殿下。
” “融王?”沈少孤眯起眼,碎冰猛自眸底迸裂,修长的指尖终自弯刀上眷恋不舍地松开。
眼前的人沉着稳重,一如武康沈门下的历任总管。
昔日沈氏家仆中那唯一一个愿跟随在自己身边跳脱飞扬的少年,怕是再也寻不得了。
沈少孤低下头,慢慢微笑:“我还是错了。
当日被我视如兄长的祁千钦早不存世上了,如今在世上的,只是丞相府的祁总管,对不对?” 祁千钦无言以对,弯腰沉默半晌,直了直身子,温言道:“融王既来了东朝,邺都城也近在眼前,为何不入城?主公若知道融王到来,必然欣喜万分。
” “沈峥会欣喜?”沈少孤眺眼望着天边,似在疑惑,片刻后,唇角微勾,“也是,我倒也想不出他有憎恨我的理由。
仔细想想,我欠沈氏的寥寥,沈氏欠我的却是难以计数。
” 祁千钦忍不住道:“往事已逝,二公子不必……” “孤乃柔然融王,不是什么二公子。
”沈少孤冷冷截断他的话,“十年前,沈弼不认我是沈氏族人,如今本王也不必赶着去往沈府高门。
劳烦祁总管告知丞相一声:若心知有愧,我此段时间居于邺都城,请勿使人打扰。
” “是,”祁千钦轻声道,“在下斗胆,敢问融王这次南下是为了——” “北朝战事。
”沈少孤微微一笑。
话至于此,言下意味却是难以捉摸。
他想了一刻,忽道:“听说北朝苻子徵南下邺都遍访群臣,想来也去过丞相府了?” 祁千钦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以告:“前段时日的确来过两次,但皆逢主公外出,主母借由将苻公子挡于府外,此后他便不曾再来过。
” 沈少孤轻笑道:“果然如我所料。
苻子徵南下动机不纯,明知丞相夫人出身鲜卑,偏选沈峥不在时拜访,倒会装模作样。
”他略一沉吟,又问祁千钦,“你这么早出城,是来接沈伊的?” “是。
” “此处是接不到他的。
”沈少孤悠然饮了口酒,“你且回城吧,沈伊在午时前定会回府。
至于沈峥让你通知他的事,也不必过急,夭绍与他一处,他也抽不了身。
” “可是——” 沈少孤道:“荆州战报即将到达都城,押解南蜀三皇子的军队也正星夜赶赴扬州。
如今前朝既要忙着封赏前线将士,又要与南蜀重拟盟约,沈峥和沈伊都有得忙了。
至于沈太后想趁建安王来邺都的期间商定沈伊和明宓郡主的婚事,怕还要再缓一缓,所以总管不必着急。
” 未想他对东朝诸事竟这般了如指掌,祁千钦诧异地看着他,微微失色。
沈少孤却只意味深长地一笑,眼角余光瞥见曲水岸边柳枝下飘起的几缕清风,起身离案:“我另有事,先走一步。
” 他说离去便离去,祁千钦忍不住追上前几步:“那玉带糕和杜康酒……” 沈少孤道:“你的心意我领了,今日无缘,改日再聚。
这段日子我住洗玉山庄,你若想来找我,也不必踌躇再三,沈峥还不至于因为这个而为难你。
” “……是。
”祁千钦喃喃地道。
拱手相送至庐外,眼望沈少孤的身影隐入广潜山下的林木间不见了,才怔怔地收回目光,将沈少孤方才的话想了又想,丢下几铢钱,跨上马直奔城中。
日色渐渐染红了云层,广潜山被霞晖笼罩着,景色清奇。
沈少孤步入山谷林荫间,未走多远,一袭谧蓝色的裙裾便自葱郁叶色间飘然而出,静立道旁。
那女子身姿十分纤长,微卷的长发浓密黑亮,面庞被一方蓝绡遮住,露在面纱之外的眉眼傲然天成,清冷中自有夺人丽色。
望着沈少孤步至眼前,她揭开面纱,低了低头:“小舅舅。
” 跟随她身后两名短衣高靴的柔然武士也迎上来,单膝跪地道:“见过融王。
” “退下。
”沈少孤挥了挥衣袖,等武士退远,才冷冷一望长靖,“为何突然南下江左?依独孤尚和郗彦的心思,既知道我来了东朝,必会将丑奴送往北方,你在中原正好能守株待兔……”话未说完,目光瞥到长靖唇边一丝讥诮的笑意,沈少孤念光飞转,面色孤寒:“怎么,难道炤将军那边有了消息?” “是,”长靖慢慢启唇,“小舅舅南下之后,我与炤将军兵分两路,我往河东,炤将军分兵绛城以北。
我那边空等半月不见蛛丝马迹,不过炤将军却发现了阿奴儿的行踪。
她还是与慕容华的那个小徒弟在一起,但云阁从旁护卫的剑士不下百人,且过了解良,一路都有鲜卑军队出没,我们夺人不易。
” 沈少孤皱了皱眉,一时沉思不语。
长靖道:“除此之外,炤将军密信说,以阿奴儿北上的路线,该是去拢右鲜卑军营。
如此说来,我们四月底接到的密报应该确实无误,长孙伦超是真的答应了鲜卑的盟约,要将阿奴儿嫁给鲜卑人。
” “问题是嫁给谁?”沈少孤揉着额,不紧不慢地道。
再思片刻,他眸中蓦然一动,恨恨一笑:“尉迟空……尉迟,尉迟,我怎么就没有怀疑过这小子的身世!” 尉迟空?长靖蹙眉:“小舅舅想到什么?” 沈少孤并不言语,只抿紧双唇,回忆往事周折,越想越不对。
待到彻底恍悟时,内心不免一阵气苦——鲜卑当年曾有勇将尉迟昌名扬塞北,十数年前暴病而亡,想来这尉迟空便是他的遗孤。
而尉迟空既一直留在慕容华膝下,断非偶然之故,更何况昔日慕容华在殷桓身边八年所图为何,至今也是不言而喻。
如此推论下来,那慕容华当年在北朝狱中说是险些遇难,怕只怕退路早已谋好,阿姐的伸手一援必然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这般看来,所谓的情债孽缘原都是阿姐的一厢情愿,慕容华却从未有真心待过阿姐的一刻,阿姐要与他斗智斗勇,今生怕是无论如何也赢不得了。
念及此处,沈少孤看着远处高岭之巅紫烟蒸腾,忍不住长叹一声:“事已至此,南下图谋不得不做更改。
” 长靖点头赞同:“我就是想到这点,阿奴儿的事已成既定,我们无力挽回,只是小舅舅南下所图却是难上加难,长靖这才急赴江左,愿为佐助。
” 沈少孤却望着她,目色沉沉,别有担忧:“只是如此?” “当然。
”长靖笑容坦然,眸光也格外清澈骄傲,“难道小舅舅以为,时至今日,江左还有什么我不能割舍下的吗?倒是小舅舅,我却担心你太过情深义重,面对江左的一些故人,无法狠心行事。
” 沈少孤深吸一口气,念光飞转,另成谋划。
但想到此事结局必定要伤及的一些人,他心下一紧,闭眸暗道:为师也是无路可退了。
(二)
马车自南城门驶入,入城之际辰时已过。日色早出,金色炎光遍及长街巷陌。
一路上高阁夹道,连甍迭迭,挡得一丝微风也吹不透。
即便车窗纱帘皆已撩起,沈伊却仍觉呼吸不畅。
入城不过一刻,他已然是满额汗珠,频频摇动手中白玉柄的竹丝扇,抱怨道:“离开时还是清风送爽,回来时就是炙火当空了。
此时就该在碧秋池中喝酒赏花,那里才是夏日乘阴纳凉的绝佳去处。
” 夭绍静坐对面,阅览书卷,头也不抬说:“你如今在朝为官,怕不能这样逍遥了。
” 沈伊瞪眼,被一盆冷水泼下来,愈发心浮气躁。
夭绍若有所觉,抬起头嫣然一笑:“怎么,我泼你一盆冷水,不消盛暑不说,你的火却越烧越旺了?”她收起书卷,递上丝帕给沈伊,又是一笑,“擦擦汗吧。
” 沈伊的火气被抑心中,继而又无可奈何地散去,叹道:“你我都是凡人,每年暑热,为何独你不受影响?难道是吃过雪魂花的缘故?改日我也弄一朵尝尝。
” 夭绍笑意微敛,话语如冰:“这个玩笑好玩吗?” 沈伊说完便已后悔,此刻看着夭绍黯淡下去的双眸,更是坐立不安,讪讪转开话题道:“你想到方才在你父母坟前上香的人是谁了没?” 提起此事,夭绍难免再陷沉思,隐约间总算想起一个人,抬头看一眼沈伊,迟疑一瞬,还是摇了摇头。
沈伊将她的犹豫看得清楚,微笑道:“谢叔叔和陵容公主生前帮助过那么多人,其中总有知恩难忘的,或正巧夜里经由兰泽山,便上去拜了拜。
” 夭绍浅笑颔首:“或许吧。
” 且说他二人自离开荆州以来,除在江夏城中探望晋阳、辞别萧璋耽搁了一日外,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回邺都。
至此日清晨,抵达邺都城外,本该从西城门入城,但夭绍想起离邺都一年不曾为父母扫墓,心中愧疚难当,说什么也要在入城之前去兰泽山拜祭父母。
此事沈伊自无劝阻,遣走一众随侍,二人单独绕道去了城南。
兰泽山上,二人在坟前方要焚香叩首,意外却见碑前炉中香雾缕缕,正是有人刚刚拜祭的痕迹。
二人心中起疑,下山时询问慧方寺守在山脚的小沙弥,谁知那沙弥却说夜间山路封闭,并无人行走。
二人满怀困惑地离开,一路绞尽脑汁地猜测,却也想不出连夜上山拜祭者为何人。
直到此刻,夭绍方才想起曾在江陵城中与沈少孤定下的一月之约,想到那日他匆匆离去,至今日已逾半月,或先她一步来了邺都也说不定。
而世上能如此记挂着她父母的,谢粲尚在荆州,谢昶忙于朝政,除了沈少孤,也无他人可想。
车厢中一时沉寂下来。
夭绍心事重重,也无心化解气氛,探头看着远处静静蜿蜒的曲水。
华光夺目的宫阙正筑在曲水流经的最高处,烈日照耀下愈显奇伟瑰丽——那是自己生活了六年的地方。
夭绍如今望着,却觉无限遥远,无限陌生。
她想着即将要面对的人和事,那仍心心念念牵挂在荆州的神思却难以回转,蓦然间只觉手足无措,急欲逃离。
“小夭,”拐过长街,沈伊忽道,“看看这边。
” 夭绍转过头来,看着沈伊所指的方向,愕然一惊:“郗府?”眼前门庭轩然,松柏傲立,虽未入庭中,却也可以想象其中焕然一新的景象。
沈伊笑着解释:“陛下在三个月前就令度支尚书和左民尚书修葺郗府,其间池馆部署、内外庭的划分均未改动,一切皆如九年前。
” 夭绍怔怔看了好一会,才移开目光,轻道:“要是改了布局倒还好。
阿彦回来如住进去,看到旧景必然想起旧事,怕难免伤心。
沈伊却悠悠笑道:“这个你不用担心,阿彦又不会一人住郗府,到时新人住入,自有新的气象。
” “什么?”夭绍一时反应不过来。
沈伊忍无可忍地叹气,伸手拍了下她的脑袋,没好气地道:“陛下用意是为免你们新婚无所居住,这才重修了郗府。
” 夭绍闻言脸色红透,微微掉过头去,轻抿住双唇。
沈伊无限倜傥地一笑,拿起竹丝扇,替夭绍扇风:“脸这么红,是热了吧?” 夭绍瞪他一眼,沈伊促狭得逞,得意大笑。
直到谢府外,夭绍脸上红晕仍未褪去。
沈伊送她至府前,与迎出来的沐冰点头招呼过,对夭绍道:“你是明早去见太后吗?要不要我为你掠阵。
” 夭绍微微一笑:“不需惊师动众,婆婆不会为难我。
”她弯下腰,福身一礼:“谢明嘉也不敢劳沈大人再奔波。
” “何必这么挤对我?”沈伊故作咬牙切齿,言罢却又无奈轻叹,“明日要小心应对。
”笑着转身,扬长而去。
眼看沈伊的马车已遥不可见,夭绍却仍站在府前,目光落在一处,略有怔色。
沐冰等了一会,忍不住催了声:“郡主为何还不入府?月出阁一切都准备好了,郡主赶路必然疲乏,去歇会吧。
” 夭绍却轻轻蹙了蹙眉,视线仍停留远处,有些迷惑地问道:“阿公不在府中?” 沐冰道:“主公一早去上朝,还未回来,想必被陛下留在宫中商事。
” “这就难怪了。
”她轻叹道,“五叔稍等我片刻。
”言罢不顾沐冰疑色,疾步朝对面深巷中走去。
一辆车帷华丽、钩膺玉瓖的马车正停在巷口,驾车老者乌袍皂巾,五官深刻异于常人。
待看到充盈暗淡窄巷的明媚紫色,老者皓眉微展,下马行礼道:“见过郡主,我家少主已等候郡主多时了。
”他打开车门,揖手道:“郡主请上车。
” “不必。
”夭绍负手立在车外。
等过须臾,那从来都带着温和微笑的修俊男子终于缓步下车。
夭绍红唇一扬:“苻公子,久违了。
上次你找阿彦是为谈买卖,今日等在谢府之前,却不知又为何事?” 苻子徵谦和地笑:“自苻某南下东朝以来,郡主一直不曾看我顺眼。
想当初在洛都,若非是我穿针引线,郡主可能顺利见到子绯?可能为谢澈一诉苦衷?就算你我不曾有过深交,却也不该是今日这般疏远吧。
” 夭绍微微一笑:“公子说得对。
若非明嘉记着你的恩惠,若非你曾是阿彦的朋友、尚的兄弟,若非你曾帮过他们许多忙,我也不会前来见你。
你若有事但说无妨,只要我能做到的,定不推辞。
” “曾?”苻子徵自然听出她的言外之意,目光转深,也不辩驳,笑道,“郡主行事既如此爽利,苻某也不必惺惺作态了。
此番前来,是请郡主为在下引见谢太傅。
” 夭绍摇了摇头:“不行。
”二字决绝,倏然转身。
“且慢!”苻子徵拦在夭绍面前,俯首之际,笑容明润温和,“郡主何故决然回头?难道此事是你做不到的?” 夭绍笑道:“公子聪慧之人,难道竟不明白我的立场?尚和阿彦都是鲜卑之后,如今中原争战如火如荼,若你是为北朝求援而要见我阿公,势必伤及鲜卑利益。
让阿彦为难、让尚受困的事,我怎会去做?” “郡主言词倒是磊落。
”苻子徵看了夭绍良久,才一字字道,“谢太傅和郡主看来都是习惯拒人千里的人,如此说来,你们对谢澈的安危是彻底置之不顾了?” 听他话语不无威胁,夭绍不禁眉心一颤,袖间双手也是一凉。
心思飞转,随即又镇定下来,她从容微笑:“大哥是奉阿公之命北上的,我信阿公疼惜子女的心,必不会让大哥步入危局。
我也信我大哥的能耐,他会无恙回东朝的。
”她看了苻子徵一眼,目光极为深刻,慢慢道,“我还相信苻公子爱妹情深,我大哥若遭不幸,子绯姐姐断难苟活。
为了子绯姐姐,苻公子也会竭力保全我大哥性命的,是不是?” 苻子徵无言可答,视线落在夭绍面庞上,一时倍觉无奈,过了一会才笑道:“也罢,那我退一步。
” 他自袖中取出一卷帛书,递向夭绍:“我已多次登门拜访谢太傅,皆被拒之门外。
太傅是百忙之人,无空见我,我也能理解。
只是此信重要非常,必需太傅一览,若是旁人我也信不得,只能劳烦郡主将此信亲手交给太傅大人。
” 信?夭绍低头去看。
密封在帛书之外的字迹遒劲潇洒,熟悉非常。
夭绍面色一变,忙接过来,确定是那人所书之后,再抬头看着苻子徵时,不由有些茫然:“你……” 苻子徵笑道:“此信也是他人托我的,我素来重信,不得不为。
今日这件重任便转交郡主了。
”不等夭绍再语,他颔首谢过,施施然转身。
纵然眼前这人举止之间依旧是优雅随和的风度,但夭绍看着他的背影,却觉模糊且神秘。
此人的真面目自己只怕从未相识——直到蓟临之缓缓地将车驾退出深巷外,夭绍仍立在原地,怔然有思。
(三)
果如沈少孤所料,荆州战报正午送达洛都。八百里加急捷报在猛如泼雨的马蹄声中传入前朝,火红色的翎羽飞扬一路,骄阳之下如流动的火焰瞬间烧灼全城。
而后,朝鼓敲动,“大捷”之声更如同雷鸣,彻底惊醒了城池的每个角落。
洛都的巷陌长街被潮涌欢呼的百姓拥挤成患,一时间山呼地动,响彻九霄。
萧祯自然是喜不自胜,由此却苦了一众大臣。
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本该悠哉歇于自家内庭慵懒浅寐,此时却要披上厚重的深衣官袍,入宫称贺议事。
其中最叫苦不迭的莫属沈伊,在丞相府临水幽静的后庐中不过才刚入眠,便满城喧闹的欢笑吵得难以入睡,而后宫中内侍奉旨传命,祁连难抵圣意,冒死将沈伊从榻上拽下地,让他迷迷糊糊地裹了官衣,交由内侍送入宫中。
沈伊到达尚书省时,官署里外虽则官员林立、折书如山,但在沈峥和赵谐的主持下倒也不显忙乱。
沈伊懒洋洋倚着门框听了半晌,大胜之下要做的事虽则繁杂,但好在人手足够,他就此心安理得地寻了一个旮旯继续瞌睡,不料才刚阖眼,就被眼明手快的赵谐抓个正形,推入一旁静室,用丝帕湿了冰水丢到沈伊的脸上。
沈伊一个激灵,神思清醒了三分,看一眼赵谐清冷的面容,心知他素来不苟言笑,也不嬉皮笑脸惹他讨厌,直接问道:“何事?” 赵谐撩袍在他对面坐下,道:“北府兵护送南蜀三皇子明日到虎林,因从江陵出发,一路水路向东,倒也不曾多生事端。
只是近日庐江太守上报虎林一带忽有许多佩剑携刀的武士出没,形迹十分可疑,怀疑是南蜀救兵。
因自虎林之后便走陆路,为免途中出现万一,朝廷要遣一大臣领兵前往接应。
” “要我去?”想着青天烈日下寸步难行的高温,沈伊暗暗叫苦,“这种事情应该派位将军才是。
广霁营洛将军就很有空。
” 赵谐淡淡看他一眼,话语无温:“洛将军要守卫邺都安稳,东朝建国以来,除非是跟随陛下出行,否则广霁营将士从不离西郊一步。
还有——”他言词微顿,朝静室外看了一眼,缓缓道,“有件事,大概你还不知道。
建安王这次入朝带了明宓郡主同行,听说太后对郡主甚为喜爱,半月前就留郡主在承庆宫,正等沈公子回来引见……” “我去虎林!”沈伊在他未尽的话语下乍起一身冷汗,灵台也清明彻底,大叫起身,“我去虎林!赵大人放心,路上定不会出差错。
我即刻动身!” 赵谐看着他踉跄奔出静室,扶了扶额,唇边难得地露出一丝微笑——这般蓬勃热血、自由任性的意气风发,自己却是许久不曾体会到了。
他怔思片刻,低下头,拿起案上的明黄帛书,再阅了一遍。
这是宣萧少卿与郗彦回朝封赏的圣谕。
如今年轻的一辈已崭露头角,风采之盛不下他们当年,只愿他们能够善始善终、情义永存,不要再像自己这一辈,到头来竟落得生死别离、恨怨难消…… 祈愿如此,然而他又深切地明白:命运之轮推动下的风云变幻,却是从无止境的。
想到今早萧祯提及中原战事时难以掩饰的骄傲和野心,赵谐叹了口气,将圣谕放入锦盒,交由外面等候的官员发往荆州。
胜报传到邺都,众臣正忙碌于前线封赏、荆州各府任命、南蜀质子到京的诸事,内患平定、神清气爽的萧祯袖手于外,闲暇之余不免寻思起心里另一桩隐秘的牵挂。
只是这事暂时还无法摆上朝堂廷议,除了太傅谢昶外,萧祯一时也想不出该和谁一吐他欲大展身手的雄心壮志。
于是谢昶正与中书省诸中丞、舍人商讨荆州新任官员的备选时,却被许远传入文昭殿,叩拜落座,等待良久,终于听萧祯缓慢问道:“苻子徵在邺都遍访群臣的事,太傅想必已有所耳闻?” 谢昶颔首:“是。
” 萧祯本欲让谢昶顺着此话延展议题,但见他甚为吝啬言词,不得已,只得自己续道:“听说他是为司马豫求援而来,白日黑夜都和朕的重臣们勾连一起,还有那班清流名士。
此人长袖善舞,其心其举可谓明目张胆。
先前因荆州战事一直吃紧,朕无法分心他顾,且前方战事还有赖此人的战马,一时也不好深究。
只是如今荆州战事已定,怕不能再任凭他在邺都胡闹下去。
朕今日找太傅,是想问问太傅对此事有何看法?” 谢昶垂首想了一刻,说道:“苻子徵为北帝南下求援应是事实,先前不递国书求见怕也是和陛下顾虑一般,那时朝廷内外皆忙荆州战事,无法他顾。
如今捷报到朝,如此人诚心求援,想来近几日便会求见陛下。
” “如此……”萧祯故作沉吟。
身下龙榻宽敞,无处可依。
谢昶说话又是这样的模棱两可、真心难辨,萧祯忍不住将身子往前探了探,轻声道:“那依太傅之见,若苻子徵上朝求见朕,北援之事该不该做?” 谢昶捋着胡须微微笑了笑:“陛下鲜有这般心急的时候。
想来北援之事背后的利害关系,陛下早已想得通透。
” 萧祯但笑不语,谢昶低声叹了口气,道:“鲜卑反叛,中原战火纷飞,司马皇室纵能逃过此劫,也将是苟延残喘、元气大伤。
而且依老臣所看,北方形势还很莫测。
司马氏军队虽多,将士虽广,却不及鲜卑精锐善战。
而且北朝经历了九年前鲜卑逆案、诸王动乱,以及不久前的姚融之祸,早已外强中空,朝中贵族争斗又素来成风,彼此相轧,打击汉人士族,难得北方民心。
因此,老臣认为,中原大战的胜负,最终还很难预料。
如今苻子徵南下求援,我们无论出兵与否,今后五十年内,怒江南北的对峙将不再如十四年前、九年前那般平分秋色。
当然,这只是司马氏得胜之后会有的局面。
” 萧祯道:“若鲜卑夺得中原之鼎呢?” “那情况就复杂了。
”谢昶言词顿了顿,目光看着玉石地面,微有恍惚,“鲜卑之主独孤尚虽则年少,却是世间难得的英雄人杰。
且自古至今,鲜卑一族历经磨难,无尽血泪之下,自成就了誓死不屈的士气。
如今鲜卑一族众志成城,满族上下都是骁勇善战的硬汉。
前些时候,鲜卑横扫拢右战场的气势比之百年前乌桓胡骑南下之时更胜三分,那样惊若雷霆的煞气,着实让人心骇。
难怪——” 他忽然止住不说。
萧祯追问道:“难怪什么?” 谢昶淡淡一笑,喟叹道:“难怪北朝建国以来,司马皇室虽任用鲜卑贵族,却从不曾放松一丝警惕。
非如此顾忌,也没有九年前的巨祸了。
” “原来如此。
”萧祯却是第一次听说司马氏暗藏的用心,同为帝王心性的他不禁琢磨起其间驭人的取舍和难以为人知的考量,想了片刻,才道,“太傅说了这么多,还不曾告诉朕,北援之事到底做不做得?” 谢昶微笑道:“虽然是说出于道义而行,却也是开疆拓土的难得机会,陛下可以把握。
只不过有件事陛下心中要有底线,我朝的军队也刚自荆州烽火中解脱,如今这个时候,将士亟须休养生息,纵是北上,也不能大举出兵……”他似忽然想起什么,明显地沉默了一下,才又续道,“而且挥师北上需渡怒江,按眼前局势来说,与北朝接壤的荆州、豫州、徐州中,荆州乱刚平,豫州水师不及徐州。
若出兵,还是北府兵为先,只是目前北府兵的统帅郗彦——” 萧祯了然接过他的话:“郗彦是独孤尚的表兄弟,血缘情深,不可不顾虑。
” 谢昶不慌不忙道:“除此之外,陛下还需考虑,我们北援能有多大作用,若司马氏政权一旦倾覆,我们便结了鲜卑这个大仇。
虽则中原战定后鲜卑必然忙着恢复元气,我们短期无忧,长远却难预测。
且如今北朝与鲜卑一南一北对阵中原,我们若援北朝,军队如何北上?想必不过是边角一番厮磨,难成大事。
若是与鲜卑联手,倒可以里应外合,攻城夺地,以图霸业……” 萧祯听到最后,微微一惊,忙打断他道:“太傅的意思竟是援助鲜卑?” 谢昶看清萧祯竭力掩饰下的惊慌,虽则是早预料到的,内心却还是忍不住有些失望,叹了口气道:“老臣的意思,北援是可以的,但眼前形势,我们既不宜劳师动众,也不能不考虑长远将来,需以最小的牺牲博得最大的利益,除此之外,也要适当顾忌荆州之战首功之臣郗将军的心情。
因此老臣认为,援鲜卑好过援北朝。
当然,等苻子徵递上国书,此事还要陛下做最后定夺。
” 萧祯犹豫起来,沉思良久,皱眉道:“即便我们愿助鲜卑,却也是一厢情愿,鲜卑人并没有邀我们联手的意图。
” “此事难说……”谢昶眼帘低垂,一笑道,“陛下放心,等郗将军回到邺都,此事自然会摆上朝堂的。
” 萧祯却不再言语了,谈话延伸至此,绝非他事先所料。
先前自己的筹谋还是太过天真和简单了——他忽觉挫败,然羞恼之外却又是另一种心动,因而就放任自己陷入漫长的沉默中,慢慢沉淀萦绕心头的诸种思绪。
(四)
自东朝开国以来,承庆宫素为历任太后居所。因殿阁筑在宫阙最北,正紧依盛载桂树的僖山,这里便终年沉浸在桂叶遍满山岩的浓郁翠色中。
虽则冬日难免肃冷了些,但每逢夏季,承庆宫内外便可得一番喜人的幽凉。
永贞元年始,沈太后住入承庆宫,因她一向畏热,萧祯命人在宫殿之后挖掘活渠引入曲水深流,清波环绕间的殿阁由此愈发清静渗凉,难比皇城它处。
六月十七日清晨,一早入宫求见沈太后的夭绍跪在承庆宫正殿已过两个时辰,重重帷帐下的殿阁深暗如同冰潭,墨青色的玉石地面更是凉意森森,跪得久了,只觉一身繁复宫衣也难抵如此寒气。
夭绍悄悄揉了揉膝盖,想起昨日入城时沈伊的戏言,忍不住暗想:碧枫池再是世人称道的避暑胜地,又怎比此刻承庆宫的冷意入骨? 正觉煎熬时,忽见帷帐中袅袅而出一缕窈窕彩衣。
那少女姿容明丽,行止端庄,走到夭绍身前将她扶起:“阿姐,太后刚醒,让你入寝殿说话。
” “明宓?”夭绍嫣然微笑,“你何时来的邺都?” “半月前,陪父王来都城看望太后。
”明宓见她久跪之后脚下虚浮,便紧紧挽住她的胳膊,让她半个身子都靠着自己,悄声道,“阿姐,我们两年未见了,你还是那样爱惹太后生气。
好像我每次进宫见你,你都跪在这边。
” 夭绍愣了愣,回忆良久,才不确定地道:“我原来总是这样不懂事吗?” 明宓一笑,不再说什么,两人相携而行,走入寝殿。
寝殿的光线比外殿更为幽暗,帷帐悬罩四壁,烛台明燃。
满殿都弥漫着汤药的味道,清苦得窒人呼吸。
沈太后虽已睡醒,却没有下榻,慵然靠着软褥,于榻前垂落的红色珠帘后望着入殿的那抹紫裙,沉默一刻,才低声叹道:“丫头,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 自入殿的刹那起,夭绍眼前就已雾气蒙蒙,此刻那温柔疲惫的声音一旦入耳,泪水夺目而出,竟是止也止不住。
明宓松开双手,夭绍跌跌撞撞地奔向榻前,拨开珠帘,看着榻上双鬓银白、面庞清瘦的沈太后,忍不住折膝再度跪地,泣道:“是夭绍不孝。
” “你原来还知道不孝?”沈太后目中亦起泪意,冷冷笑道,“哀家也想不到,你倒是真狠得下心,不过为了一个男人……” 夭绍双肩瑟然一颤,慢慢抬头看着沈太后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当真咬春饼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咸鱼飞升重关暗度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春日颂小红杏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末世对我下手了一把杀猪刀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虫屋金柜角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重生女配之鬼修雅伽莎
- 流氓老师夜独醉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真爱没有尽头科林·胡佛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纨绔心很累七杯酒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持续高热ABO空菊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单恋画格烈冶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网恋同桌归荼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宠夫日常[娱乐圈]阿栖栖
- 秃头之后,我在前男友面前变强了鱼片面包
- 听说我很穷[娱乐圈]苏景闲
- 被影帝碰瓷后[娱乐圈]唤舟
- 媳妇与枪初禾
- 金枷马鹿君
- 我和死敌的粮真香青端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球”嗨夕尧未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财神在身边金家懒洋洋
- 离心ABO林光曦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老大,你情敌杀上门了沐沐不是王子
- 他们今天也没离婚廿乱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独立日学习计划一碗月光
- 竹木狼马巫哲
- 校服绅士曲小蛐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