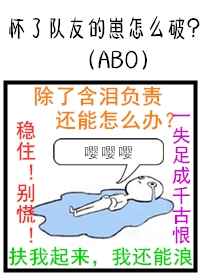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十二章 归计恐迟暮(3/3)
实话,我此生陪伴太后六十余年,从未见过她对谁是这般放任的宠溺和宽宥。
你在外逍遥了这么长的日子,如今要你回邺都陪伴她最后一程,可是强人所难的要求?” 夭绍苦笑道:“自然不是,这本就是我该做的。
” “郡主明白便好。
”敬公公对着她深深躬腰,“方才老奴言有不敬之处,还请郡主勿怪。
”言至此多说无益,他后退三步,转身正要离开时,恰对上沐奇病怏怏的一张面庞。
敬公公皱了皱眉,不发一言越过他,自去前面与侍卫首领说话。
“郡主,”沐奇犹疑了一下,才道,“方才敬公公的话我都听到了,沈太后怕是真的病重了。
郡主如今是要回邺都,还是……”他放低声音道:“去江州?” 夭绍抿唇不言,沐奇斟酌片刻,又道:“可是太傅那边也有信过来,他并不想让郡主回邺都,想来此间事情还有些蹊跷。
” “我知道。
”夭绍轻声道,望着水天之际日落金晖,双目渐黯。
不多时,诸人返身上马,将行前夭绍目光一瞥,正见菱册道上一列冗长的车队,每一辆车皆披薪积重,车轮留痕甚深,往西北慢慢行去。
她勒住缰绳,问身旁的侍卫首领:“可是粮队?” “正是,”那首领道,“今日朝上陛下当众问责了苻大人,令他即刻往陇右派遣粮草,如今看来,想必这些就是了。
” 夭绍疑惑:“从洛都运去的军粮,何时才能到凉州?而且此去中原一路上都是烽火关卡,这样走下来,少说也得一个月吧。
” 首领含含糊糊道:“此事怕是说不准。
” 夭绍看他一眼,未再多说,扬鞭上路。
沐奇紧随她身旁,低声道:“北朝北疆多为胡虏,常年战事不断,冀、雍二州的粮仓应该囤积甚多才是,且中原战场的军队自有潼关永丰仓的储备,断不会挪用冀、雍粮草太多,如今苻景略却为何要舍近取远,从洛都调粮草?” 夭绍听罢一笑:“三叔是不是想提醒我什么?” 沐奇道:“郡主一向机敏,北朝君臣角逐之局想已看明,自是不用我多嘴的。
”话虽如此,他眼角却微微斜挑,偷瞟那张被帷帽轻纱罩得朦胧的面容。
夭绍如何不知他的言下之意,环顾左右围得密不透风的侍卫,无奈叹息:“知晓局势又如何,只可惜你我无辜,如今却注定是人家局中的棋子了。
” 入夜歇在庐池驿站,一宿无事。
次日仍起早赶路,天将黑之前到达曹阳,进城时天际劈过一道闪电,白练森森,穿透阴云密布的天宇,张牙舞爪地直坠红尘。
未过一会,雨珠便飘飘扬扬地洒下来。
起初的雨下得并不大,夭绍走入驿站时,衣衫微湿,无碍大雅,就此用了晚膳,又记起北行送亲时自己也在这间驿站歇过,便选了原先住的阁楼。
自里阁沐浴出来时,夭绍听闻窗外雨声如泼,推开窗扇,方见廊檐处水帘密密,雨势甚大。
她想到去年来此时,大雪初降,虽满庭花木凋零,然月色下雪景如画,连心情也是一般剔透纯净的。
而今庭间树木繁盛,纱灯飘摇的夜色下,雨雾笼罩绿荫,模模糊糊,看不清远方一点山色,也正如此刻她的心境,思绪茫然迷乱,想着江左的诸事诸人,又想起如今的困局,不辨是思念多一些,还是伤愁多一些。
这也才知道,南北轮回一趟,变了的不止是冬夏交替、树木枯盛,人心无常,世事变迁,却是过犹不及。
她躺在窗旁榻上沉思,想要阖眼休憩,心中却始终不宁,又起身坐去书案后,端详那朵藏于晶石里娇色鲜妍的雪魂花,一时默然出神。
“在想什么?”不知何时,窗外忽有人道。
池馆寂静,他的声音低沉轻缓,穿透雨声随风送至,如幽魅飘忽而来。
夭绍一惊起身,望着窗外廊下的那人。
白袍临风,黑玉簪发,袖袂上金色苍鹰烈烈展翅,夜色中有着刺眼的璀璨。
他淡淡一笑,慢步走至窗旁,室间烛光照上他的眉目,容色华美,神情温和。
夭绍结舌:“你……你,又是这样……”神出鬼没,来去无声,恰如魂魄一般。
商之自知她的腹诽,看着她,微笑不语。
她心有余悸,又看看他浑身上下,衣裳干净,一丝不湿,更是惊讶:“难道你一直在驿站中?” “嗯,”商之眸光飘过她湿漉漉的长发上,面色忽有异样,“我来接你去明泉山庄。
” 夭绍这才想起那日在王府说的话,略起尴尬:“你当真来了?我只以为是……” “以为是戏言?”商之轻轻扬唇,“我此生从不说戏言。
” 夭绍心思却不在此处,想起前日看见的那支粮队,盯着他片刻,慢慢道:“山庄何时都能去,可如今北朝这般局势,你并不适宜离开洛都。
” “何时才是适宜?”商之看向室中,视线在雪魂花上停留一刻,又落在夭绍面庞上,“之前或有顾虑牵挂,至于今后……”他低声笑了笑:“也罢了。
” 夭绍体会着他的言下之意,良久,才勉强弯了弯唇,也不再多问,自案上收起雪魂花,又拿了南海檀木、血苍玉等诸物,抱了满怀,走到窗前。
“可以走了。
” “给我吧。
”商之将包裹取过。
夭绍飘身掠出窗外,将要行时,脚步又止:“我还要去告知一下三叔。
” “不必,”商之道,“三叔已在馆外等候。
” 夭绍闻言侧首,注视他一瞬,移开目光:“好,那你带路吧。
” 不知商之用了什么法子,一路沿着长廊走去驿站偏门,途中竟不曾遇到一个禁军侍卫,便连一直放心不下夭绍行踪的敬公公也不见如昨夜时时徘徊左右的影子。
廊下两人静静而行,毫无一分惊险地走出驿站。
外间等候着十几骑士,人与马俱悄无声息。
夭绍环顾一周,见一众披着玄色斗篷的武士之间独一人身穿灰色布袍,蓑衣斗笠,对着自己颔首微笑,正是沐奇。
商之撑开一柄油伞,罩住夭绍的身子,携着她往不远处梧桐树下的马车走去。
驾车的人是离歌,扬起脸笑望着夭绍,风灯微弱的光线下,那张沾雨的面容十分清秀明亮。
“高兴什么?”夭绍见他笑容不住,不由奇怪。
“郡主可有眼福了,主公他……”离歌话才出嘴,不小心瞥见商之微寒的脸色,又生生将话吞下,喃喃道,“没高兴什么。
”他低下头,专心致志检查手中马鞭,嘴角却仍是忍不住上扬。
“眼福?”夭绍不解地看着商之,却见他神色冷淡,看也不看她,打开车门先探身而入。
夭绍撇唇,扶着车轼上车,关上车门的一瞬,却见驿站偏门处一道暗影闪闪缩缩,朝外张望片刻,忽隐入院墙下不见。
“那人……”夭绍正要追下车去,商之却拉住她,反手将门扇“啪嗒”扣紧。
“无碍,”他淡然一笑,敲指车厢,“回山庄。
” “是。
”离歌在外清脆应声,长鞭一扬,车马迅疾没入风雨夜色。
明泉山庄筑于曹阳一处山顶,雨夜山路湿滑,离歌驾驭之术再好,上山时也不免有些颠簸。
眼见车中烛台摇晃不稳,商之却浏览着手中谍报毫无察觉。
夭绍摇头,伸手扶住烛台,运力令烛火平稳。
商之阅罢数件密函,待要引火燃去,抬起头,方见紧握烛台的细白手指。
他怔了一怔,朝对面看去,一霎又哑然失笑。
只见夭绍半靠在身后软褥上,双目阖闭,已然是昏昏欲睡。
他坐去她身边,轻轻揽住她的上身,本要令她靠着软褥躺平,谁料道路不稳,车行忽震,她身子一滑,柔软的身躯便依偎入他的怀中。
他僵了僵,低头看着她入睡的容颜,目光渐渐柔和,转眸又望着她执住烛台的手,唇角微扬,挥了挥衣袖,将烛火熄灭。
满目黑暗,他在寂静中听闻她轻柔的呼吸,心中亦喜亦哀。
原来只是在这样漆黑的夜色里,他才能如此小心翼翼地感受她片刻的温柔依靠。
他的手探上她的指尖,慢慢揉去滴落在她手背的烛泪。
她在他怀中微微一动,侧首,脸颊贴上他的衣襟。
这一刻便是最后的温存——他比谁都清楚地知道。
(七)
夭绍并未察觉自己就这般睡了过去,待耳旁迷迷糊糊听闻男子对话的声音,又响起骏马低低嘶鸣的动静,恍惚之下,猛地惊醒过来。睁开眼,才发觉自己躺在车厢中,外面灯火晔然,透着纱帘照入车内,满目光明。
她望向对面,商之已不在,茫然坐起,揉了揉脑袋,正觉昏沉时,车外有人低声道:“郡主,已到明泉山庄了。
” 是沐奇的声音。
夭绍推开车门,夜雨仍大,沐奇蓑衣未褪,将伞递给她。
撑伞下车,夭绍放眼一望,脚下黛色沉沉,山岩嶙峋,一侧悬崖深邃万丈,俯望之际云烟蔚然,她这才恍悟过来,自己已在众山之巅。
她抬头望了望,面前古树参天,青石道铺迤其间,正对一座轩昂府邸,透过大开的中门,可见一座座阁楼似悬空而筑,雕甍层叠浮出,池馆变幻无穷,夜雨之下,恰如水间晶殿、云中仙阙。
夭绍有些愕然,疑惑自己仍在梦中,只是那立在府邸前望着自己的白衣男子,却是一如平常的淡静面容。
“你这是做什么?”夭绍走上前,心道终于明白离歌方才所谓“眼福”是说什么,笑了笑道,“难道你要带我夜游山庄?” 本是玩笑之语,不料商之却点头道:“正是。
” 夭绍怔了怔,商之微微一笑,转身先行入府:“你行程也急,在庄中待一夜吧,明日一早便送你南下。
” 夭绍闻言驻足,山顶风大,又兼夜雨,湿寒之气穿透裙裾,冷意之下,她终于全然清醒。
她缓缓收了伞,跟着他走入府中长廊,状似随意道:“这里可是我向往长久的地方,让我多待一日如何?” 商之止住步伐,回首望着她。
满庭灯火虽盎然,然他站于廊柱旁,微微垂首,面庞便笼在一片朦胧的阴影中。
夭绍在他面前扬起脸,正对上那双沉沉如墨的凤目,相视许久,她微笑道:“既煞费苦心让我来了,又何必这么急着赶我走?” 商之目中隐现怒色,盯着她长久,张了张唇,却又紧紧抿住。
夭绍也始终不曾低头,明眸如水,其间情绪一丝没有隐瞒,由期待转为失望,似也不过一刻的事。
他面容一暗,挪开目光,终是什么也未说,便蓦地转身,往廊中深处走去。
“主公……”迎面走来一身披狐裘的男子,刚揖手想说什么,不料眼前白袍一掠而过,已飘入夜雨间,径往内庭。
那男子站在原地愣了一刻,掩袖轻轻咳嗽起来,半晌转过头,看着孤身立在门扉处的夭绍,笑迎上来:“郡主来了?” 夭绍恍过神,望着来人,讶然:“贺兰将军?你何时来了雍州?” “也是昨日刚到。
”贺兰柬面容仍是病弱,狐裘披身,似还不能抵住寒冷,拉了拉衣襟,稍稍避开当风处,揖手道,“郡主,主公怕是另有要事处理,我领你游一游山庄吧?”说着,一瞥夭绍不豫的神色,叹道,“因郡主要来山庄,满庄上下费了一夜一日的功夫布置如斯,人间仙境,也不过如此吧?郡主若不走走看看,主公这片苦心,可就白费了。
” 夭绍咬了咬唇,看了一眼商之离去的方向,轻声道:“如此……只能辛苦贺兰将军了。
” “不辛苦,”贺兰柬笑意从容,展臂道,“郡主这边请。
” 贺兰柬话说得轻便,然两人未逛完一半山庄,他便已累得气息不稳、手足发颤。
夭绍自知他的病情,当下也到了曾听沈伊说起奇巧可夺天工的凌空阁,已是心满意足,便道:“今夜先到此处,贺兰将军回去歇息吧。
” “也好,”贺兰柬摸着胸口,在阁中榻上坐下,努力平稳音调,微笑道,“我在此歇一会,郡主……也歇会吧。
” 夭绍见他神情有些异常,看向自己时目光深刻,像是憋着什么话,但又说不出口,于是笑笑,也不急着走,站在一旁抬起手拨弄窗旁悬坠的琉璃灯。
凌空阁筑于万丈高处,底下雨雾缭绕,如履云端。
夭绍望望外面夜色,阵雨稍住,淅淅沥沥水丝绵绵飘动,再无方才滂沱之势。
“雨要停了。
”夭绍说,伸手出窗外,任屋檐上滴落的清凉水珠滚入手心。
贺兰柬于榻上静坐无声,看着灯光下她秀丽的容颜,忽道:“我有几句话要与郡主说,不知郡主能否一听。
” 夭绍将手收回,回首笑看着他:“将军请讲。
” 贺兰柬目光流转于她面庞上,缓缓道:“郡主聪慧,想来是明白了主公深夜携郡主上山的用意。
” 夭绍默然一会,颔首:“是,明白。
” 贺兰柬微笑道:“那么郡主是在怨主公?” “不怨,他自有他的苦衷。
”夭绍别过头去,苦笑着道,“何况……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 不是第一次?贺兰柬想了想,念光闪过脑海,懊悔不已:“郡主难道是说,上次在岐原山,被沈少孤带回柔然之事?” 夭绍侧身对着他,手抚窗棂,沉默不言。
贺兰柬叹了口气:“郡主错怪人了,那次是我瞒着主公截断密信,并以郡主引开沈少孤的。
” 夭绍僵了片刻,扶在窗棂上的手乏力垂落,却依旧侧着身,背影静柔,不知何想。
贺兰柬满面愧色,站起身,在夭绍身后单膝跪了下去:“此事是我对不起郡主,私为鲜卑生存而未顾郡主安危,好在彦公子相救及时,未曾让郡主有何不测,我也因此未成罪人。
”顿了一顿,又道,“上次郡主经过云中时,我便想要对郡主说明此事,只是总找不到机会开口说明,今日才道明缘由,还望郡主莫要迁怒于主公。
” 夭绍默立长久,还是一声不吭。
夜风夹雨袭身,紫裙飞乱,冷亦不觉。
琉璃灯摇晃不住,光影茫然间,似有无数过往在眼前流逝。
她淡淡一笑,终于出声:“事过境迁,我既安然无恙,将军也不必放在心中。
”言罢,转身扶他,“将军起来吧。
” 贺兰柬颤颤起身,看着她隐隐苍白的面色,暗叹无声。
贺兰柬来到内庭书房时,已是子时深夜。
商之正写着一卷书简,见他过来,便道:“坐吧,我正有事和你商量。
” “是,”贺兰柬倦然歪坐在一旁席上,道,“郡主逛了一半说累了,我已让人送她回青蔷园休息。
” “嗯。
”商之低低应了声,烛光下那张面容平静淡漠,如冰冷的玉石般,不现一分喜怒。
贺兰柬又微笑道:“郡主说明日一早便会离开南下。
” 商之依旧声色不动:“那样便好。
” “我刚刚和她说明了岐原山一事。
”贺兰柬盛起一盏茶汤,吹着热气,状似漫不经心道。
商之面色一变,于书简上落墨的笔顿时僵住。
贺兰柬故作不察,低下头慢慢饮茶,不慌不忙道:“郡主一直都在误会主公,主公为何不解释?” 商之失神不过瞬间,下一刻面色如常,冷冷道:“解释了何用?贺兰族老今夜是闲得无聊?” “无聊?”贺兰柬含笑道,“此事干系主公终身,怎是闲事?” “贺兰柬!”商之至此耐性全无,手指冰冷,竭力按住怒意,将案边一卷密函递过去,“华伯父刚送到的信,你看看吧。
”而后不再管他,提笔蘸了墨汁,继续行书书简上,待满满一卷写罢,才停下笔来,将书简放至一旁。
贺兰柬早看完了密函,知他心中纷乱,便一直没有再出声,此刻等他望过来,方一笑开口道:“南柔然已将粮草、战马、兵器等如数运至陇右,以拓拔轩的脾性,想来金城这两日便要攻下了。
”言罢掩卷,长长叹道,“人人都说我是草原神策,但和华公子相比,却是望尘莫及。
仅长孙静一个小小的姑娘,便原来是这样举足轻重的筹码,先令柔然局势大变,鲜卑东邻顿去隐患,而今又因她使得长孙伦超顾虑万千,如此南柔然才成了我鲜卑的重要后援。
” 商之脸色稍霁,淡然一笑:“柬叔与华伯父各有所长,不必过谦。
” 贺兰柬在案上摊开一卷图志,望着西北沉思道:“我们之前估算的日子想来不差,最迟明晨,北帝必然得知拓拔轩继续攻打姚融消息。
”他看着商之,唇边笑意深深,“若是再得知金城被夺的战报,届时北帝心中的惶恐和忌惮,怕就升腾到不可不发的一刻了。
” 商之抿唇不言,烛火映照的侧颜竟不复往日冷毅,晕黄的光泽下,眸光暗晦难言。
贺兰柬皱眉:“难不成主公心中仍有顾虑?”他忍不住冷笑:“你可知今夜带了郡主离开驿站后,曹阳府兵便已倾巢而出,如今潜伏山下的人数不下万众,如此难道还不知北帝待你何心?” 商之摇头道:“他毕竟曾是我的兄长,但想终有一日要玉石俱焚,谁能安乐?” “玉石俱焚?”贺兰柬不以为然,“怕是未必。
”他指着地图道:“如今西北姚融已无应对之力,凉州迟早归为鲜卑所有,东面幽州为慕容虔公子常年经营,早已是我鲜卑附属,只幽、凉二州之间所夹并州为苻氏辖地,虽将士劲悍、戎马烈烈,但府兵如今多数调去河东战场,有谢澈公子居中策应,并州府兵与延奕殊死一战后,不足为虑。
北方三州如囊中之物,并不难取,除此之外,仅余北陵营与雍、青、兖三州府兵。
青州文风儒雅,多名士之辈,将士孱弱;兖州南临怒江,水师神勇,却可惜不擅弓马便利。
由此可见,一旦鲜卑与朝廷势如水火不得不反时,我们所面对的,只有北陵营和雍州府兵。
” 商之见他论起局势时神采焕发,再无素日的病容,无奈道:“看柬叔如此了然于胸,倒似是筹谋很久了?” “自然,此番话我早就憋在心中了。
”贺兰柬肃然望着商之,“百年来鲜卑被乌桓如何压迫,主公心知肚明,时至九年前,我们退无可退本就该反了,可惜先主公一念之仁,只平白落下一个叛逆的罪名,独孤满门含冤而死,逃难中鲜卑一族因此丧命者不下十万,我如何能不心寒?”他话语微微颤抖,闭上眼眸,叹道,“当年惨事素来是我的心病,若非我未曾及时劝说先主公,也不至于后来连番灾难……” 商之低声道:“并不能怪你。
” “而今我时日无多了。
”贺兰柬唇边露出一丝笑容,“若能在有生之年看着主公横扫中原,鲜卑一族彻底摆脱乌桓奴役,我便是死而无憾了。
” 商之默然,贺兰柬看了他一会,忽又低低叹口气:“可主公至今仍对北帝留存希望,在山庄等待的这几日,危险重重,不如尽早……” “不,”商之打断他,眸间无波无澜,“便在这一刻,他还是君,我还是臣,我只有等到——不得不反时。
” 贺兰柬一怔,点头道:“是属下操之过切了。
” 当下一室沉寂,二人都不再言语,商之将一侧墨迹已干的书简卷起,站起身,走至窗旁,望着渐渐明朗的夜空,眼前却慢慢迷蒙,仿佛前方正有什么光亮在悄然而逝,一缕一缕轻烟弥漫,渐成笼罩无尽的阴霾。
(八)
次日清晨,日色未出,夭绍便起身下了榻。出了阁楼,望见院外长廊下贺兰柬与沐奇正站在一处,边轻言笑谈边不住看向青蔷院,似是等候已久。
见她出来,两人忙走过来,沐奇瞧见夭绍的面色,皱眉:“郡主昨夜没睡好吗?” “不是,”夭绍侧过身,避开贺兰柬探询的视线,淡淡道,“昨夜逛山庄累了些,许是没有恢复过来。
” 贺兰柬望着她,含笑不语。
沐奇道:“郡主走吧,尚公子正在山下渡头等候。
” “渡头?”夭绍环望四面山色,有些怀疑。
贺兰柬微笑道:“郡主请随我来。
” 他当先而走,仍引着夭绍去昨晚的凌空阁,然近阁不入,只沿着其后山崖拾阶而下,走入一条深谷。
谷道幽邃,暗无光影,贺兰柬手提灯笼走于前方,不时提醒夭绍和沐奇小心脚下湿滑。
夭绍皱眉看着他颤颤巍巍的身影,心中却担忧他脚下不稳,忙让沐奇去一侧搀扶。
如此慢吞吞地走了近一炷香的时间,三人才走出谷道。
彼时天色仍暗,迎面山林森森,许是昨夜一场大雨的缘故,枝叶上水珠坠落不断。
贺兰柬提步走上林间的白石小道,夭绍和沐奇跟随其后,不多时,便满身湿凉,寒意入体。
阴风自林间缕缕飘出,诸人都是不自禁地打了几个冷战。
贺兰柬在白石道尽头止步,指了指前方:“郡主,昨夜未曾有时间带你来此处,这便是明泉。
” 夭绍望着山林外一片冷凝凝碧波荡漾的湖泊,忍不住近前几步,细细观赏。
这才知明泉山庄名不虚传。
所谓明泉,泉水清澈,如镜之明,映照环岸树荫,青透如纯玉,其上暖烟淡淡,飘袅直入云间。
除此以外,更令她诧异的是,泉水一侧山岩上趴伏着一只雪豹,毛色亮滑如阳光下的积雪,正闭眸而眠,姿态舒展且优雅。
沐奇也在惊奇,出声道:“那只豹……” “那是庄中世代守护明泉的灵豹,脾气暴躁,只认独孤一族的主公主母,旁人谁若近明泉半步,必会受它攻袭。
”贺兰柬解释道,因林中寒气牵动内息,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那雪豹听闻动静懒懒睁开眼眸,锐利的目光掠过贺兰柬与沐奇的面庞上,又看向靠近明泉的夭绍。
夭绍心怵于方才贺兰柬的说辞,忙退离明泉几步,可那雪豹仍凝望着她,目色流转不定,一瞬戾色充盈,一瞬又精光大盛,最终却是无动于衷地挪开视线,晃动尾巴,阖起双眸,再度趴伏而眠。
“看来它今日心情不错。
”贺兰柬深看了一眼夭绍,淡笑转身,往西行去,“郡主,我们走这边。
出了这山之后,便是渡头。
” 东方朝霞已渐渐溢出,但山中不同山外,峰岩遮挡下,光线依旧昏暗。
贺兰柬领着夭绍二人径往西行,山道愈行愈窄,至最狭隘处,不能并肩行人。
如此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前方终见一丝明亮光束射在青岩上,贺兰柬扶壁喘口气,回头笑了笑:“到了。
” 灭了灯笼当先走出,夭绍和沐奇随后离开山道,顿觉眼前豁然开朗。
晴空丽日,远处湖泊浩荡,近处桃林成荫,岸边一座古亭间,商之坐在石桌旁,正静静望着眼前水光,似有思虑。
“主公,郡主到了。
”石勒于他身边道。
商之回首,望着走向这边的三人,缓缓起身。
贺兰柬与石勒相视一眼,各有盘算。
贺兰柬坐在桃荫下的石上,抬袖擦着额上汗水,对沐奇道:“你先去船上准备准备吧,我是没力气再走了。
”沐奇正待和夭绍说,石勒却走出亭外,一把将他携走,手指前方道:“船在那边。
” 沐奇望望他二人,心中明了,瞥一眼亭中商之,淡淡一笑,自不多言。
夭绍在亭外驻足一刻,想了想,还是走了进去。
商之等她走到面前,方出声道:“我刚收到曹阳城中的消息,敬公公已离开驿站南下,许是这一路上还会继续找你。
” 夭绍点点头:“我会注意的。
” 商之又道:“阿彦他们也都知道你南下,邺都宫中会有沈伊周旋,你自这边过河至官渡后,沿途云阁都会照应,想来阿彦也会派人来接你南下。
” 夭绍怔了一下,依旧点头:“知道了。
” 而后商之不再言语,夭绍望着他,半晌,问道:“就这些吗?” “还有一事。
”商之自袖中取出一卷书简,递至她面前,“这是帮阿彦戒除药散的针灸之法,你回去拿给义桓兄看看,他会教你如何做。
” “好,”夭绍接过,紧攥于手中,仍问道,“还有吗?” 商之有些讶然,看着她,愣了一瞬,笑了笑:“没有了。
我送你上船。
” “不必。
”夭绍神色冷淡,转身道,“尚王爷留步吧。
”将要行时,身后那人却忽地将她拉住,手指刚扣住她的手臂,却又立刻松开。
她驻足而立,既不离去,也不回头,就这样背对着他。
他静默良久,才低声道:“若你为昨夜之事生气,我……”他生平首次这般拙于言词,犹豫了一刻,方道,“十五那夜,你随我弹奏《月出》之时,我便知你已清楚了。
” 夭绍依旧不语,商之轻声叹了口气:“抱歉。
” 她却还是一言不发,亭中一时悄寂只闻风声、水浪声,二人的呼吸也似闷于心头,久久难以舒解。
“尚,”不知多久,她终于轻声开口,“从兰泽山初见到现在,你从未对我有过一刻的坦诚,是不是?”话语落下,等待半晌,身后无声无息。
“罢了,”她忽而一笑,“此次一别,也不知再见何日,追究往事也无意义。
” 紫裙飘动,她提步欲走出古亭。
他却又唤住她:“夭绍。
” 她止住步伐。
商之慢慢道:“月出琴,当年谢叔叔之所以送给阿彦,用意为何,你问过他了吗?” 她回头看着他,目中有些茫然:“问过,他说只是礼物。
” “那是你父母的定情信物,怎会无故送给别人?”商之注视着她的面庞,目中似含笑意,却又似不存丝毫的温度,缓缓续道,“月出琴……却是有关一个盟约的礼物。
” 夭绍疑惑于他的言词,思忖一刻,神色骤变,颊上忽红忽白,蓦地转身。
恍然之际,往事皆明。
“我走了,你……一切保重。
”她轻声言罢,头也未回,登舟而去。
商之站在亭中,望着轻舟荡离河岸,未过一刻,转身自回山庄。
石勒与贺兰柬却站在岸边,目送轻舟飘过几重山色,怅然叹息。
“还不走?”石勒斜眸看向贺兰柬。
贺兰柬瞪着他,面无血色,脚下发软。
石勒忙将他扶住,戏谑道:“看来你倒是最依依不舍的那个人。
” “我贺兰柬生平第一次做徒劳无功的事!”贺兰柬想起这一夜的奔波劳累,咬牙切齿,“你们这些人,遇到事总是要靠我这个病弱之人……我还剩一把骨头,南南北北这样颠簸,还能活几天!” 石勒不以为然:“祸本就是你闯下的,能怪谁?再说这次是华公子遣你南下的,可别迁怒我。
”言罢轻声笑笑,身子低了低,将他背在身上,走入山中。
(九)
舟至官渡,南下兖州尽走陆路,想来敬公公并未料到夭绍与沐奇会自此方向南下,沿途竟不曾遇到任何阻拦,纵马五日,终至兖州义阳。二十四日清晨,夭绍与沐奇乘客舟渡怒江,南下东朝。
舟行两天两夜,至江州潜城,上岸后换马疾驰,赶在二十七日入夜之前,抵达江夏城外。
骏马徘徊护城河前,星空当头,旷野无声。
时已戌时,城门早闭,夭绍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城墙,不住蹙眉:“三叔,你可曾在信中说明我们达到的日子?” 沐奇叹息:“自是说清楚了,却不知何故一路都不见彦公子的人来接。
” 此人必然是故意的!夭绍恨得咬牙,自怀中取出一枚澄明的水苍玉佩,丢给沐奇:“叫守城将军,本郡主要入城!” “是!”沐奇极少见她这般着恼的模样,不由轻笑摇头,驱马上前,待要放声喝喊,不料城门闷声轰响,“喀喇”不断的铁锁声裂震夜空,“哐当”一声重鸣,吊桥放落。
“想是彦公子派的人来了。
”沐奇微笑,将玉佩递回夭绍。
夭绍轻轻一哼,面容稍暖,紧了紧缰绳,便要纵马踏上吊桥。
谁知城中却忽地奔出三匹骏骑,风驰电掣般冲过来,夭绍忙策马避让一侧,看着当先那人扬鞭纵马嚣张跋扈的气焰,抿唇一笑,摇了摇头。
“七郎!”着紫色盔甲威风凛凛的少年将军掠过身旁时,她慢慢启唇道。
声入耳中有如雷击,少年猛地勒住缰绳,惊喜回望:“阿姐?”看着吊桥旁一身男装的夭绍,谢粲忙跃下马奔过去,至夭绍坐骑前又蹦又跳:“阿姐!阿姐!你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我真要去北朝找你了!你下来下来,让我看清楚你!”说着连连拽她。
“疯言疯语,军中历练这么久,原来还没长大!”嘴上嗔责,夭绍却依言下马,看着面前的谢粲,微微一笑,柔声道,“你长高了许多。
” “你瘦了许多。
”谢粲终于看清她疲倦的面容,喉间微哑,忙道,“阿姐,入城歇息吧,少卿大哥已嘱咐人在郡守官署为你收拾了房间。
” 夭绍却突然沉默起来,转身牵过马,轻声问道:“军营离这里很远吗?” “并不是很远……”谢粲自以为摸透她的心意,展颜道,“是要去少卿大哥的营帐?江州军营便在江夏城西南三十里处,半个时辰便可到达。
” 夭绍摇头:“不,我是说……你的军营。
” “去我那?”谢粲怔了怔,旋即还是高兴,“好啊,不过北府军营离此地尚远,还须再赶五十里路。
” “嗯……那也不算远。
”夭绍低声道,掠上马背,嘴角微微上扬。
一行人再度上路,夭绍这才有心思望了一眼跟随谢粲来的二人,却是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庞,想是谢粲军中下属,于是也未在意。
入城穿过江夏街道,自西城门而出,沿途过江州军营,只见军中将士仍在操练,篝火连营,气势颇盛。
一路驰骋,江风自远处吹来,入夜竟也不觉凉意,微暖微醺,正是江左初夏的温柔感触。
耳畔谢粲对她不停说着军中诸事,眉飞色舞,若非坐在马背上,只怕是要手舞足蹈起来。
夭绍却另有牵挂,对他的话也是心不在焉地敷衍着。
谢粲见她常怔忡出神,显是兴致寥寥,便怏怏住了口。
夭绍半晌才察觉出耳边清静,回过头道:“怎么不说了?” 谢粲没好气:“你又没在认真听,剩我一个人聒噪多无趣。
” 原来你也知道自己聒噪?夭绍忍住笑,望了望他道:“对不住,阿姐今日是累了些,待日后有空,必用心听你说从军之后的诸事。
” “怕不是累,”谢粲瞄一眼她,“怕是心事重重。
” 夭绍愣了愣,失笑:“多日不见,你眼光倒是厉害了些。
” “我厉害的何止此处?”谢粲洋洋得意,问道,“阿姐有什么心事?说来我听听。
” 夭绍想了想,直言问道:“你出来接我,是阿彦让你来的吗?” “他!”谢粲重哼,“他只想让少卿大哥尽快送你回邺都而已,是少卿大哥通知我,让我来接你的。
” “如此。
”夭绍笑容隐去,面庞慢慢清冷下来。
“阿姐别生气,”谢粲劝道,“那人天生就是这样一副冰山的模样,从不多言笑语,好像多笑一笑、说一说话便会死人般……” 夭绍现在一听“死”字便觉刺耳异常,怒道:“胡说什么!” 谢粲转头看她,见她目色严厉、脸也气得通红,困惑的同时也是着恼:“阿姐竟还这样向着他?他既未死,九年间却从不来邺都找你,只让你一直愧疚自伤。
这么些年,你日日夜夜为他伤心难过,暗中流了多少泪,他在乎过,想过吗?这样狠心绝情的人,为何还要……”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我的师尊遍布修真界/全修真界为我火葬场薄夭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我始乱终弃前任后他们全找上门了倔强海豹
- 起点文男主是我爸林绵绵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仙尊一失忆就变戏精哈哈儿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御佛o滴神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咸鱼替身的白日梦顾青词
- 大风刮来的男朋友烟火人家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夕照斑衣白骨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春生李书锦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情敌五军
- 沉迷撒娇虞子酱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循规是笙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单恋画格烈冶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鱼游入海西言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春生李书锦
- 情敌五军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非典型NTR一盘炒青豆
- 根音(ABO)笼羽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有只海豚想撩我焦糖冬瓜
- 怀孕之后我翻红了[娱乐圈]核桃酸奶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老大,你情敌杀上门了沐沐不是王子
- 治愈过气天王落落小鱼饼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星星为何无动于衷秋绘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夏日长贺新郎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网恋同桌归荼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学长在上流麟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考试时突然戳到了老师的屁股怎么办?化十
- 404信箱它在烧
- 一不小心撩到豪门对家棠叶月
- 竹木狼马巫哲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
- 宠夫日常[娱乐圈]阿栖栖
- 听说我很穷[娱乐圈]苏景闲
- 弃猫效应魏丛良
- 影息何暮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