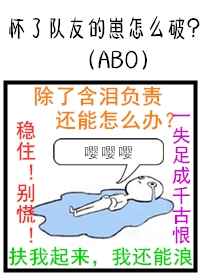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阳城十万家(3/3)
国,毕业遥遥无期,但我想我总得变成个更强大的人才能应付回国之后的所有“他们”。
他们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他们让我相亲,他们让我结婚,让我生个孩子,住在一个巨大的蜂巢里,和所有人争抢着被压缩得可怜的生存空间,一辈子就在他们嘈杂的声音里过去了,如果我没那么强大的话。
“可能你到我这个岁数,你也会犹豫了,总得有个选择。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我毕竟是个女人,家庭,未来,你总得做个二选一,这件事儿从我到美国那一天开始,过了这么多年,几乎被我忘了。
忽然我觉得害怕起来了,在这个浩荡的,朗净的星空之下,我忽然害怕起来了,因为我又想起了自己是个女人。
像是那把枪走了火,砰的一声在我心脏里炸开,炸得灰飞烟灭,弹壳密密麻麻地扎到胸腔里。
苏鹿没有意识到,她还在满不在乎地笑,她像是几年前的我一样。
“你怎么喜欢玩儿枪呢?”顾惊云在我19岁生日的时候把那把枪递给我,他漫不经心地问,“一个女孩儿。
” “非要二选一的话,我就选未来好了。
”苏鹿喝了一口酒,仍然满不在乎地回答,“如果是让我放弃未来的话,那么爱情啊稳定啊什么的还有什么价值呢?”这个回答也是被我猜到的,“可你也不能永远这样,如果你跑得很快的话,那你总有一天要停下来。
”我无趣地回答,觉得自己听上去很像简意澄。
“我不会停下来的。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8岁的时候我这么说,12岁,现在18岁,等到我再老一点我还是这么说。
等到那个时候你再问我——”她像急切地要和什么划清界限似的,“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变成那种妥协的人的,我跟你打赌,我发誓,我赌10万块钱——” 我笑了,我知道她为什么剪了短发,她刚刚磨练出自己的棱角,像块刚打好的石雕一样,意气风发,每天带着简意澄去找学校的工作人员,给他当翻译,简直是将军和他的小姨太太,她尽力地让自己显得像个男人,不化妆,不打扮,在酒桌上说着男人的话,学他们穿衣服,开玩笑,学他们杀伐决断。
她和顾惊云像个真正的兄弟一样嘻嘻哈哈让他摸不到头脑。
她学习,视死如归头破血流地学习,画画,只谈未来,不谈爱情。
可是苏鹿你知道不知道,归根结底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他们坐在谈判桌前,站在千军万马前面,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你还没到选择的时候。
你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一样,一路畅通无阻有时候甚至蛮不讲理,是因为他们喜欢看你这样。
他们喜欢看着一个小姑娘娇横,英气,不自量力胡搅蛮缠,张牙舞爪地抗争,一身男装和他们称兄道弟,这让他们更加觉得这个世界是他们的。
他们看着你就像看一个小玩具,像看着一个扮成老生的女伶人。
总有这样的审美情趣,鱼玄机,扈三娘,季莫申科,我,你,都是一样,她们永远都只是男人的历史里香艳的点缀,再配上一个被世界抛弃的结局让后人津津乐道。
你以为是对酒当歌的兄弟的那些人,他们各怀鬼胎,爱慕你,想要接近你,想要驯服你,或者总有一天会变成这样,无人会对你心悦诚服,无人会委你重任,无人会与你百年好合,无人会同你共谋江山。
他们至多会施舍一点地方,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做成一个夺人耳目的战旗。
你永远都无法拔剑南天起,你的价值就只在于你的美丽,你螳臂当车的一点小聪明小才气,和你是个女人这个身份。
没有人会忘记这个的。
可怜的,可怜的苏鹿。
【梁超和叶思瑶】,2015
夕阳像个上帝还没熄灭的烟头一样,打了几个滚儿掉到山对面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像20世纪40年代美国小说里的主角一样足不出户。
我想当年的顾惊云,一定是和我看到了一样的事情。
西雅图,这座终年阴雨的沿海城市,在黄昏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场。
时间快到了,我对自己说,然后继续打开电脑研究着顾惊云留下来的仅剩的东西。
我的记忆虽然不好,但我从来没有留笔记的习惯。
笔记总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扭曲,就如同我面前这份顾惊云的转发记录。
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显而易见的,有人在利用顾惊云的人人记录装神弄鬼。
我听见开门的声音,然后抬起头。
思瑶拎着我给简意澄准备的病号饭走了进来,满屋子都是石锅拌饭的味道。
这姑娘两耳不闻窗外事,学习了12年,但从来就没人教过她怎么敲门。
“网断了。
”她直直地站在门口,长裙拖地,脸上的妆掉了一块,衬着她尖削的颧骨,好像是北方三月寒冷的春天,又生硬,又冷媚。
“你是要让我带你去修网吗?”我抓了抓头发,烦躁地站起身来。
“我的脚最近不知道怎么,特别疼。
而且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上帝保佑那里今天6点下班。
” “那就快点去啊。
”思瑶的左脚在不耐烦地点着地。
我叹了一口气,拿出口袋里的钥匙。
“算了,一会儿请我吃一顿日本料理就行了。
”我没指望她能请我,到时候大概还是我请她。
不过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和这种人笑着说话了,无论怎么样,你总得学会谅解。
“你还在想简意澄的事儿吗?”夕阳照进陈旧的车窗里,思瑶坐在我旁边,梦呓一样地直视前方。
“都过去多久了,他不会和你也是基友吧。
” “对他没兴趣。
”我打了个哈欠,轻轻踩了一脚油门,路上的夕阳好像尘土,穿过晚风和炊烟,穿过路边的树和几栋小房子,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窗上。
尾气像岁月一样弥漫过来,汽油味混杂着这个城市的鲜血和爱恨情仇。
“不过我最近想知道,顾惊云到底是怎么死的。
警察说的那些都是错的,我一点也不相信。
” “你也这么觉得?”隔了好一会儿,我听见思瑶轻轻地开口。
我没说话,稍微偏过头去看着她。
她的脸倒映在侧视镜里。
“顾惊云是自杀的。
” 顾惊云是自杀的,这种可怕的想法一旦有了,就像墨汁滴到纸上一样不断地扩散开来。
我盯着窗外的大厦,过了不少的岁月而让它残缺不全,电线晃晃悠悠地在风里飘,黄昏剩下的影子遮住了楼下USBank的标牌。
我听着思瑶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讲着他的孤独,他的掩饰,他被双规的老爸和总是歇斯底里的徐庆春,他对这个世界的憎恶和放弃。
这些话像是水银一样流淌在空气里,我打开车窗,晚风吹得我浑身发冷,一个闪电一样的画面掠过脑海。
那是什么日子,我已经忘了。
可能是苏鹿过生日。
她过生日总是那样,带着一大群漂亮浮华的男孩子歌舞升平,她说革命就在戏剧,舞蹈,狂欢和醉酒里。
我坐在她家客厅的角落,一杯一杯地喝着酒。
我那时候和她说话越来越少了,她的朋友们对简意澄太过丧失人性。
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新来的男孩儿和江琴一起把一包拆开的卫生巾朝简意澄的背上扔过去,后来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游戏,打中头加十分,打中鼻子加一百分。
有个叫莫妮卡的姑娘还走过去摸摸简意澄的头,劝他不要生气。
弱肉强食,从小都没有变过。
只是长大了之后这种形式变得更加圆滑和温煦。
苏鹿披着毛茸茸的皮草,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提起笔,将没完成的画作涂上最后一笔。
V形的半张脸隐没在黑暗里,衣服上别着一枝牡丹。
那牡丹花的颜色和整张画面的色调极为不相符,像是蜀中绣娘手指上滴下来的鲜血。
“这是什么?”我看到顾惊云走到她面前问。
“灭蜀。
”她不抬头,把画笔放到一旁晾干。
“公元264年的灭蜀。
” “那时候成都没有牡丹。
”顾惊云关注的重点居然不是那时候没有V字仇杀队的面具。
这些人的理解能力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这是去灭蜀的人。
”苏鹿抬起头,“寿春多赞画,剑阁显鹰扬。
不学陶朱隐,游魂悲故乡。
” “你这是想干大事儿啊。
”顾惊云笑起来。
火锅浓郁的香气在这个时候飘散开。
满屋子都是热热闹闹的气味儿,千秋万载,花好月圆。
“我只是觉得,对某些事,所有人都知道不好。
都在网上骂。
就没人去做点什么。
这些人加起来至少有1000万,但农村老大爷写封投诉信都比他们强。
” 门外的人稀稀落落地站起来。
苏鹿一点一滴地看着顾惊云——我到现在才知道这是两个穷途末路的亡命徒之间相依为命的对视,这种凝望搅着莎士比亚玫瑰上的胭脂红,搅着公元264年举着火把的叛军眼中艳丽的红,搅着卡门裙裾上那点明亮的红,穿过几千年的浓雾席卷过来,我嗅到了风暴来临之前平静的气味。
这种无坚不摧的风暴的力量从他们出生开始,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直到这一刻,流尽最后一滴。
我听见顾惊云说,就算你要当钟会,你也需要一个姜维。
思瑶终于安静了下来,黑夜吞没了最后一点光芒。
路边的灯孤独地亮了很久。
我听见车里的空调浑浊的声响。
那声音极其喧嚣,震耳欲聋,甚至盖过了轮胎在地面上摩擦粗糙的声音。
“现在说到重点了。
”她转过头来,盯着我看。
我握紧方向盘,听到窗外饭店里盘旋的意大利小调,悠扬哀伤。
“你觉得到底是谁找了人,对简意澄做出了那种事情?” 有个名字几乎脱口而出,但是被我顺利地咽了下去,等着她的回答。
她和我一起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轻轻地开口问我。
“你刚才也想说是苏鹿,对吗?” 思瑶说完这话之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好像把多年压在心底的秘密胆战心惊地吐了出来。
她仿佛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儿,把自己裹在长长的厚外套里,像是水仙花被折断的花茎一样不断地颤抖。
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略微点了点头。
她这才松开两只紧握的手,靠回椅背上。
她的眼睛里是整个城市浊热的灯光,手指轻轻地搭在嘴唇边,仿佛一只躺在浅滩垂死的水鸟。
【苏鹿】,2014
警察来找我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写作业。正写到一篇论文里无聊的论述,讲为什么美国人比中国人容易发胖。
图书馆里油墨的气味和纸张的气味让人一阵阵犯困,脚下是毛绒绒的毯子,电脑上蚂蚁爬一样的英文字迹渐渐地看不见了。
我的头不由自主地猛地垂下去,再惊醒。
旁边的美国人戴着耳机,旁若无人地喝咖啡,屏幕上是Facebook的页面。
图书馆红头发的管理员找到我,把我推醒,“警察要问你几个问题。
”她用英语告诉我,那个金发的警察眼睛就像是琉璃块一样,坚硬,透明,照出让人无可遁形的冷光。
欧美人的脸锋利得苛刻,看着总觉得少了点人情味儿。
“你就是苏鹿?”他问我,顺便伸出手来和我握一握。
“你是否介意我们问你几个关于这次暴力袭击的问题?” 我摇了摇头,心里想着食堂关门,今天估计又没东西可吃,以及怎么劝说家里在我没满18的情况下给我买一辆车。
警察严肃地讲着从现在开始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当成呈堂证供,然后拿出一张打印好的A4纸,让我在6个人里辨认出徐庆春的脸。
我确实费了好大一会儿劲,才看出证件照上学生时代的徐庆春。
她剪着短发,眼神坚毅凌厉,像是小学语文书上的那种女烈士。
简直同现在歇斯底里的徐庆春不是一个人。
这么个肃冷倨傲的姑娘,怎么就被生活败落到这种地步呢?我想不出来,只好勉强点了点那张照片。
警察满意地眨眨眼,问我她当时是怎么“袭击”被害人的。
我发现这个案子已经被和爆炸案枪击案一样定义成暴力袭击了,给警察描述了一下当时徐庆春二话不说走过来就扇耳光,连打了两三分钟的情景,心里觉得有点好笑。
我说得越严重,他们就越用力地点头,飞快地在纸上做笔录,像是听个街头的说书人讲了个武侠故事。
讲到了最后他们还意犹未尽地问我有没有。
我只好摊摊手,说真的没有了,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我不觉得她是个恐怖分子。
警察走了之后,困意和饥饿在我身体里此消彼长,一波一波像是海浪一样。
自从我下了决心剪掉头发,谁也不找了之后,我已经被困在这座小村一个多月了。
周末有江琴、林家鸿他们一起出去吃饭聚一聚,平日里大家上课,饭都是有了上顿没下顿。
我睡不着,画不出来画,浓墨和油彩都干枯在调色盘上,每天半夜醒过来从冰箱里拿一听可乐,日子过得极其无聊。
我多少次订外卖,买了一大堆酱汁浓郁又难吃的鸡翅,和江琴他们几个人一起打三国杀,有时候能凑够五个,凑不够五个的时候就打三国争霸互相乱杀,江琴抽着国内带来的烟,中华,小熊猫,抽没了就抽玉溪,用空的可乐罐子当烟灰缸。
有的被烫金的纸细细地卷起来,燃烧的时候好像在烧锦缎丝绸。
林家鸿有时候抱怨,说每天呼吸二手烟让他减寿了十年,江琴就恶作剧地吐个烟圈儿在他脸上,说你去世,我骄傲,我给国家添肥料。
电脑待机,屏幕黑下去了。
我看着自己映出来的一个模糊的影子,头顶长出了不搭调的黑发,没经梳理,咋咋呼呼地乱翘,脸色苍白了,没化妆,眉梢眼角无声无色地垂了下去,这是我吗?我看着这张被阴郁多雨的村庄融化了的脸,好像是盒打翻在污浊雨地里黏糊糊的冰激凌。
外面的雷声轰隆一下从远方滚滚而来,仲夏的西雅图憋了几天,憋得青筋暴涨,脸色灰黄,到底还是没憋住,又哗哗地下起瓢泼大雨。
我完蛋了,我想着,苏鹿,你完蛋了,你折腾了几下,终于把自己折腾成了个老太太。
你谁也不用找了,也再也没人会来找你了,你就一个人安安心心地颐养天年吧。
没过一会儿简意澄就坐到我身边来了,我打了个哈欠,心想果然我还是不能颐养天年。
他被这几天学校office的每日一谈折腾得越来越瘦弱了,“刚才警察找你了吧,”他低着头,玩着手上半长的指甲。
“找了,”我一边修改着作文一边回答道,“你和学校那边谈得怎么样?” “还是那样,像你们交代的那样,让他们同情我嘛。
现在造的声势已经越来越大了,学校说了,她再出现在学校里就立刻报警,现在官网上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报,每个辅导员都知道了这事儿——”他忽然停下来不说了,棉絮一般柔软的黑眼睛里盛满了厌倦。
“你满意了吧?”他轻声地问我。
“什么?”我抬起头,听出了他声音里的悲戚。
图书馆里走过去几个各色头发的香港人,看着他,正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什么。
他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咬咬嘴唇,勇敢地说了下去,“我终于按照你的期望走下去了,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可怜人了,可怜、窝囊、絮絮叨叨一肚子苦水、每天被人歧视的同性恋。
那些学校的辅导员、主任、警察,全都高高在上地看着我,脸上都是一样的表情,同情、怜悯,让我不要害怕不要有心理阴影,每天都有学校同性恋协会还是哪里的人来找我,问我的处境怎么样需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好像我的人生没了别的部分只剩下被徐庆春打这一件事儿,我只有一个名字叫受害者,我只有一种性格就是可怜——我够了,苏鹿,我对扮演这个受害者的角色彻底够了,我也不想再见主任见警察了,徐庆春那事儿就这样吧,我不管了。
” 简意澄从来不这么说话,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他的不高兴。
我惊异地看着他,他柔情似水地叹了口气,把手插到厚实的头发里面,慢慢地又恢复了那种贤妻良母的语调,尾音像是团软软腻腻的棉絮,和谁都像在撒娇。
“行了,苏鹿,你也别多想,我知道你们也是好意。
” 我一边不住地点着鼠标修改着作文,一边觉得自己简直是傻透了,天底下最大的一头傻×。
没错,简意澄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被取了熊胆放在笼子里任人参观的熊,他和我一样。
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儿就是被人觉得自己可怜。
这种被逼迫着把自己的伤口一遍一遍地扒开给人看的举动对他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我刚想帮他想个解决的办法,手机就在我背后的包里振动起来了,顾惊云给我发了短信,在门口等着接我回家。
想起来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我决定不能再和他在一起了,可以是别人,但不能是我。
这不是他的问题,我以后也不会再和任何人在一起了。
这副败落的样子和与他一团乱麻的关系加起来真是让人绝望。
你好,乡村绝望老太。
我看了看简意澄,告诉他我回家了,便关掉电脑往图书馆外走。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对他心存芥蒂,他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喜欢上顾惊云,那不是他的错。
满天的红霞被雨水泡得湿润了,像是长满天际大朵大朵的凤凰花一样,我穿过泥水和高草,坐上顾惊云的车,惴惴不安,闭上眼睛。
“去哪儿?”他问我,语气平静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指了指回家的方向。
“苏爷,这次怎么不出去玩儿啦?”他声音里带着强做出来的调侃,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坐在离我不到十厘米的位置,我不能直接看他,左半身好像瘫痪了似的,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操蛋的事儿,没有之一。
我想起每次和顾惊云出去玩,去西雅图,贝尔维尤,天上都是长满了今天这样的霞光,紫红色的,一团一团,云蒸霞蔚,颜色深一点的就像夕阳的淤血。
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玩的,别的地方除了墨西哥人就只剩下了狼了。
本来是干干净净的一件事儿,被徐庆春和简意澄一搅合,都完蛋了,像我一样完蛋了,脏得不成样子,和街边上的沼泽湿地一样,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塑料袋,薯片,烟盒,动物的尸骸,都一起无休无止地沉下去。
我警告着自己,往前看,不准侧过脸去看他。
潮湿的空气从四面八方渗进来,车里的空气也被蒸得潮湿酸涩,像是一壶积了很久的眼泪。
“你怎么和简意澄那么好啊?”他若无其事地问我。
“也不是那么好,就是觉得他不应该被打,我得帮帮他。
”我转过脸去,揉了揉眼睛,又加上一句,“反正这儿也没人帮他。
” “嘿,学雷锋标兵吗小妞儿。
”顾惊云按下车窗,叼上一根烟,笑一笑,在烟消云散的雾气里眯起眼睛,车过了一个巨大的水坑,那些水和喷泉一样噼噼啪啪地溅起来,扑到左右的窗户上,把大大小小的雨滴一下子洗刷干净。
铺天盖地的雨水,水声滂沱,雨气喧哗,无尘无埃。
“谈不上学雷锋,我也没对到哪儿去。
”我也学着他笑了笑,把车窗打开,这些雨带着腥咸的气味,漫过我的头顶,把我吞没了,“天理昭昭,我也会有报应的。
你看这雨下的,说不定一会儿打雷就劈到我。
” “怎么啦?被徐庆春恶心着啦?”他没看我,悠闲地把方向盘一打,头发有点蓬乱,脸色苍白,这辆车好像正在往一部冗长的法国电影里开一样。
“没,不是被徐庆春恶心着的。
”我叹了口气,把脸迎向窗外的雨。
“你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不恶心。
” 我抹了一把脸,咳嗽了两声,真的觉得有点儿恶心了。
好像是的,别人都活得好好的,就我总觉得恶心。
在这儿未来和人性让我恶心。
爱情,口水,麦当劳,扮优雅的名媛,雨水,卫生巾和掉落的头发,这些都让我恶心,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该活着还得这么活着。
让我变成一只每天居高声自远垂绥饮清露的凤凰鸟,可能我的羽毛还是会让我恶心。
恶心只是生命体的一种生理本能。
我们都需要恶心。
他把手搭过来,放在我的手上,被我轻轻地抽开了。
我对着他勉强地笑了一下,他揉了揉我的头发,手指是冰凉的。
“想太多了你。
” 我不说话,坐了一会儿,从旁边拿出他的打火机,点上火,再熄灭,再点上火,雨气喧哗的车里因为这个动作而有了几分安稳的意味。
“没事儿,我又不是那种大公主。
你吃饭了没?我们去吃牛排好不好?” “Steakhouse?”他笑着问,“又是你吃牛排,我吃菜花儿,吃得我都快变菜花儿了。
” “我有密集恐惧症,一看见菜花儿就害怕。
”想到了密密麻麻长着一颗一颗铁豆的菜花儿,我被恶心地打了个寒噤,他看着我笑了起来,我也笑,不停地笑,好像除了笑就没有别的事儿能做了,笑得脸上的肌肉撑了太久,僵硬了,从眼角流出眼泪来。
到底我们也没去Steakhouse,他知道我是说着玩儿的。
过了好一会儿,车才停到我家门口,整个世界都被大雨打湿了,低矮的楼群像一件不合体的粗布衣裳。
我看着顾惊云,他的眼睛湿漉漉的,湖泊一样安静。
“到了,”我转过脸去看窗外,“就这样吧,”我的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闭上眼睛,紧紧攥住车把手,感觉全身被雨水浇了个透。
“——我们也就这样吧。
” 他什么也没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像两株灌木一样坐在车里,被雨浇得无声无息。
雨不停地泼在前面的车窗上。
时间彻底地停滞不前了,一分,一年,一百年,都是一样的,古时候的金戈铁马在我耳膜里呐喊厮杀,寒光四溅,冲锋陷阵,烟消云散。
“——行吧,就这样吧,”顾惊云好像经过了漫长的跋涉,跋涉了整整一辈子,看起来无比疲惫,终于决定了什么似的拍拍我的肩膀。
“我还是觉着与其每天让你恶心着,不如我自己一人恶心。
恶心多了,吃不下饭,容易得胃病。
” “嗯。
” “回家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别想太多英年早逝了,我还等着看你画的画儿呢,以后我和别人一说,我在美国认识一大画家,多牛×。
” “嗯。
”本来我是该笑他连人话都不会说的,但现在这一个字已经耗费了我全部的力气了。
雨点敲在车顶上,我捏紧了拳头,好像胸椎骨被人打了一拳,喀拉一下粉碎了,每摁一下就觉得有水从胸腔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溢出来,漫过眼睛。
“明儿个我还来找你玩儿啊,带上林家鸿、江琴,咱一起吃牛排去,我吃菜花儿。
” “嗯。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几乎要破涕为笑了,然后抓起放在膝盖上的包,走出车外,回过头去对他摆了摆手。
我走到屋檐下面,面对楼梯,背对道路,听着他发动机发起来的声音,轰隆一声狠狠地从我心上压过去,水花四溅乘风破浪。
我蹲在地上,眼泪忽然一滴一滴地掉出来,不断地从脸上抹下去,又漫出来,流得我直生气,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脸。
寒意从四面八方渗到我的骨髓里。
完蛋了,我想,完蛋了,什么都没了,这下你真的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了,天地间空空荡荡的,就剩下你自己了,你们这两个蠢货,不够果敢也不够懦弱,不够善良也不够狠毒,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想方设法地自虐,自我惩罚,自我牺牲,结果什么都没了,都死了,埋在坟墓里,化成灰。
苏鹿,这种结局就是为你这种人准备的。
我拿起包,站起来,鞋跟撞在楼梯上,空空荡荡地回响,我继续满意地咬牙切齿,往楼梯上踩过去,让声音大一点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再大一点。
房屋的结构是中空的,这声音好像它被人一下下地敲着骨头,敲着胸腔,敲到心脏上。
都过去吧,用刀砍用火烧把神经挑开用钩子把今天从我的脑子里挖出来,不管怎么样让他妈的今天快过去吧。
什么都没有,从来什么都没有过。
该死的眼泪飞快地漫过眼眶,烧得我眼睛火辣辣地疼。
几片乌云迅速聚拢,然后夹杂着雷声的雨点敲在屋顶上。
西雅图沉闷而漫长的仲夏。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我的师尊遍布修真界/全修真界为我火葬场薄夭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当真咬春饼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与婠婠同居的日子李古丁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春日颂小红杏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他的余温阿宁儿
- [综]混沌恶不想算了!安以默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我就是馋你信息素[娱乐圈]夂槿
- 射雕英雄传金庸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乾坤剑神尘山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剑海鹰扬司马翎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星星为何无动于衷秋绘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眼泪酿宴惟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春生李书锦
- 沉迷撒娇虞子酱
- 循规是笙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夕照斑衣白骨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阻流三眠柳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金蝉脱壳风弄、彻夜流香、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我只想好好谈个恋爱!爱吃肉的羊崽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
- 他只是我男朋友廿小萌
- 竹马危机萧二河
- 秃头之后,我在前男友面前变强了鱼片面包
- 被影帝碰瓷后[娱乐圈]唤舟
- 继子难驯蓉城之月
- 这个小贼姓苏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