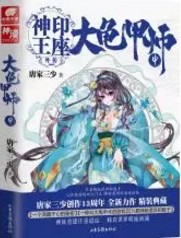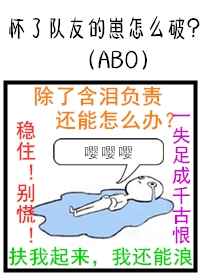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阳城十万家(2/3)
鬼神的局,她们都是些傻×,偏偏还要高兴得像在宫斗片儿里胜利者最后当上九五之尊一样。
你可以抢东西,但是如果你抢来的是人,不是东西,整个事情就会变得很没意思了。
我躺在房间里胡乱想着,开着灯,我知道就算我睡着了,简小姐也会破门而入把我吵醒,而且在我袓国度假的阿玛尼哥隔三分钟就用非主流字体给我发过来的“莪想伱”一类的微信让我很烦躁。
我简直想像《画皮》里的陈坤一样戳瞎自己的钛合金狗眼。
虽然有点儿阻碍国家经济建设,但我真心觉得有的时候农村真的不应该通网。
村长的儿子也不行。
简意澄破门而入的时候我已经昏昏欲睡了,他踮着脚,静悄悄地,和我打了个招呼,回身轻轻地关上门。
声音又软又腻,软得让我心慌。
“嗨,”他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其实我可以睡在地上,没关系的。
”他那娇滴滴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喝多了酒。
“没事儿”我做出一副含含糊糊的样子,像是个睡前的人。
“你上来吧,没事儿。
”我没翻身,回手去拍了拍我身边的半个位置。
他蹑手蹑脚地走过来,身上一股很浓重的宝格丽男香的味道,呛得我晕头晕脑。
他坐在床上就像只小鸟儿一样,我都没感觉到床塌陷下去。
他连呼吸都是软的,让人脑壳儿痛心里发慌的那种软。
房间黑漆漆的,沉默无声。
沉默是两个半生不熟还必须躺在一张床上的人之间那种该死的沉默,外面在下雨,被子,床单,都是潮的,混着雨的那种声音,让人觉得腻得心烦,像是融化了的甜筒冰淇淋上滴下来的奶油,流得整个房间一片肮脏。
“琴姐,”简意澄软软地摇着我的胳膊,他是习惯于打破沉默的那种人,“你睡没睡嘛,你要是没睡的话,就和我聊聊天——”他一边说话,一边玩儿着手中的手机,那手机是苏鹿送给他的,蓝色的棒棒糖,像是一块薄薄的糖霜蛋糕在黑暗里发出蓝莹莹的光。
“快睡吧,明儿还得上课呢。
”我嘟囔着,他仰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徐庆春她在到处找我吧,每天都这样,满学校都知道了,她是为什么啊,她那疯疯癫癫的样子,顾惊云也能喜欢她?琴姐你也不喜欢她吧?我知道,我能看出来——”简意澄转过来看着我的脸,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琴姐,如果你真的是个男的,我说什么也得和你在一起。
” 从黑暗里看过去,手机的亮光简直刺眼了。
他屏幕上是张照片,刚刚拍出来的,是顾惊云的房间,徐庆春的艺术照还挂在那儿,民国的旗袍,嘴里叼着一根烟,表情老练得像个女特务。
我不知道他要把这张图片给谁发过去,但我琢磨着,心里已经有个数儿了。
我的手机放在枕头下面,短信发来的时候会振动,徐庆春刚刚才给我发过来一条“最近看到那小贱人没,看到贱人就告诉我。
”她说的小贱人就躺在我的身边,正在使尽所有奇谋妙计,想着法子把她气成心肌梗死。
我觉得我像个他妈军统联络站的站长,明面儿上就是个酒楼老板,迎来送往八面玲珑,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我是谁的人呢?我问自己,我记得以前我老爹和我说过,当时的大人物都是双面间谍,八方周旋见风使舵。
我他妈谁的人也不是。
外面的雨声让我觉得恶心,每天都在下雨,我在这种潮湿恶心的天气里慢慢地睡过去,徐庆春有一把刀,一把菜刀,她曾经挥舞着菜刀四处追赶顾惊云,她真的劈了下去,头发蓬乱着,像个疯子一样,一脚踩着高跟鞋,眼睛里全是血丝,嚷着我听不清的话。
我做梦梦见了那把刀,沉甸甸,冰凉的,刃上淌着几滴血。
【苏鹿】,2014
我的头发长了,比我从前想象的还要长,打着卷,分了叉。每次我洗澡的时候都要洗好久。
水声和着模糊的灯光,排风扇旋转的时候和我千里之外的家乡没有区别,就像是泡过木芙蓉的新鲜雨水,顺着青石板慢慢地流到每个缝隙中一样。
雪化后的水流进漫长的夏天里,我的脑子里总有这样的场景。
我在哪儿呢?我一边擦着头发,一边抹着蒙上一层雾的镜子。
烫过的头发长出来一截,乱蓬蓬的,不直也不卷。
水滴在瓷砖上啪嗒啪嗒。
我是谁呢?总不该是一个在舞台上没完没了唱着咏叹调的歌剧演员吧! 最近每当我画画的时候,我都莫名其妙地想到这么个舞台,也许是舞厅吧,老式的音乐,红色的帷幔,人人都旋转着,名贵的丝绸和旗袍,光线让人目眩神迷。
我现在身边的那些人,我也说不好应不应该叫他们同学,我在现实里面不会经常想起他们,也不会和别人提起来,可是我做梦的时候总会梦见他们。
从小我就会有这样的梦,像一帧帧色彩失真的胶片。
徐庆春是个军阀家提着枪的小姐,江琴是个地下党联络站的站长,夏北芦喜欢坐在咖啡店里看书,穿着一身浅底儿苏绣的旗袍。
顾惊云端着盘子,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要点儿什么?”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简直让人捧腹大笑了。
而我自己呢,我曾经有那么一次机会看清我自己,衣服是棕红色的皮夹克,洛可可式的,夸张的叠堆起来的卷发,轮廓尖利,眼窝深陷。
我是在一个商场的橱窗上,一个黄铜的镜面上看到我自己的。
我把这个场景画了下来,但是这不是我,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这只不过是一幅画而已。
“半生记。
”我在描画霞光下长长的影子的时候为它取了个名字。
半生记。
我用了很多灰秃秃的色彩,像是凉凉的雨天一样,让人看着胸闷,心里害怕。
我从来没有想要让别人害怕过,我也从来都不怕别人,不怕他们给我各种各样的脸色,但我却开始害怕我自己的画了。
想到这个我就开始笑起来。
随后我的洗手间门被敲打起来了,“干什么?”吹风机的声音太大了,连我自己都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我拨开往下滴着水的乱蓬蓬的头发抬起头来,“干什么!”我吼叫着又重复了一边。
“我去个洗手间。
”是林家鸿的声音,我刚想问你怎么闯进我家来的,他好像也意识到了哪儿不对,解释道,“我们都来了,一会儿咱一起去小肥羊吃饭。
” 我的头发吹得半湿不干,裹着毛巾开了门。
我觉得人想上厕所的时候在外面憋着总不是件好事儿。
棕色的巨大浴巾堆在我头上,我看起来像刚从一个阿拉伯商队里出来。
水滴在脖子上,掺着洗发露,一滴一滴地往四肢百骸里渗进去,刺得浑身发冷。
我看到顾惊云靠在门框上,看见了我,眯起眼睛轻闲地笑笑,好像刚刚脱下绸缎长褂放下手里的鸟笼一样。
“哟,大爷,”我一边用毛巾揉着头发一边和他开着玩笑,“你也在?我还以为你被徐姐绑架了。
” “哪儿啊,”他嚼着口香糖,一口北方话卷着舌头在嘴里打着转,含糊地回答道,“徐姐早就不跟我玩儿了。
”他对着我点点头,后面刚好有个人推开门,是张生面孔,我从前没见过。
“张伊泽,”他马马虎虎地把那个瘦削的男孩子一把搂过来,像是归拢一把大葱,然后拍了拍他的背。
“这是张伊泽,”他对着我和厅里的几个人介绍道,“一起玩儿过的,你们该记得吧。
” 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那个人,我并不擅长记人的面孔。
那是个蜜水里泡大的,看来娇生惯养的男孩儿,眉眼长得很细致,有点儿媚气,像是一条街上沙沙作响的法国梧桐一样。
皮肤和我比起来都太过嫩了一些。
他穿着一双gucci的男靴,随意地在玄关的垫子上蹭了蹭,我看着他,但是不喜欢他,这个戴着爵士帽一身名牌的家伙。
他是很多女孩儿会喜欢的那种,像是卡布奇诺上心形的奶油小泡泡。
他抬起头来,瞪着我看,脸上还带着那种柔软泛着金边儿的笑。
我也瞪着他,但是他的目光很快地就扫过去了,朝着我点了点头,走到我家的客厅里,和刚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林家鸿他们很有礼貌地称兄道弟起来。
我想刚才他瞪着我看的眼神大概是我的一个错觉。
一直到了小肥羊,我还是觉得脖子后面满是水渍,像被长长的针扎了进去一样发冷。
我身旁坐着简意澄,他和那个张伊泽坐在一起。
“昨儿你去哪儿啦?”简意澄住在我们家的客卧,昨天他那双经常穿的红色乔丹运动鞋不在了,我是晚上出去煮一碗方便面的时候看到的。
他平时很少晚上出去,我当时想起一个鞋自己走动的鬼故事,吓得心慌。
“我?”他不知道在给谁发短信,一边玩儿手机,一边笑着,“我哪儿也没去,在家里睡觉。
我从来晚上都不去哪的。
”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谎,要么就是闹鬼了。
我不再说话,把眼前的牛肉羊肉鱼丸虾丸一股脑儿地倒进火锅里,火锅咕嘟咕嘟的,上面漂着一层红彤彤的油,雾气慢慢地升起来,好像里面煮化了热气腾腾的一轮太阳。
“我这学期刚来,”我听见张伊泽转过身去对桌子那边的林家鸿说起来,他们一个是省,一个是直辖市,同在一个地方,说的本来是差不多的方言,在一起却偏偏说起普通话来。
“我妈妈本来是要送我去读私立高中的,实际上他们已经把录取通知书寄来了。
后来我爸爸说读社区大学吧,出来锻炼锻炼,毕业也能快一点,还不用考SAT,SAT特别难考呢,”他优雅地端着筷子,夹了碗里的一个鱼丸,然后转过来对着我这个方向,仍然是那种泛着烫金的金边儿的笑,“你说是不是呢,鹿姐?”他的语气真的就像个天鹅绒包裹着出生的,天真的小孩子一样。
我不说话,用大勺捞着火锅里的油和煮烂了的粉条,热气熏得我一直冒汗,汗把我的妆花了,流下来刺得我眼角发痛。
我看了看对面的江琴,再看看旁边不断地去洗手间补妆的玛丽莲,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变得阴阳怪气儿的。
“噢,你在和我说话吗?”我好像刚刚反应过来似的,哈着嘴里热辣辣的蒸汽,对他笑起来,“我不知道,我没考过SAT,我也不是你姐姐。
” “哎哟,张总挺厉害嘛,”顾惊云从桌子的另一头抬起头来,手里晃晃悠悠地夹着筷子,“私立高中,是哪个啊,伊顿公学?” “伊顿公学是英国的,”张伊泽仍然一脸笑容,说话的语调好像在读诗一样,“另外,顾大哥,不用叫我张总,叫小张就可以了。
我可担不起什么爷什么总的。
” 我们从来不管顾惊云叫顾大哥,一般都是叫顾爷。
说实话,这儿的人都习惯了某爷某总的开玩笑,像是表达熟络的某种方式一样,第一次听到人这种看似谦卑的拒绝,江琴愣了一下,我能看到她的脸上有点别扭,“苏爷,”她半开玩笑地叫着我,“我吃饱了,陪我去一下洗手间吧。
”我站起来,看到林家鸿在闷着头吃饭,他推了推眼镜,脸上有点汗津津的。
那个叫张伊泽的人是梁超带来的,他班上的同学。
梁超也低着头努力地对付着一条长长的油菜,谁也不看谁。
我往外走,餐厅里是暗红色的,光滑的色调,天棚很低,地面映出我们薄薄的影子来。
江琴走在我前面,气氛怪异而沉闷。
她走了几步,往店门口扫了一眼,忽然停下了,好像快要踩到地雷阵似的,一个转身捂住我的嘴,一手拉住我,“别动!”她的眼神忽然变得很急迫,带着点慌张,她用力地扭着我,弯着腰,从吧台前面躬身滑过去,躲到嵌着暗红色瓷砖的洗手间旁边,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怎么回事?”我的声音不伦不类地从她的手指缝里传过来,她皱着眉头,指指门外,脸上严肃而惊恐。
她终于来了。
我看见徐庆春蹬着一双12厘米的高跟鞋,白色的高领毛衣,扬着头走了进来,手里提着路易威登,好像在提一个炸药包一样,杀气四溢,虎虎生风,我看着她,她的腰板挺得直直的,像是用了自己所有的力气才把它挺起来的,有那么一瞬间吧,我觉得她好像马上就要坐在地上尖叫哭号起来了,但过了一秒,那张锋利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满了杀人两个字,密不透风。
暗红色的空气变成了刀子,变成了刀刃上渗出的鲜血,味道生腥而新鲜,每个人都闻得出来。
前台的小姐犹豫地凑过去,“女士,请问你要——” 她面无表情地一甩胳膊,把那可怜又不识时务的小姐狠狠地甩到了一边,高跟鞋咔哒咔哒地直往顾惊云那张桌子冲过去,店里的客人都慢慢地寂静下来了,只剩下无数个火锅在透明的桌子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她的高跟鞋好像刀子一样在瓷砖地上一刻一个洞,她径直走到缩在角落里的简意澄前面,啪地把包往旁边一扔,抬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他的脸上迅速地留下了一个血印子。
徐庆春不说话,没有表情,也没有要放手的意思,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咚咚地往墙上撞起来,用膝盖往他的肚子上狠狠地顶过去,咣啷一声撞翻了椅子。
她不尖叫,不骂,一句话也没有,凌厉宛如刀刻,只有简意澄的头撞到墙上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响着,像是枪炮的响声,一声,两声,三声,漫长得好像永恒。
江琴死死地从背后抱住我,手压在我的肩膀上,事实上我也没有起身的意思了,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木木地看着这个场景,满眼都是暗红色的光,桌子上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她这种旁若无人又视死如归的气势已经把所有人都震慑住了。
徐庆春顺手抄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砸到简意澄的头上,玻璃杯哗啦一声碎掉了,水流了简意澄一脸一身,她好像要把简意澄捏碎一样,歇斯底里地按着他,撕打着他,要把他生吞活剥,就像猛兽见到猎物那样。
她手上什么都没有,却像是拿着一把刀一下一下地朝着简意澄狠狠扎过去。
简意澄终于开始尖叫挣扎起来了,我以为他已经死掉,已经窒息了。
顾惊云这时候闷闷地站起身来,挡在简意澄身前,他高得几乎把简意澄完全遮住了,“你够了吧。
”他对徐庆春说。
见了这场景,桌上居然有人痴痴笑了起来。
我离他们距离远,看他们的唇形能猜到是“原配打小三”一类的话。
徐庆春抿着嘴,脸色铁青,她简直不是一个活人,我当时脑子里只有这一个想法,从天而降,力大无比,好像是天灾,带着视死如归的蛮劲儿,她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变,越过顾惊云奋力地去打简意澄,啪啪地甩着他耳光,顾惊云推着她,把她轻轻松松地抱住,她恶狠狠地奋力挣扎却动弹不得,简意澄这时候也稍稍地能活动了些,从桌上抓起一个易拉罐朝着徐庆春的头上打过去,徐庆春又用尽全力地与他扭打了一会儿,简意澄徒劳无功地抓着她的一只手,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愣愣地抬起头,对着顾惊云,又转过脸去向着满桌子的人,踩在高跟鞋上摇摇欲坠,“他敢还手,你们看看,”她的声音里满是空空洞洞的哀怨,那种不知道该怨谁的怨恨,就像一个为官老爷们表演的戏子在戏台上声嘶力竭地控诉,凄凉地唱了一嗓子苏三离了洪洞县,“他还敢还手啊!” 可是徐庆春的嗓音已经喑哑,已经无声,好像被什么烧灼过一样。
她控制不住,重重地低咳了两声,所有的人像是一瞬间又被按了开关,忙忙碌碌地活动起来了。
林家鸿沉静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埋了单,梁超上去小心翼翼地拉着徐庆春,僵在那里的前台小姐也复活了,“这位小姐请你出去,”她几步走过去,指着徐庆春说,“你如果再不出去的话我就报警了——” 徐庆春看着乱糟糟一片的场景,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她,桌上的人,店里的其他宾客,都在饶有兴味地看着她,好像意犹未尽似的,火锅还在煮着,煮成一锅糊烂的红汤,桌上的汤汤水水不断滴下来。
顾惊云站在简意澄面前,低着头,握着拳头,穿制服的小姐仍然指着她,“请你出去。
”她又重复了一遍。
徐庆春又是孤身一人了,她总是这样,徒劳无功,孤身一人。
这种眼光和沉默再一次把她高高地举起来,把她孤立出去了。
她眼睛里泛着死光,忽然猛地扑到桌子中间去,把还在沸腾着的一锅滚烫的火锅哗啦一声举了起来,好像拼尽了最后一口蛮力托起了整个太阳。
汤洒在炉架上锅沿上不断地发出烤焦了的响声,无比惊心动魄,桌上的菜,杯子,盘子,全都翻倒了,她的白毛衣上沾满了花花绿绿的污渍。
“都他妈离我远点儿!”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拼尽全力的绝望的尖叫,凄厉得好像把她的肺都吼了出来,“我×你们妈!我他妈要×你们妈!” 她好像慈禧老佛爷一样,站在大殿前信誓旦旦地向各国公使宣战,带着义和团准备×遍整个世界的妈。
没有人再动了,没有人想靠近那个足足有一百多度的铜锅,可徐庆春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看了看站在简意澄身前的顾惊云,就猛地把一大锅沸腾的汤全都朝他脸上泼过去,滋拉一声,又是那种烤焦的声音,红彤彤血淋淋的响声好像是撕开了一匹布。
当一个可怕的事实没发生的时候,你们悬着胆,疯狂地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当那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只能坐在那里,世界被暂时地停止了,谁也来不及做任何动作,所有人都一样。
顾惊云的脸上、身上,全都是热气腾腾的红汤,菜,鱼丸,冷下来的油味儿和火锅热辣辣的气味四处流淌。
简意澄缩在顾惊云背后呜咽起来。
徐庆春手里提着铜锅,愣愣地站在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哗啦一声坍塌下来了。
那是涨满了整个宇宙的仇恨一瞬间破裂,冷却下来的声音,还伴着爆炸过后火药的嘶嘶声。
我一直被江琴按着,保持着半蹲的姿势,实际上从徐庆春进来到现在也就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每次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候秒针都走得很慢,好像存了心思把每个镜头放慢摊到你面前让你看个一清二楚似的。
我浑身发麻,挣扎着要站起身来,想要去帮他们点儿什么忙,去帮着递个纸巾也好,但我已经没劲儿站起来了,甩脱了江琴之后就崴了脚,被自己的鞋带绊倒在地上。
我心里把这双帆布坡跟鞋骂了个遍,狼狈不堪地想要爬起来,那桌上刚刚还目瞪口呆的众人转过身来,看到我了,有几个人痴痴地笑了起来,顾惊云想要走过来,想要帮忙,他好像是刚刚从沼泽里被捞出来一样疲惫,身上还黏着水草和鱼的尸体,红色的火锅汤啪嗒啪嗒地流到地上。
他慢慢停下了,污浊的液体不停地流到他的眼角里去,让他的眼眶红肿,渐渐流下眼泪来。
然后张伊泽站起来,走过来了,朝着地上的我伸出手,他戴着爵士帽,眼睛里还带着笑,酒店里一直在放音乐,放到一首意大利哀伤的旋律,好像是《教父》的主题曲那样。
他妈的,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想到教父呢。
我看了看张伊泽,他像一个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里轻浮优雅的男主角。
“原来你一直在这儿啊,”他漫不经心地开着玩笑,对我行了一个骑士的致意礼,“快起来吧,苏爷。
” 我被张伊泽拉起来,往那张桌子上走过去,就像一个回到祖国的可耻的逃兵。
梁超和林家鸿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围着徐庆春和顾惊云劝和,徐庆春好像一个被拔掉了开关的木头人一样,目光涣散,毫无表情,手里提的铜锅还在往下滴着油,我的嘴里发甜,是那种腥甜的味道,刚才摔倒的时候不知道咬到了哪块肉。
顾惊云在桌上捡了块纸巾,徒劳无功地擦着自己的头发,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感觉到江琴从我背后朝我走过来了,“苏鹿,”徐庆春忽然叫我的名字,“去给我拿一沓餐巾纸过来。
” 我像个跑堂小妹一样忙不迭地把餐巾纸送过来,我能怎么办呢。
所有的人都在劝徐庆春和顾惊云,没有人理会满脸是伤瑟瑟发抖的简意澄,好像他本来就应该那样,他是个摆在店里的装置。
我走到顾惊云身后,没看他俩,搬了张椅子让简意澄坐下,他一直双臂抱着自己,“苏鹿,”他眼里含着泪水,声音怯生生的,头发被抓乱了,眼角眉梢都在往下滴着血,“我冷。
” 我顺手抓过林家鸿的大衣为他披上,他把头埋在椅子背里。
徐庆春拿过纸巾,认真地抬起头,旁若无人地擦着顾惊云脸上滴下来的火锅汤,他漂亮的脸蛋被烫伤了,红红的一片。
徐庆春的眼神就像四处流淌的霞光一样,哀伤而柔情万种。
“顾惊云,你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她一边一点一点地把纸巾擦过顾惊云的脸,一边像是说情话一样,温柔地看着他的眼睛,“这三年我就当给红十字会献爱心了。
×你妈。
” 纸巾用完了,她抬起手,又放下,凝视了顾惊云几秒钟,好像要把他脸上的所有细节都扫描下来一样,然后转过身去提起包,像顶着旗帜一样顶着一身花花绿绿的毛衣,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店门,高跟鞋一步步踩着来自出口碎了一地的光线,像个四分五裂的玻璃人。
她知道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她都一个也见不到了,再也不会见到了。
她世俗,干脆,活得鲜血淋漓,乱七八糟,她像一只困兽一样拼尽全力地挣扎。
她的敌人是谁呢?不该是简意澄,也不该是我吧,我没搞懂,到现在也不明白。
顾惊云颓然地坐在椅子上,“顾爷,你不去追她?”梁超试探着问。
“我够了,我他妈的够了。
”顾惊云摇摇头,“就算是我欠她的吧,也总有个还清的一天。
”对,你还清了。
我脑子里一团混乱,眼前只有简意澄像一个没被阳光照耀到的黑影一样。
我把他拉起来,“走,我带你去医院。
”说着我给贺锦帆打了电话,说不上为什么,现在在座的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看到了,我就想逃开这儿,越快越好。
“去医院?”他怯怯地问,“我想回家洗个澡——” “不能洗澡,伤口会感染。
”外面的阳光照得人眼睛发花,好像是天上撒网撒下的刀子。
我没有说出口另外一句话。
一切都够了。
对简意澄的歧视我受够了,顾惊云的不解释我受够了,那种“原配打小三理所当然”的眼神我也他妈受够了。
这个可怜的家伙变成了一个替罪羊,一个还债的筹码。
凭什么我们没有力气,凭什么我们就不能看得更远,凭什么我们就只配在爱情里攻城略地,凭什么表面再强的女人也只能对和我们一样的人下手,结个破婚,生个破孩子,安安稳稳,灶边炉台,把一辈子葬送进坟墓里,这就是你们拼将一生求之不得的东西是吗?男人可以拥抱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谁该在什么位置,可以把我们捏在手心里看着我们挣扎,可以看着我们为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东西挥舞着尖利的牙齿和爪子互相想要致对方于死地,然后再斟一壶酒上几碟小菜就像是看戏。
凭什么,凭什么,我不要和你们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了,我不是个奴隶,我希望你也能明白你不是一只兽。
我退出,我退出。
【江琴】,2014
我再看到苏鹿的时候,她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剪得比我还短。美国的理发店水平不行,她剪成了那种毛毛躁躁的男孩儿头,多出来的几撮发丝尖的扎手。
剪了头发之后,她看起来完全变了个人,以前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妩媚劲儿全都没有了,像个从明信片上走下来的小男孩儿。
我们坐在屋顶上,喝着啤酒,聊着天,实际上我们这个小区是不允许人坐在屋顶上的。
她从来都不管这个,两条腿晃晃悠悠的,拿着一罐啤酒,“我妈让我订婚了,”我看着钢笔水一样硬朗的天空,喝一口酒,我得和人谈谈这个,最好是和这个自行殒落了的party女王。
没落的贵族和迟暮的红颜说的话都比别人好玩儿,剩下仅存的自尊,玩世不恭,固执傲慢。
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太久了,久得都快长毛发霉了。
“我今年22,我觉得不着急,她说女孩儿还是快点稳定下来好。
” “不结,小哥,结什么婚啊,才这么小。
”我就猜到她会是这种回答,我可能是需要这种回答来给我一点鼓励吧。
我在美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我的师尊遍布修真界/全修真界为我火葬场薄夭
- 当真咬春饼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怀了队友的崽怎么破西山鱼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综]混沌恶不想算了!安以默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同桌乃是病娇本娇候鸟阳儿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圣武星辰乱世狂刀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仙尊一失忆就变戏精哈哈儿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重生女配之鬼修雅伽莎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极品修真狂少墨世
- 剑海鹰扬司马翎
- 大风刮来的男朋友烟火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