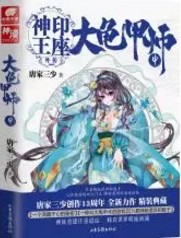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派克街口的卡门(2/3)
当天晚上就把我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搬过来了,我也知道这儿乱,但有什么办法呢。
”她在谈到苦难的时候总有一种嘲讽的欢愉语气,像是一个饱经沙场的老将军掏出来金光闪闪的徽章。
“等过一阵儿就不乱了,来,给爷吃一块炸苹果。
”我看到顾惊云从厨房柱子的后面手里夹着烟走进来,对着苏鹿笑了一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混球儿在听到别人对他的贬低的时候,总表现得波澜不惊,他要么就是已经淡然到了一种境界,要么就是真的无耻——我想多半是后者。
他比平常的人长得高些,却不见得漂亮到哪儿去。
活像野史流言里听书遛鸟的地主家长子,神态里总带着些奇怪的玩世不恭。
“是给你吃的吗,你个变态男。
”思瑶调笑似的,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说好今天晚上带我们出去玩的,你又去哪儿泡妹妹了。
” “泡什么妹妹啊,今天我哥们儿过生日,我去陪他喝两杯。
”他放下身子,往盘花的椅子上一靠,歪着头,眯着眼,吐出一个烟圈儿来,又笃定的朝着苏鹿笑了笑。
“十点半了,外面都关门了,上哪儿玩去。
” “才十点半,”苏鹿甩了甩手上的泡泡,往窗外无边的黑暗里看过去,洗洁精的香味混着泡沫,让人神飞意扬。
“十点半算什么啊,国内才刚刚开始。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这大农村,还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 “就是嘛,才十点半,鹿鹿她懒得要命,都不带我去吃火锅——”思瑶的声音很柔软,你不会觉得她在撒娇,而是会认认真真地相信她说的话。
她没经过什么风月情事,但是比苏鹿懂得怎么去做女人。
顾惊云靠在椅子背上,往后仰着闭上眼睛,“好了,小姑奶奶们,就让我休息一下——” “你是怕动一下掉肉,大年三十晚上卖不出去吗?”还没等别人笑,苏鹿自己先笑了,“没事儿,我先预定了,大过年的总得杀头年猪。
” 顾惊云睁开一只眼睛看着她,嘴角上撇出一点笑,“你这小丫头,整天的就会损我。
”没等思瑶跑过去娇滴滴地揉他肩膀,他就把烟掐到旁边的烟灰缸里,一缕缕烟雾安详地升腾起来,好像是烟的魂魄一样,“好吧,带你们去西雅图吃螃蟹。
” “你也跟着一起来吧。
”苏鹿披了黑色毛绒绒的披肩走出去,到了门口忽然回过头,朝我笑笑,灯光打下来,她的眼睛里好像弥漫了十年不遇的大风雪一样,“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林家鸿。
”我看着她,脑子里想起一道难解的代数题。
顾惊云走在前面,忽然回转过头来,“对了,有件事儿,”他的脸上仍然满是饱蘸浓墨的笑意,“徐庆春过两天就要回国了,休一个学期的假。
到时候我们家就整天都有人来玩,你们也随时都能来。
” “好啊,太好了——”思瑶在雪地里蹦跳着,拍着手,锦红色的碎花裙子一摇一摇的,那是种由衷的,投入的欢乐,把黑夜里的雪地融化成了肃杀的背景。
我们挤上顾惊云的车,他把车轰隆一下发动起来,整个脸都被安然降临的灯光点亮了。
“你想吃什么?”顾惊云偏过脸去问苏鹿,眯起眼睛来温柔的笑,语气里是我从没有听到过的深情。
我看着他朝苏鹿看过去那一瞬间的表情,我很熟悉那种表情,斗牛士艾斯卡妙在昏暗的酒吧里看到卡门,安东尼在渡船上看到埃及艳后,都是这样的表情,那种迷醉的,山雨欲来的危险,好像是整箱摆放在那里的炸弹,一个小小的火花轻轻一点就能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可是苏鹿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把脸朝向窗外,漫不经心地哼着歌,哼着悠然的意大利小调—— 这场悲剧就要开始了。
灯光点亮了,前奏响起来了,台下的观众坐得黑压压的,都屏着呼吸。
苏鹿,我的斑比,你就该上场了,你可得准备好啊。
【苏鹿】,2013
我听着手机嗡的一声震动起来了,不用看,一定是徐欣。内容一定是问思瑶吃没吃饭,睡没睡觉,今天干了什么,明天又要去哪儿。
他每天都给我发这么一个短信,我向来不理他,无聊。
外面的雪下得越来越大,几乎把整个道路都淹没了,“操,这车走不动了。
”顾惊云在旁边轻轻地敲着方向盘,“过两天换一个新的。
” “明天肯定不用上课了,”思瑶坐在车后面,声音一如既往的娇嫩,“苏鹿啊,我想去南方中心购物,还有,吃寿司。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寿司了对不对。
” “南方中心远着呢,”我叹了一口气,“明天下大雪,估计公车又要取消了,就算不取消的话,一个小时来一班,还要转好几次,我可受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来了这儿,那种在国内深信不疑,引以为傲的欢乐和热情都像被浇了盆冷水似的,慢慢地熄灭下去了。
“坐什么公车嘛。
”思瑶轻轻地笑了一下,“留着徐欣干什么用的。
”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轻轻地打了个哈欠。
“别麻烦别人,他又不是你什么人。
” “他自己愿意那样嘛,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思瑶轻轻地按动着手机,“话又说回来,其实他对我还真的不错——” “行了,”顾惊云踩了一脚油门,连看向前面的路的眼神都是那种带笑的,深情的,我觉得,古代人说的那种“眼含桃花”就是说他这样的人。
“明天你们要去哪儿,我带你们去。
” “×,瞧你丫那怕老婆的德性,就不信你放假还能出得去——”林家鸿在后面接了一句,大家都笑了,这种笑像窗户上的雾气一样慢慢地荡漾开,还带着缓缓升腾的花纹。
顾惊云拐出门口的一大片沼泽地,车就被前面的一辆雷克萨斯猛的拦了一下,雪地里飞溅起来大片大片的雪花,啪啪啪地打到我这边的车窗上,“×——”他踩住刹车,挂了挡,拍一下方向盘,喇叭和着外面的雪光,车灯是两团雾蒙蒙的黄。
“思瑶,”徐欣的声音在大雪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被冻得又干又硬,“苏鹿,你快叫思瑶下来我找她有事儿——”他站在驾驶位的前面拍打着车窗,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名字可以被人叫得那么难听。
“你干什么?”我皱着眉头打开车门,思瑶不动声色地站在我身后。
外面的风雪像细小的针一样前赴后继地扑在我们脸上,他嬉皮笑脸地端着一捧玫瑰花过来,“瑶瑶,我听说今天是橙色情人节,今天下午特地去西雅图买了花送你,我看看——”他回过身去把车的后车厢打开,满满当当地堆了一车的玫瑰花,馥郁的好像雪地里淌血的尸体。
我打了个寒战,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雪糕车叮铃铃摇晃的铃声里,车上的冷冻冰柜下藏着还年轻娇嫩的人头。
徐欣走过来拍拍思瑶的肩,满身都是冰箱的味道,好像是一具刚从冷冻柜里爬出来的尸体。
“橙色情人节是日本东京流传过来的,”他像背课文那样背起来,在黑夜里打了个哆嗦,围巾上簌簌地掉下来几片雪花,“一般都会去电影院看两场电影——” “我们要去吃火锅。
”我指了指他身后停着的车,顾惊云把音响的声音调大了,许哲佩的歌声在寒冷的雪地里稚嫩得发抖,他眯起眼睛来,眼镜上盖了一片片的薄雾,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浓郁地把雪气包裹住,说不出来的暧昧,好像是暖气开得太大的房间。
“徐庆春走啦?”他问我。
“嗯。
”我点点头,外面的雪变冷了,无休无止的和着音响的声音刮过来,睫毛就像黏糊糊的蜘蛛网,闭上眼睛就是一片白蒙蒙。
他走过来,伏在我的耳边,“和顾惊云玩的时候小心点。
他在我们这儿名声不好。
” 我本来想说我其实只是在和思瑶玩,听了他这种对白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抹了把脸上没化尽的雨水,打开顾惊云的车门,回身对着徐欣笑一笑,“想太多了对脑子不好。
”我听见雪融进我的声音里,凉意从裤脚渐渐地漫上来。
思瑶在引擎发动的轰鸣声里低着头,满眼都是寂静的欢喜,那种神色让我心里一抖。
我看着她,无奈地笑笑,“思瑶你别管他。
说什么今天是橙色情人节,其实每个月的十四号都是各种情人节,像大姨妈似的每个月一次——” 林家鸿坐在前面一直憋着,终于像是漏气的气球一样扑哧笑了起来。
“苏鹿你说得太对了,”他笑嘻嘻地说,“徐哥从来的飞机上开始就一个一个地追女生,前两天还刚甩了个日本妹子,这回估计是他第一次受挫成这样,还去西雅图买了一车玫瑰,这小子真舍得下本儿。
” “是,”顾惊云的声音懒洋洋地响起来,“凯莱这儿可是个乱世,群雄汇集,多好的人都有,多坏的人也有——”林家鸿情绪明显变嗨了,很不给他面子地接了一句,“比如你。
” “去,”顾惊云在薄薄的雪地上拐了个弯,嬉皮笑脸地接上他的话,“我这是好心给学妹提个醒,你打什么岔。
” “我跟你们说,”林家鸿转过来撑着椅背,故作认真的表情被外面柔和的路灯点亮了,“顾惊云可是凯莱大名人,著名的小老婆狂魔,就跟绯闻女孩儿里面那个Chuck一样,专挑小新生下手。
” “他都有女朋友了还跟着凑什么热闹。
”思瑶脆生生地回答道,然后转过身来握住我的手,“苏鹿,你说他都这样了,我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他——” “你可别这么想,”林家鸿用脚打着音乐的拍子,“想当年多少妹子因为这套电视里几年前就演过的剧情上了徐哥的当,就那日本妞,前两天从日本回来了,徐哥闭门谢客,死活躲在屋里不见她,那妞急得差点就把整个凯莱翻过来了,我们当时在徐哥家打DOTA,没办法了就一起帮徐哥瞒天过海,说他早就回国了,结果有个兄弟憋不住笑场了,那妹子不信,坐在地上不走了,我们足足折腾了五个小时才把老佛爷请出去,你说徐哥也是个人物,就在衣柜里一直藏了五个小时,出来变成了一具丧尸,开门就啪地倒下了——” “大猩猩就是大猩猩,”我笑着伸了个懒腰,“过两天给动物园打电话,快送回去。
” 车里充满了轻轻的笑声,思瑶用力攥了一下我的手。
“怎么啦?”我看着她,她摇摇头,闭上眼睛,“就是现在忽然觉得特别失落。
”她叹了口气,“我觉得在这边就认识了你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 “没事啊,”我也捏捏她的手,她的手暖洋洋的像是小猫的爪子,“你看凯莱里面那些成群结队的人都来了多少年了,我们还年轻呢,绝对更有发展。
” “爷我觉得你的性格更吃得开。
”她哀伤地看着我,“你以后混得开了可不要抛弃我。
” “怎么想到这儿去了,”我笑笑,这孩子总是莫名其妙地忧郁,可能是看多了郭敬明,“妞儿不抛弃我就好。
”我对着她点点头,许哲佩的歌唱到最后一句,满车都是稚嫩的伤感。
“滴滴滴,滴滴滴答滴答滴滴滴,毛毛雨,装满一整杯的lemontea。
” 这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梦里又出现了那个被黑暗覆盖的游乐场,那个游乐场好像废弃了好久了,但每个午夜来临的时候,它一定会重新地旋转起来,所有的角落都亮起灯,那是你从没有见过的,极尽绚丽的色彩,那种颜色鲜艳得好像有毒一样。
整个世界都被喧嚣的狂欢笼罩起来了,但是你永远见不到这些狂欢的人群在哪里,过山车夹着风声,隆重地慢慢停下来了,汽笛声嘶力竭地悲哀地长鸣,然后立刻被喧哗的声音一波波地盖过去,没有回应。
这是哪部电影里的游乐场呢?我走过叮叮咚咚的旋转木马,那颜色真浓郁,我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它了,但我知道每当我的生活里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之前,我总会到这个游乐场里来。
摩天轮把世界上所有艳丽的颜色一下喷薄出来,那些光芒挥霍的真过分啊,整个世界简直都在颤抖了,我没有停下,一直在往前走过去,前面就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完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我快要走到鬼屋了,鬼屋前面有个小丑,穿着斑斓的、绿底的衣服,脸上的妆是夸张的笑,那些颜料都是有毒的,他每次见到我都会用那种奇怪的嗓音向我打招呼,就像是小学时候第二套广播体操的播音员一样,金属的音色回荡在高高的天空上,我害怕他。
然后我就看到了徐欣。
他穿着那件黑色的、羊绒的风衣,平时那种浅薄的、浮夸的神色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
我怎么能在这里看到他呢?我想了想,这个地方不是我的游乐场吗?“你是怎么闯进来的?”我的声音一定是脆生生的,带着点好奇,但是在梦里面我听不见,好像被扔进了深深的水底,一张嘴只能吐出一串串的泡泡。
“你是从后门进来的吗?” “我来找他。
”徐欣抬起手,指着慢慢旋转的摩天轮,摩天轮的每个厢房都发出耀眼的明黄色光芒来,可是我看到了最顶上那个座位里面坐的人,那是顾惊云。
他是怎么看到我的,还朝我挥着手笑,那个笑容就像一个谜。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了?”我终于听见我的声音了,嘶哑的颤抖着,还带着恐惧。
是做梦的时候压住胸腔了吗?我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来呢?徐欣仍然慢慢摇着头,好像是一部电影的大结局一样,悲凉地笑一笑,“你都不记得了吗?”他转过身去,露出身后长长的一根丝线,穿过心脏,穿透衣服,绷得紧紧的,就像一个木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早就已经死了。
我什么都知道。
” 有一种巨大的哀伤从胸腔里无休无止地漫上来,可是我不受控制地张开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后面有人拍我的肩,我转过身去,看见那个绿色的小丑,脸上的妆比什么时候化得都鲜艳,它的嘴唇真红啊,红得就像皮肤割裂了渗出来的血。
“欢迎来到鬼屋。
”那种广播体操播音员的音色是冰凉的金属,天空被整整齐齐地切开。
我胆战心惊地站在原地,该跑到哪儿去呢?我对自己说,不能跑啊,这是我的游乐场。
这时候周遭看不见的人群忽然鼎沸起来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把所有的灯光都杀气腾腾地吞没,远处的地平线上,气势磅礴地点燃起了无数烟花。
像是烧不尽的夕阳。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思瑶趴在我面前,我费力地撑起来一点儿,感觉到头发都湿透了,湿漉漉的搭在肩膀上,像是水里捞出来的人一样。
“顾惊云没法带我们出去了,”她噘着嘴,“刚才徐庆春还因为这个生气了,和他大吵了一架跑了出去,现在顾惊云开车去找她,家里没人。
” 天空蓝得很炫目。
我看见外面一望无际的雪地,有一道光线很柔软地打下来,显得又寒冷,又寂静。
这个小镇很少有这么美好的时候。
“现在几点了?”我打了个哈欠问她。
“中午十二点。
”她抬手看了看表,“还出去吗?现在出去还来得及。
” “哪儿能不出去呢。
”我从床上坐起来,甩了甩头,想把刚才残留的那点惊心动魄的噩梦甩出去,“等我洗个澡,”思瑶已经坐在我床沿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一本时尚杂志,“我们搭下一班公车出门。
” 可是等我们走到公车站的时候,空气就已经变得阴湿冰凉了,还没化干净的雪卷着冬天的荒野凉凉的味道,不由分说地朝我们席卷过来。
“快下雨了。
”思瑶往灰暗的天空上看一看,我笑一笑,“说不定是下雪呢。
我觉得下雪比下雨要好。
” “也是,下雪就又能停课了——”公车的皮很陈旧,吱吱嘎嘎地在雪地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痕迹,“到了。
”思瑶每次在上公车的时候都要拉过我的手来,上车的几个台阶上全都是淤泥。
她挑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你看,”她的手指磕了磕窗户,灰色的,细密的雪花朝窗户飘过来。
“果然下雪了。
” 满耳朵里都充塞着印度腔、中东腔的奇怪英语,这辆公车一直摇摇晃晃地往前开,迎着灰蒙蒙的雪气,开进昏暗破败的梦里去。
【梁超和江琴】,2015
我那些王八蛋一样的朋友,大多活得很欢实。他们刚卖了一批假冒伪劣化妆品,坑了新生几百美元,诱拐了几个小学妹,都围坐在一起,吃着火锅,喝着酒,吹着牛×。
有时候还要用粤语吼几句老歌,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这时候就算是黑白无常找上门来,最多也就把他们揪起来一人扇几个耳光,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感叹一句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
而我那些短命而终的朋友,大多有种特质。
他们这种特质时时刻刻地提醒别人,他们是不寻常的,卓尔不群的,超然独立的,像是划过海面上的一道短暂的焰火。
可能是老天对他们充满了爱怜,并不想看他们在人世间遭到更多的磨砺,挫败,困苦无依,不想让岁月把这种奇异的火光慢慢熄灭,最终泯于众人。
我在iPad上注册了一个小号,浏览着顾惊云的人人和微博。
他的信息很少,仅有的几张照片是和高中同学的合影。
江琴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来,她曾经也和我们一起玩儿,我记得因为简意澄的事情,她和我们分道扬镳,闹得很不开心。
越南粉餐厅里没有人。
外面下着雨。
这一带的天气就是这样,总是恰到好处地嘲弄着天气预报。
江琴坐到我对面,把头发全都捋到后面去,我看见了她被水摧折过的脸,带了点刀兵之气。
手枪一别纸扇一摇就是乱世枭雄。
我在心里想到。
我要是个姑娘,说不定会爱上她。
“你是问顾惊云的事儿?”她拿起菜单,声音里灌满了北方寒冷的风。
“还是简意澄?我知道你记性不好,何必难为自己。
” “我都问问。
”我环视四周,餐馆的服务员是个越南人,黑发黑眼,听不懂一句汉语。
“我前些日子听警察说,顾惊云死前是跟简意澄两个人,都开着车,都在山路上,两个人要去约架,是吗?” “都有警察管这事儿了,您老人家还操什么心。
”江琴笑了一声,对着服务员在菜单上点着法式番茄牛肉粉。
“简意澄的罪不都定了吗?违规驾车致人死亡什么的,都是英语,我英语不好,听不懂他们那些专业术语。
” “不是。
”我搅着杯子里的柠檬水,思考着到底该不该告诉她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维持着我一直调查的由头。
“我和美国的警察打过720次交道。
他们什么都不会记下来,只会顺着自己的思路走。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把你当成个精神病小孩儿——” “你不是精神病小孩儿?”江琴看着我,好像听到了一件好笑的事情。
“来,老梁,你跟我说实话,你还记得简意澄是谁吗?” “记得。
”我知道她是在嘲笑我,但也没办法。
“我记得他和我一起打LOL,他喜欢用伊泽瑞尔和潘森。
我记得他让我陪他一起去comcast修理网络。
路很远,他根本就不会开车,开自动挡都费劲儿。
整个凯莱的人就只有我知道。
” 耳边的雨声越来越喧哗了。
整个小店像是被放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间一样。
江琴偏过头来,用一种又荒唐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不会开车,所以出了事儿,这不是很合理吗?” 我费力地咽着唾沫,喝了一口柠檬水,慢慢地斟酌着句子。
“我先说好,我手头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种猜想。
”对面的这个人充满了敌意,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顾惊云已经死了,简意澄的案子也结了,我的猜想没有任何意义,也救不了任何人。
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简意澄就太可怜了——” “可怜个屁。
”江琴愤愤不平地灌了一口水,“他这人,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好事儿。
给老黑献一次菊花,让那么多人没挂科,可算为社会做了点贡献。
” “琴姐,你先听我说。
”这个称呼让江琴愣了愣,好像回到了多年前,艳阳高照,蓝天如洗。
“警察的调查记录,简意澄的口供,结论都是一样的。
两个人超速行驶,简意澄在山路上超速,轮胎打滑,把顾惊云的车撞下了悬崖。
但是简意澄当时开的那辆车是香港人的,改装过,手动挡。
一个开自动挡都像娘们儿的人,根本开不起来那辆车。
更别说雨天在山路上开。
所以我觉得简意澄他根本就没有说实话。
”我停下来,看着江琴。
“你是不是更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了?” 江琴低下头,好像要从包里摸一根烟,摸到一半又放弃了,“你继续说。
” “简意澄的口供上说,雨天路滑,他想在山路上超车,多踩了一脚油门,结果前轮胎侧滑了,车辆滑出去,导致顾惊云驾驶的车辆翻车,滚下山路——他是这么说的,我没记错。
”我深深地看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里是北方一落十年的大风雪。
“我们都是开车的人,琴姐你也应该知道,车在加速的时候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后轮侧滑,轮胎失去抓地力。
那条山路是个左转弯,后轮侧滑会立刻撞到旁边的山,根本不可能波及在路右侧行驶的顾惊云。
而前轮侧滑,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紧急刹车。
车辆的转向力不足。
这样随之而来的就是车沿着路的转弯切线滑出去,或者车辆横摆路中——琴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简意澄根本就不懂车辆操作的原理。
” “所以你认为简意澄是——”江琴眯起眼睛。
“是在保护一个我们谁也不知道的人。
”我接下她的话。
“这听起来太离谱了,我也没认为我比警察高明。
但所有的警察都会认为,一个已经认罪的凶手,没有必要再撒谎。
尤其是在这种犯罪细节上。
这又不能给他减轻什么罪。
这几天我也到当时的现场看了几次。
我觉得,当时开车的人根本不是他,而是一个经验相对丰富的司机。
我不知道路上出现了什么东西,让这个人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紧急刹车,但我推测他当时一定吓坏了——” “梁超你怎么不去写小说?”江琴安静地打断我。
“警察办案不是靠猜的,既然能定罪,就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你以为他们是吃干饭的?更何况你现在对简意澄可能还没有我了解。
”她冷笑一声,“像简意澄那种人,怎么可能去保护一个人?” “我不是想洗白谁,如果简意澄是被什么人胁迫呢,如果——”雨水的声音极为寒冷,让人心头一凛。
我听见我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顾惊云的案子没几天,简意澄就出事儿了。
谁都能看出来这两件事情有关联。
也就是说简意澄案的这个幕后主使人,说不定也是抓错了人。
” “你这就有点儿扯远了,本来还想夸你有逻辑性。
”江琴沉默了一会儿,“黑人犯罪,很大程度上是随机性。
也就是说简意澄那是坏事儿做绝了,活该。
虽然作为同胞,我这么说是有点过分了。
”她叹了口气,慢慢地说,“如果你非要查下去,我也不会告诉别人。
就当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你要是忘了什么事儿,我如果有空你可以来问我。
” 她拆开筷子,冲我眨眨眼睛,番茄面已经有点凉了。
“梁超,要是有一天你写了小说,别忘了把我放在里面。
”
【苏鹿】,2013
“苏鹿,起床了——”隔了太久的年月,我只记得那么一句,气温那几天下降得飞快,满天满地都是浓重昏沉的雾气,街道上的路灯也不灭了,在雪地上照出暗淡的光来。我看着思瑶穿好了新买的小马甲,站在我房间的门口,来提醒我感恩节到了。
“快点起床啊苏鹿,”她的声音里带着一如既往的甜美和欢喜,“今天我们一起去波特兰,听说那边免税,我想给我家伊泽买点礼物呢,你说是范思哲好还是GUCCI——” “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我从被窝里钻出来,没好气地逗她,“我看张伊泽就是他们家春三家的。
把春三看得比爸爸还亲。
”春三是张伊泽养的猫,这小子每天喂它大鱼大肉的,过得比我们都好。
“那说明我们家伊泽爱护小动物,我就喜欢有爱心的男人——”她没羞没臊地冲到洗手间去了,然后美滋滋地往她春色满园的脸上涂着一层又一层的philosophy保养霜。
“苏鹿你知道吗?”我慢慢穿着衣服,一边听着她清脆的声音,这声音就像清晨的寒风似的,把我从困顿中吹得清醒,“YC和她老公居然离婚了,靠,YC那么好的女人都不要,真是神经不正常。
” “那有什么的,”我随口回答着她,“世界上每秒钟都有两三个人去领离婚证,你们干吗对这个这么关注。
”说完了我才想起来,三个人去领离婚证是不可能的事情。
“哎呀不是——”她顶着一脸白花花的面膜,像个贞子似的猛地坐到我身边来,“听说她老公拍戏的时候遇到了小三!”虽然是隔着面膜,但我能感觉到她义愤填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表妹软玉娇香渊爻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我始乱终弃前任后他们全找上门了倔强海豹
- (综漫同人)五条小姐总在拯救世界聊笙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春日颂小红杏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我就是馋你信息素[娱乐圈]夂槿
- 江湖人独孤红
- 佛系女主崩坏世界[快穿]实心汤圆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乾坤剑神尘山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锦帐春慢元浅
- 真爱没有尽头科林·胡佛
- 女配不想死(快穿)缓归矣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眼泪酿宴惟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夏日长贺新郎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夕照斑衣白骨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情敌五军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夏日长贺新郎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鱼游入海西言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游弋的鱼乌筝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不差钱和葛朗台寻香踪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羞耻狼空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恶魔总监:亿万独宠小男友浔弦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独立日学习计划一碗月光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轻狂巫哲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不差钱和葛朗台寻香踪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金蝉脱壳风弄、彻夜流香、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戏精配戏骨陈隐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一不小心撩到豪门对家棠叶月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影帝是棵小白杨闻香识美人
- 无可替代仟丞玥
- 秃头之后,我在前男友面前变强了鱼片面包
- 竹马危机萧二河
- 金枷马鹿君
- 万物留痕汉堡年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