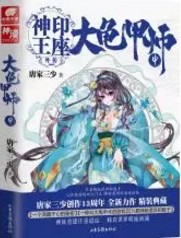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派克街口的卡门(1/3)
【苏鹿】,2015
7月4日晚上,我们这儿闹了场命案。有个叫艾伦的学生死了,尸体掉进了山崖。
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
关于这件事儿,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那天是国庆日,我们都在西雅图的海边看烟火,所以没人知道那究竟是一起谋杀还是仅仅因为酗酒酿成的悲剧。
这件事我知道得很晚。
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学校里几个消息灵通的学生已经连人人上的讣告都写好了。
那天的天气很差,云层混乱而污浊,整个西雅图地区迎来了罕见的暴雨滂沱。
大雨把村里的窝棚,树叶,市区的钢筋铁骨,派克市场,华盛顿大学,都浇上了一层气势磅礴的腥味。
这种味道像从海底席卷过来,啪嗒啪嗒地打在黑色的雨伞上,打在皮革和棉布上,打在学校大理石的花砖上,把整个世界用倦怠和疲惫笼罩起来。
我听到警察一次一次地拨打我的电话,才想起我是他在学校的紧急联系人。
我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路边,回答:“是我,我是苏鹿。
” 现在我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四周的空气里沁满了沁人心脾的花香。
黄昏非常凉,雨声昏闷细密,打在无数小砖屋的屋顶上像一场清醒的长梦。
两个警察一前一后地站在我面前撑着伞,灯光明净,头发花白。
“你的名字是苏……苏鹿。
”看起来更加年老一点儿的警察摊开手写板,翻着一沓一沓的记录。
铅笔划动的声音在雨里空落落的回荡。
“自从7月4日我们在宝佛丽市西丁山后发现了你朋友的遗体,一直没能和你取得联系。
据其他的学生说,事情发生的那一晚,你正在从西雅图市区回镇上的路上。
” “是的,先生。
”我习惯性地摸到口袋里的圆珠笔,扣动着开关。
这声音听起来令人烦躁不安。
“你知道他在深夜里一个人跑到郊外去想干什么吗?”老警官睁大了眼睛。
他的眼球布满血丝,像块沾满了血的破油纸。
“案发现场还有个来自中国云南的学生。
他说死者当时也喝醉了,不过你的另外一位同学刚刚指控这位学生一级谋杀。
” “我不知道,先生。
或许他们想去郊外看看月亮。
”我小声地回答。
那天晚上的月亮发红,就像他的眼睛一样。
“很符合逻辑。
”老警官几乎笑了出来。
他看看我,又看看地面。
“现场并没有什么肇事的痕迹,根据我们的推断,这名叫艾伦的学生有很大的可能是死于意外——但按惯例我们还是得调查一下,以排除自杀的可能。
”他和身后的女警官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恕我直言,我们听说艾伦在最后的日子里情绪不大稳定。
” “这不可能。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但一种深深的恐慌从我的血管里涌了上来。
我抬起头。
“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经常举办各种宴会。
” 他死前的日子寄住在另外一个同学家的客厅里,用塑料布帘子挡出一片隔间,头发挡住眼睛,浑身都是潮湿的烟草味道。
像是一张上个时代被水泡的发黄的遗嘱。
但我始终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
我知道那天晚上之前发生了什么。
在那个真正危险的时间点上,没有人会选择自杀。
“噢,我们只是问问。
”老警官又在文件夹上刷刷地记下几笔。
“结合现场分析,我们的看法可能已经达成了一致。
格雷佛理地区的路灯坏了,由于下雨,艾伦在看到那片悬崖的时候已经晚了,来不及刹车。
他坠落之后当场昏迷了过去,而后车厢开始燃烧……真是不幸。
”他惋惜地摇了摇头,示意他身后的女警员准备离开。
“等等。
”我往前走了几步。
“那个云南学生姓简对吗?”直觉告诉我,如果这些事情再不说出来,就再也没机会了。
“如果这件事和简意澄有关,你们应该重新调查一下,考虑谋杀的可能性。
” 老警官回过神来看着我。
西雅图的夏天静静地吸了一口气,吐出来潮湿的雨气和树木的味道。
“简意澄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在房子里聚众吸大麻,昼伏夜出。
我们曾经举报过许多次,但从来没有人相信我。
他表现得一直像个好学生。
” 可能这不是真的。
可能他会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看他的朋友打牌。
但是我的语速越来越快了,“他曾经说我们都不配在这儿。
他仇恨我们。
”简意澄是个混球儿,但他不会得罪所有人,他可能只是恨我而已。
“在国庆节几天之前,简意澄还和艾伦通过话。
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他曾经问过艾伦,你选择道歉还是选择去死?”我心里在无动于衷地笑。
“警官,你们会好好调查的,对吧?” 我希望世界上还有人和我一起调查事情的真相。
我不希望只剩下我一个人追查凶手,全世界的人对着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把多年积压在库里卖不出去的同情心一股脑儿地甩到我脸上,好像我是个看多了柯南的疯子。
雨水哗啦一声落下来,把整个世界灌满。
那个女警官的话几乎被淹没在了雨水里。
“我们会努力调查的。
天色很晚了,你的朋友会来接你吗?”她担忧地看了一眼远处的街道,山毛榉树青绿色的叶子浓得晕成一团。
疾风挤过树缝,其声如泣。
“我没朋友。
”我从台阶上站起身,两个老人对视一眼。
我面带微笑地目送他们远去,然后弯下腰拾起包。
拉链坏了,里面的钱包、手机、卷子,哗啦啦地撒了一地,幸好那些人已经走远了没看到。
雨气深重,空气里都是湿淋淋的味道,太阳还没有彻底地沉下去。
马路上汽油的味道混着雨水,往四面八方流动。
一阵风吹过来,树上堆满了陈旧的暗绿。
垂垂老矣,满目荒凉。
我才发现我的头发已经这么长了,好像是荒山上蓬茂的野草。
很久之前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的老友林家鸿找到我,说因为不满室友每天打LOL用榔头把插座砸了,问我这儿还有没有空房间。
那天我叫了一份意大利面、几块鸡翅,和他相对而坐,不知道说什么,只能相视苦笑。
这么一笑,就过了三年。
【梁超和叶思瑶】,2015
那天晚上小镇停电了。烟抽得剩下最后一颗。
车上的雨刷器坏了,天光微明,雨气滂沱。
树,白色的小房子,一团漆黑的加油站,都灰蒙蒙的。
思瑶越过车窗,呆呆地望着雨里很远的地方——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
我昨天才见过她,所以记得她。
她是我在美国小村里的最后一任室友,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永远不会爱上学习好的姑娘。
她们太喜欢自作聪明。
“停电了,商店不工作。
”加油站老板披着白色的雨披,用力挥舞双手,好像精神病患。
路上空无一人,让你觉得这个该死的地方肯定是被众神遗弃了。
雨水就是幸存者们淋下来的血肉脑浆,路上尸体横陈。
我记得从前思瑶跟我说,有一个夏天她是在西雅图度过的。
当时的室友在整个学校的留学生里声名赫赫。
许多接机送站,迎来送往的事情都是他来办。
他们就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去去,有时候不想回家,就在Crabpot里面点一大锅满满的螃蟹坐一个下午,看着太阳慢慢地沉下去。
这鬼地方竟然会有太阳,听起来倒是不错。
可惜我没经历过。
最近我常常在忘记事情,记忆像被雨浇过的野草一样乱成一团。
从前我习惯把遇到的人,发生的事儿都用手机拍下来。
自从我上一部手机丢失以来,这个好习惯也被我放弃了。
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个毛病只是一般的脸盲症——记不得日瓦戈医生的人名,记不得刚读过的课文的内容,记不得点头之交的长相。
其他的小伙伴也都这样。
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和同学讲我们班身高一米四九的班主任在纠缠班上一个富二代的爸爸,同学眼睛发直地看着我,然后给了我一拳——原来我说的那个富二代就是他。
这不影响学习,至少在国内是这样的。
因为比其他同学更熟练的笔记和清晰的短期记忆能力,我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时候经常有出人意料的好成绩。
来到这儿了就不一样,我顺利地在两年里挂了十多科,更悲哀的是有的时候我丢了课程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帮我签到。
那么从哪儿开始呢。
我握紧方向盘,右手慌乱地摸着打火机,摸了好久都找不到。
思瑶把打火机往我腿上甩过来,火苗在潮湿的车里咔嚓一声亮起来,悠远苍凉。
简意澄。
对,简意澄。
我盯着手里火机上黑人哥们儿夸张大笑的脸。
我的时间消耗在找东西,费尽全力地整理被自己弄乱的笔记,对着手机照片来辨认身边的人上。
但我不会忘记简意澄,我的朋友。
他是个基佬,因为这个,别人不喜欢他,他只有我。
雨水渗进来,打湿我半边衣服。
我把烟头弹出去,顺着雨水画出一个绝妙的弧度。
几个醉醺醺的黑人从一片住宅区里走出来,亚洲小哥们儿站在小区门口的彩旗下搔首弄姿。
前面一辆沃尔沃吱呀一声踩下刹车,对路人比出中指。
“他们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影响交通。
”我问思瑶。
其实我只是想弄出点声音而已。
“前几天的案子。
”思瑶隔了好一会儿才出声,双眼平静无神,看向前面很远的地方,“现在语言班的亚洲小哥们儿每天都不老实,成群结队地到黑人住宅区里散步,想拿免费绿卡。
” 我偏过头去看着她。
她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那个样子,恍恍惚惚,脸色青白,披着大外套好像是一个一字一句诅咒敌人部落的女巫。
听别人说她曾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回国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她以前是个漂亮姑娘。
不过我想象不到她漂亮的时候,这件事可能只是我记忆的误差。
“你在怀疑她吧。
”思瑶低下头去,一边玩弄着衣服上的绳子一边补上两个字,“苏鹿。
” 黎明非常凉,凉到窗户上浸满了薄薄的雾。
地面也滑,轻轻踩一脚油门,大雨就像一块厚重的玻璃被我撞破,满地都是亮闪闪的碎片。
“不仅是你,警察也在怀疑她。
苏鹿和简意澄不共戴天,这儿的人都知道。
”思瑶笑起来,“在这个时候做这种事儿,我看她也是不想活了。
” Slash的声音隔着音响灌满车厢,你看起来变了不少,但仍是我所爱慕的人。
失去爱情但我至少可以回忆从前。
“我一直以为他们俩打架就是小孩儿闹一闹,过两天就好了。
”实际上我已经记不得他们俩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印象里苏鹿是个风光的姑娘,并且目中无人。
和简意澄一样,做事儿都充满了孩子气。
雨气涌进车厢,四周浮起了一种危险的寂静。
“小孩子闹一闹?他们都希望对方去死。
”思瑶歪着头,靠在车窗上,动作有点稚气,像是个偷了妈妈口红的年轻交际花。
我觉得我能想起来苏鹿都做了什么事儿,不过得给我点时间。
“就冲着简意澄造的那些谣,我都看不下去。
” 简意澄总是乱说话。
我们有时候开他的玩笑,他自己也跟着我们一起笑。
后来他跟了一个36岁的广东饭馆老板,搞得不清不楚,这人就有些疯疯癫癫。
说到底在这个小村子里面,缺乏物质资源,没有吃的,又没什么好玩的事情,不少人都有些疯癫。
环境太过封闭,就像国内的寄宿学校一样,免不了几个人聚在一起,整天钩心斗角。
我以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分享,讲的是国内的网瘾治疗所搞集中营,死了好多人,没人知道。
那条微博下面的转发量还没有明星八卦的零头高,但简意澄转了。
我知道他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
“像简意澄那种人,就是社会败类,垃圾。
”思瑶清脆地冷笑了一声。
“苏鹿以前就喜欢和这些垃圾混在一块儿。
”夏天的雨往车厢里渗,我觉得有点冷。
“不过现在想起来,也就苏鹿一个人对我好一点儿。
”这条路往前开,越来越荒无人烟,我忽然发现这一幕似曾相识。
我开始怀疑身边的思瑶是不是在多少年之前真的有过甜美欢喜的声音,是不是真的有一张未经世事的洁净的脸。
“以前上语言班的时候,课少,压力也小点。
现在好日子都过去了。
”思瑶的声音像路两旁的山毛榉树一样四处流淌,融化成为一种青绿色的液体。
这种日子宜睡觉,宜葬礼,宜老僵尸们打游戏。
好日子都过去了。
三年之前姑娘们还都风华绝代,娘炮们也花红柳绿。
没人死,也没人混吃等死。
花正好,月也正圆。
三年前
【苏鹿】,2013
现在推开门,再过五秒,就能看见徐欣端着打包好的饭菜,在雪里被冻得瑟瑟发抖,眼镜上还蒙着一层薄雾。“越南粉,咖喱鸡,还有steakhouse的纽约牛排,我给你送来了。
”连对白都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黑夜里的风摧枯拉朽地呼啸着卷过来,衣服上带了点薄雪,风铃在屋檐下叮叮咚咚地碰出回声,噢,多好的镜头啊。
徐欣你这个男主角堪称完美。
深深的厌倦从我身体里漫上来,我看着他,因寒冷的空气而轻轻地跺着脚,呵出一团团白气来,“要不要进来坐坐,”话到了嘴边忽然停顿住了,干吗要陪着他演这么一出烂戏呢,我想,然后下一句话很轻易地脱口而出,带着笑意,混着冰碴,“谢谢你了,要是没事你就先回去吧。
” 他点了点头,“你也快回去吧,别冻着。
”那副隐忍的表情真到位,一转身跑进茫茫的黑夜里去了,如果这个时候再配上二胡凄凉的音乐的话,那就是北风里手握红头绳的白毛女。
“走啦?”我听到哒哒哒下楼来的声音,徐庆春是我的房东,来这个小村庄上学一年多了,和她的男朋友顾惊云租了套二层的小楼,再把房间租给我们。
她总穿着一套睡衣,头发乱乱的像是好多天没洗,眼角细长,颧骨高耸,看什么都像在冷笑。
“不错啊你,有两下子,刚来就钓上了这么条狗。
”她那种笑看起来很不自然,又拍拍我的肩膀点上一支烟。
我没说话,她的北方口音太重了,重得好像有沙子夹着风噼噼啪啪往你的脸上拍过来。
她把一缕头发挽到耳朵后面去,“其实徐欣不错,对你这么好,有钱,又有车,在这儿啊,什么都是扯淡,钱才是正经的。
”她像个包租婆似的对我点点头,在浓重的烟雾里眯起眼睛,“你看,跟了徐欣,他还能带你出去玩,不用整天地死在家里了,像我,多闷。
” “他是来追思瑶的。
”迎着被大风刮得四下飞舞的雪花,我往黑暗里望过去,越过风和雪刀兵气浓重的厮杀,被雪覆盖的平原上是一种长久的、庄严的寂静。
“思瑶说她现在不想找,而且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这么活着挺好的,也没必要非要找个人来陪。
” “你现在这么说,是因为你们还小。
”她说话的语气有种顺其自然,好像她知道她说的一定会发生,而我又不会听一样,“你又没车,而且你俩玩儿得再好,你也不能陪她一辈子。
” 徐庆春的男朋友顾惊云是我课上的同学,他那个人很潇洒,风流倜傥,对这些生活里挤挤挨挨的小事颇有些袖手人间的味道。
她就每天在家整日地陪着他,为他煮饭打扫房间,生活好像被这些俗事琐物填满了,没有缝隙,无边无际。
我看着她,生活像铺天盖地的大网一样,在她的眉毛上沉沉地压下来,已经没有了神采,我忽然想问她,你有了男朋友,不也是一样整天地在家里。
然后把这种想法压下去。
这是别人的事情,我告诫自己。
“我倒是能陪她一辈子,就是不知道她愿不愿意。
要不要吃香蕉?”我转过身到厨房里去,开了冰箱,朝她故作欢笑,听起来好像有谁往我的喉咙里倒了一桶浆。
她也走过来,朝着冰箱昏黄的光芒里看过去,我常常觉得,冰箱就像是倦怠的旅人跋涉很久才走到的北极,穹顶上还笼罩着没褪尽的壮美极光。
“香蕉还没熟,这么吃发苦,”她深吸一口气,嗅到香蕉清苦的气味,眉间的表情慢慢舒展开,变成一种愉悦,“来,我给你做香蕉奶昔。
”她忽然像个小姑娘似的,提着大大的牛奶桶,一蹦一跳地跑到榨汁机边上,看着香蕉和牛奶互相碾压,最后融化到一起,凉凉的,好像夏天夜里的栀子花。
事实上,我本来在心里是有点瞧不起她的,我从来也不瞧不起任何人,但我从小就不大喜欢那种鸡毛蒜皮灶边炉台围着男人团团转的女人。
她好像还不只是这样。
她把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男朋友身上,甚至有的时候,我看着她对着夜不归宿的顾惊云歇斯底里地哭闹、叫喊,把家里的瓶瓶罐罐全都砸烂,觉得她就像个红了眼的绝望的赌徒,把最后一点尊严、骄傲全都压了上去当作筹码,完全不顾等待她的是又一场血本无归。
但这个时候,我这种隐秘的蔑视也全都烟消云散了,和她挨着窗户坐下来,“徐姐,”我好奇地看着她,为了表示熟络而拍拍她的手背。
徐庆春的真名叫徐庆春,像是北方荒凉的万里晴空下噼噼啪啪响起的一串爆竹。
“你这么贤良的姑娘怎么就和顾惊云在一起了呢?”我半开玩笑地问起来。
“我当时和我寄宿家庭吵架,他们说中国人都是懒虫、败类,我一生气,就收拾了所有的行李搬出来,没有地方去,当时他正在追我,我用手机的最后一点电给他打了个电话,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徐庆春叹了一口气,有种心满意足的凄凉写在她脸上,“当时我拖着一大堆行李,在那种黑黑的小路上一直走、一直走,偶尔有辆车大开着灯轰隆隆地开过来,我就觉得我要死了,干脆一下撞死我吧。
然后我老公来了,把我接到他的车上,我当时觉得他就是神。
”她现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还是会跳动起来一种热切、一种心醉神迷。
“其实你也觉得我比他好是吧,哈哈,我得告诉他。
”她忽然高兴得像个未经世事的小姑娘。
“苏鹿你快来给我开门啊。
”有人在我家门口咚咚咚地敲着我的门,我知道是思瑶来了,她的声音真甜美,像是新鲜的牛奶一样四处流淌,我跑过去给她开门,她在门口用力踩了踩,留下些白色的残雪,然后裹着一身凉气冲进来,“——鹿鹿我饿了,你去给我找点吃的吧。
” “你进来吧,我给你做炸苹果吃。
”说不上是为什么,我每次看到她都是小心翼翼的。
像是上学的时候,老师给发下来一大摞崭新的A4纸,我不敢把它们放到书桌里,那么整齐、那么干净的白纸怎么能放到我乱成一团的书桌里呢,放到桌面上又怕被风吹散了,就只能捏在手里,直到角上被我捏出一个脏兮兮的指纹。
“你怎么和她聊上天了,”思瑶站在油腻腻的厨房中间,碎花的裙子,皮肤白得像是一个刚刚出炉的瓷器,把她放到这么凌乱污浊的厨房里简直不像话。
她的语气里是那种不屑的调子,“我就觉得她,像那种社会上的人。
”她自信地加重了语气,然后在厨房的桌台上发现了徐欣送来的那盒饭。
“天啊!苏鹿,你哪儿来的这东西,”她顺手抄起一双筷子,吃了块咖喱鸡,表情瞬间变得愉悦了,“下这么大雪,谁给你送来的?” “送你的,留级班有个人闲得没事儿做要锻炼身体。
”我把沾满面粉和奶酪的手往围裙上抹了抹,存心不想提起他的名字。
她却皱起眉头,压低声音,“是徐欣吧。
林梦溪和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她轻轻地翻了个白眼儿,“他没机会,想都别想。
” “是,”我用纸擦了擦手,然后拍拍她的头,“不喜欢他就别勉强自己。
” “不过,苏鹿,”她像是若有所思,从我的左侧绕到我的右侧来,轻轻的,妩媚地摇了一下腰肢,“你说,人家这大下雪天的,不远万里跑来给我送饭,我是不是不该这么铁石心肠?” “然后现在一定在网上发帖,把自己编造成一个悲壮的、凄凉的痴情人,大雪天去给人送饭却没等到一句谢谢。
”我对着那两坨饭扬了扬头,示意思瑶继续吃下去,“他那种人,不是喜欢你,就是喜欢那种默默忍受着的、飞蛾扑火的过程。
他自己觉得自己特了不起、特痴情,每次制造一个经典的浪漫场景,就等着台下的观众哗啦啦地响起掌声来。
”我把越南粉的盒子打开,哗啦啦地往碗里倒着红辣辣的汤,“我刚才只不过在网上艾特你一下,找你来我家一起玩儿。
还真是有点风吹草动他都能发现,吓得我都不敢更新微博了。
” “对了,你有他照片儿没,”思瑶安静地绕过来拉着我的手,“徐欣,我就只是听他们说过,好像在凯莱是个人物,挺有名的,但我在学校里还真没注意过这人。
” “凯莱的名气什么的我估计在语言班留级留多的都有吧,他长得像大猩猩,”我挑了满满一筷子的越南粉,忍不住地笑了,“要不要我给你搜大猩猩?” “不至于吧,我听说长得挺好看的呢,和冠希哥有点神似呢,”她忽然来了精神,打开我的电脑,就好像被推荐上了相亲节目似的,“有没有他空间啊?我要看他照片——” “大猩猩那种东西怎么会有照片呢,”我满嘴塞了泰国的辣酱味儿,“那种东西都是在热带雨林里荡来荡去的好不好——” “哈哈,你干吗不让我看,和女儿待字闺中的封建家长一样。
”思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着饭,“我寄宿家庭的妈妈今天加班去了,晚上又没回来。
”她的声音被饭塞得满满的,说话也含混不清了,“其实,我都不太敢来你家吃饭了,因为上次徐庆春说,来你家吃饭要交钱,我害怕她——” “哈哈,有叔叔在你还怕什么。
”我大笑着摸了一下她的头,“炸苹果,香蕉奶昔,还有冰箱里的饺子,这些吃的都是我们的。
你随便吃。
” “鹿鹿你对我真好,”她的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一样,“我有时候觉得,你要是个男的的话,我肯定和你在一起。
” “得了,你还是好好地等你的张伊泽吧。
”我从锅里把炸得金黄的苹果拿出来,那种香味匀称,浓郁,像是个裹着华美锦缎的贵妇人。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怎么就能那么喜欢他。
”手中的盘子因为炸苹果的重量而微微颤抖着。
“这哪儿是讲他的时候,”思瑶欢喜地用手捏了块苹果放到嘴里,“等一会儿我们睡觉了,躺在床上,我再给你讲——” 敲门声和着暴雪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我本来以为是顾惊云从外面喝酒回来了。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心里涌上来了这个句子,从小学课本上看到它就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寂静的苍凉。
我把盘子放下去开门,门外站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缩着手,轻轻地跺一跺脚,然后疲惫地朝我笑笑,好像他看到我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一样,外面纷飞的大雪黏在他的薄衬衣上,金丝边眼镜上,把他的表情衬得更加柔软。
很遗憾的是,我和这个隆重登场的人并没有发生一段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但是,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以一种相互保全的姿态荣辱与共,一同迎接了这个世界的轰然而至,泥石俱下,一同欢笑,悲哀,策马高歌,流离失所,甚至是,相依为命。
【林家鸿】,2013
第一次看到苏鹿的时候,她在给思瑶炸苹果,满屋子里都是温暖的,往四面八方溢出来的香气。我来还顾惊云的语法书,外面的雪太大太冷了,风不断地怒吼着,卷着雪花扑过来,像是发了毒誓要把你埋起来似的。
她开了门,屋子里明亮的灯光朝我毫无保留地漏下来,我看到她一瞬间被光芒点亮的,惊慌失措的神情,黑漆漆的眸子像雪地上的小鹿。
“进来吧,”她抿抿嘴,轻轻笑了一下,空空荡荡的客厅就变得春意盎然,“我刚炸了苹果,一起来吃点。
”她几步走进厨房去,给我留下个背影,那时她可能是因为初来乍到的缘故吧,连走路都有点小心翼翼,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给这个白蒙蒙的世界抹上一块鲜亮的颜色,就像静静躺在雪地上的一抹猩红。
“你也是刚来?”我咬着一块炸苹果问她,她那时候的样子我还记得,鬈鬈的头发搭在脸的两边,眉眼之间有那么种说不出来的英气,让她的轮廓好像是一刀一刀涂抹出来的冰。
她垂下眼睛点了点头,睫毛投下一大片淡青色的阴影,就像是沉睡的湖泊。
“怎么和他们住在一起啊?”我往楼上顾惊云和徐庆春的睡房扬了扬头,忍不住地问她。
顾惊云和徐庆春是有名的“凯莱狗男女”,在我们这个社区学校名声很坏,坑蒙拐骗无恶不作,顾惊云又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每分每秒都能寻到女子相陪,惹得徐庆春神经都绷成了一条钢丝,随时准备着破口大骂剑拔弩张,四弦一声如裂帛。
“室友和寄宿家庭吵架,把他们惹急了,限我们三天之内卷铺盖走人——”她就着水声洗着锅,几乎是兴致勃勃地讲道,“我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当真咬春饼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夜行歌紫微流年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仙君有劫黑猫白袜子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江湖人独孤红
- 虫屋金柜角
- 穿书后我爱上了蹭初恋热度清越流歌
- 射雕英雄传金庸
- 圣武星辰乱世狂刀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仙尊一失忆就变戏精哈哈儿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控制欲叙白瓷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鱼游入海西言
- 学长在上流麟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羞耻狼空
- 离心ABO林光曦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竹木狼马巫哲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嗨,保镖先生棠叶月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追随者疯子毛
- 猪肉铺与小精英沐旖乘舟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不息阿阮有酒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情敌五军
- 大叔,你好大江流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财神在身边金家懒洋洋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如何才能将目标勾引到手南柯良人
- 共同幻想ENERYS
- 新婚ABO白鹿
- 没完晚春寒
- 动物爱人魏丛良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男主今天翻车了吗吐泡泡的红鲤鱼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明明有颜却偏要靠厨艺青渊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