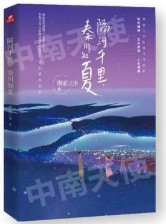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七章 大昭卷·三公(1/3)
三公者,素来两相一将。
此余与诸君皆无异议。
然则将星可为女子耶?孝武朝曾有例,女子一时掌三军。
余与晋阳令泽辩,泽曰一时之计,终成将星者乃武忠公芸也。
芸逝,天子泣于堂,三日不朝,由此可见一斑。
余笑言,女将纳后宫,安得复提。
泽不以为然,道皆妄言,武天子与女无私情。
泽素慕武朝,自与吾唇枪舌剑,然则,史辙早消,余与友不过野话一二,窥探圣朝事罢了,岂有定论耶? &mdash《野趣·说史篇》 十年前,平王找了相士算平境大运,那相士据说是前朝国师褚上人之子,文王卜卦极准,敲一敲龟壳,便知乾坤。
平王此人一生,便应了他的封号&ldquo平&rdquo,幼年不出彩地在王子堆里混着长大,封王的时候默默混在哥哥们身后,谁当天子都没他什么事儿,待到大婚,又娶了个不起眼的王妃,不出两年,安安稳稳地得了个儿子,虽然这个儿子生来瘦弱,太后太妃们看一眼便撂到脑后了,但平王还挺满意,至少是个男孩儿。
而平王世子渐渐长大,也同平王幼年时一样,混在一众秀美钟灵的王子中间,又开始了平淡无奇的一生。
相士晃晃龟壳,睁开一双晶亮的小眼睛,笑着说:&ldquo卦象好啊。
&rdquo平王眼睛都亮了。
如何好?莫非他有朝一日能成诸位王兄里最有钱、最受百姓喜爱如穆王一样的大贤王?莫非他哥哥的儿子一朝死完后他儿子有朝一日顺位继承当上皇帝,而他临老当个皇帝爹?莫非全天下的土地,有一半在某一年寸草不生,他哥哥一怒之下道,全给了平王吧?!平王想入非非,心肝直跳,问道:&ldquo怎么个好法?&rdquo 相士哈哈笑,&ldquo王爷大福,有生之年,平境都如今日一般太平。
&rdquo 平王瞬间两眼发花,挥挥手,蔫了起来。
那相士却捻着山羊胡,不肯走,迟疑道:&ldquo不过,大运之中倒有个小小的劫,不知当讲不当讲&hellip&hellip&rdquo 平王兴味索然,打着哈欠道:&ldquo先生但讲无妨。
横竖不过哪年又发了水,封地粮食又不够了&hellip&hellip&rdquo 相士断然打断他的话道:&ldquo并非如此简单。
依照卦象,平境倒像是要出女祸。
&rdquo &ldquo怎么个女祸?&rdquo平王眼睛亮了,生活已然如此索然,若是有个美貌的妲己、褒姒挠去他的心肝倒也不枉此生。
&ldquo似乎,似乎&hellip&hellip若无意外,贵宝地应是要出两个王妃,一个&hellip&hellip祸国殃民的皇后了。
&rdquo 平境共分三郡,东郡、澄江和金乌。
东郡为边境重兵把守之地,澄江以大昭第一淡水澄江为名,而金乌取名,则是因钦天监手册记载,此地为日头最圆最大,观日景最美之处,后才以&ldquo金乌&rdquo命名。
金乌与澄水接境,泛舟观日一向是文人骚客最喜好的,故而金乌一向人群熙攘。
高谈阔论、儒帽风流的是逛茶馆、妓楼的书生,沿街叫卖、粗衣油腔的是商户,缓缓悠哉、依柳而行的是马车中的公子闺秀,一身皂衣、呼来喝去的是衙吏,观形容,一切皆一目了然,泾渭分明。
只是最近一二年却来了一伙看不出道道的家伙,均是黑衣束发,手捧船只,行街叫嚷,似做买卖,句句&ldquo唯吾大道,素行封谨。
耻有遗漏,但凭随心。
无有穷富,无有名利。
如梦虚妄,皆可变当&rdquo。
如有人好奇上前,那些人手中捧着的极小极精致的船只便发出耀眼的金光,纤毫毕现的小小十六金窗扇扇璀璨摄人。
听说有富人嫌生活无趣,卖梦入金窗,说要换取人生至乐,三日后出来,便丧了斗志,不到一月,把万贯家财抛得干干净净,离家出走,不知去了何处。
又有贫穷书生,自小算命相士皆说是大贵之相,却命途多坎,考了十五次秀才仍未中,他素来爱说娶妻当娶郑光华,做官当为商李丞。
商鞅、李斯均是先朝赫赫有名的丞相,而郑光华则是当今贵妃郑氏堂妹,小小年纪便艳名远播,书生听闻可卖梦,便把此梦卖了,入了第八扇金窗,换取衣食无忧。
待他出来,果真不出半年,他便意外得了良田千顷,锦衣高楼,衣食无忧起来。
只是秀才依旧不中,郑光华也在年后堂兄郑祁封侯,郑氏权力达到巅峰时许配给了二皇子。
书生热衷算命,固执地认定自己当日入了金窗,棋高一着,复找相士算命,相士却叹息良久,并不言语,只是摇摇头。
自富人走了,书生阔了,那些黑衣人手中的小小金船益发显得神秘起来。
富贵人沉吟逡巡,不敢进,却又忍不住诱惑,穷人个个趋之若鹜。
不多时,金乌、澄江两境一夕巨富、一夕卖妻倒皆变得不甚稀奇了。
有好事的贼趁夜偷到过一只船,映着月光还没瞧出个细致明白,那金船便自己燃了,半晌,只留下余烬。
平王也听闻此事,与王妃嘀咕几句邪术之类,便无下文了。
他素来是个懒王,加之因算运道灰了心,封地的政事多半交给了世子成玖,自个儿游山玩水逍遥自在,自是不管谁富了,谁又穷了。
富户纳税,穷汉接济,税银不曾少,粮仓不曾多,也就罢了。
平王世子更是个懒人,便更不理了。
只是与他一起赌钱逛楚馆的几家纨绔公子不到半年却因此换了几茬,着实让人窝火。
&ldquo报!报&hellip&hellip世子,司徒公子来不了了,司徒老爷换了梦,莫名其妙把所有的铺子卖给旁人,带着公子走了。
&rdquo小太监擦了擦满头的汗。
成玖微笑着轻摇山河扇,捏着的酒杯却瞬间碎了。
环顾四周,寂寥无一人。
东郡边将章将军有一女,闺名咸之,芳龄十五,素来传闻美貌仙姿,见过的人无不愣神震惊,飘了手帕、摔了扇的算是正常反应。
金乌太守之女,小书呆恒春七八岁时曾见过章咸之一面,满口念着:&ldquo金屋可藏卿,芳草可饰卿,朱唇不必点,蒹葭何须念。
凤鸣到殷商,鸾鸟双周旋,心惊宜慢跳,寒冬似春暖。
复有万古念,丹心竟又迟,一日忽闻说,此为&hellip&hellip章咸之。
&rdquo魂不守舍地回到自个儿家中,嘟囔着便迷糊地发了热,辗转许久仍不好,有老人说怕是丢了魂,果真,竟抓了魂才好。
自此,章咸之美名更是传开了。
便是这样的章咸之,及笄之年,将军府的门槛显见得换了几十个,平王也含蓄地表达了要结两姓之好的美好意愿,可是将军却始终缄默不肯。
有得不到美人的世家子私下含恨道:&ldquo这美人难道心这样野,还真想去做个皇后吗?&rdquo 章咸之听闻,回道:&ldquo有何不可?才貌如斯,吾自己尚不忍糟蹋,又岂能便宜尔等庸俗无能之辈?咸之不止能做皇后,还可做元后。
此生若非元后,必镇守边关,报国为民。
&rdquo 此语,不可谓不狂妄。
平王听闻此言,想起先前相士的话,复又想起太子人品,倒也觉得是有几分实在的天作之合,便作罢了。
只是章咸之美貌、才名、霸气刚刚传到陛下耳朵里,太子却薨了。
如此一来,章咸之反倒益发嫁不出去了。
可她不大担心,章将军亦不大担心,父女俩安心守在东郡,翘首等着以文立国的东佾哪一日想不开拼了老命,空有一身好武艺的父女俩便好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报国了。
故而,章咸之那番话的最终解释,其实应是:我想当大昭第一个女将军。
只是,东佾还没来得及想不开,章咸之反倒先想不开了。
她做了一个梦,梦境十分真实。
梦中的她途中遇到一个快饿死的书生,给了那书生一块饼,转眼书生却成了权倾朝野的右相。
当朝本来已逝的太子诡异地未死,到她家来提亲,她见他一眼,魂飞魄散,几千万只白鸽齐齐从胸怀中散出,转眼,自己已经站在中宫殿中,昔日忍辱的太子成了天子。
皇帝陛下表面对她温和甜蜜,十年专宠,心中却冷淡无情,想要的只有父亲手中的一道阴兵令符。
恰逢东佾出兵大昭,父亲被任命为元帅,与东佾殊死抵抗,右相大人却弹劾父亲通敌卖国,意图谋反。
皇帝陛下毫不留情,下令满门抄斩。
父亲血溅白旗,她亲眼看着,尖叫出声,昏死过去。
醒来时,她已经身在冷宫,寒气逼人。
再过十年,一个从未见过的小太监却不知从何处拿出令牌,让她乔装成宫女,出了宫。
她刚走到城门,丧钟却响起,原来是右相大人病逝了。
小太监说:&ldquo右相大人当年,只能保您一人。
如今,也只能保您一人。
&rdquo 她道他为了一饭之恩,小太监却说,当年去提亲的,除了太子,还有右相。
转眼,皇帝陛下却已追到,居高临下,握着柄剑,抵在她的颈上。
他问她令符在何处,章咸之泪如泉涌,心中五味杂陈,&ldquo您究竟曾经喜欢过我吗?&rdquo 如若他曾喜欢过她,为了江山稳固,战功彪炳的父亲或许依她看来偶尔显得盛气凌人;可是,如若他只是口蜜腹剑,虚与委蛇,那她的父亲凭什么要忍受搭上满府六十三条人命的噩运? &ldquo不曾。
一分一毫一刻一时都不曾。
&rdquo皇帝陛下看着她,冷道,&ldquo既然不肯说,那就把这个秘密变成没有秘密。
&rdquo 鸳鸯共连理,结发为夫妻。
她想说,令符我早已给了你,可是,那剑尖渐渐穿透她的心脏,一切又归于沉寂。
她躺在虚茫一片的黑暗中,痛入骨髓,蜷缩成小小干瘪的一团,远处走来一个黄衣少女,看不清模样,却讽刺她道:&ldquo这回,你可瞧清楚了?章咸之,你记住,他不喜欢你,一分一毫一刻一时也不曾喜欢过你。
咸之,我将能借之物都借与你,你可能瞧得清晰?&rdquo 章咸之呼痛,却忽然睁开了眼,满脸汗泪。
她茫然看着闺阁之景,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是痛得哭都哭不出,握紧手,手背上的青筋暴了出来,转身,金架上的鹦鹉却摇头晃脑地念着恒春的诗:&ldquo一日忽闻说,此为&hellip&hellip章咸之。
&rdquo 大丫鬟跑来,莺声燕语,软玉温香,&ldquo娘子,有白衣少年来求亲,称自己为孤。
&rdquo 又有三两不成器的小丫头嬉笑低语:&ldquo门外有个书生,中了暑,倒在了我们家前。
&rdquo 时间:齐明十一年六月初六丑时一刻。
地点:赤水源头襄河一座破船坞上。
人物:四个沉睡书生,一个渔夫,外带一个丑布偶。
事件:黑稠不见五指的河水中,有一样东西正在悄无声息地往上爬。
爬着爬着,眼珠子掉了,爬着爬着,半截胳膊甩开了。
它爬呀爬,爬呀爬,终于爬到了船头,巍巍颤颤地站了起来,不小心被木槛绊了一跤,一个趔趄,胳膊又甩掉半只。
腥臭味瞬间弥漫了整个船坞,书生们靠着书篓睡得很熟,此起彼伏地交换空气,懵然无知,有一个似乎还做了美梦,笑得脸都起了褶子。
那东西摸黑拾到了眼睛和胳膊,又安了回去,而后使劲吸了一口气,它似乎闻到了好闻的气息,缓缓而僵硬地扭了扭脑袋,正对着月光的,是一张腐烂了一半的脸庞。
这是一只水鬼,俨然上岸来拉人了。
它躬下了身子,凑到一个眉目平凡的书生胸前,狠狠愉悦地吸了口气,悄无声息地咧开了腥臭乌黑的大嘴,哈喇子瞬间滴在了少年的布衣之上。
那少年歪在一侧,依旧没有发现,千钧一发之际,只见说时迟那时快,他背后靠着的几乎变形的书篓里却腾地蹦出来一个小东西,双手叉腰,气焰嚣张,前空翻,后空翻,鲤鱼打挺连环踢。
水鬼看愣了。
小东西却瞬间抓住了水鬼脸上的一块烂肉,打了个提溜,一个猛扑,水鬼未料到它有这样的气力,一个趔趄,扑通倒回了水里。
一声巨响,这群差点做了水鬼的书生们终于有了些微知觉。
年轻的船夫匆忙跑了进来,一一推醒众人,道:&ldquo了不得,公子们,快醒醒,水魑来抓替身了。
&rdquo &ldquo啥?啥玩意儿?&rdquo船坞中间,唯一一个华服少年跳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ldquo船家,你老母!不是说这条河最太平?!&rdquo 与他相邻的另一个满身补丁的贫衣少年擦了擦口水,温和道:&ldquo怎见得就是水魑呢?水魑又是谁取的名,可是俗称的水鬼?我只听见了咕咚声,若是取名,也该叫&lsquo咕咚&rsquo才是啊。
再者,你这样惊慌失措地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水鬼,难不成这水鬼是船家养的?不然怎的它一来你就知晓了?&rdquo 船家快哭了。
他又去摇靠在船头的一身黑衣的书生,可是书生却迟迟不醒。
他哆哆嗦嗦地伸出了手,这人却全无鼻息。
船家三魂没了七魄,号丧道:&ldquo了不得了,这小公子果真被水魑勾了魂,如今船上死了人,可怎生是好?&rdquo 船尾一直靠着书篓的扶苏迷迷糊糊地伸手到背后篓中摸了一阵,却瞬间坐起了身,脑子空白了一瞬,努力忍住一丝欢喜,没有表情地瞪着船夫道:&ldquo了不得了,我媳妇呢?谁偷了我的人?船家你偷人了!&rdquo 船家声泪俱下。
船头,没了呼吸的黑衣少年脚下的水面却缓缓浮现出一个一身麻衣,梳着东倒西歪的包子头的布偶。
本已在睡梦中悄无声息死了的黑衣书生闭着目,却伸出了苍白嶙峋的手,伸入了冰冷的水中。
许久,黑衣书生睁开了眼,仿似久病的阴冷面庞上挂了一丝不显的讽刺,食指与中指捏起一个湿漉漉的丑娃娃,虚弱地问道:&ldquo谁家的丑妇人不要了?莫要脏了一池水。
&rdquo 事件结果:扶苏莫名其妙多了三个结义兄弟,一个姓章,一个姓黄,一个姓嬴。
姓章的是个姑娘假扮的,生得千万般美貌,瓢子却跟成芸一样,粗鲁暴躁,一手推倒一个成年壮汉,大家都看出她是个女的,却老实地闭了嘴。
姓黄的是个啰唆得没了边儿的少年,心眼多得像蜂窝,有些被害妄想症。
任何一件事让他去想,他总能得出两种结论:一是除了他的旁人都是坏人,二是所有人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陷害他。
虽动不动就爱脸红,但请相信,这只是天生的,与脸皮厚薄无关。
至于姓嬴的则是一身黑色长袍,连儒帽也是黑的,随身背着药炉,整天阴森森病恹恹地靠在船头,一副下一刻就要病死的模样,对谁都没好脸,与扶苏的没有表情虽无限近似实则大不相同,扶苏的没难度,这个难度大。
总结起来,章小公子是别人都不如他,黄小公子是别人又欠了他,嬴小公子是别人别靠近他,扶苏,扶苏则是别人别&hellip&hellip发现他。
齐明十一年的六月初六,公子扶苏觉得这一天是他自从认识了丑妖怪奚山君之后的那些穷日子中,最别致的一天。
特异美貌的章公子挺爱拍人肩,似乎是种与人见礼的方式。
大半夜遭了水鬼之后,烛光荡漾中,这个诡异的少年从船头拍到了船尾,从左肩拍到了右膀。
拍黄公子的时候,他先是不敢置信,再万种惊喜,拍嬴晏的时候,他一头雾水外加肃然起敬,拍扶苏的时候,他本来心不在焉,谁知拍完左肩,章小爷的脸比上好的绢纸都白,再拍右肩,踉跄了好几步,勉强稳住脚步,挂了个极勉强的笑脸道:&ldquo弟闻听各位公子皆欲往昌泓山求学,既然有缘聚于此处,日后又是同窗,不如以天地为敬,结为异姓兄弟吧。
&rdquo 来了,来了,终于来了。
另外三个少年都在心底叹了一口气。
他们基本可以确定眼前的美貌公子是个女人了,而且基本确认,自己可能被讹上了。
不怪少年们这么想。
最近六十年来,不知从哪位姑娘带出的风气,女扮男装上学还是挺流行的,爹娘送去的还都是一等的书院,就指着姑娘们自个儿争气,挑出个金龟婿来,把户籍迁到大国去。
为什么?因为诸侯国太多了。
什么?诸侯国多又怎么了?昭天子虽不欢喜,但各国诸侯皆私下有令,除士人外,国与国不通婚。
也就是说,在户籍制度森严,各国地盘又太小的情况下,这就好比一个窝里的老鼠只能自行婚配,就算母的富余了,一公多母,也绝对不能便宜别家的公老鼠。
于是,凭什么呀,好不容易生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不去配别国英俊富强的男儿郎,还要配隔壁邻居抠脚的大汉吗?所以,家中生了姑娘的,但凡爹娘家族有一点资本,也要把姑娘推到大国书院去,不为别的,就为挑个大国的士人女婿,日后高中了,好提携家族,摆脱贱籍。
既然国君不仁,做了初一,那就休怪庶民做这十五了。
大昭建国三百余年,如今民风已十分彪悍。
各国互相封闭,除了边界走商,使者互访,民间极少互通信息,姑娘们也就不大顾忌什么名声了,就算在外面闹个不好看,可回自个儿家,关了门,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规矩,那是给贵族女子守的。
庶民女子要想改命,除了卖梦,只有嫁人这一途径了。
这些日子,家中有预备出仕的少年郎的贵族家庭都闻书院色变,有些古板的,情愿孩子在家中自读,也不肯让他们出去,被几个不知所谓的庶民贱货移了性情。
姑娘们女扮男装的手段登峰造极,有些书院严格测验了,也不免漏了几尾鱼。
而少年们之所以判断眼前的美貌儿郎是女子,是因为,据说女扮男装的姑娘们,酷爱与人结拜。
这不,他们只是坐个船,躲个雨,就已经被她瞄上,非说有缘,非要结拜。
扶苏并未出声,不动声色地等着,可是那三人都是来回地试探发招,留给少年的也就是一个后脑勺。
扶苏扭头,清水中荡漾的是一张平凡木讷的面庞,霎时间觉得,自己大概是自作多情了。
扶苏用了奉娘给的人皮,换了个脸和名字,如今叫姬谷。
这张脸不好看也不精明,反倒显得有些粗糙,那些眼高于顶的姑娘是瞧不上的。
这姑娘说要与自己结拜也许只是捎带,只为了让场面看起来更圆融。
他媳妇年后突发慈悲,扔给他一个包袱,说为了响应天上人间养童养婿的主要目的,本着不悔夫婿觅封侯的原则,让他去平国孙大家处求学。
扶苏觉得她想当皇后想疯了,可是听说孙大家家中的藏书可比拟大国,他乖觉地闭了嘴。
临行时这妖怪给他绣了个一模一样的自己,丑得令人发指,还一直慈祥地说想家了就看看娃娃,她就是娃娃,娃娃就是她。
换言之,如果娃娃被他怎么着了,奚山君必然十倍百倍地对他怎么着。
扶苏多想扔了这镇宅利器。
任谁家长大的公子都不爱这玩意儿。
扶苏面无表情,但神游天外,回过神时,三人已经拍板决定,结拜了。
没人问他的意见,扶苏也没什么意见,因为这三个人没一个是吃素好惹的,此时说要结拜只是各怀鬼胎,他懒得得罪他们,只是决定以后渐渐避开他们。
上岸休整时,破庙外,一人扯了一条柳枝,大半夜的,月亮白得瘆人,四滴鲜红的血溶到了一个破碗盛的烈酒中。
&ldquo天极为约,太一明誓,紫宫订盟,末星为鉴,吾四人今日结为兄弟,血脉共溶,心形相一,互敬互爱,永不相害。
&rdquo章姓少年如是震天吼,咕咚咽了口血酒,眼睛却直直瞪着扶苏。
黄姓书生小脸红扑扑的,微笑道:&ldquo弟十七,诸位孰为长兄?&rdquo 章少年似乎挺待见黄书生,眉眼一荡,漾出些美色道:&ldquo兄十八。
&rdquo 嬴晏虚弱地咳道:&ldquo十九。
&rdquo 扶苏面无表情,大言不惭:&ldquo我为长兄,今及冠。
&rdquo 公子扶苏这一年满打满算,刚过十七岁的生日。
这世间,有些人坏得很出色,比如成觉,也有些人,坏得不出挑,坏的目的只是为了愉悦自己,比如扶苏。
四人论了兄弟齿序,彼此见了礼,从长兄到四弟,依次是姬谷、嬴晏、章甘、黄韵。
他们皆未行冠礼,均无表字,便只以兄弟排序互称。
扶苏垂目,却听见黄四郎低缓温柔道:&ldquo弟素来不信那些空话,既然诸兄长都喝了血酒,日后若违今日盟,残害了彼此,便叫哥哥们遭五马分尸、曝晒吊颅之刑,如何?&rdquo 这是伍子胥的死法。
扶苏听着不对劲。
哦,敢情就他们三个当哥哥的得发誓,谁害他谁当伍大帅。
这人瞧着倒一脸温柔,脸红着都能给人下套。
嬴晏久病苍白的脸上显得很沉默,但许久之后,他点头应允了。
章甘啐了口唾沫,热血沸腾地瞪着扶苏道:&ldquo对,叫那等小人遭天打雷劈,死无全尸!&rdquo 扶苏淡淡笑了,喝了口血酒,拍了拍蓝袖上的尘土,拱手道:&ldquo既已结拜,本欲与诸弟在船中畅饮一番,奈何我囊中除了束脩,已无余钱,只得步行去孙大家处,如此,兄便先行一步了。
&rdquo 他面貌平庸,举止却是说不出的烟云水汽,风流高士。
他背起书篓,便要扬长而去,谁知篓中的布娃娃却瞬间卡在了庙门外的香炉口,死活拔不出来。
这最后一点洒脱的姿态便破坏殆尽了。
少年无奈地望着在香炉中头脚拉扯笑得一脸张扬无耻的布娃娃,觉得妖女的妖法无处不在,让这样一个他,原本大可以清淡婉约一些的公子在此处,看着三人脸上灿烂的笑意,也不禁带了些怒火。
他想这真是世间最可恶的妖女,脸颊却微微带了红,那吊在布娃娃颈上的绳结却绞着香炉,更紧。
黄四郎看着那娃娃,微笑道:&ldquo隐约听闻兄长是有妻室的,这娃娃与我那未曾谋面的嫂嫂有何关联?&rdquo 章甘狐疑地看着自己的左手。
她摸到过去时为何没摸到此等变故?她&hellip&hellip不是他的元妻吗? 扶苏梗了下,回头解下娃娃,握在手心,手指把娃娃的包子脸捏得益发丑,嗓音清冷,&ldquo是有一房妻室,生得貌美如花,静如处子,真真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从不上房揭瓦,与日月争着发亮。
&rdquo 孙大家名湖,字泽堂,孙武后人,乐安人氏。
昭文帝之后,举族搬迁至平国金乌昌泓山,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世代靠开书院为生。
之前的几代夫子资质平庸,教出来的弟子也平庸,如今的孙夫子是瞧着平庸,挑选的弟子也皆是落魄世家弟子,可是,组合的结果却不是平庸,而是逆天。
当先帝手下尚书阁誊录二十年中了文武榜的三甲出身时,平国昌泓书院竟占了足足三十人。
平国虽地方富足,却是个十足的小国,教育不兴,一国能中十人都属运气,更何况一郡一山,中了三十人。
百国都震惊了,纷纷打听孙湖是何人。
可是,除了知道此人是孙武后人外,旁的一概似是无什么过人之处的。
众人皆以为是偶然。
可是三年后,他又举了三十文武进士,十五文,十五武,不多不少。
孙湖弟子出身寒微,反而能使先帝放心去用,他的弟子有一处特色,便是文武兼备,虽个个达不到顶尖执牛耳之界,也即是无出将入相,拜三公之才,但文者颇识行军连纵之法,武者皆具治国入微之目,真宗十分赞赏。
到了哲宗朝,孙湖已成了教育界的一块活招牌,士子们哭着闹着要去瞻仰当世孔夫子,生得好的、家世好的却憋了一肚子火,他娘的不收不收还是不收!莫非穷的、落魄的调教出来特别有滋味?口味也忒重! 扶苏与嬴、章、黄三人是一起到的。
那三人坚持非与结拜兄长一起步行前往,这一路,倒也摸清了彼此底细。
扶苏自称是战国时晋国没落贵族姬氏五世孙,手中的名帖和推荐信一应俱全;嬴晏则是孤儿,前朝嬴氏一族叛乱,九族皆被云相处斩,只余下一痴儿。
行刑时云琅曾言,嬴族逃不过三代,三代之后,若不亡,人人得而诛之。
而嬴晏便是这痴儿的后人,到他处,已传了三代。
他来平国本意含糊,似是并非一开始便欲往书院读书,而是为了寻人,不知为何,最后却变了主意;至于章甘,只说是世家后人,却未说明是哪一家,姓章的世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有名堂的便是那么三家,一是凤阳章氏,二是崔城章氏,三便是秦帅弟子,抚东将军章氏,众人依他来时方向,猜测可能是凤阳与抚东两家中的一家;而黄韵黄四郎,形容十分贫寒,面容温和,性格却冷辣多谋,他不掩来意,求学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朝一日效仿先祖登上三公之位,至于他的先祖是谁,扶苏在脑中想了半天,从西周太公开始数,也没数着姓黄的。
孙夫子孙湖是个中等身材,不大起眼的男子,虽似貌不惊人,眼睛却十分明亮,他考校学生,不选文,不比武,十分简单明了&mdash自报家门,然后从远处的接待学生的草庐处,走到孙夫子喝茶纳凉的地方便可。
许多贵族子弟仰慕孙湖,也曾穿寒衣,造假名,可是,孙夫子老眼毒辣,扫一扫便瞧出了。
看着又一个垂头丧气被扫下来的璟郡王氏子孙,章甘有些抓耳挠腮,&ldquo他怎么就瞧出来了?!这人一身衣裳比乞丐还破,瞧着也无什么世家气度!&rdquo 黄韵含笑不语,嬴晏默默无语,扶苏神游天外。
前头的人被刷了一大半,还有一个抱着孙夫子的腿,撕心裂肺地哭道:&ldquo夫子,俺真穷,俺家真穷啊!&rdquo 孙夫子淡定道:&ldquo不,你是贵族后代。
&rdquo 章甘在远处树荫下跳了起来,骂道:&ldquo扯他娘的淡!这人我可注意观察了,手上满是厚厚的茧,若非家中贫寒,哪能生出这许多?&rdquo 黄韵继续含笑不语,嬴晏继续默默无语,扶苏继续神游天外。
终于到了最后,轮到兄弟四人了。
孙湖考校得也有点不耐烦,对着紫砂壶嘴,灌了口茶水道:&ldquo树下那四儿,一起来。
&rdquo 章甘一路走得战战兢兢,转眼看那三兄弟,没心没肺,一个比一个衣带飘飘,一个赛一个步履胜仙。
孙夫子瞟也没瞟四人一眼,问道:&ldquo让我选儿,儿有何处过人?&rdquo 章甘舒了口气,自信地露出雪白的牙齿道:&ldquo我生得俊,见过我的人都说,这世上,能与我一较高下的,只有穆王世子觉。
&rdquo 一身破衣,到哪儿都背着馒头的黄韵笑道:&ldquo我家贫。
&rdquo 一身黑袍,到哪儿都背着药罐的嬴晏默道:&ldquo我病弱。
&rdquo 一双蓝袖,到哪儿都背着媳妇儿的扶苏淡道:&ldquo我脸皮厚。
&rdquo 孙夫子依旧未抬头,瞧着莹润秀致的壶身道:&ldquo还有呢?&rdquo 章甘腾地从背后抽出一把亮【花,霏,雪,整,理]闪闪的宝剑,上蹿下跳,飞花乱舞道:&ldquo先生,我武艺高强,从小到大,就没人是我的对手。
我能徒手劈倒碗口粗的树呢,可厉害啦!&rdquo 黄韵道:&ldquo我家贫。
&rdquo 嬴晏道:&ldquo我病弱。
&rdquo 扶苏道:&ldquo我脸皮厚。
&rdquo 孙夫子挑眉,&ldquo没有别的了?&rdquo 章甘挺直胸膛,双手背在身后,笑出酒窝道:&ldquo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给您背段书吧。
我会背全本的《诗经》,外加《战国策》和《昭书》呢。
&rdquo然后,她摇头晃脑地背了小半个时辰。
黄韵道:&ldquo我穷。
&rdquo 嬴晏道:&ldquo我病。
&rdquo 扶苏道:&ldquo我&hellip&hellip&rdquo 孙夫子抬眼,打断扶苏的话,啼笑皆非道:&ldquo我知道你脸皮厚。
&rdquo而后,他抬头扫了四人一眼,指了指章甘,章甘的眼睛瞬间亮了,夫子却道:&ldquo你走,他们三人留下。
&rdquo 章甘愣了,这载歌载舞半天,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敢情他娘的谁脸皮厚谁才招人爱啊。
&ldquo为什么?&rdquo少年章愤怒了,咆哮了。
孙夫子打了个哈欠,道:&ldquo你自己心里清楚。
&rdquo 少年章咬牙,心中道:我清楚你祖母个爪儿!可想起什么,他浑身一激灵,随后从行李中扒出一张纸,恭恭敬敬道:&ldquo这是一位贵人让学生给您的。
&rdquo 孙湖看完却脸色大变,站起身,冷硬道:&ldquo我今日碍于他的情面,只得将你留下,但儿在书院中需洁身自好,好自为之!贵人瞧中了什么,你比我清楚!&rdquo 孙湖半旬以来,陆陆续续从一千多名子弟中挑出了三十人,便封了昌泓山。
学堂中右挂李子像,左挂孔丘图,中间还有一卷栩栩如生、高宽皆约三尺的孙武像。
三十名学子来自百国,穿着一样的云水鹤衫,拈了三炷香,拜祭了祖师,这才在后舍分配了房间。
扶苏与嬴晏一间,黄韵与章甘较走运,一人分到了一间较小的房。
黄韵家中特别贫寒,恩师孙泽堂便命他定时去山下做采买或做些琐碎的零活充当束脩,作息与诸位师兄弟并不相同,故而给他单分了一间屋子。
至于生得极俊的章甘,因他力气十分大,众人倒也未往她是个姑娘处考量,只想恩师兴许特别看重他,才另辟一间屋子与他。
章甘实在想不明白,&ldquo为何兄长们同四弟那样浑不吝的回答,反倒选上了,而我表现这样齐整,却不得人心呢?&rdquo 扶苏淡淡看她一眼,并不回答。
他面容平凡木讷,只一双眼睛十分清澈孤艳,让人看了未免脸热。
黄韵笑了,道:&ldquo我与哥哥们都瞧出了,孙大家选人并非按照贫富去选的。
过往说他只选贫家子,应该只是巧合罢了。
他老人家实是个十分任性的人,一切其实全凭眼缘,任凭王孙贵胄还是贫民乞丐,他瞧不上的如何都不会选,所以,我们又何必讨好他而去庸人自扰呢?只要坦率地告诉他我等是怎样的人,所求何物便足够了。
至于他愿不愿意给,就看他想要什么样的弟子了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泠泠听春雨(1v1 h)卷心菜
- 她是耽美文校花女配奶绿不绿
- 白月光拒绝渣攻求复合君九少
- 我能看穿诡异附身大侠戴草帽
- 大乾废太子,皇帝跪求别造反凌御天下
- 你走丢之后大学习象
- 装A可耻[娱乐圈]游衷
- 我,全能软饭王,被总裁老婆曝光了萨芬
- 疯了吧,校花给我生了三个娃雪中龙骑
- 重回84小渔村笔落云风清
- 小王的彩票人生尹木
- 娱乐:心动爆词条,姐你太主动了满血狐狸
- 我真没有画你的春宫一个珍惜xp的小女孩
- [综漫]混乱(NP)诉与青山
- 采薇(产乳 NPH)霍饭饭
- 雍正女儿续命日常[清穿]拙元
- 清穿之四福晋只想种田蒹葭是草
- 隐风铃望山晚舟
- 作为武者,会点仙术很正常吧!凌谟
- 年代:重生1958山之北水之南
- 全球SSS级警告,龙神出狱了!莫语听风吟
- 我的同学是兵王与泉
- 列克星敦号舰队指挥官太平洋萌新
- 亮剑:背靠未来,打造最强中械师月落乌辰
- 剑逆乾坤柳暗船
- 重回84小渔村笔落云风清
- 我!系统!懂?!云月六年
- 重生1980:从万元户到商业帝国春风笑我
- 玉桐【np】森木火火人
- 拾花录(1v2 双舅舅 禁忌)来次熊抱
- 顶级暴徒(法案之后)water
- 袚灾祛秽【蛇X人,兄弟3PH】城南大蘑菇
- 至尊獵艷路山河炙热
- 小公主nph绵橙她
- 炽焰(骨科 校园 1V1)鹿灵子
- 快穿之病娇反派llllx
- 一九九八愚礼
- 长恨书(古言 先婚后爱)柳边
- ?盛肉不颠勺
- 绑定系统后我操服女明星(简体高H)想做。
- 请把脊骨雕成我的王座(高H、NP)妃子笑
- 风象能别谈恋爱吗?(强制 np ntr)边原小玫
- 戒不掉她的手面具
- 野蛮行止(高h 囚禁)大蛋黑猫狸
- 亮剑:背靠未来,打造最强中械师月落乌辰
- 【权游】太阳之下绯星
- 小时了了(兄妹)thelittlefool
- 厮混愚礼
- 爱的关键词土笋冻
- 予你独钟愚礼
![领主沉迷搞基建[穿书]](https://www.nothong.com/img/4935.jpg)
![非典型求生欲[快穿]](https://www.nothong.com/img/4262.jpg)


![如何成为白月光[快穿]](https://www.nothong.com/img/10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