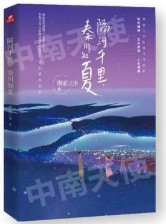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六章 奚山卷·青城(3/3)
着一朵荷花。
她蓦地流了许多鼻血,血液顺着手心滴在了那朵荷花的根茎上。
她颤抖着把那朵花递给了岸上的少年,似乎很久很久以前,他离开她时,也是这样大的年纪。
她声音嘶哑,酸涩得五脏都快要挤出来,&ldquo荷称君子,吾见汝端明秀雅,赠君此株,聊表寸心。
&rdquo 原本,这是一段太正经、太合乎话本的邂逅,忍冬想起时,都几乎被自己感动了,这辈子,说出这么一番文雅端方的话,也并不那么容易,可是,荷花中却羞答答地露出一只绿肥绿肥的毛毛虫,被雨水砸得一哆嗦,爬到了云琅的虎口上。
云琅蜷手握住了毛毛虫,斯文有礼地说:&ldquo谢殿下,臣很喜欢。
&rdquo他带着毛毛虫走了,忍冬和手里的荷花一起发呆。
这样一段往事依旧无法解释她喜欢他的缘故,可是却足够回答成泠的问题。
&ldquo他是我的心上人,这才是他做对的唯一的一件事。
你瞧他不过如此,可是在我眼中,他却是天地至美。
而天地至美,本无常主。
所以,他迟迟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rdquo 二十八岁的时候,忍冬的生命中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她的父亲死了。
第二件,她变成了帝国的大长公主,她的嫡亲兄弟继位了,年号胜文,称景宗。
而第三件,西突厥攻打大昭,战火连绵,满朝哗然,小将秦鼎崭露头角,请战西突厥,云琅作为监军,跟随到了战场之上。
朝中理宗时期的老臣一直瞧云琅不顺眼,新帝践祚,政局未稳,短期之内,本应求和,可云琅却力排众议,带着秦鼎和十万将士去了战场。
与西突厥交火的前三战,云琅都输了。
被先帝架空了权力的一众老臣趁机挑拨,景宗性子绵软,便疑了三分。
当时国内舆论,儒生、道徒压倒性地在骂云琅:&ldquo黄毛小儿,不堪大任,急功近利,不啻叛国之徒。
&rdquo 忍冬走到外城,时人纷纷骂云琅,奸相卖国之说络绎不绝。
傍晚回府之时,陛下已命人查抄了相府,撤了云琅之职,命边塞守将秋大林羁押云琅回京。
相府中,值钱的统共只有五件衣裳和几串铜钱。
如此寒酸的三公,世所罕见。
众臣却叫嚣道:&ldquo云琅定是携了家产而逃,本就预备借突厥之乱谋反。
&rdquo 一时间,众志成城,积毁销骨,云琅的三件常服和两套朝服摆在太极殿之上,就等景宗下定决心,一把火烧毁。
忍冬戴上她的青鸾冠,穿着那身绣着太阳和乌鸟的青黑直裾朝服,走到自己的弟弟面前时,这个年轻的天子笑了。
他说:&ldquo皇姐来得正巧,云相此人不可信。
朝中一心,今设祭礼,来日定除此乱臣贼子。
&rdquo 忍冬也笑了。
她站得那样挺拔,少年时的碎发现在都变成了柔顺漆黑的发丝,它们不再乱跑,安安静静的。
她抱着那叠薪柴之上的衣裳,朗声道:&ldquo陛下,臣心中有惑,还请陛下解惑。
&rdquo 天子与青城是亲姐弟,心中虽不悦她此刻出现,却挂着笑敷衍道:&ldquo皇姐但说无妨。
&rdquo 青城抬起了头,&ldquo依照诸大人所言,云琅此人,定然狡诈坚毅非常。
他五岁通读百经,六岁中童生,七岁拜入太傅门,八岁研习帝师术,垂髫辩输三大儒,十岁连中小三元,十三初入帝王门,年弱而无加薪爵,十六终于跃龙居,矢志不做三国婿。
尚书阁中理政事,东方既白仍未眠。
为官曾有千斗俸,养活万家贫儿郎。
朝中三十中郎将,云相哺育十之八。
三届状元探花郎,见之皆敬为恩师。
黄洛两水决百年,狡儿六载千秋业。
蜀陇旱涝常年灾,王君寝食皆不安。
云氏定得疏水法,粮供流民仍有余。
一朝战火烽烟起,转脸便做叛国郎。
仁君忍弃学士恩,门生尽唾上师衣。
&ldquo众君既然皆有将相才,今日羞辱云琅之时口舌朗朗,昨日敌入家门,为何充耳不闻,满朝缩头?他自幼如此聪颖坚毅,世所罕见,为何先帝驾崩时不趁乱举事,反倒如今才兴窃国之心?臣实在糊涂至极,还望陛下解惑,究竟是云白石的心太善变,还是陛下和大人们太过明察秋毫?&rdquo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朝中济济满堂,却忽然都安静了。
老臣涨红了脸,指着青城骂道:&ldquo女子何故上朝堂?牝鸡司晨者,陛下岂可听耳!她来此,不顾廉耻,是为了自己的情郎,诸君,莫要被她哄骗了!&rdquo 天子挥了挥手,咬牙道:&ldquo皇姐退下,寡人可宽恕你犯君之罪,但尔终不可为了私情,让忠君之臣寒心。
&rdquo 青城又笑了,她的笑容好似一层薄薄云气挡不住的热烈朝阳,眼睛明亮放肆得惊人。
她说:&ldquo天下万民皆知,云琅是我青城心心念念的情郎。
吾与情郎心意相通,他平生知己只我一人,他是我,我也是他,尔等今日烧他衣衫,不过懦夫行径,何妨烧了我这三国之主泄愤?&rdquo 景宗的脸色变了,怒斥道:&ldquo皇姐,莫要儿戏!&rdquo 青城却变了颜色,冷笑而似不惧身后刀枪剑戟、千军万马,掷地有声道:&ldquo他们若是忠君之臣,我便坦然做奸佞之君,又何其欢喜!今日我烧己身为云琅辩白,若从头至尾未曾发声,足见吾心之坚忍同云相之诚,只愿陛下再宽限云琅十日,十日之内,云琅倘使未大捷,陛下再作处置如何?&rdquo 青城从侍卫手中夺过火把,站在薪柴之上,闭上了眼睛。
太极殿上,火焰轰然燃起的时候,所有人的脸庞都被那明亮灼痛了。
他们都说他们从未瞧过这样胆大妄为,这样大逆不道,这样不识好歹,这样&hellip&hellip痴情的女子。
云琅的门生似有触动,心中惭愧,哭倒在一殿之上。
&ldquo皇姐!&rdquo年轻的天子惊呆了,他瞧着橘红嚣张的火焰蹿上了姐姐的朝服,喉咙梗了半晌,才颤抖道,&ldquo何至于此,何至于此!&rdquo 可是,他终究没有下旨救火。
天子握紧了拳。
众人看着火焰中眉毛也被燃着的忍冬,都不忍地闭上了目。
忍冬觉得很痛。
她咬紧了自己的牙齿,努力让自己忽略这种痛。
她抱着那叠衣服,缓缓地把它们攥在自己的胸口之上,却想起了云琅的拥抱,心中酸涩得很想哭。
火苗缠上她的手指和那叠衣服时,烈火中,所有的东西都模糊了。
她那样想念他的拥抱,怀念得如同那些辛苦茹素的日子瞧见糯米肉的一瞬间。
她知道,他必定曾经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时候,抱她入怀,那样珍重,那样怜爱。
那或许是他们的前世,只有她记得的前世。
人说讲虚妄之事是因无知,只有忍冬知道,她划定了一个虚无的前世,只是因为,太想得到。
当烈火烧遍她的全身,她想,她确定,她上辈子欠了云琅,只是,从未想过,欠他这样多。
忍冬不知,自己竟还能活着,可是,当她睁开眼时,人间已经变了天。
她昏迷了不知多久,听说,云琅在那十日之内大败突厥元帅忽而朗,之前三战皆败不过是诱敌深入之计,如今早已战胜回朝,听说,她的母亲庆德太后对天子极度不满,听说,听说&hellip&hellip青城殿下已然薨逝。
忍冬被母亲接到了身边,保护了起来。
她住在侧殿一个小小的院子中,孤独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辰。
直到她三十三岁的时候,她的弟弟景宗听说因为行事不当,被太后怒斥,次日,百国诸侯便联名上书,希望天子退位。
云相退朝,闭门不理此事,无论诸王谁请,一概不纳。
再后来,又过了些日子,听说她的弟弟病逝了。
新一任天子,是她的侄儿,景宗的嫡子成汕,人称真宗。
她若还&ldquo活&rdquo着,恐怕已成&ldquo长又长公主&rdquo。
太皇太后娘娘宫中没有铜镜,是一件世人皆知的事。
如同太液池畔的双柳墓,竟然因为当今的帝后邂逅于斯,如今已经成了天下万民心中有名的姻缘圣地。
这个载着她那样绝望的爱恋和不堪的少年时光的曾经,就这样,随着她的死亡,也渐渐逝去了。
她的母亲垂垂老矣,抚摸着她的面庞,流泪道:&ldquo我儿若颜色如故,此时想必也已生了皱纹。
&rdquo 忍冬少年时就一直闯祸,一把年纪才肯消停了。
她一直觉得她爹是不世出的明君,她娘是史册排名前三的贤后,从他们忍了她这么久,从没有亲手宰了她,就可见一斑。
忍冬挺沮丧的,自己这么个鬼模样,烧焦得连皱纹都不长,那些曾经有过的,只有公主殿下才有的霸道和单纯,似乎早已随着恭桶倒进了粪坑。
她喜欢云琅的第十五年,已经足足有五年没见过她的情郎。
她知道云琅也许没有忘记自己,因为她为他争取的十天就这样变成了一辈子。
可是,依照云琅素来的模样,没有忘记也仅仅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忘记。
太皇太后去世了。
国丧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太后,也就是她的弟媳带着三尺白绫来了。
她恨了自己很久,如果不是自己这个长姐,也许到现在,她还是皇后,而非太后。
忍冬觉得人虽固有一死,但他娘的绝不是这个死法。
所以,忍冬带着金银珠宝,很大气地从老娘给她准备的地道逃跑了。
外头的人间终究是太平了,比五年前的人心颓靡不知好了多少。
她隐姓埋名,置办了宅子,又喜气洋洋地做了云相的邻居。
第一日,她命人给云相府送了一把热情洋溢的菠菜,重新调戏到心上人,她乐不可支。
第二日,她又命人送了一把新采的粗绿野草,想起云琅那张困惑无奈的脸,忍冬窝在椅上十分开心。
她很喜欢读些志异怪闻,但是自从被火烧了,眼睛便不大好使了,命账房先生念了几段,终觉有些不是味道,便作罢了。
夏日的黄昏,漫天的橙红云霭,染了整个院落。
黑暗之前最后的光明让人那样眷恋。
昏昏欲睡的忍冬似乎是惊怔间才想起,她的美人椅不在了,她身旁的那些陪伴了她半辈子的小美人们也都不在了,一睁眼,终究物非人也非了。
再也没有人不停地挥着手帕,对远方的她温柔道:&ldquo殿下,这里,也可以瞧见云郎呢。
&rdquo 她叉着腰,踩在竹色的摇椅上,意气风发地张大嘴时,对着隔壁竹影婆娑的院落,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无论是爱还是恨,她都无法再告诉云琅。
那一场火,烧坏了她的嗓子。
云琅常常在竹林中走动,她听得出他的脚步声。
他常常站在林中读书,林影斑驳时,沙沙作响时,忍冬便坐在泥土上,双手抱膝,听他念书。
云琅似也喜爱那些鬼怪狐灵,常常读些此等异闻。
他的声音很好听,清清淡淡中,一些字句却已带了吸引人的温柔。
&ldquo时有雨,张生背书奔于荒野,四郊悄然,只闻乌啼。
夜半子时,隐约灯笼,红黄四提,无有归依,遥遥荡来。
生大骇,跌步而陷污泥,瑟瑟不能举身。
久,陡然睃目,笼中竟非火色也,盖美人抱珠环舞,皆烛芯高低,莹润不可方物。
生痴怔,触之,却轰然火光,付之一炬。
&rdquo 忍冬听得入迷,一墙之隔,云琅读到&ldquo轰然火光,付之一炬&rdquo,突然想起什么,沉默了下来。
第二日,他已换成别的故事。
忍冬翻遍了藏书,却找不到那些故事的源头。
他总是讲着教忍冬开心的故事,书里的书生和妖怪全是圆满的结局。
院中的桑葚果子熟了,她握着一大把,边吃边听故事,看着满手的红紫,料定嘴唇也是这等妖怪颜色,云琅再一本正经没有语调地念着书生迷上了哪家的妖怪,便显滑稽了。
故事就是故事。
忍冬笑得乐不可支。
她决定吓他一吓。
她教下人寻来了野猪牙和灰色兔耳,嘴上、指甲上涂满了桑葚汁。
晡时,晚霞漫天的时候,忍冬爬上了院墙。
她的记忆一闪而过,前世兴许也有这样忐忑的时候,院墙让人心颤,只是因为隔壁风光秀美。
云琅背对着青苔满布的瓦壁,手中握着一本书,颀长的手指点在了书页中的某一处。
他靠在竹树上,认真地念着什么,她模模糊糊地瞧见他的影子,便从院墙上栽了下来。
竹叶似乎也受了惊吓,全落在了云琅的直裾长袍上。
云琅没有转身,他继续读着:&ldquo有怪踩月而来,美如秋水,清如山河&hellip&hellip&rdquo 然后,果真有个兔耳獠牙的黑色妖怪踩月而来,从背后缓缓又缓缓地踮脚抱住了他。
她的泪水全部沾在了他的长衣之上。
若是她还能美如秋水,清如山河,还能时时刻刻寻着理由见到他,该有多好。
这是忍冬这辈子第一次抱云琅。
云琅怔了怔,书掉在了厚厚的竹叶之上,瞳孔一瞬间放大,握着书的手有些晃动。
他低头看着环着他的那双手,枯瘦焦黑而伤痕斑驳。
云琅闭上了眼,他轻声道:&ldquo殿下,臣曾说过,对于殿下的靠近,臣不能忍受。
&rdquo 忍冬六十七岁的时候,按照纪元,是喜欢云琅的第四十九年。
那一年,并没有什么大事,除了,云琅离世。
他临终的时候,她没有去。
世人相传,云相临终时面目十分安详,他无愧万民,含笑而终。
忍冬想起了自己还年轻时的那些日子,所有的人都说她在蔷薇丛中对云琅一见倾心,她依旧没有那刻的记忆,只是现在仔细想来,这辈子,兴许只有那一刻,自己才和云琅真正的心意相通。
那时,蔷薇丛中的小殿下忙着东挑西拣,蔷薇丛外的小状元忙着低头喂鱼。
还身为少年人时,瞧着这世间,真的真的很无聊。
无论是嫁人,还是考取功名,都一样无聊。
而人生最快乐的一日大抵便只在死前的那一日。
将死之时,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觉得这样有意思,只因知道,明天再也不会继续。
他们未曾互通情谊,他们不是夫妻,所以,一生都是那一墙之隔。
她想起自己还没有失去声音,还在太液池奔驰的时候,每一日问云琅的问题。
云琅,这件周代的爵你觉得如何?是假的吗? 是的,殿下。
云琅,你觉得那只猫生得怎么样?我瞧着胖了些。
是的,殿下。
云琅,你说,这百国之中,我可是最美的姑娘? 是的,殿下。
云琅,你喜欢我吗? 不,殿下。
君心何坚决,到死无两意。
云琅入殓时,听说怀中只有一本磨破了的《孙子兵法》,这是他临终叮嘱。
不必依山河而居,不必厚待云氏,不必享宗庙配祀,只要此书陪伴便可。
陛下悲痛万分,曾经翻过那本《孙子兵法》,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些蝇头小字,甚是潦草,似是每日赶写。
无人辨认出那些字究竟写的什么,只剩下卷尾一段空白处,字迹勉强瞧得出。
那只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ldquo有怪踩月而来,美如秋水,清如山河,生呆若木鸡,爱而不能忍,甚倾之。
&rdquo 爱到何处,已不能忍受咫尺之距。
甚倾之。
生甚倾之。
忍冬一直在想,她这辈子究竟为何来到这等红尘浊世,前半生荣华富贵,后半生形同鬼魅,这样的起伏不定,生命中还有什么是恒常的。
后来细细思量,她的来与去,似乎一直在持续一件事,那便是,和时间赛跑。
和这一生的时间赛跑,还能喜欢他多久? 她垂垂老矣,经常昏昏入睡,那一日,再次醒来时,才发现,一切不过是一个赌局。
她赢了,变回了那个痨病鬼模样的奚山君。
转身时,一袭白衣蓝袖,芝兰玉树的扶苏,倚着不知从何处跑来的梅花鹿,正坐在橘树下读书。
他抬起了眼,淡淡笑道:&ldquo你回来了,好险。
&rdquo 好险,没有输。
奉娘欺瞒了些事实,那个六十年前,只是天尊造的幻境,并非真正的六十年前。
没有人改变得了过去,更何况真正的云琅是仙体,一举一动关碍苍生,诸仙自有分寸,不愿打扰。
奚山君以阐教门徒之身,代奉娘做了回冤大头,奉娘却颇不厚道,未说出天君的最后一道意旨。
哪派门徒若是输了,便永远留在幻境之中。
奚山君有些惊讶,&ldquo那上了云琅身的是道德门下的哪位高徒?我临行前,特意把对前生心上人的爱意保留在青城身上,让她对云琅一往情深至斯。
云琅六十五岁寿终,之后如何了?&rdquo 奚山君笃定,只有真情,才能换取爱意。
奉娘笑了,&ldquo山君虽赢了,可云琅至死也未承认喜欢过你,故而并不算输,你不必为他担心。
他费尽全力,设了一个双赢的局,实乃我两教之幸。
&rdquo 奚山君眉头微蹙,问道:&ldquo是哪位仙人如此仁厚,对我这样关照?&rdquo 奉娘苦笑道:&ldquo天君突下旨意择的人,只知是个十分聪慧仁厚的公子,带着记忆进入赌局,除此之外,奴也一概不知晓内情。
这四十九日心中十分忐忑,总怕把你害了。
&rdquo 奚山君面上笑道:&ldquo我拿着对前世心上人的欢喜对陌生人,不曾动摇半分道心,又如何能输?陛下过虑了。
&rdquo 奉娘斟酌良久,才掏出一面镜道:&ldquo这面镜是灵宝天尊赐下,若我方局势危急,便会显现红光。
这四十九日,可一直是红光啊,山君,故而我这样担心。
莫非,误打误撞,奉旨入了幻境的便是山君前世的心上人?&rdquo 奚山君不动声色,似笑非笑地伸出手,&ldquo陛下马上就要飞升,我这等微末小人尽了全力,只为讨生活,还顾及什么前世的心上人呢?只请陛下把你珍藏的那几套人皮赏与我,我那小夫君马上要出山念书,不置办几个身份怕被人生吞了呢。
&rdquo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逢场入戏宁远
- 组织部长3大木
- 吧唧一口吃掉你一口时光
- 最强游戏架构师指尖的咏叹调
- 养了千年的龙蛋终于破壳了若鸯君
- 穿书后我抢了男主金手指暮七七
- 想爱就爱艾米
- [综英美]才不是史莱姆!Cii
- 穿成万人迷的炮灰竹马妾在山阳
- 婚途脉脉笛爷
- 七零娇宠小咸鱼冠滢滢
- 法师乔安程剑心
- 寄生谎言余姗姗
- 穿越后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来宠我梦.千航
- 苗家少女脱贫记潇湘碧影
- 七零金刚芭比非酋猫奴
- 田园小花仙[快穿]眯眼笑笑
- 执刑者康静文
- 纯阳剑尊一任往来
- 大佬她不想回豪门梦.千航
- 有朝一日刀在手退戈
- 神话降临如履
- 妈咪不乖:总裁爹地轻轻亲谁家mm
- 霸总的小熊软糖成精啦郑西洲
- 梦魇图鉴收集记录[无限流]酉时火
- 她是耽美文校花女配奶绿不绿
- 装A可耻[娱乐圈]游衷
- 嘴和心的南辕北撤派翠克大星星
- 不是吧?童养婿竟是战神怪味蚕豆
- 重生八零年:我狂吃能力果实,宠哭妻女小兵头子
- 都市神豪:开局解锁一亿亿资产滘南大街
- 群鸟沉默时Grauweg
- 采薇(产乳 NPH)霍饭饭
- 雍正女儿续命日常[清穿]拙元
- 荣宠手札[清]一条咸鱼0
- 清穿之四福晋只想种田蒹葭是草
- 吃货太子团宠日常[清]粉色嫩蹄
- 重回宿敌黑化时[重生]丹青允
- 我!系统!懂?!云月六年
- 作为武者,会点仙术很正常吧!凌谟
- 年代:重生1958山之北水之南
- 你假死嫁白月光在先,我再婚你哭什么麦兜兜
- 都市:开局重瞳被挖,我以神龙证道!唐镜
- 老头重生卖掉铁饭碗,白眼狼妻儿傻了!胖白在摸鱼
- 剑逆乾坤柳暗船
- 夏风微微,一个让人改变的夏天夏君嫌
- ?盛肉不颠勺
- 两千公里棕榈树(H)阿靆
- F1:开局车王教我开赛车笑傲浆糊999
- [足球同人] 异瞳者爱做猫饭的小丸子
- 气运系统:我以残躯镇诸国!迷相生海月i
- 这个反派对主角是真爱啊我不是晓七
- 凛冬似春(青梅竹马,强制爱)青柠汽水酒
- 重生后强行和反派HE了黑色籽岷
- 看上美强惨后拯救进行中噗桃圆
- 赤道雨盒粒
- 当万人迷穿成万人嫌后(万人迷np)随机刷新npc
- 戒不掉她的手面具
- 北境之笼(禁脔文学)亚路嘉
- 艳鬼压床好佳哉
- 发情期(兄妹abo)羊肉铺子
- 修真大佬的都市生活吾乃奇迹
- 叫你参加节目道歉,你现场撩妹阿杰鲁的小强
- 乱世,在尘埃中崛起芜悔
- 都市:开局重瞳被挖,我以神龙证道!唐镜
- 拯救mob文女主计划(np)俺就是咸鱼
- 萤火之春甜酒酒。
- [OP]成为被攻略的里番女主sanna
- 乔婉蝶喵
- 农女有空间:腹黑庄主娇宠妻莎妖
- 快穿之病娇反派llllx
- 引狼入心愚礼
- 爱上情敌愚礼
- 和猫猫装情侣后翻车了白云不深处
- 霸总被宝贝助理嫌弃了寞尘
- 凛冬似春(青梅竹马,强制爱)青柠汽水酒
- 囚雀衔环Enari
- 穿越柯南:我真不是名侦探赵橙橙
- 这个反派对主角是真爱啊我不是晓七
- 可行性试验(普女万人迷,NPH)涣
- 徐總他是自願的【限】午盏
- 重组家庭的你和哥哥们(第二人称|兄弟夹心)lily在复健
- 七零千里姻缘一线牵了冥
- 天降窝边草愚礼
- 在狗血文里当人渣翻车后[快穿]好苏狐
- 极品社畜当上假少爷风听我令
- 一篇水仙文温诗酒
- 你好,请收货[np]橙夏野
- 丫鬟命我是西门
- 重生95:带妹赶海致富,喂饱全家煜煜吃鱼鱼
- 群鸟沉默时Grauweg
- 荣宠手札[清]一条咸鱼0
- 隐风铃望山晚舟
- 作为武者,会点仙术很正常吧!凌谟
- 老头重生卖掉铁饭碗,白眼狼妻儿傻了!胖白在摸鱼
- ?盛肉不颠勺
- [综漫] 排球,但是已黑化齐贺美优
- 女宗背后的男人猫爱预言
- [柯南同人] 工藤警官无话可说尤利塞斯
- [柯南同人] 路人开局该怎么通关阿葡露萄
![领主沉迷搞基建[穿书]](https://www.nothong.com/img/493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