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九章 庆长 爱是深沉的幻觉(1/3)
7月夏日午后。
她醒来,从午睡竹床上起身,推开木门,走向庭院。
阳光在院子里涣散成白茫茫平原,午后炎热空气。
栀子花累累满树,散发出浓烈香气如同发酵。
她穿一双水红色塑胶凉鞋,是祖母在集市上购买。
童花头,白裙。
5岁庆长,沿着房屋之间窄小巷道,走向机耕路外大溪涧。
巷子尽头敞开,绿色山峦高耸绵延。
轰隆隆水声从远处震荡过来。
世界如同油彩般静止,没有风吹草动。
水流一路奔腾,冲击岩石和河滩。
拎着鞋子涉入水中,溪水深及膝盖。
水底遍布绿色水藻,小鱼小虾轻巧游动,鹅卵石棱角磨擦脚掌。
在烈日下穿越一条河流,走向对岸。
远处,金黄稻浪在风中波动,开阔田野蒸腾泥土气息。
紫菀花开得繁盛,无边际簇拥如同云霞。
草丛中有带刺的茅莓,她俯身摘下一枚被阳光烫热的红色果实,轻轻放入舌间。
抬起头,看到溪边堤岸石块间栖息的翠鸟飒然飞起,发出婉转清啼。
翅膀闪烁宝石般蓝紫色光泽,如同一道静谧光线飞向远处。
一切展开井然有序。
庆长的童年记忆,来自崇山峻岭之中的偏僻村庄。
这些场景从未在脑海中消失,在梦中,在入睡前的恍惚,在每一个意识与现实界限不清的时候,突兀如同一面镜子从胸口升起。
回忆真实确凿,现实却令人觉得变幻无常。
如同以往27岁的她,在凌晨疾驶于空旷平原的列车上醒来,窗外一片漆黑。
偶尔有稀疏灯火掠过,夜雾浓重。
车厢里熄了灯,只有走廊里地灯照射出窄小通道。
列车速度加快,车轮与钢轨的摩擦声带有一种锐利。
旅途正在展开,她去往瞻里。
无法辨认,梦中的旅程是目的所在,还是列车中的旅程才是一场梦魇。
在梦中出现的5岁女童,与万事万物持有的单纯而开放的关系,是她生命模式里坚固的一组结构,被深深敲入泥土无可动摇的基底。
它决定独自穿越山岭隧道走向日光花影的14岁少女的无所畏惧,决定在瞻里荒芜田野探访一座古老廊桥的27岁女子的感伤情怀,决定她在窗台上轻轻跃下跟随清池走向人世情爱的决心,也决定她从不放弃的挣扎和摸索。
她寻求真实美好闪耀出光芒的事物,信任它们,付出代价,从不退缩。
但肯定还有另外一部分自我被陷落。
决定她在人群中游离颠簸无法停靠,决定她对感情近乎偏执和贪婪的需求追究,决定她与清池在这段纠葛关系中的互相损伤,决定她貌似独立强大的表象之下,隐藏内在长久的缺损匮乏。
如同一个有勇气的人,独自遁入一座夜色中的深邃森林,远离人世,手中却没有火把。
她并没有在世间找到位置。
此刻。
30岁的她在云端匀速航行的飞机上醒来,听见耳边巨大轰鸣声。
窗外呈现环形梯田和起伏山峦,青翠连绵。
乘务员播报飞机将在半小时之后抵达贵阳机场。
与清池断绝音讯之后,定山重新介入她生活。
等待她平心静气,再次提出结婚。
她自然觉得勉强。
说,定山,你已清楚我的生活和个性,为何还要如此提议。
他说,是。
正是因为我清楚,所以我希望照顾你。
你知道,我们之间没有爱。
我们并不相爱。
结婚是一个结盟的方式。
我希望和生命的真实结盟,你是那个部分,庆长。
也许我比你更消极,但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能够付出的是什么。
你在我身边就是我的所得。
你像一束光线,庆长,你拥有真实。
他又说,我对你没有狭隘的占有之心,也并不觉得可以占有你。
我尊重你的性情和工作,你有可贵之处。
但在情感上,你始终有未生长完整的弱处。
我不想在你被陷落之时,身边一个依靠的人都没有。
你可以把婚姻当作疲累之后的休憩地,现在正是时候,我心里清楚。
我很高兴还能够站在你的身边,这是我的决定。
他们去民政局登记。
秋日清晨,阴天,清凉雨丝。
庆长穿白裙,戴上定山赠予她一枚小小钻石戒指。
定山穿蓝色新衬衣。
她30岁,他33岁。
相识5年,反复聚合,最终决定结婚。
排队很长时间,注册完临近中午。
两个人找餐厅吃顿饭,开了一瓶酒。
是一个如庆长预期中的婚礼,简单,安静,没有无关的人加入。
仅属于两个人的朴素仪式。
在餐厅,他说,庆长,我知道你对感情认真执着,我想给你安定而不是束缚。
如果某天你得到方向可以继续前行。
我希望我们能够因彼此存在而趋向更多光明,即使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愿望。
我深爱你,你要相信。
他又说,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再找一个采访线索,出去旅行和工作。
总之,不要顾虑其他。
我的薪水足够维持我们简单生活。
你只管做喜欢的事情,我会支持。
说出这段话来,他一定思量已久。
她辞去杂志社工作平日零散接活,生活责任都在他肩头,但他愿意背负。
她隔着桌子伸出手去,他牵住,轻轻抚摸她手指,两个人一时默默无言。
呵,她与他之间终究还是生疏遥远。
这个愿意承担和背负她的男子,是和她的灵魂无法产生交会摩擦的人。
她生活在他的身边,仍是那个伪装不需要爱也可以存活下去的人。
但如果这是生活愿意给她的安排,她起码已学会顺受。
人与人之间持有信任才能互相凭靠。
有时相爱不能使人信任,尊重却可做到。
30岁的庆长,对照3年前去瞻里探访一座桥的女子,渐渐拥有空旷和沉落下来的心得,不再如以往那般剧盛的偏激执拗。
一种欲顶撞现实常规不管不顾的放任。
她对某种如水流般缓缓渗透的孤独有了消化和吸收的体会。
曾经她的孤立边缘如同剃刀般锐利容不下半分迟疑不决,曾经她对行动和意志的推进持有坚定激进的目的性,曾经她是个对自己对外界容不下任何模糊边界的人,曾经她是个非黑即白一清二楚绝不妥协的人。
百转千折的煎熬和挣扎之后,经由与不同的人之间的感情,她试图清洁和照亮自己。
她去往高山上的村庄春梅。
一个来自英国的志愿者,在春梅唯一的民办小学里工作10年之久。
获知沈信得的信息,完全无心之举。
读完信得的教课笔记,她对这个女子产生极大兴趣。
事实上,沈信得在两年前已闭门谢客,拒绝一切外界采访和探望要求。
庆长做事坚韧,写电子邮件给她,附上以前做过的数篇采访,告诉对方如果做这个采访,重点和关注绝非她所介意的喧哗取众。
她说明目前没有在固定媒体供职,会自主决定发表方式。
一个月后,收到对方回信。
信得邀请她去春梅。
她说,你要摄影、采访、聊天、观摩都可以。
以我的本意,希望你像个朋友般来春梅坐一坐。
听你聊一聊观音阁桥,或其他。
一个为自己而工作深入穷山僻壤的任务。
再一次,一个人的旅途。
在贵阳汽车站旁边的小旅馆,庆长住宿一晚。
次日早晨,搭上前往孤沿的汽车。
去往榕江县。
漫长迂回的山路。
她在客车座位上头靠玻璃窗昏昏欲睡,醒来,长时间凝望窗外的青翠高山,幽美村落。
河流和田野四处纵横,妇女劳作,孩子活跃嬉戏。
这与世隔绝般封闭山区,天高地远,躲避掉外界强势汹涌的经济、商业、物化种种浪潮,和现代社会风气略有不同,依旧保留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少数民族女子的发式和衣物,延续传统的审美,手工刺绣繁复艳丽。
个体与古老历史的联结没有断裂,一切还能有条不紊。
偶尔眺望到一处木屋重重叠叠的村庄,在僻静田野边际呈现,如同被遗失的找不到归去路径的故乡。
大片水塘里盛开野地荷花,红花绿叶映衬蓝天白云,唱出一曲悠长歌谣。
庆长看着村庄在视线中逐渐消失,想起去往瞻里的山路转折处,邂逅一面遗世独立的湖泊。
世间有情万物总让她的心产生振颤。
她是如此内心敏感丰盛的女子,知道还不能够成为一个对感情失去要求的女子。
与定山共存一个屋檐之下,如同搭伴过活的同居男女,礼貌客气,略带生疏。
庆长有时失眠,需要长时间开灯阅读,与他分床睡,定山也不以为意。
一个男子安静辛勤,工作,烹煮,打扫,无可挑剔,适宜共存。
有时他在电脑前长时间工作,疲累至在沙发上直接入睡。
她给他披上御寒的毯子,脱去他的鞋子。
他们从不为琐事争执吵闹,也没有刻骨铭心的渗透和联结。
没有思念。
没有粘缠。
生命路线终究是并存而无法交叉重叠。
怜悯与感恩,能否支撑起一段婚姻的形式。
她追问自己,又为何一直没有勇气离开他。
她说她要去春梅,用6个月或更长时间做一个摄影采访。
定山听到她决定反而释然,说,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只愿意你快乐。
他说,有时我深夜醒来发现你不在身边,卫生间的门紧闭,灯长时间亮着,听不到一丝丝声音。
我会担心。
定山母亲得癌,在少年怀中闭上眼睛去世。
这使得男子对死亡持有一种薄弱感受。
成年之后,也许是一种压抑,也许是一种训练,他对待感情的形式显得钝感,过于平静克制,有时接近无情。
这关系始终是清淡而恒定的微温状态。
使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婚姻里,如同被保护起来的女儿。
庆长的性格并不女性化,也没有小女人的依赖和造作。
他喜欢她远走天涯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削弱抑制情感的浓稠和热烈,正是他所期求的状态。
他们甚至很少拥抱。
在内心他对女性的情感有一种下意识的隔离。
也许他根本没有要求,也许他是个信任中道的人,知道远离爱欲和贪恋的一边,就能避开恐惧和怨恨的一边。
庆长不清楚其他人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形式。
但她与定山的这一种,注定特殊而无解。
定山喜欢孩子,他的父亲也有此期望。
庆长从来都热爱孩子,按照常理,应该让定山实现愿望。
但她总觉得时间未到。
也许是内心还没有被拼凑完整,尚需寻找陷落之处。
也许,她不想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与定山感情之间的缝隙。
事实上,这缝隙是一个风声呼啸的深渊。
她没有定山坚韧。
他可以日复一日佯装不知或故意忽略。
毕竟是个男子,有繁忙的工作俗世的目标,但她却无法停止觉察和感受这关系的疏离和淡泊。
她和定山的婚姻,如同用一张薄薄白纸糊住的无底深渊。
谁若忍心伸出一个手指,轻轻一捅,即告破裂。
但他们两个竭力维持,在一张白纸边各自做戏,也许这就是婚姻的本质。
不管如何,无法被解决的问题只能先搁置一边。
离开城市中的生活,离开定山,再次出发踏上旅途,这是她目前唯一能实践的行动。
在开放的空间和时间里,独自一人,获得空白,查找内心失陷的角角落落。
汽车在崇山峻岭之中缓慢爬行。
颠簸将近10个小时,抵达孤沿。
庆长见到接应的男教师。
姓潘,35岁左右男子,温和消瘦,皮肤黝黑,在乡政府车站等待。
他是本地人,在春梅小学教书15年,一个人教三个班。
学校里有一台捐赠的电脑坏了,他背到县城来修复,要把它再背回去。
信得委托他来给庆长带路。
他已等她一天。
两人都没有吃饭。
庆长带着平时旅行用的60升旧登山包,里面是书籍、衣物和日用品。
穿白衬衣粗布裤球鞋,一头长发编成粗黑麻花辫子盘成发髻。
行动洒落,一看便知是习惯风餐露宿之人。
潘老师脸上露出笑容。
他说,庆长,欢迎你来。
汽车走过一段平坦公路,开始爬山。
层层山脉如同没有穷尽的画卷铺展。
山路曲折,边缘是高深悬崖。
车子始终以S形前进,一个打转,又一个打转。
黄昏暮色降落。
夕阳如血。
深邃山谷中变幻不定的光线,照耀绿色山林。
不知为何,在远离城市文明和繁华的地方,在偏远深僻的地方,庆长觉得内心自如,不再流离失所。
仿佛天生属于这里。
远离。
远离钢筋水泥的石头森林。
远离熙攘而隔绝的人群。
远离形式感和物质堆积的生活。
远离妄想。
信得说,离天空越近的地方,宇宙的讯号和信息会不会与人的生命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
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拥有他独特的天宫图。
万物星辰为任何一个生命提供能量。
而人在成年之后,渐渐失去和这股原始力量的联系,被给予种种事先设定和束缚的概念,进入自我虚设的牢笼。
一个幼小的孩子会指着红色说它是绿色,可以把前面说成后面,会询问什么是真什么又是假。
他们不分辨是非对错。
一切定义都是人为,和事物本质没有关系。
成人世界规则体系,吞噬与宇宙相联的灵性和本能,人渐渐失去与自我的真实性互相联结的能力。
她说,我们最终面对的,是一个庸俗的难以被轻易改造的世界。
3个小时后,汽车抵达叫做月塘的小村。
潘老师说,他们将在此地农户家里借宿一晚,明天一早起来爬山。
抵达春梅需要3小时左右山路,只能徒步。
一趟来回,山路迢迢耗时耗力,平时春梅村民除了赶集和交易货物,很少外出。
高山顶上的村庄。
持续上坡的路途,有时走在黄土裸露的坡道上,有时进入葱茏茂密的树林。
六月夏日,一丝风都没有,空气极为凝滞。
黏湿汗水贴在肌肤上,一会儿身上衣服全部渗出汗迹。
潘老师稳步走在前面,庆长闷声跟随,两个人都背着不轻的负担,往山顶深处行进。
随着海拔增高,视野越显空旷。
大片独特的梯田结构呈现眼前,稻苗在风中起伏。
春梅村寨出现在前方。
密密麻麻木结构房子连接蔓延,屋顶覆盖的木皮被经年风雨霜雪浸染呈现黑灰色,生长出绒密绿色苍苔。
小学在村子入口不远处。
广场上有一面红旗,沿着山腰边缘建出的一排木头房子。
树影下传出孩子响亮诵读的声音。
以前春梅小学只是几间土屋,屋顶由竹桩垒成,地面是碎石泥地,没有门,几个教室用帆布隔开。
在寒风呼啸的冬天或者缠绵雨季,学生和老师苦不堪言。
信得过来之后,因为逐渐扩展的影响力,为春梅小学找到捐助,最终重建房子。
一度时间,电视台报纸杂志各种媒体蜂拥而至采访,不同的人探访,不同的奖项要授予她,各种活动邀请出席。
当地领导觉得自豪,极欲把信得捧成一个有贡献的特殊人物,以此为当地做广告谋福利。
信得却备受困扰。
种种演变已完全违背本意。
她不需出名,也不想被当做宣传工具,只想继续静静在深山教书。
最终采取绝决,拒绝一切活动和探访。
村庄在一番泡沫般喧嚣而虚浮的名声震荡之后,重新恢复日常。
信得上课。
潘老师带庆长去宿舍。
木楼里的窄小房间,破旧粗陋,没有洗漱卫生设备。
公共厕所是由木片遮搭起来的大坑,粪水横流,苍蝇到处飞。
他们有食堂,自己蒸米饭吃。
春梅隐藏在层层深山之中,经常断电,洗澡需要去特定的接山泉的地方。
夏天酷热,冬季寒冷。
土地贫瘠,只能种玉米和土豆。
孩子读完小学,要下山去读书。
除了信得,目前都是本地男教师。
他说,这里的环境艰苦,生活条件简陋,课务繁重,学校里基本留不下人。
那些因为受信得的影响自动涌来的志愿者们,三三两两,待了半年或一年,也都走尽了。
他解释这一切的时候,表情平静。
庆长把背囊卸下来靠在墙角,伸手推开木窗。
窗外是逶迤山峦和古老枫树的枝叶。
高山围绕之中的异族村寨,远踞荒芜山顶,显得与世间格外疏离。
信得的面容特别。
细长凤眼,额头高而开阔,眉毛粗直,狭长脸形线条浑然。
脸上散落黑色小痣,数颗极为明显。
她穿当地妇女的土布衣服,布鞋,头发盘成发髻。
皮肤黝黑粗糙。
人很消瘦。
刚到中国,她也曾在初中教英文课,但后来一直选择待在春梅。
这个村级小学有207个孩子,8个老师。
加上信得,一个不领取任何工资和补助的义务工作者。
她教自然,美术,音乐,综合实践课。
每星期上15节课。
这里是高山之巅。
她说,我喜欢待在高山的顶上。
庆长每周一到两次,和信得一起去爬山。
已是秋天,山谷里漫漫无际淡黄色芒草,在风中如潮水般起伏。
山漆树、乌桕、毛果槭、榉树的叶子都已被冷霜侵红。
深浅不一的红色,使山林在阳光之下呈现出饱满杂染的颜色。
两个习惯远行的女子体力都好。
带了水壶和干粮,一前一后闷声爬上最高峰。
脱掉鞋子,一起坐在山顶巨岩上,默默无言,或交谈几句,看蓝天白云,看底下山峦起伏,天地苍茫一色。
她也跟信得一起去家访。
走10多里崎岖山路,抵达僻远村落的学生家里,有时在学生家里留宿。
真是赤贫如洗的家庭,房子用木板拼成,不能遮风蔽雨,四壁空空,灶台被烟灰染得赤黑。
几乎没有任何家具。
家里的大人基本都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子。
孩子要做很多农活,或者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上课。
来回路途遥远,中午没有饭吃。
也没有鞋子穿。
沈信得来到此地,工作10年,无疑做出了选择。
她说,新时代是辆轰隆隆势头迅猛的列车,所有人拥挤其中,身不由己,即使前面方向不清,人心惶惶,但有谁可以试图跳车或逃脱。
人可以最终相信什么。
肯定不能相信互联网,也不能相信电视电台报纸,不能相信主义制度概念形式,不能相信许诺和教条,也不能相信任何评判和结论。
任何实际的世间事物,都在变化之中,都不可获得最终的信任。
如果找不到真实自我,那么连自己也不可信任。
这个自己,只是一个被装入列车失去自由的身份。
因此,她想让孩子们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是找到自我。
她教他们编歌表达内心所思所想。
教他们观察一年四季山林树木变化,用心观察自然细节,把它们画下来。
教他们感受水流、泥土、植物、动物,置身其中,与一切亲身接触和体会,通过观察和记录,把种种情感,情绪,意识,心灵的变化和经验,在内心储存起来,转化成一种自我意识。
进行感受和创造。
她教出来的孩子,会更有活力,更有思考力。
有些一旦升级去了初中,很容易被老师不喜欢,会被开除。
未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想象空间。
能有几个孩子可以走出高山盆地,最终走出地域和身份的界限。
一旦成年,出路没有两样。
也许终生无法离开这重重高山围绕之中的土地。
谋取基本生存,进入成人的世界,喝酒,打架,结婚,生子,劳作,无视环境和心灵与自我的联系,再没有做出自我表达的机会。
一起沉入世俗底层,自生自灭。
人被环境困顿,只能在生命最基本欲望之上挣扎存活。
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人失去想象力和对理想的期待。
穷困,使人无法远行无法得到机会超越生活限制。
信得不愿意成为一个短期志愿者,因为觉得这些孩子需要真正以生命和他们互相联结的老师,如果能够拿出情感和时间,至少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光里,接受到关于审美、自我存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爆款创业清蒸日华
- 无敌天下神见
- 小李飞刀3:九月鹰飞(上下)古龙
- 驭虫师肥皂有点滑
- 邪气凛然跳舞
- 未生葡萄
- 拜我,我让你发财向远飞
- 嫁给冷血男主后我变欧了[穿书]/嫁给杀器后我变欧了[穿书]蒸汽桃
- 同萌会的一己之见楚凤华
- 和反派魔尊互换身体后镉圆
- 大地飞鹰古龙
- 炮灰请睁眼[快穿]少说废话
- 纸片人老公成真了枝景
- 尘埃之花采葑采菲
- 横滨芳心欺诈师闲豆花
- 万人迷炮灰被迫躺赢郎不知
- 勿cue,小饭桌开业了为仓
- 身为卧底的我要成为港口Mafia首领了昭文
- 定风波来风至
- 二号首长黄晓阳
- 草莓味的A不想恋爱凉皮就面包
- 我给男配送糖吃[快穿]五朵蘑菇
- 问道红尘(仙子请自重)姬叉
- 穿越种田文那些年(快穿)打字机N号
- 我一见你就笑郑三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综武:我,曹老板,挖墙角达人不弃九一
- 秦世风云录饺子面条火锅
- 穿越战国我靠杀敌称霸天下王权荣耀
- 穿越商朝,为了人族而战叫不醒的清醒着
- 穿越大唐,我靠变身闯天下美溪旺仔
- 一世豪权,一世月明非心水京
- 洪荒之鲲鹏绝不让位李九郎
- 纯阳第一掌教池宁羽
- 极品仙途闻人毒笑
- 拜见教主大人封七月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
- 武侠:莽昆仑严久霖江洲雨林
- 世间自在仙碧海蓝天是我老婆
- 邪仙偷腥的猫
- 仙道长青林泉隐士
- 古代打工日志:从退婚开始躺赢西猫西
- 乱世红颜之凤临三国孟回千古
- 综武:最强说书人,开局曝光金榜世间万般皆是苦
- 最强装逼打脸系统太上布衣
- 元末轶事享邑
- 我才不想当用剑第一桃子糖
- 苍穹战神跳神3
- 逆天七界行诸神的荣耀
- 九州造化逍仙08
- 踏雪寻青梅云笺寄晚
- 异界纵横之我在江湖搞发明锅包肉没有锅
- 温阮霍寒年温阮霍寒年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孤鸿破苍穹星光入枫海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人在古代,从抢山神娇妻开始崛起女帝
- 用户90391439的新书:悟用户90391439
- 这破系统非要我当皇帝总有那一天
- 开局力挺宁中则,李青萝求放过粤北陈老师
- 大明:人在洪武,复活常遇春冰魂修罗
- 大明锦官梦苏梦沉
- 娘娘,对不住了春山果实
- 边军凶猛赤阳
- 修仙家族:我的灵肥引情劫幽冥人
- 我在古代当镇令龙葵宝宝
- 穿越宋末,海上发家先滨
- 一世豪权,一世月明非心水京
- 学渣的传奇人生迎凤村草
- 混沌再临之灭仔纳里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
- 横行霸道踏雪真人
- 仙帝铁马金戈
- 曲樟纪事陈加皮
- 大秦海晏:嬴傒复辟记垚鑫
- 大秦血衣侯:我以杀敌夺长生鎏金淬火
- 穿越大唐:农家子弟挣钱忙智阳雨
- 从天龙活到现代的武林神话歌尘浪世
- 奉旨当里长:百姓的明义南明蓠惑
- 我让高阳扶墙,高阳为我痴狂抱星明月居
- 北疆战神:从边军小卒到杀穿蛮族一心向龙
- 用户90391439的新书:悟用户90391439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大宋:朕的专利战横扫1126心有灵犀的金毛狮王
- 大明:朱元璋的好大侄逍遥御风
- 水煮大明嗒嗒猪
- 原始蛮荒部落生存记景斯年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天娇:铁木真崛起与大元帝国前传天狼峰的古尊人
- 我的美艳师姐妹燕山夜话
- 大明权谋录Four古往今来
- 穿越大唐,我靠变身闯天下美溪旺仔
- 一世豪权,一世月明非心水京
- 道术达人虫梦
- 曲樟纪事陈加皮
- 天神之血天明
- 仙帝铁马金戈
- 千宇仙寻书生无愁
- 上山为匪彗星撞飞机
- 这个修士很危险想见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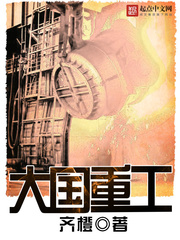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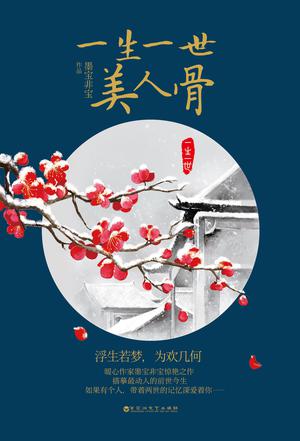
![豪门养女只想学习[穿书]](https://www.nothong.com/img/761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