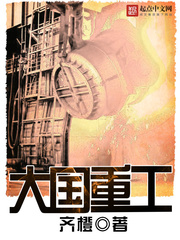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八章 信得 夜航与书(1/3)
16岁,她独自去英国读书。
大学报考分子生物学,没有选择其他热门专业。
这门学科试图了解生命现象本质及其客观构造。
感性,灵性,意识,情绪,情感,这些组成,她经由与贞谅共同生活,已触摸到此中结实血肉。
把所有经验,先大力织成一块平衡光滑的织物,再慢慢切割它的经纬,剖析它的纤维属性。
也许她一直渴望能够更广阔和客观地检视自己。
在过程中,只是逐渐感受到幻灭。
理论对了解自我质地没有最终帮助。
贞谅赋予她颠沛流离四处游荡的童年,已成为内心观念的坚硬基石。
她只信任身体力行得以检验的真实事物和直接经验。
伦敦是阴郁而不存亲近的城市。
古老建筑,人群面无表情生疏有礼,性情的保守和刻薄,与它无血缘的人无从领会。
学校里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的欧洲同学,她与他们无话可说。
细雨霏霏的气候常有,雨水使人倦怠。
休息日,她独自带一把长柄雨伞,穿黑色大衣和球鞋,背帆布包,坐地下铁穿梭整座城,逛遍博物馆,美术馆,教堂,广场,集市……所有大街小巷。
用脚步丈量地图上的每一个标记。
疲惫时,走进街角咖啡店买一杯热咖啡,一只夹新鲜奶酪的全麦小圆面包,坐在落地窗前的高脚木椅上,看着街景进食,休憩。
雨中的古老建筑,清冷轮廓湮没于水雾中。
电车开过叮叮当当。
耳边略带坚硬腔调的英语嗡嗡作响。
她说,在这个城市里,我得到完全的隔绝,因此觉得自由。
20岁,她意识到生命陆续缓慢长出新的结构和部分。
她仍旧习惯在眼皮上描出漆黑粗壮的眼线,眉间涂上戏剧化的白粉。
皮肤黝黑,东方面孔,一双眼尾细长的漆黑眼睛,单眼皮,眼神高远冷淡。
十年如一日,始终是齐眉刘海的浓密长发。
她来自高山上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村庄,唯一留存下来的样本。
同学老师以为她是日本人或韩国人。
她说她是中国人,他们会问她来自中国哪里。
她无法说明经历,生性严肃,不爱插科打诨嬉笑过场,于是从不解释也无说明。
很多人因此认为她倨傲。
她的确无法轻易说清内心容量。
那里隐藏的黑暗深沉难辨。
跟身边同龄人并不靠近,几近活在完全不同的层面。
她少年时想要和贞谅反向而走,在临远积极投身友谊寻找伴侣,成年之后却自动放弃。
投靠人群需要付出太大代价。
事实上,她并不知道如何与人互换。
她的生命在按照一种既定的秩序坚定有力地抽生、蓬勃,即使是新生的结构,也遵循同一轨道。
等她清楚自我的属性,她便也学会了坦然接受孤立。
因为失去对情感的信仰,投入情爱姿态不羁。
不交结朋友,只有恋人。
很多恋人,男性,女性,年龄身份全无限制。
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进行肉身的联结,这种短暂而迅急的麻醉,使她一度无法自控。
与旁人的关系,都以自发行动作为主要方式,直率,热烈,截然干脆。
她耽溺于性与药物。
种种方式,不过是想暂时得以忘却。
忘却存在,忘却记忆,忘却时间,抵达日常经验无法揭示的心灵层面。
听到,看到,感觉到种种清醒时无法被打开的超脱大门。
只要能够有效完成,哪怕昙花一现,时效完尽,身躯跌落大地分崩离析。
这些礼物,暂时使她忘记自身是个异质的存在:没有亲人,没有故乡,没有归宿。
她被放置在世界任一角落,随波逐流,孑然一身,自生自灭。
我们是否一定要寻找和回归故乡,这样才会联通本源,让心安宁。
15岁时,她询问琴药,并要求他日后安排时间带她去寻找春梅。
他答应她,但说,其实你未必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最终,你也不会知道要去的是哪里。
所谓故乡,我们回不去的地方,你不必担心没有家,没有血缘的认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暂存这具肉身之中的过客。
度过此生,是让灵魂完成这段旅程,让它获得超越的能量。
世间所有地方,不过都只是旅店。
也许以后我们还回来。
也许不再回来。
你希望自己回来,还是不回来。
当然不要回来。
如果回来,那说明我们的力量不够。
16岁冬天,与贞谅最后一次去往清远山。
山顶上废弃古老的寺庙,清远寺,大殿里有三座佛像,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用生长一千年银杏雕刻而成。
清远寺也许是一座真正的庙宇,古老,被废弃,永恒仪式感的佛像,没有人来烧香跪拜祈求俗世繁荣。
寺庙历经浩劫多次,被战争和权力交替轮番洗刷。
后来有一年,雷电劈击殿前老玉兰树,引燃火灾。
但始终没有人扰动三座大佛,佛像完好无损,大佛神情目空一切。
庭院里腊梅在雪后凛冽寒气中绽放,黝黑色清瘦枝干上,金黄色梅花密密排列,散发出清香,在灰白天色里显出勃勃生机。
破损墙壁上留有墨迹,有人用放逸行书抄了一首晋人的诗。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她们在诗句前伫立,长久凝望这片字迹。
晚上住在寺庙旁边的小旅馆。
这家私人旅馆名叫清宿,每次来山顶,她们都会住在这里。
旅馆有温泉,在露天温泉里浸泡,细雪落于头脸轻轻碰撞,咝咝融化在滚烫热汤里。
她和贞谅全身赤裸,偶然而稀少的亲密靠近。
她紧绷绷的身体,仿佛蓄势待放的花蕾,坚硬青涩。
身心极为早熟,也许因为身边存在一对内心深沉不驯的成人男女。
贞谅纤瘦,但毕竟是在褪色中,肉体有一种熟坠。
如同已开到盛期的花树,在释放出内里最后一股力量。
她的手臂、后脖以及后腰上的刺青,花纹均来自古代图饰。
她记得那刻当下,这个成年女子对她说的话。
贞谅说,信得,不知为何,我觉得人越老去,越觉得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像是真的。
只有我们的感情是真的。
人若死去,什么都无法带走,余留的不过是内心幸存的记忆。
只有情感与我们同行。
但它在这个假的世界里处处碰壁,最后也会如同假的一般带来损伤。
我的确渐渐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去往远处的哪里,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拥有真实的情感。
如果人得到整个世界,却没有得到感情,只是独自一人,他该如何存活。
我不愿意寂寞至死。
她说,信得,我不愿意寂寞至死。
她说,而我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明白这句话。
因为只有在那时我才能够知道,寂寞是什么。
那天是星期三。
清晨,贞谅独自外出。
她出门时穿一件红色大衣,黑色镶银线的丝袜,丝绒绣花鞋。
脸上扑了粉,涂淡淡的口红。
她对装束一向率性,有时邋遢潦草毫不在意,但这次却有郑重艳美,浑身熠熠闪烁。
她说要出门见人,黄昏时回来,但没有详细说去哪里,见什么人,做什么事。
信得也就什么都不问。
看见她手指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心有好奇,用手抚摸这枚精光闪烁的戒指。
贞谅说,你可喜欢。
她说,喜欢。
贞谅便把那戒指脱了下来。
她把它放在她手心里。
说,你喜欢就给你,可以戴着玩玩。
这是个庸常东西,不会让人显得更美。
它不过是一个旧日礼物。
她看出来这戒指极为昂贵,指圈内刻有奢侈珠宝品牌的限制编号。
贞谅遣送它的态度平淡自若,没有留恋,已不关心它出路如何。
她只开门准备离开。
她说,你逐件收拾行李,我们要走。
她问,我们要去哪里。
她但笑不语,对她摆了摆手,眼神表明一切早有安排,不必操心。
她的红大衣鲜明耀眼,在门沿边快速掠过,如同一道彩虹光线。
门外冰天雪地,阳光剧烈,湛蓝色天空如同宝石般明净而纹丝不动。
她知道贞谅已做出决定和琴药分手。
她们两个即使离开临远,不过继续面对漫长孤旅。
往前走或者往后退,都不是出路,总之哪里都不是家。
贞谅会再找一个岛屿吗。
再找一个异国小镇吗,或者再找到一个高山之巅的村庄吗。
她们最终并不知道将去往哪里。
所有存在过的都是临时决定。
她熟悉贞谅风格。
小时候某个早晨她在旅馆里睡得正酣,贞谅已打包好行李,走过来抚摸她的头发,轻快地说,起床,我们要离开。
她决定去找唯一的朋友庄一同。
穿上大衣,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抵达他家花园门口,在楼下高声叫他名字。
这个英俊软弱的男孩从里面跑出来,看见她眼睛里有喜悦惊奇光彩。
他真的喜欢她,她想。
忠心耿耿跟随在她身后,做她意愿的事情,附和她的想法,容忍她暴戾任性,为她偶尔的温柔主动喜不自胜。
以后她还会有这样的伴侣吗,或者说,这是她需要的伴侣吗。
她无力猜想,只觉得身心疲倦想获得安歇。
她说,一同,我想在你家里停留一会儿。
我要躺在床上。
他的房间她来过多次。
一起做作业,阅读,争论,看碟片,听音乐,嬉戏玩耍。
在他铺着蓝色床单的单人床上,她脱掉外衣躺进棉被里面,神情萧瑟。
他站在旁边,目光担忧,说,你是不是病了。
你是否发烧。
他抚摸她的额头,她拉住他的手,说,你进来抱着我。
他和她一起躺进棉被里,伸出手臂给她。
她把腿压在他肚子上,抱住他脖子,脸枕着他的肩头,紧紧拥抱住这具身体。
这不是她在湖边触摸过的健壮丰饶的成年男子躯体,这是一具属于少年的清洁而单薄的身体。
她不觉得他美,但此刻这一切温暖而可倚靠。
一同一动不敢动,平躺着任由她需索依赖。
也许感动,说出内心的话。
Fiona,我父母最近在协议离婚。
我父亲有了外遇,他要弃家而去。
你害怕吗。
是。
他们日日争吵。
感觉这个家随时都要破碎。
我和母亲要失去依傍,以后何去何从。
他眼中泪光闪烁。
如果你知道一切不存在任何坚固的稳定的不变的可能,你就不会畏惧。
她伸手抹掉他眼角眼泪,说,我们有什么依傍呢。
时间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能够一成不变。
他知道她在安慰他,抱住她愈发伤心,开始抽泣。
她说,我未曾拥有过如常人一般的家庭,也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出发去世界哪一个角落。
如果你觉得伤心,我是否该伤心致死。
但我还活着,一同,你要相信,我们原比自己想象得要更坚韧麻木。
一切都会变。
一切也都会完尽。
一切还会重新生发。
一切会继续行进。
他逐渐入睡,她却清醒,听他发出均匀呼吸。
轻轻从床里面爬出来,穿好衣服下楼离开。
回到家里做简单食物。
开始检查书籍、衣物,看哪些需要拿走,哪些只能留下。
她翻阅一本20年前的地图册,在地图上找到春梅的标示。
对照后来新版的地图册,春梅被删除,周围的地形和道路描绘也已改变。
老版地图册中,贞谅夹了一页素描,是她路过的春梅。
她年轻时去旅行,在长途客车玻璃窗边,为它无心而野性的美所吸引。
半途下车。
在山路边为它画下一幅素描,直至搭上下一辆车离开。
这是她和春梅一眼之缘。
地震之后它消亡于世。
她领养了此地唯一幸存的女童。
她想象在这个地方,哪一间木楼是她的家。
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家族亲戚,会有跟她一样的细长的眼睛形状吗,还有浓密漆黑的头发,粗直的眉毛,前额高而浑圆。
如果她一直没有离开那里,现在又会是什么处境。
她会在养猪放牛,做一切粗杂劳动。
她不会受到教育。
她很早就会结婚生子。
也许一生都不会越过高山。
因这注定的天性的不确定,她极渴望找到一个稳定的地方停留,得到一个地址不会更换的住所,得到一个忠实爱慕的伴侣,得到一份心有所属可托付信念的人生。
她感觉疲累,躺在床上入睡。
在梦中抵达一个火车站。
候车厅是巨大的拱顶建筑,坚固的钢骨结构。
数条轨道上停着火车,人群熙攘,语音如同沙沙雨声。
她站在月台上,手持车票,不知道该登上哪一列火车,去往哪里,完全不得要领。
又怕错过时间,滞留在这个陌生地不知何去何从,心里焦灼。
一个面目不清的成年女人出现,她的五官无法分辨,说,信得,我带你去。
她跟上这个女人,人群变成劈开的海水。
她们走的是一条孤单而空旷的通道,有密封玻璃隔离出来的廊道,两边放置形状诡异的盆景。
疏朗枝干扭曲成优美造型,挂着鲜红的圆形小果实,像大叶冬青果实。
走到一个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一朝恶妇予乔
- 我做偏执大佬未婚妻的日子白秋练
- 我给女主管鱼塘中边
- 我真的不是大佬[无限]风月不知
- 驭虫师肥皂有点滑
- 我的时光里,满满都是你(呆萌小萝莉:高冷男神太腹黑)忘记呼吸的猫
- 人生得意无尽欢六道
- 穿到七零当厂花唐柒鱼
- 纸片人老公成真了枝景
- 尘埃之花采葑采菲
- 小可怜手握爽文剧本李温酒
- 百炼成神(不灭武神)恩赐解脱
- 后宫·如懿传1流潋紫
- 我独自美丽一丛音
- 身为卧底的我要成为港口Mafia首领了昭文
- 打穿西游的唐僧涂章溢.QD
- 彩虹星球南书百城
- 功德印青衫烟雨
- 生存者1:夜舞天白饭如霜
- 草莓味的A不想恋爱凉皮就面包
- 玉昭词(今夕何夕原著小说)时久
- 我见贵妃多妩媚鹊上心头
- 我给男配送糖吃[快穿]五朵蘑菇
- 问道红尘(仙子请自重)姬叉
- 和前男友在恋爱真人秀组cp后,我爆了煮熟的螃蟹
- 聚宝乾坤碗凤九天
- 大楚武信君冷剑情
- 苟活乱世,从深山打猎到问鼎中原刀削面加蛋
- 剑魄沉星录小师弟m
- 退婚夜,我被公主捡尸了白云兴言
- 历史风口,我率领军队统一全球书就
- 明朝的名义云玖龙
- 衣冠谋冢欧阳少羽
- 状元一心打猎,皇帝三顾茅庐言者
- 太虚王座菜鸟猛新
- 无妄仙君毒尧
- 史上最强县令一骑红尘
- 穿越成献帝,我为大汉再续三百年言谈橘汁
- 万浪孤舟,沧海一粟灰烬余火
- 开局逼我替兄参军,拒绝后打猎养妻!他也可怜
- 云起惊鸿客南城巷子
- 大宋枭雄仙庙的马尔高
- 同穿:举国随我开发异世界沈见新
- 穿越后,我从厂仔变成王爷帅气周先森
- 绝品仙尊潇然
- 都市最强战神梁一笑
- 我超有钱睡芒
- 从公爵之子到帝国皇帝老庄屋
- 两界:玻璃杯换美女,买一送一宁衰人
- 签到修仙:我在青城山躺成剑仙慕斯雨
- 祖龙假死,我带领大秦走向日不落!松之江
- 退婚夜,我被公主捡尸了白云兴言
- 综武从抓邀月开始虚无幻界
- 大唐:我有一个武器库孤帆
- 万化仙主,从捡漏废丹开始!子涛
- 史上最强县令一骑红尘
- 替弟从戎成将军,全家跪求我原谅兜兜有米粒
- 重生之我是大明皇太孙朱雄英码奴翻身
- 都市最强战神梁一笑
- 从综武世界开始逍遥诸天沐阳千羽
- 我和兄弟一起穿越红楼爱吃豆豉酱的比丘斯
- 我,秦王世子,用盒饭暴出百万兵蛟变化龙
- 清宫秘史十二章马踏飞花
- 武林风云之九阳传奇息烽客
- 诸天帝皇召唤系统遗落的影子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诗泪洒江湖云里慕白
- 带着基地闯三国安安静静看书书
- 剑影书迷之宝藏寻踪喜欢半减七和弦的子豪
- 乾元盛世系统冀北省的护法神
- 这破系统非要我当皇帝总有那一天
- 开局力挺宁中则,李青萝求放过粤北陈老师
- 大明:朱元璋的好大侄逍遥御风
- 穿越大秦:红颜助国兴还钱100
- 原始蛮荒部落生存记景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