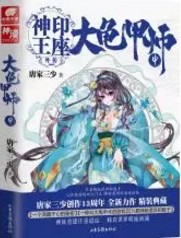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IV 你真是个天使(1/3)
艾伯丝 在距离亚伦的连任竞选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举办结婚纪念日宴会,真是个糊涂的决定。
一年之前,亚伦在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提出这个建议时,艾伯丝正在进行第二轮化疗,她把大半个晚上都花在了马桶旁边。
“明年一定不会这样了。
”亚伦说道。
他站在走廊,尽量避免深呼吸。
他这个人不会在你呕吐的时候帮你撩起头发,不过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会见证你经历的磨难。
他会努力哄你开心,许诺专门为你办一场宴会,而不是为了那些出资人。
她说过想办这种活动吗?哪怕只说过一次?他之所以变得多愁善感,原因在于她得了癌症,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不,他一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还没嫁给他的时候心里就很清楚,他的弱点就是多愁善感。
“来嘛,小艾。
我们理应热热闹闹地庆祝三十周年,”他说,“场地就定在浪花酒店,这次我们只邀请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管他会不会得罪人呢。
” 我根本就活不到明年,艾伯丝心想。
“我们不能在十一月举办宴会,”她说,“你那时要忙着竞选。
”艾伯丝对着马桶又是一阵干呕,却什么也没吐出来。
比呕吐更难受的是连吐都吐不出来。
“不会的,”亚伦说,“我是说,我的确要竞选,可是谁在乎呢?我已经连任十届众议员了。
要是仅仅因为我腾出一晚上庆祝自己结婚三十周年,他们就不选我连任,那就随这些烂人的便吧。
这件事我一定要办,小艾,不管你怎么说。
我现在就给乔治发短信,让他把日程空出来。
” 他当时一定是真的相信她将不久于人世。
可她如今尚在人世,一年过去了,她依然活着。
新长的一头小卷毛,思绪还有些糊涂,胸口落下了疤痕,但是心脏依然在跳啊,跳啊,麻木而机械地跳,活着,还活着。
凌晨4:55,亚伦穿着西装,没系领带。
他白天要飞到华盛顿,晚上八点则要赶回来参加宴会。
这次出差他实在没法推脱。
他的竞争对手,玛尔塔·维拉诺瓦——金发、大胸、共和党人——仗着资本雄厚(并不是在暗指她那对大胸)来势汹汹,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要是错过众议院的这次投票,后果他绝对承担不起。
众议院究竟为什么要在选举前几天安排如此重要的投票,这他不知道。
眼下的局势很糟糕,不只对他个人,而对于每个想连任参选的人来说都很糟糕。
今年真是空前的一塌糊涂。
把宴会前最后的准备事项交给艾伯丝打理,他十分过意不去。
在今天——他们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抛下她,他也很过意不去。
三十年了!简直不敢想象!他们当时一定是婴儿,甚至还没出生吧。
他在她头上印上一吻。
“你走吧,”她说,“一路平安。
都计划好了。
没什么要办的事,我花不了多少精神就能办完。
”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我太幸运了。
我爱你。
纪念日快乐。
” 她提出开车送他去机场,可他说她应该继续睡觉,他已经叫好了车。
艾伯丝翻了个身,想继续睡觉,睡意却迟迟不来。
倘若他把她叫醒,她一定会开车送他去机场。
自从患了癌症,她的睡眠就一直不好,每晚能睡上三个小时已算是走运,白天时总是疲惫不堪。
艾伯丝闭上了眼睛。
就在她昏昏欲睡时,忽然听见扑扇翅膀的声响,像是洗扑克牌的声音。
她睁开了眼睛。
一只鹦鹉径直向她飞来,它通体翠绿,只有脑袋是深红色的,就在它钩形的喙快要撞上她额头的时候,这只鸟忽然飞落在她摘除乳房后的平坦胸脯上。
“太太,太太,”鹦鹉说道,“醒醒,醒醒。
” 艾伯丝说她还想睡觉,但鹦鹉知道她睡不着。
她翻身侧卧,鹦鹉也换了位置,落在她手腕上。
“很多事,很多事。
”鹦鹉说。
“走开,埃尔梅德。
”艾伯丝说。
她并不知道鹦鹉的名字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是西班牙语吗?她怎么就没学过西班牙语呢?天知道,作为一名佛罗里达州政客的妻子,西班牙语可比高中学的那三年拉丁语实用多了。
她甚至连埃尔梅德是雌是雄都不清楚。
艾伯丝仍然闭着双眼,伸手在空中拍打,手臂晃得像风车。
鹦鹉又朝风车飞过去。
“要是不睡觉,我一整天都没有精神。
我今天必须打起精神。
” “埃尔梅德帮忙。
埃尔梅德帮忙。
” “你帮不上,”艾伯丝说,“你走远点才算帮了我的忙。
你让我睡一会儿就算是帮忙了。
” 鹦鹉飞到亚伦的床头柜上,开始梳理羽毛。
这个过程十分安静,不过为时已晚,艾伯丝已经醒了——装睡比强打精神迎接新的一天更耗费体力。
艾伯丝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淋浴洗头发,她洗完出来的时候,鹦鹉正站在毛巾架上。
“拜托,给我留点私人空间好吗。
”艾伯丝说。
埃尔梅德飞到她头上,用粉红色的喙啄她:“保湿!保湿!” 她走进厨房,想倒杯咖啡喝。
她本想把咖啡戒掉,可要是没了咖啡,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她看来,人活着就是不断养成坏习惯的过程,死去则是抛却这些坏习惯的过程。
死亡的地界上既没有习惯,也没有咖啡。
埃尔梅德飞落到她肩膀上。
“我今天不想让你跟着来。
”艾伯丝说。
“埃尔梅德来。
埃尔梅德来。
” “我是认真的,我要去看医生,去美发店、干洗店、花店、裁缝店、珠宝店,而且还要在那个破午餐会上致辞,还有宴会——” “宴会!宴会!” “我根本就不喜欢宴会——” “宴会!宴会!” “你不许跟着参加宴会。
”艾伯丝说。
“宴会!宴会!” “真不敢相信你怎么这么听不进道理,埃尔梅德,而且总是重复说话。
还有,你以为自己很轻,其实你压在我肩膀上重死了。
我觉得你越来越重了。
你的爪子陷进我肉里了,比内衣肩带还勒人,比铂金包还重。
再这样下去我就该找个脊柱理疗师了。
” 保姆玛格丽塔抱着一个大盒子走进了厨房。
“莱文太太,早上好!结婚纪念日快乐!不知是谁把这个包裹放在了门口的台阶上。
”玛格丽塔把盒子放在厨房的台面上。
艾伯丝看了看寄件人地址,是她最忠实的朋友——快递公司。
艾伯丝拿起厨用刀,打开包裹。
盒子里是无穷无尽的气泡纸,里面埋藏着一尊劣质雕像。
雕像约有一只大个儿阳具那么大,树脂做的,花里胡哨的配色十分生硬,像是经过后期上色的黑白电影。
一个面色红润的男人身披托加长袍,背后长着翅膀,手持一只古铜色的犹太六芒星,仿佛那是块盾牌,看来这是位犹太天使。
有犹太天使吗?有,当然有。
《旧约》里就提到过不只一位天使,所以犹太教里应该有天使。
《旧约》里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是犹太人吗?她翻过来看底座,授权证书上说这是梅塔特隆,听着像是个机器人的名字。
谁会给她送这样的东西呢?以艾伯丝的个性,她不是那种谁都会给她送天使的女人。
“哦,真漂亮。
”玛格丽塔说。
俗气的东西向来很对她胃口,她自己的打扮也很俗气。
她油亮的黑头发梳成滑稽歌舞剧女演员的发式,踩着樱桃图案的鞋子昂首挺胸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年轻的胸脯眼看就要托到下巴上。
乔治——亚伦的得力助手——只看了玛格丽塔一眼就说:“你真的想往自己家里招这样的人吗?” “什么意思?”艾伯丝问。
“意思就是,她看着会招惹是非。
” “亚伦岁数大了,我岁数也大了,”艾伯丝说,“我在家的时候比他多,再说,仅仅因为人家长得漂亮就不雇用人家,这是性别歧视。
她很聪明,而且她快要拿到雕塑专业的艺术硕士学位了。
” “招惹是非。
”乔治重复道。
“你喜欢吗?”艾伯丝一边在泡沫纸里翻找留言条,一边对玛格丽塔说。
她估摸着,人们之所以会给她送这种破烂货,是因为他们以为癌症会让她的性格变得软弱。
“那可不行,”玛格丽塔说,“这是别人专门送给你的天使。
” “说不定是别人让我专门送给你的。
”艾伯丝建议道。
“把其他女人的天使拿走,要走霉运的。
”玛格丽塔说。
“要是你不肯收留它,那它只能住进垃圾堆了。
”艾伯丝说。
“把天使丢进垃圾堆要走霉运的。
” “我的霉运还不够吗?”艾伯丝说着,捏住天使的头把它拎了起来,“我才不相信什么霉运呢,”她打开垃圾桶,顿了一下,“你觉得它是可回收垃圾吗?” “别这样,”玛格丽塔说,“说不定你会慢慢喜欢上它的。
” “不可能。
” “那议员先生呢?” “亚伦最恨这玩意儿。
” “好吧,”玛格丽塔说,“把它给我吧。
”她接过天使,把它摆在自己的提包旁边。
“你今晚会来参加宴会吗?”艾伯丝问。
“会的,”玛格丽塔说,“当然会来,莱文太太。
我绝对不会错过宴会!我亲手做了一条裙子,上身是红色的紧身胸衣,下面是带裙撑的黑色长裙,我打算戴上黑色的蕾丝露指手套,把头发梳起来,紧紧地梳在脑后,脸上罩一小块面纱,肯定会非常惊艳。
” “听着就是,”艾伯丝说,“你来参加我的葬礼时也可以穿这身衣服。
” “别那么丧气,莱文太太。
那套裙子很喜庆。
” “玛格丽塔,‘梅德’在西班牙语里是什么意思?” “小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会这样喊,叫人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不要!不要!’”玛格丽塔说。
“那如果在前面加上个‘埃尔’呢?‘埃尔梅德’。
这样意思有差别吗?” “啊,”玛格丽塔说,“这样就没有任何含义了。
” 前台向她道歉,说医生赶不上原定的日程了。
日程之后还有日程,艾伯丝心想。
艾伯丝掏出手机,上网搜索亚伦的国会竞选消息。
她已经下定决心,即便他输了选举她也不在乎。
无论别人对她的评价如何——说她才是夫妻间真正野心勃勃的那个也好,说要是没有她,他最多只能做个高中英文老师也罢——倒不是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她甚至会带着些许期盼迎接他的失败。
“艾伯丝·莱文,是你吗?” 她转过身,是阿莱格拉。
阿莱格拉老了,她看上去一副奔五的样子。
天啊,艾伯丝心想,她不是看上去老,而是真的老了。
她之所以奔五,是因为我已经快六十岁了。
艾伯丝为医院工作时,阿莱格拉曾经与她共事,她们的关系很亲近,人们总是半开玩笑地称她们为“职场妇妇”。
“阿莱格拉,我们好久没见了。
”艾伯丝说。
阿莱格拉亲了她的面颊:“希望你一切都好。
” “我去年生了病,不过现在好些了,”艾伯丝说,“我是来复诊的。
” “好……”阿莱格拉说,“好吧,你气色不错。
” “别撒谎了。
我的气色像屎一样。
”艾伯丝说。
“你看上去真的气色不错……可能有点累。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看上去很累。
” “我们今晚要举办结婚纪念日宴会,”艾伯丝说,“复诊之后我要去美发店。
得想办法把这头不中用的秃毛打扮一下。
” “我喜欢你的发型,这样很时髦,”阿莱格拉说,“而且,我知道宴会的事。
其实,我也会参加。
”阿莱格拉说。
“为什么?”艾伯丝脱口而出。
“哦,我接到了邀请。
”阿莱格拉说,“我猜是你送来的?” 我真应该记住这种破事,艾伯丝心想。
“对啊,”艾伯丝说,“对啊。
”她邀请阿莱格拉时究竟糊涂到什么程度了? “你好像很吃惊啊。
” “我没有。
我……”事实就是,她最近什么事情都记不住。
可能是化疗影响了她的大脑。
“莱文太太。
”前台叫她。
“我接到邀请很开心,”阿莱格拉说,“的确很惊讶,但更多的是开心。
不过,如果你不希望我参加……我是说,如果邀请我只是个意外……” “我真心希望你来,”艾伯丝紧紧握住阿莱格拉的手,那只手冰凉、柔软,阿莱格拉身上散发着鸡蛋花、辛香味和大地的香味,像是檀香,又像是不掺杂质的可可粉,“有时候,我大脑放空的时候比较聪明。
” 阿莱格拉笑了:“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 “我下个星期想约你一起吃顿超级漫长的午饭,”艾伯丝说,“你能答应我吗?” “要是我早点知道你病了就好了。
”阿莱格拉说。
“那时候跟我相处可没什么意思。
”艾伯丝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做些什么……” 她会做什么呢?参加五公里义跑?系条粉丝带?给艾伯丝端来碗鸡汤,好让她喝完以后吐出来?发一条充满同情的推特?“你为什么戴着猫耳朵?”艾伯丝问,“这是我的幻觉吗?还是你真的戴着一对猫耳朵?” “噢!”阿莱格拉羞涩地一笑,抚了抚黑色猫耳朵发带下面的头发,有些难为情,“这是我今年的装扮。
昨天是万圣节嘛。
” “我忘了。
”艾伯丝说。
“不过埃莫里学校的节日庆典安排在今天上午,好像跟测验有关。
我负责分发潘趣酒,有个孩子的妈妈昨晚给我发了条短信,别往潘趣酒里放坚果!谁会往潘趣酒里放坚果啊?我是年龄最大的母亲,所以他们总把我当成跟不上潮流的原始人。
” “莱文太太!”前台又叫道。
“这对耳朵跟你很配。
”艾伯丝边说边走进医生的办公室。
“今天艾伯丝感觉怎么样?”医生问。
他的母语不是英语,他似乎很害怕使用代词。
“艾伯丝发现了一个新的肿块。
”她轻快地说。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艾伯丝傻瓜似的满心欢喜。
保证会作检查!保证会做新一轮化疗!保证会死的!这些都不是值得欢喜的理由,可她就是满心欢喜。
虽然也不是因为今晚的庆祝。
也许是因为发现肿块后反倒松了一口气。
当她在洗澡时发现那个肿块,她觉得自己完蛋了,尽管她知道这是大脑在骗她,给她一个愚蠢的念头。
她的身体执意要长出不正常的增生细胞,这又不是她的错。
艾伯丝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一切都是她的错。
她很强大,却又什么事也做不好。
艾伯丝,异常增生细胞的创造者;艾伯丝,世界的毁灭者。
也许她的喜悦是因为天气。
这是干燥而寒冷的十月里一个干燥而寒冷的上午,季末的飓风没有如期而至。
她的头发尽管所剩无几,却比平常服帖许多。
或许是因为她遇见了阿莱格拉。
倘若不是那件事杀的回马枪,倘若她还有时间,她绝对会约阿莱格拉共进午餐,之后她还会再约阿莱格拉吃一次午餐,而第二次吃饭时,她们会变得熟络许多,她们会点两份甜品分着吃,让叉子齿紧密地交叉在一起,她们会把那些甜品吃得一干二净,然后艾伯丝会对服务生说,好,对了,我要一杯浓缩咖啡,阿莱格拉则会提议一起去上瑜伽课(“那可是哈达瑜伽,小艾,谁都能做。
”),而瑜伽课上,她们当中的某个人会提议组建一个读书会,艾伯丝则会重新调整生活节奏,每天都与阿莱格拉见面,每一天,直到她们其中的一个或者她们双双去世。
阿莱格拉为什么要到辉医生的办公室去?她本该问问的,她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她时常忘记自己不是全世界唯一患了癌症的人。
反过来,她也时常忘记并不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得了癌症。
她说服埃尔梅德在汽车附近等她——鸟类是不能带进医生办公室的。
埃尔梅德站在她那辆特斯拉的发动机盖上,爪子欢快地敲击着车身的喷漆。
它飞落到艾伯丝肩膀上。
“这件衬衫是真丝的,”她说,“你轻点。
” “轻点!轻点!”它说,“晚安!晚安!” 艾伯丝上了车,她的手机响了,谨慎起见,她开了免提——因为当你被各种各样的癌症缠身时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得一种脑癌。
打电话的是塔莎,亚伦在迈阿密的一名助理。
塔莎是新来的,她说办公室出了紧急情况。
不过亚伦的助理们总是反应过激,新来的尤甚。
以他们的阅历,不足以区分“特殊情况”和“紧急情况”,也分不清“危机”和“不幸事件”。
距离选举还有一个星期,什么事情不紧急呢?“让乔治处理不行吗?”艾伯丝说,“我为了晚上的宴会已经把时间安排满了。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办这场可笑的宴会……”艾伯丝挤出一声抱歉的笑。
塔莎说:“或许‘紧急情况’这个词用得不恰当,我还是称它为‘特殊情况’吧。
” “好,”艾伯丝不耐烦地说,“一切特殊情况我都可以放心地交给乔治处理。
” “好!非常好!”埃尔梅德说。
“嘘!”艾伯丝说。
“哦,不好意思。
”塔莎说。
“不,不是说你。
我在和别人说话,”艾伯丝说,“你给乔治打电话吧。
” “好吧,其实事情是这样……”塔莎把声音放得很低,低到艾伯丝听不清她说了什么,她让她大声些,“是一个小女孩。
” “什么?” “这里有个小女孩,”塔莎说,“她说她是亚伦的女儿。
”她低声说道。
“女儿!女儿!”埃尔梅德说。
“不可能,”艾伯丝说,“我们只有儿子。
” “她就在我面前呢,身高大约一米五,戴着牙套,一头卷发。
我估计她有十一二岁——” “不,塔莎,我不需要你给我描述小女孩是什么样的。
你可能不相信,但我以前也是个小女孩,我知道女孩子什么样,我并不想和你争论你面前的是不是个女孩!重点是,你面前的人不是亚伦的女儿,因为我和我丈夫只生了儿子。
”艾伯丝说。
“儿子!儿子!”埃尔梅德说。
“你能不能行行好,把嘴闭上?”艾伯丝说。
“我没说话啊。
”塔莎说。
“不是说你,是别人。
给乔治打电话,就说办公室有个疯丫头,他会告诉你怎么处理的。
我今天没空跟疯子浪费时间。
” “好吧,”塔莎说,“这我都可以做。
可是还有一件事——” “到底什么事?” “她说她姓格罗斯曼。
” 艾伯丝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个名字!“格罗斯。
”她说。
“不,格罗斯曼。
”塔莎说。
“你说第一遍的时候我就听见了。
”她多希望余生再也不必听见这个名字。
“下个星期就要选举了。
”塔莎继续说。
“对,塔莎,我知道。
”艾伯丝说。
“我知道你知道,”塔莎说,“我的意思是,办公室里这么多人,而且过一会儿还有很多人要来办公室,竞选团队、媒体什么的。
事情没解决之前,最好先把她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乔治和议员先生都在华盛顿,他们俩的电话都打不通。
我也不敢发短信,怕被别人看见。
我不想惹出麻烦来。
” 假如真的惹出了麻烦呢?假如艾伯丝不来呢?假如艾伯丝挂上电话到美发店去,按照原计划度过这一天呢?假如艾伯丝不再插手,不给亚伦收拾烂摊子,又会怎样呢?每到亚伦捅了娄子的时候,人们总觉得应该给艾伯丝打电话,这种想法本就让人生气。
有些人难道不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妻子,不让她受到残酷的现实波及吗?为什么没人把艾伯丝当成那样的妻子——那种不必直面自己丈夫缺陷的妻子呢? 多年以前,曾有过一次,艾伯丝没有插手,瞧瞧那件事落得什么下场。
“好吧,”艾伯丝说,“我来接她。
” “我现在该拿她怎么办呢?” “把她塞进扫帚橱里!我不管。
” “扫帚!扫帚!”埃尔梅德说。
“闭嘴。
”艾伯丝压低声音说。
“你是让我把扫帚橱的橱门关上?”塔莎问。
“我没和你说话。
”艾伯丝说。
“那你在和谁说话?”塔莎说,“对不起,这不关我的事。
” 的确如此,这不关她的事。
“我和埃尔……”艾伯丝说,“朋友在一起。
” “朋友?朋友?”埃尔梅德说。
“对,我把你当朋友。
”艾伯丝说。
鹦鹉依偎在艾伯丝的颈窝里,咕咕叫起来。
“我其实不确定这里有没有扫帚橱,莱文太太。
”塔莎说。
“塔莎,你是认真的吗?如今这个世道,太抠字眼要吃大亏的。
我不是非要你找个扫帚橱不可,随便把她放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等着我就行。
地下室、房顶、没人坐的办公位,你想放在哪儿就他妈放在哪儿!”艾伯丝挂断了电话。
这姑娘真是没救了。
“没救了。
”埃尔梅德说。
开车去办公室之前,艾伯丝在手机里找到了瑞秋·格罗斯曼的电话。
瑞秋·格罗斯曼,也叫“有史以来最差劲的邻居”。
没错,这个小女孩——鬼知道她究竟是谁——绝对应该由瑞秋·格罗斯曼处理,而不是艾伯丝。
艾伯丝拨打了号码,但那个号码已经无人使用。
她发动了汽车。
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接连不断。
有些铃声由热情洋溢的声音应答,有些铃声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应答,以后也不会有人应答。
一个穿连衣裙的女生写了一条推特,另一个女生穿着那条裙子的低价翻版写下一张便条——“回复:在任政治候选人开通聊天账号的利与弊”——并得出结论,即:在竞选的这个阶段加入其中,对议员先生来说为时已晚。
每个人对自己在邮件和短信中写下的字句都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谁也不能确定有没有人在监视通信或入侵电脑系统,你的本意或许是想开个玩笑,然而一旦脱离了上下文,搞错了用词的细微差别,还有,别提了,语气的变化,任何内容就都不好笑了。
尽管如此,手机短信还是比电子邮件要好些,邮件比通话要好些,通话比直接见面要好些,直接见面则是人们不遗余力想要规避的状况。
不过,倘若你非和人见面不可,喝一杯比吃午饭好,午饭比晚饭好。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手机恨之入骨,却又无法想象摆脱手机后工作该如何运转。
一个穿牛仔裤的女生向穿连衣裙的两个女生白了一眼,对穿牛仔裤的男生说,穿裙子的女生根本没做什么要紧的事(可每个人都知道,穿连衣裙的两个女生才是真正管事的人)。
一个穿短裙的女生和一个穿运动服的男生正在讨论今年高层选举的局势对低层选举是否有利。
不知是谁把一个印着“莱文2006”字样的软橄榄球随手一扔,有人大声喊:“大家安静,C-SPAN正在播放投票过程!”另一个人大喊:“没人在乎!”又一个人大喊:“我在乎!”两个穿夹克的男生在帮大家点外卖,一个穿连衣裙的女生说她绝对不会替大家买咖啡的,所以连问都别想问她。
一个系领带的男生在修改简历(不过每个人都经常修改简历),一个穿连衣裙的女孩说:“有没有人能给议员先生解释一下,如果推文开头是‘@’的话,要在前面加个句点?”接着她低声嘟囔了句“跟老古董一起工作”。
另一个穿连衣裙的女孩给CNN的熟人发了一封邮件:“纯粹好奇问一句,怎么才能成为代理人?”一个系领带的男生跟另一个系领带的男生打情骂俏,一个穿卡其色衣服的男生偷偷拿走了办公用品,并且自我安慰这是在为自己未来的竞选作储备。
一个穿连衣裙的女孩向电话另一头的母亲哭诉,然后低声哀叹:“我必须坚持到底,不然就前功尽弃了!”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每个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薪水,而且,像所有竞选办公室一样,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年轻。
在过去,艾伯丝认识许多这些男生女生的翻版,不过现在的这些版本她一个都不认识,因此也没人察觉她的到来。
多年来不温不火的名流身份让艾伯丝学会了登堂入室的技巧。
她希望被人注意到的时候,总能被人注意到;当她不想有人注意她时,她几乎从未被人发现过。
诀窍就在于摆出一副很清楚自己要到哪里去的架势,并且换上一副温和而乏味、略带一丝厌烦的神色。
她有时会用手机做道具,配上熟稔的专注神情,这是她(也是其他所有人)用来隔绝外界的壁垒。
道具也可以是一顶不起眼的帽子,但是绝不能用太阳镜。
无论她采用什么办法,年龄越大,那个隐身的开关就越容易开启。
她猜测,那一天过不了多久就会到来,开关永远卡在隐身那一档,永远也不会有人再看见艾伯丝。
艾伯丝来到塔莎的办公桌前,桌子位于她丈夫的私人办公室门口,是一个单独的接待区。
那女孩就坐在桌对面。
她身穿绉布夹克和蓝色牛仔裤,裤子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春日颂小红杏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末世对我下手了一把杀猪刀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我就是馋你信息素[娱乐圈]夂槿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虫屋金柜角
- 失忆后我招惹了前夫萝卜兔子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锦帐春慢元浅
- 剑海鹰扬司马翎
- 武极宗师风消逝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网恋同桌归荼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鱼游入海西言
- 夕照斑衣白骨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循规是笙
- 非典型NTR一盘炒青豆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夕照斑衣白骨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新婚ABO白鹿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404信箱它在烧
- 老大,你情敌杀上门了沐沐不是王子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他只是我男朋友廿小萌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单恋画格烈冶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情敌五军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影帝是棵小白杨闻香识美人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
- 竹马危机萧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