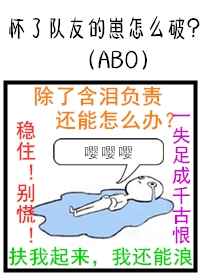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II 无论你去哪儿,你做过的事都跟着你(3/3)
“你飞这么远就是为了请我吃晚饭?”她说。
“当然了,”他说,“凭什么只允许你们玩得那么开心?” “可这本该是个女生独享的周末。
”弗兰妮说。
“我相信简不会介意的,”韦斯说,“你看起来不太高兴。
”他压低声音说。
“高兴啊,”她说,“这是个惊喜。
” “好了,”我说,“我和露比就不打扰了。
见到你很高兴,韦斯。
”我跟他握了手,带着露比离开了。
我们坐电梯回到房间。
“太尴尬了。
”刚到我们那一层,露比便说。
“我也觉得。
”我说。
“她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露比说,“她看样子有些刻薄,可她其实很漂亮,人也善良。
” 弗兰妮住在我们隔壁的房间,那天夜里,我们听见他们的争吵声穿墙而来。
主要是男方的声音,他所在的位置似乎离墙或者通风管道更近,而且他的声音又正好是那种能传得很远的声音。
“我只不过想做点好事,你非要让我感觉像坨屎,谢谢你啊,”他说,“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正好需要这种感觉,弗兰西丝。
” 他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听不清楚。
“你就是个疯子!”他大喊,“你知不知道?我说,你真的就是个疯子。
” …… “你知道奥德拉是怎么说的吗?奥德拉说,以你过去那些事,我真是疯了才会跟你结婚。
我对我的生活可是有计划的,这些计划里可没有疯姑娘的份儿。
” …… “不,不,我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我告诉过她,你当时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可奥德拉说——” “我不在乎奥德拉怎么说!”弗兰妮终于也大喊起来,声音穿透了墙壁。
“你想知道奥德拉还说了什么吗?奥德拉说你明明有四个伴娘,每一个都很乐意陪你买婚纱,可你偏要带婚礼策划人到纽约来,这件事看着就有鬼。
” “我喜欢那个婚礼策划人!” “你根本不了解她。
你其实想说你不喜欢我的姐妹吧?”他问。
“我根本不认识她们!”接着她又说了些我们没听清的话。
话音刚落,房门被摔上了。
两个人中不知是谁离开了房间。
“我的老天啊。
”露比低声说。
我们听过比这更糟的争吵。
婚礼举办之前的几个月里,人们往往会展示出自己最糟糕的一面。
不过,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最糟糕的那一面也是他最真实的一面,而难就难在人们总在木已成舟之后才能认清自己的处境。
“都是平常事。
”我说。
“不幸的新娘各有各的不幸,”露比说,“他说弗兰妮‘过去那些事’是什么意思,妈妈?” “那不关我们的事。
”我说。
“我们可以问问她,”露比说,“我敢说她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 “我们可以问,”我说,“她也有可能会说,不过那还是不关我们的事。
你唯一有权知道的过去,是你自己的过去。
” “还有你历史课要学的那些人的过去。
你真没劲,”露比说,“我要上谷歌搜一下,”她拿起手机,“弗兰西丝——她姓什么来着?” “林肯。
”我说。
“这名字太普通了,”露比说,“弗兰妮是艾力森泉本地人,还是别的地方来的?” “嘿,神探南希!别闹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说,“我猜是别的地方的人。
” “我们可以去看她的脸书主页,”露比建议道,“看看她都认识什么人。
” “你这样像个网络跟踪狂,还像个犯罪分子。
” “好吧,”露比说着放下手机,“我敢打赌,她以前肯定有厌食症,被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 “这么说别人可不好。
”我说。
“我只不过在想象可能的情况,”露比说,“她太瘦了。
” “是吗?”我说,“我没注意。
”我当然注意到了。
婚纱店的店员用了好几个夹子才把那条当作样品的裙子固定住。
弗兰妮的肩胛骨尖利得如同两把刀。
每次我亲吻或拥抱她,都担心自己会把她弄散架。
但弗兰妮也有可能天生就是这样,谁知道呢?盲目猜测别人的外表下面暗藏着什么经历,这种行为太愚蠢了。
而且我想让女儿感觉,她母亲并不关注其他女性的身材,因为我不想让她关注其他女性的身材。
我坚信一位母亲想让自己的女儿成长为什么样的女性,她自己就应该以身作则。
“你真的没注意?”露比说。
“我真的没注意,”我说,“我对其他女性的身材并不感兴趣。
” “你简直是瞎了,”露比叹了口气,“神探南希是谁?” 9 “他其实没那么糟,”弗兰妮在回程的飞机上对我说,我坐在中间,弗兰妮和露比分坐在我两侧,露比正戴着耳机做作业,“他有时候很善良,”弗兰妮说,“而且他对我们所在的社区充满关怀。
比方说,镇上的动物救助站被迫要关门了,他就去拜见每一个跟他买卖过房子的人,最终筹到了足够的钱让救助站继续运营。
正是他的这个特点吸引了我,他的公民精神,而且非常勤恳。
” “他还好,”我说,“策划婚礼的确会让人压力很大。
” “嗯,”她说,“可你还是不喜欢他。
” “我并没有不喜欢他,”我说,“毕竟我不是那个跟他结婚的人。
” “好吧,”她说,“那你会嫁给他吗?” “不会,因为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说。
“我是说,假如你是我,你会嫁给他吗?” 说实话,我不会,可她不是我女儿,甚至连我的朋友也算不上。
我很喜欢她,但她只是我的客户。
“可以假设,但我并不能确定你的处境,”我说,“所以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顿了一下,“你爱他吗?” “我爱你。
”弗兰妮说。
“不,”我说,“我不信。
” “这里太晒了,我感觉我快被晒伤了。
透过玻璃也能被晒伤吗?”弗兰妮拉下遮阳板,“我是说,我像爱朋友一样爱你。
我喜欢你对待事物的坦诚。
”弗兰妮说。
10 弗兰妮婚礼前夕,我又梦见了阿维娃·格罗斯曼。
阿维娃依然很年轻,二十岁上下,而我是她的婚礼策划人。
“要是特地给头发做个造型,”她说,“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撒谎。
” “你喜欢什么样子,就照什么样子做。
”我说。
“亚伦不喜欢我留卷发。
”她说。
“无论你作什么决定,都是正确的。
”我说。
“人们只有在没认真听或者不想承担责任的时候才会那么说。
你能帮我把拉链拉上吗?”她说。
她转过身,我看见她婚纱拉链中间裸露着一大片皮肤。
“怎么了?”她说,“不会是太紧了吧?” “等一下。
”我扯住婚纱两边,使出全身的力气,居然真的把拉链给拉上了。
“你还能坐下吗?”我问,“还能呼吸吗?” “谁需要呼吸啊?”她慢慢地坐下,我听见婚纱龙骨发出的咯吱声,暗地里为婚纱被撑破做好了心理准备。
“活在现实中的女孩才要呼吸呢,”她微笑着抬头看着我,“我从没想过你会成为婚礼策划人。
” 我醒来时浑身是汗。
我看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可能会下雪。
但是并没有下雪。
天气寒冷而澄澈,路面没有结冰,航班都没有延误,说好出席的人也都来了。
尽管连天气也给了这对新人祝福,可前一夜的梦境整天在我心头萦绕不散,我对这一天觉得非常不安。
韦斯的姐妹们还算随和,不过她们彼此亲密得让人难以置信,那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亲密。
韦斯那位不受待见的好朋友奥德拉则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我一眼就看出——也许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其实暗恋他。
这一天对她来说是场悲剧,所以我对她格外体恤,尽量和善地对待她。
我知道爱上一个并不爱你的人是什么感觉。
席勒把花摆好后跟我打了个招呼:“所有兰花都准备妥当了,太太。
你想不想趁我离开前再去看一眼?” 我跟随席勒走进宴会大厅。
映入眼帘的兰花模样有些奇怪——花朵孤零零的,透着几分可怖,仿佛是某种外星生物,而且花盆和根须看上去很不协调。
不过这未必不是件好事,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婚礼和别人的一模一样,而且以我对她的了解,兰花十分符合弗兰妮的气质。
“你觉得怎么样?”席勒自豪地说。
“你干得不错。
”我说。
“真希望每个新娘都想要兰花。
我觉得这样有意思多了,”席勒说,“这可能是所有我筹备过的婚礼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席勒掏出手机开始拍照,“等你拍完专业照片以后,能不能发给我几张?你觉得弗兰妮会介意吗?” “我想她会很开心的。
”我说。
“弗兰妮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 “对。
”我说。
“怎么?你不同意。
” “我说‘对’。
” “可你的语气好像带些别的意思。
”他说。
我并不认为我的语气有什么不对头,不过我还是四下看了看,以确认除了我们两个以外没有别人。
“这并不是针对弗兰妮,”我说,“而是我保持了许多年的一个想法。
所有这些细节——花卉、婚纱、宴会大厅——这些看上去好像都很重要。
我的工作就是要让人相信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不过归根结底,无论他们选什么,最终不过是几朵花、一条裙子和一个房间。
” “关键是什么花!”席勒说,“什么样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婚礼就像一只特洛伊木马。
我向人们兜售美丽的梦境,好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婚姻本身引开。
他们选择这些东西是为了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为了自我感觉没那么平庸,可是有什么事情比选择结婚更加平庸呢?” “你这个人想法太可怕了。
”席勒说。
“可能是吧。
” “天啊,你心情不好。
”席勒说。
“兰花好像让我格外伤感。
”我说。
“我不确定这个发型好不好看,”仪式开始前,弗兰妮说,“看上去过于复杂,而且那个人盘得太紧,我感觉快被勒晕过去了。
”她的发型是两条粗壮的发辫在头顶编成一顶王冠。
她本想要年轻姑娘参加室外音乐节时那种随性的发型,可如今,两条辫子像长了毛的蛇,要把弗兰妮从头顶生吞下去。
“把它拆开。
”我说。
“那能行吗?” “优雅质朴的风格,”我说,“你婚礼的主题就美在这里。
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 她拆开头发:“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你可能会雇用另一个我,”我说,“可能是个来自波特兰的我。
” “我真希望你没有听见那句话。
我们第一次见面韦斯就那样说,实在难听了,”她说,“他想让大家都喜欢他……他以为这样会让你印象深刻。
” “他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说。
她大笑起来,马上又掩住了嘴。
“哦,天啊,”她说,“我马上就要嫁给他了,你肯定觉得我这个人也很差劲,”她顿了一下,“你可能会想:‘她怎么能爱上那样的男人?’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
” “我真喜欢你。
”我说。
我把弗兰妮的服装袋拉上,又把鞋和衣服装进她的运动提包。
“哦,这些事不用麻烦你了!”她说。
“我很乐意做,”我说,“这是我的工作。
” “好吧,简。
谢谢你。
你可能已经被我说烦了,但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母亲……”弗兰妮的眼睛湿润起来,但我并不想让她哭,因为化妆师已经走了,便递给她一张纸巾。
“沾一沾,”我说,“不要抹。
深呼吸。
” 她沾了沾眼睛,深呼吸。
“我读到过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在加利福尼亚,”我说,“她假扮成伴娘,趁参加婚礼的人不注意时把婚宴上的财物洗劫一空。
我记得她偷过大约五十场婚礼。
” “但她最终还是被抓住了。
”弗兰妮说。
“最后被抓了,但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最天衣无缝的犯罪方式。
婚礼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别的地方。
” “除了你以外的每个人。
”她说。
“而且有一半的客人互相都不认识。
”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弗兰妮说。
“我一点也不认为你是个差劲的人,而且你应该知道,人们会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结婚,爱情只是其中一个——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冷酷无情——但几百场婚礼策划下来,我甚至不能确定爱情是不是你嫁给一个人的最重要的原因。
” “哦,简,这是唯一的原因啊。
” “好吧。
”我说。
“可假如我看错了韦斯,这可是终身大事。
”她说。
“并不是,”我说,“假如你发现自己看走了眼,也没人会判石刑把你砸死。
没有人会在你胸口戴上一个红色的‘D’。
你活在二十一世纪。
雇个律师,你结婚时带来了什么,可以尽数带走——基本尽数带走——改回自己的姓氏,到别的地方去,重新开始。
” “你说得真轻松。
要是我有了孩子呢?” “那样确实会更加复杂。
”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她说。
“听我说,要是你真的认为这是个错误,我现在就可以出去,让所有人都回家。
” 11 度完蜜月,韦斯到店里付给我剩余的钱。
“弗兰妮说她要来,我告诉她没必要。
简的办公室离我只有大约一百五十米。
” 我接过支票,放在抽屉里。
“真的只有一百五十米远吗?”我问。
我的工作特点让我很少斤斤计较,但韦斯身上的某种特质让我总想反其道而行之。
度完蜜月回来,他晒黑了不少,待人也比从前更加傲慢,来结算欠款还以为我会对他感恩戴德。
“可能有八百米吧。
”他说。
“即便是这样,那也比一百五十米远。
”我说。
“随你怎么说,简。
”他一副懒得和我一般见识的样子,“这是弗兰妮给露比买的。
”他把一个塑料水晶球摆在我桌上,里面只有水和几个塑料零件:一只鼻子、一顶礼帽、一根胡萝卜、三块木炭。
“这是佛罗里达的雪人。
”他说。
“她考虑得真周到。
”我说。
“谢谢你做的一切,”韦斯说,“婚礼很美,而且我知道你的友谊对弗兰妮来说意义非凡。
”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我说。
他转身要走,又转了回来:“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啊。
”我说。
“我可不这么想。
奥德拉听见了你和弗兰妮的谈话。
她说你差点就劝服她不和我结婚了。
”韦斯说。
“我觉得奥德拉其实暗恋你。
我猜她只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想搅起事端,”我说,“因为事情并不是那样的。
” 韦斯点点头:“是因为我让你想起了他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我说。
“你尽可以装傻,不过我在雇用你之前调查了你的背景。
我只是想确认你没有犯罪前科。
你的确没有——算是没有吧。
但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的真名。
” 露比走进门来。
“你好,韦斯特先生。
”她说。
“嘿,小露比。
很高兴见到你。
”他笑着跟她握了握手。
“我正要送韦斯出去呢。
”我说。
“替我跟弗兰妮打个招呼!”露比说。
“没问题,”他说,我把他送到门口,他即将迈出门槛时压低声音说,“你不用担心,简。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就连我妻子也不会说。
这件事跟谁都没有关系,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 过去的事永远不会真的过去。
只有白痴才会相信。
我走到门外,在身后带上了门:“我不知道你以为自己知道些什么,但你其实一无所知。
” “别装了,”他说,“连照片都有——” 我打断了他:“即便这件事是真的,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我并不是在威胁你,简。
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下,”他说,“要是大家知道你是性丑闻里的明星主角,恐怕对婚礼策划的生意没多少好处。
” “有意思,”我说,“你观察事物的角度真有意思。
你还年轻,可能不记得——那时候连我都还没出生——不过在1962年,约翰·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作过一番演讲,提出了共同毁灭原则。
你记得吗?” “当然了,”韦斯说,“就是说,只要你手里的炸弹比对手更多,你就可以高枕无忧。
” “你这么说过于简单了,”我说,“不过既然你想从政,知道这个原则对你有好处。
”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你自认为有我的把柄。
而我千真万确有你的把柄,”我说,“我知道弗兰妮的事,她的过去。
” “她不会告诉你的。
”他看了我一眼,又移开了目光。
“镇子这么小,如果你参加竞选,那你这个未来的艾力森泉大人物的前景可有点渺茫,有个那样的妻子……” “闭嘴。
”他说。
“即便你把对我的猜测告诉别人,又能把我怎样呢?人们或许会感兴趣,也有可能不感兴趣。
我不过是个普通人,不需要其他人为我投票,明白吗?再不济,我总是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给人策划婚礼。
”我耸耸肩膀。
“你真是个贱人。
”他说。
“可能吧。
我猜你看见的是这么回事,而我之所以这么猜,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阿维娃·格罗斯曼是我在迈阿密大学的室友,我们过去关系很好,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也没有她的消息。
告诉你吧,韦斯,我有时还会梦见她。
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为情,不过更让人难为情的是你竟然犯下这样的错误。
但我不怪你,谁知道你在网上花低价能买到什么破背景调查?你没有把这件事查清楚情有可原。
你是个大忙人,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用这件事要挟你。
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这就是道德沦丧的标志。
” “谢谢。
”他说。
“你看,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向他伸出手,“跟我握握手,”我告诉他,他照做了,“跟你合作很愉快。
希望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 我望着那个窝囊废离去的背影,虽然算不上一溜小跑,但他脚下很麻利,迫不及待地想离我远一点。
我心想,韦斯·韦斯特,你跟亚伦·莱文根本没法比。
不过,这么说可能有失公允。
很难说今天的我遇见莱文会对他作何感想。
也许他跟韦斯·韦斯特的确有几分相像——他们都是自大的野心家。
在莱文身上,这些特点被其他气质中和了,比如他的聪慧,比如他对身边人强烈而真挚的同情心。
话虽如此,我还是得说……抛开这一切不谈,我对莱文的评价更好,也许是因为与他相识时我还处在更容易被打动的年纪,因为与他相识时我还年轻。
12 五月,露比快过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碰巧看见韦斯·韦斯特从办公室走出来。
他正往集市广场的方向走,我与他相对而行,要去席勒的花店——我在那里约见了一对即将结婚的新人,爱德华·里德和爱德华·安第维洛,大家叫他们里德和艾迪。
里德是一位园林景观设计师——他婚礼上的花卉绝不可掉以轻心;他想要的是“建筑学园艺”风格,只有席勒能胜任。
艾迪在弗兰妮工作的学校做老师,里德和艾迪都参加了林肯、韦斯特夫妇的冬季婚礼,他们很喜欢我的策划。
我想他们看中我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有为他们重名这件事而大惊小怪。
“大家的反应让人很厌烦。
没错,我们两个重名,”我们讨论婚礼邀请函时艾迪说,“我们是两个重名的男人。
这种事时有发生。
没什么稀奇,也没什么好笑的。
”婚礼日期定在八月,主题是“精英派对”。
顺便说一句,缅因州在去年十二月通过了同性婚姻的法案,最直接的成效是同性婚礼让我的客户数量比翻了一番还多。
我甚至在考虑雇用几位全职员工。
回到正题,韦斯·韦斯特正在打电话,他一边通话一边指点江山,仿佛是戏台上的演员,又仿佛世界之大,只容得下他自己,其他人都不存在似的。
又或者我们也存在,只不过我们生来就要做他的观众,瞻仰这通电话大戏,为这位精明强干的房产中介而折服,如此种种。
他朝我迎面走来,我也迎着他走去。
我知道他并没看见我,但即便看见我,他也不会为我让路的。
他没有为那位绳子乱成一团的遛狗者让路,没有为那个推着婴儿车带孩子的女人让路,没有为走出邮局的老人让路,也没有为牵着手的少年情侣让路,他凭什么要为我让路呢? 那天下午我只觉得洒脱利落,决定试试露比提出的假设——假如一个人向你迎面走来,而你坚决不让路,会发生什么事。
那天阳光和煦,街上没有积冰,我甩开手臂大步向前。
我径直向他走去,眼看就要撞在一起了。
我的鼻尖离他只有大约二十厘米远了,我依然勇往直前。
他让开了。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表妹软玉娇香渊爻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与婠婠同居的日子李古丁
- 我始乱终弃前任后他们全找上门了倔强海豹
- 起点文男主是我爸林绵绵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春日颂小红杏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综]混沌恶不想算了!安以默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同桌乃是病娇本娇候鸟阳儿
- 我就是馋你信息素[娱乐圈]夂槿
- 射雕英雄传金庸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乾坤剑神尘山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流氓老师夜独醉
- 他从雪中来过期白开水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真爱没有尽头科林·胡佛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情终孤君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星星为何无动于衷秋绘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单恋画格烈冶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鱼游入海西言
- 夕照斑衣白骨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春生李书锦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情敌五军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情终孤君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夏日长贺新郎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夕照斑衣白骨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循规是笙
- 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后桑奈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替身夺情真心
- 财神在身边金家懒洋洋
- 怀孕之后我翻红了[娱乐圈]核桃酸奶
- 流量小生他天天换人设西西fer
- 轻狂巫哲
- 猪肉铺与小精英沐旖乘舟
- 万物留痕汉堡年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