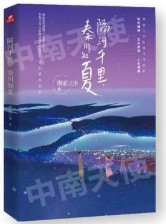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部 13(3/3)
哦!抱歉,哦!”我冲每一位恼火的先生女士招呼了一路,磕磕绊绊地碰到了许多双腿,我步履蹒跚地穿过了一排座位,朝引座员和大门走去。
和舞台的喧闹相比,外面的大堂真是清净。
意大利人正坐在衣帽间看报纸。
我走向他,他嗤笑一声。
“他没在这儿。
”我问起比尔时他回答道,“表演一开始他就不在这儿了。
你要拿斗篷吗?” 我说不用了。
我离开剧院,向德鲁里巷进发——我很在意我的西装、闪亮的皮鞋还有别在翻领上的花。
走到米德尔塞克斯时,我看到一群男孩正在研究节目单,并对着表演评头论足。
我走上前,越过他们的肩膀猛瞧,想找出那个我需要的名字和节目。
沃尔特·沃特斯与姬蒂,我终于看到了。
我震惊地发现姬蒂去掉了“巴特勒”的姓氏,还得借由沃尔特的旧艺名上戏。
如比尔所说,他们差不多排在下半场的开头——单子上的第十四个节目,排在一名歌手和中国魔术师后面。
票亭里坐着个穿紫罗兰色裙子的姑娘。
我走到窗前,朝大厅点点头,“现在谁在台上?”我问道,“第几个节目了?”她抬起头,看见我的装束,嗤嗤地笑了起来。
“你迷路了,亲爱的,”她说,“你要看的是歌剧,就在拐角那儿。
”我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她收起微笑,“好吧,阿尔弗雷德爵爷[45],”她随后讲道,“现在是第十二个,贝拉·巴克斯特,东区的考克尼女歌唱家。
” 我买了张六便士的票——当然,她做了个鬼脸:“早知道我们应该铺块红地毯的。
”实际上,我不敢坐得离舞台太近。
我想象比利小子跑来剧院告诉姬蒂,他见着我了,还有我的打扮。
我依然记得,在一个小剧场里,当你踏出聚光灯,你就能看到观众席和舞台离得多么近。
当然啦,加上我的外套和领结,我会变得相当显眼。
要是姬蒂在我看她表演时瞧见了我,她本应为沃尔特献歌,眼神却要与我交汇,那将会多么可怕啊! 所以我去了楼上的边座。
楼梯特别窄,我转个弯看到一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
我需要侧过身,贴着经过他们。
就和票亭里的姑娘一样,他们瞪着我的西装,随后嗤笑起来。
隔着墙我就能听见乐队的敲敲打打。
等我登上最高那级台阶到达门口时,敲打声更响亮了,我的心脏随之在胸腔里剧烈跳动着。
最后我穿过大厅,走进昏暗炫目的灯光中,热气、烟雾还有人群散发的臭味几乎让我踉跄。
台上的女孩穿了身火红的裙装,她扯动下身的裙子,好露出里面的长袜。
她唱完一首歌时,我正扶着柱子让自己站稳。
之后她又唱起了另一首歌。
观众似乎对此心知肚明,送上了掌声和口哨。
在掌声渐弱前,我穿过走道找到一个空位。
它一旁就坐着一长串男孩——显然,这是个糟糕的选择。
他们看见我的观剧套装和胸花时,聚拢到一块,嗤嗤窃笑。
其中一个举起手咳嗽一声——好像在说“有钱人!”。
我不看他们,转而专注地看向舞台。
过了一会儿,我掏出一根烟点燃。
划火柴时,我的手在颤。
考克尼的女歌唱家终于唱毕,赢得阵阵喝彩。
舞台清空了一会儿,观众席传来了喊声、脚步声和骚动。
乐队奏响了一段叮叮当当的中式旋律,迎来下一个节目,引得我前排的一个男孩跃起,大叫道:“蒲叮叮!”幕帘升起,魔术师和女孩登场,台上还有口黑色箱子——和戴安娜卧室里的那口没啥差别。
魔术师响指一打,出现一阵闪光,噼啪作响,接着喷出一股紫烟。
看到这些,那群男孩把手指贴近唇边,吹响口哨。
我已经看过,或者说我觉得自己看过上千遍这样的演出。
可现在的我,双唇紧紧夹着香烟,看着这一幕,心中愈发难受不安。
我回想起自己坐在坎特伯雷宫的包厢里,心脏怦怦直跳,紧攥着那副蝴蝶结手套的时光,那些日子似乎遥远又陌生。
可我曾经对这些如此熟悉,我抓紧了座位上发黏的丝绒布套,望向舞台通向侧翼的一隅,隐约看见有根缆绳垂在灰蒙蒙的地板上,我想到了姬蒂。
她就在那儿,就在帷幕后面的某处,也许正在调整自己的装束——不管她穿了什么;也许在和沃尔特或是弗洛拉聊天;也许听着比利小子告诉她碰见我的事,愣愣地出神——也许微笑,也许落泪,也许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没想到呢!”——然后将我抛在脑后。
我把这些可能都想了一遍,此时魔术师变起了最后一个戏法。
又来了一阵闪光,然后是更多的烟雾:它们甚至飘到了楼上的边座,呛得全体观众纷纷咳嗽,可他们一边咳嗽一边发出欢呼。
帷幕降下,又是短暂的清场,以准备下一个节目。
随着灯光师更换了聚光灯的滤光片,舞台上闪过蓝色、白色和黄色的光芒。
我抽完一支烟,又摸起第二支。
这时,坐在我那排的男孩们都见到了我的动作,于是我递上烟盒,他们一人拿了一支,说着:“真大方。
”我想起了戴安娜。
我猜想要是歌剧已经结束,她会不会还在等我,一边咒骂一边拿节目单拍着自己的大腿?或者她丢下我,一个人回费里西蒂广场去了? 可之后音乐奏响,帷幕拉起。
我望向舞台——沃尔特登场了。
他看上去特别壮,比我记忆里还要壮。
也许他又长胖了,也许他在演出服里垫了些东西。
他的小胡须精心梳理过,显得特别扎眼滑稽。
他穿了条格纹阔腿窄脚裤,配了件绿丝绒的外套,头上戴着圆顶吸烟帽,烟斗插在口袋里。
他身后挂着张会客室的布景,身旁放了把扶手椅,他靠在上面唱歌。
舞台上只有他一个人。
我从没见过他穿演出服以及带妆的样子。
他和我有时梦里见到的样子大不一样——梦里的他披着松垮的衬衫,胡须湿漉漉的,手放在姬蒂身上——我又看向他,皱起眉,看到他站在那儿,心里却没什么感觉。
他是个温和的男中音,唱起歌来悦耳动听,他的首个亮相就博得了一阵掌声,现在又迎来第二轮赞赏的鼓掌,还有一两声喝彩。
然而,他的歌曲内容却很奇怪:歌里在唱他走丢的儿子,名叫“小杰基”。
这歌分成好几节,每部分都以相同的副歌结束——大概是这样唱的,“在哪儿呢,哦,小杰基现在在哪儿呢?”我感到这场景真是诡异,他独自一人唱着这样一首歌。
姬蒂在哪儿呢?我深吸了口烟。
我没法想象她戴着丝质礼帽,配着领结,拿着花,融入这样的场景里…… 突然间我脑海中生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沃尔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拿它擦了擦眼睛。
我就猜到接下来他会提高声音开始唱副歌,不少声音加入进来,齐声唱道:“在哪儿呢,哦,小杰基现在在哪儿呢?”我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心想,千万别是那样!哦求你了,求你了,千万别是那样的演出! 可偏偏就是那样。
沃尔特正哀怨地唱着,舞台边传来一个尖尖的嗓音:“你的小杰基在这儿呢,父亲!这儿呢!”一个身影奔上舞台,抓住他的手,并亲吻起来。
那是姬蒂。
她穿着一身小男孩的水手服——一件肥大的白衬衣,系着蓝色宽腰带,白色的灯笼裤,长袜子,以及一双棕色的平底鞋,她背后还有顶草帽,用缎带拴着。
她的头发又留长了,梳成了一个卷。
现在乐队奏起另一段旋律,她和沃尔特唱起了二重唱。
观众为她送上掌声与微笑。
她跳起来,沃尔特弯下腰在她面前摇了摇手指,全场大笑。
他们喜欢这个段子。
他们喜欢看到姬蒂——我可爱、俏皮、神气的姬蒂,穿着及膝长筒袜扮演她丈夫的孩子。
他们看不到我涨红了脸,尴尬万分。
就算看到了,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为何会如此。
就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
我只是在可怕的羞耻前感到痛楚。
哪怕他们对她发出嘘声或是朝她扔鸡蛋,我都不会这么难受。
可是他们喜爱她! 我努力看向她。
这时我想到了我的观剧镜,便从口袋里掏出来举到眼前。
透过镜片望去,她离我很近很近,近得就像在做梦一样。
她的头发尽管更长了,但还是栗色的。
她的睫毛还是那么长,身段依旧像柳树般纤细。
她把她可爱的小雀斑遮盖起来了,取代它们的是几点滑稽的污垢。
可是我——曾经如此频繁地用手指触摸过它们——相信自己能够隔着妆容捕捉到下面的形状。
她嘴唇依然那么丰满,唱歌时亮晶晶的。
在唱段中间,她抬起嘴巴,把吻落在沃尔特的胡须上。
看到这儿,我扔下观剧镜。
我发现旁边的男孩们正一脸嫉妒地盯着我的观剧镜,于是把它递给他们传着看——最后大概是传到了顶层楼座的一个姑娘手里。
我看回舞台,姬蒂和沃尔特看上去变得特别小。
他低低地坐在椅子上,把姬蒂拉到膝上坐着,她抱着胸,穿着男孩单鞋的脚不住地摆动。
我一眼也看不下去了。
我站起身。
男孩们叫嚷起来——我并没听清。
我跌跌撞撞地穿过走道,找到出口。
回到皇家歌剧院,我发现歌手依然在台上尖叫,铜管依然隆隆作响。
这还只是我隔着门听见的。
我不敢一路穿过正厅坐回戴安娜身边,也无法直面她的不悦。
我把票给了衣帽间的意大利人,之后坐到了大堂的天鹅绒椅子上,看着街道渐渐拥挤起来,有等候的马车,有卖花的女人,还有妓女和男妓。
最后传出“好极了!”的欢呼,以及赠予女高音的喝彩。
剧院的门大开着,大堂里挤满了喋喋不休的人群,戴安娜、玛丽亚,迪基还有狗适时地出现了,她们看见我等在一旁,走上来打着哈欠斥责我,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说我在男厕所里犯了恶心。
戴安娜把手放上我的面颊。
“看来今天的惊喜你是受不过来了。
”她说道。
可她的语气极为冷淡,返回费里西蒂广场的一路上我们均是一言不发。
胡珀太太把我们引进门,随即把身后的大门上了闩,我随戴安娜走到她的卧室,但从她身边走开了,走向自己那间。
正要过去时,她把手放上我的胳膊,问道:“你要去哪儿?” 我甩开自己的胳膊。
“戴安娜,”我说道,“我感觉糟透了。
让我一个人待着。
” 她又抓住了我。
“你感觉糟透了,”她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你觉得你的感受会和我有一丝半点的关系吗?马上到我的卧室来,你这个小荡妇,还有,把衣服脱了。
”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不,戴安娜。
” 她靠近我说:“什么?” 有钱人在说“什么”两字时有种特别的调调:这个词被磨尖磨利了,从他们口里冒出犹如一把匕首出鞘。
这就是戴安娜现在的样子。
在那条昏暗的走廊里,我感觉芒刺在背,萎靡不振。
我咽了口唾沫。
“我说了‘不,戴安娜’。
”但声音很小。
可当她听完,一把抓起我的衬衫,我一个趔趄,说道,“放开我,你弄疼我了!放开我,放开我!戴安娜,你会扯坏我的衬衫的!” “什么,你说这件衬衫?”她应声道,手指随即插进纽扣下面猛扯,直到衬衫被撕裂,露出了我光裸的胸脯。
随后又抓住我的外套从我身上剥下——全程她一边动手一边喘着粗气,四肢紧紧地挨着我。
我摇摇欲坠,靠在墙上,用胳膊挡着脸——我以为她会揍我。
可最后我看见她脸色铁青,不是因为盛怒,而是因为欲望。
她拿过我的手,将手指放在了礼服的领口。
我悲哀地发现,这才是她想要我做的。
我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下体一颤。
我用力拉扯她的蕾丝,听到了几处针脚崩开的声响,这声音对我起了作用,就如同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
我将她那件黑白银三色的礼服扯下,这件从沃斯买来与我的服装相配的礼服现在变成一堆破布踩在我们脚下。
她让我跪在这堆破布上干她,直到她一次又一次达到高潮。
之后她还是把我送回了我自己的房间。
躺在黑暗中,我瑟瑟发抖,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来。
床边的衣柜上,我的生日礼物在星辉下闪着微光,是那块腕表。
我拿起它,感受它在我指尖的凉意。
但当我把它贴近耳朵时,我战栗了——它一直都在念着:姬蒂,姬蒂,姬蒂…… 我丢开它,把枕头捂在耳朵上想要隔绝那个声音。
我不会哭!我不会哭!我甚至不会去想。
我只会让自己屈服,永远地,沉溺于费里西蒂广场没心没肺的日子,再也感觉不到季节的变迁。
那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我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而我漂亮手表上的指针正缓缓地掠过这些日子。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她是男主好兄弟发电姬
- 你未曾坠落星海南薄荷
- 爱豆家里有道观言朝暮
- 浮生若梦1:最后的王公缪娟
- 营养过良芥菜糊糊
- 学完自己的历史后我又穿回来了荔箫
- 从火影开始卖罐子剑符文
- 反派他过分阴阳怪气[穿书]从南而生
- 人渣味儿四月一日
- 法师乔安程剑心
- 修真大工业时代试剑天涯
- 寄生谎言余姗姗
- 穿越后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来宠我梦.千航
- 锦鲤大佬带着空间重生了浮世落华
- 七零金刚芭比非酋猫奴
- 入骨娇宠烟云绯
- 田园小花仙[快穿]眯眼笑笑
- 大将军和长公主洬
- 大佬她不想回豪门梦.千航
- 有朝一日刀在手退戈
- 山河盛宴天下归元
- 谍变黯然销魂
- 相公是男装大佬兆九棠
- 梦魇图鉴收集记录[无限流]酉时火
- [综]重生后我的结婚对象又换人了风的铃铛
- 天灾前崽崽上交了种植空间秃猫追毛球
- 她是耽美文校花女配奶绿不绿
- 川崎浮吞
- 我能看穿诡异附身大侠戴草帽
- 丫鬟命我是西门
- 重生后从网红到娱乐圈神豪花雨无忧
- 你走丢之后大学习象
- 全球动漫降临现实流水无情FD
- 爱的关键词土笋冻
- 都市神豪:开局解锁一亿亿资产滘南大街
- 重生95:带妹赶海致富,喂饱全家煜煜吃鱼鱼
- [综漫]混乱(NP)诉与青山
- 喃喃白兰氏鸡精
- 荣宠手札[清]一条咸鱼0
- 吃货太子团宠日常[清]粉色嫩蹄
- 诸天末世军团系统不痴刀
- 我!系统!懂?!云月六年
- 孤鹰惊世放牛的野人
- 列克星敦号舰队指挥官太平洋萌新
- 重生悍匪之快意恩仇阿南德龙
- 锈色的时光每时每刻都很好
- 前女友母亲怀上双胞胎,她急哭了草鹿久千流
- ?盛肉不颠勺
- 歧途(姐弟骨nph)睡不醒的小雨
- F1:开局车王教我开赛车笑傲浆糊999
- 惊悚神祇故骨
- 我在饥荒年代,成功诱拐了王爷秋云不觅
- 渣了疯批女主后她黑化了[快穿]八两白酒
- 长恨书(古言 先婚后爱)柳边
- 群鸟沉默时Grauweg
- 秋雨有来信(校园 1v1 h)树耳
- 我在西游搞黄油NPH切西亚
- 乖娇(1v3 兄妹 h)惊春时
- 戒不掉她的手面具
- 堕爱(西幻 复仇 NPH)日之白月
- 風月录王局长
- 群星间迷航之花[ABO NPH]冥王星
- 每日情报,你实习警察一等功拿到手软?白熊
- 你假死嫁白月光在先,我再婚你哭什么麦兜兜
- 乱世,在尘埃中崛起芜悔
- 男主出轨合集(np)雪梨汁
- 拯救mob文女主计划(np)俺就是咸鱼
- (强制h)什么模拟世界?我要回家!秋月白
- 这爱真恶心郑楠
- 快穿之病娇反派llllx
- 【全职高手】成为黄少天的猫后云声
- 七零千里姻缘一线牵了冥
- 把我偷走吧愚礼
- 沙雕攻穿书后从下有心
- 极品社畜当上假少爷风听我令
- 假少爷他柔弱可妻一只胡萝卜酱
- 这个反派对主角是真爱啊我不是晓七
- 每日情报,你实习警察一等功拿到手软?白熊
- 沪上危情我系统呢
- 重组家庭的你和哥哥们(第二人称|兄弟夹心)lily在复健
- 快穿之病娇反派llllx
- 炮灰不做工具人蓝桥空
- 谁说AA恋不行[电竞]通幽博士
- 虺(h)舟渡白
- 泠泠听春雨(1v1 h)卷心菜
- 白月光拒绝渣攻求复合君九少
- 我能看穿诡异附身大侠戴草帽
- 大乾废太子,皇帝跪求别造反凌御天下
- 嘴和心的南辕北撤派翠克大星星
- 重生八零年:我狂吃能力果实,宠哭妻女小兵头子
- 小王的彩票人生尹木
- 清穿之四福晋只想种田蒹葭是草
- 后宫佛系指南不枝周
- 孤鹰惊世放牛的野人
- 全球SSS级警告,龙神出狱了!莫语听风吟
- 全喵界都在等我破产娜个小作家
- 列克星敦号舰队指挥官太平洋萌新
- 老头重生卖掉铁饭碗,白眼狼妻儿傻了!胖白在摸鱼
- 都市异能之凌霄传奇章台杨柳007
- 全球神祇峡谷之巅达芬奇.CS
![非典型求生欲[快穿]](https://www.nothong.com/img/426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