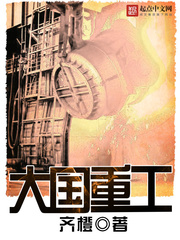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民国廿二年•夏•上海(3/3)
曲终人散,人也朦胧地入睡了。
怀玉睡不着,顺窗望出去,满天的星繁密忙乱,虽然全无声息,然而又觉一天热闹意。
整个上海,陌生的城市,开始安静地入睡了。
空气是透明的,隔着空气,只见她如婴儿般沉沉蜷伏。
脸色是银白的。
她常说道:年来也没几觉好睡,如今陡地放下心来,芳魂可以自主地遨游。
完全因为放心。
带着一点微微的笑意。
怀玉捻亮了灯,一看闹钟,是三点半。
闹钟——这以前,在北平唤“醒子钟”,倒是稀罕的。
玻璃下压着怀玉的照片,压得密不透风,铁案如山,他又记得她这样说道:这下可好,从此逃不了。
在他夜半点灯殷殷窥探之际,段娉婷乍醒,好似仍被一个好梦纠缠着,硬要挣扎,不肯出来,折磨一阵,有点悲凉:“我要做梦,我不要醒!我不要醒!” 蓦见身畔的怀玉,恐慌地紧拥他,道: “给我讲句好话——” 说着童稚地泪花转乱,怀玉细语: “我在,我在。
” “圣经上说,”段娉婷笑,“一句好话,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中。
” 怀玉如同呵护一个孩子似的呵护着她。
真是夫妻情分。
踏足于此,银网子?他便摇身变为金苹果了。
他们再也不寂寞。
——只有一个人是寂寞的。
宋牡丹。
丹丹也住霞飞路,她被安顿在这高级住宅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头。
她有佣人、司机,也有一个安排得妥善的女秘书,应有的派头,提早给预备了。
她接受全新的改造,本性却没有消失,最痛苦便是这样,到底她没有自然流露的艳光。
不是这路人。
她比不上任何一个金先生的新欢——她不是新欢,她是“旧爱”。
金啸风眷顾丹丹的自由,只是隔几天来看进度。
丹丹天天试新装试发型,实在有点不耐烦,只道: “这样的改造,没完没了,又不让我拍电影去,我不干了!” 还没走到厨房,伸出半个头: “我下面去,金先生你要不要吃?” “自己下?” “她们调弄得不对胃口。
” 他由她自个儿在厨房里调弄。
自来水,自来火,她也晓得了。
末了端来两大碗的面条,寻常百姓家的小吃,丹丹很得意: “看,这是‘一窝丝’,有面丝、肉丝、蛋丝,还有海米、木耳、青瓜丝,吃来有滋有味。
” 一边吃,一边还在夸: “我还会贴饼子、包饺子,还会蒸螃蟹——不过,要当了明星,就没工夫干了。
” 金啸风饶有趣味地看着她。
“金先生……你说我不像明星,对吧?” “对,不够坏。
”他笑。
“我当然会坏,善良的女人都是笨的——为了坏男人,半死不活。
” 她停了箸,隔着氤氲的蒸汽,追问: “我什么时候可以当明星?” 他灵机一触: “她不是‘花瓶’,何必做市面?得顺水推舟才是上路。
” 上海南市区这天可热闹了。
蓬莱市场在这天落成,举行了一个典礼。
年来,既有九一八事变,又有一二八事变,全国都展开抗日救亡运动。
不过上海的经济有畸形发展,日货洋货仍充斥,国货在市场上就一落千丈,没有出路了。
有人背地里传说,金先生的资金,部分来自日方,如此一来,不免背上“汉奸”之罪名——不过此刻大家奇怪地指着市场上高悬的横布条,原来上面书了“土布运动”四个血红的大字。
未几,镁光乱闪,引出了一个标致的小姐,身穿一袭土布旗袍来剪彩,那是淡淡的胭脂红,长至足背,衣衩开在腿弯下,领袖和下摆都绲了双边。
小姐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有捺不住的紧张兴奋。
只听得宣布:“宋牡丹小姐。
” 金啸风顺水推舟,连消带打,便赞助了这个“土布运动”。
旗袍的衣料由布店奉送,并由服装店连夜赶制,目的是招徕顾客,推销国货。
不过金先生的意思,还要宣传土布为“自由布”或“爱国布”,因为这种意义,再也没有人怀疑他的“爱国”心态了。
还有,今天他们选出了一位“土布皇后”,便是眼前这美得天然的宋牡丹。
金先生轻轻往她背上一拍,示意她金剪一挥,市场欢声雷动,大家马上便接受了一个如此“端正”的皇后了。
他们鼓掌,还在喊: “宋小姐!宋小姐!” 还有人涌来请她签名——只消买下几个临时演员来带头起哄,一切水到渠成。
丹丹瞥到人群中有人在挥手,她微微一笑——是沈莉芳。
众沸沸扬扬传颂,不消几天,金先生的地位,宋小姐的声誉,便被肯定。
市场还点燃了一串爆竹,噼噼啪啪地响了半天。
丹丹很快乐。
每个人心头都有一团火,她点燃了——他那么地照拂。
虽然她的皇后当过了,爆竹也燃过了。
红彤彤的残屑,到了夜晚便被竹帚一下给扫掉,露出灰白的泥地。
游戏已经完毕,但名衔到底是亘存的。
她还被绕上彩带呢。
晚上,丹丹拥着彩带,睡得不好。
青春的活力令她的一团火沿着血液浑身跑。
她一步一步地,赢给他俩看。
顷刻之间,她已发觉自己身上有一种焕发的自保的说不上来的力量,那是可贵而又可怜的。
她很怜惜地,抚摸自己贲起的胸脯,有点羞涩。
她摆脱不了命运的操纵,她又“生”了。
如握着一头待飞的小鸟,她的身体。
也许真的如传说中一般——一个女人,捧她的人多了,她的命就薄了。
“那不要紧。
”她对自己说,也对金先生说,同样的话,“我只要几年。
我才不要长命百岁。
” 有一句话却在心头打转:“我要报仇!”忽地只觉背上一暖,忆起金先生轻轻一拍。
那斯蒂庞克轿车把金啸风和丹丹送至静安寺路畔的跑马厅去。
还没来得及下车,已经有记者来拍照了。
金先生很自然,顺势搂一搂她。
丹丹没有抗拒,一切都像循序渐进,他往她背上一拍,他把她肩膊一搂,如同慢火煎鱼,到了后来,她便在他手上给烧好了。
也许这是男人的奸狡——他在制造一个表面的事实,人人以为她是他的人,目下还不是,不过,谁知道呢?他们都若无其事地让人家拍照,这一回,丹丹势将有名有姓地,以她“土布皇后”的身份来示众。
赛马在下午举行,尤其是星期六的下午,场地中间,掘了沟渠,障着土阜,马匹到了这里,必须超越而过,称为“跳浜”。
很多银行、洋行,往往按例停止办公半天,让人看跑马去。
这天真是人山人海。
丹丹下了车,只见跑马厅四周,有短栅没墙垣,有些人便备了长凳,专供小市民站在上面看,隔岸远观,每人收几枚铜板,作为租费。
也有年纪相若的姑娘,满脸好奇地朝里头引颈翘首的。
丹丹傲然地随着金先生作入幕之宾去了。
高昂的票价,严格的规例,都不在眼内——如果她不是宋牡丹,她便只好被摒诸门外。
老实说,她之所以有今天,完全因为被看中,她不会不明白,生平第一遭来看跑马,分外地专注,驰道分外档和内档,骑师穿着各种颜色的服装作为标识,绕场若干匝,直至靠东南角的石碑坊为止,以定胜负。
还没开跑呢,所以胜负未见。
正游目四盼,忽见不远处也围上了记者。
看真点,不是他是谁?他高大了一点,也英俊了一点——因为隔了一段日子不见了,有一点姑息和企盼,觉得他实在很好,只是他改穿了西装,而她呢,今天不穿旗袍了,身披一件荷叶袖连衣裙,领口翻飞着一层又一层的轻纱,腰间系了蝴蝶结,一双白手套,这时装真摩登,怪道“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像。
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
丹丹恨自己落伍而且尴尬。
与此同时,金先生也见到了。
他握住丹丹的小手,拍拍她的手背。
丹丹放心,天塌下来,也有人顶住。
他明白她的自卑,笑道: “咦?啥事体作事没长性?” 她咬唇一笑,有点惭愧。
史仲明递来一沓香槟票,给她玩儿。
她一看,什么A字香槟、B字香槟、大香槟、小香槟……跳浜、赛马之后,还来个摇彩。
金先生问: “那边厢是啥闲账?” 史仲明回话: “那有声电影‘人面桃花’快拍完了,要上了。
趁此白相白相。
” “哪间电影院放?” “片子没完,还未有排定。
” “老黄一向跟中央打交道。
” 丹丹不知就里,对他们的话题一点也不明白,只一脸纳闷地呆听。
金先生很照顾,安慰她:“让他们热火热火吧,好不好?” “不好!” “那怎么办?我可没有能力不许人家拍照的呀。
”他逗她。
丹丹刚刚出的一阵风头,马上又波平浪静了,她一阵失意,真难为啊,到底还是败在她手上。
“小丹。
”他喊她,她不应。
他又笑道:“宋牡丹小姐,看你多小器。
我就是要来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 丹丹狠狠道: “我要比她红!” 金先生无意地问:“她身旁的是男主角,唤唐怀玉——” 丹丹马上接话碴儿: “我不认识他!” “好好,吃饭去。
” 说着说着,丹丹忽听得四周闹闹嚷嚷喊:“六号!六号!” 六号也是他们买下的号码,它跑出了。
丹丹一时忘我,抓住金先生的双臂,大喜:“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丹丹缩缩脖子缩回手。
“人面桃花”在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也超出了预算,原来黄老板打算投资十二万的,到结账时,已花了十八万五千多。
一般的戏拍完了,便要请戏院老板喝几盅,红红脸孔,然后提出上片的要求,希望老朋友帮个忙,给一个映期。
要是对方口气不热,还得赶着把拷贝给送过去审定审定。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电影市场,映期好,对本对利也说不定,映期不好,三天两头的,便要陪戏院老板吃饭孵温堂喝咖啡上跳舞场……不过“人面桃花”忒新鲜,不必怎么轧朋友,中央、金城等大戏院已来接头。
万众瞩目,要看演戏的片上发声。
好吃香。
段娉婷和唐怀玉经了一番宣传,也吃香起来了。
银坛新配搭,戏还没上,黄先生先约了在红房子吃大菜。
红房子经营的是法式西菜,价钱很贵,他们点了烙蛤蜊、奶酪出骨鸡、海立克猪排……末了还来一客白脱起司酥和奶油泡芙。
怀玉已然十分地习惯他手中一杯滚烫的咖啡了,也开始有派头了。
黄先生开门见山,掏出一份文件: “我想跟二位签个合同。
” 他要捧他,也要留她,签个合同自是上算。
而且因着互惠的情况,条件订得高。
段娉婷比较老手,一向不肯受束缚,这回眼看形势很好,且有声片一出,谁还再去拍无声片了? 对面的黄老板肥头胖耳,相处下了,也不算什么刁枭厉害胚子。
自己是个明星,明星这行业不保险,一不小心,就过气了,过气也就完蛋了。
不知自己在哪一天走下坡呢?总不成到走下坡那一日,才发觉危险。
故此,听了价钱,便提出加倍,进进退退,终于给加五十巴仙,她就当场签了,怀玉也签了。
三年。
合同规定在一年内拍三部电影,如果拍不了既定之数,不用补戏。
不得外借给其他电影公司…… 待二人签好这份合同,电影就扰攘地预备在中央大戏院上了。
首映礼,真是一时之盛。
在中央戏院二楼的大堂设了酒会,可以请来的行内人,都来了。
男女主角没有一道,分开一先一后地到。
西装笔挺的唐怀玉,由电影公司的人员陪同亮相了,大家惊诧他的气色很好,天时地利人和都应了,神采飞扬,眉梢眼角之间,有股阴霾扫尽的英气——他又出人头地了,终于等到今天了。
想想,多月之前,还是一头一脸的灰,简直不敢抬起头来做人,空有一身好本领,六面没出路。
如今嘴角挂上笑意,竭力掩藏傲慢,与各界周旋。
周旋,便是:“谢谢大家来,都是黄老板的面子大,请多指教!”哼,谁要谁来指教!生死有命,富贵由天,也全凭个人造化。
未几,段娉婷由玛丽陪同着,也来了。
一来,记者们起哄,要男女主角亲热点合照。
段小姐总爱笑着解释:“哎,不是啦,我跟唐先生根本不熟,拍戏的时候才见得多点儿,拍完了大家研究一下演技,希望演得更好——别乱说了,那是宣传伎俩,不信问问唐先生。
”唐先生又道:“我当然希望追求段小姐,不过她裙下不二之臣可多着,也许我得施展十八般武艺来较量。
不排除这可能性。
” 记者们诸多要求,一时要她绕着他臂弯,一时要他搂着她香肩,作出十八种姿态来满足照相机和镁光灯。
拍完又煞有介事地分开了。
而,金先生也来了。
黄老板亲迎,他很高兴自己有这个面子,金先生道:“我有兴趣看看片上发声多新鲜!” 方转身,唐怀玉神清气朗脱胎换骨地迎上来,他把握这个良机,正正地看着他的对手,一字一字地道:“金先生,上海真是个好地方,一个筋斗,也就翻过来了!你肯来,真是我的光荣!” 金先生颔首微笑,道: “听说你筋斗翻得不错。
” 怀玉也笑:“是么?我自己倒也不在意。
反正有就是有。
哈哈!” 金啸风脸色一沉,马上便回复常态: “这,才是第一部电影吧?” “是的金先生。
不过已经订了三年合同了,眼看快要忙不过来。
” “恭喜,跟咱上海攀上关系了啦?” 怀玉一笑,仗着年轻,说: “才三年。
我有的是三年又三年。
” 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还不看风驶尽? 段娉婷走过来,也是举杯敬酒,一脸笑意,娇艳欲滴: “金先生,难得啊。
小戏院小片子,今儿晚上没约人吧?我们陪你看。
” “约了。
来了。
” 回头一看。
谁? 是她! 是她! 怀玉一直都不相信这个事实。
丹丹也脱胎换骨地自门外袅袅而来,史仲明伴在身后。
他猜想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一个最大的疑团。
他还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的敌人,有些胆战惶惑。
她? 她是谁?怀玉从来都没发觉丹丹汪汪的眼睛不经意地如此媚人。
庄重地,又泄漏了一点风声——一定经过不得已的变迁。
人丛中有人喊: “土布皇后!土布皇后!” 啊丹丹也是镁光的焦点呢。
如今各领风骚了。
只见她一头短发,贴着精致的头脸,额前一排稀疏刘海,若有若无。
细模细相,油光油滑,衬托一袭一点也不肯炫人的旗袍,贴合着身份。
金先生笑:“我的皇后来了。
” 怀玉万分迷惑,她留下了?她来了?他认不得她。
多少话想说,但沉下去,重压在心头。
他的嘴唇不争气地喃喃: “丹——” 丹丹虎着脸过来,伸着手,先发制人地报复: “宋小姐。
” 他只好这样地跟她见过: “宋小姐。
” 段娉婷一瞥,只维持着微笑,寒暄: “哦,宋小姐当了‘土布皇后’呢,很好。
先土布,下一回一定可当绸缎、织锦什么的,很好啊。
” 丹丹不知如何应付,便变了色。
段娉婷体贴地: “慢慢来啊。
多参加首映礼,让记者拍拍照,还怕没人找你拍电影去?——嗳,我真忌妒,从前哪有捷径好走?” 丹丹急了,忙借点势力:“我但听金先生的。
” 段娉婷见怀玉只强笑,便捏捏丹丹的旗袍料子: “好料子!是不是当选送的礼物?” 她认得这丹丹。
最好她不是冲着自己来。
自己名成利就,而她刚迈出第一步,初生之犊不畏虎。
她这样地出现,多像角儿登场,眼下是出什么戏?有没有威胁? 她把她的旗袍捏了又捏,捏了又捏: “咦?有点皱,不是土布吧?” 史仲明觑此形势,便帮腔: “这名堂够新鲜吧?是金先生特地给设计的。
” 段娉婷不及对“金先生特地……”起反应,史仲明还不让她喘息: “就是看市面上一般形象太滥了,有意给塑造一个端正点进步点。
宋小姐这样出道了,还没什么雷同的呢,就图气质特别。
” 丹丹感激地看了史仲明一眼。
有个靠山就有这点好。
且不劳那位高手多说半句,马上就有亲信出头解围、还击、对付。
史先生看出来自己的位置,想他也看出来段小姐的位置。
做人甚是上路。
丹丹冷笑,跟二人对峙着,但觉一帮人都向着她,心底凉快到不得了,把对面的奸夫淫妇踩跺成泥巴。
末了还在门坎上给擦掉。
只是自己不免有点凄酸苦楚,不可言喻。
转瞬已是入场看戏的辰光,人潮一下子生生把他们拆散了,各与各的人,终于坐到一块。
丹丹向金啸风使小性子,狠道:“哼,看到一半,我便跑!我故意的!你是不是也一道。
” 金啸风自己也意料不到,他看丹丹的眼神,可以柔和起来。
像秋日阳光,日短了,火红的颜色淡了,路旁的法国梧桐率先落下第一片叶子。
丹丹并没有“真正”成为他的情妇,这点令她有点奇怪。
他只要她陪他,看着她,心魂飘忽至她身后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十分诧异她的日渐精炼成长。
从前若他道: “幸亏拉了你一把,你看,报上都骂歌舞团。
连鲁迅也写,说卖大腿的伤风败俗。
国难当前——” 她会瞪着大眼睛问:“鲁迅是谁?” 如今在上海浸淫一阵,她精刮了。
他怠慢点,她也怠慢点。
像看谁先低头。
他还有正事要办,最近方把日夜银行所吸收了的大量资金,挪出大部分来买进浙江路上一块地皮,造了批弄堂房子。
她在霞飞路寓中孵一个礼拜,秘书向他报告: “宋小姐花钱倒水一样,用来发泄。
天天上街,都架不同的太阳眼镜来瞩目。
” 他冷一阵,来个德律风,她会气得摔掉了。
老虎跟猫,它们是如此地神似,差别在于是否激怒。
这里头一定有些神秘而又可爱的因素——她觉得他既驯了她,便要负责任,他没负责任,也没尽义务,倒觉韶华逝水,望望无依。
金啸风终着史仲明把她接到公馆来,当天也约了电影公司的黄老板,和两个场面上的朋友,一起打牌、吃蟹。
其中一位范先生,是军政府的,另一位杨先生任职买办,一向跟外国的香烟商打交道。
丹丹到的时候,牌局已近尾声,上落的数目她不清楚,只闻金先生笑道: “待会有工夫再算,先喝一盅,来来来,入席了。
” 原来吃的是来自崇明岛的阳澄湖大闸蟹,顶级本有十两重,不过蟹季还未正式开始呢,是今年的头遭,赶着上,也不过七八两。
同桌的除开一帮男人,丹丹是惟一女客。
他为她摆设筵席。
“小丹,”金啸风为她剥开一只大闸蟹,“这是青背白肚、黄毛金钩,你看,又唤作‘金爪蟹’。
” 佣人过来侍候,一桌都是精致繁杂的小工具,他不管,只为她剔去糜烂的紫苏叶,只道她是没吃过蟹的囡囡,嘱咐: “在蟹壳中央,蟹膏上面,有一块八角,最寒了,不要吃。
” ——他只道她没吃过。
她有点气,还嘴:“我知道!我自家还会蒸呢。
” “怎么蒸?” “全扔进沸水锅里蒸的。
” “哈哈哈!”金先生好玩儿地取笑: “没加上紫苏叶?没放蒸笼上隔水加热?蟹身没翻转——还有,蟹是给松了绑的?” 不不不。
前尘往事涌上心头。
为什么?为什么北平的螃蟹是张牙舞爪的,上海的螃蟹是五花大绑的?还有繁复的程序,慢慢地守候,还没有死,早已烦死了。
虽然阳澄湖的蟹,是全国最好。
膏是鲜腴的,肉是肥美的……到底,她也是吃过螃蟹的人呀,顿兴离乡背井的落寞,当初,是谁与共? “真好,蟹季来了,我也就馋得恶形恶状了。
”那范先生道。
“一公斤蟹苗可收成五六万。
”史仲明附议,“有得你馋。
” “可惜蟹季短,拼尽了也不过两三个月,好日子真不长。
”杨先生叹道。
金先生忽有发现:“咦,这蟹,吃起来比去年还要好?” 范先生压低了声浪: “对呀,此中自有玄机。
” 一直不怎么开腔的黄老板问道: “说来听听。
” “——不好说。
” 不说不说,当事人的范先生也说了: “你们知道吗?有战事了,蟹特别地肥美——尸体沉在湖底,腐烂了,马上成为它们的食粮……” 金先生举起花雕:“喝酒喝酒,吃蟹赏菊,只谈风月。
” 金啸风瞧了丹丹一眼,示意: “花雕去寒,喝一口?”又笑,“酒烈,怕不安全,别喝醉。
” 举座哄笑。
丹丹看看那杯香烈的液体,她竟在酒中见到他的影儿了——那夜,丹丹持蛐蛐探子撩拨老娘嫁后孑然一身的志高。
怀玉劝他:“你可不能一点斗志都没有。
”……她记得他讲的每一句话呢,在那贫瘠的夜晚,只有蟹,没有酒,但她有人。
很丰富。
人。
刹时杯弓蛇影,心里一颤,手中一抖,酒便洒了:她的斗志。
丹丹站起来,夺过佣人的酒壶,自顾自再满斟。
然后,一口干了。
烈酒如十根指爪,往她喉头乱叩。
几乎没呛着,她很快乐,终于一口把一切干掉。
杨先生循例起哄: “你这‘蛟腾’,把小姐灌醉,正是黄鼠狼给鸡拜寿。
” “什么?”丹丹惺忪问。
“——没安好心。
”史仲明道。
“月亮还没有出来?——”丹丹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抬眼透过窗纱,真的,见不到一点寒白的月色。
只是浑身火烫。
吃得差不多,便见那黄老板即席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
先迟疑一下,才又填上了银码,递给金先生。
金先生一见,便笑道: “白白相,消遣消遣而已,老哥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
” “不不,”黄老板道: “愿赌服输。
” 金先生把支票拈来一瞧: “别调划头寸了,多麻烦。
” 说着乘点烟时,便把那支票给烧掉了。
只补上: “闲话一句,你把你们电影公司股份送我五十一巴仙。
” 无意地,随口又再补上:“还有些什么演员合同,那段娉婷、唐怀玉什么的,一并归我,弄部电影玩儿玩儿。
就这么办。
”——丹丹的心狂跳。
丹丹的酒意上了头脸,一跤跌进一个酩酊而又销魂的神奇世界中。
四周是一片金黄的璀璨的光影,她身畔是双闪耀着强烈感情的眼睛——不管她什么时候,无意投过去一瞥,他都是看住她的。
中间有一个水火不容的境界,只待她一步跨过去,甘愿地。
她有点飘忽地由佣人领着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自来水的蒸汽,叫眼前一面圆形大镜有点迷乱,丹丹伸出一根手指,指着镜中的自己,说道: “你要小心!” 心跳得很厉害,面颊微微地也痉挛着,一滴眼泪偷偷滚了出来,心底升起又浓甜又难受的感觉和感动。
——他把一切都买下来,重新发落! 他是为了她。
丹丹跌跌撞撞地,没有再到筵席上去,佣人报告了她的醉。
金啸风到了他的房间,一时找不着丹丹,正诧异她又跑到哪儿浪荡去了? 四下一瞧,只见丹丹蜷坐一角,正正对着那几个打开了的铁笼子,她一定吓呆了。
人住的地方,竟尔藏了一头蜥蜴、一条响尾蛇,和一只蜘蛛。
她误打误撞地放生了。
青白着脸,战栗起来,神志不清,有点像着魔,一见金啸风,便颤着。
“金先生——” “你要什么?” “杀掉!杀掉!” “别怕!”金啸风走到他床边,在床下搜出一把手枪来。
“砰”的一下,先把蛇干掉了。
丹丹飞奔过来,夺过枪,也朝那蜥蜴一轰,不中,再来,血肉模糊地,认不出真身。
只有那头大蜘蛛,也被他用重物击拍得一塌糊涂的绿浆,肚子中竟跑出数之不尽的小蜘蛛来,一时间四散奔窜,看得人毛骨悚然。
“别怕!”他拥着她。
丹丹实在不怕了,一切的死伤,啊,惯见亦是寻常——她什么没见过,没经历过? 忽然间兴起一阵厌倦,厌倦一切的死伤,追和逃,这念头突如其来地,漫遍全身,是的,心肠肺腑,末了付诸血污。
只余空虚苍白,不着边际。
当她拥着这一座山似的男人时,停步四望,还是他最可靠。
谁愿再努力苦撑?日子变得全无意义,只想倚靠他,直到下一生。
“小丹,”他喃喃呐呐,“看不出你杀气腾腾的。
” 地欲陷天欲堕。
她也意外: “是呀,我都不知道会是这样的。
” “给你一点酒,就原形毕露了?” 她厌倦了追和逃。
血花纷飞的刺激,令她变得容易悸动,也令他兽性大发起来。
他疯狂而又急煎地向她探索和进逼。
把她的脸转过来,使劲狰狞地加添她无限的疑惧。
他的宠物都报销了,她是目前惟一的宠物了。
而且,难道他不知道这还是个雏儿? 有些事,是女人逃避不了的。
丹丹只念,凡事需要决绝,自是早比晚好。
也许是酒意,也许是自欺,不知如何,她由衷萦绕着一种新鲜事体,譬如说,对男人的渴想。
真奇怪,这渴想蹑手蹑足地来了,原来潜藏着已久,伺机便爆发——或是在暗中已猜测过? 浑身都有不安的兴奋。
越来越强。
她还是一个得宠的人呢。
不再被抛弃,幸福在五内焚烧,身体熔成一摊。
嘴唇枯焦,伸手不见五指。
她很紧张,甚至是被动的。
玻璃丝袜像一层皮似的被煎下。
她不敢动。
金啸风设法令她蜷曲的身体舒展开来。
面对他的威武,她只能更加软弱,一贯的刁横无影无踪。
她像一块承受刀俎的鱼肉,猛然地:“哎!我很疼!你放过我吧!” 他的小满—— 他到她的满意“书寓”去。
她心中没有他,只奉他一杯茶……他不可能天天打茶围,终有一回,趁着盲母不在,他非要她不可。
“小满,我一见你的脸就想——” 满意力竭声嘶地抗拒,一地都是推翻了的清茶水烟袋和瓜子,零落如草莽。
男人一旦要一个女人了,简直如洪水猛兽,眼睛血红——他不明白,自己已是个一等的案目了,他对她明显地偏私,照拂日久,难道她一点也不领情? 因她挣扎得太不留余地了,拼死一样,他凶暴起来,在她娇嫩的尖白脸盘上刮了两记耳光,马上,双颊辣辣地透红。
他气喘咻咻。
满意一呆,大吃一惊,泪水冒涌,叫道:“你不要逼我!我心里已有人!” ——金啸风直至今天,也不知他究竟败在谁的手里?这永远是一个隐伏在青天白日的敌人。
他也许一生也翻查不出底蕴。
只是那一天,他如雪崩海啸似的豁出去了,极度的亢奋也令满意走投无路…… 忽地,措手不及,满意拾到一块茶碗的碎片,在自己瓜子仁儿的脸上划了一个鲜血斑斓的十字,她失常地惨叫:“我的脸坏了,你放过我吧!” 金啸风忽觉这经不起人道抽搐着的丹丹,舌尖都冰凉了,她凄凉婉转地长叹一声: “我——要死了!” 她很惶恐就此死去,然而她再也使不出半分力气,意乱情迷群魔扰攘似的。
金啸风爱怜地捧着她的脸,他又重蹈他最初的恋慕。
——莫非是夙世的纠葛,那么不可能的人,如今压在他身体下。
他深深地吻着丹丹,无限地痛楚。
他喊:“小满!” 小满遭野兽般的蹂躏,一脸一床的血。
第二天,她就跳黄浦了。
她一定是浑身都系了最重的物体,石块铁块,血海深仇一并沉没在江底至深,不肯给他一个机会。
即使他夜夜在江边,眼看汹涌的水流混沌一片,如心事般沉重。
夜渡灵柩一样漂流着,岸灯闪出阴险的微光。
隔不了多天,总是有山穷水尽的人来跳黄浦。
不过,只是不爱他而已,她倒情愿一死?以后,金啸风高升了,他为了他那未曾公开过的“金太太”,终生不娶。
绝口不提。
丹丹空余一身细细的汗,半息游丝——竟全没有工夫念到,何以一夜之间,她就是他的人了。
一切都是渺茫…… “哈哈,哈哈,啊哈哈……”怀玉笑给段娉婷听。
“嗯,这样绷的笑法,好假。
” “不是假,是难。
”怀玉道,“每个角色的笑法都不同,既要形似,又要神似。
孙悟空的笑跟猪八戒的笑也不同。
” “孙悟空怎么笑?” 怀玉给她作一个眯眯乐孜孜的猴儿脸,段娉婷很开心,又问:“猪八戒怎么笑?” 怀玉木然。
“怎么笑?” “笨笨的一个大鼻子搁在嘴巴上,怎么笑法,都没有人知道。
也许,它从来不笑。
” “你怎么笑?” 怀玉这才打心底笑出来了,得意地笑。
“人面桃花”在中央大戏院,连满了一个月。
虽然,毛病还是出来了,几乎每一场都有毛病,因为放映时,一方开映机,一方开唱机,彼此快慢稍有不同,片上演员的动作跟发音便脱节了,有些场先张嘴,后出声;有些场先出声,后张嘴。
这种唱双簧式的蜡盘配音,是有一点点的“遗憾”,不过,第一部,大家都迷上了。
也都迷上了片中的男主角。
他一笑,来劲了,就把他半生学来的笑,师父教过的,自己见过的,都跟他的女主角表演了。
什么冷笑、奸笑、强笑、骄笑、媚笑、狂笑、苦笑、羞笑、妒笑、僵笑、骇笑、谄笑、傻笑、痴笑、狞笑、惨笑……笑得累了,怀玉一弹而起:“到邮局去。
” 段娉婷倚在床上,燃着一根香烟。
隔着袅袅的漫卷的烟篆,她开始想,今天笑完了,明天哭,哭完了,便愁。
七情六欲,也许几下子就过去,一一演罢又如何?他一天比一天壮阔,她却一分一秒地老。
情,像手中的香烟,烧烧就烧掉,化作一缕幽幽的白气。
怀玉换了一身轻便的运动装走在霞飞路上。
霞飞,这正是他那放浪的心。
天气凉了,然而上海的秋阳是暖烘烘的,像一个女人,烘在你的脸上。
他原不必自个儿到邮局去,而且他也不必那么早便到邮局去,然而只为了一点“自由”的辰光,抽身出来。
当他走着,霞飞路也驶过一辆车子。
史仲明有点意外地,发现他伴着的宋牡丹小姐,再也不像他的初遇。
她有奇异的蜕变,变得最多的是眼神,乌亮闪烁,不由自主。
她来了多久?但眉梢眼角,暗换了芳华。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一朝恶妇予乔
- 不是你的朱砂痣[穿书]阮寐
- 人间正道周梅森
- 我做偏执大佬未婚妻的日子白秋练
- 我给女主管鱼塘中边
- 小李飞刀3:九月鹰飞(上下)古龙
- 心悦臣服卓涵月
- 邪气凛然跳舞
- 暴君每晚梦我五月锦
- 爱与他梦筱二
- 三途志崔走召
- 撩倒撒旦冷殿下晨光熹微
- 重度痴迷多梨
- 尘埃之花采葑采菲
- 奇迹王座半醉游子
- 百炼成神(不灭武神)恩赐解脱
- 万人迷炮灰被迫躺赢郎不知
- [聊斋]活人不医南陶
- 定风波来风至
- 兔子必须死一梦黄粱
- 至尊剑皇半步沧桑
- 全民皆萌宠暖暖的茶
- 我见贵妃多妩媚鹊上心头
- 我给男配送糖吃[快穿]五朵蘑菇
- 女配求生日常[穿书]陆灵儿
- 都市最强战神梁一笑
- 从综武世界开始逍遥诸天沐阳千羽
- 穿越北宋靖康耻灭吾主沉浮我心依然1326
- 三国:我辅佐刘备再兴炎汉我才是猫大王啊
- 踏雪寻青梅云笺寄晚
- 替弟为质三年,归来要我让战功?芳龄真的二十
- 异界纵横之我在江湖搞发明锅包肉没有锅
- 清宫秘史十二章马踏飞花
- 明末造反:我的盲盒能开神装七辛海棠
- 逆命武侠行随风飘扬的喜哥
- 逆世灵霄纪书写杨意
- 诸天帝皇召唤系统遗落的影子
- 用户90391439的新书:悟用户90391439
- 永乐入梦我教我自己当皇帝用钱打我
- 碎星阁神速熊猫
- 人在古代,从抢山神娇妻开始崛起女帝
- 诗泪洒江湖云里慕白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命理探源【译注】陈缘字长青
- 带着基地闯三国安安静静看书书
- 大宋第一猎户:女帝别低头!一起抓水母
- 王伦逆天改命称帝失控的牛
- 大明锦官梦苏梦沉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大明:人在洪武,复活常遇春冰魂修罗
- 陌上!乔家那位病公子百越春秋
- 踏雪寻青梅云笺寄晚
- 七窍欢Roxi
- 清宫秘史十二章马踏飞花
- 人在古代,从抢山神娇妻开始崛起女帝
- 逆命武侠行随风飘扬的喜哥
- 带着基地闯三国安安静静看书书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穿越古代我的空间有军火:请卸甲百万负翁不想再负
- 物流之王之再续前缘笔尖路悠然
- 乾元盛世系统冀北省的护法神
- 大明:人在洪武,复活常遇春冰魂修罗
- 东汉末年:我携百科平天下特特eve
- 重生六9:倒爷翻身路惊恐不安九仙君
- 混沌再临之灭仔纳里
- 刺世天罡夜阑听雪落
- 权倾朝野,女帝求我别反准备起飞
- 九道真仙扫地的研究僧
- 拜见教主大人封七月
- 宇宙本源诀冰冷眼泪
- 上山为匪彗星撞飞机
- 重生归来之神帝薛九玄清方观世
- 苦闯仙侠界云隐青山
- 在成为西门吹雪的日子里笑点烟波
- 丹武大帝关东大侠
- 综武:天道曝光我九世负心鸟羊
- 纵横诸天:从修炼辟邪剑法开始不吃鱼虾的猫咪
- 三国:我辅佐刘备再兴炎汉我才是猫大王啊
- 替弟为质三年,归来要我让战功?芳龄真的二十
- 清宫秘史十二章马踏飞花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永乐入梦我教我自己当皇帝用钱打我
- 平推三国,没人比我更快以空空
- 一剑独尊自摸一条
- 大明中兴之我是崇祯三千纸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我热痢的马
- 穿越大秦:红颜助国兴还钱100
- 龙吟三国小川流水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我在古代当镇令龙葵宝宝
- 天赐良臣爱吃炝炒丝瓜的胡掌柜
- 大明权谋录Four古往今来
- 纯阳第一掌教池宁羽
- 道术达人虫梦
- 冷艳总裁的超级狂兵北冥听涛
- 在成为西门吹雪的日子里笑点烟波
- 古代打工日志:从退婚开始躺赢西猫西
- 仙帝铁马金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