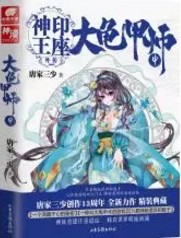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部 豌豆花(3/3)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锻炼出一种令玉兰惊奇的忍耐力。
她忍耐了许许多多别的孩子不能忍耐的痛楚,不论是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
鲁森尧娶玉兰,正像他自己嘴中毫不掩饰的话一样: &ldquo你以为我看上你哪一点?又不是天仙美女,又带着三个拖油瓶!我不过是看上你那笔抚恤金!而且,哈哈哈!&rdquo他猥亵地笑着,即使在豌豆花面前,也不避讳,就伸手到玉兰衣领里去,握着她的乳房死命一捏,&ldquo还有这个!我要个女人!你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rdquo 对豌豆花而言,挨打挨骂都是其次,最难堪的就是这种场面。
她还太小,小得不懂男女间的事。
每当鲁森尧对玉兰毛手毛脚时,她总不知道他是不是在&ldquo欺侮她&rdquo。
玉兰躲避着,脸上的表情老是那样痛苦,因此,豌豆花也跟着痛苦。
再有,就是鲁森尧醉酒以后的发酒疯。
鲁森尧酗酒成性,醉到十成的时候就呼呼大睡,醉到七八成的时候,他就成了个完完全全的魔鬼。
春季里的某一天,他从下午五点多钟就开始喝酒,七点多已经半醉,玉兰看他的样子就知道生意不能做了,早早地就关了店门。
八点多钟玉兰把两个小的都洗干净送上床,嘱咐豌豆花在卧室里哄着他们别出来。
可是,鲁森尧的大吼大叫声隔着薄薄的板壁传了过来,尖锐地刺进豌豆花的耳鼓: &ldquo玉兰小婊子!你给我滚过来!躲什么躲?我又不会吃了你!&rdquo嘶啦的一声,显然玉兰的衣服又被撕开了,那些日子,玉兰很少有一件没被撕破的衣服,弄得玉兰每天都在缝缝补补。
&ldquo玉兰,又不是黄花闺女,你装什么蒜!过来!过&mdash&mdash来!&rdquo不知道鲁森尧有了什么举动,豌豆花听到玉兰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悲鸣,哀求地嚷着: &ldquo哎哟!你弄痛我!你饶了我吧!&rdquo &ldquo饶了你?我为什么要饶了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一直在想念着你那个死鬼丈夫,他有多好?他比我壮吗?比我强吗?看着我!不许转开头去&hellip&hellip你&hellip&hellip他妈的贱货!&rdquo &ldquo啪&rdquo的一声,玉兰又挨耳光了。
接着,是酒瓶&ldquo眶啷啷&rdquo被砸碎在柜台上,和玉兰一声凄厉的惨叫。
豌豆花毛骨悚然。
他要杀了妈妈了!豌豆花就曾亲眼目睹过鲁森尧用玻璃碎片威胁要割断玉兰的喉咙。
再也忍不住,她从卧室中奔出去,嘴里恐惧地喊着: &ldquo妈妈!妈妈!&rdquo 一进店面,她就看到一幅令人心惊肉跳的场面。
玉兰半裸着,一件衬衫从领口一直撕开到腰际,因而,她那丰满的胸部完全袒露。
她跪在地上,左边乳房上插着一片玻璃碎片,血并不多,却已染红了破裂的衣衫。
而鲁森尧还捏着打碎的半截酒瓶,扯着玉兰的长发,正准备要把那尖锐的半截酒瓶刺进玉兰另一边乳房里去。
他嘴里暴戾地大嚷着: &ldquo你说!你还爱不爱你那个死鬼丈夫?你心里还有没有那个死鬼丈夫?你说!你说!&rdquo 玉兰哀号着,闪躲着那半截酒瓶,一绺头发几乎被连根拔下。
但是,她就死也不说她不想或不爱杨腾的话。
鲁森尧眼睛血红,满身酒气,他越骂越怒,终于拿着半截酒瓶就往玉兰身子里刺进去,就在那千钧一发的当儿,豌豆花扑奔过来,亡命地抱住了鲁森尧的腿,用力推过去。
鲁森尧已经醉得七倒八歪,被这一推,站立不稳,就直摔到地上,而他手里那半截酒瓶,也跟着跌到地上,砸成了碎片。
鲁森尧这下子怒火中烧,几乎要发狂了。
他抓住豌豆花的头发,把她整个身子拎了起来,就往那些碎玻璃上揿下去。
豌豆花只觉得大腿上一连尖锐的刺痛,无数玻璃碎片都刺进她那只穿着件薄布裤子的腿里,白裤子迅速地染红了。
玉兰狂哭着扑过来,伸手去抢救她,嘴里哀号着: &ldquo豌豆花!叫你不要出来!叫你不要出来!&rdquo &ldquo啊哈!&rdquo鲁森尧怪叫连连,&ldquo你们母女倒是一条心啊!好!玉兰小婊子,你心痛她,我就来修理她!她是你那死鬼丈夫的心肝宝贝吧!&rdquo说着,他打开五金店的抽屉,找出一捆粗麻绳,把那受了伤、还流着血的豌豆花双手双脚都反剪在身后,绑了个密密麻麻。
玉兰伸着手,哭叫着喊: &ldquo不要伤了她!求你不要伤了她!求你!求你!求你!求你&hellip&hellip&rdquo她哭倒在地上,&ldquo不要绑她了!她在流血了!不要&hellip&hellip不要&hellip&hellip不要&hellip&hellip&rdquo她泣不成声。
屋顶上有个铁钩,勾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的是一些农业用具,小铁锹、小钉锤之类的杂物。
鲁森尧把竹篮拿了下来,把豌豆花背朝上、脸朝下地挂了上去。
豌豆花的头开始发晕,血液倒流的结果,脸涨得通红,她咬紧牙关,不叫,不哭,不讨饶。
玉兰完全崩溃了。
她跪着膝行到鲁森尧面前,双手拜神般合在胸前。
然后,她开始昏乱地对他磕头,不住地磕头,额头撞在水泥地上,撞得咚咚响,撞得额头红肿起来。
&ldquo说!&rdquo鲁森尧继续大叫着,&ldquo你还爱你那个死鬼丈夫吗?你还想那个死鬼丈夫吗?&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爱,不爱,不爱,不爱,不爱&hellip&hellip&rdquo玉兰一迭连声地吐出来,磕头如捣蒜,&ldquo不想,不想,不想,不想&hellip&hellip&rdquo &ldquo说!&rdquo鲁森尧得意地、胜利地叫着,&ldquo豌豆花的爸爸是王八蛋!说!说呀!说!&rdquo他一脚对那跪在地上的玉兰踢过去,&ldquo不说吗?不肯说吗?好!&rdquo他把豌豆花的身子用力一转,豌豆花悬在那儿车辘辘似的打起转来,绳子深陷进她的手腕和脚踝的肌肉里。
&ldquo啊&hellip&hellip&rdquo玉兰悲鸣,终于撕裂般地嚷了起来,&ldquo他是王八蛋!他是王八蛋!他是王八蛋&hellip&hellip&rdquo 这是一连串&ldquo酷刑&rdquo的&ldquo开始&rdquo。
从此,豌豆花是经常被吊在铁钩上了,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了。
鲁森尧以虐待豌豆花来惩罚玉兰对杨腾的爱。
玉兰已经怕了他了,怕得听到他的声音都会发抖。
鲁森尧是北方人,虽然住在乌日这种地方,也不会说几句闽南语,于是,全家都不敢说闽南语。
好在杨腾是外省人,玉兰早就熟悉了国语,事实上,豌豆花和她父亲,一直都是国语和闽南语混着说的。
豌豆花虽然十天有九天带着伤,虽然要洗衣做事带弟弟妹妹,但是,她那种天生的高贵气质始终不变。
她的皮肤永远白嫩,太阳晒过后就变红,红色褪了又转为白晳。
她的眼睛永远黑白分明,眉清而目秀。
这种&ldquo气质&rdquo使鲁森尧非常恼怒,他总在她身上看到杨腾的影子。
不知为什么,他就恨杨腾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他从未见过杨腾。
他常拍打着桌子発子怪吼怪叫: &ldquo为什么我姓鲁的该这么倒霉!帮那个姓杨的死鬼养儿育女,是我前辈子欠了他的债吗?&rdquo 玉兰从不敢说,鲁森尧并没有出什么力来养豌豆花姐弟。
嫁到鲁家后,玉兰的抚恤金陆续都拿出来用了。
而小五金店原来生意并不好,但是,自从玉兰嫁进来,这两条街的乡民几乎都知道鲁森尧纵酒殴妻,又虐待几个孩子,由于同情,大家反而都来照顾这家店了。
乌日乡是淳朴的,大家都有中国人&ldquo明哲保身&rdquo的哲学,不敢去干涉别人的家务事,但也不忍看着玉兰母子四个衣食不周,所以,小店的生意反而兴旺起来了,尤其是当玉兰在店里照顾的时候。
鲁森尧眼见小店站住了脚,他也落得轻松,逐渐地,看店卖东西都成了玉兰的事,他整天就东晃西晃,酗酒买醉,随时发作一下他那&ldquo惊天动地&rdquo的&ldquo丈夫气概&rdquo。
这年夏天,对豌豆花来说,在无数的灾难中,倒也有件大大的&ldquo喜悦&rdquo。
原来,豌豆花早已到了学龄了。
乡公所来通知豌豆花要受义务教育的时候,曾被鲁森尧暴跳如雷地痛骂了出去。
豌豆花虽小,在家里已变得很重要了,由于玉兰要看店,许多家务就落在豌豆花身上,她要煮饭、洗衣、清扫房间,还要帮着母亲卖东西。
&ldquo讨债鬼&rdquo仿佛是来&ldquo还债&rdquo的。
鲁森尧无意于让豌豆花每天耽误半天时间去念什么鬼书,而让家里的工作没人做。
本来,乡下孩子念书不念书也没个准的。
可是,这些年来,义务教育推行得非常彻底,连山区的山地里都建设起&ldquo国民小学&rdquo来了。
而且,那个被鲁森尧赶出去的乡公所职员却较真了。
他调查下来,孩子姓杨,鲁森尧并没有办收养手续,连&ldquo监护人&rdquo的资格都没有。
于是,乡公所办了一纸公文给鲁森尧,通知他在法律上不得阻碍义务教育的推行。
鲁森尧不认识几个字,可是,对于&ldquo衙门里&rdquo盖着官印的公文封却有种莫名的敬畏,他弄不懂法律,可是,他不想招惹&ldquo官府&rdquo。
于是,豌豆花进了当地的&ldquo国民小学&rdquo。
忽然间,豌豆花像是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带着七彩光华的绚丽世界。
她的心灵一下子就打开了,惊喜地发现了文字的奥秘、文字的美妙和文字的神奇。
她生母遗留在她血液中的&ldquo智能&rdquo在一瞬间复苏,而&ldquo求知欲&rdquo就像大海般地把她淹没了。
她开始疯狂地喜爱起书本来,小学里的老师从没见过比她更用功更进步神速的孩子,她以别的学童三倍的速度,&ldquo吞咽&rdquo着老师们给她的教育。
她像一个无底的大口袋,把所有的文字都装进那口袋里,再飞快地咀嚼和吸收。
这孩子使全校的老师都为之&ldquo着迷&rdquo,小学一年级,她是全校的第一名。
有位老师说过,杨小亭&mdash&mdash在学校里,她总算有名有姓了,让这位老师了解了什么叫&ldquo冰雪聪明&rdquo&mdash&mdash那是个冰雪聪明的孩子!事实上,一年级的课上完以后,豌豆花已经有了三年级的功力,尤其是国文方面,她不只能造句,同时,也会写出简短的、动人的文章了。
可是,豌豆花的&ldquo念书&rdquo是念得相当可怜的。
她经常带着满身的伤痕来上课,这些伤痕常常令人不忍卒睹。
有一次她整个小手都又青又紫又红又肿,半个月都无法握笔。
另一次,她的手臂淤血得那么厉害,以至于两星期都不能上运动课。
而最严重的一次,她请了三天假没上课,当她来上课时,她的一只手腕肿胀得变了形,校医立刻给她照X光,发现居然骨折了,她上了一个月石膏才痊愈。
也由于这次骨折,他们检査了孩子全身,惊愕地发现她浑身伤痕累累,从鞭痕、刀伤、勒伤,到灼伤&hellip&hellip几乎都有。
而且,有些伤口都已发炎了。
学校里推派了一位女老师,姓朱,去做&ldquo家庭访问&rdquo。
朱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未久,涉世不深。
到了鲁家,几句话一说,就被鲁森尧的一顿大吼大叫给吓了出来: &ldquo你们当老师的,教孩子念书就得了,至于管孩子,那是我的事!她在家里淘气闯祸,我不管她谁管她!你不在学校里教书,来我家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当我的老师不成!豌豆花姓她家的杨,吃我鲁家的饭,算她那小王八蛋走运!我姓鲁的已经够倒霉了,养了一大堆小王八蛋,你不让我管教他们,你就把那一大堆小王八蛋都接到你家去!你去养,你去管,你去教&hellip&hellip&rdquo 朱老师逃出了鲁家,始终没弄清楚&ldquo一大堆小王八蛋&rdquo指的是什么。
但她发誓不再去鲁家,师范学校中教了她如何教孩子,却没教她如何教&ldquo家长&rdquo。
朱老师的&ldquo拜访&rdquo,使豌豆花三天没上课。
她又被倒吊在铁钩上,用皮带狠抽了一顿,抽得两条大腿上全是血痕。
当她再到学校里来的时候,她以一副坚忍的、沉静的、让人看着都心痛的温柔,对朱老师、校长、训导主任等说: &ldquo不要再去我家了,我好喜欢好喜欢到学校里来念书,如果不能念书,我就糟糕了。
我有的时候会做错事,挨打都是我自己惹来的!你们不要再去我家了,请老师&hellip&hellip再也不要去我家了!&rdquo 老师们面面相觑。
私下调査,这孩子出身十分复杂,仿佛既不是鲁森尧的女儿,也不是李玉兰的女儿。
户籍上,豌豆花的母亲填的是&ldquo许氏&rdquo,而杨腾和那许氏,在户籍上竟无&ldquo婚姻关系&rdquo。
于是,豌豆花的公案被搁置下来,全校那么多孩子,也无法一个个深入调查,何况外省籍的孩子,户籍往往都不太清楚。
学校不再过问豌豆花的家庭生活,尽管豌豆花仍然每天带着不同的伤痕来上课。
豌豆花二年级的时候,玉兰又生了个小女孩,取名字叫鲁秋虹。
秋虹出世,玉兰认为她的苦刑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她终于给鲁森尧生了个孩子。
谁知,鲁森尧一知道是个女孩,就把玉兰骂了个狗血淋头: &ldquo你算哪门子女人?你只会生讨债鬼呀!你的肚子是什么做的?瓦片儿做的吗?给人家王八蛋生儿子,给我生女儿,你是他妈的臭婊子瓦片缸!&rdquo 玉兰什么话都不敢说,只心碎地回忆着,当初光美出世时,杨腾吻着她的耳垂,在她耳边轻声细语: &ldquo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好!我都会喜欢的!你是个好女人,是个可爱的小母亲!&rdquo 同样是外省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玉兰并不太清楚,&ldquo外省&rdquo包括了多广大的区域,也不太了解,人与人间的善恶之分,实在与省籍没有什么关系。
鲁森尧骂了几个月,又灌了几个月的黄汤,倒忽然又喜欢起秋虹来了。
毕竟四十岁以后才当父亲,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这一爱起来又爱得过了火。
孩子不能有哭声,一哭,他就提着嗓门大骂: &ldquo玉兰!你八成没安好心!是不是你饿着她了啊?我看你找死!你存心欺侮我女儿!你再把她弄哭我就宰了你!难道只有杨家的孩子才是你的心肝?我姓鲁的孩子你就不好好带!你存心气死我&hellip&hellip&rdquo 说着说着,他就越来越气。
玉兰心里着急,偏偏秋虹生来爱哭,怎么哄怎么哭。
鲁森尧越是骂,孩子就越是哭。
于是,豌豆花、光宗、光美都遭了殃,常常莫名其妙地就挨上几个耳光,只因为&ldquo秋虹哭了&rdquo。
于是,&ldquo秋虹哭了&rdquo,变成家里一件使每个人紧张的大事。
光宗进了小学,男孩子有了伴,懂得尽量留在外面少回家,常常在同学家过夜。
乡里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孩子的命苦,也都热心地留光宗,所以,那阵子光宗挨的打还算最少。
光美还小,不太能帮忙做事。
而豌豆花,依然是三个孩子中最苦命的。
学校上半天课,每天放学后,豌豆花要做家事,洗尿布、烧饭、洗衣、抱妹妹&hellip&hellip还要抽空做功课。
她对书本的兴趣如此浓厚,常常一面煮饭一面看书,不止看课内的书,她还疯狂地爱上了格林童话和安徒生。
她也常常一面洗着衣服一面幻想,幻想她是辛德瑞拉,幻想有番瓜车和玻璃鞋。
可是,番瓜车和玻璃鞋从没出现过,而&ldquo秋虹&rdquo带来的灾难变得无穷无尽。
有天,豌豆花正哄着秋虹入睡,鲁森尧忽然发现秋虹肩膀上有块铜币般大小的淤紫,这一下不得了,他左右开弓地给了豌豆花十几个耳光,大吼大叫着说: &ldquo你欺侮她!你这个阴险毒辣的小贱种!你把她掐伤了!玉兰!玉兰!你这狗娘养的!把孩子交给这个小贱人,你看她拧伤了秋虹&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没有,我没有!&rdquo豌豆花辩解着,挨打已成家常便饭,但是&ldquo被冤枉&rdquo仍然使她痛心疾首。
&ldquo你还耍赖!&rdquo鲁森尧抓起柜台上一把铁铲,就对豌豆花当头砸下去。
豌豆花立刻晕过去了,左额的头发根里裂开一道两寸长的伤口,流了好多血。
乌日乡一共只有两条街,没有外科医生。
玉兰以为她会死掉了,因为她有好几天都苍白得像纸,呕吐,不能吃东西,一下床就东歪西倒。
玉兰夜夜跪在她床前悄悄祈祷,哭着,低低呼唤着: &ldquo豌豆花,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死了都没脸去见你爸爸!豌豆花!你一定要好起来呀!你一定要好起来呀!我苦命的、苦命的、苦命的孩子呀!&rdquo 豌豆花的生命力是相当顽强的,她终于痊愈了。
发根里,留下一道疤痕,还好,因为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遮住了那伤疤,总算没有破相。
只是,后来,豌豆花始终有偏头痛的毛病。
这次豌豆花几乎被打死,总算引起了学校和邻居的公愤,大家一状告到里长那儿,里长又会合了邻长,对鲁森尧劝解了一大堆话,刚好那天鲁森尧没喝醉,心情也正不坏,他就耸耸肩膀,摊摊手说了句: &ldquo算我欠了他们杨家的债吧!以后只要她不犯错,我就不打她好了!&rdquo 以后,他确实比较少打豌豆花了。
最主要的,还是发现秋虹肩上那块引起风暴的&ldquo淤血&rdquo,只是一块与生俱来的胎记而已。
可是,豌豆花的命运并没有转好。
因为,一九五九年的八月七日来临了。
6
一九五九年的八月七日。最初,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在南海东沙群岛的东北海面上,形成了不明的风暴,以每小时六十海里的风速,吹向台湾中部。
八月七日早上九时起,暴雨开始倾盆而下,连续不停地下了十二小时。
在台湾中部,有一条发源于次高山的河流,名叫大肚溪,是中部四大河流之一。
大肚溪的上游,汇合了新高山、阿里山的支流,在山区中盘旋曲折,到埔里才进入平原。
但埔里仍属山区,海拔依然在一千公尺以上。
大肚溪在埔里一带,依旧弯弯曲曲,迂回了八十多里,才到达台中境内,流到彰化附近的乌日乡,与另一条大里溪汇合,才蜿蜒入海。
这条大肚溪,是中部农民最主要的水源,流域面积广达两万零七百二十平方公里,区内数十个村庄,都依赖这条河流生活。
在彰化一带,大部分的居民都务农,他们靠上帝赋予的资源而生存,再也没料到,有朝一日,上帝给的恩赐,上帝竟会收回。
八月七日,在十二小时的持续大雨后,海水涨潮,受洪流激荡,与大肚溪合而为一,开始倒流。
一时间,大水汹汹涌涌、奔奔腾腾,迅速地冲击进大肚溪,大肚溪沿岸的堤防完全冲垮,洪水滚滚而来,一下子就在平原上四散奔泻,以惊人的速度,淹没土地,卷走村舍,冲断桥梁,带走牲畜!&hellip&hellip而许多犹在睡梦中的农民居民,竟在一夜间妻离子散,丧失生命。
这夜,豌豆花和妹妹光美睡在小屋里,弟弟光宗又留在一个同学家中过夜。
由于大雨,那天没有上课,豌豆花整天都在帮着做家事,带弟妹、洗尿布,雨天衣服无法晒在外面,晚上,整个屋子里挂满了秋虹的尿布,连豌豆花的卧房里都拉得像万国旗。
秋虹跟着父母,睡在隔壁的卧房里,鲁森尧照例喝了酒,但他那夜喝得不多,因为睡前,豌豆花还听到他在折辱玉兰的声音。
大水涌进室内,是豌豆花第一个发现的,因为她还没睡着,她正幻想着自己是某个童话故事中的女主角,那些时候,她最大的快乐,就是读书和幻想。
大约晚上十点钟左右,她首先觉得床架子在晃动,她摸摸身边的妹妹,睡得正香,也没做噩梦,怎么床在动呢?难道是地震了?她摸黑下床,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却一脚踩进了齐腰的大水里。
这一下,她大惊失色,立刻本能地呼叫起来: &ldquo光美!光宗!淹水了!淹水了!妈妈!妈妈!淹水了!淹水了!淹水了!&hellip&hellip&rdquo 慌乱中,她盘水奔向母亲的房间,摸着电灯开关,灯不亮了。
而水势汹汹涌涌,一下子已淹到她的胸口,她开始尖叫: &ldquo妈妈!妈妈!&rdquo 黑暗中,她听到&ldquo扑通&rdquo一声水响,有人跳进水中了,接着,是玉兰的哀号: &ldquo光宗!光宗在刘家!我要找光宗去!光宗&hellip&hellip光宗&hellip&hellip&rdquo &ldquo妈妈!&rdquo她叫着,伸手盲目地去抓,只抓到玉兰的一个衣角,玉兰的身影,就迅速地从她身边掠过,手里还紧抱着秋虹,一阵&ldquo哗啦啦&rdquo的水声,玉兰已盘着水,直冲到外面去了。
豌豆花站立不住了,整个人开始漂浮起来,同时,她听到屋子在裂开,四面八方,好像有各种各样恐怖而古怪的声音:碎裂声、水声、人声、东西掉进水中的&ldquo扑通&rdquo声&hellip&hellip而在这所有的声音中,还有鲁森尧尖着嗓子的大吼大叫声: &ldquo玉兰!不许出去!玉兰,把秋虹给我抱回来!玉兰!他妈的!玉兰,你在哪里&hellip&hellip&rdquo 四周是一片漆黑,头顶上,有木板垮下来,接着,整个屋子全塌了。
豌豆花惊恐得已失去了意识,她的身子被水抬高又被水冲下去,接着,水流就卷住她,往黑暗的不知名的方向冲去,她的脚已碰不到地了。
她想叫,才张嘴,水就冲进了她的嘴中,她开始伸手乱抓,这一抓,居然抓到了另一只男人的手,她也不知道这只手是谁的,只感到自己的身子被举起来,放在一块浮动的床板上,她死命地攀着床板,脑子里钻进来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光美,光美还睡在床上!她放开喉咙,尖叫起来: &ldquo光美!光美!光美!你在哪里?&rdquo 她这一喊,她身边那男人也蓦然被喊醒了。
他在惊慌中仍然破口大骂: &ldquo原来我救了你这小婊子!豌豆花!你妈呢?&rdquo接着,他凄厉地喊了起来: &ldquo玉兰!玉兰!你给我把小秋虹抱回来!秋虹!秋虹!玉兰!你伤到了秋虹,我就宰了你!玉兰&hellip&hellip玉兰!我的秋虹呢?我的秋虹呢?&rdquo 豌豆花死力攀着木板,这块载着她和鲁森尧的木板,感觉到木板正被洪流汹涌着冲远,冲远。
她已经无力去思想,只听到鲁森尧在她耳畔狂呼狂号。
这声调的凄厉,和那汹涌的水势,房屋倒塌的声音,风的呼嘯,全汇合成某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同时,还有许多凄厉的喊声,在各处飘浮着。
无数的树叶枯枝从她身上拉扯过去。
这是世界的末日了。
整个世界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
她摇摇晃晃地爬在木板上,水不住从她身上淹过来,又退下去,每次,都几乎要把她扯离那块木板。
她不敢动。
世界没有了,这世界只有水,水和恐怖,水和鲁森尧。
鲁森売仍然在喊叫着,只是,一声比一声沙哑,一声比一声绝望: 秋虹!我的秋虹!玉兰!你滚到哪里去了?秋虹&hellip&hellip我的秋虹&hellip&hellip&rdquo 豌豆花挣扎着想让自己清醒,她勉强睁大眼睛,只看到黑茫茫一片大水,上面黑幢幢地漂浮着一些看不清的东西,大雨直接淋在头顶上,没有屋顶,没有村落,整个乌日乡都看不见了。
木板在漂,要漂到大海里去。
豌豆花努力想集中自己那越来越涣散的思想:大海里什么都有,光宗、光美、秋虹、玉兰&hellip&hellip是不是都已流入大海?她的心开始绞痛起来,绞痛又绞痛。
而她身边,鲁森尧的狂喊已转变为哭泣: &ldquo玉兰&hellip&hellip玉兰&hellip&hellip秋虹&hellip&hellip秋虹&hellip&hellip&rdquo 不知什么时候起,泪水已爬满了豌豆花一脸。
热的泪和着冷的雨,点点滴滴,与那漫天漫地的大洪水涌成一块儿。
恍惚中,有个黑糊糊的东西漂到她的身边,像个孩子,可能是光美!她大喜,本能地伸手就去抓,抓到了一手潮湿而冰冷的毛爪,她大惊,才知道不是光美,而是只狗尸。
她号哭着慌忙松手,自己差点摔进洪水中,一连灌进好几口污水,她咳着,呛着,又本能地重新抓紧木板。
经过这一番经历,她整个心灵,都因恐惧而变得几乎麻痹了。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木板碰到了一棵高大的树枝,绊住了。
树上,有个女人在哭天哭地: &ldquo阿龙哪!阿龙!是阿龙吗?是阿龙吗?&rdquo 立刻,树上老的、年轻的,好几个祈求而兴奋的声音在问: &ldquo是谁?阿龙吗?阿升吗?是谁?是谁?&rdquo &ldquo是我。
&rdquo鲁森尧的声音像破碎的笛子,&ldquo鲁森尧,还有豌豆花!&rdquo &ldquo噢!噢!噢!&rdquo女人又哭了起来,&ldquo阿龙哪!阿龙哪!阿龙&hellip&hellip阿龙&hellip&hellip噢!噢!噢&hellip&hellip&rdquo &ldquo嗬,嗬嗬!嗬嗬!阿升,富美,嗬嗬&hellip&hellip&rdquo另一个年轻男人也在干号着。
树上的人似乎还不少。
&ldquo免哭啦!阿莲!阿明!&rdquo一个老人的声音,嗓子哑哑的,&ldquo我们家没做歹事,妈祖娘娘会保佑我们!阿龙会被救的,阿升他们也会好好的!免哭啦!我们先把豌豆花弄到树上来吧!豌豆花!豌豆花!&rdquo 豌豆花依稀明白,这树上是万家阿伯和他家媳妇阿莲、儿子阿明,万家三代同堂,人口众多,看样子也是妻离子散了。
她想回答万家阿伯的呼唤,可是,自己喉咙中竟发不出一点声音,过度的惊慌、悲切、绝望,和那种无边无际的恐怖把她抓得牢牢的。
而且,她开始觉得四肢都被水浸泡得发胀了。
有人伸手来抓木板,木板好一阵摇晃,鲁森尧慌忙说: &ldquo不用了!我抓住树枝,稳住木板就行了!树上人太多,也承不住的!唉唉&hellip&hellip唉唉!秋虹和玉兰都不见了!&rdquo他又悲叹起来,&ldquo唉唉唉!唉唉!&rdquo &ldquo噢!喚!噢!&rdquo他的悲叹又引起阿莲的啼哭。
&ldquo嗬嗬!嗬嗬!嗬嗬嗬&hellip&hellip&rdquo 哭声、悲叹声、水声、风声、雨声、树枝晃动声&hellip&hellip全混为一片。
豌豆花的神思开始模糊起来。
昏昏沉沉中,万家阿伯的话却荡在耳边:&ldquo我们家没做歹事,妈祖娘娘会保佑我们!&rdquo 是啊!玉兰妈妈没做歹事,光宗、光美、秋虹都那么小,那么好,那么可爱的!好心有好报,妈祖娘娘会保佑他们的!可是,妈祖娘娘啊,你在哪里呢?为什么风不止?雨不止?滔滔大水,要冲散大家呢?妈祖娘娘啊,你在哪里呢?迷糊中,她仿佛回到几年前,大家在山上大拜拜,拜&ldquo好兄弟&rdquo,可是,爸爸却跟着&ldquo好兄弟&rdquo去了。
想着爸爸,她脑中似乎就只有爸爸了。
她几乎做起梦来,梦里居然有爸爸的脸。
杨腾站在矿坑的入口处,对着她笑,帽子戴歪了,她招手要爸爸蹲下来,她细心地给杨腾扶正帽子,扶好电瓶灯,还有那根通到腰上的电线&hellip&hellip爸爸一把拥住了她,把她抱得好紧好紧啊!然后,爸爸对她那么亲切地、宠爱地笑着,低语着: &ldquo豌豆花,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全世界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孩!&rdquo 哦!爸爸!她心中呼号着,你在哪里呢?天堂上吗?你身边还有空位吗?哦!爸爸!救我吧!救我进入你的天堂吧&hellip&hellip她昏迷了过去。
&ldquo豌豆花!豌豆花!&rdquo 有人在扑打她的面颊,有人对着她的耳朵呼唤,还有人把一瓶酒凑在她唇边,灌了她一口酒,她骤然醒过来了。
睁开眼睛,是亮亮的天空,闪花了她的视线,怎么,天已经亮了?她转动眼珠,觉得身子仍然在漂动,她四面看去,才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皮筏里,皮筏上已经有好多人,万家五口、鲁森尧、王家两姐妹和其他几个老的少的。
两位阿兵哥正划着皮筏,嘴里还在不停地大叫着: &ldquo什么地方还有人?我们来救你们了!&rdquo 豌豆花向上看,灌她酒和呼唤她的是万家的阿明婶,她看着阿明婶,思想回来了,意识回来了。
被救了!原来他们被救了!可是,可是&hellip&hellip她骤然拉住阿明婶的衣襟,急促而迫切地问: &ldquo妈妈呢?光宗、光美和小秋虹呢?他们也被救了,是不是?他们也被阿兵哥救了,是不是?&rdquo她的声音微弱而沙哑。
&ldquo大概吧!&rdquo阿明婶眼里闪着泪光,&ldquo阿兵哥说已经救了好多人,都送到山边的高地上去了。
我们去找他们,我家还有五个人没找到呢!大概也被救到那边去了。
&rdquo &ldquo哦!&rdquo豌豆花吐出一口气来,筋疲力尽地倒回阿明婶的臂弯里。
是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们一定被救走了,一定被救走了。
忽然间,她觉得好困好困,只是想睡觉。
阿明婶摇着她: &ldquo不要睡着,豌豆花,醒过来!这样浑身湿淋淋的不能睡。
&rdquo 她努力地挣扎着不要睡觉。
船头的阿兵哥回头对她鼓励地笑笑: &ldquo别睡啊,小姑娘,等会儿就见到你妈妈和弟弟妹妹了!&rdquo 她感激地想坐起身子来,却又无力地歪倒在阿明婶肩头上了,她勉强地睁大眼睛,放眼四顾,一片混沌的、污浊的洪流,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漂浮着无数牲畜的尸体和断树残枝,还有许多铝锅木盆和家庭用具,正涛涛滚滚地奔腾消退着。
雨,已经停了。
一切景象却怪异得令人胆战心惊。
三小时后,他们被送到安全地带,在那儿,被救起的另外两百多人中,并没有玉兰、光宗、光美和秋虹的影子。
阿兵哥好心地拍抚着鲁森尧的肩: &ldquo别急,我们整个驻军都出动了,警察局也出动了,到处都在救人,说不定他们被救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次大水,乌日乡还不是最严重的,国姓里和湖口里那一带,才真正惨呢!听说有人漂到几十里以外才被救起来。
所以,不要急,等水退了,到处救的人集中了,大概就可以找到失散的家人了!&rdquo 豌豆花总算站在平地上了,但她的头始终晕晕的,好像还漂在水上一样,根本站不稳,她就蜷缩在一个墙角上,靠着墙坐在那儿。
阿兵哥们拿了食物来给她吃,由于找不到玉兰和弟妹,她胃口全无,只勉强地吃了半个面包。
鲁森尧坐在一张板凳上,半秃的头发湿答答地垂在耳际,他双手放在膝上,看来一点都不凶狠了,他嘴里不住地叽里咕噜着: &ldquo玉兰,你给我好好地带着秋虹回来,我四十啷当岁了,可只有你们母女这一对亲人啊!&rdquo 三天后,水退了。
乌日劫后余生的居民们从各地返回家园。
在断壁残垣中,他们开始挖掘、清理。
由于海水倒灌,流沙掩埋着整个区域,在流沙下,他们不断挖出亲人的尸体来。
几乎没有几个家庭是完全逃离了劫难的,一夜间家破人亡,到处都是哭儿唤女声。
有的人根本不知被冲往何处,积水三尺中,黄泥掩盖下,无处招亡魂,无处觅亲人,遍地苍凉,庐舍荡然。
人间惨剧,至此为极。
鲁森尧在五天后,才到十里外的泥泞中,认了玉兰和秋虹的尸。
玉兰已经面目全非,只能从衣服上辨认,至于手里抱的婴儿,更是不忍卒睹。
至于光宗光美,始终没有寻获,被列入失踪人口中。
鲁森尧认完尸回到乌日,家早就没有了,五金店也没有了。
豌豆花正寄住在高地上的军营里,还有好多灾民都住在那儿,等待着政府的救济,等待着亲人的音讯。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当真咬春饼
- 玩家糯团子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起点文男主是我爸林绵绵
- (综漫同人)五条小姐总在拯救世界聊笙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他的余温阿宁儿
- [综]混沌恶不想算了!安以默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01入学篇(上)佐岛勤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虫屋金柜角
- 射雕英雄传金庸
- 圣武星辰乱世狂刀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重生女配之鬼修雅伽莎
- 流氓老师夜独醉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控制欲叙白瓷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持续高热ABO空菊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星星为何无动于衷秋绘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网恋同桌归荼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球”嗨夕尧未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不朽神王犁天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眼泪酿宴惟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春生李书锦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共同幻想ENERYS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有只海豚想撩我焦糖冬瓜
- 考试时突然戳到了老师的屁股怎么办?化十
- 新婚ABO白鹿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影帝是棵小白杨闻香识美人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悲惨大学生活风弄
- 竹马危机萧二河
- 宠夫日常[娱乐圈]阿栖栖
- 情终孤君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眼泪酿宴惟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学长在上流麟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替身夺情真心
- 如何才能将目标勾引到手南柯良人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没完晚春寒
- 天真有邪沈明笑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我要这百万粉丝有何用宝禾先生
- 我只想好好谈个恋爱!爱吃肉的羊崽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悲惨大学生活风弄
- 无可替代仟丞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