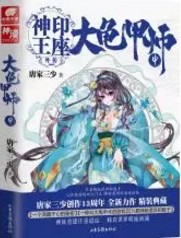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部 豌豆花(1/3)
十月暮,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 窗外的小院里, 开满了豌豆花, 一片紫色的云雾, 紫色的花蕊。
她&mdash&mdash 这小婴儿&mdash&mdash 出生在豌豆花盛开的季节里。
1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台湾正笼罩在一片低气压的云层下,天空是阴暗的,气温燠热而潮湿。
时序虽然已是仲秋,亚热带却无秋意。
热浪侵袭下,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汗水。
许曼亭在她那木板搭成的小屋里,已经和痛苦挣扎了足足二十小时。
小屋热得像个烤箱,许曼亭躺在床上,浑身的衣衫早被汗水湿透,连头发都像浸在水中般湿漉漉的。
而新的汗水,仍然不断地、持续地从全身冒出来,从额头上大粒大粒地滚下来。
从不知道人类的体能可以容忍这么大的痛楚。
许曼亭在半昏沉中想着,难道自己也曾让母亲受过这样的疼痛吗?母亲,不,这时不能想到母亲,还是去想体内那正要冲出母体的婴儿吧!孩子,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hellip&hellip求求你,不要再这样拉扯了,不要再这样撕裂了,不要再这样坠痛了&hellip&hellip 啊!体内一阵翻天覆地的绞痛,使她再也忍不住,脱口叫出声来,无助地、哀求地、惨厉地叫出声来: &ldquo啊!救我&hellip&hellip杨腾!救我!救我!救我&hellip&hellip&rdquo 那等待在小屋外的杨腾被这声凄厉的呼叫声整个震动了,他如同被电击般跳了起来,冲开小屋的门,他往里面冲去,嘴里喃喃地、胡乱地呼唤着: &ldquo曼亭!让天惩罚我!让天惩罚我!&rdquo 他要向那张床扑过去,但是,床边正忙着的三位老妇人全惊动了,邻居阿婆立刻拦过来,抓住他就往屋外推去,嚷着说: &ldquo出去!出去!女人生孩子,男人家不要看!急什么?头胎总是时间久一点的!出去!出去!稍等啦,没要紧,稍等就当阿爸啦!人家阿土婶接过几百个孩子了,不要你操心!出去等着吧!&rdquo 许曼亭的视线,透过汗水和泪水的掩盖,模糊地看着杨腾那张年轻的、轮廓很深的脸和那对惊惶的大眼睛。
他被推出去了,推出去了&hellip&hellip她徒劳地向他伸着手,呻吟地哭泣地低喊: &ldquo杨腾,不行&hellip&hellip你走,我和你一起走!不管到什么地方!我和你一起走!&rdquo 仿佛间,又回到了战乱中。
仿佛间,又回到全家老老小小都挤在火车车厢里的日子。
火车中没有座位,一个车厢里挤满了人,许多陌生人混在一起,谁也照顾不了谁。
车子越过原野,缓缓地、辘辘地碾过劫后的战场,车厢外的景色诡异,燃烧过的小村庄,枯芜的田垄,没有人烟的旷野,流浪觅食的野狗&hellip&hellip&ldquo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rdquo她倚着车窗,脑海里萦绕着《古从军行》的诗句,战争不分古今,不分中外,苍凉情景皆一样!她看着看着,泪珠潸然而下。
然后,杨腾悄悄地挤近她身边,为她披上一件外衣,拭去她颊上的泪痕&hellip&hellip她转眼看他,杨腾,是她奶妈的儿子,以&ldquo家仆&rdquo的身份随行。
战乱中不分主仆,战乱中没有阶级。
今日相聚,明天就可能挨上一个炸弹,让整个车厢炸成飞灰&hellip&hellip她看着杨腾,那大大的眼睛,深深的双眼皮,年轻而热情的脸庞,关怀而崇拜的注视&hellip&hellip 疼痛又来了,像个巨大的浪,把她全身都卷住了。
她感觉得到那小生命正在自己体内挣扎,要冲破那裹住自己的黑暗,要冲进那对他仍然懵懂的世界里。
好一阵强烈的坠痛,痛得她全身都痉挛起来。
阿婆捉住了她的手,阿土婶和阿灶婶在一边喊着: &ldquo用力!用力!阿亭哪,用力呀!&rdquo 用力?她徒劳地在枕上转着头,痛楚已经蔓延到四肢百骸,全身几乎再也没有丝毫力气。
她抽泣着,泪和着汗从眼角滚落。
她拼命想用力,但是,她的呼吸开始急迫,痛楚从身体深处迸裂开来,她觉得整个人都要被拆散了,她只能吸气,脑子开始昏沉,思绪开始凌乱&hellip&hellip模糊中,她听到三个老妇人在床边用闽南语低低交谈: &ldquo好像胎位不对&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要烧香&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羊水早就破了&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会不会冲犯了神爷&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外省女孩就是身子弱&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要不要叫外省郎进来&hellip&hellip&rdquo 要的!要的!她喊着,嘴里就是吐不出声音。
啊,不要,不要。
她想着,不要让杨腾看到她这种样子,这份狼狈。
杨腾眼里的她,一向都是那么高雅的!&ldquo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rdquo冰肌玉骨?怎样的讽刺呢?清凉无汗?怎样可以做到清凉无汗?她摇着头,更深地吸气,更深地吸气&hellip&hellip她的思绪又飘到了那艘载着无数乘客的某某轮上。
船在太平洋上漂着。
整个船上载了将近一千人。
船舱那么小,那么挤,那么热。
他们许家虽然权贵,到了这种时候,也只能多分得一个舱位。
她无法待在那透不过气的船舱里,于是,她常常坐在船桥下的甲板上,夜里,她就在那儿凝视着满天星辰。
&ldquo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hellip&hellip&rdquo 这是唯一的游戏。
坐在那儿,望着星空背唐诗。
然后,杨腾溜了过来,靠近了她坐下,用手抱着双膝。
她看星星,他看她。
背唐诗不是唯一的游戏了。
她的眼光从星空中落到他脸上,他的眼睛炯炯发光。
他们相对注视,没有语言,只是相对注视。
她知道什么是礼教,她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ldquo儒家教育&rdquo。
但是,在这艘船上,在这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星星在天空璀燦,波涛在船缘扑打,海风轻柔地吹过,空气里带着咸咸的海浪的气息。
而他们正远离家乡,漂向一个未知的地方。
在这一刻,没有儒家,没有传统,没有礼教,没有隔阂。
她深深地注视着她面前这个男孩,这个从她童年时代就常在她身边的男孩&hellip&hellip那男孩眼中的崇拜可以绞痛她的心脏,而那烈火般的凝视又可以烧化她的矜持&hellip&hellip他悄悄伸过手来,握住她。
然后,他再挨近她,吻住了她,在那星空之下,大海之上。
一阵剧痛把她骤然痛醒,似乎自己已经昏迷过一段时间了。
她张开嘴,仍然只能吸气。
阿土婶用手背拍打着她的面颊,不住口地喊着: &ldquo阿亭,醒来!醒来!不可以睡着!阿亭,阿亭!&rdquo 三个老妇人又在商量了。
&ldquo&hellip&hellip不能用躺的&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准备麻袋了吗?&rdquo &ldquo&hellip&hellip沙子,稻草&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弄好了吗?就这样&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来,把她搀起来&hellip&hellip&rdquo 她们要怎样呢?她昏昏沉沉的,只是痛、痛、痛&hellip&hellip无尽止的痛。
忽然,她感到整个人被老妇人们挟持起来了,她无力挣扎,两个老妇一边一个挟着她的手臂,把她拖离了那张床。
啊,她猛烈地抽着气。
阿土婶又来拍打她的面颊了: &ldquo蹲下来!用力!再用力!再用力!&rdquo 不要。
她想着。
这是在做什么?她半跪半蹲,双腿无力地垂着。
然后,像有个千斤重的坠子,忽然从她体内用力往外拉扯,似乎把她的五脏六腑一起拉出了体外,她张大嘴,狂呼出声了: &ldquo啊!&hellip&hellip&rdquo 有个小东西跌落在地上的麻袋上,麻袋下是沙子和稻草,三个老妇人齐声欢呼: &ldquo生了!生了!生出来了!&rdquo 生出来了?生出来了?她的孩子?她和杨腾的孩子?被诅咒过的孩子?她勉强张开眼睛,看到的是殷红的血液&hellip&hellip血,殷红地流向麻袋,迅速地被麻袋下的沙子吸去&hellip&hellip 血。
是的,那天,父亲在盛怒下打了杨腾。
那时已经在台湾住下了,战争被抛在过去的时光里,新建立的家园又恢复了显赫的体系。
不是火车里,不是大海上。
在结实的土地上,礼教和尊严再度统治一切。
可是,青春的火焰已经燃烧,爱情没有办法掩人耳目。
父亲在盛怒下打了杨腾,用手臂一般粗的棍子,打得他头破血流,殷红的血从他额头、鼻孔和嘴角涌出来,染红了他那件白汗衫。
奶妈哭泣着在一边狂喊: &ldquo不要打他!杀了我吧!杀了我吧!&rdquo 杨腾倒下去,又挣扎着站起来,挺立在那儿。
父亲的棍子再挥下去,她挣脱了母亲和姨娘们的手臂,直扑向杨腾,哭着大叫: &ldquo打死了他,我也跟着死!&rdquo &ldquo你不要脸!&rdquo父亲怒吼,一棍打向她肩上,杨腾大惊,用手臂死命护住她。
那一棍结结实实打在他手腕上。
杨腾对她大喊着: &ldquo别管我!你走开!走开!走开!&rdquo &ldquo不!不!不!&rdquo她死缠住他,让父亲的棍子连她一起打进去。
父亲暴怒如狂: &ldquo杨腾!你给我滚出去!滚到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否则我会宰了你!&rdquo &ldquo我走!&rdquo杨腾挺立着说,&ldquo我马上就走!我再也不做你家的寄生虫!我要走到一个地方,去创造我自己的世界!我走!我马上就走!&rdquo &ldquo杨腾,不行&hellip&hellip&rdquo她哭喊着,&ldquo你走,我和你一起走!不管到什么地方!我和你一起走!&rdquo &ldquo曼亭!&rdquo父亲怒吼,&ldquo你要跟他走,你就跟他一起滚!滚到地狱里去!我诅咒你!下贱卑鄙的东西!你如果跟他一起滚,你们都不得好死!你们生下的孩子,也永世不得超生&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要再说了!&rdquo母亲尖叫起来,&ldquo曼亭,如果你敢跟他走,你就是杀了我了!&rdquo 奶妈走过来,直挺挺地跪在曼亭面前了: &ldquo小姐,我的好小姐,你就放了他吧!让他一个人走!我一生只生了两个儿子,大的是阿腾,小的叫阿勇。
你知道吗,小姐?因为我来你家喂你奶,把刚出世的阿勇寄在农家,结果,阿勇死了,阿腾的爹变了心,另娶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阿腾,你让他走吧!小姐,阿腾配不上你,你是念过书的大家小姐,他是做粗活的乡下孩子!你跟了他,也不会幸福!&rdquo &ldquo奶妈,奶妈!&rdquo曼亭哭着,也对奶妈直挺挺跪下去了,&ldquo我跟你说,我从不知道阿勇的事,现在我知道了!一切算是命中注定吧,我们许家欠你一条命,我这条命,就豁出去跟了阿腾了!你别再说,别再说了!是我自愿的!是我甘愿的!受苦受难受诅咒,都是我甘愿的!&rdquo 杨腾依然挺立在那儿,听到这里,他闭上眼睛,泪珠和着额上的血,沿颊滚落。
他用手摸索着曼亭的头发,哑声说: &ldquo你好傻!你好傻!你好傻!&rdquo &ldquo滚!&rdquo父亲狂叫,&ldquo不要在我面前让我看着恶心,我有五个女儿六个儿子,少了你一个根本不算什么!你给我马上滚!&rdquo &ldquo不要!&rdquo母亲也跪下了,对父亲跪下了,&ldquo你饶了她吧!她才十九岁,不懂事呀!&rdquo 于是,父亲那三个姨娘也跪下了,她的四个姐妹也跪下了。
那天,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许家那日式房子的大花园里,就这样黑压压地跪了一院子的人。
&ldquo&hellip&hellip咕哇,哇,咕哇&hellip&hellip咕哇&hellip&hellip&rdquo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三位老妇人还在床边忙着,她已经躺回床上了,汗水仍然在流着,渗入身下的草席里。
头发依旧湿答答,浑身上下,依然分不出哪儿在痛。
但是,孩子在哭呢!咕哇,咕哇,咕哇&hellip&hellip多么动人的哭声,这是生命呢!是由她和杨腾制造的生命呢!她转侧着头,呻吟着低语: &ldquo孩子&hellip&hellip孩子&hellip&hellip&rdquo 阿婆走近她面前,摸摸她的额,用毛巾拭去她额上的汗,用带着歉意的语气说: &ldquo是个女孩子呢!不要紧,头胎生女儿,下一胎一定是个男孩!&rdquo 女孩子?她的心思飘浮着。
杨腾会失望了,奶妈泉下有知,也会失望了,杨家还等着传宗接代呢!她对门口望去,杨腾似乎冲进来好多次,都被推出去了。
现在,杨腾又冲进来了,他直扑到她的床前,两眼发直,眼中布满了红丝,面色紧张而苍白,他伸手摸她的手、她的面颊、她的下巴,嘴里急促地问: &ldquo你好吗?你还好吗?你怎样了?你怎么白得像枝芦苇草呢!你能说话吗?你&hellip&hellip&rdquo &ldquo杨腾,&rdquo她微弱地、怜惜地、歉然地说,&ldquo是个女孩&hellip&hellip对不起&hellip&hellip是个女孩&hellip&hellip&rdquo 他一下子就把头扑在她的枕边,他的手指强而有力地紧攥着她,他的声音从枕边压抑而痛楚地迸出来: &ldquo不要说对不起!永远不许对我说对不起!是我把你拖累到这个地步,是我害你吃这么多苦,如果不是跟着我,你现在还是千金大小姐&hellip&hellip&rdquo &ldquo杨腾!&rdquo她衰弱地打断他,勉强地想挤出微笑,她的手指触摸着他那粗糙的掌心。
她多想抬起手来,去抚摸他那粗黑浓密的头发啊!但,她的手却那么无力,无力得简直抬不起来。
阿婆又过来了,端着一碗东西,她粗声地命令着: &ldquo外省郎,你就让开一点,让你的女人吃点东西!柑橘麻油鸡蛋!吃了就有力气了!&rdquo 杨腾又被推开了。
一碗带着酒味、麻油味、柑橘味的东西被送到她嘴边,阿土婶和阿灶婶扶着她,强迫地把一匙黄澄澄油腻腻的食物喂进她嘴中。
她才吞下去,骤然引起一阵强烈的恶心,顿时,整个胃都向外翻,她用力扑倒在床边,不让呕吐物玷污了席子。
可是,她觉得体内正有股热浪,从两腿间直涌出去&hellip&hellip直涌出去&hellip&hellip直涌出去&hellip&hellip 她的思绪又飘远了,飘远了。
第一次来到中部这个小村落的时候,她真不太相信自己会住下来。
那单薄的小木屋,像一挤就会压碎的火柴盒,既挡不住风雨,也遮不了烈日。
可是,杨腾在这儿,他已经在这儿工作半年了。
他在这儿,这儿就该是她的家。
杨腾是在挨打后的第二天失踪的。
有好一阵子,奶妈天天哭,她也哭。
许家把她软禁着,对奶妈也呼来喝去,没有好脸色。
曼亭的日子变得那么难挨,姨娘们对她冷言冷语,姐妹们对她侧目而视,父亲对她怒发冲冠,而母亲却天天数落着她的&ldquo不是&rdquo,和她带给家门的&ldquo羞辱&rdquo。
这种日子漫长而无奈,她以为自己挨不过那个秋天和冬天了。
她总想到死,总想一了百了。
总想到星空之下和大海之上的时光。
&ldquo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rdquo 又回到背唐诗的日子,背的全是这类文句,随便拿起纸和笔,涂出的也都是&ldquo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rdquo。
她以为自己终将枯竭而死了,可是,她发现奶妈不再哭泣了,不但不再哭泣,而且,常常带着抹神秘的喜悦。
于是,她知道了,知道杨腾一定和他母亲取得联系了。
于是,她在许多夜里,就匍匐在奶妈膝上,请求着,保证着,哭诉着,央告着&hellip&hellip于是,有一天,奶妈带着她一起离家私逃了,她们来到了这个小村落,投奔了正在当矿工的杨腾。
这个小村落是因为瑞祥煤矿而存在的,所有的男人都在矿里工作,所有的女人都在院子里种花椰菜、种豌豆、种葱,种各种蔬菜,或养鸡鸭来贴补家用。
忽然间,唐诗完全没有用了,忽然间,孔子孟子四书五经宋词元曲都成为历史的陈迹。
她的&ldquo过去&rdquo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新的世界里只有杨腾、奶妈和满园的花椰菜、满园的豌豆&hellip&hellip 她学习着适应,冬天,皮肤被冷风冻得发紫,夏天,又被阳光炙烤得红肿&hellip&hellip她没有抱怨过,甚至没有后悔,她只是不知不觉地衰弱下去。
奶妈是春天去世的,那时,曼亭刚刚知道怀了孕,奶妈临终时是含着笑的: &ldquo亭亭,&rdquo她唤着她的乳名,&ldquo给杨家生个儿子!生个男孩子,杨家等着他传宗接代!&rdquo &ldquo咕哇&hellip&hellip咕哇&hellip&hellip咕哇&hellip&hellip&rdquo 孩子在哭着。
女孩子?为什么偏偏是女孩子? 曼亭在枕上转着头,室内三个老妇人的声音嗡嗡地响着,像来自遥远的深谷: &ldquo&hellip&hellip不许碰水缸!产妇流血不停,不能碰水缸&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抓起她的头发,把她架起来&hellip&hellip&rdquo 又有人把她架起来了,她全身软绵绵,头发被拉扯着,痛、痛、痛。
最后,她仍然躺下去了。
室内似乎乱成了一团。
&ldquo&hellip&hellip念经吧!阿婆,快去买香!&rdquo &ldquo&hellip&hellip外省郎,烧香吧,烧了香绕着房子走,把你的女人唤回来&hellip&hellip&rdquo &ldquo&hellip&hellip到神桌下面去跪吧&hellip&hellip&rdquo &ldquo咕哇&hellip&hellip咕哇&hellip&hellip咕哇&hellip&hellip&rdquo 孩子在哭着。
怎么呢?难道她要死了吗?曼亭努力要集中自己涣散的神志。
不行,孩子要她呢!不行,她不要死,她要带孩子,她还要帮杨腾生第二胎,她还要在杨腾带着满身煤渣回家时帮他烧洗澡水,她还要去收割蔬菜&hellip&hellip她努力地睁开眼睛,喃喃地低唤: &ldquo杨腾,杨腾,孩子,孩子&hellip&hellip&rdquo 杨腾一下子跪在床前,他的脸色白得像纸,眼睛又红又肿,粗糙的大手握着她那纤细修长的手,他的声音沙哑粗暴而哽塞: &ldquo曼亭!你不许死!你不许死!&rdquo &ldquo呸!呸!呸!&rdquo阿婆在吐口水,&ldquo外省郎,烧香哪,烧香哪!念佛哪!&rdquo 空气里有香味,她们真的烧起香来了!有人喃喃地念起经来&hellip&hellip而这一切,离曼亭都变得很遥远很遥远。
她只觉得,那热热的液体,仍然在从她体内往外流去,带着她的生命力,往外流去,流去,流去。
&ldquo孩子,&rdquo她挣扎着说,&ldquo孩子!&rdquo &ldquo她要看孩子!&rdquo不知是谁在嚷。
&ldquo抱给她看!外省郎,抱给她看!&rdquo 杨腾颤巍巍地接过那小东西来,那包裹得密密的,只露出小脸蛋的婴儿。
他含着泪把那脆弱而纤小得让人担心的小女婴放在她枕边。
她侧过头去看孩子,皱皱的皮肤,红彤彤的,小嘴张着,&ldquo咕哇&hellip&hellip咕哇&hellip&hellip&rdquo地哭着,眼睛闭着&hellip&hellip曼亭努力地睁大眼睛看去,那孩子有两排密密的睫毛,而且是双眼皮呢!像杨腾的大双眼皮呢! &ldquo她&mdash&mdash会长成&mdash&mdash一个很&mdash&mdash很美很美的&mdash&mdash女孩!&rdquo她吃力地说,微笑着,抬眼看着窗外。
十月暮,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窗外的小院里,开满了豌豆花,一片紫色的云雾,紫色的花蕊。
她&mdash&mdash这小婴儿&mdash&mdash出生在豌豆花盛开的季节。
&ldquo豌豆花。
&rdquo她低低地念叨着,&ldquo紫穗,杨紫穗!豌豆花!一朵小小的豌豆花!&rdquo 她握着杨腾的手逐渐放松了,眼睛慢慢地合拢,终于闭上了。
生命力从她身体里流失了,完完全全地流走了。
&ldquo咕哇,咕哇,咕哇&hellip&hellip&rdquo新的生命力在呐喊着。
杨腾瞪着那张床,那张并列着&ldquo生&rdquo与&ldquo死&rdquo的床。
他直挺挺地跪在床前,两眼直直地瞪视着,不相信发生在面前的事实。
他不动,不说话,不哭,只是直挺挺地跪在那儿。
一屋子念经诵佛的声音。
那女孩就这样来到世间。
她的母亲临终时,似乎为她取过名字,但是,对屋里每一个人而言,那名字都太深了,谁也弄不清楚是哪两个字。
阿土婶曾坚持是&ldquo纸碎&rdquo或是&ldquo纸钱&rdquo之类的玩意,认为这女孩索走了母亲的命,所以母亲要她终身烧纸来祭祀。
杨腾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曼亭曾重复地说过: &ldquo豌豆花!一朵小小的豌豆花!&rdquo 于是,她在小村落中成长,大家一直叫她&ldquo豌豆花&rdquo。
她没有名字,她的名字是&ldquo豌豆花&rdquo。
2
豌豆花出生后的三个月,杨腾几乎连正眼都没瞧过这孩子,他完全坠入失去妻子的极端悲痛中。一年之内,他母丧妻亡,他认为自己已受了天谴。
每天进矿坑工作,他把煤铲一铲又一铲用力掘向岩石外,他工作得比任何人都卖力,他似乎要把全身的精力、全心的悲愤都借这煤铲掘下去,掘下去,掘下去&hellip&hellip他成了矿场里最模范的工人。
矿坑外,他是个沉默寡言、不会说笑的&ldquo外省缘投样&rdquo,&ldquo缘投&rdquo两字是闽南语,&ldquo样&rdquo是日语。
翻成国语,&ldquo缘投&rdquo勉强只能用&ldquo英俊&rdquo两个字来代替,&ldquo样&rdquo是先生的意思。
杨腾始终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豌豆花出世这年,他也只有二十三岁。
于是,豌豆花成了隔壁阿婆家的附属品。
阿婆姓李,和儿子儿媳及四个孙儿孙女一起住。
阿婆带大过自己的儿子和四个孙儿孙女,带孩子对她来说是太简单了。
何况,豌豆花在月子里就与别的婴儿不同,她生来就粉妆玉琢,皮肤白里透红,随着一天天长大,她细嫩得就像朵小豌豆花。
乡下孩子从没有这么细致的肌肤,她完全遗传了母亲的娇嫩,又遗传了父亲那较深刻的轮廓,双眼皮,长睫毛,乌黑的眼珠,小巧而玲珑的嘴。
难怪阿婆常说: &ldquo这孩子会像她阿母说的,长成个小美人!&rdquo 豌豆花不只成了李家阿婆的宝贝,她也成了李家孙女儿玉兰的宠儿。
玉兰那年刚满十八岁,是个身体健康,发育得均匀而丰腴的少女。
乡下女孩一向不被重视,她的工作是帮着家里种菜喂猪,去山上砍柴,去野地找野苋菜(喂猪的食料)以及掘红薯,削红薯签。
当地人总是把新鲜红薯削成签状,再晒干,存下来,随时用水煮煮就吃了。
玉兰的工作永远做不完,但是,在工作的空隙中,她对豌豆花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抱那孩子,逗那孩子,耐心地喂豌豆花吃米汤和蔬菜汁。
孩子才两个月,就会冲着玉兰笑,那笑容天真无邪,像传教士带来的画片上的小天使。
阿婆的人生经验已多。
没多久,她就发现玉兰经常抱着豌豆花去杨腾的小屋里,&ldquo让豌豆花去看阿爸&rdquo。
阿婆看在眼里,却什么话都没说。
女孩子长大了,有女孩子的心思,那&ldquo外省郎&rdquo可惜是外省人,别的倒也没缺点,身体强壮,工作努力,赚钱比别的工人多。
而且,他能说闽南语,又相当&ldquo缘投&rdquo。
杨腾终于注意到豌豆花的存在,是豌豆花满一百天之后的事了。
那天晚上,玉兰又抱着孩子来到杨腾的小屋里。
孩子已会笑出声音了,而且一对眼珠,总是骨碌碌地跟着人转。
杨腾洗过了澡,坐在灯下发着呆,那些日子,他总是坐在灯下发呆。
玉兰看着他摇头,把孩子放在床上,她收起杨腾的脏衣服,拿到后院的水缸下去洗。
单身男人,永远有些自己做不了的事,玉兰帮杨腾洗衣或缝缝补补,早已成为自然。
那晚,她去洗衣时,照例对杨腾交代过一句: &ldquo杨哎,看着豌豆花!&rdquo 玉兰称呼杨腾为&ldquo杨哎&rdquo,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习惯,只因为杨腾是外来的人,不是土生土长,没个小名可以由大家呼来喝去。
于是,简单点儿,就只在姓的后面加个语助词来称呼了。
玉兰去洗衣服后,杨腾仍然坐在灯下发呆。
三个半月的豌豆花,虽然只靠米汤、肉汁、蔬菜汁胡乱地喂大,却长得相当健康,已经会在床上滚动、翻身。
杨腾正对着窗外发怔,那夜是农历年才过没多久,天气相当凉,天上的星星多而闪亮&hellip&hellip他的思绪飘浮在某某轮上,星空之下,曼亭正坐在船桥下望星星。
蓦然间,他听到&ldquo咚&rdquo的一响,接着是孩子&ldquo哇&rdquo的大哭声。
他大惊回顾,一眼看到豌豆花已从床上跌到床下的土地上。
在这刹那间,那父女连心的血缘之亲抽痛了他的心脏。
他惊跳起来,奔过去抱起那孩子。
豌豆花正咧着嘴哭,他粗手粗脚地抚摸孩子的额头、手腕、腿和那细嫩的小手小脚,想找出有没有摔伤的地方。
就在他的手握住孩子那小手的一瞬间,一种温暖的柔软的情绪蓦然攫住了他的心脏,像有只小手握住他的心一般,他酸痛而悸动了。
同时,豌豆花因为被抱了起来,因为得到了爱抚,她居然立刻不哭了,非但不哭了,她破涕为笑了。
睁大了那乌黑的眼珠,她注视着父亲,小手指握着父亲粗壮的大拇指,摇撼着,她嘴里&ldquo咿咿呀呀&rdquo地说起无人了解的语言。
但,这语言显然直刺进杨腾的内心深处去,他惊愕不解,迷惑震动地陷进某种崭新的感情里。
豌豆花!他那小小的豌豆花!那么稚嫩,那么娇弱,那么幼小,那么可爱&hellip&hellip而且,那么酷似曼亭啊! 他怔住了,抱着豌豆花怔住了。
同时,玉兰听到孩子的哭声和摔跤声,她从后院里直奔了进来,急促地嚷着: &ldquo怎么了?怎么了?&rdquo 看到杨腾抱着孩子,她立刻明白孩子滚下床了。
她跑过来,手上还是湿漉漉的,她伸手去摸孩子的头,因为那儿已经肿起一个大包了。
孩子被她那冰冷的手指一碰,本能地缩了缩身子,杨腾注意到那个包包了。
&ldquo糟糕!&rdquo他心痛了,第一次为这小生命而心痛焦灼了,&ldquo她摔伤了!她痛了!怎么办?怎么办?&rdquo他惶急地看着玉兰。
&ldquo不要紧的呢!&rdquo玉兰笑了。
看到杨腾终于流露出的&ldquo父性&rdquo,使她莫名其妙地深深感动了,&ldquo孩子都会摔跤的,我妈说,孩子越摔越长!&rdquo她揉着孩子的伤处,&ldquo擦点万金油就可以了。
&rdquo 玉兰满屋子找万金油,发现屋里居然没有万金油。
她摇摇头,奔回家去取了瓶万金油来,用手指把药膏轻轻抹在孩子的患处上。
因为疼痛,豌豆花又开始哭了,杨腾心痛地抱紧孩子,急切地说: &ldquo别弄痛她!&rdquo &ldquo一定要上药的!&rdquo玉兰说,揉着那红肿之处,一面埋怨地看了杨腾一眼,&ldquo交给你只有几分钟,就让她摔了。
真是个好阿爸啊!来,我来抱吧!她困了。
&rdquo 杨腾很不情愿地松了手,让玉兰抱起豌豆花。
玉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怀抱着婴儿,轻轻地摇晃着,孩子被摇得那么舒适,不哭了。
玉兰怜爱地看着孩子的脸庞,一面摇着,一面唱着一支闽南语催眠曲: 婴仔婴婴困,一瞑大一寸, 婴仔婴婴惜,一瞑大一尺。
摇儿日落山,抱子紧紧看, 囝是我心肝,惊你受风寒。
婴仔婴婴困,一瞑大一寸, 婴仔婴婴惜,一瞑大一尺。
同是一样囝,那有两心情, 查埔也要疼,查某也要成。
婴仔婴婴困,一瞑大一寸, 婴仔婴婴惜,一瞑大一尺。
疼是像黄金,成囝消责任, 养你到嫁娶,母才会放心! 婴仔婴婴困,一瞑大一寸, 婴仔婴婴惜,一瞑大一尺。
&hellip&hellip 杨腾带着某种深深的感动,看着玉兰摇着孩子,听着她重复地低哼着&ldquo婴仔婴婴困,一瞑大一寸&rdquo的句子。
玉兰的歌喉柔润而甜蜜。
她那年轻红润的面庞贴着孩子那黑软的细发。
她低着头,长发中分,扎成两条粗黑的发辫,一条垂在胸前,一条拖在背上。
灯光照射着她的面颊,圆圆的脸蛋,闪着光彩的眼睛&hellip&hellip她并不美,没有曼亭的十分之一美,但她充满了大自然的活力,充满了女性的吸引力,而且,还有种母性的温柔。
她抱着孩子的模样,是一幅感人的图画。
&ldquo婴仔婴婴困,一瞑大一寸&hellip&hellip&rdquo 孩子已经睡着了,杨腾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注视着那孩子甜甜的睡态,孩子在吮着嘴唇,合着的两排睫毛不安静地闪动着。
&ldquo她在做梦呢!&rdquo杨腾小声说。
&ldquo是啊!&rdquo玉兰小声答,抬起头来,她对杨腾微微一笑,杨腾也回了她微微一笑。
这是第一次,玉兰看到杨腾对她笑。
那笑容真切诚挚而令她怦然心跳。
这以后,带豌豆花似乎是玉兰的喜悦了。
玉兰不只帮杨腾带豌豆花,她也帮他洗衣,整理房间,处理菜园里的杂草,甚至于,把家里煮好的红薯饭偷送到杨腾这儿来给他吃。
&ldquo玉兰!&rdquo玉兰的妈生气了,常常直着喉咙喊,&ldquo你给我死到哪里去了?整天不见人影,也不怕人说闲话!&rdquo &ldquo哎哟!&rdquo阿婆阻止了儿媳妇,&ldquo女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表妹软玉娇香渊爻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玩家糯团子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夜行歌紫微流年
- 咸鱼飞升重关暗度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怀了队友的崽怎么破西山鱼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圣武星辰乱世狂刀
- 乾坤剑神尘山
- 穿成废材后他撩到了暴躁师兄是非非啊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控制欲叙白瓷
- 持续高热ABO空菊
- 你们练武我种田哎哟啊
- 少帝春心寒鸦
- 咒术界不普通夫夫关山月下
- 我有幻想成真系统[娱乐圈]蝎言蝎语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不息阿阮有酒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游弋的鱼乌筝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春生李书锦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球”嗨夕尧未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游弋的鱼乌筝
- 循规是笙
- 大叔,你好大江流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学长在上流麟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杨九淮上
- 恶魔总监:亿万独宠小男友浔弦
- 怀孕之后我翻红了[娱乐圈]核桃酸奶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404信箱它在烧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穿女装被室友发现了怎么办linglongzizizi
- 轻狂巫哲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秃头之后,我在前男友面前变强了鱼片面包
- 他喜欢白月光味信息素等登等灯
- 小可怜开心是福嘛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球”嗨夕尧未
- 沉迷撒娇虞子酱
- 循规是笙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大叔,你好大江流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考试时突然戳到了老师的屁股怎么办?化十
- 没完晚春寒
- 国色天香南风歌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独立日学习计划一碗月光
- 撒谎精发芽芽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我姿势都摆好了,你都不上我秽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