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章 不露相思意(3/3)
上坐下来:&ldquo听唱片好吗?&rdquo 顾左右而言他,他的一贯伎俩。
也不晓得是只对她,还是早养出来的习性。
桌上摆着个蜡筒留声机,漆黑的大喇叭比那留声机的盒子大了几倍,在深夜里,在台灯下,朝着他们,有些骇人。
傅侗文打开抽屉,挑拣着圆柱型的唱片。
他想听戏,这里没有:&ldquo我去楼下看看,有新的唱片机。
&rdquo 没多会儿,老翁披着褂子,迷糊地抱着个能听唱片的留声机上来。
傅侗文在身后,将挑拣的黑胶唱片搁在一旁。
老翁小声赔不是说,是他们老两口喜欢听戏,才挪用了三爷的东西。
傅侗文不大在意:&ldquo久不用也会坏,我走了,你们再搬下去。
&rdquo 人家走了,他摆弄着。
大张旗鼓弄个留声机,这是要守一夜的做派? 她轻拽他的衬衫袖子:&ldquo还是我守着吧。
&rdquo他熬下去不是个法子。
傅侗文没回头:&ldquo再等等。
&rdquo 他将唱片摆妥当,身子倚靠过来,胳膊搭到她肩后头:&ldquo小子云的《文昭关》。
&rdquo 胡琴声骤起。
那里头的人行腔曲折,一句句顿挫入耳。
他的两指轻刮在她的肩上,来来去去,穿着拖鞋的脚在打着点儿,眼望着唱片机。
从她这里瞧,他眼里有浮光。
&ldquo你在北京也是这样的吗?&rdquo 他被她的声引过来:&ldquo怎样?&rdquo &ldquo这样。
&rdquo她指唱片机。
她认识的傅侗文是在海上的、新式的、留洋的新派男人。
那深宅大院里的他,影影绰绰,早没了具体的轮廓,只记得咳嗽、雨、雕花灯笼。
他笑:&ldquo我听戏是去百顺胡同,自己听会显落寞,家人也会认为我病了。
&rdquo 浸于声色犬马,傅老三是这样的。
昏黄的灯光下,他端详她的脸,低声说:&ldquo回去后,你会不喜欢三哥。
&rdquo &ldquo不会的。
&rdquo她下意识地反驳,回得太快,凸显出心急来。
傅侗文的脸已经过来,想要吻,又迟迟不动。
柜子上,景泰蓝镶的玻璃罩子里有个时钟,正指到三点。
叮叮当当敲了三声。
这样巧,逗得他笑了,这回换了口气,轻松不少:&ldquo被女朋友不喜欢也是很惨,你要是想分手了,不要说出来。
留个念想,让我以为你会回来。
&rdquo 唱片里正是那句一一&ldquo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hellip&hellip&rdquo本就是装落寞可怜的话,被这戏文陪衬着,更显哀戚。
&ldquo&hellip&hellip我没说要分手。
&rdquo沈奚被他说得更心急了。
傅侗文笑。
他人挨近了,又想去吻她。
仓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他马上警觉了,关上留声机。
沈奚要起身,被他用手按在膝盖上,阻止了动作。
哪怕真是危险到来,也用不到她一个女孩子做什么。
脚步近了,停下。
&ldquo侗文,我。
&rdquo是谭庆项。
&ldquo谭先生!&rdquo沈奚欣喜去开门,将人放进来。
谭庆项浑身湿透了,满裤腿的泥,走几步,就留几步的印子。
手里的毛巾估计是楼下拿上来的,胡乱擦着头发和脸:&ldquo长堤、西濠口、下西关、澳口,全淹了。
我是出了大价钱,让人帮我逃过来的。
&rdquo他喘息,将眼镜戴上,&ldquo浮尸都是从身边飘过去的,太可怕了这洪水[2]。
&rdquo 他们的行李都在船上,沈奚见他这样子不行,下楼去问老翁要了衣裳来,给谭庆项。
衣裳都拿到楼下去,先洗了。
她忙活完回来,看到谭庆项换上了灰褂子,光着脚踩在地上,滑稽得要命。
&ldquo我怕你们被困在十三行,拼命想过去,出多少钱都没人肯,&rdquo谭庆项心有余悸,看了眼表,&ldquo那里起大火了,街上是洪水,屋子联排地烧,没地方逃。
&rdquo 那太可怜了,下午茶楼挤那许多人,在避洪水&hellip&hellip 又是十三行,又是一场大火。
她恍惚听,好似面前是父亲,他在讲着咸丰六年的大火。
两人说了半个时辰。
沈奚和谭庆项都坚持让傅侗文先休息,把人劝上床,在门外又聊了许久。
谭庆项虚掩上门:&ldquo我出去看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不。
&rdquo 这也是她想要做的。
不过她是个女孩子,深夜出去,最怕是帮不上忙,还让人记挂。
两人最后议定结果是,等天亮了,谭庆项出去看水势,顺便想办法打探码头的消息。
沈奚就在临近街上看一看。
可事实是,天亮后,一层已经进水了。
两人先帮老夫妇将一楼的食物移到二楼,再蹚过一楼的水,离开公寓。
水浸了街,很深。
&ldquo你等我先去看看。
&rdquo 谭庆项去探了圈,真有低洼地方逃过来的,许多女人、孩子,也有受伤的人。
&ldquo我寻思着,可以带一些回来,挑妇女孩子,受不住的那些。
&rdquo毕竟人生地不熟,收男人不安全。
&ldquo我帮你去。
&rdquo沈奚就将裙子系到大腿上,要下去。
人还没下去,老妇人追出来,握上她的手腕:&ldquo那水脏啊,女人不能进这么脏的水。
&rdquo 老妇人当着谭庆项不好说很仔细,可两个医生在一块,怎会不知道女人下边是怕脏东西的,可靠谭庆项一个人也不成。
&ldquo让她去。
&rdquo傅侗文人站在楼梯半截上,望着这里。
老妇人:&ldquo先生,你劝她啊。
&rdquo 傅侗文一笑:&ldquo沈小姐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抛下我,去救别人。
&rdquo 也不是吧&hellip&hellip沈奚犹豫着。
他笑,其实是在调侃。
&ldquo我倒喜欢看女孩子的背影,&rdquo傅侗文掉头,上了楼,对老妇人吩咐着,&ldquo一楼厨房淹了,我们要弄到热水,帮帮这两位医生。
&rdquo 这倒像是在表白心意。
沈奚还傻愣在那儿。
这是傅侗文第一次直白地说他喜欢什么。
谭庆项将脸上雨水抹掉,笑:&ldquo调侃你呢,他这人就喜欢讨个嘴上便宜。
来,跟上我。
&rdquo 他先蹚水下去了。
沈奚也没敢耽搁,两人摸到临近两条街上,帮着人将伤员挪到没有水的地方。
到中午水退下去一些,很快又涨上来。
这公寓多了两个女人和五个孩子,沈奚检查了几个孩子,都无碍,将他们让到客房去休息。
全是在水里困了一日夜的人,七魄散了,哭啼啼,更寻不着三魂。
倒也好照顾,老翁一人就足够应付。
一楼淹的水退了。
地板上留下的淤泥,形如浅滩沙,臭不可闻。
沈奚和谭庆项都没来得及冲澡,只洗净手脸,坐在一处吃面。
&ldquo这是连香糕酥馆的莲蓉酥,&rdquo老妇人将盒子打开,&ldquo爷说,拿给你们吃。
&rdquo 她的灵台忽然清明,他在楼上。
老妇人先将厨房清理了,又去擦前厅的地板,总算收拾出了样子。
吃着吃着,谭庆项给她讲起了傅侗文那个青梅竹马,是如何在走之前,想成就夫妻之实,再用让他去法国治病的法子,双管齐下把他骗出去。
可傅侗文此人,却真是不同的,倘若那女孩真是坚持所追求的,抛下了他,他倒有可能和她成亲。
一人一国,各自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也算是佳话。
可女孩这样,不只羞辱了她自己,也全然瞧不起傅侗文的理想。
这才有灵魂陌路的说法。
讲完了,谭庆项抹去额头上的汗,笑了。
他早该想到,从沈奚第一次冲上去执意要救人开始,到那夜,再到今日,傅家老三如何能不将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放在眼前,留在心上? 填饱了肚子,在老妇人的催促下,她去洗了个热水澡。
街上的水是真的脏,夹带着成千上百的垃圾和泥水,浴池里的水换了两次,她终于觉得自己干净了。
见沈奚没有换洗衣物,老妇人翻出来女儿留下的衣裳给她,小小的纽子,从领口绕过前胸,到身子一侧,她系着,很觉有趣。
像袄裙,可又不像。
&ldquo我女儿嫁了个华侨,他们华侨女人喜欢穿这个。
&rdquo老妇人笑说,大了点,看上去倒是适合她。
沈奚人出浴室,倒扭捏起来,望一望屋里。
没人。
去哪儿了? 沈奚的皮鞋在水里泡烂了,也穿了老妇人女儿的鞋,大了,脚跟都站不稳。
开门,向外找人,正见着傅侗文抱着带回来的小男孩,在给人家穿裤子。
他坐在小凳子上,腿太长,又穿了剪裁合身的西裤,板正的布料,弯起腿不舒服。
于是这三少爷就只能伸长两只腿,人靠在对门外的墙上,皮鞋搭在了她这里的门框上。
他见她出来了,笑问小男孩:&ldquo姐姐像个女英雄,是不是?&rdquo &ldquo是。
&rdquo小男孩咧嘴笑。
裤子穿好了,他又将小孩的裤绳打个结,一拍那小屁股:&ldquo去吧。
&rdquo 小男孩抱他的脑袋,在脑门子上吧唧亲了口,光着脚丫啪嗒啪嗒地跑进去。
没跑两步,好似听了房里人的话,兜回来,将门关上。
他这才像眼里有她,微笑着,上下瞧着她。
她低头看自己:&ldquo有点奇怪。
&rdquo 她长发披散着,将鹅蛋脸衬得更显白,仿佛浸过水的一双眸子,干干净净的,人也坦坦白白,肉嘟嘟的小脸红了。
她将头发捋到耳后,小声说:&ldquo我替你把把脉吧。
&rdquo 傅侗文手撑了地板,借力起身,去拉她的手。
拉着她走回到两人的房里去,也不作声,将她牵到床边上。
孩子们饿了,叫嚷着,打开门。
来回跑着,隔着一道木门很清晰。
隐隐地,竟还有个女人在哼着曲子:&ldquo月光光,照地堂&hellip&hellip落雨大,水浸街&hellip&hellip&rdquo 两人都笑起来,歌谣也是这样应景。
他们两个像置身在很嘈杂的马路上,好似四周都围着人,多少双眼看着他们似的。
&ldquo昨日唱到哪里?还记着吗?&rdquo他问。
&ldquo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rdquo这两句,她印象颇深。
&ldquo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rdquo 沈奚对这戏并不熟,摇头。
&ldquo先上床,&rdquo他说,去摆弄那个留声机,&ldquo放给你听。
&rdquo 又上床&hellip&hellip都说过去京城公子哥的喜好是,卧在榻上烧一杆烟,整日不下地。
从轮船到这里,傅侗文算是给了她一个见识的机会。
傅侗文瞧她没动,笑了:&ldquo不乏吗?&rdquo 哗的一声轻响,窗帘被他带了大半,挡去床上的光。
他走来,弯腰替她脱了鞋。
温热的手,忽然近了,沈奚将脚缩着,心跳得快了。
他偏过身子来,也上了床。
长裤的布料从她脚面上滑过去。
她脚指头被刺激,蜷起来,下意识地、局促地只有个念头冒出来,去拿另一个枕头,拿另一个&hellip&hellip 黑胶唱片嗞嗞转动,里头人咿咿呀呀地唱起来,是这句:&ldquo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mdash&mdash&rdquo &ldquo听着没有?&rdquo他低声问,&ldquo三哥我&hellip&hellip好比是鱼儿吞了钩线。
央央,是不是?&rdquo 她觉得脑后硬,是顶在了墙壁上,眼见着他人过来。
湿热的触感,真实落到嘴唇上。
他不急不忙地将她嘴唇吃进去,一会儿含着、咬着,一会儿又小口小口地吮着。
这样湿漉漉的亲吻,像被他突然推下深海,失了重,无力地沉下&hellip&hellip 没了氧气,眼前都是水。
&ldquo小孩儿,外头&hellip&hellip&rdquo她推他。
&ldquo三哥有分寸。
&rdquo他笑,手在解自己衬衫领子的纽扣。
被单子是累赘,被她搅在身上、腿上,像多穿了一层衣裳。
他吻她,是在吃荔枝,去了壳,吮着水,将细白的果肉吃下去。
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吻人的法子。
七月的广州,裹多一层布料出汗太容易。
他的后背也很快湿了,汗浸透的衬衫布料,湿热着。
他说:&ldquo这样和我好,你就不能许别人了。
&rdquo 他又说:&ldquo许了别人,可不成样子。
&rdquo 他再笑:&ldquo你倒和三哥说说话。
&rdquo 清白的小姑娘经不得这样的调戏,面红着,等被他抱着,滚在床上,身子倒不像是她自己的了。
一个洗尽妆容呈素姿的心上人。
就算云雨不成,可黏腻在一块,两情相和,总有千般温存、万种疼惜的手段。
&hellip&hellip 最后清醒,是汗被他擦掉。
他下床去给她从楼下拿了热水来,让她润喉。
润了唇齿喉舌,他又低头去吃了会儿她的唇舌,蜜渍的杏,在两人舌上兜转着,最后还是他诱着她,喂给了他。
那黑胶唱片来来去去地听,七八分钟换个曲儿,听到尽头,没了声响。
&ldquo好香&hellip&hellip&rdquo她后知后觉闻到了,不会是被香熏过吧? &ldquo从楼下找的,点来试一试。
&rdquo他低声说,把玩她领口的纽子,额头压在她额头上,望着她的眼。
沈奚困了,想阖眼,可想着他总有话要说。
她这套衣裳的布料有暗纹,在昏暗的房间里变幻着,她动一下身子,那上头的花纹就换个样子。
他赏看了会儿,说:&ldquo有两句话,我说,你听着。
&rdquo &ldquo嗯。
&rdquo &ldquo你家人过去是做革命的,清朝虽亡了,但北洋一派和革命党是势不两立。
沈家也还有仇人在世,所以除了我和庆项,你不可对第三人说自己的身世。
&rdquo 她应了。
这个她懂,在纽约也始终守口如瓶。
&ldquo外头想要我命的人很多,把我们的事藏在心里,&rdquo他说,&ldquo三哥不想做你的催命符。
&rdquo 那天陈蔺观对傅侗文的唾弃,她还记得,船上那唱戏的男人,她也还记得,这并不是在唬她。
沈奚又点点头。
见他不说话了,她倒心慌慌的:&ldquo还有吗?&rdquo 他的手指,压到她眼皮上:&ldquo歇一歇,我定了黄包车,天黑前走。
&rdquo 沈奚抱住枕头,依着他,闭了眼。
天黑前,水退了不少。
傅侗文给老夫妇留了钱,是给屋子陌生的妇人和孩子的。
沈奚要走了,还在左右拽着床单,想拉平了,可又总觉有&ldquo可疑&rdquo的褶子。
这女孩子的纠结害羞落到傅侗文眼里,倒是可爱,在沈奚临出门时,把她换过的衣裳都丢在上头。
凌乱着,归还本来面目。
到码头上,天黑透了。
月在云雾里,很小,光也黯淡。
游轮的烟囱冒着滚滚黑色浓烟,从她这个角度,将月都吞没了,和儿时见过的一比较,完全是两种样子。
古人还是错了。
那明亮的,是在心里梦里的故乡。
管家看他们在开船前归来,很是庆幸,在用英文说着,他们还在担心着,倘若客人赶不回来,要将行李托送去哪里。
傅侗文没留过在广州的地址。
傅侗文被困在广州那间公寓,两个老夫妇没有看报的习惯,他也没见到国内的报纸。
上了船,草草冲洗干净,问管家要来了几份报纸,在私人走廊看起来。
久违的中文,每个字都不放过。
文人在报上大骂袁世凯,骂他&ldquo授卿令&rdquo的假仁假义,骂他祭天的狼子野心,一直骂到他和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ldquo二十一条&rdquo&hellip&hellip这&ldquo二十一条&rdquo披露在报上,条条触目,字字惊心,看得傅侗文心一阵地急跳,胸口又是闷得透不过气。
他在十三行的茶楼里也听了几句,没来得及深究,就被洪水冲乱了步伐。
如今条条框框,详尽地罗列下来,远超他的想象。
可笑的他,还在船上和杜邦公司的董事据理力争。
沈奚看着他的脸色变差,看着他烦躁地皱起眉,又不敢去夺他手里的报纸,频频求助去看谭庆项。
&ldquo好了,你洪水都逃得过去,别为几份报纸失了风度。
&rdquo谭庆项说。
傅侗文目光沉沉,自嘲笑着,沉默不语。
几份报纸带来的阴霾,直到旅程的最后一日,还弥漫在他们当中。
甲板上,沈奚将自己的皮箱子收拾妥当,准备跟着人流下船。
身旁是衣装笔挺的傅侗文,他脚边有三个皮箱子,一大两小。
稍后,船上的人会帮他运下船。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分别下船,分道扬镳。
傅侗文手里揉着一支烟,他已经将上海公寓的地址、钥匙,还有他的一封手写书信都交给了她:&ldquo三个月,我会安排人来接你。
&rdquo 离国这么久,去时和此时已是天翻地覆,他不能冒险带她在身边。
他当年费了力气救她,不是要她为自己涉险,是想要她有自己的新生。
细碎的、棕色的烟丝掉在甲板上、她和他的皮鞋上。
沈奚应了,喉咙口被什么堵着,不晓得再说什么。
傅侗文看一看怀表上的时间,又去瞅她。
分分秒秒,分别就在眼前。
钟表这个东西,把时间分得那样细碎,在你眼前,一秒秒地让你感知着流逝&hellip&hellip 这样的近,两个人的膝盖都挨到一处,却什么都没做,傅侗文将揉烂的香烟塞到长裤口袋里。
&ldquo假若三哥死了,会有法子让你知道。
&rdquo他说。
这是那天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人流涌动,沈奚费力地提起自己的皮箱子,带着她从美国带回来的书、衣服和私人购买的手术器械,挤入下船的旅客中。
她像一个普通的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穿着新潮的连衣裙和高跟鞋,走入下船的甬道。
走一步,心收紧一次,想回头,没顾得上,已经被人推搡着下了船。
[1]杨毓麟,字笃生,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1911年他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列强妄图分裂中国,悲愤交加,以致旧病复发,深感无以报国,将大部分的个人钱财交给黄兴作为革命资金后,在利物浦跳海自尽。
[2]1915年7月,广州遭遇两百年最大洪峰,称&ldquo乙卯水灾&rdquo,受灾人口378万。
广州有街头水浸4米。
7月13日,十三行在洪水中失火,焚毁商户2000家,死者上千,伤者不计。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爆款创业清蒸日华
- 不是你的朱砂痣[穿书]阮寐
- 我做偏执大佬未婚妻的日子白秋练
- 驭虫师肥皂有点滑
- 心悦臣服卓涵月
- 暴君每晚梦我五月锦
- 我的时光里,满满都是你(呆萌小萝莉:高冷男神太腹黑)忘记呼吸的猫
- 拜我,我让你发财向远飞
- 嫁给冷血男主后我变欧了[穿书]/嫁给杀器后我变欧了[穿书]蒸汽桃
- 三途志崔走召
- 纸片人老公成真了枝景
- 热搜女王育儿手记/每天都会上热搜!宋家小四
- 横滨芳心欺诈师闲豆花
- 身为卧底的我要成为港口Mafia首领了昭文
- 兔子必须死一梦黄粱
- 至尊剑皇半步沧桑
- 二号首长黄晓阳
- 炮灰的马甲又又又掉了冰糖火锅
- 痴傻蛇夫对我纠缠不休安曦
- 我见贵妃多妩媚鹊上心头
- 对的时间对的人顾西爵
- 重生之大画家轻侯
- 穿越种田文那些年(快穿)打字机N号
- 我一见你就笑郑三
- 和前男友在恋爱真人秀组cp后,我爆了煮熟的螃蟹
- 五年必死?修仙模拟器,开!善恶到头终有豹
- 朕乃天命大反派,开局怒斩重生女帝白灼青菜心
- 某某宗弟子修仙日常江上白
- 护法他做不到啊象八亿
- 手握剧本后,龙傲天竟成我小弟两只小蛙
- 冰临谷初岚迷泓
- 此去直上青云路卿岁岁
- 我,贾府孽障,但贾府也不当人爱吃毛豆炒青椒
- 三藏还俗孙九曰
- 聚宝乾坤碗凤九天
- 苟活乱世,从深山打猎到问鼎中原刀削面加蛋
- 让你当伴读书童,你替女少爷考上状元?二熊出没
- 带着现代军火系统闯大明静静的思考人生
- 大乾风云起苍穹云中飞蛾
- 无名剑主刘治宏
- 玄武:从零开始书二丫
- 历史风口,我率领军队统一全球书就
- 明朝的名义云玖龙
- 综武:堵门道观,开局截胡五绝甜御上弥
- 英烈传奇爱笑的花猫
- 大唐:我有一个武器库孤帆
- 状元一心打猎,皇帝三顾茅庐言者
- 大明朱棣:好圣孙,汝当为千古一帝!最喜纯爱大后宫的萌新
- 穿越之原始之路命运时
- 大宋枭雄仙庙的马尔高
- 冰临谷初岚迷泓
- 七窍欢Roxi
- 娘娘们别作妖,奴才要出手了肝火旺
- 死后宿敌给我烧了十年香余何适
- 史上最弱男主角我更在乎你
- 带着现代军火系统闯大明静静的思考人生
- 大楚武信君冷剑情
- 铜镜约金钩钓金鲤
- 明朝的名义云玖龙
- 综武从抓邀月开始虚无幻界
- 大宋枭雄仙庙的马尔高
- 神雕:龙女为后,贵妃黄蓉伊鲁卡老师
- 开局被捉奸,从小吏到权倾南北荒唐客
- 葬魂天刃西门冷血
- 灵气复苏:全民海克斯我与君同醉
- 玄德公,你的仁义能防弹吗?爱吃鱼2021
- 世子凶猛:谁敢和我抢女人?南朝陈
- 抱歉了小师弟,伤害男人的事我做不到!由山自海
- 孤鸿破苍穹星光入枫海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人在古代,从抢山神娇妻开始崛起女帝
- 诗泪洒江湖云里慕白
- 幸福生活从穿越开始男人苦咖啡
- 一剑独尊自摸一条
- 穿越古代我的空间有军火:请卸甲百万负翁不想再负
- 五年必死?修仙模拟器,开!善恶到头终有豹
- 娘娘们别作妖,奴才要出手了肝火旺
- 大唐:我李承乾,绝不被废崔山口
- 冰临谷初岚迷泓
- 无名剑主刘治宏
- 剑荡江湖快意恩仇每时每刻都很好
- 英烈传奇爱笑的花猫
- 混沌宝典之灵源诀踏月斩尘
- 大明朱棣:好圣孙,汝当为千古一帝!最喜纯爱大后宫的萌新
- 万化仙主,从捡漏废丹开始!子涛
- 替弟从戎成将军,全家跪求我原谅兜兜有米粒
- 开局逼我替兄参军,拒绝后打猎养妻!他也可怜
- 云起惊鸿客南城巷子
- 穿越后,我从厂仔变成王爷帅气周先森
- 大明辽国公空樱
- 乱世猛卒燕麦叶
- 从公爵之子到帝国皇帝老庄屋
- 我让高阳扶墙,高阳为我痴狂抱星明月居
- 北疆战神:从边军小卒到杀穿蛮族一心向龙
- 孤鸿破苍穹星光入枫海
- 平推三国,没人比我更快以空空
- 大明第一墙头草随轻风去
- 带着基地闯三国安安静静看书书
- 剑影书迷之宝藏寻踪喜欢半减七和弦的子豪
- 穿越古代我的空间有军火:请卸甲百万负翁不想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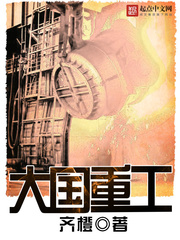



![豪门养女只想学习[穿书]](https://www.nothong.com/img/761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