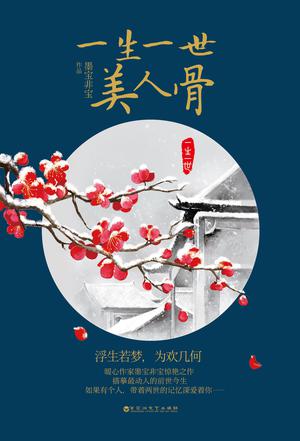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章 明月共潮生(1/3)
少顷,沈奚急匆匆携茶壶归来。
两个男人正拿着纸和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写满了法文和英文。
谭医生一直想回国后翻译出书,抽空就会要傅侗文和他讨论。
&ldquo看不懂了?&rdquo谭医生睨她,&ldquo我读书的时候,只会英文不行。
很多的资料都是法文的。
&rdquo &ldquo方才&hellip&hellip你说你教授研究的病患都是梗死。
&rdquo重点是这个&ldquo死&rdquo字,她倒热水时想到了,但凡看过的资料,病发了,大多逃不过死。
&ldquo原来是为这个跑回来。
我早和你说过,他目前身体状况稳定,不到你想的这么严重。
你啊,在心脏学上还是外行。
我只是担心他最后走到这步,&rdquo谭医生笑睨她,写下了一个英文单词,&ldquo他是这个。
其实就是少爷命,让着他、顺着他好了。
&rdquo 沈奚看了看,类似心痹。
此时,被讨论的傅侗文表示,他想喝茶。
沈奚双手将茶杯递给他,柔声说:&ldquo烫,你慢着些。
&rdquo 此话一出,她先窘。
真像是恨不得给他吹两口,吹凉了。
傅侗文和谭医生都笑了,前者无奈,后者打趣。
&ldquo说回前话吧。
&rdquo傅侗文替她打圆场。
&ldquo来,议议这个,&rdquo谭医生指报纸边沿写的英文,&ldquo心闷痛?心抽痛?窒息疼痛?&rdquo 傅侗文沉吟。
&ldquo《内经》有说过心痹&hellip&hellip有些中医书里也有说厥心痛,&rdquo沈奚建议,&ldquo暂译绞痛吧,绞痛这词我们也有,&lsquo当归芍药之止绞痛&rsquo。
&rdquo &ldquo好,就绞痛。
我翻译出书,用它,&rdquo他拍了拍傅侗文的手臂,&ldquo记住,你是心绞痛。
&rdquo 傅侗文不以为然,拿过来那张报纸:&ldquo此事刻不容缓,我们对于西学,还是要有自己的教育书本。
你回国不要再耽搁了,尽快着手做起来。
&rdquo 她附和:&ldquo我也可以帮你,谭先生。
&rdquo 谭医生气笑:&ldquo过去是一人指使我,如今倒好,成双了。
&rdquo 沈奚低头一笑,把玩起钢笔。
傅侗文又好似没听到,将茶杯搁下。
他单手握着报纸,去读印刷的文字。
一月的《每日邮报》,全是过时的旧新闻。
去年耶稣诞节,西部战线一部分德军、英军和法军为了这伟大的节日,短暂停止互相射击,还举行了一场战地球赛。
傅侗文几眼扫完:&ldquo这场球赛谁赢了?&rdquo 谭医生扯过报纸,也翻看:&ldquo没写吗?&rdquo &ldquo英国赢了,&rdquo沈奚说,&ldquo另一张报纸有写。
&rdquo &ldquo细想下去,谁赢都一样。
&rdquo他又说。
战场残酷,到最后踢球的人都活不下来。
傅侗文将报纸叠好,留在手边。
他人离开这里:&ldquo我去谈个小生意。
&rdquo 在这游轮上,能谈什么生意?沈奚猜想了一个上午。
当天下午谜底揭晓。
他们的私人甲板上多了一个狙击手,是傅侗文在船上问那些商人们借买来的。
那个人身材矮小,也不与他们交谈,每每从她面前经过,她总能留意到这个狙击手脚上漆黑锃亮的靴子,是警靴。
他也喜欢抽烟,就是不讲究,喜欢将烟头在靴底踩扁,每回都是服务生或是临时管家将烟头收走。
就此,他们多了位临时旅伴。
在这晚入睡前,沈奚做足了准备。
谭医生说过,傅侗文的作息很规律,于是她决定要在他熟睡后再上床。
为不露声色,她还将谭医生的书全都搬到了套房里。
钟表极缓慢地一分分跳动,指向九点。
她翻着书,留意到他在洗手间,用纯白的毛巾擦着手。
她的手,撑在耳后,小拇指无意识地绕着自己的头发,快去睡吧,快去睡。
傅侗文的皮鞋经过,略停顿,没进卧室,却走向她。
&ldquo是不是庆项和你说,我每晚九点会准时躺到床上,所以你准备了这些书?&rdquo他将那页书替她翻过去,&ldquo说来听听,准备几点睡?&rdquo &ldquo我读书时习惯了,&rdquo沈奚仰头看他,十足十的诚恳,&ldquo有时一抬眼,就是天亮。
&rdquo 傅侗文替她合上书。
沈奚画蛇添足地解释:&ldquo我在说真的。
&rdquo 他笑:&ldquo总看专业书也无趣,我带了本《仁学》,想看吗?&rdquo 谭嗣同的著作,是禁书。
她意外:&ldquo我听顾义仁说过,是出了日文版,难道还有汉字的?&rdquo &ldquo我让人私下印的。
&rdquo他做了解释。
如此珍品,自然是要看的。
傅侗文在衣柜下层翻出了那本书,丢去床上:&ldquo上床来看。
&rdquo 沈奚听到这句,方才醒悟,他在用这个打破两人之间若有似无的暖昧。
总要有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让她上床去,否则,怕她真会挨到天明&hellip&hellip 她在洗手间里磨蹭了十几分钟,再出来,吊灯都灭了。
两盏壁灯,一左一右,悬在床头上。
傅侗文还是穿着衬衫,倚在那里,在看书。
刚登船收拾衣裳的时候,她看到他是带了睡衣的,可今晚仍是穿着衬衫。
不过,她又何尝不是怕误会,完全不敢换上睡衣,只挑了夏日最轻薄的连衣裙充数。
沈奚也上床,盖了被子,将《仁学》拿在手里。
果然没有印刷厂的名号,是私印的。
书是好书。
可她的念头,一溜到了天外。
此时的傅侗文,是一种酒阑人散的慵懒。
她在想,他在伦敦念书时,是否也这般神情和态度,闲阶独倚梧桐。
想了会儿,默念了几句荒废,勉强静心读了进去。
傅侗文这边,恰好翻看完最后一页,合了书。
穿衬衫睡觉是一桩苦事,身体和手臂都被一层板正的薄布绑缚,活动不开。
他人乏,书也翻完了,于是无所事事地靠在那儿,观赏起了她。
她今夜穿的是丝绒的连身裙子,细白的一截手臂露在外头,没有任何装饰品,和船上的那些贵族小姐、商人太太一比,太过朴素。
倒是耳垂上坠着两粒小小的珍珠,赝品,但挺漂亮。
傅侗文难得对女孩子用&ldquo漂亮&rdquo这两个字,嘴上没提过,心里也大多不屑。
还是缎面的发带,颜色不同,斜扣着的珍珠也是赝品。
看来她将所有钱都用在了学业上。
傅侗文将书搁在床头,关上壁灯,宣告结束夜读会。
她从光明处,望向暗处的他:&ldquo你看完了?&rdquo &ldquo也不用都在今天看完。
&rdquo 也是。
她又问:&ldquo要让我检查一下再睡吗?&rdquo &ldquo我很好。
&rdquo他回。
片刻的沉默。
两人又都笑了,傅侗文说:&ldquo好了,躺下。
&rdquo 沈奚缩进了棉被里。
傅侗文笑着摇摇头,下了床。
他趿拉着拖鞋从床尾绕过去,走到她那一侧的床畔,关掉了灯。
在黑暗中,她看到他是换了睡衣的长裤的,光着脚。
&hellip&hellip 那日起,连着十几个夜晚,她都被梦魇压身。
梦中,那个男人来索命,说他有万千错,也轮不到她来杀。
沈奚每到噩梦都呼吸急促,辗转难安。
傅侗文总是耐心地隔着棉被将她抱起来,在她半梦半醒里,轻声和她说别的话,将她从深渊拉回现实。
有一夜,她在黑暗中听他说,他和船上的厨子讨论一品锅,人家不晓得,倒是认得炒杂烩,李鸿章访美时带过去的美食,在美国风靡了好一阵子。
&ldquo想吃的话,三哥明日让人给你做。
&rdquo他俯身,将她乌黑的长发捋到枕边去。
发丝柔软,在他手指上打了结。
这回他没有硬拽,多了解扣的耐心,没扯断她的头发。
这夜后,她终于不再做同一个噩梦。
如此,他们的旅程算真正开始了。
早晨,傅侗文会比她起早半个钟头,每回都以拉开窗帘的方式,叫醒她。
白日他们会在私人甲板闲聊,这两位男士见多识广,从不让她冷场,从战争到商业,再到医学,还有傅侗文所学的哲学,最后落到莎士比亚歌剧和宗教问题上。
只是顾及安全,她的活动范围很小。
晚上两人也有了&ldquo夜读&rdquo的共识,都倚在床头,各自翻书,间或交谈两句,声音也都放得很低。
和他同住久了,她会留意到傅侗文在私底下是个随便惯了的人,开门出去,是个翩翩公子哥,一扇门闭合,屋子里的却是个不修边幅的读书人。
起初大家还顾着礼,慢慢地,他也放松下来。
他会两三日不剃胡须,让人将饭送入房内,不出门见人,就不收拾自己。
一回她回房,看到他穿着衬衫、长裤,光着脚,单手撑在桌上,身子倚靠着,在看一叠纸,上头是他自己前几日才写的东西。
她看他那一刻,他抚乱自己的短发,语气自嘲地笑:&ldquo看我做什么?&rdquo 随即,手稿被丢入垃圾桶,毫不留恋。
一个月过去。
沈奚在外人眼里,始终是个旧时代的太太,寸步不离傅侗文。
傅侗文待她也是极尽体贴,她常在早晨醒来,悄悄地将他的枕头拉过来,脸压在上面,想,他们这样和夫妻好像真没什么差别。
某晚,她下床喝水,看到侧卧的他在睡梦中,迷糊着,去将自己衣裳解开。
解到第四粒纽扣时,被绊住,微蹙眉。
沈奚悄然地蹲在他身前,伸出两手去,想帮他,可触及到纽扣又不敢了。
哪怕给自己灌输&ldquo这是在照顾病人&rdquo,也难以再进前一步。
他的锁骨和脖颈,还有大半的皮肤裸露着在眼前,让她不敢再看下去。
她怕他受凉,替他拉高被角,掩上那风光旖旎。
这晚,她睡得极不踏实。
一念想他被衬衫束缚着难过,一念又想他是否要受凉。
清晨六点,傅侗文撑着手臂起来,懒散地倚在床头,发现她醒着,偏过头问她:&ldquo没睡好?&rdquo整晚没开过的嗓子,沙沙的,磨过她的耳和心。
她带着鼻音&ldquo嗯&rdquo了声,将棉被遮住了半张脸,闭眼不看他。
傅侗文只当是女孩子起床的脾气大,笑笑,推开棉被,趿拉着拖鞋去了洗手间。
他再出来,见到沈奚趴在棉被上,将两人的枕头垫在手臂下,看外头的天。
&ldquo三哥你看,外头又下过雨了。
&rdquo 海上是一片云一场雨,云过,雨过。
每天不晓得要来几场才算完。
她这是没话找话。
傅侗文慢条斯理地绕到她身后:&ldquo我换衣裳。
&rdquo &ldquo嗯。
&rdquo她答应着。
傅侗文将衣服脱下来,背对着她,背脊皮肤光滑紧实,在晨光里有柔和的光泽。
沈奚听到衣裳被丢去椅子上,又听到从衣柜取出衣裳的声响。
她懊恼地将脸埋在枕头里。
听力忽然这么好,是要了人命。
傅侗文将长裤套上,也在看她。
这位小姐完全不清楚她在占用他枕头的同时,并没有将她的身体隐藏好,两条小腿都露在外面,沉在雪白的棉被里。
他知道,自己从这个角度去欣赏她很不道德,也不绅士。
和一个没名没分的女孩子共处一室这么久,又是同床,是形势所迫,也是权宜之计。
可惜,人心是无法掌控的,包括他自己的。
&ldquo想不想去公共甲板?&rdquo他突然提议,&ldquo那里视野好。
&rdquo &ldquo可以去吗?&rdquo沈奚惊喜回头。
傅侗文还光着上半身,手里拎着衬衫。
她怔住。
他无事一般,在安静中进行他的穿衣步骤。
沈奚出溜下床,抱起枕边准备好的长裙:&ldquo我去洗手间换,你接着穿。
&rdquo跑入洗手间,她还在尽责地医嘱,&ldquo穿多些,有风雨。
&rdquo 一扇门,隔开两个人。
洗手间里有小小的窗子,她将两手撑在上头,看海,脑海里都是他。
她想到,在纽约留学生里也能被分出两派来:一派是惯性保守的,但也会热情洋溢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派直接了许多,为了摆脱掉落后、死板、保守的东方人的帽子,从肢体到语言,都会大胆表达感情。
到大学还没有性爱经历会让一个西方女孩子很沮丧,尤其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女孩子,她们会认为自己没有魅力,才没能享受到愉悦的性爱。
许多人也会讲述,在家里和仆人、司机,或者是和没有婚约的男人之间的种种。
这些也感染到了开放派的留学生。
沈奚虽然是医学生,对身体结构并不陌生,可心理上还是偏保守的。
她自认是保守派。
刚刚他只是穿好了长裤,全被她看干净了。
他的坦然倒显得她才像个登徒子。
沈奚懊恼不已,应该更镇定,不该用逃离姿态,要泰然处之,像个医生&hellip&hellip又不是没见过尸体&hellip&hellip等她换好丝绒长裙,离开洗手间,傅侗文已经不在了。
她走到梳妆台前,挑选耳饰,发现,多了一副新的珍珠耳坠和一条项链。
不是赝品,是纯天然的金色珍珠。
并不全因为这从天而至的礼物,还有许多,关于他的所有,都在渗入她的血液,流到心深处。
她只剩了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休说是去法兰西定居,就算让她去德意志称帝,她也绝不会受到诱惑,离开中国。
沈奚收好梳妆台上的东西,还是戴了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只是发带换了个新的样子。
房间外,傅侗文在走廊上等着她。
见她出来,他没问她关于珍珠的事,她也没提。
两人走到公共甲板时,风很大。
露天的地方,都是积水。
沈奚上去前,将脚腕上的裙角打了个结,用这个简单的法子让长裙短了三四寸,避免沾到积水。
她直起腰,留意到狙击手在角落里,注视着他们。
她悄声问:&ldquo花了不少钱请他吧?&rdquo如此尽忠职守。
傅侗文两手斜插在长裤口袋里,给狙击手打了个眼色,让他离远些:&ldquo他和雇主在路上起过冲突,我去问,才让给我。
所以花费并不高,毕竟船已经离岸,他需要在海上找到工作。
&rdquo 海风骤起。
沈奚按住自己发上的缎带,傅侗文走向海浪的方向:&ldquo带你看一看大西洋。
&rdquo 风把他的话吹散。
遥远的海平线上掀起了一道可见的大浪,暴风雨要来了。
水手们在甲板的四周忙碌着,在做完全的准备,狙击手在角落里张望四周,谭医生靠在避雨的地方,在抽烟。
所有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只有他们在甲板尽头,无所事事地站着。
乌云压顶,一道闪电劈过铅灰色的天空。
沈奚仰头:&ldquo在这里会被雷劈到吗?&rdquo &ldquo说不准,&rdquo他将右手递给她,&ldquo要不要试试,一死两命,也算是佳话。
&rdquo 人体导电吗?她当他是玩笑,可当真握上去,却只余肌肤摩擦而过的心悸,从指间滑到掌心,每一寸都是。
两人的手最终交握在一起。
&ldquo胆量还不小。
&rdquo傅侗文笑着说。
风将海水抛到半空,如烟火般炸开,像细碎的沙,洋洋洒洒地落了她满身。
她余光里尽是他的影子。
傅侗文,傅三爷,三爷,三哥&hellip&hellip侗文。
侗文。
接连两道厉闪,撕开云层。
傅侗文将西装脱下,披到了她单薄的肩上。
也由此放开了她。
另一端甲板上的吵闹声渐起,有船员落水。
约莫十分钟的样子,救人的和落水的都被拉上来,落水的那个昏迷不醒,被平放在甲板上抢救。
有人过来,劝说他们退回去,去避雨的半露天休息室。
风太大了。
两人回到避风雨的地方。
傅侗文竟去和谭医生要纸烟,谭医生听到他的要求,满面错愕。
不过他接了烟,捏着纸烟卷在金属栏杆上磕着,烟丝落到谭医生鞋上。
谭医生恼火:&ldquo你这人,真是糟蹋东西的好手。
&rdquo &ldquo记账上,全赔你。
&rdquo傅侗文将揉烂的烟,塞回到原主人手里。
谭庆项想到刚刚看到两人在牵手,可又疑心是自己错看了,犹豫着还是没问。
&ldquo我去更衣室。
&rdquo沈奚委婉地说。
傅侗文应了,随她离开。
公共甲板对全船开放,里外两道门,里边那道门里是洗手间。
外边这里算是半个休息室,也是真正的更衣室。
她在洗手间里听到两个褐发的女孩子在说,昨天靠岸时,见到特等舱的管家去替贵客们采办新鲜牛奶和水果。
&ldquo一等舱也有的。
&rdquo其一小声说。
&ldquo亲爱的,不如这样,你看旅途漫漫,我们总要找到一个可人的男孩子谈场恋爱,&rdquo两人低声笑着,&ldquo我要一个月才到,你呢?&rdquo&ldquo下一次靠岸,他们是这么说的。
&rdquo 沈奚在她们的谈笑中,听她们说干脆去一等舱找一位先生同住,莫名冒出了谭庆项的脸。
她被自己的想法逗笑,离开洗手间。
更衣室是一条狭长的走廊,几个隔间的门都敞开着,沈奚没看到傅侗文。
她想,他应该在更远的地方,于是挑了个隔间进去,对着半身的古铜镜子端详自己的脸和头发。
她两手捧着自己的脸,盯着眼下的一道乌青时,听到隔壁房间的门上了锁,很快,伦敦口音的英文出现&hellip&hellip不对,重点不是口音,而是内容。
&ldquo亲爱的,我爱你,不要怕。
&rdquo这是女人的声音。
&ldquo对不起,亲爱的,我弄疼你了,&rdquo男人的回应,有着介于男生和男人之间的羞涩,&ldquo我没有真的实践过。
在伊顿公学时,我在我的姑妈那里住过,她的贴身女仆很喜欢我,可我们也并没有真的做什么&hellip&hellip&rdquo 沈奚约莫猜到是什么内容,她想要悄然离开。
镜子里,出现了傅侗文的身影,他手里拎着买来的新纸烟,来接她。
沈奚在看到他的一霎,猜到他会开口,两步上前,手压到他鼻梁下,挡住嘴。
傅侗文惊讶地垂眼,她握住他拿烟的手,脸红地摇头。
&ldquo我只摸过她的前胸&hellip&hellip&rdquo男人的声音传过来。
&hellip&hellip这位伊顿公学的贵族青年,请你不要再叙述你和女仆之间的性启蒙了。
沈奚面红耳赤,祈祷着傅侗文能领会她的意思,两人可以在不打扰这对幽会情人的情况下,体面地离开。
可是当隔壁陷入安静,她却感觉到自己的手贴着的位置,是他的嘴唇,他鼻端呼吸的热量也落在她的手背上。
他平稳的呼吸节奏,比那一对小情人的对话让她更无法承受。
无声地,傅侗文将烟盒放到了铜镜前,这样空出了手去扶着她的腰,另一手去拉门的扶手。
他给他们的更衣室也上了锁。
沈奚的手从他脸上缓缓滑下,无处可放,虚握成拳,空悬在两人之间。
他的银色领带,被一根珍珠别针固定着,黄金色的珍珠。
乍一看,和她的那副耳坠、项链像是一套。
隔壁男人在说:&ldquo当然,她也对我做了一些事,比如像你现在这样,抚摸我,她很热情&hellip&hellip&rdquo 为什么西方人会这么喜欢说出来,只去做就好了啊。
哎,很好,没有声音了。
哎?不是停止,是在实践。
男人在低低地说着爱你,呼吸粗重,女人没有发出声响,看来,还是无法突破第一次的阻碍,选择的是另一种方式。
沈奚开始自责,不该听婉风和那些英国女孩的经验分享,此类知识获取太多了。
时间漫长,漫长到她开始自问,为什么要等?刚刚直接离开岂不是更好?&hellip&hellip 可等到现在,那边随时会落幕,又不好走。
这里的更衣室没有窗,一面镜子一面门,余下两面墙壁上都是五彩玻璃。
玻璃后是灯,光从玻璃透出,落在人脸上,让人目眩。
这个更衣室比他们房里的衣橱还小,就算两人不贴在一处,也分隔不开。
傅侗文的手变得烫人,她的头脑也开始发昏&hellip&hellip 沈奚想推他的胸口,想将身子离开他,可想到最后也没付诸实行。
傅侗文的右手仍是搭在那里,握着她的腰。
慢慢地,他的手挪后、挪高了一些,换了一种更亲密的,情人间搂腰的姿势,也更自然了。
那头小剧场落了幕。
隔壁门打开,人走出去,女人低声用英语惊讶地说着,竟会有狙击手在门外。
难道这里还有别人吗?两个人脚步匆匆,远去,将他们这两个被迫的听客留在这里。
困在这里,困在他们留下的氛围里。
&ldquo三哥&hellip&hellip&rdquo 她想说,我们也走好不好,谭医生等久了也不好,你看,狙击手也等在外头。
不晓得的还以为根本是你我两个挤在这里,排解长途航行的苦闷&hellip&hellip &ldquo方才,只当是游园惊梦,不要放在心上。
&rdquo他说。
沈奚脑子嗡的一声。
她只晓得《游园惊梦》这曲子明明是个小姐遇见俏书生的无边春梦,还记得那唱词里有:和你把领扣儿松,衣带宽&hellip&hellip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hellip&hellip 傅侗文先笑了:&ldquo也不太恰当,当我没有说过。
一会儿出去,庆项问起去了何处,就说我们提前去了珠宝酒会,那里对头等舱贵宾提前开放。
&rdquo 她轻声应了。
他却并未放开她。
在这游轮上,傅侗文像在坐牢服刑。
因为英德的战争,从二月起国内的联系就断了,海上航行这么久,靠了岸,足足六个月的消息空白,他忧心国内又会是何局面。
忧心无用,徒增烦恼,只能等,等到岸。
海上的日子是他这些年最清闲的时候,能看书,也能好好坐下喝口茶,闲谈两句。
人和人之间讲的还是因缘。
放在过去,他绝没心思去干这种事,现在&hellip&hellip 他们是被狙击手的叩门打断的,门外的人用蹩脚的英文说,甲板上出了事,见了血。
沈奚仓促离开他,傅侗文开了锁。
她跟他走出去时,脸上有着不自然的红晕。
狙击手见怪不怪,对他来说,就算两人当着他的面干什么,他也能背对着他们,为他们站岗。
更何况,只是在更衣室内消遣一下而已。
他建议傅侗文尽快带沈奚回头等舱,不要再去公共甲板:&ldquo落水的水手醒过来,怀疑有人推他下船,内部起了争执。
刀扎腹部,三个人大出血。
&rdquo这里并不安全。
谭庆项也寻了来:&ldquo对,你们快上去。
&rdquo 十米外的休息室,正有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入,也有人出来,满手的血。
&ldquo好好的,干什么怀疑人推他?&rdquo沈奚奇怪。
&ld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不是你的朱砂痣[穿书]阮寐
- 重生后我撩我自己冷冻玻璃渣
- 横滨有座万事屋拌葱白菜
- 人间正道周梅森
- 神明的金丝雀Sonata
- 我做偏执大佬未婚妻的日子白秋练
- 爱与他梦筱二
- 与你沉沦[娱乐圈]一夜从灯
- 穿到七零当厂花唐柒鱼
- 三途志崔走召
- 同萌会的一己之见楚凤华
- 炮灰请睁眼[快穿]少说废话
- 百炼成神(不灭武神)恩赐解脱
- 横滨芳心欺诈师闲豆花
- 后宫·如懿传1流潋紫
- 定风波来风至
- 蝼蚁你爸爸
- 二号首长黄晓阳
- 彩虹星球南书百城
- 炮灰的马甲又又又掉了冰糖火锅
- 全民皆萌宠暖暖的茶
- 痴傻蛇夫对我纠缠不休安曦
- 玉昭词(今夕何夕原著小说)时久
- 我家别墅能穿越传山
- 女配求生日常[穿书]陆灵儿
- 葬魂天刃西门冷血
- 开局被捉奸,从小吏到权倾南北荒唐客
- 铁骑红颜:大秦霸业乖巧的松鼠
- 踏雪寻青梅云笺寄晚
- 从天龙活到现代的武林神话歌尘浪世
- 替弟为质三年,归来要我让战功?芳龄真的二十
- 奉旨当里长:百姓的明义南明蓠惑
- 温阮霍寒年温阮霍寒年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我让高阳扶墙,高阳为我痴狂抱星明月居
- 武林风云之九阳传奇息烽客
- 世子凶猛:谁敢和我抢女人?南朝陈
- 星极宇宙社恐的中年人
- 我在北宋教数学吉川
- 诸天帝皇召唤系统遗落的影子
- 逆仙未朗
- 用户90391439的新书:悟用户90391439
- 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青岳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一剑独尊自摸一条
- 带着基地闯三国安安静静看书书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大宋第一猎户:女帝别低头!一起抓水母
- 系统带我闯武侠汴梁的夏大夫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同穿:举国随我开发异世界沈见新
- 重生之我是大明皇太孙朱雄英码奴翻身
- 纵横诸天:从修炼辟邪剑法开始不吃鱼虾的猫咪
- 绝品仙尊潇然
- 从天龙活到现代的武林神话歌尘浪世
- 两界:玻璃杯换美女,买一送一宁衰人
- 踏雪寻青梅云笺寄晚
- 新科状元的搞笑重生路2二月沫
- 穿越东齐,从匪窝杀奔庙堂我是踏脚石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南岳清水湾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大宋:朕的专利战横扫1126心有灵犀的金毛狮王
- 大明中兴之我是崇祯三千纸
- 物流之王之再续前缘笔尖路悠然
- 开局力挺宁中则,李青萝求放过粤北陈老师
- 秦世风云录饺子面条火锅
- 七情碗夜凰
- 道术达人虫梦
- 洪荒之亘古大道审判者
- 傲神传蚂蚁
- 苦闯仙侠界云隐青山
- 仙道长青林泉隐士
- 丹武大帝关东大侠
- 五鼎封天古道行者
- 大宋枭雄仙庙的马尔高
- 大明辽国公空樱
- 陌上!乔家那位病公子百越春秋
- 我超有钱睡芒
- 开局被捉奸,从小吏到权倾南北荒唐客
- 从公爵之子到帝国皇帝老庄屋
- 大秦血衣侯:我以杀敌夺长生鎏金淬火
- 孤鸿破苍穹星光入枫海
- 用户90391439的新书:悟用户90391439
- 大宋:朕的专利战横扫1126心有灵犀的金毛狮王
- 大宋第一猎户:女帝别低头!一起抓水母
- 我,大楚最狂太子蜗牛王子
- 修仙家族:我的灵肥引情劫幽冥人
- 穿越战国我靠杀敌称霸天下王权荣耀
- 穿越商朝,为了人族而战叫不醒的清醒着
- 天赐良臣爱吃炝炒丝瓜的胡掌柜
- 大明权谋录Four古往今来
- 我的春夏秋冬:人生全记高山流水兮
- 纯阳第一掌教池宁羽
- 拜见教主大人封七月
- 苦闯仙侠界云隐青山
- 天神之血天明
- 仙帝铁马金戈
- 上山为匪彗星撞飞机
- 战傲穹苍半世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