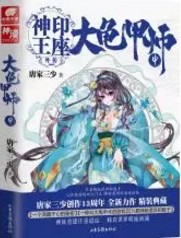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7(1/3)
1946年1月18日 两年来第一次和莫里斯在一块儿吃午饭——我打了电话请他见我。
我坐的公共汽车在斯托克韦尔塞了车,结果我迟到了十分钟。
有一会儿,我又有了往日里总会有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害怕会出点什么事情,把这一天给弄糟,害怕他会对我发火。
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自己先发火的欲望。
发火的习性似乎同我身上许多其他的东西一样,已经死去了。
我想见到他,问问他亨利的事情。
亨利近来表现反常。
他同莫里斯一块儿外出去酒馆喝酒,这事很奇怪。
他平常只在家中或者自己加入的俱乐部里喝酒。
我想他或许和莫里斯谈过。
如果他是在为我而担心,那可真怪了。
自打我们结婚以来,再也没有什么比现在更不用担心的时候了。
不过我同莫里斯待在一起时,同他待在一起的理由似乎就是要同他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别的理由。
而对于同亨利待在一起的理由我却始终也没能搞清楚。
他不时地试图让我感到难受,并且他成功了,因为他是在让自己难受,而我看着他让自己难受就会真的受不了。
我和莫里斯吃午饭,是不是破坏了自己当时发下的那个誓言呢?一年前我会这么想,但现在不会。
那时候我很刻板,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因为我对爱情没有信心。
我们在鲁尔斯吃了午饭。
只要同他在一起,我就感到高兴。
只有一小会儿我不高兴。
在那个阴沟盖上道别时,我觉得他想再吻我。
我渴望他的吻,但当时我突然咳嗽起来,结果时机就过去了。
我知道,他走开时心里一定在想着种种不真实的东西,并因为这些东西而感到难受,而我则因为他感到难受了,自己也很难受。
我想背着人哭一场,于是便去了国家美术馆,但那天是一周里向学生开放的日子——人太多,所以我又回到了仕女巷,走进那座光线总是太暗,让你看不清邻座的教堂。
我在里面坐下来。
教堂里除了我和一个走进来在后面一排长椅上默默祷告的小个子男人外空空荡荡。
我记得头一回进这种教堂时,自己曾经多么地讨厌它。
我没有祷告。
我已经因为祷告太多次而吃够苦头了。
我像对父亲——如果我能记得自己有过父亲的话——说话那样对天主说道:亲爱的主啊,我累了。
1946年2月3日 今天看到了莫里斯,但他没看见我。
他正在去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的路上,我跟在他身后。
我已经在雪松路上花了一小时——冗长乏味的一小时——试图听懂可怜的理查德所说的那些道理,但从中得到的却是一种信仰颠倒的感觉。
难道有谁能对一个传说如此当真,并为它而如此争论不休吗?当我真的听懂什么的时候,那东西总是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事实,而在我看来,那个事实又几乎总是无助于证明他有道理,比如说像表明基督确有其人的证据之类。
我疲惫而又绝望地从他那里走出来。
我上他那儿去,为的是想请他帮我摆脱一种迷信,但每次我去时,他的狂热都使我的迷信更加根深蒂固。
我在帮助他,但他并没在帮助我。
或许也可能他是在帮助我?有一个小时的光景,我几乎没去想莫里斯,可是后来他突然出现了,正在街尽头的地方过马路。
我一路尾随着他,不让他离开视线。
我们一起去过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这么多次,我知道他会去哪个吧台,要点什么。
我在想:我是不是该跟在他身后进去,自己要一份东西,看着他转过身来,然后等待着一切重新开始呢?那样一来,早晨就会充满希望,因为亨利一走,我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而傍晚也堪可期待,如果亨利提前告诉我说他要晚点回家的话。
而且现在我可能会离开亨利。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没有钱能带给莫里斯,而他写书所挣的钱除了养活他自己外也剩不下多少,但是有我的帮助,光是打打字,我们一年也该能攒下个五十镑来。
我不怕穷。
有时候量入为出比胡乱开支、自作自受更容易。
我站在那家酒馆门口,看着他走进了酒吧。
我对天主说:如果他转身看到我,我就进去,但他并没有转过身子。
我开始往家走,但脑子里无法做到不去想他。
我俩之间形同陌路差不多已有两年时间。
我不知道一天里某个具体的时刻他都在做些什么,可现在他已不再是陌路人了,因为我像以往一样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他会再喝上一杯啤酒,然后回到那间熟悉的屋子里去写作。
他每天的习惯一如既往,我爱它们,就像一个人爱一件旧衣服一样。
我觉得自己被他的这些习惯保护着。
我从来也不想要新奇怪异的东西。
我想:我会让他多么快乐呵,而且我是多么容易地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重新开始渴望看到他快乐地大笑。
亨利不在家。
他同人约好了中午下班后一起吃午饭,他又打电话回来,说晚上要到七点钟才能到家。
我会等到六点半,然后我就给莫里斯打电话。
我会说:我今天晚上和从今以后的每一天晚上都会去你那儿。
对没有你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
我要收拾东西,把它们装到那只蓝色的大衣箱和那只棕色的小提箱里。
我要带上足够度一个月假期穿的衣服。
亨利是个文雅的人,到一个月末了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情就会办妥,当下的怨恨会过去,家里需要的其他东西我可以慢慢来拿。
怨恨不会很多:我们两人并非好像还是一对情侣似的,婚姻早已变成了友谊。
稍稍过上一段时间后,友谊会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
我顿时有了一种解脱和快乐的感觉。
我再也不去担心你了,穿过公共草坪时我这么对天主说,不管你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不管你是否会再给莫里斯第二次机会,也不管这一切是否都是我的凭空想象。
也许这是我为他要求的第二次机会。
我要让他快乐,这是我的第二个誓言,天主,你要是能够阻止我的话就阻止我,你要是能够阻止我的话就阻止我。
我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给亨利写信。
“心爱的亨利……”我写道,但这听上去很虚伪。
“最亲爱的”则是一句谎言,所以得用一个像是称呼熟人用的称呼:“亲爱的亨利……”于是我这样写道:“亲爱的亨利,恐怕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爱着莫里斯·本德里克斯。
我们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但是没有用。
没有他我无法快乐地生活,所以我走了。
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没有怎么尽到一个做妻子的本分,而且自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后,我也完全没有能做一个情人,所以我周围的每个人过得都不好。
我一度以为自己可以让这份恋情就这么维系着,相信它会慢慢地、以大家都满意的方式结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
我比一九三九年时更爱莫里斯。
我想自己一直太过幼稚,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一个人迟早要作出选择,不然就会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弄糟。
再见了,天主保佑你。
”我重重地划掉了“天主保佑你”这一句,让它看不出来。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自以为是的味道,说到底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我的师尊遍布修真界/全修真界为我火葬场薄夭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夜行歌紫微流年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失忆后我招惹了前夫萝卜兔子
- 仙尊一失忆就变戏精哈哈儿
- 史上第一祖师爷八月飞鹰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穿成废材后他撩到了暴躁师兄是非非啊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纨绔心很累七杯酒
- 剑海鹰扬司马翎
- 武极宗师风消逝
- 大风刮来的男朋友烟火人家
- 你们练武我种田哎哟啊
- 女主是被大佬们氪大的糖丸丸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夏日长贺新郎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离婚后我和他成了国民cp禾九九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夏日长贺新郎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阻流三眠柳
- 离心ABO林光曦
- 恶魔总监:亿万独宠小男友浔弦
- 新婚ABO白鹿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他们今天也没离婚廿乱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和校草联姻之后芝芝猫猫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听说我很穷[娱乐圈]苏景闲
- 被影帝碰瓷后[娱乐圈]唤舟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不息阿阮有酒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游弋的鱼乌筝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循规是笙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替身夺情真心
- 动物爱人魏丛良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国色天香南风歌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有只海豚想撩我焦糖冬瓜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