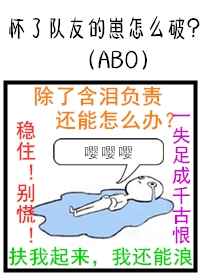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十二章 彼岸(2/3)
你这么久,你终于肯来了!&rdquo &ldquo海潮儿,他不是&hellip&hellip&rdquo 凌郁不理会。
她亲吻那只手,热切呼唤着:&ldquo大哥,大哥!&rdquo 这呼唤亘古绵长而又撕心裂肺,泪水落在手背上,充满了灼人的力量。
龙益山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开口道:&ldquo凌&hellip&hellip慕容姑娘,是我。
&rdquo 凌郁迟疑地张开双眼。
水雾中升起龙益山黝黑的面庞。
这面庞熟悉而又陌生,眉目之间隐匿着慕容旷的神情。
她情不自禁伸手去摸他浓密打结的眉心:&ldquo大哥,你眼里面,怎么有这么多悲伤?&rdquo 龙益山把头微微一偏:&ldquo你认错人了,我不是阿旷。
&rdquo 凌郁心中充溢的悲伤&ldquo轰&rdquo地炸开。
幻象打破,灰飞烟灭,她再也无法欺骗自己。
&ldquo益山兄&hellip&hellip&rdquo她终于认出龙益山:&ldquo你来了,就好像是大哥他来了。
&rdquo &ldquo阿旷他再也来不了了,他已经不在了。
&rdquo龙益山把牙根咬得咯咯作响。
凌郁抽冷子似地缩回手来,良久方道:&ldquo他们都假装不怨我,强作欢颜,就好像已然忘了大哥是怎么死的一样。
益山兄,我还是情愿见你这样。
你从来不假装,我从你眼睛里就看得见我自己。
我宁肯你这么恨我,也不愿看你伪装的宽恕。
&rdquo 龙益山如何不怨恨凌郁,他最亲爱的两个人相继惨死,都要归咎于这个狠心的女子。
他狠狠道:&ldquo你如何下得了手?&rdquo 凌郁脸色煞白,怔怔望着龙益山。
她恍惚觉得龙益山是上苍派来给她最终审判的天神,他紧闭的口中就含着一纸判词。
徐晖深恐龙益山出言过重,刚欲劝止,却听他低声道:&ldquo那时候我们俩在茶园给静眉守灵。
阿旷说是你害死了静眉,我急了眼立时便要去找你。
他死命拦住我,求我放过你。
他说他永远不再见你了。
可那些日子他心烦意乱,魂不守舍。
我瞧得出来,他是在跟他自个儿打架。
后来他还是上姑苏找你去了。
他待你,就如同待他自己,无论你做什么,他都没法子怨怪你。
&rdquo &ldquo可他再不到我的梦里来了,他再不回来了。
&rdquo凌郁怔怔落下泪来。
&ldquo那他是不愿见你现下这样。
&rdquo &ldquo什么样?&rdquo 龙益山一时语塞,沉默半晌方道:&ldquo你以前盛气凌人,什么都不怕,如今却当起了缩头乌龟。
阿旷他最爱天高地阔,可不喜欢整日憋屈在屋子里头的人。
&rdquo 凌郁脸涨得通红,慢慢又褪成苍白。
她转头面朝墙壁,冷冷甩出一句话:&ldquo你不用激我,我的腿废了,只能憋屈在屋子里头。
&rdquo 徐晖心如刀绞,忍不住冲口吼了一嗓子:&ldquo谁说你腿废了?我不许你这么胡说!&rdquo 凌郁缓缓背身躺倒,将脸埋进棉被里。
她似乎打定主意沉沦到底,任谁也不能敲醒她沉睡的意志。
仿佛知晓各人心中的悲苦,新的一年来得悄没生息。
幸而龙益山的归来给幽谷带来了一丝生气。
除夕夜,凌波带着龙益山和徐晖做了一桌丰盛家宴,全家人一意做出兴高采烈的热闹气氛。
只有凌郁仍旧一言不发,涣散地靠在椅背上,一次筷子都不动。
她看着他们,觉得隔膜和疏远,欢乐早已是与她毫不相干的事。
凌波夹了一筷醪糟鱼丝到凌郁碗里:&ldquo来尝尝,这可是你益山哥的手艺。
&rdquo 凌郁勉强拣起一根鱼丝,如吞药般强咽下去。
慕容湛终于看不过去,拍下筷子道:&ldquo你到底想怎么样?&rdquo 凌郁拾起眼皮,勉力接住父亲沉重的目光。
这目光压得她几乎抬不起头来。
她在心里说,别逼我了,反正已经无可救药,就由我去吧,就让我一沉到底吧。
可慕容湛偏不肯放过她,寒着脸说:&ldquo你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十恶不赦,是不是?你觉得自己只能躲在这幽谷深处做一具行尸走肉?&rdquo这话正戳到凌郁心窝里去,她眼中立时便蒙了泪,只屑轻轻一点头,泪水就会落下来。
除夕夜落泪是大不吉,她便强忍着。
只听慕容湛缓了口气,接着说道:&ldquo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小孩,他生来便不知父母是谁,就跟他养父两个人住在一座高高的雪山上,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一伙恶人闯到他家里来烧杀抢掠。
他养父把他给藏了起来,这孩子才侥幸躲过一劫。
&rdquo 听到这里,徐晖心中一动,这个小孩和海潮儿自已的身世很像啊。
&ldquo后来这小孩长大了,学会了很厉害的武功,再没有人能欺侮他了。
可是他没有亲人,也没人教他怎么做人。
他以为这世上只有恶,没有善,所以他便也漫无目的地行恶。
他心里头全都是恨,可又不知该恨谁好,就把天底下所有人都恨上了。
天下人也都恨他,他们日夜诅咒,盼望这个恶魔从世上消失。
他们把坏事都推到他头上,有些是冤枉,有些又不是。
这个人的的确确干下了很多坏事。
他杀人不眨眼,瞧着不顺眼的一剑就刺下去,因为他以为人人龌龊。
他见了好人家的女子就勾引,因为他觉得她们都是惺惺作态的婊子。
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只配下地狱?&rdquo 凌郁全身一震,她听出来父亲这是在讲述他自已的身世。
慕容湛神秘的面纱终于被他自己揭开,江湖上支离破碎的道听途说被故事的讲述者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
真正的慕容湛,既不是凶神恶煞,亦非落难英雄,他长于不幸,亦制造不幸。
凌郁眼前一片模糊,恍恍看到她自己。
原来她的人生,正是延续了父亲的悲哀。
慕容湛深深望着凌郁:&ldquo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只有下地狱?他是不是一丁点儿指望都没有?&rdquo 凌郁心乱如麻,迷茫地点了点头。
&ldquo这人自己也是这么想,他想他这一生就这么完蛋罢。
可有一天他遇见一位仙女,这仙女明知他是个恶魔,却丝毫不嫌恶,反而真心诚意地相待。
他长这么大,头一回尝到幸福的滋味。
这滋味真好,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幸福原来是这么好。
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样好的女子,不配拥有幸福,可最后他竟然得到了,这真不可思议。
&rdquo慕容湛缓缓握住身旁凌波的手。
凌波眼中泪花点点,安静地微笑着,像一片明月光。
&ldquo既然是不配得到幸福,怎么还能得到?&rdquo凌郁哑着嗓子问。
&ldquo在上天眼中,这世上众生都是一样,即便是犯了滔天大罪之人也不例外。
&rdquo慕容湛声音如水,温柔深沉。
&ldquo什么样的人都能吗?&rdquo &ldquo都能,除非你自己摒弃了人世幸福。
&rdquo 凌郁的心剧烈地战栗:&ldquo难道上天不惩罚罪人吗?&rdquo &ldquo上天很公平,谁犯了错,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年轻时伤过许多人的性命,杀过别人的儿子,所以上天就夺去我的儿子,收回我的武功。
这惩罚躲也躲不过,或迟或早都会来。
&rdquo &ldquo这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呀!&rdquo凌郁捂着胸口叫道。
慕容湛微微一笑:&ldquo你一直都这样把大石头往自己身上压,是吧?这是我应受的罚,我坦然受之,你不必觉得难过。
&rdquo &ldquo可大哥,大哥他犯了什么错?上天为什么偏偏要把他夺走?&rdquo凌郁惨白着脸喃喃问道。
慕容湛的嘴唇也泛白了:&ldquo旷儿他是帮我分担了惩罚。
这孩子太好,太透亮,有时候我觉得,也许他原本就是天人,脱胎换骨来做我的孩子。
他在人世好好走了一遭,如今又回到天上去了。
&rdquo 天上劈下一道强光,霍地打入徐晖心里。
小清不也正是天上之人么?她飘然升起,化为雨露星辰。
凌郁眼中燃烧着两道寒光:&ldquo大哥是天上之人,重又回到天上去。
可我,我就要下地狱。
&rdquo 慕容湛伸手抚摸凌郁的头发:&ldquo孩子,你是得为自己做的错事受罚。
你加在别人身上的伤越深,你自己受的苦就越重。
可你别以为自个儿全毁了,幸福跟你再不相干了。
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一步,幸福就在痛苦的另一头。
那滋味,真的很好很好。
&rdquo 幸福的感觉像一根尖头锥,深深扎入徐晖和凌郁胸口,血液里混进一种带着疼痛的香甜。
凌郁低头看自己的身体,忽而觉得异样。
她感觉到慕容旷,在她不知晓时,他已悄然融入她的血脉,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
她每一次心脏的挤压,每一个呼吸的瞬间,都隐匿着他的气息。
她只觉得身体里含着一大团气,往各处乱冲乱撞。
她深深吸气,把那气团笼住,蓦地一提,气流冲破头颅,直上云霄。
温暖霎时涌遍全身。
她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一用力,自然而然就站了起来,往门口走去。
&ldquo海潮儿,你干什么?&rdquo徐晖叫住她。
&ldquo我&hellip&hellip我出去走走。
&rdquo凌郁脑海里被一片白光笼罩,迷茫混沌。
徐晖一怔,突然惊呼道:&ldquo你能走了!&rdquo 凌郁吃惊地看着自己的下肢,双腿一软,摔倒在地。
凌波跪下身揽住凌郁,眼中绽放出狂喜的光芒:&ldquo海潮儿,适才你的&lsquo拂月玉姿&rsquo上到了新境界,它甚至带动了你的腿。
你能走路了!能走了!&rdquo &ldquo我真的&hellip&hellip走路来着?&rdquo凌郁恍惚地轻轻抚摸膝盖。
&ldquo你真走路来着,你真能走了!&rdquo徐晖一把握住她的手。
慕容湛即刻为凌郁检查双腿,发现她腿部肌肉和神经受到突如其来的内力刺激,机能得到了一次大复原,虽然不能痊愈,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恢复了行走功能。
&ldquo海潮儿,你这&lsquo拂月玉姿&rsquo根基扎实,厚积薄发,是谁教你的?&rdquo慕容湛激动不已。
&ldquo是&hellip&hellip我师父。
&rdquo凌郁小声嗫嚅道。
&ldquo你师父是谁?&rdquo &ldquo我师父,我师父&hellip&hellip&rdquo凌郁踌躇半晌:&ldquo完整的&lsquo拂月玉姿&rsquo,这世上原本就没几个人会&hellip&hellip&rdquo &ldquo湛哥,是小云!&rdquo凌波眼中漫上晶莹泪光。
慕容湛眼角也湿了:&ldquo我们没能养育女儿,却有小云悉心教她。
这是命运呐。
&rdquo 从此凌郁仍旧沉默寡言,却咬着牙坚持每日练习走路。
待到春暖花开的时节,她终于可以不用人搀扶、缓慢地自行走动了。
但是她腿部的疼痛感并未消散,一部分受损的肌肉和筋络难以复原,走起路来脚微微地跛。
她素来待自己严苛,眼中不容半分瑕疵,但父亲的话一点一滴流进心底,她渐渐把这疼痛和残疾视为自己应得的惩罚。
既是应得,便当坦然接受。
除夕夜慕容湛所说的一番话,于徐晖而言就像是漫长黑夜中的第一缕晨曦。
白光扎得他瞳仁刺痛,只能淌下热泪。
他每晚反复叩问自己,连我都可以得到幸福么?连我都能获得重生么?我真能把腐烂的旧皮囊撕下来,从中生长出一个新我? 在一个花草芬芳的晚上,徐晖又和慕容湛坐在慕容旷墓前喝酒。
半醉之时,慕容湛不经意似地问起:&ldquo你已经走到另一头了吗?&rdquo &ldquo哪一头?&rdquo徐晖心上一片迷茫。
&ldquo你不是求重生吗?不咬着牙走到另一头去,哪儿来的重生?&rdquo &ldquo前辈你说过,幸福就在痛苦的另一头。
可痛苦有长有短,有深有浅。
我做错的事太多,另一头离我太远了,我怎么走也走不到。
&rdquo徐晖的声音低下去。
慕容湛摆摆手:&ldquo你说远,它就远在天边。
可我看它近,只不过在河对岸,你只要跨过一座桥就到。
&rdquo 徐晖眼前&ldquo啪&rdquo一闪亮,又黯淡下去:&ldquo前辈你不知道,我违背过自己的良心,背叛过海潮儿和我的朋友与恩人。
我是个连故乡都回不去的人。
&rdquo &ldquo你跟海潮儿一个样,总在岸边苦苦徘徊,不敢涉水去摸索桥在哪里,对岸有多远。
&rdquo &ldquo人家都说什么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前辈怎么偏偏说要往水里去?&rdquo徐晖疑惑地问道。
&ldquo回到岸上,也是苦岸,倒不如下水去,拼一把劲到对岸。
&rdquo慕容湛眯起眼睛:&ldquo人这一辈子好像漫长,最好的岁月其实一眨眼就过,最是经不起蹉跎。
&rdquo 徐晖彻夜无眠,天将放明时才合了一会儿眼。
半梦半醒间,他恍恍看到司徒清披着晨曦织就的闪亮翅膀,从他眼前翩然飞过。
&ldquo小清,小清!&rdquo徐晖柔声呼唤她。
司徒清划下一抹青翠的微笑,挂于他窗前。
徐晖张开双眼,正看到阳光初照,窗外青山如黛,温婉湿润。
他缓步走到窗前,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
太阳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轻轻拂过大地上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片树林,每一个人。
她也轻轻抚摸着徐晖干燥的脸庞,甚至把她温暖的手臂探进他衣衫,照亮了他昏暗浑噩的身体和灵魂。
初生的阳光里,徐晖看到自己的灵魂重新升起,禁不住泪流满面。
徐晖出门时,己是一个全新的人。
他看到身边的一切也都焕然一新。
青草胆怯而勇敢地拱出泥土,头顶着晶莹的露珠,颤巍巍向这世界探出第一眼注视。
溪水涨满了河床,唱着欢快的小调,一路跳过河底卵石奔向远方山谷。
墨山和银川两匹马儿在不远处打着响鼻,晨光为它们的鬃毛染上了一层金色,远远望去,像是两匹神驹。
一位雪白衣裳的女子站在它们旁边,仿佛站在太阳的中心,黑发和白裙在风中飞舞,金光璀璨,耀眼夺目。
徐晖如第一次见到凌郁那般着迷地凝视着她,看她微蹙眉心,紧抿嘴角,艰难地向前迈出一步,身子晃了晃,终于坚强地挺直。
这时凌郁微微侧过脸,瞧见了徐晖,不经意露出一弯浅浅微笑,有如白雪初融,洁净深邃。
徐晖心中溢满了大海一样深澈的爱情,浪花一波一波拍打在他胸口,激烈壮阔而又温情脉脉。
&ldquo早上我梦见大哥了。
&rdquo凌郁喃喃低语。
&ldquo慕容兄说什么了?&rdquo &ldquo我听不真切,只看见他含笑的眼睛。
他像一朵云彩,飞过无数高山大河。
&rdquo凌郁抬头仰望重重青山外的蓝天。
徐晖柔声说:&ldquo你记得吗?咱们曾经说好,要一起去许多好看的地方。
你说好不好?&rdquo 在这似曾相识的话语里,凌郁依稀闻到了江南九月的桂花甜香,香气里沾着恋人嘴唇的气息。
她想再瞧真切些,却被无数血淋淋的记忆所阻隔。
腿部的疼痛压过了一切,她佯装冷漠地背转身去:&ldquo以前的事我全不记得了,也不想再听你提起。
&rdquo &ldquo你不记得了吗?不记得你抱着我从山崖上跳入这幽谷里来?不记得九月临安城月光明净?不记得这枚东海珠?你当真全不记得了吗?&rdquo徐晖扯开衣襟,露出脖颈上系着的一根细细绳子。
昔日他送她的那颗东海珍珠,原来一直贴在他胸口上。
凌郁心窝里蓄满了泪水,往事一幕幕,眨眼间就翻过了。
可慕容旷和司徒清亲切的面容浮现上来,挡住了所有通往幸福的道路。
凌郁用背影悲哀地注视徐晖,你怎么不明白呢,相爱已经不可能,再也不可能。
她的心一沉到底,冷酷地摇摇头:&ldquo全不记得了。
&rdquo 白马银川忽然仰天嘶鸣,黑马墨山把头向它靠拢,发出低沉的咆哮,像是应和,又似对答。
它们一起向前奔跑去,欢快地长吟短吁。
徐晖头一次见到这两匹孤僻的马儿如此开怀地嬉戏玩耍。
他望着它们,忽然下定了决心。
徐晖大步走到凌郁面前,直视着她双眼:&ldquo不记得没关系,权当我们原本不相识。
我叫徐晖,你叫我阿晖就成,我的朋友都这样叫我。
&rdquo 凌郁怔怔看着他。
往昔岁月如浪淘沙,那个静谧的黄昏再次冲到眼前,一个陌生男人温暖地向她微笑。
那个时刻如一道柔软的光,轻轻叩动她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
&ldquo你呢?你叫什么?&rdquo徐晖温柔地问道。
凌郁全身打了个颤,脑海中一片空白。
是呀,我是谁?我叫什么?当初我是怎么说的,现下又该如何作答?她迟疑着开口:&ldquo我&hellip&hellip我叫慕容怡,我爹娘&hellip&hellip他们喜欢叫我&hellip&hellip海潮儿&hellip&hellip&rdquo 凌郁看到有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徐晖眼眶中滚落下来。
他哽咽着喃喃说道:&ldquo好,我就叫你&hellip&hellip海潮儿!&rdquo 凌郁听到从自己身体里传来啪啪的声响,那是寂静深夜里海棠花朵怒放时发出的声音。
她终于了解了开花的全部奥秘,原来那娇艳的红花是用鲜血浇灌的。
她鲜红欲滴,颤巍巍在枝头绽放,打开每一片花瓣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磨难。
只有以剧痛为代价才能得来一次盛放。
凌郁眼前一亮,一束巨大的光亮从她胸口喷出,投下无比深刻的疼痛和喜悦。
她低头看着自己,刹那间一切都变得分明。
她问了自己许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我是谁?这个充满了痛与美的躯体就是我呀,这就是我呀。
&ldquo你再叫我一声。
&rdquo凌郁战栗着请求说。
徐晖饱含深情地轻声呼唤:&ldquo海潮儿!&rdquo &ldquo&hellip&hellip阿晖!&rdquo凌郁心上的坚冰&ldquo嘭&rdquo地碎开,她终于呼唤出深锁于她心底的那个名字。
徐晖和凌郁惊骇地望着对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够如从前那样纯粹无遮拦地相爱,究竟是对他人的愧疚将压垮他们的爱情,还是这爱终于能够战胜阴影,一切都未可知。
但是从这犹豫而又热切的呼唤声中,他们终于认出了对方,也认出了自己。
这是他们的名字,其中含着全部不为人知的欣悦与悲伤。
唯有他们知道,唯有他们自己。
徐晖和凌郁出谷那日,春雨连绵。
凌郁向父母拜倒,行三叩大礼。
千言万语压在胸口,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慕容湛扶起女儿道:&ldquo出门是好事。
去吧,去看看山川锦绣,天地宏阔,然后你们就把自己看得更真切了。
&rdquo 这番话徐晖和凌郁听得半是明白,半是糊涂。
他们囫囵吞枣地记下了,将有日后漫长的岁月细细体会。
凌郁又转身向龙益山拜倒。
龙益山涨红了脸,但他知道这是凌郁对自己重重的托付,便不退让,也深深回了一礼。
&ldquo益山哥!&rdquo凌郁低声叫他。
龙益山遽然发现,原来自己已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喜乐哀愁从此都要他一肩扛着,再猛烈的风雨也决不许砸到他亲人的头上。
他不觉挺了挺背脊,承受责任压到肩上的分量。
他感到身体无比沉重,却比任何时刻都更充满力量。
&ldquo妹妹,你放心。
&rdquo他向凌郁点点头。
慕容湛望着这个朴实爽直的孩子,心头柔软煦暖。
原来上天终究还是厚待他的,赐予旷儿做他天上的儿子,益山来做他人间的儿子。
凌波从马厩里牵出墨山和银川,把缰绳交与徐晖。
徐晖忙道:&ldquo墨山是慕容兄的坐骑,我如何能据为己有。
&rdquo &ldquo你们带着旷儿的骸骨,旷儿便与你们在一起。
墨山也是这么想的,是不是?&rdquo凌波伸手轻轻抚摸墨山面颊。
墨山便低头在她身上磨蹭,好像是在应答她的问话。
徐晖和凌郁牵过墨山银川,辞别诸人,默默穿过山洞,步出幽谷。
他们放马缓行,心中怀有同样的迷惘与忐忑。
离愁别绪渐渐淡去之后,萦绕在心头的是对尘世的隔膜与惶恐。
毕竟他们已有近一年的光景离群索居,骤然回归喧嚣拥挤的江湖,他们都隐约升起一种心潮茫茫之感。
&ldquo海潮儿,你说咱们往哪儿去好?&rdquo 凌郁浑身打个激灵,脑海里不由己地冒出一个地方来。
她甩甩头,想把这个念头甩进记忆深处。
&ldquo你说你想去哪儿,咱们这便去!&rdquo徐晖握住凌郁的手。
那个地方直冲舌尖,凌郁咬住嘴唇,硬把它咽了回去,才展开一个敷衍的笑容:&ldquo去哪里都好。
&rdquo 徐晖觉出凌郁手背轻微的颤抖。
他的目光深入她乌沉雪亮的眼睛,略一沉吟,便有了计较。
凌郁也不多问,听凭徐晖引领方向。
两人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在司徒家族执行任务、结伴出行的岁月。
马匹、驿站、浮光掠影的城镇世情,就是他们的生活。
凌郁双腿承受着细微而绵长的疼痛,这疼痛成为她肢体感觉的一部分,她几乎已忘记没有疼痛相伴的光阴。
或许疼痛本就是生命的常态。
长时间骑马,她的腿痛便会愈发强烈,间或伴随短暂的抽搐。
她常常一言不发强自忍耐,但细密的汗珠霎时爬满额头,徐晖见了甚是心疼。
自此他改了行程,每日骑马至多三个时辰,每行数里便扶凌郁下马慢慢走上一段,并在歇脚时按照慕容湛传授之法为她推拿按摩腿脚,缓解肌肉承受的力度。
一日晌午,他们在一座大市镇的酒楼上打尖。
邻座几位客人高声攀谈之声,不时传入耳来。
&ldquo小兄弟,你这一身功夫不赖呀,怎么流落在此卖艺?&rdquo一个粗壮的嗓音问。
&ldquo俺卖两天艺,赚几个盘缠好赶路。
&rdquo一个北方青年口音朗朗答道。
&ldquo这是要去哪儿啊?&rdquo在座另一位年纪较长者问道。
&ldquo去江南,投奔司徒家族去!&rdquo那青年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兴奋。
徐晖和凌郁原未留意他们言谈,忽听得&ldquo司徒家族&rdquo几字,猝然都绷紧了心弦。
这一路他们极力回避这个名字,可又似乎一直在期盼着它。
这名字那般熟悉又生疏,亲切又扎人,它霎时就擒住了他们的肝肠。
徐晖忍不住调头望去,正撞见一张生气勃勃的年轻面孔,眼中满是憧憬。
他转回头来闷头扒饭,胸口隐隐发酸。
却听那粗嗓音汉子接口道:&ldquo这光景,还投奔司徒家族做什么?司徒老爷子早垮台了!&rdquo &ldquo啪嗒&rdquo一声,凌郁筷子掉落在地。
徐晖也怔住,一颗心上下翻腾,只想奔过去问个究竟。
&ldquo怎么会?&rdquo那北方青年却已代他们发问:&ldquo司徒家族不是把雕鹏山都给灭了么?江湖上数司徒族主最有能耐,哪儿就会垮台?&rdquo 那年长者放低声音说:&ldquo兄弟是打小地方来的吧?前阵子江南江北都传遍了,司徒峙结交异族,叫江湖上的前辈押到少林寺给扣了大半年。
司徒家族那么大个摊子,他手下那位什么汤爷可罩不住。
族主一走,大小帮派跟着就反了天,那汤子仰白白赔上了性命。
&rdquo 徐晖的心给人揪住,他觉得疼,可仍然想听下去,听他们细说司徒峙近况。
他们仿佛知晓他心思,偏不再提司徒峙,只一劲议论司徒家族如何土崩瓦解,家财如何流散,美妾侍婢如何为人所占。
徐晖转头望向凌郁,但见她神色木然,只嘴角微微抽动。
两人各怀心事,对此绝口不提。
又行月余,渡江而下,一路过镇江、丹阳、常州,直抵无锡。
再往前行,就将进入平江府辖境。
凌郁起了疑,拉住徐晖问:&ldquo我们这是去哪里?&rdquo 徐晖笑而不答。
凌郁勒马停住:&ldquo我们这究竟是要去哪里?&rdquo &ldquo姑苏。
&rdquo徐晖深深注视她。
凌郁一怔,尖声嚷道:&ldquo天下那么大,为何非要回姑苏?&rdquo &ldquo海潮儿,别骗你自己了。
打从一开始,我就从你眼睛里面瞧出来,你想去那儿,想去见他。
你心心念念想着他,你想跟他再见一面。
既然如此,咱们就去。
&rdquo 凌郁被徐晖戳穿深埋于心底的渴望,霎时潸然泪下。
一跨进安详缄默的齐门,姑苏城那混着花香、脂粉和水腥味的熟稔气息就扑面袭来,把徐晖和凌郁团团围住。
三月平江,芳菲倾城。
徐晖还依稀记得头一次到司徒家族的情形。
他踌躇满志,亦步亦趋追随司徒峙的脚步。
从那时起,他就竭尽全力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以为那就是他自己,哪知潺潺河水中,映出的却是司徒峙的倒影。
他死死攥在手心里的荣耀,原来是别人头上光环的余辉。
徐晖打了个寒战,不由伸手去握凌郁的衣袖,觉出她竟然也在微微颤抖。
走在姑苏白光光的日头里,凌郁低头瞅见脚下一个少女的影子。
不必再伪装的人生,一朝成为现实,竟而让人觉得惶恐。
她忍不住一再整理衣衫,恍惚以为自己是个小小婴孩,赤裸着身体招摇过市,路人只不经意的一瞥,就让她惊惶羞怯。
凌郁仿佛不是走进一座城池,而是走入一个被粉碎的记忆。
这座城是她的地狱,可她偏偏无法将它从心中抹去。
一次次她在梦里归来,游荡过城郭的每处角落。
在遗落的童年时光里,她看到她昔日的伙伴们,她也看到她自己。
可是任凭她如何寻觅张望,有一个人裹在重重雾气之中,始终无法看清。
正疑恍间,司徒家族的白墙黛瓦遽然撞进眼帘,凌郁整个人顿时就僵住。
银川仿佛嗅到了什么令人不安的气味,也犹豫着不肯向前,只不住低声咆哮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表妹软玉娇香渊爻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反派带我成白富美[穿书]婳语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前男友总撩我[娱乐圈]夂槿
- 看见太子气运被夺后花里寻欢
- 他的余温阿宁儿
- 诅咒之王又怎样南极海豹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同桌乃是病娇本娇候鸟阳儿
- 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01入学篇(上)佐岛勤
- 虫屋金柜角
- 首辅大人重生日常/今天也没成功和离时三十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御佛o滴神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穿成废材后他撩到了暴躁师兄是非非啊
- 怀了豪门霸总的崽后我一夜爆红了且拂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武极宗师风消逝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夏日长贺新郎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单恋画格烈冶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夕照斑衣白骨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小镇野兔迪可/dnax
- “球”嗨夕尧未
- 沉迷撒娇虞子酱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学长在上流麟
- 循规是笙
- 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后桑奈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夕照斑衣白骨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根音(ABO)笼羽
- 戏精配戏骨陈隐
- 新婚ABO白鹿
- 动物爱人魏丛良
- 没完晚春寒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404信箱它在烧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无可替代仟丞玥
- 情终孤君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沉迷撒娇虞子酱
- alpha和beta绝对是真爱晏十日
- 学长在上流麟
- 非典型NTR一盘炒青豆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财神在身边金家懒洋洋
- 如何才能将目标勾引到手南柯良人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流量小生他天天换人设西西fer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我要这百万粉丝有何用宝禾先生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
- 轻狂巫哲
- 猪肉铺与小精英沐旖乘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