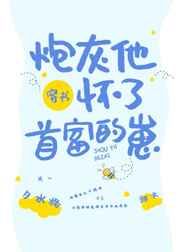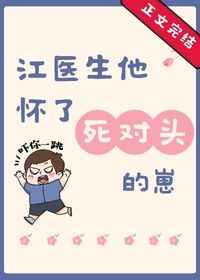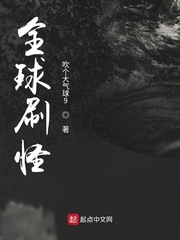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煮酒论史篇】 汉朝没有马鞍马镫吗?(2/3)
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
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
’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
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
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⒄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
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⒅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
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
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
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
”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
”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
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
”(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
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
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
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
’”(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
”(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
”(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
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
”(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
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
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
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
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
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
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夸夸我的神探祖父穿越爹渝跃鸢飞
- 这甜宠给你要不要啊[快穿]岁砚
- 赴火耿其心
- 阴阳执掌人洛冰
- 管家总被人觊觎[快穿]豆腐军团
- 撩肾达人/万千荣光甜醋鱼
- 大魏宫廷贱宗首席弟子
- 剑啸灵霄流浪的蛤蟆
- 反派修为尽失后一丛音
- 掩盖武和平
- 我在古代当先生北沐南
- 给卫莱的一封情书梦筱二
- 大宋有毒第十个名字
- 阴阳鬼术巫九
- 窈娘春未绿
- 重生东京黄金时代安静的想
- 一觉醒来成了神二代橘子球
- 九阳神王寂小贼
- 和豪门大佬隐婚后林多多
- 原谅她范月台
- 醒日是归时含胭
- 穿书后我被美惨强反派掰弯了衾寒月暖
- 郎骑竹马呼啸来PDG
- 原来我是修仙大佬木下雉水
- 我在女团艰难求生[穿书]兔子蛋糕
- 一剑天下冷光月V
- 太古造化诀咸鱼
- 异世厨神爱美食的喵
- 我能继承角色天赋白马寺钟晚
- 都市修仙狂徒毛三十六
- 穿成宠物晕乎乎,兽夫爱到不撒手中原红
- 穿越成女魔头,修真界被我拿捏了隐月霜
- 万界天尊胡霜拂剑
- 修仙:记录美好生活浑身上下六个肝
- 星火逆穹日月星晟
- 这株含羞草不对劲半醒的喵喵
- 修罗混沌经涅盘毛
- 没你就不行之新征途林木儿
- 万古第一禁忌HeyMy
- 太虚归藏青霜寒月
- 秦始皇魂穿之帝临万界四叶戏子
- 这个修士有点心计指间香烟
- 从小青蛇到逆天狂龙秦时飞剑
- 神级系统我在白蛇传当许仙秋意寒
- 高武纪元寒武光
- 不好!我的师尊是变态我即我见
- 大庆:理理美人计,贪吃铁棍下班分子
- 赤月天殇吕洞宾的葫芦
- 摆烂宿主与故障系统的互怼日常霜降十三月
- 开局负十体质,咱不想成为女仆鸭九不是玖
- 无上仙朝,从召唤罗网开始玖姝
- 何以逆天胖一不会饱
- 雪域镇魔录紫气东来黄貔貅
- 穿越高武界,我的抽奖系统不对劲小聊看书
- 攻略精灵(西幻万人迷NP)珀长烽(请监督我写文)
- 变身女剑仙,她们总想当我道侣谁拿走了我的脑子
- 普通人该如何角色扮演长枝青
- 反派对我产生了食欲怎么办?四藏
- 九龙夺嫡:从废柴皇子到永恒天帝我吃青苹果
- 修真从重生开始大鲲吞乌云
- 从流浪混沌开始制霸诸天龙海十三
- 贫穷的我靠拣垃圾飞升我不是飞不起来的鱼
- 开局陆地神仙,皇帝狗都不当无敌小床
- 怎么会有这样的队伍!!!沉迷于发财的土狗
- 穿越成女魔头,修真界被我拿捏了隐月霜
- 不朽战神雨上江南
- 诗剑长生:儒道妖魔卷冰狼水若寒
- 直男龙傲天也要被压么砚浔
- 八零文艺妇女木头山
- 当我上门遛狗发现狗主人是大帅比后七宝酥
- 这株含羞草不对劲半醒的喵喵
- 玛丽苏之心害我狗命(西幻np)许慎之
- 无敌大数据系统扑街的小喵
- 初智齿怀南小山
- 太古五行诀辉煌之途
- 陨落天骄逆袭成神记图克哈尼维岛的雷音
- 香江大厨[八零]小胖柑
- 我靠线人系统在刑侦文里当热心市民张小一
- 苍穹之下:我的文明重启计划二手沙发猫
- 无上仙朝,从召唤罗网开始玖姝
- 我用充电宝给千年雷法女魔修充电留云借月君
- 变身女剑仙,她们总想当我道侣谁拿走了我的脑子
- 炽夜[先婚后爱]枝在也听
- 你到底钓不钓啊苏景闲
- 反派对我产生了食欲怎么办?四藏
- 普通人该如何角色扮演长枝青
- 师父每天求我别破境了乌珑白桃
- 阴符吞墟录亮眼的咸鱼
- 天道之女怎么会有这种先天圣体啊泠言泠语
- 模拟诸天,我的天赋可以无限叠加清风茶楼
- 直男龙傲天也要被压么砚浔
- 悠闲的都市怪谈生活葱大王
- 一剑天下冷光月V
- 不朽传承骑着蜗牛去旅行
- 怎么会有这样的队伍!!!沉迷于发财的土狗
- 我有七个神兽奶娘烧饭的李小帅
- 帝尊之路从皇宫签到开始横推诸天清方观世
- 穿越成女魔头,修真界被我拿捏了隐月霜
- 穿成魔门杂役,被师姐骗去当炉鼎养鹿人
- 洪荒:我能强制置换下本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