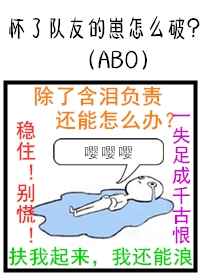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尾声(3/3)
死。
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看到阿加特在今天早先所做出的事。
回忆让他的胃开始纠结,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又喝了一口酒,这次是一大口,试图减轻当他想起那个男人时,那混杂着震惊、白热的怒火,以及在他心中翻搅的羞耻与痛苦的感情。
但是毫无效果。
阿加特。
这两个男人曾亲如兄弟。
曾经。
但麦坎达挑选来接受训练的第三名种植园奴隶……她毁掉了这份亲密。
麦坎达一直趁着夜色秘密地前来种植园,没有人出卖过他。
那些能够——或者说有胆量——的人们偷偷溜去参加集会,在集会上,他告诉他们,离开种植园、离开奴役,他们将能够拥有怎样的生活。
一开始,他只是说话。
告诉他们他自己的人生,自由,能做想做的事。
随后,他教这些迫切渴望着的奴隶们读和写。
“我会与那些值得的人分享许许多多,”他承诺说,“而这,也许是我能够给予你最有力的武器。
” 轻浮的小珍妮,她喜欢这些。
她也喜欢阿加特。
曾经有一次,巴蒂斯特撞见他们手拉着手。
他嘲笑他们,警告说麦坎达会不高兴的。
“你不够坚强,”他鄙夷地告诉珍妮,“你所做的只是让阿加特从他的训练中分心。
” “训练?”她看着他们两个,这样问,“用来做什么?” 巴蒂斯特绷着脸,将他的“兄弟”拽走,去同麦坎达私下会面:“她永远也成不了一名刺客,”他告诉阿加特,“她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不完全是。
她的心底里不是。
” 麦坎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些时日之后。
她学会了读写,但再无其他。
他从未邀请珍妮加入那些真正的训练。
当巴蒂斯特意识到麦坎达,这名还在孩提时就因甘蔗压榨机上发生的一次事故失去了一条手臂的前任奴隶,不仅仅能够逃离、还能够领导人们的时候,他的心中溢满着骄傲。
在这种特殊训练中,巴蒂斯特和阿加特学习了如何使用武器——以及如何不用武器进行攻击。
如何调制毒药——以及如何下毒,比如将粉末掺在饮料中,或在飞镖上涂厚厚一层。
这两个男孩学到了如何杀人——公开地,或是从阴影处下手。
甚至,如麦坎达所展示的那样,只用一条手臂就做到这些。
而当他们最终留下懦弱的珍妮、逃离种植园时,他们确实杀了人。
鼓声变强了,将巴蒂斯特的思绪从快乐的过去带回了冷峻的现实。
今晚,他,巴蒂斯特,将会主持这场仪式。
这,同样,也是麦坎达教给他的。
巫毒。
不是真正的仪式,不,而是其表象。
符号的力量,以及并非魔法、却形似魔法的力量。
“让他们对你感到恐惧,”麦坎达说,“让那些恨你的人。
哪怕是那些爱你的人。
尤其是那些爱你的人。
” 今夜的仪典将会改变一切。
必须如此,否则,麦坎达曾为之奋斗的一切——巴蒂斯特为之奋斗的,以及,曾几何时阿加特曾为之奋斗的——都将分崩离析。
参加仪式的众人喝下了许多他给的朗姆酒,并未意识到杯中除了酒还有别的。
很快,他们将准备好接受仪式,准备好目睹那些否则他们绝不可能目睹的景象。
去相信那些否则他们会质疑的事。
去做那些否则他们不会做的事。
鼓声逐渐激烈,攀上一阵近乎狂暴的渐强鼓点,随之一声哭嚎、一声怒吼从一边传来。
一头公牛被领了上来,粗壮的脖子上围了一个花圈。
它被下了药,保持着平静,将完全不会挣扎。
巴蒂斯特站起身,有力的手指紧抓着砍刀刀柄。
他是个高大、肌肉强健的男人,而他以前也为麦坎达的典礼做过同样的事。
他轻巧地跃下平台,大步走向那头野兽。
早先,在他的命令之下,它已经经过了沐浴,并涂上了从某些前任奴隶主那里偷出来的香油。
现在,它转过长着角的脑袋,大睁着的大眼睛凝视着他。
他拍了拍它的肩膀,它发出轻哼声,温和如同一头老牛。
巴蒂斯特抓着砍刀,转向他的人民。
“是开始典礼的时候了!我们将对罗阿(4)奉上祭品,请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兄弟会该怎么做才能继续前行!” 这些语句离开他的嘴边时带来了一阵痛苦。
麦坎达。
二十年来,从十三岁到三十三岁,巴蒂斯特和阿加特一直在他身边作战。
他们了解了导师对兄弟会的愿景——一个没有被仁慈或怜悯这种不合时宜的理念所冲淡的愿景。
他如此向他们保证,而他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那些是弱点,而不是力量。
没有人是真正无辜的。
一个人如果不是支持你,那就是反对你。
用某种方式来说,一个人如果不是刺客,就是圣殿骑士。
一名不会鞭打奴隶的奴隶主依旧是一名奴隶主。
一名所有者。
即便是那些并未拥有奴隶的人,依照法律,他们仍然可以拥有奴隶,因此他们是有罪的。
他们服侍于圣殿骑士,即使他们自己不知道。
麦坎达的世界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巴蒂斯特的世界里也没有。
而这就是为什么,巴蒂斯特——和那些现在停下了舞蹈、转而面向他的人们——在几个晚上之前,试图向那些他们被迫与之分享这个岛屿的殖民者投毒。
但他们失败了,而他们的领导者代替他们付出了代价。
“弗朗索瓦·麦坎达是我们的导师。
我们的兄弟。
他启迪了我们,并以身作则。
而他到死都没有背叛我们——他被折磨而死,他的尸体被火所吞噬!” 咆哮声四起。
他们已经醉了、被下了药、并且愤怒,但他们正听着他的话。
这很好。
照巴蒂斯特的计划,很快,他们所做的将会更多。
他继续道:“而在这哀恸和愤怒的时刻,我的兄弟——你们的兄弟——之中的一个,也离开了我们。
他并非在一场争斗中被杀,他也并未受到火焰的折磨。
他只是离开了我们。
离开了我们!阿加特像个懦夫一样地逃跑了,而不是接过弗朗索瓦·麦坎达以他的生命所换来的遗赠!” 更多的咆哮。
哦,是的,他们确实愤怒。
他们几乎就和巴蒂斯特一样愤怒。
“但我在这里,作为你们的祭司,向罗阿恳请以求他们的智慧。
我没有背弃你们!我绝不会背弃你们!” 他举起手。
砍刀长长、钢制的刀刃上反射着火光。
随后,巴蒂斯特将它劈下,迅速、利落,将他身体里的全部力量都放入这一击。
血液从这个牲畜被劈开的喉咙中如泉水般涌出。
它试着要发出声音,却发不出来。
它身下的大地因这公牛的生命之源而变得血红、松软。
但它死得很快。
也许比它在一个种植园主的屠宰场里所可能遭受的要迅捷得多,巴蒂斯特想到。
痛苦则肯定更少,因为那些药剂的作用。
他在兽皮上擦净刀身,随后用手指蘸入热血之中,用它描画自己的脸。
他抬起双手,做势邀请。
现在他们涌上来了,麦坎达的人们用那猩红为自己涂画,将死亡置于自己的身上,一如它触及他们的灵魂。
过一会儿,这具尸首将会在中央的巨大篝火上被烤熟。
人们会用砍刀切下大块美味、多汁的肉。
生者将借由死亡而继续生存。
但在那之前,巴蒂斯特有个计划。
当聚集来的每个人都用祭品为自己染血后,巴蒂斯特宣布道:“我将啜饮毒药,并要求罗阿降临于我。
他们会降临,一如他们曾经降临。
” 当然,他们从没降临过,也没有降临于麦坎达过,尽管他们两人都经历过一些有趣的幻象。
他所准备的的合剂在到达某种剂量后将会致命,而摄取少剂量会引起不适,但无害。
而巴蒂斯特深谙为了不同的目的分别需要多少剂量。
现在,他在两手间碾碎芳香的药草,闻到那干净、清新的气息混合在血之中。
随后,在旁人看来他似乎是凭空变出一个小小的毒药瓶。
人群中掠过一阵惊喘。
巴蒂斯特藏起笑意。
他是灵巧把戏的大师。
他挥舞着它,并大喊:“今夜,当死亡与我们的记忆如此接近,我将这头强壮公牛的死亡献给戈地·罗阿!今晚是谁将通过我给予智慧?是谁将告诉我们这些麦坎达的人民应该怎么做?”随即他将这苦涩一饮而尽。
三次呼吸之后,世界开始改变了。
颜色变幻,似乎开始闪烁。
鼓声响着,鼓声,但却没有人在击鼓.那个声音失真,混杂着某种因狂喜或折磨发出的尖叫。
噪声渐强,压倒一切,巴蒂斯特在痛苦中呻吟着,双手捂住耳朵。
随后他意识到了这响声来自于哪里。
那是他自己的心,击打着他的肋骨,叫嚣着想要出来。
随后它确实出来了,撕开他的胸膛,躺在他面前的地上,鲜红、搏动着、散发着热血的恶臭。
巴蒂斯特低头注视着它在自己身体上撕开的那个洞,惊骇万分。
是因为那毒药。
我喝得太多了。
我会死。
恐惧席卷了他全身。
尽管他知道这是个幻觉,却愚蠢地伸手去抓他那仍旧在跳动着的心。
它从他血淋淋的双手中滑出,像一条鱼,四处跳动着。
他冲它追去,它跳着逃脱。
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
这种梦境状态—— “这是因为这并不是个梦。
”一个声音说道,流畅、充满了幽默,那种幽默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残忍。
巴蒂斯特抬起双眼,看见那个骷髅在冲他微笑。
并尖叫。
他抓挠着自己的双眼,逼迫自己看清楚,但尽管他的视野变得清晰,那个影像却并未离开。
骷髅的身体慢慢变形,长出血肉和隆重的着装,看起来像是那些优雅、有钱的种植园主中的一名,如果种植园主有着黑皮肤,以骷髅为头的话。
“巴隆·萨枚第(5)。
”巴蒂斯特低语。
“你要求被一名罗阿附身,我的朋友,”巴隆以丝般的声音回答,“你在邀请人参加派对时应该小心。
” 在巫毒教中,罗阿是人类和遥远神祗庞度之间的媒介灵魂。
戈地·罗阿是死之灵魂。
而他们的首领是墓场之王——巴隆·萨枚第。
现在,这名罗阿大步走向这跪倒在地、浑身颤抖的刺客,伸出一只手。
“我想,对你来说更合适,我的脸比牛血更合适。
”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将佩戴它,明白吗?” 巴蒂斯特抬起他血淋淋的双手,触摸自己的脸。
他没有感觉到温暖的、活生生的肉体……只有干涩的骨头。
骷髅俯视着他,狞笑着。
巴蒂斯特闭上双眼,疯狂地揉着,但他的手指抠入空空如也的眼眶。
他哭泣起来。
他的脸——巴隆·萨枚第拿走了他的脸—— 别像个小孩一样,巴蒂斯特!你是清楚的!你自己调制的这副毒药!这只是个幻觉!睁开你的眼睛! 他照做了。
巴隆仍旧在那里,狞笑着,狞笑着。
而在他的身边,站着麦坎达。
巴蒂斯特的导师看起来一如生前那样。
高大、肌肉虬结、骄傲而强壮,比巴蒂斯特大十岁左右。
就如在活着时一样,他没有左臂。
“麦坎达。
”巴蒂斯特低语。
眼泪从他的眼中涌出——欢喜、解脱以及惊异。
他的双膝仍跪在血淋淋的地面上,朝他的导师伸出一只手,去抓他穿着的长袍。
他的手碰到了什么并非布料的柔软东西,并穿了过去。
巴蒂斯特猛向后缩去,震惊地盯着一只沾满烟尘的手。
“我死了,被那些本应死于我手上的人们所烧死。
”麦坎达说。
这是他的声音,他的嘴唇动了,但那些字句似乎漂浮在这名导师周围,如同烟雾,在巴蒂斯特的头颅边萦绕扭曲,钻入他的耳中、他的嘴中、他的鼻子中—— 我在呼吸他的骨灰,巴蒂斯特想着 他的胃开始翻搅,就像之前一样,他开始干呕。
一条蛇从他的口中出现——粗如他的手臂,黑色,因巴蒂斯特的唾液而闪烁,扭动着从他的身体中钻出。
当他最终吐出了这条大蛇的尾部后,这个爬行动物滑到了麦坎达的幽灵身边。
麦坎达俯下身,将它捡起,放在自己的肩上。
它的舌头闪烁,小小的眼睛注视着巴蒂斯特。
“大蛇是智慧的,并不邪恶。
”巴隆·萨枚第说,“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脱皮,这样就可以比以前长得更大、更强壮。
你准备好要脱掉你的皮了吗,巴蒂斯特?” “不!”他大叫道,但他知道这毫无用处。
巴隆·萨枚第退后一步,脱下他那正式的礼帽交给麦坎达,露出下面的头骨——他没有头发,正如他的脸上没有血肉。
“是你召唤了我们,巴蒂斯特,”麦坎达说,“你告诉我们的人民,你永远不会背弃他们。
现在我已经死了,他们需要一个领导者。
” “我——我会领导他们,麦坎达,我发誓,”巴蒂斯特结结巴巴地说,“不管你要求我做什么,我都不会逃跑。
我不是阿加特。
” “你不是。
”麦坎达回答道,“但你也不会领导他们。
我会领导他们。
” “但你已经……” 麦坎达开始化为烟,他肩上的蛇随着他一同消失。
烟漂浮在空中,如同武器,随后拧成了卷须,开始朝巴蒂斯特飘来。
陡然间,巴蒂斯特明白了将要发生的是什么。
他试图站起身。
巴隆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强壮的双手——有血有肉,并非骨头,但即便如此仍冰冷如坟墓——紧夹住巴蒂斯特的肩膀,让他无法动弹。
那细细的烟汇聚成的卷须飘向他的双耳、他的鼻孔,寻找着入口。
巴蒂斯特咬紧牙关,但巴隆·萨枚第咂了咂舌头。
“哎,哎。
”他责备道,并用他那镶着骷髅头的手掌轻拍巴蒂斯特紧闭的嘴。
巴蒂斯特的嘴张开了,烟雾进入。
而他既是他自己……也是麦坎达。
还有三项任务,随后我们将领导他们。
巴蒂斯特瞪视着他丢下的那把砍刀。
砍刀落在他仍搏动着的心脏旁边。
带着一种奇怪的疏离感,他意识到他不需要他的心。
这样更好,不需要关心。
不会对他人感到爱或是希望。
唯一重要的只有他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需要。
因此,他将他的心脏留在原地。
但他拾起了那柄砍刀。
他将它慢慢地用右手举起,并伸出他的左臂。
他的一部分尖叫着要他不要这么做、尖叫着作为他自己他也能领导得很好。
但另一部分——他的一部分,不是麦坎达、不是巴隆·萨枚第——想要这么做。
还有,药物也对痛楚起作用。
巴蒂斯特举起砍刀,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仅仅一击,将他的左臂从手肘上方齐齐切下。
血似乎从伤口爆发,疯狂地喷洒着,但他是对的。
这并不痛。
被截下的肢体落在地上,变成一条大蛇,这一条爬向那骷髅脸庞的罗阿。
在他的脑中,麦坎达低语道:“很好。
现在,你就像我一样了。
你不再是巴蒂斯特了。
你将成为弗朗索瓦·麦坎达。
他们看见了你的举动。
他们知道我驾驭着你,就如他们驾驭着一匹马。
通常,罗阿会在事成之后就会离开。
“但我不会离开。
” 巴蒂斯特平静地将他腰上系的饰带抽出。
在失血杀死他之前,他自己将涌着血的伤口系紧。
说到底,他和巴隆不同,他还活着。
巴隆·萨枚第同意地点点头。
“很好。
他与你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
我也是。
”他点了点自己的下颚骨,“戴着我的面容,麦坎达。
” 巴蒂斯特点点头。
他明白了。
他同意了。
自这一刻起,流言四起。
麦坎达没有死,人们悄声说。
他从燃烧的火刑柱上逃脱了。
他在这里,而他满心是憎恨与复仇。
而自这一刻起,将无人再见到巴蒂斯特。
他仍是他自己,没错,但他的名字将是麦坎达,而他的脸上将会戴着、将会涂画成白色,这颜色会突显于他黑色的皮肤上:那是狞笑着的巴隆·萨枚第白骨磷磷的面孔。
实验体: 林 林听着索菲亚·瑞金博士第三次耐心地解释,林必须以她的自我意愿进入阿尼姆斯。
林交叠着双臂,凝视着,没有回答。
“我知道上一次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创伤性的。
”索菲亚说。
她大大的蓝色眼睛友善但疏离。
在它们深处有着慈悲,但并没有真正的同情。
“你什么也不知道。
” “创伤性”是个完完全全轻描淡写的说法,一个苍白、冷淡的词汇。
完全无法描述出林的先祖,一个名为邵君、由小妾成为刺客的人,在五百年前看到、而林则在现在被迫目击的景象。
五岁。
在当时的新皇帝、后人称为正德皇帝的朱厚照下令处死一名策划谋反的宦官时,邵君五岁。
刘瑾是一伙拥有强大权力的宦官们的首领,在朝野中他们被称为八虎。
但他被他们中的其他人所背叛,就像是他出卖了他的皇帝一样。
因这极端恶劣的叛国罪,正德皇帝下令,刘瑾要受到与此大罪同样可怕的折磨——凌迟千刀处死。
最后,行刑在切下了超过三千刀之后才结束。
这可怕的景况持续了三天。
刘瑾很幸运,他在第二天、只挨了三四百刀时就已经死了。
旁观者只用一文钱就能买到一块这个男人的肉,用来就着米酒吃。
好多天,林都无法将这个景象从她的脑海中抹去。
当她痉挛着、尖叫着倒在阿尼姆斯房间的地板上时,浮现在她头顶上方索菲亚那忧心忡忡的面孔与恐惧感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即便现在,林只要看着这个女人就想吐。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大多数时候,对于你将会经历什么,我们同你一样一无所知。
”索菲亚继续说。
“真让人安慰。
” “报告显示你的状态很好。
”索菲亚热切地说,“我想要重新进入。
上次回溯之后,我们排查了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而我相信,这一次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段记忆,既重要、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许多东西,又不那么地……”她搜寻着那个词,随后,在片刻的诚挚中,冲口而出,“恐怖。
” 林没有回答。
她的绑架者——这是她唯一能够将他们视作的身份,此刻对邵君的了解比她自己要多。
林最最希望的,就是不再回到那个可怜女孩的体内。
这个小孩,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花花公子的众多小妾之一。
不。
这不完全正确。
林最最希望的是保有她的理智。
而她知道他们会送她回去,不管她是否愿意,不管回忆是否恐怖。
索菲亚·瑞金也许想要相信,自己是在邀请林重新进入那可怕的机器,但两个女人都知道她并不是在邀请。
她是在命令林。
林所拥有的唯一选择是她要如何遵从——自愿,或是非自愿。
很长一段时间后,她说:“我会去的。
” 回溯:北京,1517年 夏季已经来到北京,但还不到朝廷移居避暑山庄的时候。
黯淡的灯笼将闪烁的光线照在许多女人身上。
她们中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正在几近令人窒息的酷暑中断断续续地沉睡着。
这间庞大的房间是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的乾清宫内九个大房间之一。
现在,它华丽雕刻的木质天花板完全被黑暗所遮蔽,但光线仍旧照出了以金叶画成的龙身上的微光,以及那华丽、但紧锁着的门把手闪出的光芒。
十二岁的邵君轻易地打开了那巨大的门,静悄悄地走过黑色的大理石地板。
这座宫殿是紫禁城内殿中最大的三座建筑之一。
这里是正德皇帝、他的皇后以及他最宠爱的妃子的住所。
邵君出生于此,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妃子的女儿。
那名妃子未能熬过生产的磨难。
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称之为她的家,那么这里就是了:它精雕细琢的天花板,巨大、舒适的床铺,以及那些女人们学习符合她们身份的艺术时的喃喃细语。
那些艺术包括舞蹈、乐器、刺绣,甚至如何走路、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充满魅力地微笑。
她也需要学习这些。
但不久之前,她那几乎不属凡世的美丽舞姿和杰出的杂技天赋吸引了年轻的正德皇帝的注意,他立即就利用她来勘察他的敌人,或者耍把戏给他的朋友们看。
邵君小心地爬上那张她和另两个人共享的大床,尽力不吵醒张,但是没能成功。
张睡意蒙眬地说:“总有一天你会爬到我们床上来,然后把我们都吓死。
” 君轻声笑着:“不,我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的。
” 张打着呵欠给她让出位置,困倦地枕在朋友的肩膀上。
在被灯笼光照亮的黑暗中,邵君微笑了。
邵君很早就被正德皇帝钦点出来担任工作(三岁的时候,皇帝让她翻跟头),这让其他嫔妃一直对她充满敌意。
有的嫔妃半遮半掩,也有的不那么含蓄。
她的出身比较卑微,在这正德置于三宫中、只能远远遥望天子的数百号人中,晋升得却相当迅速。
因此,当张,一名大殿侍卫的女儿,有着小小的、束紧的胸部和小脚,端庄的仪态,贝壳般白皙的皮肤和温柔的大眼睛,一个典型的中国完美女性,一年前被带到这宫中时,邵君以为她也会像别人一样。
但当张听说了邵君之后,她就找到了她。
以她身为皇帝最宠爱的密探的经验,邵君对于朝臣和其他嫔妃的虚情假意特别警惕。
最开始,她极为小心、滴水不漏。
张似乎能够理解,并没有强求。
但慢慢地,有些奇怪的事发生了。
皇帝的首肯能够如同字面意义一般定夺一个人的一辈子,是荣华富贵,还是死无葬身之所。
在向皇帝争宠时,她们明明应该是彼此的对手。
但张却似乎从来不这么觉得。
一次,她的一句不假思索的评价狠狠刺痛了邵君。
那时,邵君刚刚在宫廷的缎带舞比试中击败了她。
“没人能做出像你那样的动作,邵君,”她崇拜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对你只能远观景仰,望尘莫及。
” “但你那么美丽,张!”君指着她自己从未缠裹的胸和脚,抗议道。
正德不许她缠足和裹胸。
你太擅长躲藏和攀爬了。
他这么说。
邵君知道,没有缠足、裹胸,男人永远也不会觉得她迷人的。
“我永远也没法像你一样,永远!” 张笑起来了。
“你的舞姿就像兔子,而我的笑容就像蝴蝶。
”她说道,这两种动物在中国被尤为喜爱。
没有哪只特别宝贵,也没有哪只比另一只更好。
它们只是有所不同。
她能明白。
邵君这样想着。
她不得不转过头去,以免任何人看到她眼中突然涌出的喜悦的泪水。
自那时起,她们就成为了姐妹。
而现在,张躺在她身边时,一如往常地开口说道:“告诉我。
” 邵君说着这些故事的时候,同时感到欢喜和痛苦,因为她知道、张也知道,稍年长一些的张绝不可能经历这些事情。
蝴蝶像只蟋蟀似的被关在笼中,但兔子却是自由的。
曾经,邵君想要带张去看她的世界。
那是几个月以前,不到三更——到三更时,鼓楼上的士兵就会敲响十三记铜鼓,唤醒仆人们为每日朝见做准备。
当然,嫔妃们不用起床,但宦官、朝臣和他们的下属都必须做好准备,在四点与皇帝会面。
这样的朝见在一天中还会再进行两次。
当然,正德憎恨这个安排。
他提出改成在晚上进行一次朝见,事后附带一场盛宴。
但似乎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事事如愿,这个主意受到了激烈地反对。
邵君知道,想要偷偷溜出寝室四处探索,这是最佳的时机。
因此她和张在这时候溜了出去。
很多宦官们都在他们的岗位上睡着了,而邵君很轻易就能把其他人骗走、让他们分心。
她们溜上来大街,张抬头看见了布满星星的夜空——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
过去,即便嫔妃们被准许在夜晚外出参加庆典或其他活动,她们周围的灯笼也会将羞怯的星辰遮掩。
她们一路前行。
这许多年来,邵君已经找到了很多隐秘的小道,但张太害怕,不敢从结满的蜘蛛网和尘土间爬过去。
邵君劝着她、保证说自己会帮助她的,但张的脸变红了,单单说了一句:“我的脚。
” 邵君感到好像被人当头一棒。
她已经忘记了嫔妃们和出身高贵的女人们被缠足的另一个理由:这样她们就不会跟着其他男人逃跑了。
她难受地看着她的朋友,注视着她自己的哀伤倒映在张柔和的双眼之中。
她们回去了,而邵君再也没有提议出来过。
但张决心要逃离她贵重的牢笼,哪怕仅仅是从邵君的冒险中感受到一点点自由。
就像现在,她总是让她的朋友讲述自己的故事。
邵君侧耳倾听,床上的其他女孩似乎都熟睡着。
其中有一个甚至轻轻地打着鼾。
她开始在张的耳边轻声低语: “今晚,”她说,“我在豹房表演了。
” “有豹子的地方?”张问道。
正德皇帝下令将豹房兴建于紫禁城之外,用来存放异国动物,进行杂技和舞蹈表演。
那里也是用来偷听的好地方,但邵君没把这点说出来。
这会把张置于危险之中,而她绝不会这么做。
“今晚没有豹子,”邵君答道,“但有两头狮子和七头老虎。
” 张咯咯笑起来,用手捂着嘴抑制笑声。
“这里也有七虎哦。
”她说。
邵君没有笑。
朝廷中,最重要、最有权势的宦官们被合称为八虎。
就像张指出的,现在他们只有七人了。
邵君曾被迫观看,他们的领袖刘瑾被极度痛苦地处死的过程。
就连张也不知道这一点。
“确实。
”邵君只简单附和了一句,随后继续详细地描述着那些大猫强有力的肌肉,它们美丽的金色、橘色与黑色相间的毛皮,朝臣们有多怕它们,而让邵君直接在它们的笼子上进行表演又有多么刺激——她随时都可能直接跌入笼子里去。
“还有昨晚呢?”昨晚张睡着了。
因此邵君热心地告诉她,昨晚,正德进行了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
“我知道你听说过的。
”她逗弄她。
张玩笑地打了她一下:“但我又没见过。
” “好吧。
他昨晚又下令布置好集市,而这次,他假扮成一个从南京来的平民。
他让马永成扮成卖蘑菇的农民,而魏斌则是卖丝绸的。
” 让这些位高权重的大人们假扮成普通的农民和小贩,而他,他本人,装成个寒酸的顾客,能给正德带来极大的乐趣。
但被迫扮演这些角色的朝廷官员们可不这么觉得——尤其是八虎的成员们。
“那高凤呢?” “他卖蜗牛。
” 张把脸埋在枕头里捂住自己的笑声。
邵君也咧起嘴。
她必须承认,这些傲慢的人咬着牙忍耐这些“演出”的场景绝对值得一看。
“那你呢?” “我?我帮忙煮面条。
” “再告诉我一些。
”张愉快地轻叹着。
她的双眼又合上了。
邵君照做了,讲了更多这好笑的场景,轻柔、絮絮地说着,直到张的呼吸变得缓慢而平稳。
但邵君没办法轻易入睡。
正德告诉她,他想要了解北边正在发生的战斗,以击退蒙古军阀达延汗所领导的袭击。
“也许我会私下进行,”他这么说着,在说话的同时继续琢磨着这个点子,“我需要另起一个名字——就像我在扮集市商人时那样!你觉得‘朱寿’这个名字怎么样?” “如陛下所言,我敢肯定这是个好名字!”她急急地回答。
但他还没说完:“我会需要我聪明的小猫咪邵君在营帐旁边漫步,替我去探听。
”他对她说。
尽管想来,如果跟随皇帝上战场,邵君所处的境地将会比张更加危险,但她却忍不住认为事情会截然相反。
张并不愚蠢,但她的本性中却有邵君自己从未有过的无辜和脆弱。
正德有时会把邵君叫做猫,她似乎总能稳稳落地。
八虎正在密谋着什么,而嫔妃中则充满诡计和欺骗。
她不想将张一人丢在这其中。
但她没有选择——这次没有了。
如果天子要她在自己对蒙古人进行攻击时陪伴左右,她就不得不去。
邵君注视着她朋友平静的睡脸,一股激烈的保护欲在她心中升起。
我在此立誓,张,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
如果你需要我,我便会来。
不管为什么、不管在何处——我会为你而来,保护你的安全。
无论有什么威胁、无论有什么圣旨,只要你需要我,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我为你而来。
永远。
不知怎的,睡梦中的张仿佛听见了邵君那在心中的低语。
她微笑起来。
———————————————————— (1) 原文为“Saimon”,意即鲑鱼——编者注。
(2) “那格拉”:一种印度鼓;“萨兹琴”:一种弹拨乐器。
——译者注 (3) 伊斯兰服饰。
——译者注 (4) 对巫毒教中多个神灵的称呼。
——译者注 (5) 巫毒教中的死之神灵。
——编者注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咸鱼飞升重关暗度
- 起点文男主是我爸林绵绵
- 仙君有劫黑猫白袜子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怀了队友的崽怎么破西山鱼
- 看见太子气运被夺后花里寻欢
- 心意萌龙扣子依依
- 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01入学篇(上)佐岛勤
- 首辅大人重生日常/今天也没成功和离时三十
- 圣武星辰乱世狂刀
- 独行剑司马翎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御佛o滴神
- 史上第一祖师爷八月飞鹰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全星际都等着我种水果一地小花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极品修真狂少墨世
- 武极宗师风消逝
- 你们练武我种田哎哟啊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网恋同桌归荼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鱼游入海西言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游弋的鱼乌筝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循规是笙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红楼大贵族桃李不谙春风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情敌五军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学长在上流麟
- 离心ABO林光曦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他们今天也没离婚廿乱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无可替代仟丞玥
- 哏儿南北逐风
- 摆烂式带娃后我火爆全网谷一不胖
- 情终孤君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眼泪酿宴惟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游弋的鱼乌筝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循规是笙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阻流三眠柳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离心ABO林光曦
- 有只海豚想撩我焦糖冬瓜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竹木狼马巫哲
- 撒谎精发芽芽
- 穿女装被室友发现了怎么办linglongzizizi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
- 听说我很穷[娱乐圈]苏景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