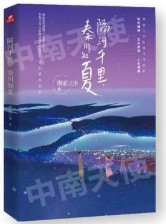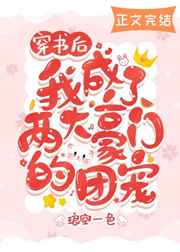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5章 行于天地,再遇自己(2/3)
才偶然得知:她们都是义工。
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在法鼓大学召开大会期间,前来担任义工,从凌晨到深夜,马不停蹄,像走马灯似的忙得团团转,本单位所缺的工作时间,将来会在星期日或者假日里一一补足。
她们不从大会拿一分钱。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是非常感人吗? 我没有机会同她俩细谈她们的情况,她们的想法,她们何所为而来,以及她们究竟想得到些什么。
即使有机会,由于我们的年龄相差过大,她们也未必就推心置腹地告诉我。
于是,在我眼中,她们就成了一个谜,一个也许我永远也解不透的谜。
在大陆上,经济效益,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个人利益,是颇为受到重视的。
我绝不相信,在台湾就不是这样。
但是,表现在这些年轻的女义工身上的却是不重视个人利益。
至少在当义工这一阶段上,她们真正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
对于这两句话,我一向抱有保留态度。
我觉得,一个人一生都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某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在某一件事情上,暂时做到,是可能的。
那些高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往往正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家伙。
然而,在台北这些女义工身上,我却看到了这种境界。
她们有什么追求呢?她们有什么向往呢?对我来说,她们就成了一个谜,一个也许我永远也解不透的谜。
这些谜样的青年女义工有福了! 1999年5月9日 重返哥廷根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又回到这个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小城里来了。
我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难道是一个梦吗?我频频问着自己。
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这毕竟就是事实。
我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
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想到了;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事,想到了。
我那些尊敬的老师,他们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眼前。
我那像母亲一般的女房东,她那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我眼前。
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
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我眼前来。
一霎时,影像纷乱,我心里也像开了锅似的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一停,我飞也似的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
忽然有一首诗涌现出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怎么会涌现这样一首诗呢?我一时有点茫然、懵然。
但又立刻意识到,这一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我的心灵深处,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
我曾在这里度过整整十年,是风华正茂的十年。
我的足迹印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
我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
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我的心灵上打上永不磨灭的烙印。
我在下意识中把它看作第二故乡,不是非常自然的吗? 我今天重返第二故乡,心里面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感情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重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似欣慰,似惆怅,似追悔,似向往。
小城几乎没有变。
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的铜像,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
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
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声呼哨,飞上了后面大礼拜堂的尖顶。
我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
我们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
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
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是当年的那一位,我仿佛昨天晚上才在这里吃过饭。
广场周围的大小铺子都没有变。
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
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
总之,我看到的一切都同原来一模一样,我真的离开这座小城已经三十五年了吗? 但是,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江山如旧,人物全非。
环境没有改变,然而人物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我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一些人,有的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过了一百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
那些计算起来还没有这样老的人,我也不敢贸然去问,怕从被问者的嘴里听到我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我只绕着弯子问上那么一两句,得到的回答往往不得要领,模糊得很。
这不能怪别人,因为我的问题就模糊不清。
我现在非常欣赏这种模糊,模糊中包含着希望。
可惜就连这种模糊也不能完全遮盖住事实。
结果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我只能在内心里用无声的声音来惊呼了。
在惊呼之余,我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
首先我要去看一看我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
我知道,我那母亲般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早已离开了人世,但是房子却还存在。
那一条整洁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
从前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来洗刷人行道,现在这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才洗刷过似的,躺下去打一个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尘土。
街拐角处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窗子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
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
我走到我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楼我那一间房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
我蓦地一阵恍惚,仿佛我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来了。
我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
我没有用钥匙去开门,因为我意识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外一家人了。
从前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恐怕早已安息在什么墓地里了,墓上大概也栽满了玫瑰花吧。
我经常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却是人去楼空了。
我在这里度过的十年中,有愉快,有痛苦,经历过轰炸,忍受过饥饿。
男房东逝世后,我多次陪着女房东去扫墓。
我这个异邦的青年成了她身边的唯一的亲人。
无怪我离开时她号啕痛哭。
我回国以后,最初若干年,还经常通信。
后来时移事变,就断了联系。
我曾痴心妄想,还想再见她一面。
而今我确实又来到了哥廷根,然而她却再也见不到,永远永远地见不到了。
我徘徊在当年天天走过的街头,这里什么地方都有过我的足迹。
家家门前的小草坪上依然绿草如茵。
今年冬雪来得早了一点,十月中,就下了一场雪。
白雪、碧草、红花,相映成趣。
鲜艳的花朵赫然傲雪怒放,比春天和夏天似乎还要鲜艳。
我在一篇短文《海棠花》里描绘的那海棠花依然威严地站在那里。
我忽然回忆起当年的冬天,日暮天阴,雪光照眼,我扶着我的吐火罗文和吠陀语老师西克教授,慢慢地走过十里长街。
心里面感到凄清,但又感到温暖。
回到祖国以后,每当下雪的时候,我便想到这一位像祖父一般的老人。
回首前尘,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我也没有忘记当年几乎每一个礼拜天都到的席勒草坪。
它就在小山下面,是进山必由之路。
当年我常同中国学生或德国学生,在席勒草坪散步之后,就沿着弯曲的山径走上山去。
曾在俾斯麦塔,俯瞰哥廷根全城;曾在小咖啡馆里流连忘返;曾在大森林中茅亭下躲避暴雨;曾在深秋时分惊走觅食的小鹿,听它们脚踏落叶一路窸窸窣窣地逃走。
甜蜜的回忆是写也写不完的。
今天我又来到这里,碧草如旧,亭榭犹新。
但是当年年轻的我已颓然一翁,而旧日游侣早已荡若云烟,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远走高飞,到地球的另一半去了。
此情此景,人非木石,能不感慨万端吗? 我在上面讲到江山如旧,人物全非。
幸而还没有真正地全非。
几十年来我昼思夜想最希望还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我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居然还都健在。
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是八十六岁。
一别三十五年,今天重又会面,真有相见翻疑梦之感。
老教授夫妇显然非常激动,我心里也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们围坐在不太亮的电灯光下,杜甫的名句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四十五年前我初到哥廷根我们初次见面,以及以后长达十年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
那十年是剧烈动荡的十年,中间插上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能过上几天好日子。
最初几年,我每次到他们家去吃晚饭时,他那个十几岁的独生儿子都在座。
有一次教授同儿子开玩笑:“家里有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到学校去又可以张扬吹嘘一番了。
”哪里知道,大战一爆发,教授的儿子就被征从军,一年冬天,战死在北欧战场上。
这对他们夫妇俩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
不久,教授也被征从军。
他心里怎样想,我不好问,他也不好说。
看来是默默地忍受痛苦。
他预订了剧院的票,到了冬天,剧院开演,他不在家,每周一次陪他夫人看戏的任务,就落到我肩上。
深夜,演出结束后,我要走很长的道路,把师母送到他们山下林边的家中,然后再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
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那一座漂亮的三层楼房里,只住着师母一个人。
他们的处境如此,我的处境更要糟糕。
烽火连年,家书亿金。
我的祖国在受难,我的全家老老小小在受难,我自己也在受难。
中夜枕上,思绪翻腾,往往彻夜不眠。
而且头上有飞机轰炸,肚子里没有食品充饥,做梦就梦到祖国的花生米。
有一次我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报酬是几个苹果和五斤土豆。
回家后一顿就把五斤土豆吃了个精光,还并无饱意。
有六七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学习、写论文、参加口试、获得学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
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东西,哪一点不饱含着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 现在我们又会面了。
会面的地方不是在我所熟悉的那一所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
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赠给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一所养老院里了。
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
据说,饭食也很好。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
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人的耳朵。
他们不是来健身的,而是来等死的。
头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饭、聊天,第二天早晨说不定就有人见了上帝。
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
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伶仃,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授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
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高兴,我无法加以描绘。
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
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
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
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
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常吃的食品。
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地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
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
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
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
在他们前面,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 我心里陡然凄凉起来。
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待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待些时候。
但是,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站起来,想告辞离开。
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我只好又坐下。
最后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们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
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样子是难舍难分。
此时我的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
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
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了哥廷根。
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
坐在车上,同来时一样,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错综纷杂。
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凑到我的眼前来;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体多了。
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有一个特别清晰、特别具体、特别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
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
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 1987年10月在北京写完 满洲车上[1] 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太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
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
这几乎是唯一的可行的路;但是有麻烦,有困难,有疑问,有危险。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这里有危险。
过了“满洲国”,就是苏联,这里有疑问。
我们一心想出国,必须面对这些危险和疑问,义无反顾。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仿佛成了那样的英雄了。
车到了山海关,要进入“满洲国”了。
车停了下来,我们都下车办理入“国”的手续。
无非是填几张表格,这对我们并无困难。
但是每人必须交手续费三块大洋。
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我们真有点舍不得。
既要入境,就必需缴纳,这个“买路钱”是省不得的。
我们万般无奈,掏出三块大洋,递了上去,脸上尽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更是特别小心谨慎,前去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
幸而没有出麻烦,我们顺利过了“关”,又登上车。
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个个谨慎小心,说话细声细气。
到了夜里,我们没有注意,有一个年轻人进入我们每四个人一间的车厢,穿着长筒马靴,英俊精神,给人一个颇为善良的印象,年纪约莫二十五六岁,比我们略大一点。
他向我们点头微笑,我们也报以微笑,以示友好。
逢巧他就睡在我的上铺上。
我们并没有对他有特别的警惕,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旅客而已。
我们睡下以后,车厢里寂静下来,只听到火车奔驰的声音。
车外是大平原,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去看,一任“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直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我正朦胧欲睡,忽然上铺发出了声音: “你是干什么的?” “学生。
”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北京。
” “现在到哪里去?” “德国。
” “去干吗?” “留学。
” 一阵沉默,我以为天下大定了。
头顶上忽然又响起了声音,而且一个满头黑发的年轻的头从上铺垂了下来。
“你觉得‘满洲国’怎么样?” “我初来乍到,说不出什么意见。
” 又一阵沉默。
“你看我是哪一国人?” “看不出来。
” “你听我说话像哪一国人?” “你中国话说得蛮好,只能是中国人。
” “你没听出我说话中有什么口音吗?” “听不出来。
” “是否有点朝鲜味?” “不知道。
” “我的国籍在今天这个地方无法告诉。
” “那没有关系。
”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的国籍了,同时也就知道了我同日本人和‘满洲国’的关系了。
” 我立刻警惕起来: “我不知道。
” “你谈谈对‘满洲国’的印象,好吗?” “我初来乍到,实在说不出来。
” 又是一阵沉默。
只听到车下轮声震耳。
我听到头顶上一阵窸窣声,年轻的头缩回去了,微微地叹息了一声,然后真正天下太平,我也真正进入了睡乡。
第二天(9月2日)早晨到了哈尔滨,我们都下了车。
那个年轻人也下了车,临行时还对我点头微笑。
但是,等我们办完了手续,要离开车站时,我抬头瞥见他穿着笔挺的警服,从警察局里走了出来,仍然是那一双长筒马靴。
我不由得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
回忆夜里车厢里的那一幕,我真不寒而栗,心头充满了后怕。
如果我不够警惕顺嘴发表了什么意见,其结果将会是怎样?我不敢想下去了。
啊,“满洲国”!这就是“满洲国”! 游兽主(pa?upati)大庙 我们从尼泊尔皇家植物园返回加德满都城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当年铁甲动帝王步帘衣
- 逢场入戏宁远
- 吧唧一口吃掉你一口时光
- 没人要的白月光酒几徐
- 悍妇她来抢男人了金珠玉豆
- 糖多梨
- 最强游戏架构师指尖的咏叹调
- 营养过良芥菜糊糊
- 穿成万人迷的炮灰竹马妾在山阳
- 刀客传奇戊戟
- 婚途脉脉笛爷
- 学完自己的历史后我又穿回来了荔箫
- 儒道至圣永恒之火
- 苗家少女脱贫记潇湘碧影
- 锦鲤大佬带着空间重生了浮世落华
- 当天才遇上穿越女/天才的自我修养苏家木偶
- 大将军和长公主洬
- 执刑者康静文
- 纯阳剑尊一任往来
- 有朝一日刀在手退戈
- (综漫同人)当人类最强转生成狗老肝妈
- 穿成霸总拐走炮灰昔我有梦
- 霸总的小熊软糖成精啦郑西洲
- 我辣么大一个儿子呢归途何在
- 梦魇图鉴收集记录[无限流]酉时火
- 泠泠听春雨(1v1 h)卷心菜
- 天灾前崽崽上交了种植空间秃猫追毛球
- 失控雪山北途川
- 被分手后,乖绵羊爆改狼崽玩强爱疯修半缘
- 川崎浮吞
- 我能看穿诡异附身大侠戴草帽
- 重生后从网红到娱乐圈神豪花雨无忧
- 大乾废太子,皇帝跪求别造反凌御天下
- 装A可耻[娱乐圈]游衷
- 涅槃·小凤凰太磨人(简)花相芍芍
- 予你独钟愚礼
- 气运系统:我以残躯镇诸国!迷相生海月i
- 听我的[骨科]屁屁果
- 残荷(bg1V2)瑶台月下
- 小农民的千年鬼妻西门五哥
- 清穿之四福晋只想种田蒹葭是草
- 雪里遇晴天兔七林
- 我在贵族学院当班长[穿书]高塔女巫
- 医宝双修之我是大魔王熵烬回声
- 我!系统!懂?!云月六年
- 全球SSS级警告,龙神出狱了!莫语听风吟
- 我的同学是兵王与泉
- 列克星敦号舰队指挥官太平洋萌新
- 都市异能之凌霄传奇章台杨柳007
- 快穿攻略:赖上病娇男主温小受
- [快穿]每个世界遇到的都是变态不要有杀心
- 特种兵之龙行天下疯子周
- 余温(纯百)蟹黄堡不好
- 绝对暧昧(高干1v1h)层林尽染
- 泠泠听春雨(1v1 h)卷心菜
- 我真没有画你的春宫一个珍惜xp的小女孩
- 采薇(产乳 NPH)霍饭饭
- 装b失败后(abo 父子盖饭 高h)绣刀
- 秘书长的崛起之路一战封神
- 听雨的声音小花喵
- 艳鬼压床好佳哉
- 袚灾祛秽【蛇X人,兄弟3PH】城南大蘑菇
- 指挥使大人的娇软弟媳(糙汉 伯媳 古言高h 1V1)花思燕
- 全喵界都在等我破产娜个小作家
- 豪门嗲精变小哑巴后龄寻
- 黑屋警告!万人迷反派竟是我自己薄荷味的咕呱
- 女官韵事-续acgp
- 农家“乖”夫郎梧南风
- 猫猫警官花秋月
- 重生之妖妃你中计了gl顾家七爷
- 他的占有欲浮四水
- 徐總他是自願的【限】午盏
- SólfallKi
- 秋雨有来信(校园 1v1 h)树耳
- 穿越进黄油的我今天抽到了什么马赛克?粉红美丽
- 软硬皆湿 NPH没有尾巴
- 穿成香饽饽后我在星球挑丈夫羽痕
- 豪门嗲精变小哑巴后龄寻
- 渣O爱我金新
- 捡到对家A的崽后被迫同居公子欢
- 把月亮带回家乱曲
- [综漫] 当双黑被妮妮抚养明兮子
- 不小心钓到竹马校草爱睡觉的江楼
- [综漫] 在虚圈修炼成精后牛奶燕麦不放糖
- 重生70:让你守门,你整了个蘑菇云?历史小尘埃
- 我在迪迦世界里养怪兽全秋包邮
- 从异界开始的300直播系统落魄星尘
- 元帅他总想谋反孤纵
- 烈焰朱棠怎吃香菜
- 社恐受和龙傲崽娃综爆红庭芜
- 夜幕之下瓦松绿
- 穿书后觉醒反派雇我剧透顾沐黎
- 影帝成天和我飙演技[娱乐圈]看朱忽成碧
- 哥哥还想往哪儿跑吾七柚
- 隔壁大佬总在觊觎我钩山
- 带着电脑系统去古代开工厂查理富不豪
- 纯属故意荆棘小花
- 坠落岛屿的晴天清悦天蓝
- 影后钓系O对我预谋已久公子幸川
- 为了避难嫁给病秧子后喵家酸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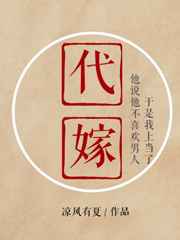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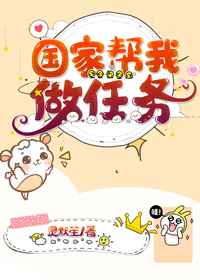
![恶毒男配不争了[重生]](https://www.nothong.com/img/59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