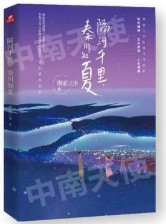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八节(2/3)
近米兰时才醒过来。
我的耳朵发胀,有点痛。
我们毕竟是夜里驶过戈特哈尔德山口的,我感觉到海拔高度的差别。
我哈欠连天,那种耳聋的感觉终于随着一声响消失了。
意大利艳阳高照,百花盛开,在这个可爱的南方世界,我每进入一公里就越幸福。
在热那亚我们等了很长时间。
卧铺车厢是这趟火车的最后一节,停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黑墙上往下淌着水。
后来火车终于动起来了。
卧铺车厢的乘务员清理我的床。
当我们缓缓地驶出热那亚时,我坐在窗前,喝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
只见到很大的船停在灰灰的船坞里。
这里的码头跟铁轨挨得很近。
俄顷我就看到海了。
从那里开始我一路上几乎都在看它,直到边境。
火车沿着意大利的海岸线行驶。
我看海上的船只,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我看到沙滩上人很多,我又看到了棕榈树、桉树、橙子树和五彩缤纷的花卉。
这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停,许多人上上下下,但卧铺车厢里客人很少。
我又感觉到,我这一生中从没体验过我对昂热拉产生的这种感情。
我们俩都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
我不知道,卡琳会作何反应,我的痛会如何发展,我的案子会有何结果。
我只知道,我正去见昂热拉的途中,这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行驶的旅程对我就像是一场快乐的梦。
我非常渴望能再听到昂热拉的笑,因为我爱她的笑。
我想,为了补偿人类生活的所有忧愁、艰难和痛苦,上帝给了人类三样东西:笑、睡觉和希望。
当这里的山脊和岩石越来越突兀地从海里钻出时,我们仍然在不停地穿越隧道。
我看到隧道入口处挂有牌子,所有的隧道都有名字。
一会儿之后,我放弃了数数。
隧道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49 在尼斯的机场上我们曾经跑向对方——越跑越快,上气不接下气。
在文提米格利亚,在这座巨大的、形象可憎的火车站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我从卧铺车厢里下来,乘务员把我的箱子送给我,我把它放在站台上。
火车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了,他们迅速消失了。
乘务员喊叫一个行李员,因此我站在那儿等。
火车旁的站台像有鬼似的一下子空了。
太阳火辣辣地燃烧。
我看到瘦削、失落的昂热拉站在很远的地方,在火车头附近。
开始我只看到她的红得发亮的头发,后来我认出了她。
昂热拉身着蓝上衣和白裤子。
她也看到了我。
但是她停住不走,我也停住不走。
事后我们谈起过这一瞬间,问对方为什么我们会呆住了,只是凝视着对方。
昂热拉说:“我已在站台上站了几个小时。
我是九点开车离开戛纳的,老怕来晚了。
这天早晨我的举止像个机械的木偶,不像一个人。
当我后来看到你时,我根本动弹不得。
我简直相信我要瘫痪了。
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
但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跑向你、拥抱你、吻你。
我无法离开原地。
我的向往和我的欢乐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变得如此巨大,当我终于看到你时,当我本来应该高兴时,我反而无比伤心了。
这是最奇怪的。
对,我心情悲伤,非常严肃,亲爱的。
” 我同样如此。
我不能理解,今天还不能。
但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文提米格利亚那座外形可憎的边境火车站的站台上,太阳火辣辣的,我非常严肃。
我连伸手打招呼都不能,昂热拉也一动不动。
一个意大利行李员推着车过来了。
我把我的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放到车上。
他说,他在出口处等我。
他推着他的车子,我跟在他身后,像木头人似的,冷冷地无所适从,跌跌绊绊。
昂热拉仍然不动。
我沿着长长的火车往前。
行李车消失在一架下行的货梯旁。
我继续走啊走。
我来到了昂热拉身边。
她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又克制。
站台上只剩下了我们,阒静无声。
我们四目相对。
我又一次看到,在昂热拉棕色的大眼里我非常微小。
我们不讲话。
我们默默地拥抱,用尽全力抱紧,拥抱了很长时间。
昂热拉抓起我的手,我们缓缓地沉默地走向通地下通道的台阶。
过道在铁轨下面,通向火车站大楼,里面非常脏,有来苏儿的臭味。
我们继续前行。
现在,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对望。
我们仍然是沉默严肃。
我们沿着另一道台阶上去,穿过一道栏杆和一个厅,来到站前广场上,昂热拉的车停在那里,搬运行李的行李员也等在那儿。
下午的这个时辰,烈日当空,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家家窗户紧闭,木制窗棂或白或绿。
火车站对面有一家酒店,人行道上有几张桌子,它们属于一家咖啡馆。
一只毛蓬蓬的狗贴着墙趴在那里。
这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
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面,为我打开她旁边的车门。
那一刻我想到了死。
我想,它比爱情更强大,它会找上每个人,结束一切,包括最伟大的爱情,我们对此必须忍受。
当我上车时,我非常顺从。
我再没去过文提米格利亚。
50 昂热拉一如往常把车子开得很稳很平静。
我们来到意大利的海关,然后来到法国海关。
官员们站在露天里,他们也非常热。
他们穿着衬衫和裤子工作,他们的衬衫上汗斑点点。
那些官员非常有礼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
无论是在意大利一边还是在法国一边,官员们都跟昂热拉调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没有反应时,他们就悄悄地停止了。
我们开上一条高速公路,昂热拉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交费。
公路上的空气似乎在沸腾。
我脱去上装,扔在后座上,解开领带。
我们还是没有交谈。
昂热拉开车很快,大约五分钟后她踩刹车,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停下来。
接下来的瞬间我们相互拥抱接吻,那么猛那么使劲地搂着对方,甚至带着绝望,好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保护和支撑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终于能开口交谈了。
“昂热拉” “我亲爱的,我真高兴。
” “我也是。
” 我们又狂吻。
当我们讲话时,我们相互在脸上、额上和眼睛上吻了无数次。
我们长时间地吻对方的唇。
“你在我身边,终于来了,罗伯特。
我已经想过,我没有你会失去理智。
” “咱们在一起。
我现在就留在这儿。
” “噢,罗伯特,”她说“在那个可怕的火车站上,当时我突然起了一种可怕的念头。
” “什么念头?”我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脸。
“我我想,只有一件事能分开咱们俩。
这一件事会找上每一个人,也终有一天会找上我们。
那时,咱们就被分开了。
那时,一方就得孤独地生活下去。
我想过,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追随你而去,因为孤独生活我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的爱情再也不能够了。
” 原来她也想到了此事 “不过现在,”她说“它过去了。
现在一切都美妙神奇。
”她笑“咱们在一起,罗伯特!咱们又在咱们的天堂里了!”她这下变了个人。
她曾经让我觉得是那样忧虑,而她现在是如此自由、如此开心、如此愉快。
“你饿吗?什么也别讲。
当然你饿。
我,我饿死了!我今天早上激动得连杯咖啡都没喝。
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开车回家,好吗?” “行,昂热拉。
” “我认识这里一家很好的饭店,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咱们开车去那儿。
你觉得合适吗?” “我什么都合适。
”我说“开车吧,昂热拉。
” 她又发动了,内胎摩擦,她发动得那么突然。
我回头望。
我们身后扬起了白色的灰尘。
我们旋下车窗,打开了推顶。
我坐在那里,从侧面定睛望着昂热拉,心里充满无比的骄傲,这女人像我爱她一样爱着我。
不,不是骄傲,我充满了感激,非常大的感激,感激生活、上帝或谁负责此事的,感谢他让我们相遇了。
我看昂热拉的双手。
我看到那浅色的色斑。
它变得更白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昂热拉的手这期间被太阳晒得更黑了,我想。
“咱们去艾泽。
”昂热拉说。
51 要去艾泽,我们得离开高速公路。
沿着陡峭的海岸有三条路。
昂热拉开上了中间的那条,峭壁中路,它满是灰尘。
然后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灰尘更厉害的路上,它陡直地上升。
艾泽村庄在高处,在一个山顶上面。
山峰下面,在村头,有一座停车场。
我们把车停在这里,沿着一条陡峭的胡同继续上行。
两侧岩壁高耸。
房屋依山而建,老掉了牙。
一座支撑着另一座,狭窄的胡同那么陡,一家的房门常跟邻房的窗户位于同样的高度。
这里的一切一定是中世纪修建起来的。
下面的停车场旁边是纪念品商店和一堵墙,倚墙摆放着许多幅画。
我看到那些画家坐在画前等候着买主。
房子里有许多店铺——鞋店、裁缝店和食品店。
最多的是工艺品商店。
我看到旧铜罐、圣母像、酒杯、雕刻品和许多花边台布。
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在街头卖的。
一切都非常小、非常挤、非常陡,是一座侏儒城市。
岩壁之间很凉爽。
在这上面生活的当地人肯定不足五十人,顶多六十人。
这是游客们的郊游目的地。
小胡同七拐八弯。
昂热拉和我手拉手走着。
许多男人在他们的店门外冲我们微笑,也有女人。
这些人都客客气气。
那条小胡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
我们站在一座大楼前,它完全保持着村庄的风格。
“这里就是了。
”昂热拉说“这是‘金山羊’。
” “金山羊”店内满是珍贵的古董。
我们穿过许多房间,来到一个布置时髦的餐厅。
这里面和那外面相隔数百年。
我们在窗边找到一张桌子,它还空着。
饭店老板让我们点菜。
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依然手拉着手,望着外面。
我远远地眺望大海,过去,我从没从地球上这么远的地方眺望过。
好像我看到的是整个地中海。
它跟天空一样湛蓝,远处海天交融。
我们下面延伸着第二条沿海岸的路,那条小科林斯路。
汽车小小的。
岩壁间有座游泳场,那里的人还要小得多。
“这里漂亮不漂亮?” “漂亮,昂热拉。
”我说。
“我要让你看一切特别漂亮的东西。
我是这么打算的。
” 我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吻她。
她的嘴唇张开来。
我让第二只胳臂也箍着她。
她用她的胳臂缠着我。
昂热拉低声呻吟。
“喂,卢卡斯先生!” 一个女人的声音。
昂热拉和我突然分开来。
我抬起头来看。
我面前站着一男一女——德赖尔夫妇。
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赖尔夫妇,德赖尔先生和德赖尔夫人,卡琳的朋友。
伊尔瑟-德赖尔有可能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女人,身材苗条,不能算不漂亮,但嘴巴周围有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的表情。
德赖尔要年长得多,头发短短的。
这两个人过分夸张地穿着时髦的夏装。
他们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
“我们绝对不想打扰您,”伊尔瑟-德赖尔说“我们正准备走。
当我们经过您的桌旁时,弗朗茨说,这不是卢卡斯先生吗。
你好吗,卢卡斯先生?” 我站起身。
“谢谢,”我说“我很好。
” “这看得出来。
”德赖尔先生说,朗声大笑。
伊尔瑟-德赖尔盯着昂热拉。
昂热拉也迎视着那目光。
出现了一阵冷场。
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德赖尔夫妇冷冰冰地站着。
“我来介绍一下”我非常含糊地讲出名字,昂热拉的名字。
伊尔瑟-德赖尔微笑地脱口问道:“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我叫黛尔菲娅,德赖尔夫人。
”昂热拉说,同样微笑着,讲的是德语,非常清楚。
“昂热拉-黛尔菲娅。
” “很高兴认识您,黛尔菲娅夫人。
”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德赖尔夫人。
” “您认识卢卡斯先生?他可从来没讲到过您!”伊尔瑟说。
这情形让她丈夫很不舒服。
“不要这样,”他说“不要这样,伊尔瑟。
”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遇上您,这可真滑稽,卢卡斯先生,是不是?您知道,我们来这里旅游。
我们住在胡安派恩斯。
我丈夫今年提前休假了。
我们还要呆十四天。
这里多美啊。
” “是的,”昂热拉说,仍然微笑着“不是吗?” “我们现在确实不想再打扰了”德赖尔先生催着说。
他妻子似乎不听他的。
“您知道,黛尔菲娅夫人,我们是卢卡斯先生的老熟人。
这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他妻子的朋友,尤其是我。
您不认识卢卡斯夫人吗?” “不,德赖尔夫人。
”昂热拉说。
我忍无可忍。
“我们不想耽搁你们。
遇到你们我真高兴。
”我说。
“是吗,您高兴,卢卡斯先生?”伊尔瑟问。
“这还用讲!”我说。
“这也是我的荣幸。
”昂热拉说。
“那就再见了。
”伊尔瑟说。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在偏执狂怀里撒个娇[重生]茶栗
- 她是男主好兄弟发电姬
- 杏花如梦作梅花王世颖
- 你未曾坠落星海南薄荷
- 摘星2林笛儿
- 爱豆家里有道观言朝暮
- 最强游戏架构师指尖的咏叹调
- 剑胆琴心独孤红
- 过野纵澜
- 婚途脉脉笛爷
- 学完自己的历史后我又穿回来了荔箫
- 从火影开始卖罐子剑符文
- 儒道至圣永恒之火
- 天赋是卡牌培育天泽时若
- 寄生谎言余姗姗
- 锦鲤大佬带着空间重生了浮世落华
- 大将军和长公主洬
- 神话降临如履
- 妈咪不乖:总裁爹地轻轻亲谁家mm
- 相公是男装大佬兆九棠
- 如果蜗牛有爱情丁墨
- 鹤高飞司马翎
- 贵妾之女君子迁
- 家有兽夫:发家致富好生活蛋蛋蚁
- 不想变狐狸就亲亲他愫遇
- 人在东京,猎杀噩梦驯为鹰犬
- 阿福呀(1v1amp;nbsp;amp;nbsp; h)沈尽欢
- 绝世剑帝九界散人
- 绝对掌控(woo18)多梨
- 全裸,做愛,獸人作品收集金色狂风01
- 大唐之逍遥王爷120笑话
- 春秋我为王七月新番
- 超能神警六划先生
- 最强特种兵剑韵
- 超级保镖百年一木
- 重生影后:顾少,放肆宠胡萝北呀
- 天龙八部之风流林枫风信子
- 当万人迷穿成万人嫌后(万人迷np)随机刷新npc
- 他说我有病但实在美丽[快穿]我怀
- 超神学院之猴哥传承我爱我的梦想
- 有关悖论雨升升
- 都市之布医神相师言道
- 重生娱乐圈女皇凰然若梦
- 有只猫说我是她老婆太古季叶人
- 【BG】不上床,就去死!amp;nbsp;amp;nbsp;(NP/简体)李子李
- 林宇的传奇人生格子衬衫
- 清冷魔尊恋上我决木
- 穿越之山野田间尽悠然老妖精18
- 前夫哥结婚了,新娘竟是我自己?自见山去
- 精灵最强大师一笛横晚风
- 超能力修炼指南住在云里
- 大圣传承:我的鉴宝人生开挂了勇敢猫猫冲鸭
- 神眼:捡漏极品玻璃种,女总裁馋坏了!来点烧烤
- 被家族除名,觉醒九龙护体你后悔了?银芽白菜
- 冰凰劫:医武镇归墟月幕思华
- 系统大人,你家宿主要吃糖风子风
- [综漫] 高专美少女日常佐佐末
- 不想当海贼王的剑豪大人七里晴树
- 灵巫古纪酒师公
- [综英美] 斯塔克家的父与子京鲸
- 一觉醒来成为世界唯一一位alpha(GB+NP)月桃仙人掌
- 行至彼岸(兄妹)南谯居北
- 千禧姜戈
- 请把脊骨雕成我的王座(高H、NP)妃子笑
- 南望今霄(1V2)檀东意
- 顶级暴徒(法案之后)water
- 夺梨色千夜孤舟
- 回航柚子茶
- 俗骨(强制爱 1V1 H)摸凹猫
- 我本意其实是爽一晚就走(百合abo)暮虬
- 我的系统太离谱,但真香!七宝幻梦守护人
- 都市最浪天师:我在人间斩阴阳秘书郎小张
- 唯剑独尊九界散人
- 绝世剑帝九界散人
- 嫡女要狠幺蛾子大人
- 大圣传承:我的鉴宝人生开挂了勇敢猫猫冲鸭
- [综英美] 了不起的胡安娜Aak
- 乱世军阀!我为东北王!倒立窜稀看日落
- 撰书人之我出生在90年星a辉
- 异能鉴宝:开局被女友爆头望江的黄副总
- 春秋我为王七月新番
- 新大明帝国木允锋
- 穿越军嫂之肥妻大翻身叫陈皮的橘子皮
- 【快穿】正直帥哥被惡女強姦後楠离
- 天龙八部之风流林枫风信子
- 审判倒计时[无限]落上弦
- 矩阵天王白雨涵
- 植妖界葡萄莫得糖
- 林宇的传奇人生格子衬衫
- 天团与皇冠青律
- 穿越之山野田间尽悠然老妖精18
- 饥不择食H_mark
- 来自山野的征服万峰真人
- 鬼食山野道人
- 天后A在娃综偶遇亲闺女江溶棠梨
- 死神喜欢搓麻将卡托普利
- 帝尊放肆宠:腹黑神医妃转弯
- 诡幻灵白虎大圣
- 我,京圈太子爷,外号活阎王听风弄雨
- 黄金六零:赶山打猎,把老婆宠成一枝花一缕沐光


![如何成为白月光[快穿]](https://www.nothong.com/img/10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