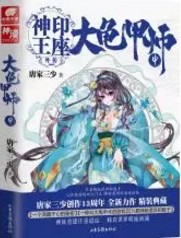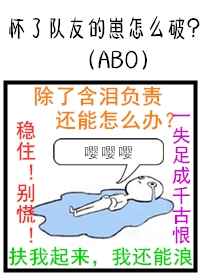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十六章 分途(2/3)
,无忧无虑。
阁中内室,烛火映着珠帘明光流转,照得两人的脸色都透出几分难得的红润来。
郗彦自案上取来针囊,回过头,但见夭绍坐在榻上,捧着卷书简,聚精会神地看着。
他走到她身边,她丝毫不为所动,只对着书简,愈发地心无旁骛。
郗彦微微皱眉,握着针囊在榻侧静站了半晌,终于出声道:“躺下吧。
” 夭绍并不理会,举高书卷,遮住脸:“做什么要躺下?” 明知故问,问得蹊跷。
郗彦默然无声,夭绍等了一会不见有人答话,又慢慢将挡在眼前的书简落下,瞥了眼郗彦手里的针囊,嫣然笑道:“我正在看医书呢。
有人说,我这些日子看了这么多医书,想来知道怎么治自己的腿疾。
郗公子大驾,今日又何来的操心?” 郗彦定定看着她,目光沉静似古井之水,波澜难兴,唯有暗潮在深处涌动,看不明晰的晦涩。
“夭绍,”他缓缓启唇,温润的笑颜一如当年对她不离不弃的清俊少年,柔声道,“躺下吧。
” 夭绍笑意凝住,眸中隐隐浮出湿润的雾气。
她微微低头,娇嗔不再,眉眼依旧是往日的温柔。
依言躺下,依言闭眸,只要是他叮嘱的。
金针刺穴,柔力通脉,此刻都不是痛,重重的心事又莫名添了一件,辨不出来由,分不出喜怒,却平白夺去了她所有的心情。
他对她如此的忽冷忽热,似曾相识。
以前是为什么?如今又是为什么?她不住思索着。
施针半个时辰的相对,两人都静气屏息,各自沉默。
待郗彦取下所有金针,夭绍睁开眼,望见郗彦额上的汗珠,下意识地便伸出手去拭。
指尖刚触碰到那冰雪般寒冷的肌肤,郗彦身体一挣,略略侧身避开。
夭绍的手顿在半空,良久,才若无其事地笑了笑,缓缓将手臂收回,又撑着胳膊坐起身,想要下榻,不料双腿如灌冰铅,沉重,僵硬,丝毫挪动不得,顿时大惊失色,瞪着身旁的人:“阿彦!” 郗彦轻垂眼眸,肤色雪白得几乎透明,此刻任珠帘光色摇闪,也无法再将他的面庞映出先前的红润。
他收好针囊,淡然一笑:“夭绍,我方才接到了东朝的密报,南蜀与殷桓私连,江州战事紧急,不得不尽快南下。
” 夭绍起伏的心绪终于自腿上的禁锢转移,此时不需细想,已然明白其中原委,盯着郗彦看了好一会,还是抑不住惊怒,冷笑道:“所以,你要舍了我独自南下?” 郗彦沉吟了片刻,抬起双目,望入她努力掩饰慌急的眼眸,慢慢道:“你腿上的剑伤虽然不深,但因先前的旧患本就未好,如今再添新伤,未免沉疴难养。
我此行南下须日夜不断赶路,纵马疾驰,等不得你乘马车。
” “腿伤!腿伤!”夭绍懊恼难当,“你能再找个好一点的借口吗!” 郗彦注视着她,半晌,微微而笑:“这里,洛都,有你舍不得的人。
” 目光相对,毫不避忌,他竟说得如此坦然。
夭绍的面庞瞬间褪去了所有的颜色,浑身冷颤——是什么逼得他如此无情,冰凉的剑刃所指,竟要这般利落地直戳她的心口?曾经在那里留下的伤痕刚刚结疤,薄纱罩着,朦朦胧胧,心肝灵慧的两人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碰触,等着它痊愈,等着它淡却。
然而此时此刻,他却要这样迫不及待,狠心将她的心伤再度撕裂,让她猝不及防、无路可逃。
“我不是……”语出唇齿,虚弱颤微,话已不成音。
不是什么?她倏地有些茫然。
殊不知烛火却照清了她眸中的情绪,从未有过的羞惭,从未有过的黯淡。
怔忡中,只听他如释重负般轻声叹了口气,淡淡道:“明知不可为,偏偏任性而为,从小到大,屡屡如是,该改了。
你留在洛都养好腿伤,再图南下,又有何不可?”他说得如此的平静,又是如此的漠然,仿佛两人中间隔着的,是万里山河、九重天阙,那样的遥不可及。
昔日的耳鬓厮磨、生死与共原来只是水月镜花,但凡一丝微风吹来,便可如约而逝。
夭绍静静地看着他,忽然轻声一笑。
这笑声太过突兀,有着透穿一切的蛊惑,趁着他微怔的神思长驱直入,清晰而又温柔地,触摸着他心底的苦和恨。
他不免微生狼狈,只是言尽于此,他也再无解释的必要,移开目光,站起身。
青衣隐没于紫纱帷幔中,没有一丝的踟蹰。
好像只有这样无情决然地离开,才能带走一帘的风月、满眸的柔情,然而步履迈出,四肢百骸无不沉哀生疼,如被冰封、如受火炙,喘息、挣扎,脱离不出,心中竭力压抑着那样激烈的情绪,让他连喉间何时涌出了腥甜也不自知—— 早知如今的离别,又何必当初义无反顾地深陷。
“阿彦,等等!”帐后蓦地扑通一声闷响,艰难的呼唤迸出唇间,终归还是牵绊住了他的脚步。
他回过身,拨开幔帐,僵立片刻,才俯身扶起无力倒地的夭绍,冰冷的指尖慢慢伸出,抹去她眼角沁出的泪珠。
夭绍唇边挽起一丝微笑,指了指一旁的雪魂花:“别忘记带走它。
” “好。
” 夭绍就势握住他的手,待要再语,郗彦却不容她开口,手指微动,点上她的睡穴。
那双明净的眼眸犹含着来不及诉诸于口的不舍,却只能就此忿忿不甘地、阖目而睡。
梦中不知人间岁月,清风吹入室中,卷起紫色绫纱,包裹住两人的身躯,柔如东山的春光。
郗彦低下头,寒凉颤抖的唇,终于碰上那温暖的柔软。
微甜,微苦,深深一吻,久久难离。
嘴角溢出的血丝沾上她的红唇,浓浓一缕,瞬间染成触目惊心的妖娆。
如花美眷,如玉容颜。
到底不如似水流年。
我给不起—— 郗彦将她抱上软榻,盖了锦被,慢慢抹去她唇上的殷红。
就此别了吧。
(四)
夜过亥时,天河明净,宵禁下的洛都灯火寂灭,正是万物俱籁之际,城南定鼎门却哗然而开。十二匹骏骑自城洞下飞掠而出,城墙上火束明照,映着当先一人高举的金箭权令,夜色下格外地张扬刺目。
马背上,十二人俱是一色的黑衣斗篷,随着响鞭急作、铁蹄如风,飘逸流绸滚滚振飞,宛若是深水暗潮惊浪而起,绝尘奔往东南官道。
这队南下的人马,正是连夜出城的郗彦一行。
此行东朝贵在神速,又免打草惊蛇之虞,因此偃真只自云阁剑士里挑了八人随行,马匹行李一切从简。
轻骑疾驰,凭着大司马慕容虔的令箭夜出洛都,在月色下沿着敞直平坦的官道连赶数十里,方在枫岭之西踏上漫漫崤山道。
迂曲萦回的古道在寂静中逶迤无尽,波雨般的铁骑声一旦深入丛岭,回声不绝,飘荡群谷,瞬时捣碎了宁深的山夜。
又行三十里,在崤山道与菱册道交汇处的驿站换过马匹,诸人毫无喘歇,再度急奔。
初时月色洒照满途,迎风驰骋,倒也畅怀。
直到月过中天,缓缓西沉,道侧隆峻的峰峦将清光遮得一丝不漏,徒剩无尽的森郁叠压眼前时,诸人方才感慨深山嵯峨、层林森郁,端是深不可测的险峻。
钟晔让人点了火把,黑暗中摸索向前,再无方才的电掣风驰的神速,越过最为狭窄的云台隘口,再过十里,眼前终于豁然开朗。
远处的平原强压山色,崤山道于此处转向雍州庐池,官道笔直宽广,夜色下一望寥落,毫无阻拦。
诸人都是松了口气,唯有郗彦忽然一勒缰绳,对着前方道途生出几分犹豫。
他一停下,随后的人马俱是挽辔而止,钟晔驱马上前,疑惑道:“少主,为何不走了?” 郗彦理着缰辔,还未出声,懒洋洋走在最后的沈伊突地一拍双手,大笑道:“妙极,此处竟有酒庐当风!”不管不顾地,他已驰了马向西奔去。
诸人这才将视线从正南方收回,转头望去,果见壁岩下有茅舍连排,酒旗飘展。
深夜如斯,道上行客早已杳然,此间酒庐却依旧门庭大开,粗陋的窗牖间透出摇烁的烛光,照在慵慵倚在门框的小厮身上。
似是久不逢客经过,小厮正瞌睡连连,见着沈伊奔来,这才如梦初醒,揉着眼睛,站起身。
“可有酒?”沈伊抚摸腰间空空的青玉酒葫。
“自然,公子请进!”小厮不住躬腰,又看着远处停驻不动的人马,高声招呼道,“诸位连夜赶路必是劳累了,何不停下歇会,买些酒喝?” 钟晔似乎是被说动,望了眼前方无垠的广道,言道:“少主,不如停下歇会?” “也好。
”郗彦掉转马头,朝酒庐慢慢行去。
小厮的同伴听闻动静,忙从庐间迎出,挑起竹帘,恭请诸人进屋。
半夜迎到这么多的客人,而且沈伊抛出酒葫后便扔出两枚金铢,两个小厮喜从天降,伺候在诸人案前,不住赔笑招呼。
郗彦静静坐在窗旁,望着夜色,自有沉吟。
云阁剑士们分坐四周,一张张面庞遮蔽在黑纱斗笠之下,也是僵石般的沉默。
满室沉寂,只有沈伊倚在郗彦身边,软趴趴地如没骨头一样,口中不住抱怨:“为何就不能明天走?昨天劳累了一夜,今天又是这样奔波,赶了一百里路毫无停歇,我浑身骨头都散了!” “百里路?”为他倒酒的小厮笑着道,“原来公子们是从洛都来?” 沈伊目光清亮,望着他,含笑道:“你倒清楚得很。
”边说着,边得寸进尺地将浑身重力都压在郗彦身上,极舒服地闭目养神。
郗彦皱了皱眉,伸手将他推开。
沈伊顽石一般,纹风不动。
刚刚走入酒庐的钟晔看不过眼,上前一把拎住他的衣襟,随手丢在一旁,将携身而带的水囊递给郗彦:“公子。
” 郗彦接过水囊,并不急着饮,只看了眼对着他的佩剑偷偷打量的两个小厮,忽然问道:“两位多大了?” 小厮们怔了须臾,一个笑答“十八”,一个依旧懵懵地,说道“我十五”。
“可惜了。
”郗彦轻声叹道,这时方解开系在脸上挡风避尘的黑巾,慢慢饮了一口水。
墨色绫绸映衬的肤色白得怵目,小厮们却盯着他如画的眉眼,一时仿佛看得失了神。
郗彦放下水囊,缓缓笑道:“劳驾两位,给我热两坛文君,我路上带着喝。
” “是,公子稍等。
”两个小厮交换了视线,挑起竹帘,齐齐闪身里面去了。
酒庐间顿时是一片沉寂,连沈伊也是默默地喝着酒,不再吭声。
“偃叔,”郗彦微微垂眸,话出唇齿,恰似静水无澜,“你也去后面帮帮忙吧。
” “是。
”偃真身影如风,飘入竹帘。
须臾,便有两声凄厉的惨叫悚然传出。
沈伊握着酒盏的手指僵了僵,瞥了眼无动于衷的郗彦,慢慢沉下一口气。
偃真从内舍出来,衣襟磊落,神色从容,全无杀戮后的煞气,手提一笼子的白鸽,将一卷墨迹未干的丝绡呈在郗彦面前。
“少主料得不差,这两个小厮果然是殷桓的细作。
”偃真道,“且依这丝绡上所写,前去庐池的路上怕是埋伏重重,不可再行,须得另择旁道。
” “旁道?”钟晔拧眉,“说得轻巧。
眼下除了南去庐池的路外,已别无旁道,除非返程,西行菱册道,再折转南下。
” “太过费时了。
”沈伊翻眼。
钟晔瞪了瞪他,转过头,随着诸人无声的目光,看着郗彦,等他定夺。
郗彦垂首思索片刻,烛光下目光淡如水波,忽地微微一动,抬头朝谧蓝的夜空望了一会,言道:“阿伊,借你暖玉箫一用。
” “啪嗒”一声,玉箫飞落案前。
郗彦执箫近唇,气息悠然吐出,凭借深沉的内力,将清越的音色送去九霄之外。
偃真等人无不狐疑,只有钟晔在箫声下恍悟过来,仰头望着天宇深处,瞧见那道优雅展翅的白色飞影后,不免轻轻“咦”了一声。
白色飞影旁另有黑影流空,顺着长风齐齐俯冲,落在酒庐窗棂上,一鹤一鹰,俱是神采奕奕。
“这是……石勒的鹰?”偃真盯着黑鹰,有些不确定地问钟晔。
钟晔没出声,只看着白鹤,略有怔愣之色。
郗彦止了箫声,白鹤跃入窗内,长颈贴上郗彦的肩头,不住厮磨。
郗彦微笑,抚摸它的羽毛:“九年了……你依旧长寿,我,也还未死。
”白鹤似有感触,晶莹水意淌过眼眸,就此落了下来,又将尖喙轻轻啄着郗彦的衣袂。
郗彦默然片刻,低声道:“你是想她吗?她……这次未随我一起,下次再见吧。
”白鹤终于抬了脖颈离开他的身子,轻声啾鸣,如在对语。
“知道了,”郗彦站起身,笑道,“请鹤老带路。
” 鹤与鹰再度振翅,盘旋高空。
诸人出了酒庐,翻身上马,顺着两只大鸟指引的方向,驰入深岭小径。
路上,沈伊再无先前的懒散,全身紧绷,似在竭力忍耐着什么,只是忍了再忍,还是忍不住问郗彦:“那是不是你和小夭当年在东山养的白鹤?”见郗彦点头,他立刻一个寒噤,觑着天上那道白影,面色如土。
“它怎么还未死?”沈伊咬牙切齿道。
“鹤都是长寿的。
”钟晔一路郁闷的心情刹那间霁朗起来,横了眼沈伊,调侃道,“事隔这么多年,想必鹤老也已经忘了沈公子当年是如何折磨它的了。
” 话音刚落,一粒石子从空中落下,正打在沈伊的额头。
“畜生比人还要记仇!”沈伊倒吸凉气。
钟晔瞧着他紧捂额角的痛苦模样,不禁笑得开怀。
然而与他的心情相悖,山间的道路却是越发坎坷难行起来。
此刻冷月虽还未尽数西坠,丝丝凉光透过壁岩缝隙斜射入墨黛的山色里,更显得前途凄恻幽清。
狭长的小道在嵬崔山峦间折转无尽,走到最艰难处时,不见径道,全是乱石峭坡,众人不得不下马,牵辔步行。
如此折腾下来,等再度出山时,望见东方天际曦光暧昧,方知此刻已是拂晓时分。
山外长风广漠,清流蜿蜒,鹤与鹰犹不停歇,拍翅徜徉,引着诸人在浅滩上急驰数里,直到完全穿越出崤山山脉,到达一片浩荡湖泊。
白鹤引颈,飞鹰长啸,这时才自云端缓缓飞落下来。
郗彦举目远望,晨天之下水色茫茫,云兴霞蔚,几只轻舟泊在汀渚上,桃荫夹岸,碧波锦浪,景致安静宁和,宛若是世外瑶池。
渡头,古亭寂寂,两人相对坐于其间,白衣清雅,黑衣沉着,正专注于盘中弈局。
石勒与段云展领着鲜卑武士候立亭外,听闻远处的马蹄声,忙道:“主公,彦公子他们到了。
” 白衣公子闻言转头,商之微微一笑,不动声色地,将黑子落入棋盘。
“我又输了。
”白衣公子掉回目光,望着局中一片狼藉的形势,勉强撑到现在,已是退无可退,只得弃子认输。
他站起身,落寞长叹道:“九赌九输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综]纲吉在暗黑本丸伽尔什加
- 玩家糯团子
- 与婠婠同居的日子李古丁
- 我始乱终弃前任后他们全找上门了倔强海豹
- 仙君有劫黑猫白袜子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怀了队友的崽怎么破西山鱼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虫屋金柜角
- 穿书后我爱上了蹭初恋热度清越流歌
- 首辅大人重生日常/今天也没成功和离时三十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乾坤剑神尘山
- 穿成废材后他撩到了暴躁师兄是非非啊
- 玫瑰帝国6·辉夜姬之瞳步非烟
- 锦帐春慢元浅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纨绔心很累七杯酒
- 控制欲叙白瓷
- 极品修真狂少墨世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咸鱼替身的白日梦顾青词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平安小卖部黄金圣斗士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不息阿阮有酒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游弋的鱼乌筝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春生李书锦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后桑奈
- 不差钱和葛朗台寻香踪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情终孤君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大叔,你好大江流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阻流三眠柳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共同幻想ENERYS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如何才能将目标勾引到手南柯良人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他们今天也没离婚廿乱
- 一不小心撩到豪门对家棠叶月
- 嗨,保镖先生棠叶月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竹马危机萧二河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星星为何无动于衷秋绘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情敌五军
- “球”嗨夕尧未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杨九淮上
- 阻流三眠柳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戏精配戏骨陈隐
- 恶魔总监:亿万独宠小男友浔弦
- 老大,你情敌杀上门了沐沐不是王子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治愈过气天王落落小鱼饼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我只想好好谈个恋爱!爱吃肉的羊崽
- 舌尖上的男神随今
- 轻狂巫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