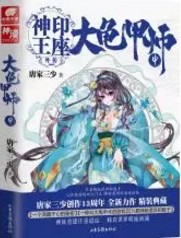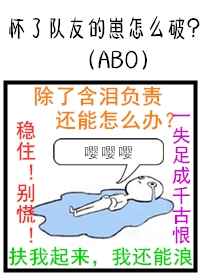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船歌(3/3)
是黑人,再偷偷地卖给香港东南亚那些喜欢玩儿大麻的。
自从听他说了这个,每当他半夜三更钻进我房间的时候,我都会菊花一紧。
我一直觉得如果和什么人在一块儿连打三国杀都能变成一种折磨的话,那这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比如简意澄。
每次打从洗牌开始他就像一坨泡了水的橡皮泥一样黏在张伊泽身上,嗲声嗲气地问小泽给我看看你的牌好不好给我看看你的身份卡好不好放权给我好不好桃子给我吃好不好。
我们每次洗牌都是林家鸿,这家伙最喜欢用孙权和袁术,都浪费牌。
他把牌发给江琴之后,江琴亮出自己的武将牌贾诩,然后把牌往桌子上一甩,啪地拍了桌子。
我们吓尿了,以为她要开局乱武。
结果她指着简意澄怒喝道,“你能不能闭嘴。
” 简意澄默默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把抓着张伊泽桃子的手收了回来。
他喜欢用甄姬,说是因为甄姬是个诗人。
我一直没好意思告诉他《洛神赋》其实是曹植写的,而且和甄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点子也是太背,洛神的第一张牌就是红色的,然后求助似的看了看张伊泽,又把胳膊吊在了他的肩膀上。
张伊泽叹了口气,丢出一张梅花的诸葛连弩,武将牌上的张角闭着眼睛,仿佛不忍直视。
打了一圈下来发现少了个忠臣。
我知道问题就出在张伊泽和简意澄那里。
简意澄撒娇的声音混杂着窗外噼噼啪啪的雨声,这雨已经下了十天了,兴高采烈,若无其事。
厨房里煮了三天的糯米团气味四散开来,渗进地上满是污渍的地毯里。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再好了。
“我×,你有完没完了?”我把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弹到装了水的纸杯里,然后扔下牌站起身来走出去。
面前的蔡文姬脸色泫然欲泣。
后院的雨水,落英,败叶,朽木,连成一排一排一模一样的小房子,远处云气四溢的雪山,都像是这个抑郁的少女合上双眼的脸。
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我听见张伊泽过了没多久就从屋子里出来了,站到我的身边,我习惯性地菊花一紧。
徐庆春的宝马Z4从小区门口开过来,溅起一路的水花。
我知道他们是去找三楼的那家香港人。
我们这些屌丝站在门口的屋檐下,长年被人展览参观,像是舞台上被弄脏了一块的幕布。
徐庆春看也不看我,高跟鞋踩得整个楼梯都摇摇欲坠。
“她又包养了一个新的?”张伊泽看了看早已经被徐庆春关上的门,然后半通不通地问我,脸上还露出心领神会的笑意。
“这次是那个香港小哥吧,喜欢玩洋妞传照片的那个——” “包了个广东人。
”天色渐渐暗下来,现在是下午3点50。
如果在国内,这个时间大概被叫作冬天。
在这里一年四季都一样,区别的只是3点天黑和10点天黑。
“好像姓宋,总跟在那个香港人屁股后面转。
她还送了那小哥一辆车——” “对于这么丧心病狂毫无节操的事儿,我只想说四个字,请联系我。
”张伊泽在潮湿的屋檐下吐了个烟圈,眼色妩媚得好像十里流水宴上风华绝代的旦角儿。
我没理他,扭过身往房间里走,“团战可以输,陆逊必须死——”江琴的声音中气十足,无忧无虑。
“我没跟你开玩笑。
”张伊泽抓住我的肩膀,薄荷和樟脑的味道冲进我的大脑反复回荡。
“跟徐庆春说说,让她联系我。
” 雨气弥漫开来,千回百转。
刮过树枝的风像一块刚开封的剃须刀片一样,凉爽而狞厉。
【林家鸿】,2014
雨终于停了。黄昏时分没有太阳,像是一瓶所剩不多的墨水。
飞机闪着一明一灭的灯从天上渐渐飞过去。
我从来都喜欢夜航胜过白天。
刚到美国的时候觉得机舱里黄色的小灯特别漂亮。
清静温暖得好像不在人间。
后来往返的时间长了,渐渐没了这种感觉。
因为一飞就要飞十多个小时很不幸地还有转机。
后来我总觉得那是冰箱或者冷冻柜里方方正正的灯,一飞机的人都是冻肉、白菜、火腿肠,被打包装箱塞好防腐剂。
印度的是咖喱。
他们的孩子很厉害,能连续不停地哭15个小时以上,哭得你特别想开了窗户把他们扔出去。
我就是这时候见到徐庆春和张伊泽在一起,混在一大群宿醉的男男女女中间。
社区服务处为了迎接圣诞,挂起一串串跳跃的圣诞老人光团。
那些人满身酒气,东倒西歪地往小区里面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车歪斜地停在门口。
张伊泽把手搭在徐庆春的肩膀上,眉目流转巧笑倩兮,到了楼梯口上还依依不舍难解难分,像是一出霸王别姬——徐庆春是项羽,他是虞姬。
可惜天地搭不起漂亮的舞台,阴惨惨地憋足了一场大雪。
这是整个西雅图最泥泞灰暗的几天,张伊泽毛茸茸的短靴边上沾满了灰黑的雪泥。
远处几个韩国和俄罗斯的留学生缩着脖子站在角落里,吐出一大口烟。
眼睛里满是呆滞和厌恶。
我觉得我作为这幅景象的一个细节,一定也是他们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
这种广漠的厌恶像是永不间断的大雨,淅淅沥沥地覆盖在整座城市之上,沉沉地压在人的眼眶上,一望无际,滚滚向前。
张伊泽从来不能给人什么好的联想。
他这些日子来来回回地在这个小区里出入,当然身边的人都不是简意澄而是徐庆春。
简意澄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每天上学,放学,在人人上传照片秀恩爱,灯塔,大海,各式各样的食物。
迫不及待地给人们展示他有多愚蠢。
厌恶感附着在人们被泥水浸泡了一冬天的靴子上,地毯和炉台的污渍上,总是裹着一层油腻的胃里,疙疙瘩瘩的脊梁骨上,一切都变得很快。
人们像是自然界飞速迁徙繁衍的动物,趋利避害是本能。
只有听到别人失恋,家暴,打人,车祸,退学这类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嗅觉神经才会变得异常敏感,两眼放出凶光,像是终于嗅到人肉腥味的丧尸。
我关掉前车灯,从后视镜里看到徐庆春和张伊泽已经消失在了楼道的阴影里。
面前的树丛被某个不高明的司机撞得乱七八糟,地上堆满落叶,仿佛埋着小动物的尸骨。
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简意澄就从右侧的车玻璃上反射出来。
蓬乱着头发,眼妆晕得乱七八糟,一只脚踩着拖鞋,另外一只脚上的UGG沾满雪渍,整个人看起来就像超市里摆放整齐的烟熏培根。
他噼噼啪啪地敲着我的车门,声音在寒冷的空气里一波三折。
“张伊泽呢?” “我怎么知道啊——”我从车里狼狈地钻出来,吞咽了一口唾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不那么僵硬。
他抬头死死地盯住我,目光被蒙上一层蜘蛛网。
我于是改了口,“这个……我不能说。
” 话一出口,我几乎要被我自己暴露的智商逗笑了。
简意澄也嘲讽地笑笑,凛冬将至,朔风遍野。
我用眼神示意了他D座的位置,没敢伸出手来指,像是面对着太君明晃晃的刺刀,唯恐那根指路的指头被咔嚓一声切掉。
他踩过树丛,草坪,化成一摊摊的雪地,朝着无休无止的吵骂厮打狂奔而去,乱蓬蓬的黑头发像一面猎猎的旗帜,从背影来看他简直神飞气扬,掉了一只鞋也没顾得上捡。
踩在每一寸这里的土地上都是他顾影自怜的资本,好像不闹出点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来就不配称为美剧女主角。
我从后车座上拎起刚买来的炸酱面,往苏鹿家慢吞吞地走过去。
雪地上倒着的UGG上沾满黑泥。
天色渐暗,四下里灯光芜杂。
D座一楼的房间里女人的哭泣声,摔盆摔碗的声音,尖叫声,劝架声,适时地和灯光一起亮起来。
几栋房子二楼三楼的香港人兴致勃勃地探出头往窗外看,排列整齐,摇摇晃晃,有几个嘴上沾着奶酪和番茄酱,让人忍不住有拔出枪把他们爆头的冲动。
我敲着苏鹿家的门,没人应。
从门外就能听到几个黑人口音浓重地讲了个什么笑话,摇着装在一次性纸杯里的骰子,醉酒高歌,欢声笑语,甚至还掺杂着王东那个死基佬猥琐的嘿嘿笑声。
黑夜一寸一寸地把荒村吞噬。
风吹到耳朵里刮得生疼。
直到有人喊着“外面又有人打起来了”、“小瓜子板凳节操都准备好了大家快去看热闹啊”才有人跑过来给我开门。
浊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一眼就看到江琴和梁超像一对闺蜜一样坐在桌边,意气高昂地痛骂着他们的前男友前女友,手边是带着血腥气的黑方,倒在塑料杯子里,像是吸血鬼们隔了夜的食物。
一个叫不上名字的黑人嘴里叼着大麻,摆弄着墙角的电子琴。
简意澄满身都是泥水,气喘吁吁,妩媚地倒在苏鹿脚边,絮絮叨叨地念着童年往事,像是五代十国某个昏庸帝王的宠妃。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我妈妈每天酗酒,赌博,不干人事儿,把自己作的得了胃癌。
虽然我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很靠谱很喜欢我的新妈妈,她依旧是我的亲人。
”简意澄脸色平静,虚假的优雅面具化开了,融成柔若无骨的绸丝。
壁炉噼噼啪啪的响着,炭火溶溶,棠烛高烧。
苏鹿一杯一杯的给自己倒着酒,那种气势让人胆战心惊,像是个一掷江山的亡国之君。
“我很久没见到她。
以为她已经死了。
直到有一天我妈妈让我去参加她的结婚典礼。
那饭店真小,又矮又破。
里面的人都穿得很邋遢,菜里有90年代的味儿。
我都不敢相信我小的时候觉得那就是天堂。
” 我就着简意澄做作的苦笑,把半杯啤酒一仰头倒进胃里,一滴不剩。
厨房里有个陌生的女孩在炸苹果。
苹果放在锅里许久没动过,已经冒出了浓烟。
她在厨房的水龙头旁边弯着腰,不停地往脸上拍着水。
厨房的地面,冰箱,锅台,到处都是煎炒烹炸过的陈旧污垢。
幸好天花板上的自动报警器被塑料袋套住,警察才没有因为满屋子的滚滚红尘而赶过来。
“她的新丈夫六十多岁,秃顶,笑起来牙齿很黑。
我去他桌子旁边给她敬酒,把这些天攒下来的红包递给她,她就像看着其他客人一样,特别客气的跟我说谢谢。
” 长期待在屋子里会让人混淆时间地点。
让人错觉这是在热带。
荒凉,破败,就是没有冬天。
永远人声鼎沸,万古长青。
炸苹果的姑娘从水池边上抬起头,“小哥,别看了。
”她张开五指在我眼前晃了晃,笑嘻嘻地说道,“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来,吃一块炸苹果。
” “前两天听说她真的死了。
还怪不是滋味儿的。
回国之后得去看看她,毕竟是我妈妈——”够了别听了。
我咬住牙,憋住一个即将到来的喷嚏,把眼眶憋出一阵热潮。
“这世界上一直都剩下我一个人。
伊泽他不喜欢我,他宁可跟着徐庆春走。
但是如果连我都不管他,谁还会管他呢——” 我眯起眼睛,甚至在出了门之后就忘却了那姑娘的长相。
“你叫什么名字?” “我大名不好听。
”她噘起嘴,“你可以叫我莫妮卡。
” 我和她就见过这么一次面。
后来听说她颠沛流离,转了几次学,几经波折,最后莫名其妙地客死异乡,据说是司机酒后驾车不慎掉到海里——这么个傻×才信的理由。
打三国杀遇到小学生连跪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那个晚上。
苹果一边炸糊了,一边没熟。
烫嘴的苦味儿混着烟熏火燎,夹杂着满屋子浓郁的伏特加气味。
人生太脏了。
就算捧出肺腑里的一腔热血也没办法把它擦干净。
【江琴】,2014
——我觉得徐庆春其实挺牛×的。至少和顾惊云分手之后现在活出了个人样儿。
——是吗? ——哎苏鹿。
听说你最近认识了好多小新生,快帮姐姐物色几个。
——梦溪姐你早说。
现在稍微有点姿色的小新生都被挑走了。
你看这个。
——哎哟这小孩儿长得真帅……等等,这不是刚被徐庆春勾搭上手的那个吗?叫张什么来着。
——张伊泽。
——听说前两天简意澄还去跪着求他回心转意。
现在求回来了吗? ——还是那样,张伊泽不愿意理他,还说他是死基佬。
看得我都替他们着急。
——嘿你这腐女。
我站在苏鹿卧室的窗台外面,嘴里叼着一根烟,漫不经心地往楼下的沼泽池子里丢一块废电池。
池子里无数只青蛙作死地嚷嚷着,简直像老板娘跑了跳楼甩卖的小贩。
两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两块钱您买不了上当。
苏鹿每天都抱怨着房间闹鬼屋顶漏水楼下青蛙叫个没完。
虽然在我的眼里这套房子其实挺好。
楼下的韩国人架起烧烤炉子,烧烤酱裹着肉浓郁的香味直往人鼻子里钻。
烟雾白蒙蒙的,对面的租客长满花藤的阳台上插一面美国国旗。
笑声,骂声,敲打键盘的声音,英雄联盟金克丝主题曲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一股脑儿地涌过来,让人联想起一个叫“美国梦”的逗比词汇。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自己如此丧心病狂地在那个美国寄宿家庭交了一年的租金。
每次看到他们趴在沙发上一边啃着一种速冻派一边看电视,那种鼻子下面好像有苍蝇的厌恶表情,我就想走上去问问他们为何放弃治疗。
Whygiveuptreatment. 农村。
亚洲人扎堆的小区放远了一看仍然是农村。
美国人的房子在荒野里一栋接着一栋,院子里摆几个雕像,荒草衰败,从不点灯,让人疑心里面住着变态科学家或者女巫布莱尔。
在这种地方待久了,连蹦蹦跳跳的约德尔人也得变成一块宅在家里不动的石头。
身上阴暗潮湿,发了霉,每天揪下自己身上长的蘑菇炖汤喝。
当然像徐庆春那种把自己车砸坏了再去找保险公司索赔的机智的果子狸除外。
小区的栅栏被上学的中国人掏了很大一个洞。
国人在走捷径这类事情上的机智总是出乎人的意料。
烟雾顺着窗户,慢慢爬上来。
我眯着眼睛,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扒开四周的灌木丛和铁丝网,慢吞吞地越过一片草地,在树木间的阴影处站定。
烧烤的香味也掩盖不住一阵浓郁的大麻气味儿。
我皱了皱鼻子,憋住从鼻腔里涌出来的喷嚏,看到一个染了黄毛的香港人从E座噔噔地跑下来,手里还捏了一把什么东西,大概是零零散散的美元。
“这次就这么点儿。
老黑从来就不靠谱。
”王东油腔滑调的声音在黑夜里蔓延开来,和着烧烤的白雾,植物烧焦的气味。
小镇被接踵而来的山风灌满,我抬头看了看天,红云烧尽,凛冬将至。
“没事儿,没事儿。
”香港人拙劣地模仿着北方口音,舌头像被柠檬水泡肿了。
还生硬地拍了拍王东的肩膀。
“你跟玛丽莲怎么样啦?大家都很担心你。
” “早甩了。
”王东穿得很单薄,缩着脖子,把手插在两个袖子里,端着肩膀,看起来像个进城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
“哦,不对,就前两天的事儿。
”他又这么改口。
E座二楼的房主开了厨房的灯,这时候光线能够稍稍照到王东身上一点。
借着小区外面美国人一晃而过的车灯,我能看见王东身上穿的是玛丽莲的一件薄毛衫。
可能他本人也感觉到了什么不自然,连忙接了一句,“甩了还是在一起玩儿。
买卖不成情意在。
” “我懂。
”香港人的笑声在黑暗里显得很促狭。
王东转过身去,从原来那个不大不小的洞往外挤,一边草草地挥了挥手。
我拉开玻璃门,身后房间里已经聚了四五个女生。
夏北芦,苏鹿,玛丽莲,连简意澄也跟过来凑热闹。
似乎丝毫不知道他身边这些姑娘前一分钟还躲在房间里兴高采烈地说他坏话。
几个人规规矩矩地围成一团,把手伸出来等着林梦溪看手相。
无论在什么地方,妇孺们对吉祥话的迷恋程度几乎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看了那么多爪子,找到皇上没有?”我把半截烟头抛出阳台外面。
“没皇上。
”野生神婆林梦溪戴着一副大眼镜,看起来像是从哈利·波特电影里刚走下来的特里劳妮。
“这几个小丫头片子,连个贵妃命都没有。
” 小丫头片子简意澄毛茸茸地缩在苏鹿的枕头旁边,两只爪子飞快地在手机上敲出一行行字。
“这么说,没找到那个让你跪拜高呼吾皇万岁的主公?”我把桌子上的三国杀往床上一扔。
“正好五个人,来打三国杀。
简意澄洗牌去。
” 张伊泽以前和我说过,以前他和徐欣、王东、简意澄,都是在一起玩儿的好基友。
后来王东每天把50多个黑人带到家里来做起大麻生意,他们每天都觉得菊花不保,把家里的肥皂全部销毁。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小受收拾细软连夜逃跑。
看来这事儿他还真没骗我。
【梁超】,2014
大半夜到韩国城来打台球是简意澄的主意。虽然有时候看着他觉得可怜,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果然在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搭公车到韩国城之后又迷了路。
手机还在没完没了地放着歌。
张伊泽和简意澄也很有默契,不吵不闹不秀恩爱,让人觉得他们重新接受了治疗。
路灯,车灯,带着泡菜味儿的湿咸的风,全都搅拌成一团,变成色彩斑斓浓郁的一锅凉汤。
树木和黑夜的气味无边无际地弥漫在四周。
无人在街上独行,无人弹着吉他唱歌,无人走出路边的酒吧。
Somedancetoforget.我跟着耳机哼着音乐。
他们跳舞是为了遗忘。
“饿吗?”张伊泽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话。
简意澄也顺其自然地接上“不饿这大半夜的就别吃东西了”。
话音未落我们就反应过来,这货是在对着路边汪汪叫的小狗说话。
一边说还一边蹲下抚摸着狗头,自得其乐笑而不语。
“你他妈就对你的同类有爱心。
”我对着他撅起来的屁股踢了一脚。
“你看,我就是被你们这几个大丧尸带坏的。
”张伊泽站起来,一笑之间乍寒还暖,像是竹林隐士栽出来的海棠。
雪消炉火灭,风动酒波平。
“要是早个几十年你们这些流氓全得拉出去挂牌子游街。
” “还能不能做好朋友了还能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我一抬眼,就看见徐庆春从不远的烤肉店里面走出来,长发散乱,风霜沾衣,还不知道自己嘴角沾着一点儿烧烤酱。
简意澄不易察觉地挺了挺脊背,用尽了浑身的力气吊在张伊泽的胳膊上。
这种寂静在一瞬间还让人有点儿享受,可惜一下子就被简意澄打破了。
“小泽,我们还是不是朋友?”简意澄的声音像是被风扯碎的柳絮。
“啊?”张伊泽诧异地笑起来,“你想怎么——” “喏,你看她。
”简意澄朝前方努努嘴,“我们要还是朋友就去给她点教训,好不好?”扯碎的柳絮在他嘴里囫囵了一圈,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像含着一个枣核。
徐庆春低着头,双手插在兜里,往这边慢慢地走过来。
“也不用打一顿。
打她一个耳光就可以。
” “你在学校这么刁,你爸妈知道吗?”我压低了声音,觉得他最近在家看了一部起点上360章的黑道小说。
“简意澄,你要是不装×我们还是好朋友。
” 但显然徐庆春不想和他做好朋友。
她扯一扯嘴角,几步走到简意澄眼前来。
身上的连帽衫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你想打谁呀?”她扬起脸来,势单力薄地面对着我们三个人,我们在她的眼角膜下挤成一团,像西雅图的繁华和腐臭一样不值一提。
“别闹——”张伊泽刚挤出个花团锦簇的笑脸,徐庆春就一掌将他拨开,一双豹爪准确地提起简意澄的领子,嗓音凄厉得吊了起来,尾音被风折皱得百转千回,“小王八换了身黑壳就想装人啦?你想打谁!” 简意澄咬牙切齿地盯着她,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从黑道小说里学来的疯劲儿。
“把你脏爪子拿开!神经病!”说着就死死地抓住徐庆春的手要把她拉开。
徐庆春这只豹女变了身,哭天抢地地往简意澄脸上扑,咬,抓,挠。
简意澄的头发被扯掉了一缕,露出白惨惨的头皮来。
“你少跟我劲儿劲儿的!”徐庆春揪着简意澄的外套破口大骂,活像我们初中的班主任,“你想打谁?啊?” 我一看这两方英雄在野区单挑起来的架势,连拉架都犹豫了好半天。
估计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野怪。
张伊泽稍微强点,是一红buff。
“行了两位,”我面对着简意澄,像石像一样伸展着胳膊,把他们搅在一起的手臂努力拉开。
两边的吐沫星子一个劲儿地朝着我脸上喷,喷完了左边喷右边。
“大半夜的都是出来玩儿,别在大街上闹了——” “是她先打我的。
”简意澄越过我的肩膀盯着徐庆春,嗓音甜甜腻腻的,简直像个跟老师告状的小学生。
“你看我有老公你没有,嫉妒吗?”笑容在他的脸上肆无忌惮地泼开。
我的后背猛地被撞击了一下,一个踉跄倒向一边。
徐庆春抡起手里的包哗啦一声甩在简意澄的脸上,他的脸立刻被划出了一个大口子,头发蓬乱像我们小学课本里画成贞子的烈士。
赵一曼,江姐,刘胡兰。
简意澄抿着嘴,一声也不吭,迎着徐庆春的拳脚步步紧逼,也把手里的书包一下一下地往她脸上肩膀上抽。
那包没有拉链,里面的化妆品,镜子,手机,钱包,乱七八糟地洒了一地,居然还有两块卫生巾。
我不知道他把这个东西随身带着是想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提醒自己那天被人扔卫生巾的耻辱。
张伊泽走过来,背对着简意澄,整个地把徐庆春迎在怀里。
徐庆春脚上踩着高跟鞋,比他还高出一小截,“徐庆春别闹了,我知道你,你不就是烦他吗?”他脸上带着歇斯底里的笑意,头发被风吹得毛茸茸,看起来真的像探险家伊泽瑞尔一样,又飘逸又漂亮。
“我也烦。
我早他妈受够了。
你这就见了他两面,他天天待在我家不走,天天在一起,我什么感觉?” 简意澄愣在原地,抿着嘴唇,脸上一道血痕触目惊心,风把他的头发吹往四面八方,看着像从古罗马的角斗场上忽然被扔到了这儿,满头的青丝还喊着陷阵之志有死无生。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马上就要凄凄凉凉地走过来几步,唱一腔人言洛阳花似锦,偏奴行来不是春,然后一纵身投进太平洋。
张伊泽仍然低声地絮絮叨叨劝着徐庆春什么话。
一会儿一起去玩。
请她吃饭。
徐庆春也不听,鞋尖把地上的一片卫生巾踢开,小心翼翼地拉开自己宝马的车门。
“上来啊?”街道上满是熄不干净的霓虹灯,像是扔在脚底下踩不灭的烟头。
徐庆春没坐进座位里,在车门上靠了好久,两只脚轮换着重心,烦躁异常。
“不用你们请吃饭了,你们俩到底上不上来?” 张伊泽缩着脖子,把两只手藏在衣袖里,也不敢看简意澄,只尴尬地盯着我。
“赶紧去。
”我朝他厚厚的羽绒服上拍了一把。
“你俩去好好玩玩,也别让我干等着,一会儿没有公交车了。
” 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简意澄被孤零零地扔在那里等公交车。
他靠在公交车的站牌上,抬起头,把眼泪倒流回眼眶里。
他的眼睛就像两罐盛满沸水的水壶,雾气腾腾,眼泪从里面咕嘟咕嘟地蒸发。
“一个大老爷们儿,哭什么。
”我不轻不重地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摇了摇头,用袖子抹了抹眼睛,似乎想要习惯性地抓住我的袖子,又缩了回去。
“你们都觉得我很恶心,对吧?”他像问一个真正的问题一样,认真地看着我。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人间值得春风遥
- 与婠婠同居的日子李古丁
- 起点文男主是我爸林绵绵
- 瑶妹其实是野王星河入我心
- 末世对我下手了一把杀猪刀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虫屋金柜角
- 仙尊一失忆就变戏精哈哈儿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穿成废材后他撩到了暴躁师兄是非非啊
- 玫瑰帝国6·辉夜姬之瞳步非烟
- 他从雪中来过期白开水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真爱没有尽头科林·胡佛
- 怀了男主小师叔的崽后,魔君带球跑了[穿书]猫有两条命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控制欲叙白瓷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咸鱼替身的白日梦顾青词
- 不朽神王犁天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眼泪酿宴惟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不差钱和葛朗台寻香踪
- 替身夺情真心
- 他儿子有个亿万首富爹狩心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CP狂想曲痛经者同盟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404信箱它在烧
- 一不小心撩到豪门对家棠叶月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我变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肿么破?!等,急!笨小医
- 轻狂巫哲
- 追随者疯子毛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情敌他失忆了紅桃九
- 你叫什么?我叫外卖晒豆酱
- 喜提祸害舍木氓生
- 听说我很穷[娱乐圈]苏景闲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情敌五军
- 对家总骚不过我四字说文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非职业偶像[娱乐圈]鹿淼淼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爱不可及三秋月999
- 没完晚春寒
- 男主今天翻车了吗吐泡泡的红鲤鱼
- 校服绅士曲小蛐
- 和校草联姻之后芝芝猫猫
- 我要这百万粉丝有何用宝禾先生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