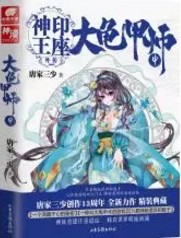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和我跳舞吧,洛丽塔(3/3)
那么开心——”她塞了满满一嘴的菜,用餐巾纸擦了擦,留下几道口红印来,梁超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不管她说什么都听得像耶稣布道。
我给苏鹿介绍的新室友坐在桌角和苏鹿聊天,苏鹿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谁都能聊得一见如故,还都能用她们喜欢的表达方式解决问题,跟我永远都是走兄弟请你吃饭去,跟小清新小淑女们就一口一个宝贝亲爱的,她以前给我读过一篇小说叫《永远的尹雪艳》,我就觉得她和那个尹雪艳差不多。
“我就是想学习,”那个叫夏北芦的小孩认真地咽下去一口米饭,“我之所以从CCA里搬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法学习了,”她看着苏鹿,皮肤在光线下面能看见淡青色的血管,“我那个巴基斯坦的室友,每天回家就是叫我刷碗,洗盘子,刷厕所,每天还都嫌什么杯子不干净,半夜也能来敲我屋的门让我起来重刷,每天我们有什么乱丢垃圾吃饭不洗盘子她还都和我们室友说是我干的——” “宝贝这不行你得反抗,”苏鹿放下筷子,“你买自己的餐具让她们自己解决自己的。
” “CCA的人还总进来查房,一点儿隐私都没有。
” “那群校狗。
”苏鹿笑了笑。
夏北芦托着下巴无限神往,“我要是能搬出来自己住的话,让我天天做饭洗碗干什么都行。
” “哈哈,”苏鹿笑眯眯地看着她,“我可舍不得你天天做饭洗碗,就有两个问题,一我得画画,经常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来灵感;二是我这群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什么的,你不介意和我们一起玩吧。
” “我想多认识点人,”夏北芦的声音像是刚融化的奶酪,“只不过我妈死活都不同意我出来住,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以后我和我妈视频的时候你恐怕得躲着点儿——” “没问题没问题,”苏鹿很豪气地摆了摆手。
落地玻璃外面轰隆隆地滚过一声惊雷,肥厚的灰云飞快地聚拢又散开。
开始下雨了。
【梁超】,2014
我第一次看到玛丽莲是在一个下着雨的黄昏。天边描上了被水晕开的晚霞,整个世界都湿漉漉的,深吸一下就全是混浊的雨味,好像树叶都生了锈。
在这么寂静的天色里,永远没完没了的雨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
她在我前面走着,不打伞,披了件蓝色的大衣,那件普通的卡其布衣服在她身上就显得很妖娆。
从我们旁边疾驰过一辆车,引擎声轰然作响,夹着雨水,好像是汹涌的海浪,那种无可抗拒的力量让你觉得一个人无比渺小。
叶子上的水珠纷纷震落下来,然后她转过脸,抹了把脸上的水,所有的水珠都像是被撩拨过的大提琴的弦,在那一刻一起颤抖着摇曳生姿。
我混到顾惊云这一群人里,不夸张地说,全是为了她。
班里那几个中国的男生嚷嚷着要去打魔兽,贺锦帆拍着他旁边那人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程妙人也去,一旁的一个小孩撇了撇嘴,她又不会打魔兽,明摆着借机会来钓凯子。
程妙人,名字都像是我喜欢的港产电影里被旗袍裹着浅吟低唱的女人,一举一动都繁华似锦妩媚入骨。
在那一圈人里面,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人物叫苏鹿,人人都说她美,可能是因为她和顾惊云非同寻常的关系吧,每个圈子里,总有个闪闪发光的中心人物,和被这个中心人物捧若至宝的漂亮女人。
但我一直觉得,她不过是个好看一点的小孩儿,色泽太过鲜明,好像随时随地都能做出点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
玛丽莲不一样,她身上有种来自人间烟火的,妖娆的沉堕,所有的颓靡厌世都能被精雕细琢,让富豪们的后代千金散尽,一晌贪欢。
她成了一道焰火。
她的绽放是这个末世一样的小村里最后的狂欢。
那是个中国的年夜,小镇一如既往的寂静,外面下了点薄雪,又冷又空旷,洋人佬儿永远开着电视,大狼狗在雪地里汪汪叫着。
苏鹿他们租的房子外挂了两纸薄灯,瘦弱的红在夜色里晕开,染了点雪,微微地摇晃着。
屋子里在煮火锅,有人倒了点沙茶酱,红乎乎的一团,火锅冒着热腾腾的白气,把屋子熏出醉生梦死的温暖,像是一锅香气四溢的太阳。
几个人吞云吐雾地打着麻将,麻将牌细碎的声音和着顾惊云油腔滑调和人打趣的声音,这里变成了一个没落荒凉人间里声色犬马的大观园。
程妙人轻轻叩了几下门,笑吟吟地把门推开,轻轻扫了扫身上的薄雪,抖下满天满世界的寂静,四周霎时间变得红艳艳光闪闪,今天是大年三十,我这才想起来。
好像有烟花鸣放四海升平的声音,一下下敲击着我的耳膜。
我总以为我该出生在关锦鹏王家卫电影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香港,韶光锦屏,风情万种,刀光剑影下苟且偷安的甜蜜沉堕可以让人心安理得地拼将一生休,度尽今日欢。
跟那时候比起来,这个僵白生硬的年代简直什么都不是。
但自从遇到玛丽莲之后,我发现,这个年代其实被我错怪了。
曾经有个叫王东的富二代点一支烟,歪着头嘿嘿地笑,说不就是个漂亮的婊子嘛,凯莱这个地方有的是,扔点儿钱就前赴后继地来找你。
这些家伙总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无耻。
除了过年之外,那几天还是苏鹿的生日,其实除了过生日,任何一个理由都能让他们像老爷过寿似的大办三天。
顾惊云不知道从哪儿凑来了一大票人捧场,我坐在一边百无聊赖地听着他们捧着礼物嘻嘻哈哈,玛丽莲坐在我旁边,翘着腿,轻轻地把垂下来的头发拨到耳后去,这种不经意的动作总能恰到好处地摆成一个柔若无骨的弧度。
她对我说陪我出去走走吧。
外面寂静得好像所有人都凭空消失了,黑夜里的雪打在我脸上,我们站在屋檐下,身后的灯光和喧哗都变成了摇摇晃晃快要熄灭的蜡烛。
我看着她,她湿漉漉的眼睛就像是外面一望无际的黑暗,盛着大雪,一落十年。
她对我说,苏鹿真幸运,你知道吗,我做梦都想像苏鹿一样,遇到一个顾惊云。
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抱紧她,她的头发拂到我的脖颈上,瘦弱的身体贴近我的心脏,我能听到她在风雪里沉重的心跳声。
玛丽莲,我多庆幸你没有推开我,对我来说有这么个回忆就够了。
我轻轻地摸着她丝绸一样的头发,对她说这个该死的生日宴会马上就过去了,如果到最后没人陪你,我陪你。
学校里的那些看客们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的爱情指手画脚,王东,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的。
【林家鸿】,2015
现在我在开往加州的路上,苏鹿坐在我旁边,给我和江琴一人买了杯咖啡然后靠着窗子睡过去了,头发搭在像陶瓷一样的脸上,阳光把她的色彩勾得更加鲜明,像是张单反拍出来加了LOMO效果的照片。路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载着货物喷着可口可乐公司图标的卡车在我旁边轰然碾过去,突突地扬起尘土。
江琴懒懒地喝着咖啡,和我讲着她一个叫金尚寒的宅男兄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割腕了,没成功,室友们沾了光,全得了4.0的GPA。
这条高速路比我们的小村更加荒凉,阳光打在玻璃镜上反射的刺眼,我忽然想起初中语文书上写的,飞鸟各投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种想法让我莫名地愉悦起来,然后把车里的音响开大,凯蒂佩瑞的声音隔着杂乱的世界震荡出来。
“×,你看,奥迪A8——”江琴指着路上一辆黑色的轿车精神抖擞,我听出来她声音里的笑意,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兴奋,当年简意澄和他后来的小男朋友张伊泽一直认认真真地和我们说一定买一辆新的奥迪A8,连毕业以后转到同一所大学把那辆车开过去都计划好了,可惜这个美好愿望一直没得实施,搞得那些小兄弟一见到张伊泽就一个个地问说好的奥迪A8呢,有一阵给他弄得差点带着简意澄退隐江湖。
我还记得简意澄这个家伙当年在我们那儿到底搅起过多大的波澜。
说实话,他不是那种活在腐女画册上一笑倾人国的妖孽受,但他天生有一种淡然的温煦,永远都是坐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着你,他那种注视不会让你觉得紧张,反而会觉得他是在欣赏你,让你做什么都更加自然。
当你习惯了这种注视,他的眼神忽然从你身上消失了,你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他如果是个女人,一定是个能陪良人过荆钗布裙烟火日子的人,就像一杯温水。
但这个看似淡然的家伙好像过早地把爱情当成了他生命里的信仰,更糟糕的是这人迷信,拜完了佛祖转身就去拜基督。
在连续被班里的四个外国小哥拒绝之后他盯上了性格温顺的贺锦帆,好像知道贺锦帆不会对他说出狠话来似的——这家伙被我们叫作老道,别人纵酒高歌熙熙攘攘时候他也能无比淡定地在一旁写作业,仙风道骨,是个人物。
自从简意澄跟着贺锦帆硬挤进这个圈儿以来,他就被大家自然地尊称为道姑。
我记得有一天道姑又喝醉了,站在客厅里披头散发不断地闹,拉着贺锦帆说你为什么不理我,哭得除了丢盔弃甲这个词以外根本没别的可形容。
贺锦帆人很保守,别人笑得越厉害,他就越不知道怎么办,脸涨得通红,不断地擦着额角的汗,想弯腰下去拍拍简意澄的肩,手隔了两厘米又停住了,好像隔着玻璃看一个展品。
“帆帆,”简意澄在叫贺锦帆的时候总能让我不自觉地起一身鸡皮疙瘩,“我知道你嫌弃我。
你觉得我们都是男的。
但是爱情是不分性别的,你的前女友能给你做饭洗衣服,我也能——”他又开始不管不顾地哭喊起来,旁边的几个小孩儿也喝多了两杯酒,起哄着让贺锦帆去房间里陪他,推推搡搡地丢进去关上了门,没过一会儿贺锦帆就气喘吁吁地逃出来。
“他,他想抱我,还让我背他——”他猛烈地咳嗽,弯下了腰,好像刚参加完一场1500米长跑。
那几个小孩儿更起劲了,江琴也在,带着人躲在门边看,颤颤巍巍带着好奇,像在动物园里看一只老虎,生怕他扑出来把人拖进那个屋子。
果然没过多一会儿,道姑就衣衫不整地冲了出来,“帆帆,帆帆你又去哪儿了,我就那么让你想跑吗你就那么讨厌我吗——”他的声音变得很凄厉。
高亢地震得整个屋子都在回响。
江琴去拦他,他啪的一下打上江琴的手,“你们都是一伙的,”他指着满屋子的人恍然大悟,“你们就这么讨厌我吗?你们全都有事瞒着我,你们就是不想让帆帆和我在一起——”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他还像演琼瑶剧一样变本加厉地把所有的碟子,杯子,碗儿全摔了,“我算是看透你们了,”在一个玻璃杯破碎的清脆声音里他带着哭腔喊道,“你们,你们就是想看我的笑话!顾惊云——!”简意澄咬牙切齿地指着他,“今天晚上就是你把我灌醉的,你把我害成这样的你对我负责——” “哎哟,这你还记得,”顾惊云吐出一口烟雾来,悠闲地对着他笑,好像在看一只笼子里乱飞乱撞的白鹦鹉,这只白鹦鹉正在泪眼朦眬地找他的帆帆,“帆帆,”他摸索着往前走,“帆帆你不能不要我啊你在哪里——”又有几个小孩儿看着贺锦帆哄笑起来,贺锦帆终于忍不住了,踩着一地的酒和玻璃碎片走过去,“大哥,”他无奈地看着简意澄,“我是真的不喜欢你也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对男人没兴趣。
求求你了,就别拉着我和你一起丢人了行不行。
” 他沿着一地黄乎乎泛着泡沫的酒猛地扑了过去,“帆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显然极具一个良好的戏剧演员的天赋,“帆帆你在哪儿?”他被一个滑溜溜黏糊糊的凳子绊了一脚,摔在满地的狼藉里面,身体扭成一个草长莺飞的角度,还是很敬业地对着天空念着独白,“帆帆,我头好晕,我要回家,帆帆你背我回家——”他一边说着还一边抬起头来狠狠地撞着地,那种破碎的声音让人胆战心惊。
酒气和着潮湿的油味袅袅地升起来,就像满室挥发的硫磺。
“把他送回去吧。
”满屋子嘲讽的寂静里苏鹿的声音轻轻响起来。
顾惊云往一个罐子里弹了弹烟,靠在椅背里眯着眼睛笑:“我不去,”他摇摇头,“人家指名道姓让帆帆送呢,我怕路上他一高兴把我当成帆帆,我就贞洁不保了。
”屋子里的人笑得更欢了,贺锦帆满脸的难堪,好像要把头深深地埋到地下面去。
“那我去吧。
”苏鹿站起身来,“车钥匙借用一下。
”她带点歉意地笑了笑,朝顾惊云摊开手。
顾惊云看了看她,几秒钟的对峙之后他叹了口气,“行吧,我去送,”他认输一样地站起身来,轻轻嘟囔了一句,“这大雪天的。
”说不清是想挽回什么。
戏剧的女主角一走,大家也都失却了看戏的热情,纷纷手机电脑该玩儿什么玩儿什么,这种狼藉的屋子里短暂的平静被江琴的一声惊叫“哎我×——”终止了。
对,别以为惊叫就是指扶着心口娇喘连连的画面,春哥踩到了一大摊牛粪也会发出一声惊叫。
我忍不住好奇第一个凑上去看。
我看到简意澄把他QQ人人Facebook所有的状态都极其奔放地改成了“HeyFernandoIdon'tlikeyourgirlfriend,Ithinkyouneedanewone.Icanbeyourgirlfriend(顾惊云我不喜欢你的女朋友,我想你该换女朋友了。
可以考虑下我。
)”,还在顾惊云的留言板上刷了十多条这句话。
Fernando是顾惊云的英文名,我当时猛然觉得,他已经不是琼瑶笔下的人物了,是J.K.罗林笔下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奇幻色彩。
这句话显然不是针对苏鹿的,而是直指一切冲突矛盾的中心——徐庆春。
被一个如此心直口快热情奔放的基佬把歌词用到这儿,我觉得身处不远的加拿大的鉴婊狂魔艾薇儿现在一定噩梦连连。
然后顾惊云回来了,抖一抖身上的薄雪,被冻得微微缩起脖子,指尖还夹着烟,他看着一地湿漉漉闪闪发光的碎片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是凯旋归来的英雄,完全不知道满屋子的寂静里已经兵荒马乱刀光剑影。
江琴认真地看着顾惊云:“你是怎么的简意澄了?”她把手搭在椅背上,“我相信你的性取向,你肯定没对他做什么。
对了,估计是就因为你没做什么,他很失落受到了伤害想报复你——”有几个人此起彼伏地笑了,但我能感觉到有种巨大的东西充塞在空气里,他们连笑声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触碰到它。
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疲惫地靠在沙发背上,“徐姐后天就回来了,”他的声音里带着沮丧,“现在闹这出,大家赶紧收拾收拾细软跑吧。
” 江琴用眼神瞟了瞟围在人群中间的那台电脑,人们自动地给顾惊云分开了一条路,我能感觉到他像个舞台上经验不足的生角儿,脚步看似仪态万方,但步伐已经乱了,没有一拍踩在鼓点上。
“我×——”他看到了那几行字,拼尽全力地想在那张俏脸上摆出平时的那种悠闲嘲讽的笑来。
没有人能接得下去他的话,他自己也接不下去,寂静像个体积庞大的充气球,在这个空间里越吹越大,我忽然想起小的时候,我还住在那座省会城市旁边的小镇里,夏天的夜晚有人放电影,蛾子和无数的小虫子迷醉地绕着无数盏聚光灯飞来飞去,然后灯光暗了下来,人群慢慢地寂静了,这种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的寂静每次都让我手足无措,好像下一秒钟他们所有人就会一起长长地呼吸一口气,吹散黑夜里数千只蛾虫扑火的灵魂。
直到胶片慢慢地转动起来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好像岁月流动,电影屏幕上打出白森森的字,那时候放的都是老电影,常常有京剧清脆悠然的过门儿,一开始是打着散板,接着有行云流水一样的二胡声,最后锣鼓“啪”的一声响,是种不由分说的尘埃落定。
——一场戏开始啦。
【江琴】,2014
徐大小姐是在一个山雨欲来的下午回来的,天空就像一得了绝症仇恨社会的病人一样,把一切用力浇灌得阴冷苍白。我站在停车场的顶棚下面远远地看到了她,她十厘米的高跟鞋愤世嫉俗地踩在水坑里,一下一下溅起的水花好像手榴弹,方圆十米内都没有人想靠近,刚刚做完护理的长头发不断地往下滴着水,满脸都是被雨浇花了的黑色烟熏妆。
她像武侠小说里的高手一样抹一把脸,甩一甩头发,把Prada的单排扣大衣霸气地往我车里一扔,这就对了,李莫愁,梅超风,好像都是在这种天气里出场的。
“×他娘的,”她一屁股坐到后座上,把湿淋淋的雨气成团地带了进来,我觉得我的车一下沉了下去,“我跟你说,顾惊云那王八蛋绝对是跟哪个小贱货好上了,老娘这次回去把整个凯莱翻个底朝天也要给她找出来。
江琴我告诉你我跟那小贱货没完!” 我想起来今天早上登人人,不知道谁把徐庆春的机票信息照了照片发到网上,一下被人转载了30多次,转载回复都是热热闹闹的同一句话,“快收拾细软跑啊。
”幸亏这姐姐只玩儿微博,不上人人也不上QQ,否则准被气死,估计哪天想不开就得拎一炸药包到凯莱门口去来个同归于尽。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拐了个弯,好奇地问她,“谁告诉你的?” “用不着谁告诉我,我自己看出来的。
”她气哼哼地按了两下手机,“这么多年老夫老妻了这点事儿还看不出来。
走,江琴,我今天就给他来个突袭,看看他那小蜘蛛精到底长什么样——” 当然顾惊云没和什么小蜘蛛精在一起,徐庆春风风火火地冲进房间的时候他还没睡醒,我在楼下等着他们顺便煮了一袋速冻饺子,还没倒进去第二杯水就听见徐庆春歇斯底里地尖叫,“顾惊云我操你妈!你告诉我这简意澄是谁!他卷纸夹为什么在你床上——!”好嗓子,四弦一声如裂帛。
“你急什么啊,”顾惊云不慌不忙地抖了抖卷纸夹,“这是个男的。
我借我同学的作业来抄一下,你想到哪儿去啦?” “哼,王八蛋你就编吧,”徐庆春冷笑一声,“男的能写出这种字?是个男的也是同性恋,和女的有什么区别?贺锦帆不是你们班上的吗?林家鸿也是,你他妈怎么不管人家借作业非要找这个小贱人的?你们那些事儿你以为我没听说过?你的贱人在我空间里明目张胆地挑衅你知道吗?我在国内每天给你打十个电话你就像手残疾了似的不会接,躲我?好,你牛×,我这就搬走——”她把路易威登的旅行箱从楼梯上一脚踢了下来,回头指着顾惊云的鼻子骂道,“你别以为老子搬走你就得好了,告诉你老娘和你没完,我就让你那个贱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她又从二楼扔下一个AlexandraMcQueen的包,什么化妆镜睫毛膏全都碎掉了,哗啦啦的几声巨响。
顾惊云从房间里走出来,靠着门框,“你搬哪儿去?” 显然徐庆春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她几步走到前面去,朝着他的膝盖狠狠地踢了一脚,应该是用力过猛,满屋子都是她凄厉的尖叫,好像划破了一块玻璃,“顾惊云你个傻×我×你妈,你他妈滚啊,有多远滚多远——”我抬头往上看,她慢慢蹲下来了,声音里有浓重的哭腔,顾惊云走过去,也蹲下来轻轻地问她,“脚不疼吧?” 我忍不住地笑了,第一次听见有人被踢之后问踢人的人脚疼不疼的,徐庆春放声大哭起来,狠狠地抱住顾惊云,用力地捶打着他的背,“你怎么不去死啊。
”她趴在顾惊云的肩膀上吸了吸鼻子,声音沙哑,湿淋淋的,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跟你那个小婊子一起去死吧。
”顾惊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拍着她的背,“别吵了,”他的声音轻得就像无声无息飘下来的雪花一样,“别吵了。
已经没事了。
” 这两个人也是神奇,白天吵得张牙舞爪恨不得杀了对方,晚上就能若无其事地叫上一大票人出去唱K。
徐庆春不喜欢顾惊云的那些朋友,一路上话里冷嘲热讽,摆出一副压寨夫人的架子来,扬着头走路一扭一扭,都不拿正脸看人家。
苏鹿从林家鸿的车上下来,我能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地偷偷看着她,她仍然笑嘻嘻的,和平时没什么两样,还搂着夏北芦——夏北芦和所有凯莱的女孩儿都不一样,不化妆,不打扮,是那种从学校里刚走出来的真正的单纯,甚至是个无性别的小孩子模样,一点也没有这个年纪少女的体态。
我在她面前都不敢讲荤段子,甚至不敢大声笑。
徐庆春进了包厢就黏在顾惊云身上开始玩手机,贺锦帆和林家鸿他们几个点了一大堆陈奕迅张震岳的歌唱得风生水起,玛丽莲坐在我旁边,偶尔低着头对我笑笑。
我看到她修长的手指松松地挽起头发,肤如凝脂明眸善睐。
“江琴,你喝不喝奶茶?”她站起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声音哑哑的,好像是风吹过焜黄的梧桐叶。
“啊,好——”我对着她仓促地笑笑,正好对上她黑宝石一样流光溢彩的眼睛,她V领的薄毛衣把身体裹出一个曼妙的弧度。
我看着她摇曳生姿地走出去,心里莫名的一抖,然后看着自己身上笔挺僵硬的衬衫和凉凉的男式手表。
我残留的最后一点美丽和热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岁月完全地吞噬干净了。
好像被磨掉了边角再也转不动的旧齿轮。
16岁那年刚刚出国,迫不及待地把原来的校服剪成旧抹布,在国外的购物商场里一件件地试衣服,聚光灯照在镜子上,把我的轮廓照得圆润柔和—— 妈的,老子当年也是个妞。
我眯了眼睛看屏幕上陈奕迅声嘶力竭地吼着你当我是浮夸吧,脸上露出点嘲讽的微笑来。
然后徐庆春终于从你侬我侬里醒了过来:“给我点一首洛丽塔。
”她用命令的口吻对坐在点歌机前面的苏鹿说道。
夏北芦抬起头来,皱着眉头看了她一眼,轻轻摇了一下苏鹿的腿,贺锦帆坐在角落里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大姐您今年都20了还洛丽塔——” “姐愿意,你管呢。
”徐庆春跋扈地扬了扬头,夹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做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来,跟着音乐唱起歌。
可能是因为喊多了,她的声音粗糙得好像一个风中哗啦哗啦响的编织袋,配上这首甜美的歌显得格外的奇怪。
“和我跳舞吧,洛丽塔,白色的,海边的沙。
爱情还是要继续吧,十七岁,漫长夏。
” 徐庆春唱得很投入,完全没有发现身边的人已经静了下来,有的像看一个拙劣的小丑一样笑着看她,有的干脆低着头玩起了手机。
林家鸿推开门走出去了,“我要去洗手间——”他摆摆手解释道,那动作简直就是落荒而逃。
“喜欢一个人,洛丽塔,只喜欢一天好吗?或许从没有爱上他,只是爱了童话。
” 徐庆春在满屋的寂静里握紧了话筒,她也发现了四周充满了敌意,这种嘲讽的敌意像是四面八风席卷来的海浪,把她淹没了,吞噬了,她的话筒就像是一块木板,让她在死鱼和叶子烧焦的腥味里无休无止地漂流,她在这片孤独的敌意里底气不足地把脚别得紧紧的,像是被剥夺了王位的女王一样,挺了挺瘦削的脊背,咳了几声,硬撑着继续唱下去。
“那个野菊花开了的窗台,窗帘卷起我的发,我把红舞鞋轻轻地丢下,不在乎了,洛丽塔。
” 跟着献给爱丽丝轻灵的旋律,周围响起了轻轻的笑声,梁超往靠背上一躺,拖了长长的声音,“切了吧,大姐——”他朝苏鹿使了个眼色,苏鹿背朝着我,坐在点歌机前面,留下个色泽鲜艳的背影,然后她转过身,我本来以为她要去切歌,谁想到她忽然拿起麦克风来,迟疑地慢慢和上徐庆春的节拍。
“田野金黄了,洛丽塔,舞台就快搭好了。
我们一样吗,洛丽塔,对孤单习惯了。
” 苏鹿的声音很柔和,比徐庆春的声音略低一点,正好像是缓慢流动的温水一样,把一块破败不堪的编织袋温柔地轻轻托起来,轻盈地越过沙滩,越过礁石,变成水面上铺开的帆。
更多玩手机的人抬起头来了,他们本来以为苏鹿一定会找一切机会让徐庆春下不来台,眼神里都充满了讶异。
可是这两个声音合起来就有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绝妙的温暖,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满是来来回回冲刷的暖意,他们好像在被一种悠然降临的力量清洗。
“如果我不做自己的观众,还以为在爱着他。
我坐着飞机到海边找他,多疯狂啊,洛丽塔。
” 这首歌的旋律太单薄了,单薄得就像在寒冷里颤抖的蝉翼。
玛丽莲就踩着这片单薄的旋律,拿着几杯奶茶撞了进来。
本来拿着麦克风的人在KTV里是毋庸置疑的主角,但我忽然觉得我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哪怕只为了这一刻对上玛丽莲波光潋滟的眼睛。
在我张开嘴的那一刻,顾惊云和贺锦帆同时慢慢地哼起了这首歌的旋律,他们永远不会唱一首女生的歌,能哼出来调子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极限了,我在灯光交融的空旷里闭上眼睛,所有人的声音融在一起,好像几万股溪流汇集起来,变成了足以抵御寒冷的浪涛。
“都会忘记吧,洛丽塔,来不及带走的花,努力开放了一个夏,十七岁,海边,他。
” 玛丽莲和夏北芦也一个接一个地唱起来,小小的房间里被猝然来临的善意涂抹的光亮四射,好像是傍晚所有的路灯一瞬间亮起的长街。
所有的脸上一分钟之前的嘲讽和敌意变得荡然无存。
洛,丽,塔,舌尖轻轻碰触下颚,这是小仙女在黑夜里轻盈地擦亮的萤火。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房间里荡漾的是热腾腾的奶茶的甜香气味,然后所有人都静了下来,等徐庆春唱完最后的结句,“爱情还是要继续吧,十七岁,漫长,夏。
”几秒钟的默然,大家心照不宣地互相笑一笑,在这一刻所有人的眼神里都是从未有过的温情脉脉,平时他们就像看戏一样,事不关己地看着别人的大喜大悲。
屋子里的所有人在短暂的静默之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来,为了徐庆春,为了在场的所有人,也为了自己。
徐庆春坐在正中央,惊诧地看着大家,低下头去喜悦而羞涩地微笑了一下,那种表情就像一根被蓦然点亮的火柴,她转过脸去,迫不及待地看了一眼顾惊云,好像要分享这一刻的荣耀一样,顾惊云对她轻闲地笑,这两个人之间从来就没有过这种缓慢流动的安详。
直到我们走出了KTV,周围还是被一种温熙热闹的美好气氛笼罩着。
在西雅图空旷的黑夜里,我看到徐庆春感激地看了一眼苏鹿,然后走进顾惊云的车里——她们在这个晚上,共同分享了一个奇迹。
直到后来,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或者在大张旗鼓的广告牌上看到洛丽塔这三个字,都会不自觉地想起这个晚上。
我想,就凭这那一刻魔法一样在每个人心里猝然亮起的善意,就足够让我们这些命运多舛后来各自流落到天涯海角的人再相思相忆许多年。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玩家糯团子
- 反派逆袭攻略钧后有天
- 全修真界都想抢我家崽儿Yana洛川
- 我始乱终弃前任后他们全找上门了倔强海豹
- 起点文男主是我爸林绵绵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他的余温阿宁儿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同桌乃是病娇本娇候鸟阳儿
- 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01入学篇(上)佐岛勤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江湖人独孤红
- 九州·云之彼岸唐缺
- 佛系女主崩坏世界[快穿]实心汤圆
- 虫屋金柜角
- 首辅大人重生日常/今天也没成功和离时三十
- 芙蓉如面柳如眉笛安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纸之月角田光代
- 穿成废材后他撩到了暴躁师兄是非非啊
- 全星际都等着我种水果一地小花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浪漫事故一枝发发
- 每天都在偷撸男神的猫红杉林
- 我叫我同桌打你靠靠
- 路过人间春日负暄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我的男友是霸道总裁月下笙歌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沉迷撒娇虞子酱
- 被抱错的原主回来后我嫁了他叔乡村非式中二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非典型NTR一盘炒青豆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农村夫夫下山记北茨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网恋同桌归荼
- 烽火1937代号维罗妮卡
- 煎饼车折一枚针/童童童子
- 发动机失灵自由野狗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共同幻想ENERYS
- 离心ABO林光曦
- 天才作家o白野o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挚爱白鹭蓂荚籽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竹木狼马巫哲
- 听说,你要娶老子寒梅墨香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一觉醒来和男神互换了身体浮喵喵喵
- 情终孤君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夏日长贺新郎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怀了总裁的崽沉缃
- 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后桑奈
- 不差钱和葛朗台寻香踪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根音(ABO)笼羽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没完晚春寒
- 怀孕之后我翻红了[娱乐圈]核桃酸奶
- 戏精配戏骨陈隐
- 有只海豚想撩我焦糖冬瓜
- 天才作家o白野o
- 流量小生他天天换人设西西fer
- 我还喜欢你[娱乐圈]走窄路
- 撒谎精发芽芽
- 变奏(骨科年上)等登等灯
- 竹马危机萧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