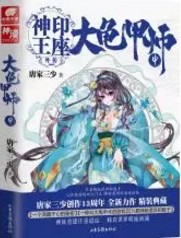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1 姐姐的丛林(2/3)
——是你姐呀!我还以为是高二的那个王什么婷。
——SB!没看见戴着S大的校徽呢。
——我靠!老子就是没看清楚又怎样? ——姐,你好! ——林安琪再见!还有姐,再见…… 好像他们不喊着叫着就不会说话一样,可是喧闹过的楼梯突然安静下来,还真有点让人不习惯。
姐姐突然说:“安琪,告诉你件事,你不可以对任何人说。
” “你有男朋友啦?”我惊讶地笑着。
她不理我,自顾自地说:“绢姨怀孕了。
” 我一时有点蒙:“那,那,也无所谓吧。
反正她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
” 姐姐笑了:“这个孩子不是‘奔驰’的。
”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在想什么——确切地说,我的思维在一片空白的停顿中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想什么,该想什么。
姐姐还是不看我,还在说:“我今天到绢姨那儿去了,门没锁,可她不在家,我看见了化验单,就在桌子上。
前天,前天她才跟我说,她和‘奔驰’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做过。
” “做过”,这对我来说,是个有点突兀的词,尽管我知道这代表什么——我是说,我认为我知道。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一直到家门口,我突然问姐姐:“妈知道吗?” “安琪。
”姐姐有些愤怒地凝视着我,“你敢告诉妈!” “为什么不呢?”我抬高了嗓音,“妈什么都能解决,不管多大的事,交给妈都可以摆平不是吗?”激动中我用了刘宇翔的常用词。
“安琪。
”姐姐突然软了,看着我,她说,“你答应我了,不跟任何人说,对不对?” …… “我知道,我没想说,我不会告诉妈,你放心。
”我看着姐姐惶恐的眼神,笑了,“没有问题的,绢姨也是个大人了,对吧。
她会安排好。
”我的口气好像变成了姐姐的姐姐。
我深呼吸一下,按响了门铃。
餐桌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妈妈、绢姨、姐姐和我。
四个人里有三个各怀鬼胎——绢姨怀的是人胎。
妈妈端上她的看家节目:糖醋鱼。
她扬着声音说:“难得的,今天家里只有女人。
”“我不是女人。
”姐姐硬硬地说。
“这么说你是男人?”绢姨戏谑地笑着。
“我是‘女孩’。
”姐姐直视着她的眼睛。
“对,我也是女孩,我是小女孩。
”我笑着说。
这个时候我必须笑。
“好。
”妈妈也笑,“难得今天家里只有女人,和女孩,可以了吗?” “大家听我宣布一件事。
”妈妈的心情似乎很好,“今天我到安琪的美术老师那儿去过了。
安琪。
”妈妈微笑地看着我,“老师说他打算给你加课,他说明年你可以去考中央美院附中,他说你是他二十年来教过的最有天分的孩子。
” “天哪——”绢姨清脆地欢呼,“我们今天是不是该喝一杯,为了咱们家的小天才!”然后她就真的取来了红葡萄酒,对妈妈说:“姐,今天无论如何你要让安琪也喝一点。
” 妈妈点头:“好,只是今天。
还有安琪,今天你们班主任给家里打电话了,他说你最近总和一个叫刘什么的孩子在一起,反正是个不良少年。
妈妈不是干涉你交朋友,不过跟这些人来往,会影响你的气质。
” 绢姨突然大笑了起来。
“你吃你的。
”妈妈皱了皱眉。
“姐,你还记不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一个字都不差!” “你——”妈妈也笑,“十四岁就成天地招蜂引蝶,那个时候爸就跟我说,巴不得你马上嫁出去。
” “你还说!”绢姨开心地嚷,“爸最偏心的就是你,从小就是……” 对我而言,所有的声音都渐渐远了,我的身体里荡漾着一种海浪的声音,遥远而庄严地喧闹着。
“中央美院附中”,我没有听错,我不惊讶,这一天早就应该来临,可是我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一辈子画画了吗?一辈子把我的生活变成油彩,再让油彩的气息深深地沉在我的血液中,一辈子,不离不弃?天哪我就像一个面对着神父的新娘——“新娘”,我想我脸红了。
“嘿——小天才!”我听到那个似乎危机重重的“准新娘”愉快的声音,“是不是已经高兴得头都晕了?绢姨星期一要出去拍照,大概两个星期才会回来。
最近我突然想到郊外去逛逛,所以决定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带上你和北琪,把谭斐也叫来,明天我们四个一起去玩,怎么样?” “叫他干吗?”姐姐皱了皱眉。
“你说呢——”绢姨有点诡异地笑着,眨了眨眼睛。
“你们说。
”妈妈突然开口了,“谭斐跟我们北琪,合不合适?” “妈!”姐姐有点惊讶,有点生气地叫着。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妈妈笑了,“你以为我跟你爸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叫他来?要是你和谭斐……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有你爸爸在,谭斐一定会留在这所大学里,你们当然可以一起住在家里。
把你交给谭斐,爸爸妈妈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姐姐重重地放下了碗。
她盯着妈妈的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我配不上谭斐!” “胡说些什么!”妈妈瞪大了眼睛。
“什么叫胡说?”姐姐打断了她,“你看得见,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见,要不是因为讨好爸,他谭斐凭什么成天往咱们家钻?我就算是再没人要,也不稀罕这种像狗一样只会摇尾巴的男人!” “闭嘴!”妈妈苍白着一张脸,真的生气了。
“北琪。
”绢姨息事宁人地叫她。
“你们胡说。
”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
刚才的那场大人们的争吵中,她们都忘记了我。
“安琪这跟你没关系。
”绢姨有点急地冲我眨了一下眼睛。
“你们胡说。
”我有点恶狠狠地重复着。
我绝对、绝对不能允许她们这样侮辱谭斐,没有人有资格这样做。
我感觉到了太阳穴在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我的神经,我的声音有一点发抖: “谭斐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谭斐才不是那种人,你们这样在背后说,你们太卑鄙了。
”我勇敢地用了“卑鄙”这个词。
“你懂什么?”妈妈转过脸,有点惊讶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没有退缩,跟她对视着。
尽管我知道,也许妈妈会看出我的秘密来,可我还是要竭尽全力,保护我的谭斐。
我在保护他的什么呢?我不知道。
眼泪突然间开始在身体里回响,就要蔓延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电话铃的声音。
感谢电话铃,我有了跑出去的理由。
听见妈妈在身后跟绢姨叹气:“她们的爸爸把她们宠坏了——” 我拿起电话,居然是刘宇翔。
“林安琪。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沙哑,“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个干什么……” “麻烦你告诉你姐姐,我要追她。
”说完这句话他就挂了,酷得一塌糊涂。
三 刘宇翔 就这样,又一个角色在姐姐的舞台上登场,以一个有点荒唐的方式。
我没有追问刘宇翔为什么喜欢上了姐姐,姐姐也该有个人来追了,虽然这个人有点离谱,也是好的。
我没有了关心其他人的心情。
原来我搞错了真正的情敌,原来这不关绢姨什么事,他们想把姐姐塞给谭斐。
好吧,这下我更不会输了。
等一下,如果不是为了绢姨,谭斐为什么总是来我们家?他知道爸爸妈妈心里想的吗?也许。
谭斐难道会真的是为了姐姐?不可能的。
难道说……我的心就在此时开始狂跳了。
不对,林安琪,我对自己说,人家谭斐是大人,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可是那又怎样呢?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天哪,我长长地叹着气:让我快一点长大吧,我就快要长大了不是吗? 我依然在午夜和凌晨时分画画。
大块的颜色在画纸上喧嚣着倾泻,带着灵魂深处颤抖的絮语,我震荡着它们,也被它们震荡着。
我听得见身体里血液的声音,就像坐在黑夜里的沙滩上听海潮的声音一样,自己的身体跟这个世界之外某种玄妙而魅惑的力量融为一体。
我想如果是绢姨的话,她会用三个字来概括这种感觉:“真性感。
”性感,是这样的意思呀。
绢姨出去拍照的这一个礼拜,姐姐天天晚上都会到我的小屋来聊天,带着那种我从没见过的红晕。
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姐姐总是几乎一字不落地“背诵”她和刘宇翔今天电话的内容。
刘宇翔采用的是他惯用的方式,“初级阶段”用比较绅士的“电话攻势”,尤其是对比较羞涩的女孩子。
刘宇翔告诉过我:“对那些好学生、乖乖女,欲速,则不达也。
” “他问我周末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姐姐扬着脸,对着窗外的夜空,抑制不住地微笑,“我说我下星期要考试了,很忙,你猜他怎么回答我?”姐姐转过脸,眼睛是被那个微笑点亮的,“他说:对不起请你听清楚,我是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不是问你有没有时间。
”姐姐笑了,“他还挺霸道。
” 鬼知道刘宇翔那个家伙用上了哪部片子的台词。
“姐。
”我有点不安地问她,“你不是就只见过他一次吗?”“对呀,是只有一次,但是我记得他很帅的对吧?”“他比你小三岁。
”“那又怎样?”姐姐问。
“而且他是个万年留级生,就知道抽烟泡迪厅打群架。
爸爸妈妈准会气疯。
”“有什么关系吗?”姐姐几乎是嘲讽地微笑了。
“我没有问题了。
”我像个律师那样沮丧地宣布着,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笑得几乎是妩媚的姐姐。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姐姐夜空下泛红的、可以入绢姨镜头的笑脸。
我进了大学,看够了那些才十八岁却拥有三十八岁女人的精明的女孩,看够了她们用自己的头脑玩弄别人的青春,我才知道:那一年,我二十岁的姐姐,为一个十七岁的小混混在夜空下闪亮着眼睛微笑的姐姐,原来这么可爱。
周末姐姐自然是答应了刘宇翔的约会。
那天早上我们家的信箱里居然有一枝带着露珠的红色玫瑰。
姐姐把它凑到鼻子边上,小心地闻着,抬起头笑了:“安琪,我还是更喜欢水仙花的香味。
”她的声音微微发着颤,脸红了。
“拜托。
”我说,“哪有这种季节送水仙花的?”“也对。
”她迟疑了一秒钟,然后拿起了电话,第一次拨出那个其实早已经烂熟于心的号码,“喂,刘……宇翔吗?是我。
我今天有空。
” 星期六的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小屋里画画,听见姐姐哼着歌出门。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感觉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姐姐的声音里有种很脆弱的甜蜜。
我知道姐姐没看见过刘宇翔紧紧皱眉的样子,只不过在她的想象中,刘宇翔已经成了她的情人。
爱情,到底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才绽放,还是早就已经在那里寂寞开无主地绽放着,只等着一个人的出现呢?想象着姐姐和刘宇翔约会的场景,我都替姐姐捏一把汗。
她连平时的小考试都会紧张得要死,真不知道她有没有办法来应付刘宇翔那个有的是花招的家伙——比如,他们会接吻吗?如果刘宇翔坏笑着猛然俯下头去,姐姐懂得自然而然地迎上自己的嘴唇吗?很难讲,不过要是我的话,如果谭斐在某一天突然吻住我,我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
会有那一天的,我对自己说。
“早就想看看你的画了。
”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怎么会——是谭斐呢。
谭斐对我微笑着——他的脸真的是完美——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微笑,“安琪,其实我早就想看看你的画,可以吗?” “可以。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该死,我应该更大胆一点不是吗? 他走了过来,很有兴趣地看着我的画纸。
“这么多的蓝色,”他说,“这幅画叫什么名字?”他笑着问我,就像在问幼儿园的小孩儿。
我冷冷地看他一眼,什么都没说。
“我想你画的是大海。
对吧?一定是大海。
”他依旧是那种语气,好像认为他是在帮助一个叼奶瓶的小朋友发挥想象力。
“《将进酒》。
”我说。
“什么?”他显然是没听清楚。
“就是李白的那首《将进酒》,这些蓝都是底色,一会儿我要画月亮的。
我要画的是喝醉了酒的李白眼睛里的月亮。
”除了我的老爸和谭斐以外,我最喜欢的男人就是李白。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真他妈的性感,“如果我是个唐朝的女孩。
”我对谭斐说,“我一定拼了命地把李白追到手。
” “你要画李白吗?”他问我,明显认真了许多。
“不画,只画月亮。
因为没有人可以画李白。
”我说。
“我可以问,你想把月亮画成什么样子吗?”他专注地看着我,用他很深的眼睛。
我低下头,每一次,当他有些认真地看着什么的时候,那双眼睛就会猝不及防地烫我一下。
“裸体。
”我的脸红了,“膝盖蜷在胸口的女人的裸体。
李白没有爱过任何女人,除了月亮,月亮才是他的情人。
”我说得斩钉截铁。
我没有告诉谭斐,我的这个感觉来源于一个叫《情人》的电影。
是我和刘宇翔他们在一个肮脏的录像厅里看的。
他们激动地追随着那些做爱的场面——术语叫“床戏”,可我,忘不了的是那个女孩子的身体,那种稚嫩、疼痛的美丽,苍白中似乎伤痕累累。
“可是今天的月亮已经变成《琵琶行》里的那个女人了。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屈原李白杜甫们都死了,天文望远镜照出来她一脸的皱纹,再也没人来欣赏她。
她是傻瓜,以为她自己还等得来一个李白那样的男人呢。
” 谭斐有点惊讶地望着我。
然后他慢慢地说:“安琪,你很了不起。
” “画好了以后我把它送给你。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但还是勇敢地抬起头,注视着他的脸。
“谢谢。
”他笑了。
尽管那依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微笑,但我已经很高兴了。
我低下头,装作调色的样子。
我绝对不可以让他看出来我的手指在发颤,他会猜出来我喜欢他的。
客厅里一声门响,然后是姐姐的脚步声。
“姐你回来啦——”我叫着。
跑了出去。
姐姐脸上没有那种我想象中的红晕,她现在反倒是淡淡的,就好像她是和平常一样刚从学校里回来。
“姐,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挺好。
”她笑笑,像是有一点累的样子。
“再讲讲嘛——” “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挺好。
”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奇怪的温柔。
“北琪你今天很漂亮。
”谭斐对姐姐说。
“谢谢。
”姐姐点点头,没有表情。
姐姐再也没有对我提过那天她和刘宇翔的约会。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接吻。
只知道从那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刘宇翔只打过两个电话。
接完第二个电话的那天,姐姐没有吃午饭,妈妈摸摸姐姐的额头:“是不是病了?”姐姐把头一偏:“没有。
”我看见姐姐的眼里泪光一闪。
我拨通了刘宇翔家的电话:“刘宇翔,你给我滚到学校来,我在操场等你。
” 那是记忆里最漫长的一个下午。
春天的风很大。
学校的操场上扬着沙。
我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差一刻钟就满三个小时的时候,刘宇翔来了。
他的头发被风吹乱了。
慢慢地,走到我的面前——我就站在国旗的旗杆下面,他一眼就看到了我。
我们都没说话,我想如果有人在操场边上的楼里看着我们的话,会奇怪地发现两个在风中沉默的小黑点。
“林安琪……” “刘宇翔。
”我们同时开了口。
他说:“你先说。
” “刘宇翔。
”我问,“如果你不喜欢我姐姐,为什么要追她?”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他慢慢地说,“可能因为是傍晚了吧,光线的关系,觉得她真像吴倩莲。
可是真到约会那天,在阳光下看她,发现错了。
对不起,我……”他困难地解释着,“我知道我说的不清楚,可是我承认,我承认决定追她是有点仓促了——” “刘宇翔。
”我打断了他,几乎是有点悲愤地打断了他,“我从一开始就有点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姐姐不够漂亮,不,不是不够漂亮,是很不漂亮,可是她善良——好像你们男生不太在乎这个。
我还以为这一次,姐姐真的找得到一个人来爱她——”我重重地喘着气。
“林安琪。
”他说,“只有你这种小孩儿才动不动就爱不爱的。
我——”他笑了,“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我追女孩儿是为了泡,不是为了爱。
” “你浑蛋。
”我说。
他看着我:“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 “浑蛋。
”我重复。
他走近了两步,低下头,吻了我。
一阵短暂的眩晕,远方的天在呼啸。
他放开我,开始点烟。
可是风太大了,他按了好多次打火机才点着——他正点的点烟姿势因此变得狼狈。
终于点着的时候,他瞟了我一眼——居然有点羞涩。
“刘宇翔你这个王八蛋!”我尖叫着扑了上去,打掉了他的烟和打火机。
我不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骂尽了我知道的脏话。
他扭住了我的胳膊,我挣脱不出来,于是我用膝盖狠狠地撞他的肚子。
他真的被我激怒了,他开始打我,他的拳头落在我的背上、肩上。
我撕扯他的衣服,用尽全身力气咬他的手臂。
有一双陌生的手从后面护住了我的背,把我们拉开。
我依旧尖叫着,挣扎着,挥着拳头。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吼:“你这样打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丢脸!”然后是刘宇翔的吼声:“你自己问她是谁先动的手?!”那个陌生人紧紧地抱着我,箍着我的身体,他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小拳头。
他说:“好了,安琪。
听话——”我终于安静下来。
他不是陌生人,他是谭斐。
眼泪是在这个时候涌出来的。
我梦想过多少次,在我无助的时候,谭斐会像从天而降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还以为这种事永远只能发生在电影里,现在这变成了真的:他就在这儿,紧紧地搂着我。
他的外套,他的味道,他的体温……可是我把我的初吻弄丢了,那是我留给谭斐的,刘宇翔那个混蛋夺走了它。
我哭着,我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这么难过过。
“安琪,乖,好孩子,没事儿了安琪。
”谭斐的声音真好听。
他理着我乱七八糟的头发,看着我,伸出手抹了抹我的泪脸,然后笑了。
我也笑了,是哭着笑的。
笑的时候发现嘴角里腥腥的,我想是刚才让刘宇翔的手表划破的。
他捧着我的脸:“听我说,安琪,是你爸爸让我来学校找你的。
我们必须马上到医院去。
你绢姨出车祸了,很严重。
” “她会死吗?”我问。
“还不知道。
”他说,“正在抢救,所以你爸爸才会让我来找你。
” 我点点头。
谭斐拉起我的手,我们走了出去。
他的手真大,也很暖和。
其实那家医院离我们学校特别近,可是记忆中,我们那天走了好久。
是绢姨的灾难把那天的我还有谭斐连在一起的,这样近,要不是绢姨还生死未卜的话,我就要感谢上天了。
绢姨的劫难就在这种温暖的瞬间里变得遥远,变得不真实,直到我看见手术室上方的灯光。
妈妈有点异样地望着我的脸。
我这才发现原来谭斐一直拉着我的手。
我的手从谭斐的手里坠落的一瞬间,手术室的门开了,惨白的绢姨被推了出来。
这么说她没死。
我看见姐姐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她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算得上是“神色”的东西。
爸爸妈妈迎上那个主刀的医生。
医生白衣、白帽、白口罩,露着那双说不上是棕黑色还是深褐色的眼睛,像是个鬼。
后来一个身段玲珑的女护士走了出来,袅娜地扭着腰,怀里抱着的白床单上溅满了血。
很多血,我奇怪我为什么依然认为我见到的是一条白床单。
她心满意足地哼着歌,是王菲的《红豆》。
我走到了洗手间。
打开水龙头,把水撩在脸上。
从对面脏脏的镜子里看见了窗外的夕阳,火红的。
我在自己那么多的画里向它致敬,为了它的化腐朽为神奇——经它的笼罩,再丑陋的风景也变得废墟一般庄严,再俗气的女人也有了一种伤怀的美丽;可是就是它,我爱的夕阳,跟我的姐姐开了这样大的一个玩笑。
我模糊地想着,走出那间不洁净的洗手间。
谭斐站在绢姨病房的门口,逆着夕阳,变成一道风景。
可对我来说,这已经没什么神圣的了。
“安琪。
”他有点不安地叫我,“安琪你怎么了?” 我想我快要睡着了。
闭上眼睛的一刹那,我的眼前是一片让人目眩的金色,金色的最深处有个小黑点——我一定是做梦了,我梦见我自己变成了一块琥珀。
四 我 我生病了。
妈妈说我倒在绢姨的病房门口,发着高烧。
病好了回到学校以后,再也没见过刘宇翔,有人说他不上学了,还有人说他进了警校,我倒觉得他更适合进公安局。
绢姨正在痊愈当中。
我和姐姐每天都去给她送妈妈做的好吃的。
绢姨恢复得不错,只是精神依旧不大好。
她瘦了很多,无力地靠在枕上,长长的卷发披下来,搭在苍白的锁骨上。
原来没有什么能夺走绢姨的美丽。
我们终于见到了一直都很神秘的“奔驰”——个子很矮、长相也平庸的男人。
他站在绢姨的床前,有点忧郁地望着她的睡脸。
可是他只来过一次,后来就没有人再提绢姨的婚礼了。
这场车祸让她失去了腹中的孩子,倒是省了做人工流产的麻烦,但是“奔驰”知道了她的背叛。
还有一个秘密,妈妈说这要等绢姨完全好了以后再由她亲自告诉绢姨:绢姨永远不会再怀孕了。
我倒觉得对于绢姨来讲,这未必是件坏事。
——不,其实我不是这么觉得,我这样想是因为我很后悔。
要是我当时跟妈妈说了这件事,也许妈妈不会让绢姨出这趟远门的,至少会……也许这样,绢姨的婚礼就不会取消。
想到这里我告诉自己:不,这不关我的事,绢姨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对吗? 绢姨出院以后又搬了回来,所以我和姐姐又一起住在我们的小屋里。
不过姐姐现在只有周末才会回家。
家,好像又变回以前的模样,就连那幅《纽约》都还依然挂在墙上。
只不过,星期六的晚餐桌上,多了一个谭斐。
妈妈的糖醋鱼还是一级棒,可是绢姨不再像从前那样,糖醋鱼一端上桌就像孩子一样欢呼,只是淡淡地扬一下嘴角,算是笑过了。
所有的人都没注意到绢姨的改变,应该说所有的人都装作没注意到。
倒是谭斐比以前更主动地和绢姨说话,可是我已经不再忌妒了。
那次手术中,他们为绢姨输了很多陌生人的血。
也许是因为这个,绢姨才变得有点陌生了吧。
日子就这样流逝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察不出来的方式,直到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我环顾着饭桌,每个人都有一点惊讶,“我不想去考中央美院附中了。
” 寂静。
“为什么?”爸爸问我。
“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画画。
”我说,故作镇静。
“你功课又不好,又不喜欢数学,以你的成绩考不上什么好高中……” “好高中又怎么样呢?”我打断了爸爸,“姐姐考上的倒是最好的高中,可要不是因为爸爸,不也进不了大学吗?” “少强词夺理。
”爸爸皱了皱眉,“姐姐尽力做了她该做的事情。
你呢?”爸爸有点不安地看看姐姐。
姐姐没有表情地吃着饭,像是没听见我们在说什么。
“那你们大人就真的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事情,什么是不该做的吗?” “你……”爸爸瞪着我,突然笑了,“安琪,你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啊?”于是我也笑了。
“先吃饭。
”这是妈妈,“以后再说。
” “安琪。
”谭斐说,“你这么有天赋,放弃了多可惜。
” “我们家的事情你少插嘴。
”姐姐突然说,“你以为自己是谁?” 满座寂静的愕然中,姐姐站了起来:“对不起,谭斐,我道歉。
爸,妈,我吃饱了。
” 绢姨也突然站了起来:“我也饱了,想出去走走,北琪你去不去?” “还有我,我也去。
”我急急地说。
至今我依然想得起来那个星期六的夜晚。
刚下过一场雨,地面湿湿的。
整个城市的灯光都变成了路面上缤纷的倒影。
街道是安静的——这并不常见。
汽车划过路面,在交错的霓虹里隐约一闪,在那一瞬间拥有了生命。
绢姨掏出了烟和打火机。
“你才刚刚好一点。
”姐姐责备地望着她。
绢姨笑了:“你以为我出来是真的想散步?”打火机映亮了她的半边脸,那里面有什么牵得我心里一疼。
“北琪。
”她长长地吐着烟,“知道你有个性,不过最起码的礼貌总还是要的吧?”她妩媚地眯着眼睛。
绢姨终于回来了。
姐姐脸红了:“我也不是针对谭斐。
” “那你就不该对谭斐那么凶!”我说。
“你看。
”绢姨瞟着我,“小姑娘心疼了。
” “才没有!”我喊着。
“宝贝。
”绢姨戏谑着,“你那点小秘密瞎子都看得出来。
” “绢姨。
”姐姐脸上突然一凛,“你说什么是爱情?” “哈!”她笑着,“这么深奥的问题?问安琪吧——” “我是认真的。
”姐姐坚持着。
“我觉得——”我拖长了声音,“爱情就是为了他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
” “那是因为你自己心里清楚没人会逼你去为了他死。
”绢姨说。
我有一点恼火,可是绢姨的表情吓住了我。
“我爱过两个男人。
”她继续,“一个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另一个就是……”她笑着摇摇头,“都过去了。
” “另一个是谁?绢姨?”我急急地问。
是那个让她怀了孩子的人吗?现在看来不大可能是谭斐。
总不会是我爸爸吧?一个尘封已久的镜头突然间一闪,我的心跳也跟着加快了。
“安琪,问那么多干吗?”姐姐冲我使着眼色。
虚伪。
我不服气地想。
你敢说你自己不想知道? 一辆汽车划过了我们身边的马路,带起几点和着霓虹颜色的水珠。
绢姨突然问:“我住院的那些天,他真的只来过一次吗?我是说——后来,在我睡着的时候,他有没有来过?” “他是谁?”我问。
“没有。
”姐姐和我同时开的口,“不,我是说,我没有见到。
” “那个孩子是一个大学生的。
”绢姨静静地说,“我们就是一群人去泡吧——我喝多了……本来觉得没什么的,本来以为做掉它就好了……”她眼眶一红。
“绢姨。
”姐姐拍拍她的肩膀。
“我太了解他了,”灯光在绢姨的眼睛里粉碎着,“他不会原谅这些。
不过这样也好。
我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要是我们真的结了婚,说不定哪天,他会听说我过去的事情,那我可就真的惨了。
”绢姨笑笑。
谁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他。
我还以为绢姨不过是看上了那辆奔驰,我还以为他不过是有了香车还想要美女。
那个个子很矮、长相平庸的男人,我的绢姨爱他,我美丽的绢姨。
那天晚上姐姐回学校去了,当然是谭斐陪姐姐回去的。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我睡不着。
我也不想画画。
这是第一次,在很激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用颜色去宣泄。
我知道了一件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它超出了我的边界——就是这种感觉。
闭上眼睛,我的眼前就会浮现错落的霓虹中,绢姨闪着泪光的眼。
可是姐姐就知道这一切。
我想起那天,姐姐告诉我绢姨怀孕时那一脸的忧伤。
原来姐姐之所以难过是因为绢姨背叛了她自己的爱情。
是从什么时候起,姐姐了解了这么多呢? 妈妈在外面敲着门:“安琪,天气热了,妈妈给你换一床薄一点的被子。
” 妈妈进来,换过被子以后,她坐在床沿,摸着我的头发:“安琪,爸爸和妈妈都觉得,你会更优秀。
” “噢。
”我心不在焉地应着。
“安琪。
”妈妈继续着,“你发烧的时候,一直在叫‘谭斐’。
” 我抬起头,愕然地看着妈妈的脸。
“妈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想去考美院附中,但我觉得这和谭斐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宝贝,妈妈也有过十四岁——”妈妈笑了,“可是妈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如果我真的跟我十四岁那年喜欢的男人结婚,我会后悔一辈子。
安琪,爸爸和妈妈觉得你是个有天赋的孩子,你的一生不可能被圈在一个城市里,你应该而且必须走出去;至于谭斐呢,是个不错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很希望他跟你姐姐……但是你,妈妈知道将来安琪的丈夫是个优秀的男人,而不仅仅是‘不错’而已,你懂了吗?” “不懂。
”我说。
“我十四岁那年喜欢的是宣传队里一个跳舞的男孩。
”妈妈说,“那个时候我只能坐在台下,仰着头看他。
妈妈今年四十岁了,如果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大概今天我不会再抬着头看他,因为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她知道世界上还有你爸爸这样的男人。
安琪,爸爸妈妈爱你们,所以我们要为你的前途尽一切力量,我们也要为了你姐姐一辈子的幸福尽一切力量。
安琪是好孩子,不要给姐姐捣乱,明白了?” 妈妈亲亲我的额头,走了出去,轻轻地关上门。
我最终还是去考了中央美院附中,不过我没有考上。
放榜那天我挤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意料之中地没有找到我的名字。
周围有人开始欢呼,有人开始大哭,有人踩了我的脚。
一切都变得像个站台。
印象中,站台上总是难过的人多些。
北京真是个大城市,我想,容得下这么多的人。
回来后我的老师拍着我的肩膀:“安琪,这没什么,很多大画家年轻的时候,都不被人赏识。
” 这话对我没用,因为就算那些人年轻的时候不曾被人赏识,他们毕竟成了大画家。
只有成功的人才有回忆“不堪回忆”的资格。
回到家以后我最不想见的人就是绢姨,因为最终让我决定去考这个倒霉的学校的人,是她。
那是一个碰巧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家的下午。
那段时间我正和爸爸妈妈僵持着,我不肯去美术老师家上课,妈妈只好给老师打电话说我不舒服。
就是那个下午,绢姨走到我面前,像所有的人一样问我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去考中央美院附中。
我已经受够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跟她说不考又死不了人。
绢姨看着我,问:“你是害怕考试,还是害怕考上?我想是后者,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么问?”我盯着绢姨,“你也跟我妈妈一样,以为我是害怕去北京念书就要离开谭斐对不对?”我的声音不知不觉间抬高了,“为什么你们大人都这么喜欢自作聪明呢?你们以为我这些天过得很高兴是不是?告诉你,我不想去考是因为我害怕画画了。
再这样画下去,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眼泪闯进了我的眼眶,可我依然倔强地仰着脸,“我画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可是我自己画完以后就会觉得它是真的,可是它总归还是假的!我不想变成一个一辈子都分不清真假的人!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问我为什么,我真的说出来你们会懂吗?” “这么说,你怕的还是考上?”绢姨的语气依然安静。
“就算是吧。
”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
“你还没有去考,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考得上?”她慢慢地说。
这句话打中了我。
“你知不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讲,你想的东西都太奢侈了?——因为你从小什么都不缺,你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考上这个学校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在北京拍过那些孩子们,从很偏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我的师尊遍布修真界/全修真界为我火葬场薄夭
- 表妹软玉娇香渊爻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白月刚马桶上的小孩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与婠婠同居的日子李古丁
- 被空间坑着去快穿南宫肥肥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他的余温阿宁儿
- 召唤富婆共富强蒙蒙不萌
- 江湖人独孤红
- 射雕英雄传金庸
- 全娱乐圈都以为我是嗲精魔安
- 复刻少年期[重生]爱看天
- 燕云台(燕云台原著小说)蒋胜男
- (综漫同人)异能力名为世界文学谢沚
- 全星际都等着我种水果一地小花
- 玫瑰帝国6·辉夜姬之瞳步非烟
- 锦帐春慢元浅
- 真爱没有尽头科林·胡佛
- 神州奇侠正传温瑞安
- 剑海鹰扬司马翎
- 武极宗师风消逝
- 影帝霸总逼我对他负责牧白
- 少帝春心寒鸦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过分尴尬小修罗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深处有什么噤非
- 烈酒入喉张小素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眼泪酿宴惟
- 方寸暂停一切事务所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夏日长贺新郎
- 不息阿阮有酒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你听谁说我讨厌你飞奔的小蜗牛
- 催稿不成反被撩一扇轻收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跌入温床栗子雪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学长在上流麟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我估计萌了对假夫夫怪我着迷
- 杨九淮上
- 大叔,你好大江流
- 不朽神王犁天
- 红楼大贵族桃李不谙春风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老公你说句话啊森木666
- 方圆十里贰拾三笔
- 前炮友的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的前炮友,我们在一起了灰叶藻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可怜在娃综成了大佬团宠飞禽走兽
- 春生李书锦
- 沉迷撒娇虞子酱
- 循规是笙
- 不差钱和葛朗台寻香踪
- 阻流三眠柳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离心ABO林光曦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天才作家o白野o
- 祖谱逼我追情敌[娱乐圈]李轻轻
- 我是个正经总裁[娱乐圈]漫无踪影
- 和校草联姻之后芝芝猫猫
- 校园禁止相亲!佐润
- 轻狂巫哲
- 他喜欢白月光味信息素等登等灯
- 意外招租而苏
- 被男神意外标记了青柠儿酸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被宠坏的替身逃跑了缘惜惜
- 眼泪酿宴惟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狭路相逢我跑了心游万仞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分手后我们成了顶流CP折纸为戏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成了死对头的“未婚妻”后桑奈
- 巨星是个系统木兰竹
- 卖腐真香定律劲风的我
- 人帅路子野a苏生
- 我到底上了谁的婚车[娱乐圈]五仁汤圆
- 戏精配戏骨陈隐
- 老大,你情敌杀上门了沐沐不是王子
- 天才作家o白野o
- 明日星程金刚圈
- 色易熏心池袋最强
- 错位符号池问水
- 和校草联姻之后芝芝猫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