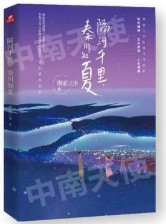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部 19(2/3)
头朝下抬到脚灯那里,想把他的头发点着。
”听到这话,拉尔夫眨了两三下眼,然后急忙往帐篷里看,仿佛要确认里面没有火苗,不会有哪个不友好的观众想用它来捣乱。
然后他厌恶地看了一眼他的烟,把它给扔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我应该再去把演讲过一遍。
”我还没来得及张开嘴表示不同意见,他就溜走了,留我一个人在那里抽烟。
我并不介意,站在外面比帐篷里面舒服多了。
我用嘴唇夹住烟,双臂交叉靠在帐篷的帆布上。
然后我闭上眼,让阳光照在脸上。
我把烟从嘴里拿开,打了个哈欠。
正在这时,我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喔!在所有来参加这个工人集会的女孩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南希·金了!” 我睁开眼,任烟头掉在地上,转过身看到这个女人,不禁叫出声来。
“泽娜!真的是你吗?” 就是泽娜,她站在我旁边,比我上次见她时更加丰满,更加俏丽,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外套,戴着一个有挂坠的手链。
“泽娜!”我说,“哦!见到你真好。
”我拉过她的手握了一下,她笑了。
“今天我在这儿见到了所有我认识的女孩。
”她说,“又看到有个人站在帐篷的旗子下面,嘴里叼着烟,我心想,天啊,她看起来真像过去的南·金!如果真的是她就太好了,过了这么久,竟然在这儿看到她!我又走近了一点,看到你的短发,就确定是你了。
” “哦,泽娜!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呢。
”她听到这话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想到这件事,我更用力地握住她的手,用完全不同的语调说,“不过,你真是太不厚道了!你把我那样子留在基尔伯恩!我以为我要死了。
” 她摇了摇头。
“哦!你也让我损失不小啊,那笔钱。
” “我懂。
我真是个没良心的!我想,你应该没去成殖民地吧……” 她吸了吸鼻子:“我朋友去了澳大利亚又回来了。
她说那里都是粗人,他们不需要女房东,他们需要的是——老婆。
那之后我就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挺好的,住在斯特普尼。
” “你现在住在斯特普尼?那我们差不多是邻居了!我住在贝斯纳尔格林,和我的爱人在一起。
看,她在那儿呢。
”我把手搭在她肩上,把那个拥挤的帐篷指给她,“靠近舞台边,怀里抱着婴儿的那个。
” “什么,”她说,“不会是弗洛·班纳吧?在孤女之家工作的那个?” “难道你也认识她?” “我有几个朋友曾在弗里曼特尔之家住过,她们都说过弗洛·班纳有多好!我想,那里有一半的女孩都疯狂地爱上她了。
” “爱上弗洛伦丝?你肯定?” “我保证!”我们又朝帐篷里看了一眼。
弗洛伦丝站起来了,朝讲台上的演讲者挥舞着手中的纸卷。
泽娜笑了,“你和弗洛·班纳!真有意思。
”她说,“我敢说她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
” “你说对了。
”我仍旧盯着弗洛伦丝,尽管惊讶于泽娜说的话,“她确实不会。
” 我们又走到阳光下。
“那你呢,”我问她,“我猜你有女朋友了,对吧?” “有了,”她羞涩地说,“实际上,我有两个女朋友,嗯,我没法决定在两个人里面选哪个好。
” “两个!我的天!”我想象了一下有两个弗洛伦丝这样的恋人,这个想法让我头疼,然后开始打哈欠。
“其中一个今天来了,就在会场里,”泽娜说,“她也是工会的一员,看,她来了!莫德!”听到她的呼唤,一个穿着蓝色和棕色格子外套的女孩看了看四周,然后走了过来。
泽娜挽着她的胳膊,她笑了。
“这位是斯金纳小姐,”泽娜对我说,然后又对她的恋人说,“莫德,这位是南·金,音乐厅的歌手。
”斯金纳小姐大约十九岁,我在不列颠剧院演最后一场的时候她大概还穿着短裙呢。
她礼貌地看着我,向我伸出手。
泽娜继续说:“金小姐和弗洛·班纳住在一起。
”听到这话,斯金纳立刻我把抓得更紧了,眼睛瞪得大大的。
“弗洛·班纳?”她说,口气和泽娜一样,“是协会的弗洛·班纳?哦!我想——我把节目单放哪儿了——金小姐,你看,你能帮我找她签个名吗?” “签名!”我说。
她拿出一张标着演讲者顺序和摊位位置的纸,颤抖着递给我。
我看到弗洛伦丝的名字和一两个别的组织者印在一起,“呃,”我说,“其实,你可以自己找她要啊,你看,她就在那儿呢。
” “哦,我不敢!”斯金纳小姐说,“我太不好意思了……” 最后我拿着那张纸,说我会尽我所能。
斯金纳小姐看起来非常感激,然后跑过去告诉她的朋友,说她见到我了。
“她挺天真烂漫的吧?”泽娜又皱了皱鼻子,“要不我就甩了她,找另一个……”我摇了摇头,又看了一眼手上的纸,然后放进短裙的口袋里。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泽娜说:“那么,你在贝斯纳尔格林过得挺快活的?这和你以前日子的差别可不小啊……” 我做了个鬼脸说:“我真不愿意去想那些日子了,泽娜。
我已经完全不是过去的我了。
” “我敢说是的。
不过,那个戴安娜·莱瑟比——嗯,你肯定见到她了吧?” “戴安娜?”我摇了摇头,“不可能!你觉得在那个该死的派对之后我还会回费里西蒂吗?” 泽娜盯着我,“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啊,她今天来了!” “来了?不可能吧!” “她真来了!我跟你说,今天下午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来了,她也是其中之一。
她就在那个什么报纸还是杂志的桌子边。
我看到她差点昏死过去!” “我的天啊。
”戴安娜来了!这个想法真是糟透了,而且……嗯,就像人们说的,老狗从来不会忘记女主人教给它们的把戏,我感觉自己一听到她那个讨厌的名字就开始有点激动了。
我立刻朝帐篷里看了看,弗洛伦丝还在朝讲台挥舞着胳膊,然后我又看了看泽娜,“她在哪儿,”我问她,“你能给我指一下吗?” 她迅速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带有警告的意味,然后拉着我的胳膊带我穿过人群,走向湖滨浴场,停在一丛灌木后面。
“看,那儿,”她低声说,“就在那张桌子附近。
你看到她了吗?”我点了点头。
她站在一个展台旁——那是她帮忙运营的女性杂志《箭矢》—正在和另一位女士说话,我想那位女士就是在她的化装舞会上扮成萨福的人之一,现在她胸前挂着一个妇女参政的绶带。
戴安娜身着灰色的衣服,帽子上有一块面纱,但是这会儿她把面纱掀起来了。
她和以往一样高傲而美丽。
我看了看她,脑海中浮现出鲜明的记忆——我躺在她旁边,屁股上散落着珍珠;她骑在我身上,摇晃着那个皮具,蹭得床垫都快翘起来了。
“你觉得,”我对泽娜说,“如果我过去她会有什么反应?” “你不是真要去吧?” “为什么不?要知道,我现在不受她控制了。
”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戴安娜一眼,便感觉到那种奴颜婢膝又回到我身上了,或者,我不该用奴颜婢膝这个词。
她就像个音乐厅的催眠师,而我像个不停眨眼的女孩,已经准备好了在观众面前任她摆布。
泽娜说:“我才不要靠近她……”但是我没有听进去。
我迅速看了一眼演说的帐篷,然后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朝那个摊位走去,随即整了整领带。
我离她大概有二十码,当她转过头来,我把帽子摘下,她似乎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目光立刻变得严肃,带着嘲讽和欲望,一如我印象中那样。
我的心抽动了一下,一定是惊吓的!我好像被钩住了。
但是当她张开嘴,说的却是:“雷吉!雷吉,这里!” 这让我踉跄了一下。
距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回应道:“来了!”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男孩从草丛里走来,有些生气地看着戴安娜,手里拿着一个冰激凌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滴下来弄脏了裤子。
他的裤子非常帅气,裤裆处有个凸起。
这个男孩又高又瘦,头发是黑色的,剪得很短。
他的脸很俊秀,嘴唇粉红,像个女孩…… 当他走到戴安娜身边,她从他口袋里拿出了一块手帕,开始在他的大腿上擦拭——看起来他还是把冰激凌滴在了裤子上。
摊位上的另一位女士看到这一幕,笑了笑,轻声嘀咕了些什么,于是那个漂亮的男孩脸红了。
我站在那里,眼前的一切让我有些震惊。
我往后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
我不知道戴安娜是不是又抬头看了一眼,我也没停下来看。
雷吉拿起冰激凌舔起来,他的袖口褪下一点,我看到他手腕上的表闪闪发亮……我眨了眨眼睛,然后摇了摇头,又回到灌木丛中。
泽娜仍在那里偷看,我把脸埋在她的肩上。
当我再次穿过树叶看到戴安娜,她挽着雷吉的手,他们的头靠在一起哈哈大笑。
我转过身去看泽娜,她正在咬嘴唇。
“这世界上真是只有恶魔才会富有啊。
”她说。
然后她又咬了咬嘴唇,偷笑起来。
我也笑了一会儿,然后又痛苦地看了一眼那个摊位说,“好吧,我希望她如愿以偿!” 泽娜抬起头问:“谁?戴安娜还是?” 我扮了个鬼脸,没有回答她。
我们一起走回演说的帐篷,泽娜说她最好把她的莫德找回来。
“我们还能做朋友吧?”我和她握了握手。
她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说,你一定要把我介绍给班纳小姐。
我很想认识她。
” “嗯,好的。
你一定要抽空来做客,告诉她你已经原谅我了,她觉得我对你做的事简直禽兽不如。
” 她笑了,然后看到了什么,转过头去。
“我的另一个情人来了。
”她指着一个肩膀很宽、看起来有些男子气的女人。
那女人正皱着眉头看我们聊天。
泽娜做了个鬼脸,“那个人,喜欢当叔叔。
” “她看上去确实有点难对付。
你赶紧过去找她吧,我不想另一只眼睛也被打青了。
” 她笑了,然后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看到她朝那个女人跑去,亲了她的脸颊,然后和她一起消失在摊位之间的人群中。
我回到帐篷里面。
帐篷里人更多了,更热了,空气里充满烟味,人们的脸上满是汗水,被透过帆布的午后阳光晒得愁眉苦脸。
讲台上有个女人用嘶哑的嗓音磕磕巴巴地演讲着,观众席里有十几个人跳起脚来和她争辩。
弗洛伦丝坐回前排位置,西里尔在她的大腿上乱蹬。
安妮和雷蒙德小姐在她旁边,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金发美女。
拉尔夫也在旁边,满头是汗,面孔因为紧张而僵硬。
弗洛伦丝旁边的座位空着,于是我穿过草丛,在她旁边坐下,接过她手中的西里尔。
“你去哪儿了?”帐篷里吵闹的声音很大,她不得不大声说,“真是糟透了。
有一群男孩进来了,想捣乱。
可怜的拉尔夫下一个讲,他现在浑身发烫,你都可以在他身上煎蛋了。
” 我把西里尔放在膝盖上。
“弗洛,”我说,“你想不到我刚才看到谁了!” “谁?”她问。
突然间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不会是埃莉诺·马克思吧?” “不,不——不是那回事!是泽娜,我在戴安娜·莱瑟比家认识的那个女孩。
不仅是她,还有戴安娜!她们一起出现了,你能想象吗?我的天啊,我又看到戴安娜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我摇晃着西里尔,直到他开始尖叫。
然而弗洛伦丝的脸色变得严肃了。
“我的天!”她说。
那语气让我倒吸一口气,“能不能不要用你那乱七八糟的过去来搅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游行?你今天一个演讲都没有听,我猜你一个摊位也没有看。
你想的看的都是自己的事情,你曾经的女人,你曾经……” “我曾经上过的女人,我猜你是想说。
”我低声说。
我从她身旁挪开,心中又震惊又难过。
然后我生气了,“哼,至少我和每个情人都做过,比你从莉莲那里得到的多。
” 听到这话,她张大了嘴,眼中出现了泪光。
“你这个人,”她说,“你怎么能跟我说这种话呢?” “因为我听够了你说莉莲,你总是说她有多好多好,真是烦死我了!” “她确实好极了,”她说,“应该是她在这里听这些演讲,而不是你!她会理解这一切,而你……” “我猜你是希望她在这里,”我气急败坏地说,“而不是我?” 她盯着我,眼泪顺着睫毛落下来。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也刺痛了,喉咙也开始变得干涩。
“南希。
”她用更柔和的语气说——但我抬起头,把脸转过去。
“我们说好了的不是吗?”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苦涩。
她没说话,然后我又说,“天知道,我马上就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了。
” 我这么说是为了气她,然而当她站起来,躲开我用手去擦眼睛,我心里便难受极了。
我想把手帕从口袋里拿出来,摸到的却是斯金纳小姐让我给弗洛签名的日程表。
我盯着日程表,还没有从这个下午发生的诸多事情中缓过神来。
讲台上的女人一直在用嘶哑的声音和观众席上的质问者争论,空气中弥漫着争吵、烟味和糟糕的感觉。
我抬起头,看到弗洛伦丝站在帐篷的帆布墙边,旁边是安妮和雷蒙德小姐。
她摇了摇头,她们用手握着她的胳膊。
安妮后退了一步,看到了我,便朝我走来,露出一个疲惫的微笑。
“你不应该和弗洛丽争论的,”她在我旁边坐下,“她是我认识的最刀子嘴的人。
” “她说的都是真的。
”我痛苦地说,“这比什么都尖锐。
”我叹了口气,然后换了个话题,问她,“你今天过得好吗,安妮?” “挺好,”她说,“一切都好极了。
” “你的埃玛旁边那个女孩是谁?”我朝雷蒙德小姐旁边那个金发女郎点了点头。
“那是科斯特洛太太,”她说,“埃玛守寡的姐姐。
” “哦!”我以前听说过她,但是没有想到她这么年轻漂亮,“她多好看啊,真可惜她不是——和我们一样。
你看有可能吗?” “恐怕不可能。
不过她真是个可爱的姑娘。
她死去的丈夫真是个好人啊,埃玛说她都不抱希望能再找到一个比得上他的了。
追她的只剩下拳击手了……” 我无力地笑了笑。
实际上我并不关心科斯特洛太太。
安妮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弗洛伦丝,她现在站在帐篷的另一侧,手里攥着手绢,眼泪已经擦干了,面色苍白。
无论我怎么盯着她看,她都不愿意看我。
我几乎想要走过去了,但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喧哗,讲台上的女人演讲完了,人群中传来一阵不情不愿的掌声。
当然,这意味着拉尔夫该上台了。
我和安妮转过身去,看到他在小舞台的一侧不自信地走来走去,被叫到名字后步履不稳地走上了台阶,站在讲台前面。
我看着安妮,做了个鬼脸。
她咬住嘴唇。
帐篷里安静了一些,但并不十分安静。
下午那些认真听演讲的人已经累了,离开了,他们的位置坐上了游手好闲的人、打哈欠的妇女和粗鲁的小伙子。
拉尔夫在漫不经心的听众面前站好,清了清嗓子。
我看到他手里拿着讲稿,我猜是为了防止忘词。
他额头上都是汗,脖子也很僵硬。
我知道他不可能让后排的人听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喉咙太紧张太僵硬。
他咳嗽了一声,开始演讲。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下午我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我和安妮坐在第三排都听不太清楚。
我们后排有人喊起来,“大声点!”然后是一阵笑声。
拉尔夫又咳嗽了一下,然后声音大了一点,但非常嘶哑。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我会尽量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真是谢天谢地!”一个男人听了喊道。
我就知道有人会捣乱。
拉尔夫慌乱地在帐篷里扫了一眼,看起来完全分神了。
我绝望地看着他方寸大乱,不得不盯着手里的几页纸。
当他找到词的时候,四下一阵可怕的沉默,等他再次开口就是照本宣科了,就像他之前在我们奎尔特街的家里一样。
“你们听经济学家说过多少次,”他说,“英格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发现自己在和他一起背,催着他赶快继续,然而他磕巴了,开始喃喃自语,还有一两次不得不借着光照着稿子读。
人群开始呻吟、叹气,来回走动。
我看到主持人坐在舞台后面,没想好要不要走上前去叫他要么大声点,要么就别讲了。
我看到弗洛伦丝脸色苍白,哥哥的窘态让她焦躁不安。
此刻她已经将自己的悲伤抛在脑后。
拉尔夫读到数据那一段了:“两百年前,不列颠的土地和资本总值五亿英镑,而今天,总值是——”他又开始看稿子,这时有个人站起来喊道:“你是谁啊,伙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小学校长?”拉尔夫愣住了,仿佛有人给他上了发条。
安妮小声说:“哦,不!可怜的拉尔夫!我看不下去了!” “我也看不下去了!”我说着便一跃而起,把西里尔丢给她,然后三步并作两步,从侧面的台阶跑上讲台。
主持人看到我,站起身想要阻止,但我挥手示意他坐下,然后走向沮丧的拉尔夫——他正在不停流汗。
“哦,南希。
”他说。
我头一次看到他都快哭出来了。
我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让他在观众面前站稳。
观众沉默了一阵子,我想是因为他们很高兴看到我如此戏剧性地跳上了讲台,站在拉尔夫旁边。
此刻我利用起台下的安静,几乎是吼着把我的声音投掷出去。
“你们不喜欢数学?”我从拉尔夫停下的部分开始讲,“上百万的数字可能太大了,那么我们就以万为单位。
就说三十万吧。
诸位觉得我指的是什么,市长大人的薪水?”台下一阵窃笑——几年前,市长的薪资引发了一个丑闻。
我感激地抓住了这一阵笑声,对他们说道,“没错,我说的不是英镑,也不是先令。
我说的是人。
我说的是成千上万生活在伦敦救济院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伦敦!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最富裕的帝国里最富裕的城市——就在我演讲的这一刻!” 我继续这样讲下去,笑声慢慢停止了。
我讲到这个国家的乞丐,还有那一年所有在贝斯纳尔格林救济院的床上死去的人。
“在救济院死去的人会是你吗,先生?”我大声说——我发现自己演讲时加入了一些押韵的修辞,“会是你吗,小姐?或者你的老母亲?或者这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开始哭了。
“我们死去的时候多大年纪?”我问道,转向拉尔夫,他正以毫不掩饰的惊讶看着我,然后我用让所有观众都能听到的声音说,“班纳先生,贝斯纳尔格林的男女平均死亡年龄是多大?” 他目瞪口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我用力掐了一下他的胳膊,他大声说:“二十九岁!”我觉得还不够大声,于是又问:“是多大?”我感觉自己像是滑稽舞剧里的女主角,而拉尔夫像是和我唱双簧的。
他用比刚才更大的声音喊道:“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我对观众说,“如果我是个女士呢,班纳先生?如果我住在汉普斯特德,或者圣约翰伍德,在布莱恩特梅公司有股份呢?这些女士的平均死亡年龄是多少?” “五十五岁,”他立刻回答,“五十五岁!几乎是两倍。
”现在他想起台词了,在我沉默的催促下,他继续以几乎和我一样强有力的声音开始讲,“那些富人区每死一个人,东伦敦就要死四个。
许多人会死于疾病,而对于应该如何防治这些疾病,他们聪明又富有的邻居清楚得很。
还有些人,他们会因为自己工厂的机器事故而伤亡,或者就是死于饥饿。
真的,伦敦今晚就会有一两个人仅仅因为饥饿而死”。
“而关于这一切,两百年后的经济学家只会告诉你,大不列颠的财富增长了二十倍还多!伦敦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 有人开始呐喊了,但是我们等到他们安静下来才开始继续讲。
我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很轻,让人们不得不皱起眉头侧耳倾听。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是因为劳动人民都在大手大脚地花钱吗?因为我们宁愿花钱买琴酒和波特酒,去音乐厅,买烟,赌博,而不是给我们的孩子买肉,给我们自己买面包?富人经常这么写,这么说。
但这是真的吗?当有钱人谈起穷人的时候,他们口中的真相总是十分狡猾的。
想想吧,如果我们闯进富人的宅子,他们会说我们是贼。
如果我们踏入他们的庄园,他们会说我们是入侵者,而且放狗来咬我们!如果我们拿了他们的金子,我们就成了小偷。
如果我们让他付给我们钱,拿回他们的金子,我们就成骗子了! “这些富人的财富是什么?换个词来说就是抢劫!富人从他的竞争者手中偷盗,他偷走了土地,又筑起高墙;他偷走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自由;他偷走了我们的劳动果实,并迫使我们从他手中买回来!他会称之为抢劫、蓄奴和欺骗吗?不,他们说这是企业,是商业技巧,是资本主义。
他们说这是本性。
“但是,我们的婴儿因为没有奶喝而饿死,这是本性吗?女人们在拥挤窒息的工厂里缝制裙子和外套直至深夜,这是本性吗?男人和男孩们为了给他们搬运取暖的煤而丧生或者成了瘸子,这是本性吗?面包师为了烤面包而被熏得喘不过气,这是本性吗?” 我提高了声音,然后又低下来。
“你们觉得这是本性吗?你们觉得这公平吗?” “不公平!”立刻有上百个声音回答道,“对!不公平!” “社会主义者也这么认为!”拉尔夫喊起来。
他手中握着演讲稿,大声对人群喊道,“我们看够了财富和资产直接流入那些懒惰的富人口袋里!我们不想要那种钱——不想让富人偶尔赏赐给我们!我们想看到社会的大变革!我们想看到金钱被投入使用,而不是拿去产生利润!我们想看到工人的孩子们变得强壮,救济院被夷为平地,因为没有人再需要救济了!” 人群中有人叫好,他举起了手。
“你们在欢呼,”他说,“或许在这样阳光灿烂的天气里大家心情都不错。
但是只有欢呼还不够!你们必须行动。
有工作的人——不论男女,都参加工会吧!有选举权的人,用上你们的选票!把你们自己的人选进议会。
为女同胞们争取权利,为你们的姐妹、女儿和妻子——让她们拥有选票,来帮助你们!” “今天晚上回家,”我向前一步,继续说,“问问自己今天班纳先生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你将发现你也会得到和我们一样的答案。
‘因为英国的人民,’你会说,‘在资本主义和地主制经济下变得更加贫穷,更加病弱,更加痛苦而恐惧。
因为弱势群体境况的改善不是靠慈善机构和微不足道的改革,不是靠税收,不是靠选举另一个资本主义政府,甚至不是靠废除上议院!而是让工人来接手土地和工业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当年铁甲动帝王步帘衣
- 在偏执狂怀里撒个娇[重生]茶栗
- 仙界归来静夜寄思
- 你未曾坠落星海南薄荷
- 吧唧一口吃掉你一口时光
- 养了千年的龙蛋终于破壳了若鸯君
- 反派他过分阴阳怪气[穿书]从南而生
- 法师乔安程剑心
- 修真大工业时代试剑天涯
- 穿越后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来宠我梦.千航
- 当天才遇上穿越女/天才的自我修养苏家木偶
- 烈火如歌·大结局明晓溪
- 八零年小月亮啃苹果的猫
- 入骨娇宠烟云绯
- 穿成年代文里的前任小姑夜斩白
- 协议标记[穿书]童柯
- 大佬她不想回豪门梦.千航
- 穿成霸总拐走炮灰昔我有梦
- 东宫娇娥李息隐
- 相公是男装大佬兆九棠
- 摁住他的易感期咿芽
- 如果蜗牛有爱情丁墨
- 位面掮客/国家帮我做任务灵默笙
- 逃婚女配不跑了美人无霜
- 叔,你命中缺我裸奔的馒头
- 我遗落在一九九八年的爱情碎片秋芦
- [综漫] 我的真命天子自带BGM遥想入仙行
- [历史同人] 始皇后宫传冰镇柠檬水
- [综英美] 和前男友分手后他想把我按进地里雾里鬼
- 薄荷过敏茜橙
- 岭城炙爱胤爷
- 直播写玄学文的我在全网封神罂娆
- 心声暴露后,真公主被全天下盛宠一弯仙月
- 重生后,阴鸷摄政王被我撩晕了心向往栀
- 你總在我身後(1v1)池生烟
- 变成血族是什么体验神行汉堡
- 养大的老婆变成疯批了赋见
- 他真的在钓我荒人说梦
- 小夫人又美又甜昼白夜明沉九襄
- 姜四娘重生日常橙与白
- 学长他和想象中不一样泊淮酒
- 相亲对象真是豪门大佬乘酒兴
- 校霸的信息素甜过头了一只小尧
- 恋爱演绎法寒鸦
- 老婆今天怀崽了吗[快穿]奶鲨
- 都市极品医仙临风
- 快穿: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雀
- 秘书长的崛起之路一战封神
- 软硬皆湿 NPH没有尾巴
- 渣了优等生男友后被肏坏了(高H)小熊说话啊
- 让你出狱娶妻,你跑去沾花惹草?六好青年
- 小公主nph绵橙她
- 这爱真恶心郑楠
- 血色脐带缠绕法(母女gl,纯百,吸血鬼)屁屁鼠王
- 馐玉(古言1v1)果皮酱
- JO乙短篇存放处卡卡卡卡里
- 精通兽语,农女她家养百兽超富贵捌陆S
- 嫁给漂亮蠢货后[种田]金鞍玉勒
- 宦官当道,小厨娘制霸皇宫面包小狗哭哭
- 南柯Klaelvira
- 你總在我身後(1v1)池生烟
- 快穿: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雀
- 深渊二重奏胡旋舞
- 余温(纯百)蟹黄堡不好
- 我在西游搞黄油NPH切西亚
- 背主(现代1V1)林漓
- 命運之核 :宿命交錯晴媛
- (强制h)什么模拟世界?我要回家!秋月白
- 循循善诱(骨科 豪门 np)烟头
- 警界锦鲤,未入学已功勋满墙玄巽尧
- 一年一度中暑事件番大王
- 重生成龙蛋,被死对头养了红糖火锅
- 黑泥万人迷短篇合集慕哲
- 【权游】太阳之下绯星
- 唐风之承乾千棵树
- 狐狸设陷渔珥
- 南柯Klaelvira
- 神医绯途圣天尊者
- 一天一骷髅,我稳坐枯骨王座晨初
- 华娱特效大亨余生所念
- 假千金忙玄学,撤回宅斗申请灯盏空青
- 黑莲花重生归来,婆家瑟瑟发抖饭碗114
- [综漫] 我带付丧神建设一个家格卿
- 我的兄弟是妖怪星七ysq
- 我,小猫,碰瓷白露未霜
- 唐风之承乾千棵树
- 归云千山泽雪
- 风信录百草雨雨
- 纯属爱情:CP营业守则捷思敏
- 末不弃_随笔BE合集末不弃
- 重生76:觉醒空间,宠妻致富我都要明日之星
- 软饭吃吗籽潋
- 新婚予你杯倾酒
- 心声暴露后,真公主被全天下盛宠一弯仙月
- 小情郎云深处见月
- 表姑娘她弱不禁风三只鳄梨
- 纨绔对咬逐柳天司
- 顶级暴徒(最新法案)water
- 红象2.0平淡如水
- 路人甲总是在被示爱少女春宵
![非典型求生欲[快穿]](https://www.nothong.com/img/4262.jpg)

![恶毒男配不争了[重生]](https://www.nothong.com/img/59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