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7章(3/3)
执,命令把使者拘押起来,弄清了此人的身份再说:而且,他誓死要保卫马孔多镇。
没等多久。
自由党人失败的消息就越来越可信了。
三月底的一天晚上,不合节令的雨水提前泼到马孔多街上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紧张的宁静突然被撕心裂肺的号声冲破了,接着,隆隆的炮击摧毁了教堂的钟楼。
其实决定抵抗纯粹是疯狂的打算。
阿卡蒂奥指挥的总共是五十个人,装备很差,每人顶多只有二十发子弹。
诚然,在这些人当中有他学校里的学生,在他漂亮的号召激励之下,他们准备为了毫无希望的事情牺牲自己的性命。
炮声隆隆,震天动地,只能听到零乱的射击声、靴子的践踏声、矛盾的命令声、毫无意义的号声;这时,自称史蒂文森上校的人,终于跟阿卡蒂奥谈了一次话。
“别让我戴着镣铐、穿着女人的衣服可耻地死,”他说,“如果我非死不可,那就让我在战斗中死吧,”他的话说服了阿卡蒂奥。
阿卡蒂奥命令自己的人给了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让他和五个人留下来保卫兵营,自己就带着参谋人员去指挥战斗。
阿卡蒂奥还没走到通往沼地的路上,马孔多镇口的防栅就被摧毁了,保卫市镇的人已在街上作战,从一座房子跑到另一座房子;起初,子弹没有打完时,他们拿步枪射击,然后就用手枪对付敌人的步枪了,最后发生了白刃战。
失败的危急情况迫使许多妇女都拿着棍捧和菜刀奔到街上。
在一片混乱中,阿卡蒂奥看见了阿玛兰塔,她正在找他:她穿着一个睡衣,手里握着霍·阿·布恩蒂亚的两支旧式手枪,活象一个疯子。
阿卡蒂奥把步枪交给一个在战斗中失掉武器的军官,带着阿玛兰塔穿过近旁的一条小街,想把她送回家去。
乌苏娜不顾炮弹的呼啸,在门口等候,其中一发炮弹把邻舍的正面打穿了一个窟窿。
雨停了街道滑溜溜的,好似融化的肥皂,在夜的黑暗里只能摸索前进。
阿卡蒂奥把阿玛兰塔交给乌苏娜,转身就向两个敌兵射击,因为那两个敌兵正从旁边的角落里向他开火。
在橱里放了多年的手枪没有打响。
乌苏娜用身体挡住阿卡蒂奥,打算把他推到房子里去。
“去吧,看在上帝份上,”她向他叫道。
“胡闹够啦!” 敌兵向他俩瞄准。
“放开这个人,老大娘,”一个士兵吆喝,“要不,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阿卡蒂奥推开乌苏娜,投降了。
过了一阵,枪声停息,钟声响了起来。
总共半小时,抵抗就被镇压下去了。
阿卡蒂奥的人没有一个幸存。
但在牺牲之前,他们勇敢地抗击了三百名敌兵。
兵营成了他们的最后一个据点。
政府军已经准备猛攻。
自称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的人,释放了囚犯,命令自己的人离开兵营,到街上去战斗。
他从几个窗口射击,异常灵活,准确无误,打完了自己的二十发子弹使人觉得这个兵营是有防御力量的,于是进攻者就用大炮摧毁了它。
指挥作战的上尉惊讶地发现,瓦砾堆里只有一个穿着衬裤的死人。
炮弹打断的一只手还握着一支步枪,弹夹已经空了;死人的头发又密又长,好象女人的头发,用梳子别在脑后;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链条,链条上有条小金鱼。
上尉用靴尖翻过尸体,一看死者的面孔,就惊得发呆了。
“我的上帝!”他叫了一声。
其他的军官走拢过来。
“你们瞧,他钻到哪儿来啦,”上尉说,“这是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呀。
” 黎明时分,根据战地军事法庭的判决,阿卡蒂奥在墓地的墙壁前面被枪决了。
在一生的最后两小时里,他还没弄明白,他从童年时代起满怀的恐惧为什么消失了。
他倾听他的各项罪行时是十分平静的,完全不是因为打算表现不久之前产生的勇气。
他想起了乌苏娜--这时,她大概跟霍·阿·布恩蒂亚一起,正在栗树下面喝咖啡。
他想起了还没取名的八个月的女儿,想起了八月间就要出生的孩子。
他想起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出来打仗时,她为了第二天的午餐而把鹿肉腌起来的情景,他记起了她那披到两肩的头发和又浓又长的睫毛,那样的睫毛仿佛是人造的。
他怀念亲人时并没有感伤情绪,只是严峻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开始明白自己实际上多么喜爱自己最憎恨的人。
法庭庭长作出最后判决时,阿卡蒂奥还没发现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即使列举的罪行没有充分的罪证,”庭长说,“但是根据被告不负责任地把自己的部下推向毫无意义的死亡的鲁莽行为,已经足以判决被告的死刑。
”在炮火毁掉的学校里,他曾第一次有过掌权以后的安全感,而在离这儿几米远的一个房间里,他也曾模糊地尝到过爱情的滋味,所以他觉得这一套死亡的程序太可笑了。
其实,对他来说,死亡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才是重要的。
因此,听到判决之后,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留恋。
他一句话没说,直到庭长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
“请告诉我老婆,”他用响亮的声音回答。
“让她把女儿取名叫乌苏娜,”停了停又说:“象祖母一样叫做乌苏娜。
也请告诉她,如果将要出生的是个男孩,就管他叫霍·阿卡蒂奥,但这不是为了尊敬我的大伯,而是为了尊敬我的祖父。
” 在阿卡蒂奥给带到墙边之前,尼康诺神父打算让他忏悔。
“我没有什么忏悔的,”阿卡蒂奥说,然后喝了一杯黑咖啡,就听凭行刑队处置了。
行刑队长是个“立即执行”的专家,他的名字并不偶然,叫做罗克·卡尼瑟洛上尉,意思就是“屠夫”。
毛毛丽不停地下了起来,阿卡蒂奥走向墓地的时候,望见天际出现了星期二蛧站:?????.??????s.????z灿烂的晨光。
他的留恋也随着夜雾消散了,留下的是无限的好奇。
行刑队命令他背向墙壁站立时,他才发现了雷贝卡--她满头湿发,穿一件带有粉红色小花朵的衣服,正把窗子打开。
他竭力引起她的注意。
的确,雷贝卡突然朝墙壁这边瞥了一眼,就惊恐得愣住了,然后勉强向他招手告别。
阿卡蒂奥也向她挥了挥手。
在这片刻间,几支步枪黑乎乎的枪口瞄准了他,接着,他听到了梅尔加德斯一字一句朗诵的教皇通谕,听到了小姑娘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在教室里摸索的脚步声,感到自己的鼻子冰冷、发硬,就象他曾觉得惊异的雷麦黛丝尸体的鼻子。
“嗨,他妈的,”他还来得及想了一下,“我忘了说,如果生下的是个女孩,就管她叫雷麦黛丝吧。
”接着,他平生的恐惧感又突然向他袭来,象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上尉发出了开枪的命令。
阿卡蒂奥几乎来不及挺起胸膛和抬起脑袋,就不知从哪儿涌出一股热乎乎的液体,顺着大腿往下直流。
“杂种!”他叫喊起来。
“自由党万岁!” - ------------ 第七章 ------------ 五月里,战争结束了。
政府在言过其实的公告中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说要严惩叛乱的祸首;在这之前两个星期,奥雷连诺上校穿上印第安巫医的衣服,几乎已经到达西部边境,但是遭到了逮捕。
他出去作战的时候,带了二十一个人,其中十四人阵亡,六人负伤,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跟他一起的只有一个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
奥雷连诺上校被捕的消息是特别在马孔多宣布的。
“他还活着,”乌苏娜向丈夫说。
“但愿敌人对他发发慈悲。
”她为儿子痛哭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下午,她在厨房里制作奶油蜜饯时,清楚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
“这是奥雷连诺,”她一面叫,一面跑去把消息告诉丈夫。
“我不知道这个奇迹是咋个出现的,可他还活着,咱们很快就会见到他啦。
”乌苏娜相信这是肯定的。
她吩咐擦洗了家里的地板,重新布置了家具。
过了一个星期,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这一次没有发表公告),可悲地证实了她的预言。
奥雷连诺已经判处死刑,将在马孔多执行,借以恐吓该镇居民。
星期一早上,约莫十点半钟,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连诺·霍塞穿衣服,乱七八糟的喧哗声和号声忽然从远处传到她耳里,过了片刻,乌苏娜冲进屋来叫道:“他们把他押来啦!”在蜂拥的人群中,士兵们用枪托开辟道路,乌苏娜和阿玛兰塔挤过密集的人群,到了邻近的一条街上,便看见了奥雷连诺。
奥雷连诺象个叫花子,光着脚丫,衣服褴楼,满脸胡子,蓬头垢面。
他行进的时候,并没感到灼热的尘土烫脚。
他的双手是用绳子捆绑在背后的,绳端攥在一个骑马的军官手里。
跟他一起押着前进的是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也是衣衫破烂、肮里肮脏的样子。
他们并不垂头丧气,甚至对群众的行为感到激动,因为人们都在臭骂押解的士兵。
“我的儿子!”在一片嘈杂中发出了乌苏娜的号陶声。
她推开一个打算阻挡她的士兵。
军官骑的马直立起来。
奥雷连诺上校战栗一下,就停住脚步,避开母亲的手,坚定地盯着她的眼睛。
“回家去吧,妈妈,,他说。
“请求当局允许,到牢里去看我吧。
” 他把视线转向踌躇地站在乌苏娜背后的阿玛兰塔身上,向她微微一笑,问道:“你的手怎么啦?”阿玛兰塔举起缠着黑色绷带的手。
“烧伤,”她说,然后把乌苏娜拖到一边,离马远些。
士兵们朝天开了枪。
骑兵队围着俘虏,朝兵营小跑而去。
傍晚,乌苏娜前来探望奥雷连诺上校。
她本想在阿·摩斯柯特先生帮助下预先得到允许,可是现在全部仅力都集中在军人手里,他的话没有任何分量。
尼康诺神父肝病发作,已经躺在床上了。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没有判处死刑,他的双亲算看望儿子,但是卫兵却用枪托把他俩赶走了。
乌苏娜看出无法找中间人帮忙,而且相信天一亮奥雷连诺就会处决,于是就把她想给他的东西包上,独个儿前往兵营。
卫兵拦住了她。
“我非进去不可,”乌苏娜说。
“所以,你们要是奉命开枪,那就马上开枪吧,”她使劲推开其中一个士兵,跨进往日的教室,那儿有几个半裸的士兵正在擦枪。
一个身穿行军服的军官,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脸色红润,彬彬有礼,向跟随她奔进来的卫兵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就退出去了。
“我是奥雷连诺上校的母亲,”乌苏娜重说一遍。
“您想说的是,大娘,”军官和蔼地一笑,纠正她的说法。
“您是奥雷连诺先生的母亲吧。
” 在他文雅的话里,乌苏娜听出了山地人卡恰柯人慢吞吞的调子。
“就算是‘先生’吧,”她说,“只要我能见到他。
” 根据上面的命令,探望死刑犯人是禁止的,但是军官自愿承担责任,允许乌苏娜十五分钟的会见。
乌苏娜给他看了看她带来的一包东西:一套干净衣服,儿子结婚时穿过的一双皮鞋,她感到他要回来的那一天为他准备的奶油蜜饯。
她在经常当作囚室的房间里发现了奥雷连诺上校。
他伸开双手躺在那儿,因为他的腋下长了脓疮。
他们已经让他刮了脸。
浓密、燃卷的胡子使得颧骨更加突出。
乌苏娜觉得,他比以前苍白,个子稍高了一些,但是显得更孤僻了。
他知道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知道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自杀;知道阿卡蒂奥专横暴戾,遭到处决;知道霍·阿·布恩蒂亚在粟树下的怪状,他也知道阿玛兰塔把她寡妇似的青春年华用来抚养奥雷连诺.霍塞知道奥雷连诺·霍塞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刚开始说话就学会了读书写字。
从跨进房间的片刻起,乌苏娜就感到拘束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他那整个魁梧的身躯都显出极大的威力。
她觉得奇怪的是,他对一切都很熟悉。
“您知道:您的儿子是个有预见的人嘛,”他打趣地说。
接着严肃地补充一句:“今天早上他们把我押来的时候,我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龙与凰(百合.gl.1v1.伪快穿,轻H)白曦
- 我被作死系统绑架了调香的人
- 快活街小宝爷
- 用星际废品在古代当神万万千千也
- 冷落三年提离婚,顾机长哭晕了叶漠漠
- 恶毒主母洗白日常采薇采薇
- 漂亮情人六时
- 阴翳小少爷的贴身保镖日月十五
- 无名六处笔纳
- 穿进恐怖小说后我变成了路人甲咔咔乱吃
- 被男女主抢夺的女装大佬云养喵
- 独家姻缘:前妻,离婚无效忆江
- [综漫] 迹部老板要给我加薪鹤眠
- 极品兵王闹花都六能
- 爹!快躺下,女儿让你做太上皇南婉徐
- 心机女渣了高岭之花仙君后[穿书]如是念绿来
- 甜宠总裁乖妻易夏
- 逍遥武神穷得叮铛响
- 踏出SSS女子监狱,我医武双绝夜雨笙箫
- 微菌(1V1,SC,人外)第五密度
- 溺毙(校园万人迷 强制NPH)混沌
- 我什么都吃一点(1v1短篇合集)iiu
- 好想摸老婆的猫耳朵她姜
- 重生清冷钓系上司处处开屏过渡
- 高傲少爷撞到爱情尧尧王
- 捡漏我是认真的,空间里全是帝王绿请让我火一次吧
- 金属牙套【骨科gl】n君
- 情迷1942(二战德国)JCYoung
- 慰藉[姐弟1V1]群青鸢尾
- 湖底(亲父女)小斐
- 我靠玄学算命爆火画月弦
- 我直播玄学吃瓜后全网爆火唧唧喵
- 快穿:我在无限游戏当路人黑猫乐子人
- 重生成崽咸鱼上娃综木炽丹枝
- 主攻随笔十贰点
- 绑定男妈妈系统后,我把反派养弯了是啊瑶呀
- 山海花铺赖床不想动
- 穿越之赘婿北沐南
- 听妈妈的话(纯百)嗜甜
- 她沒有想死,只是不想活Aoao
- 你總在我身後(1v1)池生烟
- 漫丽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校园1V2)鱼嬷嬷adc
- 乙女游戏之邱将军爱吃肉(古言.NP.H)晓风拂柳
- 狼性掠夺1v1(高h)扶猪上树
- 在恐怖游戏里差点被超市 无限np绝望的文盲
- 抽屉(亲姐弟)不说话的书
- 八零换亲,早死的军官回来了明月清衣
- 阴翳小少爷的贴身保镖日月十五
- 你有我会撩吗不缺觉
- 来弟(姐弟骨科)虚与委蛇
- 恋爱克莱因(1v1,sc,人外)第五密度
- 我真的是好人[快穿]语梦希
- 恶女她直接火葬场懒尸
- 小侯爷跑去和情敌he了笑相逢
- 异能特别监察处时今
- 星盗雄虫恋爱法则[虫族]也懒
- 穿成真少爷在帝国搞事业[星际]虞郁雨
- 即将倒闭的乌有乡安尼玛
- 哭哭又怎样牧苗酒
- 心机女渣了高岭之花仙君后[穿书]如是念绿来
- 潜艇厨子:透视深海,我即是天眼吃榴莲皮剌嗓子
- 女子监狱归来,我无敌于世二少本尊
- 踏出SSS女子监狱,我医武双绝夜雨笙箫
- 微菌(1V1,SC,人外)第五密度
- [甄嬛传同人] 一睁眼,甄嬛跪在我面前小产了南山脸脸
- [综漫] 巡猎持明,柯学追杀丰饶酒厂云间蔓
- 夺爱豪门:总裁,我不嫁!柒洛樱
- 杀死那个男人李子李
- 重生1985:从收猴票开始首富之路魔手佛心
- 结婚对象竟是撒娇怪七层枇杷
- 穿成年代文里的极品亲妈黎家七七
- 回国后和前男友协议结婚了深深深深深几许
- 竹马难养远树
- 戒掉女装之后桃听孤/菇咕孤
- 我们才没有卖腐不续灯
![领主沉迷搞基建[穿书]](https://www.nothong.com/img/4935.jpg)

![反派疯狂迷恋我[无限]](https://www.nothong.com/img/909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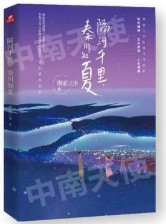

![和女二手拉手跑了[穿书]](https://www.nothong.com/img/42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