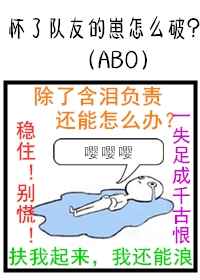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章 相思(2/3)
蕴藻见了我,非咬下我一块肉来不可。
趁早别打这个主意,你们两个小的要好也没用,家大人都咬着牙呢,还能处?就跟一只碗磕裂了,再锔也是破的,不能以次充好了,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 她当然是明白的,也知道容实说那些傻话是为逗她高兴。
他再不靠谱,也没有撂开经历过丧子之痛的父母,光图自己快活的道理。
她瞧上他,就是觉得他有担当,是个爷们儿。
如果他真来倒插门,她反倒觉得这人失了真,不那么值得爱了。
不过这样一来,她看懂了阿玛的立场,阖家上下没有一个人支持她再和容实来往,她的这段感情何去何从尚不知道?难道果然要打水漂了吗? 她瞬间气馁,低声道:“我要是还想和他在一起呢?是不是豫亲王倒了台,家里就不会反对了?” 述明皱了眉,“你挺机灵个人,到如今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既然有了成见,哪怕天时地利人和,也不顶用了。
老太太的脾气你不知道?说一不二的主儿,你能让她回头?” 她陷进绝望里,昨儿老太太还打算指派人上容家骂街来着,不满容家老太太和太太,连带着容实也不受待见。
可她又觉得不能放弃,她信得过容实,只要障碍扫除了,凭他那股死皮赖脸的劲头,应当不会比阿玛当年差。
连阿玛都知道买鸽子讨好丈人爹,他就不会吗? 心里装着深情,日子却归于平静。
有时候会突然一阵心慌,手上正忙什么事,乍然听见脚步声,总忍不住回头。
以为他来了,其实没有。
已经习惯他硬往上凑了,现在渐渐少了,渐渐没有了,说不出的失落和失望。
她的寂寞不动声色,差事照样办,井井有条纹丝不乱,乱在心里,别人看不见。
阿玛已经不要她上夜了,因为上次出过豫亲王留宿的事,他能来一回,就能来第二回。
说起那个豫亲王,颂银对他的评价只有几个大字——真不是东西!他这么缺德,得不到的不说毁了,就让你坏了名声,如果容家不要她,她再不肯嫁给他,那就真要当老姑娘了。
唯一的出路大概只有嫁外埠,比方科尔沁啊、察哈尔啊,那里的爷们儿糙,不像关内眼里不揉沙。
女人婚前出了点什么纰漏或是嫁过人,人家基本不放在心上。
相思苦啊,就像害了病,常常干什么都有气无力。
她知道他在忙,郭贵人临盆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好多地方要部署。
那么些侍卫,虽然三殿之后换上了正黄旗和正白旗的人,但谁又能吃得准人家心里所思所想。
他必须挑亲信出来,这个门那个门,一道一道就像多重的锁,锁上就能保证有来无回。
她掰着指头算,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很快就能见分晓了。
她这里要办的事也都齐了,内务府必须挑选稳婆、乳母、保姆。
凤子龙孙们都有定例,也是人员庞杂,必须逐个审查,以保万无一失。
又因为临近年尾了,节下要张罗的事儿也多,光是辞岁的一场大宴就够她忙的了。
这几天是不得闲了,到了下值的时候,或是夜深人静了,想起来一阵儿,掏心掏肺的恨不得立刻见到他,狠狠抱上一抱。
天渐暗,积雪成丛,下值后还得上冰窖胡同看看棺椁打造的进程。
其实拼起来不费什么事,麻烦的是雕花和上漆,全靠工夫硬耗。
为皇帝做棺这种事儿秘密进行,那溜围房的窗户都得加固,桃花纸内蒙麻布,防着有人捅窗户纸。
一盏小小的羊角灯引她进后院,那些匠作处的太监见她进门都打千儿,管事的带她瞧,说:“上用五棺二椁,五棺完成了一多半。
就是外头一个大椁费时候,光用漆就是二十斤。
眼下只剩一口内棺,照着小总管的吩咐日夜赶制,不出五日就能全做完……您来瞧瞧这彩画和雕工,棺身上绘八仙、引魂人,材头上刻团寿,还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听您的示下。
” 颂银举灯仔细看,里外材料全是上等楠木,木纹中的金丝在烛火里闪耀出细密瑰丽的光泽。
拿手一敲,沉闷的笃笃声,仿佛浸在水中似的,激不起回音来。
她点了点头,“上用的含糊不得,没旁的,审慎用心,就成了。
回头大总管再来瞧,我这里觉得都好,不知他怎么看。
这漆要晾多少天?” 管事的说:“要能搁到当院放风,四五天上一遍漆。
要是闷在屋里头,天儿冷,七八十来天,也没准儿。
” 要上八十一道漆,算一算,那得耗时多久?她说:“抬到院儿里去吧,着人看着,不许人进冰窖,违令的抓起来。
” 管事的应了个嗻,她略逗留一会儿就离开了,景山和补儿胡同一南一北,得跑上好半天。
夜深了,她歪在轿围子上打盹,夏天还能偷溜进慈宁宫花园睡个午觉呢,冬天不能了,一到天黑她就犯困。
闭着眼睛随轿子摇晃,听轿夫的鞋子踩在积雪上吱嘎作响。
正是昏昏欲睡,不知怎么停下了,直觉应该没那么快的。
打帘往外看,这里不是家门前,怎么半道上停下了?难道是路坏了不好走了? 她问:“怎么了?” 轿夫叫了声二姑娘,吞吞吐吐的,轿子既不走,也不下肩,想是被挡了道。
她掫起毡子瞧,对面一顶精美的八人抬大轿拦腰横跨胡同,把原本不宽的去路堵了个严实。
她心里一蹦,暗说大夜里的,别再出什么事儿。
惹不起躲得起,把毡子放了下来,吩咐轿夫绕道。
那边慢悠悠传出个嗓音来,不怒自威,“你敢。
” 她早就料到是他,他出了声,也不感到惊讶。
只是找上门来了不得不应付。
要问她的心里话,就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但凡她有能耐,早打他个肠穿肚烂了。
可这是位碰不得的主儿,暂且不能得罪,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鹿死谁手。
她只得让轿夫停轿,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轿外了,金冠玉带,及地的青狐大氅把那身量拉得愈发长了,站在那里像尊佛,眼里一轮沉沉的光晕包罗万象。
颂银上前蹲了一安,他竟从那却步一福里窥出了不满,“现如今不在我旗下了,见了我不打招呼就要走?我好歹是你的旧主子,莫说你,就连你阿玛也不敢这样。
” 他又来卖弄主子的威严了,颂银无可奈何唯有退让,“六爷说笑了,我不是这样的人。
先前您没露面也没出声,我不知道是您在,要知道了,怎么也得来请个安。
”她抬眼看了看那轿子,依旧那么嚣张地拦截着。
她迟疑问,“六爷是恰好路过这儿?恰好碰见我?” 他说不是,“我就是来堵你的。
” 她额角一跳,这话倒毫不遮掩,敞开了说也好。
她努力压住了火气,“六爷找我必然有示下,听您吩咐。
” 他慢慢踱了两步,“没什么,许久没见你了,想你,来见见你。
” 她脸上一红,左右看看,两边的轿夫加上他的戈什哈,足有二十来人,他就直剌剌地说出来了。
她简直觉得丢人,他办事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大概只有在想利用你的时候会含蓄些,其余的,只要他高兴,直接扔到你脸上,你不接也得接着。
她尴尬笑了笑,“六爷体念我,大约知道奴才近来忙,没得闲上府里请安。
” 他又说不是,“我是听说你被容家回绝了,特特儿瞧瞧你。
” 原来是看热闹来了,她感觉怒火熊熊往上涌,这个始作俑者,用了这么多手段做成了缺德事,这会儿安然来查验成果了。
她打量他的脸,他眼角含笑,十分自得的神态。
她急促地喘气,恨不得抓花他的脸,叫他再使坏!可是不能,她还有理智,她依旧不敢得罪他。
“我好得很,谢谢六爷关心。
原本我和容实要成亲,得上您那儿调档,现在不用了,等我瞧上了别人,说嫁就嫁了。
” 他哼笑一声,“因为你的旗籍不在镶黄旗了?我那个档子房烧了个精光,你们的户籍册子一天没交付正黄旗,你一天在爷手上。
” 颂银简直要憋不住了,她梗着脖子气愤地望着他,“您究竟想让我怎么着?和容家已经不成,您怎么还不满意呢?” “我自然不满意,因为你还没嫁我,我不高兴,就和你作对、为难你,直到你当我的福晋为止。
” 这人是不是疯了?有他这么结亲的态度吗?就因为他是天潢贵胄,得不到就逼,把人逼得没了退路,叫人别无选择? 颂银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您今年多大了?我记得过完年二十五了吧?” 他说是,“你问爷的年纪干什么?” “那也不小了呀,干的事儿怎么这么膈应人呢?” 他吃惊不小,以为她不敢这么和他说话的,没想到她吃了熊心豹子胆,终于要发作了。
他抿唇一笑,妙得很,他就是想见识一下她的真性情。
如果他这样不择手段地欺压她,她还能同他虚与尾蛇,那就说明他看错了,她是个面人儿,将来也不会有钢火。
可掌着内务府的女官,怎么能是那样的!她想说他幼稚是不是?只不过嘴上还留着神,不敢那么直接。
他点点头,“是不小了,那又怎么样?爷就爱整治你们俩,看见你们好我就不高兴。
” 颂银气得厉害,瞧了四周围一眼,“我不能骂您,要不咱们也交个手吧,打一架就痛快了。
” 他立刻拿轻蔑的眼光打量她,“你胆子不小,爷输谁也不能输你吧!不过今儿不和你打,我被容实弄伤了胳膊,下不得场子了。
你把账记上,等时机到了,管叫你痛快。
” 他一语双关,颂银不是傻子,全听出来了,顿时恼得面红耳赤。
边上那么多双耳朵听着呢,她大声一喝,“都给我滚远点儿!” 众人面面相觑,豫亲王抬了抬手,“听福晋的话,都散开。
” 谁是他的福晋?连容实都没管她叫少奶奶呢,他的福晋倒叫得爽口! 她攥着两手说:“我和您说了不止一回了,您这么不依不饶的,到底想干什么?就算我和容实断了,也没您什么事儿,您早早儿歇了心吧!” 他冷冷哼笑,“你都到了这份上了,还傲性呢?你不嫁我嫁谁?你能嫁谁?谁又敢要你?” 她高声说:“我嫁不掉就当姑子去,为什么非得嫁人?我用不着依仗男人,我自己也能养活自己。
” 是啊,她说得响嘴,将来内务府都是她手上的玩意儿,要多少钱没有,还指着男人养家吗?他也被她激怒了,这种时候为什么不顺着台阶下,非要跟棵朝天椒似的,逮谁呛谁。
天上又下起雪来,飘飘洒洒的,撒盐一样。
他瞧她穿得单薄,解下大氅给她披上,她浑身长刺,不许他碰,不稀罕他的示好。
他这人就是这样,她越反抗他越是非得办到不可,使了蛮力把她狠狠裹起来。
她嘴里不屈地叫着,“往后我和您两不来去!” 他充耳不闻,“男人的事儿女人别管,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 她想说他分明布库输给了容实,有什么脸说这句话。
可是她吃不准,不知他是不是有意落败,好叫容家女人们如临大敌,自发地来退她的婚。
其实换个视角看,的确胜利者是他,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叫他们内斗,把她放到一个十分难堪的位置,迫使她妥协。
难道在他眼里这就是喜欢?是爱吗? 她哽咽了下,“您对我有感情吗?” 他说有,“以前我只觉得你是个有能耐的女人,现在我觉得你是个有能耐的好女人,适合给我当福晋。
” “那您不问问我喜不喜欢您?”她眼泪汪汪说,“您能把我当人看吗?能尊重一下我的决定吗?您要我跟您过日子,您起码先征求征求我的意见,看看我瞧不瞧得上您呐。
” 他一听不悦,“用得着问?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你不喜欢我,还能喜欢谁?我是和硕亲王,前途不可限量。
你不想当主子娘娘吗?当个四品的破官儿,后脑勺插根单眼花翎,成什么气候?爷让你戴东珠朝珠,叫所有女人都羡慕你,这样还不够?” 他以为许个皇后的宝座就能收买她了,想让她当皇后,也得看他有没有造化当皇帝! 他隔着大氅抱住她,被她一脚踢在了胫骨上,“您瞧我像个贪慕虚荣的女人?要说名声,本来我还有点儿,我是整个大钦唯一的女官。
我不靠端茶送水,不靠自荐枕席,我也能在紫禁城立足。
可后来全被您毁完了,你让我丢尽了脸面,现在您还来和我说这个?” 他忍痛扣住她,天上下雪也不管,两个人淋得一头白,他胡乱给她掸了掸,好言道:“你有什么怨气,想发泄就发泄吧,发泄完了你还得跟我。
你不想争口气给容家瞧瞧?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她挣扎了半天,终于把他的大氅扯下来扔在了地上。
她不喜欢他的味道,以前还觉得清润甘甜,现在只剩厌恶。
尤其他还是个颠倒黑白的人,她愈发嫌弃他的品格了,“人家在感情上头没有对不住您,您为什么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容实诚心投奔您,您就这样对待人家?我虽然和他没能修成正果,可我的心是公正的,我觉得您这么做不厚道,您应当用人不疑,难道不是吗?” 他却说得俯仰无愧,“谁让他和我抢女人。
”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嫁给男配的大佬哥哥/我在豪门混吃等死林绵绵
- 皇家福星午时茶
- 穿越之知青时代[空间]酥肉曲奇
- 剑灵也要被迫修罗场星棘
- 想你想疯了奚六
- 不做替身许君三生
- 他来时星光璀璨[快穿]北聆
- 魔天记忘语
- 银子小姐注孤生[综]拌葱白菜
- 败给温柔江萝萝
- 她不当刁民很多年/禁骑司日常蓝艾草
- 元龙任怨
- 为师到底怀了谁的崽瓜子猫
- 大佬全是我养的猫[穿书]白夜未明
- 大小姐人设崩了!板栗子
- 诸天我为帝兴霸天
- 穿回来后嫁给残疾大佬池陌
- 楚留香新传:借尸还魂古龙
- 奶牛猫的恐龙牧场枫香
- 在惊悚游戏搞网恋[无限]榆鱼
- 我在修仙界发展美食禅猫
- 鸿蒙仙缘[穿书]看泉听风
- 高调宠婚臣年
- 重生七零芳华浓杨李涛涛
- 治愈偏执的他[八零]咚太郎
- 陵中鸟远桥清浅泛莲舟
- 哨向:从万人嫌苟成万人迷郁南栀
- 灾变游戏:我随手普攻,你们却说是禁咒如闻我名
- 双系统伺候你一人,这福气小得了?方向不明
- 追源者不弃胡腾方
- 九重奇异录邵家六少
- 公路求生,我被萌物幼崽们带飞甜蜜蜜月儿
- 轮回密钥:双生系统觉醒山海梦呓者
- 丫丫历险记之地府木兰青
- 怀蛇胎,嫁狐仙猫吉祥
- 时空回响:程楠的千年棋局大雄的狂想曲
- 我在大靖当神捕会游泳的傻鱼
- 末日系统:开局囤爆三十层物资稻花儿香
- 黑暗哨向:我的星星自由平等粮食柿柿
- 我以饕餮镇诸天薛逸辰
- 回望之风云骤起迟未晚
- 噬骸武装爱吃芦荟生食的鲁钝
- 两只蚂蚁闯天下望着天空的小赵
- 救赎莫问天心痴念
- 玩死亡局,我从不出局云浅梦深
- 欧皇?我吗?也就十连出金吧莫莫不吃药
- 丧尸也怕三刀流老柴酸菜牛肉面
- 觊觎平行宇宙的挚友骑士棋
- 恶灵信息库北极猎手
- 阴阳五术,风水凶局目垂觉
- 怀蛇胎,嫁狐仙猫吉祥
- 公路求生,我的房车是移动别墅锦司司
- 我以饕餮镇诸天薛逸辰
- 基因暗码:血色螺旋安徽淮南鲍玉佳
- 觉醒功德系统:靠断案成警界神话芒果爱嘉慧
- 渊墟烬生清风漫卷
- 回望之风云骤起迟未晚
- 幽谷怨灵爱吃花朵馒头的郭锐
- 全民文明进化生存猫朕
- 山海纪元:灵契觉醒周日魔王
- 觊觎平行宇宙的挚友骑士棋
- 七日终焉回响小包很困
- 恐怖游园万能蔬菜土豆大王
- 雪人迷踪爱吃蓑衣米酒的清芷
- 超未来世界韦小宝深渊岛的魔息大帝
- 从404空军基地开始的星海征程卡门线上的幽灵
- 天河璀璨之硅碳战争月亮下的老拐
- 柯学:妃英理三年抱俩不弃九九
- 大妖三千神奇小小猪
- 废土之王笑死鸟
- 重生归来:我提前一年预警末日枫香晚花静
- 茅山后裔之小道归元一一同人小说小力金刚掌
- 穿到星际,本喵靠摆烂拯救全人类照月亮的猫
- 渣雌回归后:兽世傲娇父子求抱抱星糖萌主
- 太素佛主:启量子幻域究佛魔玄机诗天意
- 哨向:从万人嫌苟成万人迷郁南栀
- 九重奇异录邵家六少
- 绝境回响:救赎边缘用户45295799
- 怀蛇胎,嫁狐仙猫吉祥
- 这个出马仙有点der微雨问冷风
- 末日系统:开局囤爆三十层物资稻花儿香
- 斩妖灭鬼,从高中开始白雪里黑
- 我以饕餮镇诸天薛逸辰
- 诡神,杀!AAA鬼手七
- 救赎莫问天心痴念
- 综影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清蒸毒蘑菇
- 舌尖女帝:我在三界涮锅搞事情爱吃水铺蛋的弘一法师
- 山海纪元:灵契觉醒周日魔王
- 寄生家园绿小霜
- 灵异执笔者银河赠予的糖
- 双届孤行秦皇岛主
- 全球高温:我囤好物资吹空调偏死猪猪
- 末世祸水!丧尸美人被强制圈养后非关阴晴
- 重生归来:我提前一年预警末日枫香晚花静
- 茅山后裔之小道归元一一同人小说小力金刚掌
- 上岸后,我靠摆烂当星际霸主花卷奶茶青
- 雪宣折痕我很苦的
- 绑定哪吒,我成华夏神明团宠乏乏四十一
- 典当师饺子面条火锅
- 盗墓之可单开族谱聊聊呗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