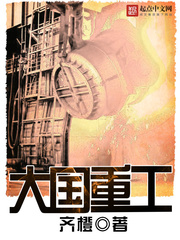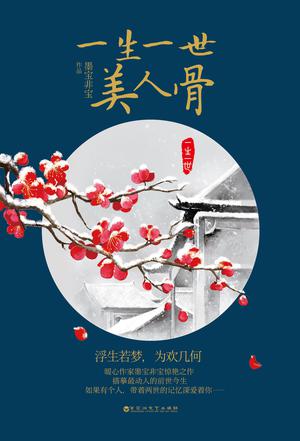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一章 江边明月为君留(1/3)
一 帝京康宁殿内,尚睿读着齐安传回来的消息,信写得极简单,平铺直叙,不带任何感情。
齐安的一手蝇头小楷,在仓促奔波的情境下也写得十分漂亮,信中有一行字——徐敬业自缢于风回镇,尸身已送还徐家军。
尚睿盯着那句话看了许久,心中竟然十分平静,无喜无乐,不悲不哀。
他终究还是亲手将徐敬业送上了这条路。
然后,他去了太后的承褔宫。
太后并未歇下,年纪大了晚上睡得早,又总是睡到半夜就醒了,现在实在睡不着,便起身去佛龛前念经。
从上次争执后,她一直对尚睿拒而不见。
如今得知尚睿突然子夜前来,已在殿外等候,她心中已经有了些预感,草草换了衣服便叫他进来。
尚睿进门刚刚坐定,便将徐敬业的死讯告诉了她。
他觉得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总比太后听着别人带来的消息好。
太后呆愣着,静坐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皇帝切莫忘了你对哀家的承诺。
”说完这句,拿帕子擦了擦湿润的眼眶。
尚睿点点头。
太后无声地哭了半晌,待眼泪擦干后,顿了顿,清了一下嗓子:“这春日里天气好,哀家想去舜州的行宫住一住。
” “如今南边未定,怕是路上遇见刁民冲撞了母后,不如再缓缓。
” “哀家一个老太婆,有什么可怕的,过去这京里的魑魅魍魉都奈何不了哀家,何况区区刁民。
” 尚睿淡淡道:“儿子不孝。
” 太后冷笑一声:“你留着哀家一条命已经是孝顺至极了。
” 尚睿知道太后性格执拗,越劝越讨不着好,便不再说。
他一停下来,气氛更加不好。
太后又说:“哀家走后,你也别太惯着皇后。
王家人该管就管,你别宠出第二个徐家来。
” “儿子谨记母后教诲。
” 他在夜色中出了承褔宫,绕过了流波湖,漫无目的地走着。
后面跟着的内侍和宫女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只好远远跟着。
明连走上前替他掌灯,也被他拒绝了。
天空乌黑无光,一颗星星也没有。
夜已深,各处都熄了灯,只能远远看到角楼上还亮着光。
此刻不知为何,他仿佛有种这漆黑的宫墙内只有他一个人的错觉。
夏月跟着李季学医学了好些天了。
她刚开始还有些消沉,后来一心扑在替子瑾治病这件事情上。
暗处的姚创看在眼中,也放下心来。
他没想到尚睿上次的方法十分见效。
一软一硬的两句话,恰到好处地拿捏着夏月的软肋。
李季本来就是个一板一眼的人,教起人来也是不含糊。
夏月将子瑾的症状详细地写了下来,他粗略地瞥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从最入门的开始教。
他讲的那些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别经……夏月之前就略通,所以学起来没有费多大的功夫。
再来,他一边教各条经脉的规律,一边教她用针。
李季说:“古法多以纯金、纯银制作针。
金针一般八分金两分铜。
柔软易弯,若非修行内劲,一般人无以得用,但是对急症重症,好于银针。
”说着,他将几种针展开给夏月看,“而银针施针的时候,可以凹面弯曲推进而不折断,可用于较深的穴位。
” “我还见过铁针。
”夏月想起以前穆远之的针。
“对的,用的是马嚼子上的那块纯铁,叫马衔铁。
” “其他铁不行吗?”夏月问。
李季摇头:“铁中金有伤人的锐气,《本草》里有记载,以马属午火,火克金,所以金气已除,才可用在人身上。
” 两个人在书房里,一问一答,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
李季见夏月还想继续,便说:“闵姑娘,学医切忌急功近利,还是慢慢来得好。
” 夏月被人看透心思,不禁有些羞愧,只得拿着李季给的医书告退。
走了几步,又退回来:“先生那日为何突然应允我,愿意教我医术?” 李季不太会和人打马虎眼,便直说:“我也是受人所托,并非一时大发善心。
” 夏月从李季那里回来,却见荷香坐在屋里,神色不定。
“怎么了?上街前都好好的。
”夏月问。
如今她是被软禁起来了,出不了李季府,好在荷香还可以随意进出。
荷香眼中蓄着泪,抬头说:“小姐还记得以前在翠微楼唱曲的余家姐妹吗?” “余音儿和余画儿?”夏月自然记得。
“今天我上街遇见余音儿在街上喊冤,拦了一位大人的轿子,说要为她姐姐伸冤。
” 夏月预感不妙,忙问:“她姐姐怎么了?” “我远远听着她说她姐姐被王淦强抢回府,然后又被他活活打死了,她告状无门,这才上街拦轿申冤。
” 夏月听见王淦那个名字,心中像被针蛰了一般,嘴唇抖了起来:“王淦也在帝京?” 荷香没有注意夏月的脸色,擦了一下眼泪又说:“应该是吧,听余音儿说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 “余音儿拦的是谁的轿子?” “我倒不知道,只是那个大人也不是个好官,他先还说要给余音儿做主,后来听说对方是王奎之子便怂了,还责骂余音儿,说她被人买通了专门挑这个时候来污蔑王家,污蔑皇后。
” 夏月听着,拳头握紧,久久不言。
荷香又问:“王淦真的是皇后的亲戚?” 夏月冷笑一声:“那自然是错不了。
” 荷香怕她饿了,拿出刚才从街上买回来的点心,又斟了一杯热茶。
夏月擦了手:“后来呢?” “后来那大人的侍从将余音儿掀到一边就走了。
倒是旁边有好心人,凑了一些银子给她。
我不敢上去怕给小姐惹事,就将小姐给我买东西的碎银全部托旁人偷偷塞给她。
结果,她都没要,她说她不稀罕银子,她只希望这青天白日下还能有个公道。
” 荷香说完又哭了。
第二天,尉尚睿在乾泰殿将弹劾王奎的折子一把摔在他的跟前:“你自己看看。
” 王奎哆嗦着拾起一本读了一遍,辩解道:“微臣的孽子虽然年少无知,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微臣冤枉。
”他刚调回帝京不过几日,便认定这些肯定是政敌的下作手段而已。
“你还狡辩,”尚睿眯起眼睛,“你儿子的所作所为朕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难不成朕也冤枉你?” “微臣……微臣……”王奎完全不知道尚睿说的亲眼所见是什么缘由,擦着汗不敢接话。
“他当着朕的面说的那些话,估计你都没胆子听。
”说到这里,尚睿倒是不怒了,冷冷地看着跟前的王奎。
王奎跪在地上,全身都瘫软了。
这时殿外来禀,说皇后来了。
尚睿讥讽道:“她倒是来得快。
” 王奎一听,就跟见着救星似的,顿时人又来了精神。
其实王奎来之前就知道不妙,便派人去妗德宫求援。
王潇湘走到殿内,先给皇帝行了礼,又一一拾起地上那四五份折子,将它们规整好放回御案上。
“皇后来得正好,”尚睿说,“这就是皇后跟朕所说的王奎教子有方?如今徐家大权更替,唯恐朝廷不稳,你们一个个不但不谨慎,还做这种欺男霸女的事情……真是混账。
” 他本来是骂王淦,说到“欺男霸女”这四个字的时候,自己脸上的神色滞了滞,突然不自在起来,于是顿了一下,胡乱加了句“真是混账”草草了事。
旁边的明连知道其中缘由,垂着头,不敢有一点异动。
王潇湘一脸窘迫:“臣妾偏听误信,还请皇上降罪。
” “你确实应该好好醒醒,那孽畜拿着你的名号到处为非作歹,竟然还有人跟朕说他品行端正,”尚睿冷笑,“朕真后悔当日在酒楼里没一刀剁了他。
” 王潇湘对王奎道;“王大人回去叫王淦到廷尉府自首吧。
” 王奎又擦了擦汗:“回禀娘娘,这孽子他……已经两日未归了。
” “去哪儿了?”王潇湘问。
“微臣真的不知啊。
”王奎急忙伏地叩首,对尚睿辩白道,“微臣丝毫不敢欺瞒陛下和娘娘。
” 尚睿斜睨着王奎,没工夫揣摩他话中真假,直接说道:“朕给你三日,你若是三日内交不出人来……” 王奎不待尚睿发话,便急急说:“臣便自己去廷尉府请罪。
” “朕倒不是那样的昏君。
王淦虽是你的养子,但他所犯的人命,却不是经你之手,杀人奸淫之罪并不株连。
只是你教子无方,倒是早该罚一罚。
” 王奎大气不敢出,只敢连声称是。
尚睿又说:“这事先交廷尉查实,若是罪证确凿,朕定不饶他。
” 王奎和王潇湘刚走,贺兰巡就来了。
“皇上。
”贺兰巡匆匆前来,“这是刚收到的密函。
” 尚睿接过信匆匆一览,然后对贺兰巡说道:“尉冉郁要约朕密谈。
” 贺兰巡忙问:“在何处?” “他要来帝京。
”尚睿答。
贺兰巡喜出望外:“恭喜皇上兵不血刃。
” “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尚睿看着桌上的茶盏,抬手在茶里蘸湿了食指,然后用指尖在盏口描着圆圈。
云中失而复得。
这是他走得最险的一步棋了,如今胜果唾手可得的时候,他却没有预想中那样欢喜。
徐敬业已除,太后搬进离宫再不理国事,淮王气数已尽朝不保夕,连尉冉郁也甘愿助他,看起来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他求而不得的,可是…… 他想起摇摆颠簸的车厢里,那双替他揉搓十指的手,又想起那一夜他怒火攻心后的失控。
此刻,一颗心陡然像是被什么人拿捏在了掌中,跳动都不由他自己。
成年后他连脸上的喜怒忧思都要控制分寸,何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那根仍然在盏口画圈的手指猝然用力,茶盏应声翻倒,水洒了一桌。
明连急忙用自己的袖子阻断了快要滴到尚睿身上的茶水,又轻声唤人进来收拾。
尚睿从椅子上站起来,静静地看着宫女和内侍将桌子擦干,又将浸水的折子一一平铺开。
贺兰巡见他脸色不太好,拱手叫了一声“皇上”。
尚睿敛神,转身问道:“朕要你去办追封先储帝位,将他们夫妇迁至古舜皇陵的事情怎么样了?” “臣和太常寺拟了几个待选的庙号,正要请皇上定夺。
”说着他将预备好的折子递了过去。
尚睿瞄了一眼,又合上:“到时候让冉郁自己拿主意吧。
” 贺兰巡又说:“此事朝中还是有人颇有微词,先储若是追了位,那皇上君临海内这十载,又以何而正?” 尚睿挑眉:“众口悠悠,若朕要管,也只管得了一时,管不了后世之事,何苦自寻烦恼。
随他们去吧。
” 贺兰巡将那折子接了回去,放在袖中。
“另外,”尚睿说,“还有一事,当年先皇喜爱冉郁,封了他一个燕平王,却是虚衔,并无封地,你们看看,指哪一处给他比较好?” 贺兰巡思忖了一下,当即就说:“皇上是要将他留在身边,还是远放?” 尚睿懂他的顾虑,说道:“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心思太喜欢拐弯。
” 贺兰巡也不反驳:“臣……” “我看云中就很好,富足又自在。
” “云中?那是皇上龙潜之时,先帝御赐给皇上的封地。
” “朕欠他的,一并还他吧。
”尚睿淡淡道。
“臣却认为不妥。
梁州、吴州与云中都相距不远,如果其中一人再起异心,相互连成一气,恐怕又是一场淮王之乱。
” 尚睿负手踱了两步:“朕多日来也在想这事,所以朕有个想法,虽并不急于这一时,但是现在还是可以私下和你说说。
” 贺兰巡洗耳恭听:“微臣愿为皇上分忧。
” 尚睿蹙眉:“淮王这事是前车之鉴,更让朕想废了这藩国制。
” 贺兰巡心中一骇,愣在原地,因为太过惊讶,半晌才出声问道:“皇上真的要废藩?” 尚睿一笑:“本来不敢想,但是这些藩王中以淮王风头正劲,现今已拿他开了刀,看来最先啃下这块硬骨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淮王尚且如此下场,其他人更加不敢妄动。
贺兰巡心中顿时明了,当初尚睿为何说出“就怕淮王不反”这样的话来,原来在徐敬业和淮王之后,尚睿早已经预想到了这一步。
他自己是两朝之臣,当年年轻气盛之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无人敢提,废藩之事稍不注意便会酿成千古大罪,所以大家都得过且过地回避着。
藩王之祸由来已久,却不想尚睿有这样的气魄。
想到这里,贺兰巡觉得胸中有东西激荡开来。
“朕的祖父太宗皇帝曾经推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句话,便叮嘱先帝多封藩,这样让他们互相削弱,国小而不生邪念。
朕不敢说太宗皇帝有错,只是朕临御之内不想继续这般听之任之。
藩国割据四方,皇命阻绝,西域外邦对我朝虎视眈眈,日夜枕戈待旦。
若是想绝后世之患以四海承平、八方宁靖,唯有削藩。
”说到这里,尚睿的话语微微一顿,问道,“伯鸾,你可愿助我?”伯鸾是贺兰巡的字。
他问完话,等了等,却未闻贺兰巡开口,但见对方撩起袍子跪在地上,沉沉地叩首。
贺兰巡平时是个巧言善辩之人,时刻却居然闷着声,许久才重重地应了一句:“皇上所愿,臣誓死追随。
”眼中竟然隐隐噙泪。
尚睿挥挥手让明连扶他起来,浅浅笑道:“当然,朕不是傻子,如今时机未到,提这个还早,只是朕有这个想法,先跟你通个气。
这事仅有你知我知,先搁在心底,切忌操之过急。
” “臣明白。
” 须臾,贺兰巡不解道:“既然皇上决心削藩,为何又要加封燕平王?” “本来就有十余个,也不多他一人。
别人有的,朕自然要给他。
” 不觉已到了午膳时间,尚睿顺便留了贺兰巡一同用了膳。
膳后,尚睿说:“别慌着出宫,朕换身衣服,和你一起走。
” “皇上这是?” “去李季府。
” 贺兰巡犹豫着说:“皇上……臣有一句话,还望皇上不要怪罪。
” 尚睿猜到他要说什么,斜睨着他:“既知出口有罪,那就不要说了。
” 贺兰巡叹着气,他怕尚睿这般聪明天纵,却损在一个“情”字上面。
二 李季继续在书房里教夏月用针的方法。
屋子中央放着一鼎香炉,几缕淡烟从炉子里袅袅升起。
“这蟾蜍需要夏秋二季捕获,洗干净以后,把它耳后和皮肤上的浆汁挤出来晒干制成蟾酥。
要用时将蟾酥融在酒里,再淬在针尖上。
” “蟾酥莫非和麻沸散一个功效?”这是夏月的声音。
“不错。
之后针尖还要用再入火微煅,然后再淬蟾酥液,反复多次,其次才打磨针锋。
一切完工后,配着古方来煮针。
”李季说,“即便不是新磨的针,久放未用也要按此蒸煮。
这方子你可记一下——麝香五分,胆矾、石斛各一钱,穿山甲、当归尾、朱砂、细辛各三钱。
” 夏月在旁忙乱道:“先生,你说慢些,我写得没有那么快。
” 李季倒是好脾气,又缓缓重复了一遍。
此刻春意已尽,院中的草木已经有了初夏的颜色,帝京的春天总是特别短,不过树上的枝条却抽得十分快,每天都换着模样。
尚睿一直站在门外,一字不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衬着这弥漫开的浅浅夏意,心中竟然十分惬意。
李季教完制针又开始说针法:“针法有纳甲法、养子法、脏气法……” 这时,李府的管家突然从游廊走来,看见尚睿正要行礼,那声“洪公子”还未出口便被尚睿噤声的手势止住。
管家只好恭敬地略过他,进了书房:“老爷。
” 李季被打断:“怎么?” 管家便说了前厅来了亲戚,要李季去处理。
李季听闻后叮嘱了夏月几句话,就随着管家出来,走到门口看见尚睿。
尚睿摆了摆手,仍旧叫他不要出声。
李季走后,屋内外都变得安静起来。
尚睿继续站在廊下。
夏月则坐在椅子上誊写自己刚才记下的方子,过了一会儿记起昨天李季给她的书还在桃叶居,于是搁了笔,想趁着李季回来之前去取来。
她挪开椅子,带着小跑,疾步出了书房,走到门外,她疑惑地朝四周看了看。
刚才这里似乎是有人,但是此刻却空荡荡的。
她知道这李府表面上似乎任由她进出,其实不过是为各自留了一份薄面而已。
那夜尚睿带着怒意推门而入便可知道,她的一举一动皆在别人的掌控之下,可笑的是她居然舍不得杀了他,还怕他因她而死,在那颠簸冷硬的车厢内,她藏着刀,怀着惊恐和胆怯,连眼睛也不敢眨地护着他。
夏月站在树下,自嘲地苦笑。
取了书,夏月又回到书房,发现李季已经在屋内等着她了。
夏月好奇地问了一句:“先生平时都这样清闲吗?” 李季本来坐在桌案旁边,在查看前几日的医案,闻言抬头看了夏月一眼,自知不能跟她明说他这些时日被特准赋闲在家的缘由,只得答:“你看我哪里清闲了?虽然不用像前朝太医院那些人一样事无巨细地查看后宫嫔妃的情况,但也不闲着,每天要研究医案,又要试药,做些笔录。
各有追求,说起来,哪个人又是真正地闲着呢?“ 李季放下手上的东西,走到一侧的书架旁边,从一堆装订成册的医案中抽出一本册子:“这是我自己编撰的针灸纪要,你也可以拿回去看看。
”说完这句,李季又瞧了她一眼,真心告诫道,“我还是那句话,急于求成是学医大忌。
” 夏月神色一黯,点了点头。
三 尚睿回到宫里,去了妗德宫用晚膳。
王潇湘事先不知道他要来,她早就吃过了,如今又叫了人来摆膳。
王潇湘见他默不作声,误以为他还在为王淦之事不悦,心中自知理亏,只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用膳时,尚睿胃口不太好,一顿饭草草用完,又有人端着水让他漱口。
他接过茶盅,抬眼看了一眼端着托盘的人,正是他从前下令不许再出现在康宁殿的那个宫女。
她身量高,四肢和姿态倒是和夏月有几分相似,当时他看着心烦,又厌恶皇后的用意,于是就说了那样的话。
王潇湘见尚睿多看了她两眼,本想再撮合一下两个人,又怕自作聪明地惹恼他。
尚睿收回视线,摆了摆手叫人下去。
“这人不要留了,过几日就放她出宫去。
”尚睿漫不经心道,看样子又是要留宿在妗德宫的样子。
王潇湘便命人去准备。
这几个月,她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除了来妗德宫,竟然没有让任何人侍寝。
外人只以为她霸着今上一个人,独宠后宫,可是这其中真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她的寝宫里一直摆着两张榻,其他人都以为她睡眠不好,所以夜里要和尚睿分榻而眠。
熄灯后,他咳嗽了两声。
她不禁道:“皇上晚上可不要贪凉。
” 他翻了个身,没有答话。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他翻过身来,突然冒出一句:“潇湘,我哪点不如皇兄?” 王潇湘一愣,对于先储的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爆款创业清蒸日华
- 重生后我撩我自己冷冻玻璃渣
- 无敌天下神见
- 小李飞刀3:九月鹰飞(上下)古龙
- 心悦臣服卓涵月
- 未生葡萄
- 暴君每晚梦我五月锦
- 我的时光里,满满都是你(呆萌小萝莉:高冷男神太腹黑)忘记呼吸的猫
- 人生得意无尽欢六道
- 兽血沸腾静官
- 与你沉沦[娱乐圈]一夜从灯
- 穿到七零当厂花唐柒鱼
- 嫁给冷血男主后我变欧了[穿书]/嫁给杀器后我变欧了[穿书]蒸汽桃
- 白发魔女传梁羽生
- 同萌会的一己之见楚凤华
- 重度痴迷多梨
- 万人迷炮灰被迫躺赢郎不知
- 身为卧底的我要成为港口Mafia首领了昭文
- 定风波来风至
- 功德印青衫烟雨
- 炮灰的马甲又又又掉了冰糖火锅
- 草莓味的A不想恋爱凉皮就面包
- 玉昭词(今夕何夕原著小说)时久
- 我家别墅能穿越传山
- 重生之大画家轻侯
- 水煮大明嗒嗒猪
- 学渣的传奇人生迎凤村草
- 锦衣卫:陛下,何故谋反!叁金诶
- 边军凶猛赤阳
- 天赐良臣爱吃炝炒丝瓜的胡掌柜
- 暖房丫环,建社团当大佬浩浩荡荡大淘金
- 都市我能望穿万物忘忧无虑
- 我的美艳师姐妹燕山夜话
- 重生六9:倒爷翻身路惊恐不安九仙君
- 傲神传蚂蚁
- 超级聚魂幡星际黑伯爵
- 武侠:莽昆仑严久霖江洲雨林
- 在成为西门吹雪的日子里笑点烟波
- 邪仙偷腥的猫
- 曲樟纪事陈加皮
- 惭愧惭愧,小爷天生富贵菲硕莫薯
- 五鼎封天古道行者
- 地府通行证风化羽
- 重生仙尊归来恰同学少年
- 上山为匪彗星撞飞机
- 最强反套路系统太上布衣
- 易鼎荆柯守
- 元末轶事享邑
- 逆天七界行诸神的荣耀
- 欺世盗命群青微尘
- 北军悍卒虎虎
- 大宋:朕的专利战横扫1126心有灵犀的金毛狮王
- 王伦逆天改命称帝失控的牛
- 剑影书迷之宝藏寻踪喜欢半减七和弦的子豪
- 科举:我的过目不忘太招祸!我热痢的马
- 我,大楚最狂太子蜗牛王子
- 乾元盛世系统冀北省的护法神
- 大明锦官梦苏梦沉
- 穿越战国我靠杀敌称霸天下王权荣耀
- 我在古代当镇令龙葵宝宝
- 穿越宋末,海上发家先滨
- 我的春夏秋冬:人生全记高山流水兮
- 古代打工日志:从退婚开始躺赢西猫西
- 纯阳第一掌教池宁羽
- 拜见教主大人封七月
- 极品仙途闻人毒笑
- 宇宙本源诀冰冷眼泪
- 上山为匪彗星撞飞机
- 重生归来之神帝薛九玄清方观世
- 大明:雄英别怕,二叔来了!戴夫本夫
- 千宇仙寻书生无愁
- 战傲穹苍半世浮生
- 末日进化:捡垃圾就能变强千易寻
- 逆魔战天七输
- 大秦:九皇子百夜承欢醉月孟浪
- 逆命武侠行随风飘扬的喜哥
- 霍东觉之威震四方夏夜晨曦
- 大明:我崇祯,左手枪右手炮二月十八
- 命理探源【译注】陈缘字长青
- 大明第一墙头草随轻风去
- 大宋第一猎户:女帝别低头!一起抓水母
- 我在仙侠世界研究科学甜荔酒
- 乾元盛世系统冀北省的护法神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这破系统非要我当皇帝总有那一天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穿越商朝,为了人族而战叫不醒的清醒着
- 学渣的传奇人生迎凤村草
- 洪荒之鲲鹏绝不让位李九郎
- 道术达人虫梦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
- 五鼎封天古道行者
- 我才不想当用剑第一桃子糖
- 逆天七界行诸神的荣耀
- 欺世盗命群青微尘
- 六道教主造化斋主
- 死后七百年:从城隍开始签到九灯和善
- 乱世饥荒:从开局选妻开始钟声挽
- 天玄剑传奇断臂小仙
- 征帆天涯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