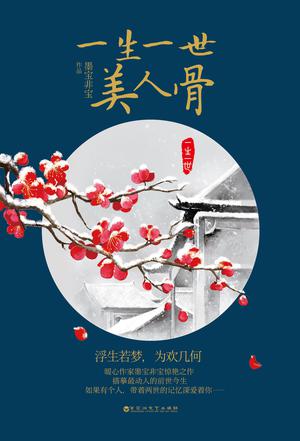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九章 芙蓉向胜两边开(2/3)
田远接着贺兰巡的话,说道:“皇上准备发出最用力的一击了,把所有的琉璃球都弹到它应在的位置。
”只要徐承致肯听话,他便能全身而退。
贺兰巡和田远并肩,出了皇城宫门。
在李季的精心调理下,夏月已基本康复,浑身都是劲儿。
夜里,荷香喂了阿墨牛乳后,又去给夏月煎药,一时忘记将狗留在了桌子上。
阿墨舔了舔自己后,想下桌子去,却发现桌子太高了,于是站在桌边望着下面嘤嘤唔唔地着急。
夏月本来在榻上看书,听见它的声音,抬头瞧了瞧。
阿墨探了一只脚下去,又害怕地收了回来。
她无奈地放下书,起身走去将它抱了起来。
她刚才手上捧着手炉,双臂都是暖和的,阿墨的脑袋不禁贪恋地蹭了蹭。
这是她第一次抱它。
那黑色的毛绒小脑袋撒娇,突然触及了她心里很柔软的那个地方,不禁趁着荷香不在时和它多玩耍了一会儿。
睡觉前,夏月叫荷香将上次老太太给的包袱拿出来,取出里面的一些银两,对荷香说:“明日该去辞行了。
这些银两走的时候交给李大人。
”她本想再花些功夫请李季回心转意给子瑾看看病,现在看来是无望了。
荷香说:“小姐你这身子骨刚好,再调理两三天吧,要是落下病根可不好。
” “那——后天走,你可别再拦我了。
” 荷香点点头:“我们回哪儿去?” “先回舅舅那里吧。
反正房子也空着。
” 睡到半夜,有东西在脚边动来动去,夏月摸黑起身查看,发现竟然是阿墨。
她也没撵它,随它怎么折腾。
过了一夜后,阿墨便黏着她,一直跟在她脚边。
小狗又矮又小,跟得也紧,好几次夏月都差点踩着它。
万般无奈,夏月只好将它搂在怀里。
四 散朝后,尚睿照例去承褔宫问安。
徐太后正跪在佛像前的蒲团上诵经礼佛。
他无心打扰,便绕到院子里溜达了一圈,没想到却见到魏王遗孤冉鸿。
自从魏王被诛后,冉鸿就跟故意躲着尚睿一般,再也没敢在尚睿跟前出现过。
他虽然被贬为庶人,却没有旨意要送他去哪里,于是便留在了宫里。
若非时不时有人在朝堂上提醒尚睿留了魏王的余孽势必后患无穷,他几乎忘了这孩子。
其实,不是遗忘,而是不敢去想,怕又忆起孩子的父亲,他的这位兄长。
因为徐太后的缘故,他和兄长们的关系都不甚亲厚,只是魏王做事没心没肺,和谁都能自来熟,所以算起来尚睿居然和他的交集最多。
王潇湘懂尚睿的心思,一直照顾着冉鸿,和皇子冉浚同吃同睡,没受过委屈。
在太后的院子里撞见时,两个孩子正在专心逗太后的那窝狗崽,一见尚睿立马就站了起来。
尚睿招了招手,将儿子叫过来,然后又看了看冉鸿,示意他也过来。
冉浚倒是蹦蹦跳跳的,而冉鸿磨蹭了好一阵子,才一步一步地挪近。
尚睿在凉亭的凳子上坐下。
冉浚请安道:“浚儿见过父皇。
” 冉浚的话还没落地,冉鸿就赶紧跪下:“罪臣之子冉鸿给皇上请安。
” 尚睿眉心一揪,连看了冉鸿两眼,心中有话,可是张了张嘴,却不知究竟要说什么。
他瞥了儿子一眼。
冉浚素来平和聪慧又善解人意,立马扶起冉鸿:“鸿哥哥,你别这样,你是我的哥哥,父皇自然也是你的叔父。
” 冉鸿却再一次跪下,慌忙地叩首道:“罪臣之子不敢造次。
” 尚睿的目光冷下来:“平日里是谁教你这些话的?” 冉鸿却不敢答,跪在地上,背弓得像一只虾,瑟瑟发抖。
尚睿见状又不忍责问他,半晌后,缓了缓自己方才的语气:“鸿儿,你起来回朕。
” 听了尚睿的话,冉鸿瑟瑟地站了起来:“回皇上,是冉鸿自知身……”冉鸿的话还没说完,一抬眸被尚睿的眼色吓住了,不敢再继续往下说。
正好王潇湘也来承褔宫见太后,远远瞧到这一幕,走近劝道:“瞧皇上您把这孩子给吓得,怎么在母后这里教训孩子的不是?”随后,将这两个孩子牵着领回了自己的妗德宫。
王潇湘命宫女拿了些点心给孩子吃。
冉浚含了一嘴的果子,偷偷地瞅了一眼尚睿。
而冉鸿的手还在哆嗦。
王潇湘摸了摸冉鸿的头,又对尚睿道:“你别难为他了,无论如何他也是不敢对你实话实说的。
” 话已经挑得很明了,这偌大的宫里,能让所有人都对他守口如瓶的还能有谁,所以王潇湘才将话岔开,带人离开了承褔宫。
尚睿不是不懂,是心气无处撒。
冉浚毕竟还是小孩子,见父亲母亲都在跟前,咽了嘴里的东西,才敢小心翼翼地替冉鸿辩解道:“是皇奶奶说的,皇奶奶说若是鸿哥哥不知罪孽,不守本分,皇奶奶她就……她就……” 旁边,冉鸿的眼泪已经“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却不敢发声。
冉浚也被感染了一般,忽然哇的一声哭道:“父皇,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皇奶奶,皇奶奶叫鸿哥哥不能告诉我,更不可以告诉别人。
要是皇奶奶知道以后,会不会真的要鸿哥哥死。
” 王潇湘将孩子揽在怀里。
尚睿看了看冉鸿,伸手去牵他。
冉鸿虽然心中有些戚然,但还是走到尚睿跟前。
尚睿道:“鸿儿,宫里的太傅可有教你,何为国何为家?” 冉鸿点了点头。
尚睿语气稍改,又道:“我们是天家子弟,和常人不同,家即为国,国即是家。
冉鸿的父亲也是朕的哥哥,哥哥犯了国法,受到了处罚,朕也很难过,碍于亲疏也许比冉鸿少几分,所以朕可以体会你的痛苦。
可是你没有错,哪怕是你父亲违逆了国法,你却没有错。
你父亲临刑前,朕去看过他,他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你能好好活着,堂堂正正地做个有用之人。
你这一生的本分就是要带着你父亲的期待活得更好,而不是背着莫须有的罪孽自怜自哀。
” 冉浚听完这一席话,顷刻扑在尚睿胸口,紧紧抱住他号啕大哭了起来,嘴里一边抽噎一边喊着:“九叔,九叔……”那声音旁人听了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尚睿用了半日的时间陪着两个孩子在妗德宫玩弹珠,直到用了午膳,该午歇了。
尚睿看着王潇湘领着两个小孩子走后,神色渐渐凛冽。
明连站在尚睿身后,丝毫不敢大意。
王潇湘从偏殿去而复返,看到他微微一怔。
“皇上。
” 尚睿周遭散发出来的寒意与戾气几乎将他整个人裹了起来。
小几子上摆的瓷瓶里斜插着几支开得艳丽的桃花,这扑鼻的春意却没有将他那张俊脸渲染出半丝暖色。
他一言未发地回了乾泰殿,命人磨好墨后,屏退了包括明连在内的所有宫人,他亲自蘸了浓稠的墨汁,展开桌上的卷轴,缓缓落笔。
半个时辰后,明连才在门外听见尚睿唤他,随即又跟着他再一次去了承褔宫。
这一回,太后刚刚午睡起身,头发绾了个新式样,整个人显得十分精神。
她抬头一见尚睿的面色,便知道他有话要说,便叫旁人都退下了。
偏殿里,只剩母子二人。
太后平了平衣上的褶子:“说吧,何事?” 尚睿开门见山道,“儿子方才拟了两份旨意,母后看看,究竟是发哪一份好?” 说完,他将两幅卷轴都放在太后身边的案头几上。
太后展开一幅,匆匆读了一遍,带着怒意瞪了一眼对面坐着的尚睿,重重放下后,又拿起另一幅,还未读完整个人已经变得怒不可遏,一把将手里的东西狠狠地扔到尚睿脚边:“混账东西!你这是要逼死哀家?” 尚睿听着太后口中“混账东西”这四个字,平静地回道:“母亲养了儿子这么多年,最后也只是当儿子是件东西吗?” 太后勃然怒道:“你还知道哀家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却要灭了徐氏满门?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尚睿不答。
太后见他这般态度,指着他的鼻子,大喝道:“你给哀家跪下!” 听闻太后的责骂,尚睿起身照做。
“你看你写的这些都是什么,”太后被气得双手哆嗦,拿起案头几上另一幅卷轴,含着怒念道,“今国难在即,魏王徐敬业空握兵权,大败叛军。
之后竟与叛贼联合,意欲谋反,其心可诛。
现革去徐敬业魏王称号,剥其世袭之权。
朕念徐氏为我大卫朝国亲,特赦其族无恙。
然,徐氏一族终生不得为官,若非奉旨召见不得随意进京,若有违背,株连九族……”到后面,太后都念不下去了,一把将圣旨拍在桌面上。
徐太后本身就是个烈性子,越说越怒,抄起桌子上剩下的半碗薏米莲子粥朝尚睿砸过去,没想到他竟然没躲,碗砸在他胸口,落地碎成两半,粥泼了他半身。
尚睿跪地,默不作声。
“你倒是给哀家说话啊!”太后怒视。
尚睿垂眸,淡淡道:“儿子能说什么,母后您也并非不知徐敬业他为何会被尉尚仁生擒。
” 太后一愣,这事她自然是已经知晓,支吾着说:“你……你舅舅……他不过是收到五妹的书信,说是可以救徐阳一命。
你知道徐阳是他的命根子,所以他才冒险带着心腹……”太后口中的五妹便是淮王妃。
尚睿冷斥:“这事不知母亲从何得知,他们为了欺瞒您,竟然编出这样一个父子情深的谎话。
” 他继续道:“信确实是淮王妃所写,可是里面写的却是徐敬业为谋划他心中所图,句句皆是劝他与淮王连手,妄想与之携手平分天下。
” 太后怒视他,全然不信:“你怎能断定,哀家知道的是假,你知道的却是真?” “那封信,儿子已经派人拿到,不日就可以送到帝京,让母亲可以亲鉴淮王妃字迹。
” 徐太后闻言有些语塞,于是又说:“你怎知不是尉尚仁的反间计?” “母亲可知,昨夜司马霖已经找到徐阳。
” 徐太后诧异:“他不是被尉尚仁捉住了吗?” “南域哗变,徐阳在叙州大营骑兵突围,被困石城山,混战中身负重伤,被一猎户所救。
” 太后听闻,连忙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双手合十走到佛像前拜了一拜:“菩萨心善,菩萨心善。
” 尚睿见状,眸中染着清冷:“母亲修来的菩萨心肠只对徐阳他们,却没有冉鸿他们吗?” 徐太后驳斥道:“你懂什么,没有徐氏哪有你的今日,尉家这些人早就把我们母子吃了。
” 她一边说,一边又从佛龛前走了回来:“就算徐阳无恙,也不能证明你舅舅他有了逆心。
” 此刻,徐太后已经平静了许多,对尚睿的话虽不是全信,却也有了疑心,她以为尚睿肯定会继续拿话来劝说她,没想到尚睿却一点头,答道:“不错。
” 他抬眸继续说:“但是朕要它是真的,就能是真的。
朕会叫人模仿徐敬业的笔迹,写封回信给尉尚仁,有了之前淮王妃的手书,铁证如山,假的也会成为真的。
那尉尚仁捡了个渔翁得利,多半也会继续把戏做下去。
若是他不识时务,偏要和徐敬业撇开干系,那就更好办了,朕可以说他是做戏想要保护徐敬业而已。
时机一到,朕再将这张旨意发下去。
母亲,您说到时会如何?” “你疯了!”徐太后惊骇道,“你知道若是徐家军被你逼得临阵倒戈,会有何后果吗?” “朕若让徐氏满门血流成河,那鱼死网破是其一;若是他们与尉尚仁结成一气,反过来要了儿子的命,这是其二。
本来成王败寇,儿子无话可说,可是到时母亲您如何善终?” “那你拟这样的旨意作甚?”徐太后气极反问。
“所以儿子才拟了另一份,请母亲定夺。
”尚睿垂手,将刚才被太后摔在他脚边的卷轴拾起来,双手呈上,“徐敬业若是能自裁于叛军狱中,儿子会以国礼待之,迎回尸身,将他按封王品阶葬于王陵,徐家卸了兵权,可保永享圣宠。
” 太后看着尚睿手上的那份圣旨,久久不曾说话,也未伸手拿。
尚睿也保持着那个姿势没有动。
尚睿看着太后:“母亲可知徐敬业伙同朝中同党贪污一事?” 徐太后摆了摆手:“他之前和哀家说过。
有些同僚同乡总抹不开情面,就是这样的小事,王机和御史台却总要找他麻烦。
” 尚睿冷笑道:“小事?”他将圣旨放下,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子,“这是朕收到的之前梁马渡贪污案三司会审后的上疏。
” “结果如何?” “梁马渡招供,徐敬业才是幕后主事,徐敬业一党和朝中官员勾结,不但买卖官职,甚至倒卖军中军粮,单是梁马渡一系人所认罪画押的涉案粮款粗略统计已达三百五十万石。
”尚睿目若寒潭,“三百五十万石——母亲自然知道自儿子登基以来,全国每年所征秋粮也不过四百万石。
” 徐太后惊道:“你所说是真?” 尚睿答:“儿子所言句句属实。
母亲若不信,可前往大理寺亲审。
徐敬业一党之所为,件件皆是要亡我尉家天下,其心可诛。
”他说话的语气不疾不缓,却如锤錾在心。
徐太后的手指用力地搅着手中的丝帕,几乎将它绕破:“可是,他是哀家的亲哥哥,徐家百年基业系于他一身,等哀家死后有何颜面去见徐家的列祖列宗。
” 尚睿垂眸道:“假使在儿子和徐氏之中只能选一个,母亲会选谁?母亲有没有想过,待日后銮舆西归之时,母亲的神位应供于尉家,还是徐家?何况儿子此刻并未要母亲舍弃徐氏一门,仅要徐敬业一人而已。
” 徐太后眼眸微动,却紧闭着嘴。
两个人一跪一坐,均未再言。
他虽跪着,但是身体却直得像棵青松,而太后的心反而越来越颤。
一炷香之后,太后才悲恸地叹道:“何至于此啊,睿儿。
” 喊完他的小名,太后泪水潸然。
尚睿直直地跪在地上:“古人云,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
徐敬业如此贪财揽权,目无王法,欺上瞒下,不死难以服天下道义。
” 言罢,他将刚才的折子放在圣旨旁边,朝着太后沉沉一叩首,直起背缓缓又说:“母亲,天下只能姓一家,而帝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 太后听闻此言,知他已心若磐石,心中无比悲痛,双眼一闭,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良久才走到尚睿身前,蹲身颤抖着伸手拿起那份圣旨,双手展开,来回看了很多遍。
“可是他如今在尉尚仁的狱中,生死也由不得他自己做主。
” “此事母亲可以放心。
”尚睿说。
“子章那边……” “待洪武的援军一到,司马霖和洪武二者久经沙场,双管齐下,自然会有办法,再加母亲修书一封,子章定不生疑。
而徐承致已然是朕的人。
” 徐太后将圣旨递还给他,喃喃说道:“你有万全之策,那是再好不过。
只是子章和阳儿,何其无辜。
” “只要他们对得住儿子,儿子绝不株连。
” 徐太后虚弱地点点头,缓慢地走到殿门口将门打开,唤人进来,又转身折回将尚睿扶了起来。
明连也跟着人进了殿。
太后看到尚睿身上的污渍,对明连说:“去取衣裳先给你们皇上换了再走。
”说完就径直进了内室,再没出现。
那日,阳光十分浓烈,尚睿从太后的承福宫走了出来,脚下的影子被拉成细长,他垂头看了半晌后,负手离去。
五 尚睿再一次到李季府的时候,夏月和荷香正在园子里逗狗。
夏月看见他,愣了愣。
荷香则只身挡在夏月的面前。
夏月说:“荷香,你抱着阿墨回房,我有话要跟洪公子说。
” 尚睿阻止道:“不用了。
我和你出去一趟。
”看得出来心情不太好。
夏月戒备地看着他。
尚睿苦笑:“吃不了你,带你去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回来。
有话路上说。
” 夏月看了看荷香,又转脸看了一下尚睿,点头道:“你等我一下。
”转身回到房里换了身衣服,当时姚创带着荷香来寻她的时候没有带什么首饰,此刻她的一身打扮也是极其简单,但是她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从枕头下取走了那根琳琅坊的簪子,但并没有戴在发间,而是贴在胸前藏着,才随他离开。
马车出了城。
尚睿和她并坐着,中间隔了张小几子。
夏月目不斜视,也没有问他要去何地,左手时不时地去摸一下藏在胸前的那根簪子。
“李季说你的手也好了?”尚睿问。
“嗯。
” “你不问我为何会知道你是喻昭阳?” “你想说自然会说。
”夏月头也不转地回道。
尚睿轻轻一笑,倒是也不继续问了。
马车到了城外一个马场,尚睿掀帘下车:“一会儿有山路,我骑马带你?” 他那嘴角挂着的笑让夏月想起上回马上的难堪,于是毅然拒绝道:“不用。
” 尚睿倒是没有意外,叫人给她找了一匹马。
不一会儿,旁人就牵来一匹枣红色的马,全身皮毛又亮又油,像缎子一般,夏月忍不住上前摸了一摸。
那马儿虽然健硕高大,性格却纯良温顺,一点也不抗拒她。
她出门前,不知道尚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想着换一身窄袖的衣衫,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见机行事,没想到正好派上了用场。
“走吧。
”他翻身上马,回身看她。
夏月没话说,接过旁人递来的斗篷,披着系好后,自己踩着脚蹬也跨上马背。
两匹马一前一后往东走了一截官道。
夏月跟着他,翻了几个小山丘后,地势平坦起来。
尚睿的马一直走在她前面,不近不远,刚好隔了一丈,有时她慢一点,他便会慢下来,她若是快,他也会快。
他始终没说话,也没说要去哪里,连头也没有回。
夏月有些不服气,想要追上他,问个究竟。
没想到,她一夹马肚,他也驾着马跑了起来。
她素来没什么耐性,直接朝他喊了一声:“喂——” 尚睿闻声回头。
“这是要去哪儿?”她问。
“你方才不是说你不想问我,我想说时自然会说吗?”尚睿斜睨她,“我现在不想说。
” “你!”她有些恼。
她生气的时候,脸颊会红,然后嘴笨得半晌挤不出一个字来。
尚睿眼睛一弯,笑容从嘴角漾开,忽然之间,仿佛春风随之而生,萦绕在他身侧。
他看着她,忽然问道:“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 夏月闻言傻傻一愣,她虽说不拘小节,但毕竟是个未出阁的大姑娘,平素里除了家里人,连男子也很少接触,哪会想到有人会将这样的话,当着自己的面就脱口而出,顿时呆住了。
“我就喜欢你对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说完,他朗声笑了起来,扬鞭策马。
夏月的脸霎时从红转白,几乎想追上去将他一把拉下马来揍一顿。
只见他前行了一截路后又拉住缰绳,折返到她身旁说:“听说你小的时候你父亲专门请过北疆的师傅教你骑马,不过我看你骑术也不怎么样,要不要比试比试?” “你认识我爹?”夏月诧异地看着他。
“想知道?”尚睿扬眉反问。
夏月坐在马背上,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若骑马赢了我就告诉你,可是……”他歪了歪头,嘴角泛开一丝玩味的笑,“你若是输了,就让我亲一口。
如何?” 他话音未落,她一怒便扬起手上的马鞭朝他甩过去,没想到他机灵极了,身手又快,人和马往前一蹿便躲开了。
她气红了脸,策马上前想要追上去,将他从马上踢下去。
哪知他带着马一跃,又蹿得更远,还扬扬得意地回头道:“要不要我让你先行二十丈再比?” “我为何要跟你比!”她气极。
“你不敢?”他激她。
“谁说我不敢!” 他手挽着马鞭,指着前方说:“朝北走十里地的尾闾海边有块黑壁崖,谁先到就是谁胜?”语罢又斜睨着她道,“你要是不敢,就循着来路自己先回去。
” “比就比。
”夏月恨得牙痒痒地说,“朝北走十里,海边黑壁崖,我去过,不用你指路。
”说完,不等他发话,夏月便策马绝尘而去。
尚睿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嘴角挂着笑,也缓缓地跟了上去。
这十里地,是帝京到尾闾海最宽阔平坦的一段路,朝北的黑壁崖极少有人去,草地中的曲折小径又难以辨认,于是马儿在路上撒欢跑着。
她很久没有骑过这么快了,只听见风在耳边呼啸。
好在马儿十分温纯听话,刚开始她还有些紧张,后来渐渐和这匹枣红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手脚也放松了起来,全身都伸展开了。
春寒料峭。
策马奔驰中,风吹落了斗篷的帽子,她也无暇顾忌,任由那带着寒意的风吹割着双颊,却不觉得痛。
眼见两侧的小树林,飞速地消失在自己的身后。
她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这么畅快过了,仿佛那些郁结于心的情绪都在此刻消散,她甚至都忘记了身后的那个人,直到一直奔驰到黑壁崖的山脚下,她勒马回身,才看到一直跟着她的尚睿。
她喘着气,因为跑得太快,脸颊被吹得通红,一双眼珠子湿漉漉的,像极了东苑猎场里那些多次从他弓下逃生的小鹿。
她扬起下巴,按捺不住心中的得意,对他宣布道:“你输了。
” 他不以为意,翻身下马。
方才她实在跑得有些快,却不是他追不上她,而是突然有些担心,于是不敢放肆地跑,只好紧紧跟着,就怕她一个不小心摔下来,连眼睛也不敢眨,没想到就抱着这个念想,居然忘了之前为了捉弄她的挑衅。
“下来吧,后面的路是骑不上去了。
”他说。
夏月放开缰绳,跳下马来。
于是,两个人将马系在山下,并肩朝上走。
黑壁崖是一块巨大的崖石,耸立在海边,因为近乎黑色而得名。
它一面是缓坡,临海那面则是峭壁。
前人在缓坡上凿了上顶的台阶,但是经历多年的风吹日晒,许多地方已经难以下脚。
刚开始,两个人还能并肩而行,渐渐地夏月落在了后面。
顶上一段陡坡,三尺高的岩石,尚睿轻轻一跃而上,而后又回头伸手拉夏月。
她借着他的力,终于爬到了坡顶,眼前顿时豁然开朗。
黑壁崖这边明明是朗朗晴空,可是远处海的那一边却是乌云压顶。
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吹得头发四处飞散。
夏月这才发现头上唯一一根绾发的发簪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她索性抬起手臂,拆掉了头发重新草草地绾了一下。
风开始变急了。
岩下的海浪越来越高。
远方海那一边的乌云似乎都要沉到海里去了。
忽然,天边的乌云沉了一下,并未看见闪电,但雷声已经从远处缓缓滚过来,沉沉闷闷。
“这是今年的第一声雷。
”站在旁边的尚睿喃喃自语道。
她闻声转头看他。
他在岩石上负手而立。
那海风不停地吹,除了被掀起的衣角,他整个人纹丝不动,站得又直又稳,跟她被吹得东躲西藏、头发四散的狼狈相完全不同。
一袭素衣,却宛若日月。
他迎着风,身姿挺拔豪气,静静地注视着那团乌云,似乎旁边一切都和他无关,全然置身于这俗世之外。
而后,海上好像是下雨了,渐渐起了雨雾。
海浪汹涌。
而他们站的这边海岸依旧是晴天朗日。
这样的景致,忽而让人觉得世间万物都变得渺小起来。
过了许久,他才转过头对她说:“我头一回看见海上这样下雨。
” 夏月终于看清楚他的眼睛,那黑亮的眸中还残留着一股孩子气般的新奇。
“我也是。
”她说。
就是说这些话的时间,头顶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然后那些雨水迅速朝岸边移了过来。
雨雾如飞一般地扩散着。
忽地,就变了天。
夏月一仰头,已经能够感到有零星的雨点落在了自己的脸上。
雨势来得如此汹涌,让人措手不及。
他们站在光秃秃的山崖上,连棵树都没有,完全找不到可临时避雨的地方。
正在夏月犯愁的时候,尚睿说道:“这边有条路,跟我走。
”不等她回答,他就拉着她往一侧走去。
原来膝盖高的一堆野草丛,走进拨开后现出一条通往峭壁下方的小径。
夏月紧跟着他。
小路的石阶依靠着石壁,迂回盘旋着往下。
没走几步,就见路边有个石洞。
与其说是石洞,不如说是石壁凹进去两尺宽的一个地方,刚刚有一人高,站进去,身体刚好被头上的岩石遮住。
豆大的雨滴,猛然落了下来。
却不想,海风实在太大了,虽然能遮住身体,那倾盆的雨又被迎面灌入的风送到石壁下,山洞太浅,根本挡不住。
只见他没有迟疑,迅速地解开外衫脱下来,背对着外面,用手支在洞壁的顶端。
转瞬之间,他和他的外衣便成了一道温暖的屏障,挡住了那些风雨。
她的背紧紧贴着身后的岩石,而身前,隔得很近的地方,是他的胸膛。
他们俩离得很近。
一时之间,她不知道该朝哪里瞧,只好偏着头,垂眼看别处。
她能感到他的鼻息落在她的额头。
一下,两下,三下…… 舒缓,且沉静。
忽地,有一滴水滴到她的眼睑上,她伸出手去抹,然后下意识地抬头。
她仰脸抬眼,看见他的脸。
些许雨水沿着衣服和岩石的缝隙中滴了下来,正巧这时有一滴落到他的额头中央,然后那滴水,一路向下,从眉间滑过。
他两只手撑着自己的外衣,腾不出手来擦掉它。
只见那滴雨水流至他的鼻尖,才止住继续的势头。
何曾想,第二滴雨又在同一个地方往下流,再和之前的雨水一并重叠在他的鼻尖,顿了一顿,最后还是滴了下来。
又落在她的脸上。
他浑然未觉,目光一直看着别处。
眼见,雨水又从别的地方渗下,接连落在他的睫毛上,她再也忍不住,伸手替他抹了抹鼻尖上的水滴。
对于突如其来的触碰,他先怔了怔,随后开口说:“刚才的赌约,你还认吗?” “当然认了,我赢了。
” 尚睿扬眉,明显不赞同。
“谁先到黑壁崖谁就赢,我先到。
”她据理力争。
“我明明记得是我先到。
”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头顶。
夏月这才发现,他指的是他先上山顶,所以要算他赢。
她刚要急着和他争辩,忽地想起他就是故意要捉弄她。
于是她憋了口气,拧着眉,再也不和他搭话。
他眼角含着笑意,垂头看着她一双眼睛如梅花鹿一般晶莹透亮,此刻不服气的心情全写在脸上,觉得她真是有趣。
他再次失笑。
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一会儿,就停了。
骤雨过后,阳光又倾泻而下。
尚睿将半湿的外衣拧了拧又穿在了身上。
他们沿着小径蜿蜒而下。
因为海边潮湿,又被草丛覆盖住,石阶有些地方长了青苔,所以走得格外小心。
悬崖底下是一片滩涂,因左右都是海水,又有石壁阻挡,滩涂外就是海。
别处的海岸是沙滩,而这里却全是黑色的礁石。
她刚准备朝海边走去,却不想尚睿拉住她的胳膊,轻轻说了一句:“你回头看看。
” 她狐疑中照做。
转身抬眼的刹那间,她呼吸一滞,愣在了原地。
所有人都爱站在黑壁崖上眺望尾闾海,将海岸线尽收眼底,何曾想过站在崖下回望黑壁崖却是这样的风景。
那黑色的崖壁上布满了一种叫紫重葛的爬藤。
这是京畿野地里常见的植物,却不想它们会如此茂盛地长在这海边的崖壁上,而在这个时节,正是它的花期,满满一块崖壁的紫重葛得了春风,竟然全都盛开了,将半个黑壁崖包裹成了紫色,像一块巨幅的花屏,既壮观又美。
海风袭来,紫重葛随着风势摇曳。
落英缤纷,从半空而来。
她这才看到脚下居然也铺了一层紫色的落花,她刚才因为看海心切,全然未曾注意,现下竟然不敢下脚。
“真美。
”她轻声惊叹,“你是如何发现的?” 黑壁崖的这面朝海的悬崖是上凸下凹,站在悬崖上完全看不到下面还有这样的景致,而且这块石滩两侧都被海水封住,仅有刚才那条不起眼的小径才能到这里,若不是有心,根本不会发现。
“我幼时有一次随父亲坐船出海,回程的时候看见。
那时是初夏,虽然紫重葛的花只剩下一半,但是在海上看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想,这里怎么能叫黑壁崖呢,明明是紫重葛的花墙。
”他喃喃地解释着,脸上的神情似乎也被这一片紫色吞并了。
“海上看着更美吗?”她好奇。
“一样美。
”他嘴角含笑,眼眸中似乎融着春阳。
说话间,海水涨潮了。
海水漫延上了滩涂,已经淹没了一些紫重葛的花瓣,将它们卷入水中。
幸而,她早早跟着他站在了高处的礁石上。
骤雨后的海岸仍然不太平静,海水由远及近起起伏伏,最后狠狠地拍打在礁石上,顷刻碎成雪白的碎屑,再迅速消散。
忽高忽低,如此反复。
夏月看得有些出神。
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听着奔腾激昂的惊涛声,久未说话。
尚睿站在她的身后。
一个巨浪拍过来,激起一人高的银白浪花,朝她脚上扑来。
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没想后背撞在尚睿的身上。
他伸手去牵她的手。
她一惊,手指被他碰到的时候,仿佛被烙铁烫了一般,猛地抽了回来。
一番接触,她用余光又开始打量他。
这个男子,他竟然能叫出她的真名,还能让李季给她治病。
更何况,他明明姓洪,却又长了一副尉家人的好面皮,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据说开国的太祖皇帝,也是个鼎鼎有名的美男子。
而自大卫开朝以来,好几代都是择美入后宫,所以尉家人的五官底子越来越好。
她未见过先储,也未见过其他皇室宗亲,却有一年元日随着父亲远远瞧过先帝的龙颜,知天命的年纪却温文沉宁,风姿犹存。
再想想子瑾。
她和子瑾从小一同吃喝,彼此熟稔得跟左右手一般,她自然习惯了他的容貌,也不以为意。
突然,她想起那一夜王淦几人亵渎子瑾的话,面色霎时就白了,胸中顿时痛得似乎要滴出血来。
若是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神明的金丝雀Sonata
- 我做偏执大佬未婚妻的日子白秋练
- 小李飞刀3:九月鹰飞(上下)古龙
- 和暴君一起的日子陈十年
- 总裁她总是哭唧唧李秋琅
- 暴君每晚梦我五月锦
- 嫁给冷血男主后我变欧了[穿书]/嫁给杀器后我变欧了[穿书]蒸汽桃
- 同萌会的一己之见楚凤华
- 重度痴迷多梨
- 箫声咽鬼马星
- 纸片人老公成真了枝景
- 尘埃之花采葑采菲
- 被献祭后和恶龙在一起了[重生]不渡星河
- 热搜女王育儿手记/每天都会上热搜!宋家小四
- 横滨芳心欺诈师闲豆花
- [聊斋]活人不医南陶
- 我独自美丽一丛音
- 蝼蚁你爸爸
- 至尊剑皇半步沧桑
- 彩虹星球南书百城
- 喜欢你的每一秒鹿灵
- 盈盈ABO嗜酒吃茶
- 炮灰的马甲又又又掉了冰糖火锅
- 玉昭词(今夕何夕原著小说)时久
- 我家别墅能穿越传山
- 大唐逆子:开局打断青雀的腿!明月还是那个明月
- 秦世风云录饺子面条火锅
- 修仙家族:我的灵肥引情劫幽冥人
- 我靠血条碾压修真界暮寒公子
- 学渣的传奇人生迎凤村草
- 锦衣卫:陛下,何故谋反!叁金诶
- 边军凶猛赤阳
- 我的美艳师姐妹燕山夜话
- 穿越宋末,海上发家先滨
- 我的春夏秋冬:人生全记高山流水兮
- 刺世天罡夜阑听雪落
- 道果战袍染血
- 极品仙途闻人毒笑
- 超级聚魂幡星际黑伯爵
- 宇宙本源诀冰冷眼泪
- 横行霸道踏雪真人
- 苦闯仙侠界云隐青山
- 在成为西门吹雪的日子里笑点烟波
- 古代打工日志:从退婚开始躺赢西猫西
- 权倾朝野,女帝求我别反准备起飞
- 综武:最强说书人,开局曝光金榜世间万般皆是苦
- 地府通行证风化羽
- 重生归来之神帝薛九玄清方观世
- 炎拳天剑冰灵莲
- 苍穹战神跳神3
- 异界纵横之我在江湖搞发明锅包肉没有锅
- 抱歉了小师弟,伤害男人的事我做不到!由山自海
- 明末造反:我的盲盒能开神装七辛海棠
- 小宝寻亲记姜妙姜妙肖彻
- 玄德公,你的仁义能防弹吗?爱吃鱼2021
- 星极宇宙社恐的中年人
- 大明:我崇祯,左手枪右手炮二月十八
- 剑影书迷之宝藏寻踪喜欢半减七和弦的子豪
- 综武:我,曹老板,挖墙角达人不弃九一
- 边军凶猛赤阳
- 穿越大唐,我靠变身闯天下美溪旺仔
- 穿越宋末,海上发家先滨
- 轉生成豬的我,突破只能靠雙修爱鯊客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
- 炎拳天剑冰灵莲
- 古代打工日志:从退婚开始躺赢西猫西
- 洪荒之鲲鹏绝不让位李九郎
- 九道真仙扫地的研究僧
- 横行霸道踏雪真人
- 仙帝铁马金戈
- 洪荒青莲圣卷怕老婆
- 丹武大帝关东大侠
- 星河玄幻剑圣作者火心
- 战傲穹苍半世浮生
- 最强反套路系统太上布衣
- 温阮霍寒年温阮霍寒年
- 我让高阳扶墙,高阳为我痴狂抱星明月居
- 北军悍卒虎虎
- 逆世灵霄纪书写杨意
- 一梦江湖之宸霜玄龙锁逍遥九宸天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带着基地闯三国安安静静看书书
- 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苍梧栖凰
- 剑影书迷之宝藏寻踪喜欢半减七和弦的子豪
- 杀敌就变强,我靠杀戮成就绝世杀神临水乔木
- 开局力挺宁中则,李青萝求放过粤北陈老师
- 穿越大秦:红颜助国兴还钱100
- 原始蛮荒部落生存记景斯年
- 综武:我,曹老板,挖墙角达人不弃九一
- 我靠血条碾压修真界暮寒公子
- 锦衣卫:陛下,何故谋反!叁金诶
- 东汉末年:我携百科平天下特特eve
- 混沌再临之灭仔纳里
- 刺世天罡夜阑听雪落
- 七情碗夜凰
- 穿越宋青书创最强大明形寄青峦
- 苦闯仙侠界云隐青山
- 邪仙偷腥的猫
- 逆天仙尊杜灿
- 我才不想当用剑第一桃子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