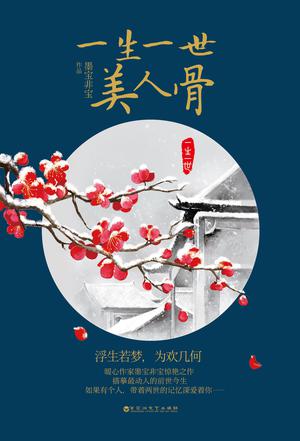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七章 侧有浮云无所寄(1/3)
一 回到药铺,夏月紧蹙眉头,心神不宁,情绪久久难以平静。
她摩挲起手中的玉蝉,暗地里责怪自己太不谨慎。
如今这玉蝉是再也不能随身带着了。
她找来一块帕子将玉蝉裹起来,然后放在妆台的首饰盒子里,随即又觉太蠢,踌躇半晌爬上桌,又垫了条凳子,踮起脚尖将东西搁在房梁上。
刚一下桌,门没敲便被人推开了。
“哎哟——我们家大小姐。
您这是要上房呢,还是要悬梁呢?”舅妈裴氏脆声问。
“舅妈。
”夏月有些不好意思地跳下凳子,“我捉个虫子。
” “你这要是让外人看见,还以为我这做舅妈的拿什么气给你受,逼得你要悬梁上吊呢。
” “儿媳妇啊,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夏月的姥姥听见动静,跟了进来。
“我怎么了?老太太,您老说话也要摸摸良心。
您儿子为了挣钱,去了南疆走货,小半年才挣那么点钱,如今生意这么难,指不准我们的好日子还能过几天。
就我一个妇道人家在铺子里忙里忙外的。
如今家里无缘无故多了个千金大小姐,难道还要我拜着供着不成?” “好了,好了。
少说两句。
”老太太劝说,“外面刘老爷家的伙计来了,等着我叫你出去。
” 舅妈点点头,走时扔了个小瓶子在桌上:“听说你今天从外面回来咳嗽得厉害,我在穆远之那里给你拿了个治风寒的丸子,你吃来试试。
” 夏月一笑:“谢谢舅妈。
” 裴氏有些挂不住脸地说:“谢什么谢,我害怕你这做惯了娇贵小姐的,万一有个不妥,你舅舅回来还不跟我拼命。
”语罢,便匆匆离开。
夏月和老太太相视一笑。
“其实你舅妈这人,嘴巴不饶人但是心眼不坏。
”老太太转而又问,“这几个月你跟远之学医,怎么样?” 穆远之是医馆里请的坐诊大夫,他脾气平和,待人和善,所以店里的人都喜欢他。
夏月笑:“反正我平时也闲得慌,没别的事可做,就算学不好他也不会生气。
” 夜里,伴着窗外潇潇冷风,她梦见了子瑾。
梦里他站在腊梅树下,可惜,却一直看不到他的脸。
他一直都不是个善于徘徊于尘世的人,所以,他在淮王那里肯定不会如意吧。
清晨,刚过卯时,夏月和店铺里的伙计一开门便见一位中年男子早已经候在门口。
此人便是穆远之。
“先生今天这么早。
”荷香欢喜地说。
夏月也点点头:“先生早。
” 穆远之刚刚坐稳,沏好的茶还没来得及入口,夏月便抱着书来问。
“先生,早些日子学生读到《金匮要略》里说黄痨病可开方,以青蒿为主,配以栀子、大黄遣药数剂。
可我又听赵大夫说他用此剂数月,病人不见好转。
是药剂有误还是用法不当?” “闵姑娘的看法呢?”穆远之问。
夏月没有立刻回答,若有所思地说:“《金匮要略》里一贯称青蒿,却独独在提到黄痨病时用‘茵陈’一词。
虽然世人都晓得青蒿是官话,茵陈是民间称谓,但是用在此处却很奇怪。
我后来问伍大爷,他说在他们南域家乡,‘茵陈’一词有时候特指的是三、四月的春季刚刚发芽的青蒿。
” 穆远之颇为赞赏地微微一笑:“不错,此处的青蒿应用三月鲜嫩的青蒿晒干入药。
只是黄痨病在帝京北地不多发,故而很多大夫偶有误用。
其实青蒿、木香等药虽然物尽相同,但若是摘采时日不当,则效用全无。
” “哦。
”夏月点点头,蹙眉又问,“学生还有一问。
有病症面赤心烦,甚则烦躁,厥逆,口燥舌赤,脉数身热,是否是虫积有蛔?” “是否食则腹痛,不欲饮食?”穆远之呷了口茶。
“对。
” “那就是了。
应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
” 夏月迅速提笔记下。
此刻,有个老妇人抱着个小孩进了店来。
“穆大夫,你给我孙女看看。
” 那女孩大概只有两三岁,大概因为发烧的缘故,一脸通红。
她先是闻到铺子里的药味,警惕地从怀里探出头看。
环顾四周,看到那装药的柜子,嘴巴一撇就哭了:“奶奶,奶奶,梅儿不瞧病!梅儿不瞧病!” “好,好,好。
不瞧病。
”老妇人一边答应一边捋起孙女的袖子让大夫诊脉。
孩子警觉地尖叫起来,在祖母怀里拼命挣扎,那叫喊简直刺耳。
夏月瞅了瞅那孩子,如今莫说给她把脉,就是让她安静下来也麻烦。
老妇人不好意思地向穆远之求助:“大夫,你看这……” 若是换作以前的赵大夫怕是早就吹胡子瞪眼,一脸不悦。
但穆远之只是微微一笑,说:“大娘,不碍事,我来看看。
” 只见穆远之打开诊箱,从里面拿了个鸡蛋出来。
夏月小声对荷香说:“先生今早又是吃鸡蛋?” “有福气。
”荷香吐了吐舌头。
那穆远之孤身一人在帝京行医,家中既无女眷,也请不起丫鬟和小厮,又对锅碗瓢盆之类的事情完全不懂。
虽说一日三餐都可以在外面凑合了事,但是随着天亮得越来越迟,这早饭却也难办。
后来夏月灵机一动,教他煮白水蛋。
“梅儿,看叔叔这里。
” 女孩抬头看了那鸡蛋一眼,好像并不太受诱惑,又是一瘪嘴继续哭。
想来她身体不适,对什么吃的都没有兴趣。
穆远之也不意外:“梅儿不哭,叔叔变戏法给你看。
”说着取了桌上的笔,在蛋壳上画了几笔。
女孩果真被他吸引过去,停止了抽泣,歪着头好奇地看着穆远之手中的东西。
只见那光滑的蛋壳上被穆远之两下三笔就勾勒出一个年画上的胖娃娃。
穆远之放在嘴边将墨迹吹干,递到女孩面前。
女孩不禁伸手去拿。
穆远之却缩回来,一副谈判的表情问:“那梅儿让叔叔抱抱,好不好?” 女孩使劲点头,张开双臂就让穆远之抱。
于是,那个被变过戏法的鸡蛋被孩子捧在手里,孩子又被穆远之抱在怀里。
荷香看了穆远之一眼,接过东西就出了门。
穆远之趁着孩子的注意力在他物上,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脉和额头,然后翻开孩子的领子,前胸后背全是脓疮。
“何时开始发疮的?”穆远之问。
“我们也不知道,她早些时候爹娘回老家了。
我后来见孩子老是挠痒痒才发现。
” “那何时开始发烧呢?”他继续问。
“昨天半夜。
” “吃饭可正常?”他又问。
“两顿没吃下东西了。
” “是吃不下,还是吃了就吐?”他再问。
“吃的都吐了。
” “孩子怕光吗?” “这个我们……没注意。
” 老妇人被他一连串的问题,越问越心慌:“大夫,孩子的病没什么吧?” 穆远之没有立即答话,过了一会儿才说:“大娘,孩子无大碍,只是生了黄疮。
” “我要带孩子进内堂施针。
”穆远之扭头对旁边的伙计说,“小伍,你帮个手。
” 小伍应着,就准备放下手中的活,一起进去。
“先生,我帮你吧。
”夏月说。
穆远之沉吟:“闵姑娘,这……” 夏月侧头有些疑惑,她不是第一次随穆远之施针,不知他为何迟疑。
“我不会捣乱的,况且小伍也正忙。
”她笑。
穆远之也只好随了她。
内室里,为了避免孩子乱动,夏月只好抱着她坐在躺椅上。
穆远之取来银针:“我们要把所有疮挑破上药,这个过程很痛苦。
所以需先施针封住血海穴、太渊穴、尺泽穴三处穴位,止住她的痛觉。
” 随即他又开了张方子给小伍:“上面这几味药,你尽快碾碎了将酱汁端过来。
” “先生不用麻沸散?”夏月有些吃惊。
“是药三分毒,麻沸散对几岁的孩子来说药性太强,若是分量不当会影响他们日后的五感。
” “叔叔要扎针?”女孩儿有些惧怕地看着穆远之摆在桌子上那些长长短短的银针。
“梅儿,叔叔只扎三下,扎了病才能好。
”穆远之温和地说。
“痛不痛?” “就像被蚊子叮了两下。
” 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闭上眼,比方才勇敢了许多。
夏月说:“先生对付孩子真有耐性。
” “孩子一般在陌生人跟前比较坚强,所以我才让她祖母留在外面。
” 穆远之施针之前问:“闵姑娘可会取这三个穴位的位置?” “血海穴位于大腿内侧,从膝盖骨内侧的上角,上面约三指宽筋肉的沟,一按就感觉到痛的地方,病者屈膝时可取。
“太渊穴位于手腕部位,手腕横纹上,拇指根部侧。
”夏月在嘴里说,穆远之随之取穴落针。
“尺泽穴位于胸前,在俞府穴正下方,下一肋间隙中。
” “那俞府穴又如何取?”穆远之问。
“上前胸,病者正面中线左右三指宽,锁骨正下方。
”夏月答。
三针扎好以后,穆远之又取一针,在一发亮的疹子上看准尖端轻轻一挑,黄色的脓汁便缓缓流出。
他左手的白帕子将其接住。
停顿了稍许,又挑了第二下,在确定脓汁已经清理干净以后,才接过小伍送来的酱汁涂在伤口上。
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足足花了半个多时辰才完事。
孩子早已坚持不住,哭了又闹闹了又哭,好歹被夏月紧紧制住,并且在四肢都无法动弹的情况下,还转过头去狠狠咬了她一口。
老妇人被唤进来抱孩子。
“大概哭累了。
”夏月将不一会儿就熟睡的孩子交给她。
穆远之说:“大娘,我将方子交给伙计了。
你去取药,两日后来复诊,切记不能碰水,不能受风,不要和外人接触。
” 老妇人谢了又谢,才出去。
夏月起身帮穆远之收拾器具,一脸苍白。
“咬疼你了?”穆远之问。
“小孩子力气还蛮大的,只是有些累。
”夏月擦汗道。
“昨日的丸子你可有按时吃?”穆远之突然问。
“啊?”原来那药丸是穆远之开的,夏月笑说,“吃过已经大好,先生医术堪称国手,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 穆远之看了看夏月,这次却没有笑,眼神有些探究。
素日里穆远之教她医术,虽然他年轻尚轻,却也异常受夏月尊敬。
不过,夏月从小就是一个逗趣的个性,偶尔说说笑,穆远之也由着她。
这次却不同。
夏月顿觉不妥。
“先生,是那孩子的病有何异常?”她刚才就有些疑惑。
“怎么个异常法?”穆远之在盆内净手,问道。
“因为学生有三点不明。
先生刚才说是黄疮,可是染上黄疮后患者并不会发烧,为其一;其二,她的脓水挑出来以后黄中带血;其三,小伍做的药汁里有贝晗和蔓梓,学生还未见过用这两味药治黄疮的。
” “闵姑娘心细,那确实不是黄疮。
这种病我也不确定,症状有些像黑殷痧。
” “黑殷痧?” 穆远之说:“这是前几年西域一带流行的一种病,很容易传染,而且多发在几岁孩子的身上,一旦病重极难医治,所以……” “所以方才先生才让我避让?”夏月说,“我身体好着呢,风寒也好多了,也不是孩子,没这么容易染上。
况且我跟先生学了多日了,好歹也算个学医之人,不该怕这些。
” 说这些话时,夏月神情坦然,并无畏惧后怕之态。
穆远之眼眸一闪。
他的五官眉目无特别过人之处,独独那双眼睛好似两团墨迹。
“先生可是有话要讲?” 穆远之迟疑道:“其实,姑娘不必这般自苦。
” 夏月愣了稍许,继而缓缓说:“我虽是女子,也想要有自立的一天。
” 穆远之看了看夏月,平复下去道:“明日是我考《金匮要略》的日子,姑娘莫要忘了。
” “先生为何不向那位大娘将病情直言?”夏月也接过话题,岔开方才的凝重。
“那孩子患病不久,如今已无大碍,若是言明,反而让亲属恐慌。
”言罢,两个人掀帘出了内室。
二 过了几日,老太太又拿出私房钱,敦促夏月带着荷香去做冬日的新衣。
夏月笑道:“我有钱。
” 虽说闵老爷一世清廉,却还有些家当。
本来除了宅子,大部分东西在他过世前全都变卖了,也不过是为子瑾存个念想,只道是有用得着的地方。
可是,子瑾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拿。
他从不和她谈这些事情。
下午在老太太的督促下,夏月和荷香出门上了街。
成衣店的老板娘刚帮夏月量完尺寸,便有个梳着垂髫的孩子掀帘跑了进来,吓了荷香一跳。
“去,去,去。
子瑾干什么呢,娘在跟客人做事。
”老板娘撵着儿子。
夏月一听他的名字便笑了,蹲下去逗那孩子:“呀,你也叫子瑾呀?”因为高辛宝玉的原因,子瑾二字成了很多人家常见的男孩名。
孩子点点头。
夏月眯眼笑道:“我弟弟也叫子瑾。
” 孩子似乎经常和客人打交道,一点也不认生,偏着头就说:“那你下次来的时候,带着他和我一起玩弹弓。
” 夏月莞尔:“那可不行,他已经是大孩子了。
” 从绣坊一出来,便看到斜对面那个金灿灿的“琳琅坊”的招牌。
这店是帝京有名的首饰店。
它怪就怪在从不做宝石玉器,单单只打金饰。
那金灿灿、黄澄澄的金子,从他家作坊师傅的手下一出来,便脱了一身俗气,不知怎的就雅致不凡了起来。
连锦洛的闺阁小姐们也为能有一件琳琅坊的首饰而自喜。
她小时候在帝京的时候,娘就在这里请人给她打了一副金锁。
后来不小心弄丢了,她还哭了好些天鼻子,直到后来爹又在锦洛新做了一副才了事。
想着这些往事,她嘴角挂起淡笑穿过街,忍不住朝那铺子走去。
那店伙计一见两个人进门就热情地招呼着,将一些寻常小姐们爱用的首饰各挑了几件摆出来,随后既看茶又设座的。
夏月本来就是进来随便看看,可是人家伙计如此盛情,倒也不好走了,只得硬着头皮坐下来。
桌子上摆着几个翻开的盒子,里面耳珰、金镯、步摇……琳琅满目。
她也是一个爱美的姑娘家,手指一一抚过去,华光耀眼,一点都不动心那是假话。
可是,她又哪有这番心思。
伙计见她要走,急忙又说:“小姐要是都不如意,正巧今天还有一批新样式。
”说着便又拿了几个锦盒子,打开给夏月看。
其中一件是一只簪子,一头是用金片打制而成的团花。
在一个葵花状的花蕊四周,分别有八个独立的花瓣,每瓣中都凹进一层。
突出的地方分别用金丝做成网纹,花瓣之后,又以八片花瓣衬托。
晃眼一看,就似一朵盛开的山菊,十分清新雅致。
夏月的目光迟迟没有挪开,忍不住伸手将它拿起来。
店里伙计是何等精明的人,把买家的脸色看在心里,立刻就叫人举着铜镜来给夏月试,同时将簪子以及夏月的眼光和容貌均捧了个天花乱坠。
夏月抬眼问:“多少钱?” 伙计眼睛眯成一条线,比了个手势:“六十两。
” 荷香心中抽了口冷气,早知道琳琅坊的东西不是凡品,且价格高得离谱,却不想竟是这样贵。
夏月眼眸微垂。
她身上不是没有银两,可是如今父亲留下的那些钱都是留给子瑾日后急用的,怎能由她任性。
夏月勉强地向伙计一笑:“我再看看别的。
”说着,伸手将那金簪从发间尴尬地取下来。
伙计忙拦着她,劝道:“小姐您戴着它,美得跟天仙似的,就要了吧?” 伙计见她继续动作,又道:“而且您可不知,这物件还大有来历,姑娘你可……” 忽然,身后一个声音骤然响起:“什么来历,说来听听。
” 她一转头看到是尚睿,眉头骤然就蹙了起来,越是厌恶的人,越是经常撞见。
伙计想必也只是想用些心思留住夏月,没想到被尚睿这么随口一问,倒愣住了,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答话。
老板却从内堂走了出来,接着伙计的话继续道:“不过是个谣传。
据说啊,太祖皇帝少时还未御极,在乡野间偶遇一女子后以一金簪定情,后来结为发妻。
我们作坊的师傅无意间得到一图,照着那图废了不少工夫才给制出来。
” 尚睿闻言一笑,自然是不信。
店家又道:“这种市井传说不过就是图个吉利。
姑娘自戴也好,这位公子想要赠人定情也罢,都适宜。
” 夏月本没有要掏银子,又见伙计店家如此热络,也不好拂了人家的热情,正愁脱不了身,见尚睿跟一冤大头似的走进来,顿时松了口气,趁机将簪子放回盒子。
那老板是何等善于察言观色之人,立即将盒子转到了尚睿眼前。
可知,她对那发饰也是极心动,忍不住侧目又轻轻瞄了一眼,略有不舍。
尚睿瞧出她的神色,淡淡一笑:“多少银子,我买了。
” 夏月听到这话,便带着荷香从铺子里走了出来。
转过角,横穿正阳街,正巧遇上某位贵胄的仪仗。
路人纷纷回避。
荷香不禁问旁边的摊贩:“这位大人是谁啊?” 那卖水果的小哥小声道:“是徐大人啊。
” 夏月问:“哪位徐大人?” 小哥嘟囔:“你们是外地的吧?当朝能叫徐大人的,还能有几个,魏王徐大人。
”那人便是尚睿的舅舅——徐敬业。
他封为“魏王”,又是君前幸臣,盛宠多年,自然车辇马队好不神气。
夏月和荷香站在人堆中一同观望。
一干人刚行至面前,对面一位银丝老头意外地从两侧的夹道中冲出去,不顾马蹄车轮,扑到开路的仪仗前,哭诉道:“草民有冤,有冤,有冤哪——” “有冤”二字,在老人的口中喊得一次比一次凄凉。
至世宗皇帝晚年,本朝盛世似乎初见端倪,像这般在帝京当众拦下一品大员的官驾还是鲜见的。
徐敬业抬手阻止正要叱骂老人的随行士兵,策马至前,和善地说:“老人家,徐某过往也只是武官一名,你有冤屈应当请人写了状纸交到衙门去,冤案等事徐某也做不了主的。
” 他说话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浑厚,在人多嘴杂的大道上,听起来仍然清晰明了,有种威武气魄。
荷香扯了扯夏月的袖口,低语道:“真有气势。
” 夏月却是一声冷嗤,不过是假仁假义。
老人却仍旧伏地:“草民的心中之事,只有大人才能决断,不然草民死后也无法瞑目。
” “哦?”徐敬业颇为疑惑,翻身下马,“老人家有何事,当着这么多乡亲的面就说吧。
”他颇有耐性地躬身下去扶老人起身,却没想到老人在抬头的一刹那居然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事发突然,周围的侍卫也措手不及。
老人甩开徐敬业虚扶自己的手,猛然退后几步,仰天长笑。
“狗贼!你徐氏一门原本不过是我大卫朝养的狗奴才,承蒙先帝厚爱才封你姐妹赐你荣华,你却暗联内宫害我先帝,此乃不忠;你等矫旨不遵,为一己私欲,另立新帝,此乃不臣;你不顾先帝知遇之恩,反灭了太子一门,毁我大卫嫡氏血脉,此乃不仁;如今你残害先帝子嗣,绞杀魏王,还敢觊觎异姓王位,此乃不义!” 夏月闻言,咬紧下唇,深深地看了那老者一眼,手也不禁捏得紧紧的。
老者所言句句扎在她的心中,也将她激得愤愤不平。
若不是这些人,若不是他们,子瑾如何会家破人亡。
却没想,尚睿不知何时也跟了来,站在她的身侧,一同隐在人群中驻足观看。
老者又道:“你这等不忠、不臣、不仁、不义的乱臣贼子居然官拜一品,世袭封号。
吾等忠君之士,岂能觉得不冤?天下百姓岂能不冤?” 尚睿悠然感慨道:“这老先生勇气可嘉。
” 夏月顾不得他说了什么,只是绷紧了心弦,牢牢地从人堆的缝隙里盯着那边,就怕那老人无辜遭人黑手。
“老夫看你尽早挥剑自刎,以祭先帝在天之灵。
狗贼你杀了我吧。
老夫今日只恨无缚鸡之力,不能手刃你这个……” 老人说到后面几句已经被旁边侍卫拿下了,捂住嘴,他却往死里拉扯,为的就是想把最后这几个字说完,可终究还是被人把嘴堵上了。
徐敬业不愠不恼,平静地举袖擦去脸上的唾沫,踱到老人跟前:“老先生适才漫骂徐某只是小事,却不该辱及我朝天子及太后。
徐某手下的侍卫不过是怕老先生再说出什么不敬之言才多有得罪。
如今徐某只得将你交予廷尉,他们自然会按我朝律法严明处置的。
”语罢,让人绑了老人送去衙门,自己翻身上马继续前进。
人们见没了热闹可看,哄然散去。
夏月看着老人被人推搡的蹒跚脚步,心中陡然升起一番复杂难辨的滋味。
尚睿看着老人远去的身影,摇头道:“年过半百赤胆忠心,可惜做起事情来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愚忠而已。
” 夏月听闻“愚忠”二字,猛然转头看他,忍着情绪道:“人家一个花甲老人,你不必如此刻薄。
” “并非我刻薄。
他们这些人念书多了,做事难免迂腐。
今日赔上一条性命,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罢了。
况且一个读书人连骂人也不见得多狠。
倘若真是有心与人为敌,隐藏了性情,在这鱼龙混杂的帝京干出点事情来,且不是要有用得多。
” 夏月冷嘲热讽道:“也不见世人都能学得公子这般口蜜腹剑的本事。
” 他回道:“可见我自是与世人不同。
” 正巧明连将马牵来,尚睿翻身上去。
夏月这才瞥到他手中还捏着个琳琅坊的檀木盒子,料定他肯定买了那金簪,想起店家方才说什么男子可以买来做定情之物的话,不禁冷笑:“只愿那将情爱真心托付于公子的女子,不会看走眼。
” 尚睿闻言,看了看手中的木盒,再瞥了夏月一眼,想说什么,却最终敛容不语。
他双腿夹了夹马肚,驭马离开,却不想走了几步,又不禁折了回来。
“既然闵姑娘怕别人看走眼,不如我将这玩意儿改赠与你,免得去祸害旁人。
”他高坐马背上,冷淡地垂着眼帘俯视着她,说完便将盒子抛出去,轻轻巧巧、不偏不倚,正好稳稳当当地落在夏月怀里。
夏月下意识地将东西接住。
“赏你了,不必客气。
”语气极其轻慢。
他本来是路过,恰巧知道夏月在首饰铺里,便好奇进去瞧瞧,察觉她对那发饰目光流连,却又不买,索性买了下来。
现下被她激得不怎么痛快,他既拉不下脸,却又忍不住不送她,于是成了这般情况。
可是,最后那句话在夏月听来完全是打发乞丐的口吻,加之他还这么居高临下地扔给她,她心中原本越积越强的怒气终于迸发出来,顺势将怀中的盒子往地上一摔,并且啐了一口,说道:“谁稀罕。
” 只见盒子朝下摔开,里面的东西掉了半截出来。
路边积压的残雪早被刚才看热闹的人群踩得面目全非,那簪子的一头便落在这样的泥泞里,沾了污渍,明晃晃得刺眼。
尚睿此生何曾被人这般拂过脸面,顿时恼了:“捡起来。
” “凭什么?”她毫不示弱,本想仰着头对视他,却觉得他这般居高临下,气势上就胜了她,于是转脸改看了别处。
“我让你捡起来。
”他压制着声音,已是怒极。
“我不!”她也拧上了。
尚睿怒火中烧,他本不应是这样易怒之人,却不知为何接二连三地因她置气。
未待她说出下一句,他便粗暴地抓着她的肩头将她拎了起来,横着扔在鞍前的马背上,随之狠狠地扬起鞭子,策马飞驰。
“公子!”明连和旁边的姚创急忙追了上去。
尚睿眼睛一横,沉着脸喝道:“谁也别跟!” 夏月的脑子一下子蒙了。
她只以为最惨的下场不过是和他打一架或者挨他两巴掌,却不想他竟然这般强行将她掳出城去。
她被马驮着,以一个别扭的姿势俯卧在马背上,极其不雅,而且那马跑得很快,抵着她的胸脯和肚子,颠得她连呼吸都有点困难。
一时间她巴不得自己就这么掉下马去,死了残了也比如此受他轻贱折辱好。
可是下一刻,心里又害怕掉下去,于是不得不抽手去抓紧身侧的马鬃。
尚睿一路策马,黑着脸没吱声。
她咬紧牙关,没让自己冒出一个求饶或是呻吟的字眼。
可是哪怕不会往地上滑,身下的骏马每颠一下,她的背和侧面肋骨便会在马鞍前磕一下,疼得渐渐让她将寒冷也忘了。
城外的风格外大,呼呼一吹,倒是让尚睿的脑子冷静了不少。
他当时一心想教训教训她,又怕她继续让他难堪,现下一清醒,顿觉自己的行为可笑,逐渐慢了下来。
他们的马走在官道上,这是进帝京的必经之路,哪怕在这样阴冷的寒冬,行人车马也是熙来攘往的。
他这般骑马驮着一个姑娘,更加引人侧目。
他便寻了岔口,走到小路上去。
哪知,走了小半会儿,看到前面的路已经被雪覆盖了厚厚一层,深浅难辨。
他骑术不错,可是也怕万一一个不小心摔着她。
他又放慢速度,片刻之后,却始终不见她出口讨饶。
“若是不适,你开口,我便让你下来。
”他悠悠开口道。
她攒足了全身的力气,敛着哆嗦的唇,憋了半晌才执拗地吐出三个字:“你做梦。
” 他挑眉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爆款创业清蒸日华
- 一朝恶妇予乔
- 不是你的朱砂痣[穿书]阮寐
- 人间正道周梅森
- 我给女主管鱼塘中边
- 我真的不是大佬[无限]风月不知
- 千门之雄方白羽
- 星空倒影弦歌雅意
- 爱与他梦筱二
- 箫声咽鬼马星
- 炮灰请睁眼[快穿]少说废话
- 纸片人老公成真了枝景
- 尘埃之花采葑采菲
- 小可怜手握爽文剧本李温酒
- 百炼成神(不灭武神)恩赐解脱
- 热搜女王育儿手记/每天都会上热搜!宋家小四
- 万人迷炮灰被迫躺赢郎不知
- 二号首长黄晓阳
- 彩虹星球南书百城
- 喜欢你的每一秒鹿灵
- 她是贵族学院的女配江溯
- 五个霸总争着宠我/被五个总裁轮流补习的日子[穿书]枯木再生
- 炮灰的马甲又又又掉了冰糖火锅
- 全民皆萌宠暖暖的茶
- 和前男友在恋爱真人秀组cp后,我爆了煮熟的螃蟹
- 综武:我,曹老板,挖墙角达人不弃九一
- 我靠血条碾压修真界暮寒公子
- 锦衣卫:陛下,何故谋反!叁金诶
- 边军凶猛赤阳
- 暖房丫环,建社团当大佬浩浩荡荡大淘金
- 我的美艳师姐妹燕山夜话
- 穿越大唐,我靠变身闯天下美溪旺仔
- 刺世天罡夜阑听雪落
- 道术达人虫梦
- 冷艳总裁的超级狂兵北冥听涛
- 傲神传蚂蚁
- 九道真仙扫地的研究僧
- 道果战袍染血
- 庆熙风云录自由飞翔的小馒头
- 邪仙偷腥的猫
- 曲樟纪事陈加皮
- 天神之血天明
- 权倾朝野,女帝求我别反准备起飞
- 乱世红颜之凤临三国孟回千古
- 透视高手在都市九霄之上
- 重生归来之神帝薛九玄清方观世
- 最强反套路系统太上布衣
- 这个修士很危险想见江南
- 易鼎荆柯守
- 苍穹战神跳神3
- 一梦江湖之宸霜玄龙锁逍遥九宸天
- 命理探源【译注】陈缘字长青
- 幸福生活从穿越开始男人苦咖啡
- 大明中兴之我是崇祯三千纸
- 我,大楚最狂太子蜗牛王子
- 大宋第一猎户:女帝别低头!一起抓水母
- 这破系统非要我当皇帝总有那一天
- 乾元盛世系统冀北省的护法神
- 大明锦官梦苏梦沉
- 娘娘,对不住了春山果实
- 假少爷回村后,成京城第一状元郎鱼又夏
- 天赐良臣爱吃炝炒丝瓜的胡掌柜
- 权倾朝野,女帝求我别反准备起飞
- 穿越宋青书创最强大明形寄青峦
- 傲神传蚂蚁
- 九道真仙扫地的研究僧
- 重生归来之神帝薛九玄清方观世
- 曲樟纪事陈加皮
- 三国:穿越成刘晔,靠玉玺谋天下帝关下的小石头
- 最强装逼打脸系统太上布衣
- 猎国跳舞
- 九州造化逍仙08
- 死后七百年:从城隍开始签到九灯和善
- 狩妖谜独白
- 十八高手山庄幽骸狂奔
- 孤鸿破苍穹星光入枫海
- 我在北宋教数学吉川
- 我李承乾,在大唐和李二斗智斗勇日月兴明
- 诗泪洒江湖云里慕白
- 大宋:开局金军围城,宰相辞职猪皮骑士
- 平推三国,没人比我更快以空空
- 大宋:朕的专利战横扫1126心有灵犀的金毛狮王
- 系统带我闯武侠汴梁的夏大夫
- 穿越古代我的空间有军火:请卸甲百万负翁不想再负
- 从边陲小将到帝国战神小皇龙
- 秦世风云录饺子面条火锅
- 我靠血条碾压修真界暮寒公子
- 学渣的传奇人生迎凤村草
- 我的美艳师姐妹燕山夜话
- 重生六9:倒爷翻身路惊恐不安九仙君
- 穿越大唐,我靠变身闯天下美溪旺仔
- 穿越宋末,海上发家先滨
- 邪仙偷腥的猫
- 上山为匪彗星撞飞机
- 重生归来之神帝薛九玄清方观世
- 最强反套路系统太上布衣
- 苍穹战神跳神3
- 大夏第一神捕木有金箍
- 末日进化:捡垃圾就能变强千易寻
- 校园风流霸王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