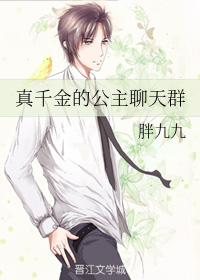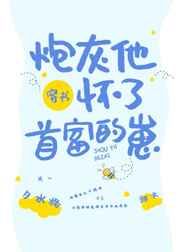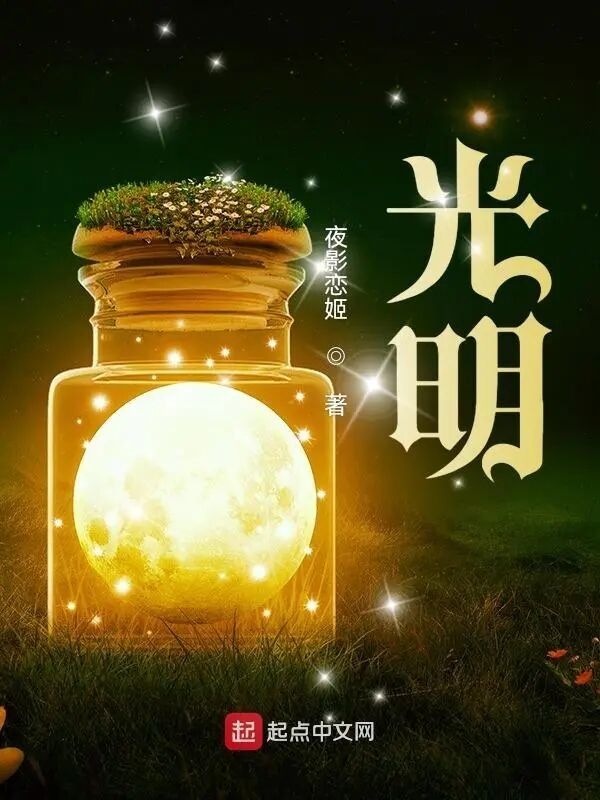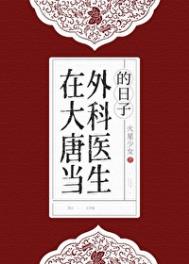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1/3)
曾经有人满怀感情地如此赞颂后湖黄册库:“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 没钱。
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
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
这可真是离奇了。
朝廷这么重视后湖黄册库,怎么会不拨款呢? 藏书的花费没有养兵那么夸张,可是库阁册架的日常修葺、管库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购买整治、官吏监生的薪俸廪米,这都是要花钱的。
更别说每十年一次的驳查,几百人在岛上起居消耗,开销更是巨大。
后湖黄册库自己不是生产部门,朝廷不给钱,日常工作怎么展开? 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务实的一面,也有一拍脑袋异想天开的时候。
在户籍制度的设计上,他深谙基层弊端,手段施展得极有节奏,不出二十年便完成了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业。
可到黄册库建立之后,一涉及钱,他却变得很天真。
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
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一处花费,居然要七八个中央和地方各个衙门来养活。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每个衙门的经费,肯定会有结余。
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
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
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
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
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朱元璋在世之时,这套“吃百家饭”的制度尚能有效运转。
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门便互相推诿起来。
当初洪武爷制定的财务政策里,有这么一个“不敷”——意思是不够花——的规定:国子监的钱不敷,就从都税司和江宁、上元二县调拨;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钱不敷,就从应天府调拨。
这么设计,是因为每个部门每年的结余款是不固定的,万一不够用,还有下家可以支应,总归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没预料到,这个却成了官僚们的一个完美借口。
官老爷别的不擅长,最擅长踢皮球。
你想要经费?对不起,本部囊中羞涩,不敷开销。
按洪武爷的规矩,您还是去别的部门问问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乐迁都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正管衙门都去了北京,偏偏后湖黄册库没有搬迁,还留在原地。
于是负责供养它的那些部门,便从户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变成了南京户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这套政府班子徒具中枢虚名,除了户部还管着南直隶钱粮之外,其他部委的权势连地方衙门还不如,对待黄册库这个拖油瓶的态度,自然更差。
连南京国子监,都忍不住跳出来,给黄册库移了一道公文:“本监惟供给监生。
”意思是,监生的费用我们承担,其他的可不管,你们自己想辙吧。
国子监还来回扯皮,一会儿直接给米,一会儿折成银钱,总之给得极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
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
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
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驳查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
而且,岛上干活的匠役民夫,由两县抽调充任,笔墨茶菜炭纸等诸项支出,由两县办税承担,连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两县官府购买三牲。
甚至监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税司派遣专人在两县路上巡检,看到赶猪进货的屠户就上前强行抽税,赶走几头——你还别小看这个税,后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这税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开销,两县咬咬牙也能熬过去。
但每十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驳查,这期间产生的费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几番,同样也得两县扛大头。
这比天塌下来还可怕。
咱们前文讲过,从宣德年开始,驳查时间越来越长,从起初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年乃至数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线上升。
每次驳查一开始,江宁和上元两县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
拿正德九年(1514年)的驳查举个例子。
当期黄册自正德八年十一月开始驳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万户黄册有问题。
在这一年里,从上元、江宁两县雇用了书手四十人,每个月工食银一两五钱;册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银九钱;纸四万八千张,笔两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员七人、监生两百人的各项茶菜炭药的日常开销……总计是一千四百两的开支。
听着是不是还好?虽然超期,但毕竟在半年之内完工了嘛。
但你得知道,这半年查完的,仅仅是整个南直隶十八府州的黄册。
它们分布在南京周边,最先运抵。
至于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的黄册,在路上还没到呢。
光一个南直隶,就要半年时间、一千四百两的驳查成本。
全国得花多少时间?用多少银子?成本妥妥超过一万两。
上元县有一百九十五个里,江宁县有一百零五里,两县合计三万三千户税基,哪里扛得下这么重的负担?更过分的是,黄册库的费用属于杂泛徭役和杂税,两县的正役正税并不因此而减免,负担更上一层楼。
这个坐落于后湖的黄册库,赫然成了盘踞在南京附近的一只吸血鬼、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应里甲,物业荡然”。
有看不过眼的当地官员警告说:“若不通融议处,照旧独累偏造,则上元、江宁二县之民,靡有孑遗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减少基层负担,可实在没想到最后却起了相反效果。
其实大明一朝的正税并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这些临时加派的杂税杂役。
没有节制,没有计划,名目众多。
上头无论有什么开支,最终一定会传递到基层,让百姓应接不暇,筋疲力尽。
黄册库之于上元、江宁两县,算是明代税赋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
两县的民力终究有限,凭你怎么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么多。
黄册库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开销,想过各种主意,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湖产上去。
比如黄册库会偷偷把湖产租给附近农民,自己收取田租。
他们还曾正式向朝廷提出过申请,征集附近渔民进入后湖打鱼,将所得鱼鲜、莲菱等物的收入,用来修理黄册库。
可打鱼才能赚多少钱?碰到开支巨大的时候,还是只能靠顶头上司——南京户部——去四处“化缘”。
比如说弘治三年吧,黄册库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万七千两百本的册壳都烂了,需要重新装订。
这个是贮藏损耗,费用没法摊派到各地,只能黄册库自己出。
管事官员算了一笔细账。
每本黄册,得用染黄厚纸两张,留出富余,一共要采购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百张,每张用银三厘;还有装订用的绵索条数,也要同等数量,每条用银一厘。
再算上人工杂费,一共是四千五百余两。
黄册库出不起这笔钱,去找南京户部要。
户部习惯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给南京吏、礼、刑、工四部,并南京国子监、应天府、都税司、上元、江宁两县,让他们“照例斟酌取用”。
可是谁都没理睬,都以本部不敷为由,踢回给户部。
就连最软的两个柿子——上元和江宁两县,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强硬态度。
两县在上一年刚遭了灾,若接了这个差事,老百姓非造反不可。
南京户部头可大了,黄册库是本管业务,万一被御史风闻,参上一本“放任黄册损毁不理”,罪名可不小。
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挖地三尺,看哪里还有银子可以挪用。
最终还真让他们找到一条路。
南京户部的下辖衙门里,有个“龙江盐仓检校批验所”,收储着大批专卖盐货,以供整个南直隶地区用度。
户部查阅了一下,发现此时仓库里还有五十四万八千六百斤余盐,不由得大喜过望。
按照规矩,这批余盐会变卖成银钱,给南京诸位官员发放俸禄,本不得挪借。
可这时候户部也顾不上这些了,皇上您不给钱养活,须怪不得我们自谋生路。
他们打了一个硬气的报告给上头,说实在没钱,不借支的话,黄册库的档案可就全完蛋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上头还能怎么办?很快皇帝批文下来,准许其变卖余盐,所得银钱挪用于纸张、绵索的购买。
但皇帝还特意叮嘱了一句:“以后续收余盐,照旧折给官员俸粮,难准再用。
”就这一次啊,下不为例。
瞧这小气劲。
要说朝廷里没高人看出黄册库财务的症结所在,我是不信的,但偏偏就是没人愿意从根本上解决。
没办法,祖宗成法,不好轻动,能糊弄就糊弄一阵吧。
再说了,大明皇帝们普遍没有财务常识,他们只认准一点,省钱的就是好事,要钱的就是无能,谁会愿意为一个冷衙门去触霉头? 这种东支西绌的财务状态,一直持续到正德年间,终于到达极限。
正德九年,黄册库又一次面临驳查之年。
他们提前做了一个估算,发现整个驳查的支出,没有两万两打不住,不禁面色大变。
再不想点什么新办法,只怕黄册库就要破产了。
穷则思变,终于有一个叫史鲁的刑科给事中站出来,给中央献了一条妙计。
这条妙计其实只有两个字:“罚款。
”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
这些罚款,都要交给南京户部转寄应天府,以后黄册库有什么开销,就从这笔钱里支取。
这条计策太好了,一来解决了黄册库的收入问题,把两县负担分摊给了全国;二来震慑了各地作弊官吏,让他们有所顾虑,不敢再篡改黄册,简直是一箭双雕。
按照史鲁的说法,从此“不扰一人,不科一夫”,让两县卸下一个巨大的负担,同赞天子圣明。
至于被罚款的那些官员,也是活该。
你要认真干活,又怎么会被罚款呢?所以这笔钱的来路堂堂正正,叫作“必取之于本分之中,求之于见成之内”。
朝廷一看,好啊,不用国库动用一分银子,就能缓解两县负担,又可解决黄册库经费,三全其美的事,自然无有不准。
这个制度听起来没什么破绽,可只要仔细一想大明官场禀性,便会知道问题多多。
黄册库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驳费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那么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再者说,虽然史鲁强调,这笔驳银罚款须由经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会想尽办法,摊派转嫁给基层百姓,这还算是清官所为。
如果是贪官的话,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银钱,肯定会层层加码,从中渔利。
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一边是盼望罚得越多越好;另外一边呢,罚得越多,他们可以借机征敛的就越多。
两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慑监督,其实深层次的利益点是一致的。
这两个本来敌对的集团,到底是如何苟合到一起,又是如何牟利的呢?咱们还是拿王叙家举例好了。
假设王叙家又败落了,沦为一亩地两头牛的自耕农。
这一年大造黄册,造册费用须由本里负担。
里长一指王叙,说你家负责出钱吧。
王叙说好,里长一拨算,说你出一两银子吧。
王叙一听,手一哆嗦:“一本册子才多厚?怎么这么贵?”里长回答:“装订册子的赵记纸铺是官家指定的,价格就这样。
你要换一家铺子或者自己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这甜宠给你要不要啊[快穿]岁砚
- 赴火耿其心
- 反派老攻为我变绿茶了雨落轻尘
- 阴阳执掌人洛冰
- 咸鱼摆烂复婚综艺[娱乐圈]塬
- 撩肾达人/万千荣光甜醋鱼
- 才上心头袖刀
- 关小姐又在写情书茴笙
- 反派修为尽失后一丛音
- 掩盖武和平
- 超神宠兽店古羲
- 你是不是输不起柒曲
- 大院二婚妻[八零]青雨梧桐
- 大宋有毒第十个名字
- 阴阳鬼术巫九
- 窈娘春未绿
- 这个沙盒游戏不靠谱太白水君
- 七十年代奇葩一家亲永岁飘零
- 抽卡无涯,日赚十亿江山沧澜
- 春宫抱空山
- 醒日是归时含胭
- 反派他早亡的妻子重生了冬十四月
- 穿书后我被美惨强反派掰弯了衾寒月暖
- 蒸汽时代血族日常thaty
- 我就是酒厂的薪水小偷哒断丹浮海
- 该猫绒绒统治世界了花秋月
- 普通人,但怪物之母西风醉
- 从找死开始挑衅柯学世界诗已至此
- 我靠古诗词成为言灵者觉玉
- 败犬圣女,把头发盘起来!黒颜瞳君
- 魔界继承人竟是我自己河里地瓜
- 史莱姆售卖店[系统]一只灰猫
- 踏梦山海山海客
- 以武冲霄夏水长天
- 该我上位了小树撞鹿
- 和影帝结婚的第七年柚子猫
- 今天丘比特降临一只狌狌
- 无限副本唯一指定清道夫Philoso
- 被强取豪夺多年后宁夙
- 乙游女主自我意识觉醒中做点黑泥尝尝
- 我才不想高攀你叶斐然
- 极道禁书巅峰荣耀
- 反派不洗白[快穿]即墨遥
- 镇狱武神,从棺中诈尸开始冷汤
- 九玄邪尊疯狂的大米
- 模范家庭道长单飞
- 如何逼疯高冷权臣第一只喵
- 和大佬穿回七零木妖娆
- 穿回现代来修仙暮时夏
- 万世轮回:我可以无限重启人生!小时家的晚饭
- 征服九大女帝后,我成就无上仙帝!飞鱼牛牛
- 该猫绒绒统治世界了花秋月
- 六道轮回塔不想早起
- 小兽浮生01
- 我在大夏窃神权码字手痛
- 普通人,但怪物之母西风醉
- 大周最强探花郎大雷封
- 魔界继承人竟是我自己河里地瓜
- 让你当宗主,你只收主角?妮娜芙
- 孤寡多年喜提一子不问参商
- 我妻筝筝观山雪
- 莽荒纪之纪炎看l星空
- 阴鸷暴君他人很好呀!女王不在家
- 【西幻】罌粟之戀赏道
- 一剑绝尘弘扬赵
- 漫画路人的我成了白月光脏脏猫Zz
- 古剑之洪荒三皇一念风
- 模范家庭道长单飞
- 给重生的小姐当丫鬟南方早茶
- 如何逼疯高冷权臣第一只喵
- 我能无限模拟死亡下个天明
- 吞噬剑帝薄荷冰凉
- 绝对交易隐语者
- 始于深渊过十不更
- [综英美]系统是黑化超英然燃繎
- 团宠国王和他的四位勇者宫槐知玉
- 我在大夏窃神权码字手痛
- 大周最强探花郎大雷封
- 史莱姆售卖店[系统]一只灰猫
- 九零沪上发家日常[弹幕]流烟萝
- 金瓯重圆一只小蜗牛
- 我才不想高攀你叶斐然
- 古剑之洪荒三皇一念风
- 玻璃灯扁平竹
- 镇狱武神,从棺中诈尸开始冷汤
- 巅峰王者之美女环绕书香ZK
- 如何逼疯高冷权臣第一只喵
- 穿回现代来修仙暮时夏
- 我能无限模拟死亡下个天明
- 北宋县令庶女苏西坡喵
- 混沌鼎:女帝逼我做道侣潇潇凉公子
- 小巷日常[八零]秋凌
- 天上白玉京莫问江湖
- 从斩妖除魔开始长生不死陆月十九
- 她的丛林法则可莉谢
- 大周鬼差只曾记得你
- 我在破烂堆里捡宝物白菜豆腐汤
- 剑出洪荒天地有缺
- 无肉不欢橘花散里
- 女装被死对头发现后长野蔓蔓